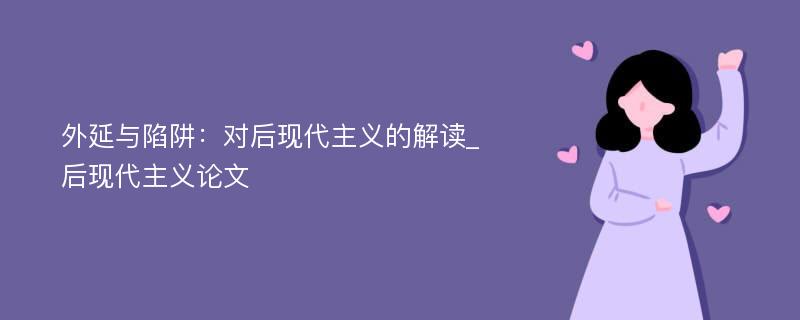
伸张与陷阱——对后现代主义的几点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几点论文,陷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1-0012-06
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为后现代主义的伸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 们站在现代主义的对立面,痛心疾首地审视和解剖现代主义扩张带来的人与自然的疏离 ,以及由此展开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后现代主义决意要摧毁现代主义的思想堡垒,他们 用反绝对、反权威、反本质、反本体、反理想、反崇高、反道德、反秩序、反规律、反 决定论、反真理、反意义的后现代主义语境替代现代主义的话语,试图在最终被夷平的 现代主义废墟上矗立起宏伟的后现代主义大厦。后现代主义的伸张无疑能对医治现代主 义痼疾、解决全球性问题起到一定作用,但这种带着极端性和片面性的张扬又极有可能 让人们遭遇陷阱,使人们滑向迷茫或危险。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反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 或文化范式影响巨大,但它的前景和命运却并不容乐观。由于自身的缺陷和其他诸多因 素,它必然会遭致内外部势力的夹击而难有所作为。
一 后现代主义究竟伸张些什么
1981年,法国《世界报》以不无震惊的语调向世人宣告,有一个幽灵——后现代主义 的幽灵在欧洲出没作崇。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如 今,就是在我国理论界,后现代主义也不断争得了地盘,屡屡向经济社会文化生活进行 渗透。因此,需要对之有个比较透彻的把握。但由于它并非是一个具有统一理论基础的 思想流派,而是众多不同、经常处于冲突之中的文化倾向的积淀物,具有“极其丰富、 复杂的思想和理论内涵”[1],故我们只是对其尽可能做到轮廓式的大致梳理,明确后 现代主义究竟要伸张些什么东西。
(1)拒斥“中心”,全面解构现代主体性
后现代主义最不能容忍的是,人的主体力量的张场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已经达到了登峰 造极的地步,什么现代大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城市化,或所谓后工业时代的消费社会 、传媒社会、资讯社会、电子社会、高科技社会等,仿佛都一股脑儿渲染和印证着现代 主义创造的神话:现代主体性开创了一个繁荣、富强、文明、进步的时代。而在后现代 主义看来,现代主体性对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功不可没,但现代主体性的无度狂奔却前所 未有地加速刺激了人类扩张性、侵略性、宰制性的主体性,膨胀了人类中心主义,人对 自然的“英雄本性”、个人对他人的“自恋人格”彰显无遗,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核 威胁、两极分化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正逐渐诱导着人类走向自毁家园之路。即如美国学者 乔·霍里德在《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观》一文中所言:“现代理性主义力图通过创造出一 种完全人工性的环境使人们摆脱自然。自然被视为可塑的,这种观点在今天达到登峰造 极的地步,以致对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带来了毁灭性的威胁。”[2]因此,后现代主 义多少有些愤疾地拿起解构的武器,旗帜鲜明地向现代主体性和主客二分(主体与客体 、人与自然的对立)思维模式开战。
首先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抨击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后现代主 义认为,人把自身视为世界的主宰和征服自然的英雄,而把自然只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 手段,这无疑破坏了人与世界、自然的和谐秩序,堵塞了人类通向未来的通路。所以, 颠覆现代主体性和人类中心主义,深切关怀人类及其生存于其中的地球的命运,成为一 切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最高旨趣和神圣使命。罗蒂、霍伊、温克勒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 人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所谓“人类就共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 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应该“予以 摒弃”[3]。因此,他们非常强调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本着这种思想,后现代哲学 先驱海德格尔提出了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人只是自然的“托管人”、“守护者”,而不 是自然的主人或主宰者。美国后现代主义者弗里德里克·弗雷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可 见,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活动”旨在赋予人与自然关系以浓厚的“生态意识”,以消除 人对自然的统治欲和占有欲,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其次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上抨击“自我中心论”,主张重建人与人的关系。后现代主义 看到,“几乎所有现代性的解释者都强调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2],人被视为皮肤包 裹着的独立的自我,“个人主义已成为社会中各种问题的根源”[4]。他们立足于人类 整体利益而鄙弃个人主义,主张消除人我对立。在他们的理解中,人是一种关系的存在 ,每个人都处在与他们有关系的人群之中,即“关系中的自我”,认为个人只有在人们 的相互关系中才可被理解。大卫·格里芬甚至把对他人作贡献当作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 ,提倡人的奉献精神[2]。这样,强调人与人的内在本质关系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 要特征,与现代主义把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定格为外在的、偶然的、派生的关系针锋相对 :其一,主张用交往主体形式替代中心主体形式,即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以此 达到平等交往、伙伴合作的关系,如法国学者梅洛·庞蒂(Merleau Ponty)在胡塞尔、 海德格尔“主体间性”理论基础上就将主体交往置于语言交流之中,使人我相互开放, 从而打破和消除主体自我与主体他人之间的界限和距离。其二,要求超越性别,建立男 女之间相互尊重、合作、负责的人际关系,实现“男性精神”与女权主义的通融。凯瑟 琳·凯勒、艾斯勒等在各自的论释中都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其三,坚决反对狭隘的 民族主义、制造灾难的军国主义以及各类暴力事件和核武器等,以期建立新型的民族与 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2)抨击理性主义,推崇非理性
理性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核心导向和坚定信条。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正是现代主义的理 性主义的泛滥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和人类灾难,批判、否定、解构理性主义而执 著于推崇非理性,就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努力方向。实际上,早自尼采时代开始,西方不 少存在主义哲学家或存在主义追随者就对旧有理性主义传统进行了无情嘲讽、否定和批 判。但后现代主义意识到,这种嘲讽、否定和批判是乏力和很不彻底的,因为用意志、 生命、无意识等非理性存在取代理性当作基础,这不但仍然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反对的基 础主义,而且并未摆脱理性的制约和纠缠,在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变了形的理性而已(如 海德格尔、罗蒂等人即明确指责尼采不能完全摆脱柏拉图主义,称尼采为后形而上学思 想家),故难以阻止理性主义的泛滥,难以消除人的主体自我优越感。面对如此尴尬的 局面,后现代主义认为彻底的否定、批判就是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实在和本质规定, 并指出现代主义追求普遍性的做法是迂腐的表现,因为以理性或逻辑为基础制定出来的 条理和方法论不过是某种类型的游戏规则而已,如果将其当作普遍规范,必然会限制人 的个性的发挥,束缚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具体而言,后现代主义对非理性的主张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其一,从非理性角度解释真理。有后现代哲学先知之称的维柯释曰,真理不是某种先 天存在的严格形式,而是人造物;帕斯卡尔声称真理为真,并非真理本身,而是我们的 “信念”问题。他们实际上执意绕开了理性门径,以非理性的旨趣解读了真理,批判了 理性中心主义。
其二,让理性在理性操作中自我否定,尽力使理性显出游戏性。以德里达为代表,提 出“只进行操作,不做任何论断”的策略,并指出只有所谓“延异”在策略上最适合思 考,因为“延异”只表现为否定。最彻底的做法,甚至不把“延异”当作一个名称。他 们有意识地让过程处于不断解构和流动的游戏状态之中,德里达们带着欢快的舞步来赞 赏、肯定游戏,着意寻求使自由嬉戏永不停止的东西,以便走出失落的思想家园。
其三,对现代理论或以理论为中心抱鄙弃的态度。肯定性的后现代主义摒弃以理论为 中心,摒弃宏大叙事,习惯于用“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和局部的、小型的叙事来取而代 之;怀疑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理论假定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实在”并不存在,理论 本身是隐匿的、失真的和模棱两可的,故他们没有兴趣构建新理论,甚至拒绝使用“理 论”这个词。之所以持这种态度,因为理论、理性与他们秉持的非理性直接相抵触。
其四,怀疑有意识的有条理的连贯的主体,主张重建非理性的主体。理查德·阿什利 、阿兰·图雷纳、曼弗莱德·弗兰克、朱莉娅·克里,斯泰娃等都是这种观点的提出者 或支持者[5]。
总体而言,后现代主义对理性主义深恶痛绝,彻底否认理性的作用,强调非理性的重 要性。但需指出的是,现代主义所倡导的非理性观念与我们所知的人本主义非理性观念 存在如下差异:迷恋于追求一种非理性的实体是尼采式的做法;后现代主义关心的是否 定任何观念、范畴、结构或理论的绝对性,使“信念”、“延异”、“游戏”等占据凸 显的位置。
(3)反对“同一性”,竭力表达不确定性
后现代主义通过推崇自由游戏、差异、多元论等宣扬不确定性,反对同一性或普遍性 。在其视野中,反复出现的事物、一般性事物不被注重,注重的是不可重复的事物、独 一无二的事物。这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在主体问题上,以“突现的主体”、“过程 的主体”、“创造性的主体”、“散乱的主体”冲击和取代普遍性的现代主体,即充分 表达一种不确定性的主体。其二,强调语言的不确定性,主张语言空无内容,语言被定 义为没有指标的、没有外延的、不受物质限制的,人的语言只不过是一种活动,这种语 言活动的实质实际是在玩“语言游戏”。如后期维特根斯坦直接用“家庭相似”批判语 言领域里对“普遍性的渴望”[6]。德里达在《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 一文中主张,应该使限制自由嬉戏的结构“断裂”、“瓦解”[7]。其三,用差异取代 普遍性而表明事物的不确定性,如勒内·吉拉德就将文化差异视为维系社会稳定和促进 和平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社会伦理观的形式阐释、论证了差异的重要性[8]。其四, 从方法论或思考方式上提出“多元论”,用以张扬不确定性而反对普遍性。他们认为所 谓方法根本就不存在,蔑视所谓程序规则。他们提出的无镜哲学、教化哲学,主张的文 化开放(打破文化的稳定性),倡导的范式平等,呼吁的“为文化特性和个人特性留下地 盘”等,都是对普遍性的批判和对不确定的推崇、颂扬。
二 后现代主义布设了哪些陷阱
实事求是地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双刃剑。后现代主义力图克服、解决现代 主义极度张扬所带来的问题、灾难和痛苦,对矫正现代主义的思维模式和操作方法能够 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后现代主义固有的特点、解构的极端性又易于导致新的问题, 在悄无声息中便设下了一个个圈套或一道道陷阱。对此,必须予以警惕。
陷阱之一:滑向过渡膨胀的相对主义。
我们承认,后现代主义以不确定性批判、否认“同一性”或普遍性,这对于反对绝对 主义、冲破传统或僵化程式具有一定意义。但是,它只承认不确定性,无限夸大不确定 性的作用,把不确定性视为事物或现象的本质的思想路径,极有可能使人滑向极端相对 主义。如果不注意到这点,不加以认真批判和驳斥,而任其自由发展,任其无限泛滥, 势必会给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诸方面的推进和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按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相对主义观点,一切都不具备确定性,那么,一切都没有普遍性, 一切知识、真理都没有权威性,显然,这是非常荒谬的。
陷阱之二:盲目放弃人的主体性。
后现代主义看到了现代主义泛滥造成的危害,从根本上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 我中心论”,对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和操作范式进行抨击、解构,这无疑有利于我们慎重 、合理地思考人我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从而有可能使我们通向健康的可持 续发展的道路。然而,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在此问题上的极端化主张——完全否认主体客 体的区分、彻底否认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则有可能使人们盲目放弃人对自然、人对他人 可能拥有的合适的权利。即是说,这不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尤其不利于人对自然 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举例来说,王正平先生在1995年《哲学研究》杂志第6期撰文 指出:“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对发展中国家推行‘双重标准’,拼命 夸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以此对发展中国家的 工业化进程进行种种阻挠。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企图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他们却不 断提高自己的经济、技术实力和生活水平。”由此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一味否认人对 自然的主体性的特点,这完全有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国家或地区所利用,如西方 环境利己主义者就打着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招牌,通过大肆渲染、强化后现代主义生态 观来淡化、消解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
陷阱之三:将非理性因素神圣化。
后现代主义具有非常强烈的非理性观念,并且赋予非理性因素以极高的地位,其绝对 形式就是用非理性的东西取代一切理性、理论。这种旨趣和追求的极端化,其所设定的 陷阱就是使人盲目将非理性因素一概神圣化,尤其易使一些青年人以非理性的态度对待 生活,甚至偏执、迷信于非理性的刺激与威力,在非理性的圈套中心甘情愿地游戏人生 。因此,我们不宜过份渲染非理性主义。对非理性因素的是是非非要有客观、冷静的分 析,尤其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理性、理论作用及其与非理性的关系的分析认识中获 得最大阵地。
陷阱之四:抛舍理想和责任。
美国学者哈维明确指出:“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表达的是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尽管 这样一种追求由于遭到不断的幻灭而往往引发受害妄想,但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表现 却是抛开了这个追求。”[9]的确,比起现代主义崇尚理想、深信美好未来和社会的不 断进步来说,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简直就是耻于提出和谈论理想,“更毋须说采取任何 方式去创造某个完全不同的未来”[9]。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任何理想都是虚无缥渺 的乌托邦,任何关于未来的美好信念都是诱人误入歧途的海市蜃楼。与此相联系,后现 代主义极为乐意于消解责任,认为责任是现代主义者一厢情愿地戴在自己身上的枷锁, 后现代人完全没有必要去理会责任,更没有必要让责任的重担压垮自己的双肩。后现代 主义漠视理想和责任的态度,极易对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我们的理想建树和责任感培植构 成威胁,诱使人们沦落为没有理想、不讲责任、目光短浅的庸夫。而事实上,我们这个 时代尤其需要崇尚理想,担负责任和义务。
陷阱之五:滋生病态人文。
后现代主义的登场,首先是以批判、颠覆人类中心主义、关心人类及其生活于其中的 地球的命运的面目出现的,因此,后现代主义不言而喻具有很浓厚的人文意味,并且, 这也是重建当代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然而,由于后现代主义以极端形式反叛现代主义 ,故它虽然为当代人文精神打开了一个通道,沿此有可能获得欢欣鼓舞的人文建树,但 也不排除滋生病态人文的可能。其一,后现代主义割弃人文精神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完 全抛开意识形态谈论人文精神,这可能使人文建设落入非意识形态的圈套;其二,否定 性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精神的追求上只破不立,摧毁了旧有的精神理想却没有建构、形成 新的精神规范,这极有可能让人走向虚无,至多做做人文游戏而已;其三,后现代主义 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偏重于纯粹的精神活动,蔑视现代主义偏重物质的倾向,这可能导致 人们不能正确认识、处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使人文建设得不到物质力量的支持;其四 ,后现代主义主张彻底消解一体化的精神世界,倡导一个多元的精神世界,反对一切形 式的精神压迫,追求一种精神无度的、狂放性的精神解放和个性自由,这可能会诱导人 承认和接纳绝对自由、放纵享乐,将其视为生命活动的本真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精华。有 迹象表明,某些所谓的“美女作家”们就已经滑进了这种陷阱,并在陷阱中不断招摇、 吸引、壮大着“新新人类”的队伍。
陷阱之六:仇视技术和泯灭科学精神。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进行“批判”的重点之一是所谓的“技术异化”,认为科学技 术的应用使人成了机器的零件和物的奴隶,科学技术对人的奴役广泛侵入到人的日常生 活世界,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加剧了对人的统治,科学技术的无限制开发利用已威胁人 类生存。由此,可能诱使人们仇视科学技术,将科学精神混同为极端的科学主义,从而 在抛弃极端科学主义的同时将科学精神一起抛掉。
此外,后现代主义也有可能在全球化方面设置陷阱,成为全球化的一种反向力量。
三 后现代主义的命运
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话语的兴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家对发达或晚期资 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状况的不同体认。詹姆逊、德里达、利奥塔、格里芬等人通过对现 代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解构,展现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的基本脉络。拒斥“中心 ”,颠覆现代主体性;抨击理性主义,推崇非理性;反对“同一性”,悦纳不确定性: 这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最基本的特征。由于后现代主义不遗余力地抨击所谓现代主义带来 的诸多问题,极端化地撕碎现代主义的灵魂,故而在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是中 国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尽管后现代主义似乎声势浩大、底气十足地横冲直撞,但无论是在域外还是在中国, 它的前景和命运却并不容乐观。
(1)后现代主义难成主流文化。因为它基本上对资本主义现状采取怀疑、批判、否定的 态度,而其话语传达给的对象又主要是并不处于权力中心的知识分子阶层,加上垄断资 本最多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工具来利用,并不可能把它真正当作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 、理想来接受,更不可能按其所宣扬的那一套去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它就难以获 得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形式。
(2)后现代主义已出现来自于两个维度的超越。一是来自基督教价值体系的超越。在后 现代文化氛围里,一些基督教学者试图调解神学与后现代的对立,提出了一些后现代神 学观点,但并不吸纳后现代主义的游戏态度,而是积极推进基督教世俗化过程中的价值 体系的建立。二是来自后现代理论家内部的超越,如后现代理论家哈桑在发出“后现代 终结”的呼声后便停止了有关后现代的著述出版。即使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也没有提出多 少建设性意见。这昭示着后现代主义最终会被新的文化形态所超越、所取代。
(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与自然关系、人我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均有科学而精辟的 论述,后现代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虽然与之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通性,但在认识、解 决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都是“不可超越的视界 ”,后现代主义无法与之相比。
当然,不管后现代主义的前途有多么黯淡,命运有多糟糕,我们都应当清楚:后现代 主义在长时期内仍将处在天使与魔鬼的交汇地带,既可把你引入美境,也可把你引入陷 阱。对后现代主义认真审视、科学把握、合理扬弃,这无疑更有利于我们所从事的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
收稿日期:2001-0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