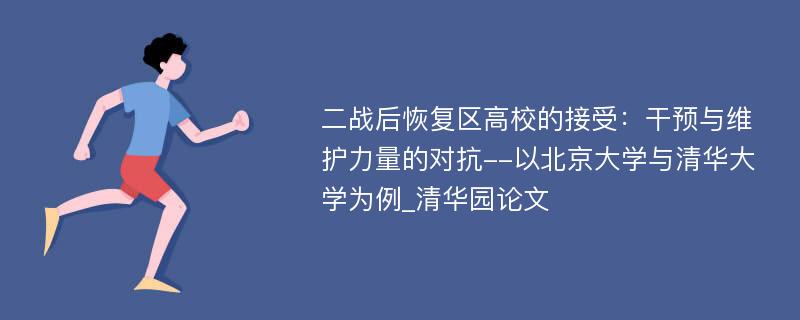
战后收复区高校接收:干预与维护力量的对抗——以北大、清华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华论文,为例论文,战后论文,北大论文,力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全面展开复员工作,收复区高校的接收即为其中一重要环节。与其他领域的复员所不同的是,高校接收中虽同样无法免除政治势力的钳制和军方势力的强势介入,但教育界这支洁身自好力量对这片净土的倾力呵护,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部力量的破坏性,故使此进程呈现出与其他领域不同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以往对战后接收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物资、交通等较为敏感的领域,长期未将高校纳入考察视野。推其原因概括有二:一是此方面的研究资料稀少且分散;二是与上述研究问题相比,教育产业并非利益冲突的焦点,即高校接收中的“问题化”特征并不显著,不尽符合革命叙事策略的选材之需。在史学研究逐步摆脱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整体论框架和“宏大叙事”范式之后,从客观中立的立场出发,实事求是地揭示战后高校接收过程中两种力量的对抗及其对高等教育进程的影响,不无学术和应用价值。
一、接收筹划:冲突隐患的埋设
抗战胜利之前,对战后高校接收的规划就已经提上了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1944年5月,根据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教育部着手拟定《教育复员计划工作计划》和《教育复员计划事别计划》,其中关于教育机构的接收作出如下原则性规定:“接收并改组收复区(通过战争手段收复的“九一八”事变后的日军占领区)、光复区(根据国际法收回的“九一八”事变前的日军占领区,即台湾等地区)敌伪之教育机关及教育事业,恢复原设置之教育机关,并酌情恢复原有教育事业。”① 但在随后一年多时间内,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教育机构接收的具体筹划和准备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就连教育部长朱家骅一再催促设置教育复员准备委员会一事,也迟迟未见下文。从客观上来说,时值国民政府疲于应付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教育部为战区高校再次内迁而奔命,相应淡化了复员准备工作;主观上,由于战局瞬息万变,大后方并没有预见到胜利降临如此之快。正如战后负责经济接收工作的邵毓麟所言:“对日胜利,随着原子弹的闪光,如疾电般的‘袭击’我们,连迎接胜利的准备时间都没有,因此对收复区的接收工作和政务工作,政府在事前没有建立制度,研究计划,更谈不上人员的训练”②。当战争骤然结束时,教育部只能仓促就事,一面紧急派员接收,一面临时制订规章。
1945年8月17日,朱家骅发表紧急广播讲话,昭示沦陷区各级学校“必须负责保存校舍、校产、图书、仪器等,不得有丝毫损坏”,维持秩序,听候接收③。同一天,教育部紧急颁布《战区各省市教育复员紧急办理事项》,责令后方各省市教育厅局即刻派员接收敌伪教育机关,并着手收复区复员工作。随后为具体指导收复区学校的接收工作,教育部将全国划为六大区,分设“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制订了《教育复员及接收敌伪教育文化机关等紧急处理办法要项》,要求接收各类学校时,“必须与当地主管军事机关商洽后会同前往接收”,并在可能范围内与原校人员或后方派遣人员联合接收。④ 这种“多头并举,联合接收”的实施原则,其出发点是为便于各方面关系的协调,并有利于互相制衡和监督,防止教育资产的流失;但由于既未明确划分参与接收各方的主辅关系,也没有考虑到再分配格局中微妙与复杂的利益纠葛,因而埋下了接收工作中职责冲突、多方牵制的隐患。
1945年9月,高校接收工作开始进入实施阶段。教育部继派出接收督导之后,又根据行政院的部署突击任命了一批特派员,并成立六大区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与各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合署办公。与此同时,战时迁移后方的高校在报请教育部批准后,也纷纷选派自己的代表分赴收复区。官方与高校同时派员接收,工作上虽有一定的互补性,但极易造成一校两接的权责冲突。以北大接收为例,教育部既批准西南联大派郑天挺负责,而此前又委派了陈雪屏作为教育部代表到该校接管,且事先未进行任何协调。后来谈及此事时,郑天挺不无伤感地说:“学校派我北上筹备复员,教育部也组织了一个平津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应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由沈兼士领导”,“教育部只要我们到重庆见一下面,并不管如何到北方展开工作。”⑤
二、北大与清华:不同的境遇
接收政策的含糊性,导致高校与官方、军方之间矛盾重重,并致使北大和清华两校的接收工作一开始便陷入僵局。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抢先接管北大,并根据新的教育甄审政策,将其改为收容与甄审沦陷区学生的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郑天挺被搁置一边。而清华园则因战时被日军用作军事医院,在日方伤兵尚未撤退之际中国军方便迅速介入,根本不容校方代表插手。面对同样问题,北大凭借自身优势迅速扭转僵局并乘机扩大战果,收获颇丰;而清华几乎无计可施,长久陷入与军方纠缠不清的漩涡而不能自拔。
郑天挺的尴尬境遇,随着北大代校长傅斯年的到来被迅速打破。1945年11月下旬傅斯年刚抵北平,即借北平临大补习班聘请伪北大教授之事当面训斥陈雪屏⑥;随后又召开记者招待会,强调“北大将来复校时,决不延聘任何伪北大之教职员”⑦。傅斯年之所以敢与教育部代表叫板,主要据其在教育界的特殊地位和政治优势。战后因胡适侨居美国,北大校长一职出缺,蒋介石意欲由傅斯年出任,但其百般推却,终因照顾各方情面才勉强同意“代理”。在不贪权的前提下,其行事自然少有顾忌。另外,傅与朱家骅是教育圈内人所共知的莫逆之交,又无形中提高了其权威地位和话语权。后来傅斯年曾专门为自己被戏称为“太上教育部长”之事出面辩解:“事实是骝先(即朱家骅)好与我商量,而十之七八不听,然而外人不知也。”⑧ 这当然是傅斯年的自谦之辞,其实只要他发话,朱家骅哪敢不听!1946年2月11日,傅就北大接收权问题专门致电教育部讨还公道,朱迅速批复:“伪北大一切校产自应归该校接收。除分电沈(兼士)特派员外,特电知照。”⑨ 随后,朱家骅又亲自出面与东北行营交涉,将其接收的伪新民学院旧址移交给北大。不仅如此,傅斯年还四处动用北大校友和自己的各种私交,打通敌伪产业处理局、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官总部等要害部门的关系,取得惊人成效。不仅迫使联合国救济总署限期让出其占用的北大校舍,还额外接管了大批敌伪资产——伪新民学院校址、改建后的相公府、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北平伪国学书院和古学院的全套家具图书。
相比而言,清华大学却没有如此幸运。在为期近一年的接收工作中,因遇到军方这一“有理说不清”的特殊对手,不仅“损兵折将”,还迟迟陷入矛盾与冲突的漩涡而不得脱身。中国军方第十一战区接收委员会卫生组抢先接管清华园内日军医院后,随即封存了该院所有物资。尽管这些物资并非战利品,其中大部分医疗器材属于战前清华大学医学院的资产,而普通器物多系该校公私财物,且教育部也曾明文规定普通物品应归还校方,但军方接收代表却借口其军事性质,不仅严禁校方插手,甚至拒绝向对方提供急需之物。为解决复员交通问题,清华代表曾向第十一战区司令部提出从封存物资中拨出4辆小汽车和10辆卡车“暂借”与校方,未获批准。旋直接与卫生组交涉,要求取出部分被服供校方接收人员过冬,仍未获准。无奈之下,清华方面只好越级上奏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要求按教育部规定,除医疗器具、药品之外的普通物品“由本校负责接管。”⑩ 不料此举非但未达目的,反而惹来更大的麻烦。军政部迅速将清华园日军医院的接收权转交给后勤司令部第五补给区。
这支军方力量来势更猛,迅即封存了校内所有仓库,并声称一切物资均要听其发落,言外之意,不仅前卫生组接收的日军医院及其所有财产要由其接管,即便校方已接手的普通物品也在其接收之列,甚至“日人所修炕之木料亦认为应为彼接收”(11)。不仅如此,这批接收大员还在校园内四处搜罗,就连正生长的树木也不放过,伐作棺材。在忍无可忍之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直接致电何应钦,控诉这批军方代表的强盗行径,并要求按教育部的指令由校方接管校内一切普通物资。何倒十分爽快,迅速答复同意清华的请求。当清华代表满怀信心地前往第五补给区交涉时,却被对方以未曾收到何总长指令为由拒之门外。其后在军政部部长陈辞修批转清华的书面请求后,接收大员却以直接受命后勤司令部为由相推诿。直到1946年7月中旬,在清华大学被迫割舍全部医疗器械、药品和大部分车辆、被服的条件下,这场争执近一年的财产纠纷案才告解决。
如果说军方代表的上述行径还只是经济人逐利本性的外显化或者说是“胜利者”占有心态表露的话,那么其故意拖延校舍交接时日的做法,则具有明显的蓄意破坏性。为巩固和扩大接收战果,军方代表人为设置障碍,千方百计阻挠清华园内日军医院的交接,致使该校复员工作一再受阻。在第十一战区卫生组最初接管该医院时,原有日军伤兵已经被陆续遣返,到1945年底便所剩无几。此时后方学校北迁之日迫近,清华方面急欲收回校园校舍以便着手修缮布置。校方越是着急,对方越是不温不火。当日方以伤兵未愈为由提出续借请求时,军政部竟爽快应允。这种“内外有别”的强烈反差,固然与国民政府“以德报怨”的对日外交政策有关,但主要是军方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驱动。对此,第五补给区司令部的复函说得非常直白:“一俟该批伤患治愈,遣送回国,并该院现有器材运清后,即行交还。”(12)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清华方面与军方交涉收回校园时,第五补给区却动议将该医院改编为后勤部第三十八兵站医院。校方震怒,立即致电第五补给区司令部,措辞极为强烈,要求军方尽快迁出,以免“滋生误会”;同时电告李宗仁,痛陈及时回收校舍之必要与可能:“该批伤患兵士现余不过90余人,治病已久,遣送回国自属轻而易举,似无另行组织兵站医院之必要。而敝校自敌人盘踞八年有余,破坏特甚,修缮维艰。又复员期迫,刻不容缓。”(13) 李宗仁尚能体念校方苦衷,要求第十一战区司令部直接处理此事并“再勿节外生枝”。李虽身为国民政府驻北方地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但其批示却未显示出应有的权威。第十一战区司令部仍敷衍塞责,令清华大学“径向第五补给区洽办”(14)。
到1946年4月中旬,日方“续借”期满,日军伤兵也已全部回国。此时,驻扎清华园的军方人员虽再无继续滞留理由,但仍无迁让之意。在迫不得已之时,清华一面越级上告到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北平办公处和军政部,要求其出面主持公道;一面将军方代表上述行径公布于众,并向全社会呼吁“甚盼其能本维护教育之旨即行迁让,不再延宕,否则不惟摧残教育,责有攸归,而军令不行,纪律何存?”(15) 在多方压力下,第五补给区又拖延了3个月之后才勉强离开。但此时,复员师生已大批抵达北平,离开学之日已不足2月,不仅校园整修工作被严重贻误,而且军方留下的创伤更是短期内难以抚平。
三、收复区高校:被玷污与受呵护的圣土
北大和清华这两所长期并驾齐名且形影相随的高校,在战后复员中境遇之差异如此之大,这确实值得深思。应当说北大的幸运除了那位能“通天”的傅斯年校长的个人魅力以及该校校友在政界、军界的重大影响力之外,主要因其校园在沦陷时期未沾染军事色彩;而后者的不幸恰在于沦陷时的清华园被充为日军医院。战后滞留清华园者尽管只是日本伤兵,但这足成为国民政府军方势力介入的借口;而且在与这些“枪杆子”打交道的过程中,校方不可避免地要遭遇“有理说不清”的尴尬。相关的研究成果表明,战后收复区接收中普遍化的“劫收”问题,主要是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之结果,因此清华的问题又较有代表性,或者说此为战后高校接收中的一幅经典缩影。
“接收”演变为“劫收”,这几乎已成定论。蒋介石曾怒斥各级接收大员“有利相争,遇事相诿,只图接收财产物资,未能配合需要”,结果“贻中外人士以‘接收即停顿’之议”,并认为这是战后国民政府的“最大耻辱”(16)。如果说这种行径发生在经济、物资、交通等敏感领域尚不足为奇的话,那么一旦染指到“油水”并不丰厚且一向被称为圣土的高校,还是不免令人匪夷所思。
针对军方代表的蛮横举止,1946年初清华代表陈岱孙就曾作出这样的预测:“一切接收事均归其管,其现在作风,就是迁入校内,直接向日人接收物资”,“以后他们走时,自是一切运去也。”(17) 随后事态的发展果如其所料。清华大学保管会主要成员何汝楫在其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军方接收人员四处搜罗一切值钱物品,“凡日(军)所建筑者如木炕、木床、白木桌椅等物,及经日(军)毁坏而又重新装制者,如室内电灯设备等,均由彼方接收,必予以拆除。”(18) 对于这些穷尽所能搜罗的物资,军方接收人员最初还半遮半掩,假借日本伤兵之手偷偷外运,而在多次受阻后便明目张胆地派军队武装押运出校,后来索性直接把商人领到校园内现场估价交易。到1946年7月中旬军方代表在撤离清华园前夕,其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以至于给同期造访的《大公报》记者留下这样的记忆:7月12日“兵员已离,但搜取工作并未停止,不仅将残存煤末成车外运,并将电灯电线逐一拆卸,使学府半成黑暗。无法移走之卫生设备,则多遭破坏。对伤兵所用之草垫,弃草而收布,以至到处稻草飞扬,有类马厩。”(19)
军方依其强势地位和先决优势介入战后接收并乘机大肆洗掠,是造成“接收即停顿”的主要原因,此亦为清华复校中的根本症结;而该问题之普遍性,几乎涉及沦陷时期沾染军事色彩的所有校园。中山大学因建筑堂皇、水电设施齐全,战时被日军用作总司令部;战后经中国军队接收“而由中山大学收回时,连桌椅板凳都没有了,水电机器被运到香港卖了2000万元”(20)。此外,军方抢占校园、校舍后迟迟不归还的现象亦非常普遍,特别是战时被日军占用之地,军方往往以其军事性质抢先接收并拒绝交出,因而屡屡“发生房产纠葛问题”,“直接影响教育复员”。(21)
虽然蒋介石曾反复强调“复员时期,教育第一”,但这种口号几乎不可能落到实处。显然,与强大的军事势力相比,尤其在军事动员时期,校方的力量根本不足以与其相提并论;即便面对政治势力,后者也明显处于劣势。鉴于战时清华校舍大部被毁并为应付复员急需,1945年底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将东长安街日本小学校址拨付该校,作为复员师生抵平后落脚之用。孰料,该校舍刚清点完毕即被第五补给区抢占,经数度交涉收回后不到3日又被三青团北平分部强占,此后多次交涉未果(22)。屋漏偏逢连阴雨。1946年3月底教育部作为补偿将伪北平土木工程学校交给清华,不意又被蒋经国看中,其直接与教育部交涉要求“暂借”于中央干部学校华北训练班。教育部无奈,只好照办,“准暂借用6个月”(23)。
军方尤其是政治势力强行介入高校接收并将“劫收”悲剧搬到学府殿堂,是一种典型的体制性腐化的标志;而其后果不仅仅是给公众留下“接收无一处无弊端”之口实,以及战后教育复员工作严重受阻乃至整个教育现代化进程的迟延,还包括或者说更致命的是由此所导致的政府权威式微及其公信力的沦丧。前述清华接收中的一波三折,不仅因校园被军方长期霸占而失去整修时机,给荣归故里的复员师生留下满目疮痍,且因“那种任性而无休止的破坏”,清华园内“那些能拿得走的,拆得掉的,敲得坏的东西”“全都拿走了,拆掉了,敲坏了”(24),使那些饱经战乱之苦的游子再度陷入困苦的境地。如果说外族强加的战争之苦无法回避也因而无法抱以怨言的话,那么战争结束后来自“胜利者”的人为祸乱之害便令人无法容忍;易言之,当满怀憧憬复员的清华师生看到昔日美丽的校园竟然被“胜利军”践踏得“有类马厩”时,他们该作何感想?他们又怎能安心投身教育事业?正如当时一教育家所言:“胜利的幻灭,现状的混乱,和前途的恐慌,正在处处刺激着青年的灵感。一切富有诗意的热情和活力,正好像被阴云所笼罩,被冷风凄雨所打击,找不到温暖光明的太阳。”(25) 在这些不利因素的刺激下,相当多的高校青年选择了与政府对抗的道路,而战后教育现代化也因此受阻。
同时还应当注意到,可以说如果没有教育界力量的积极介入与拼命抗争的话,高校接收的结局要更惨,或者说对战后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将更加严重。在北大的喜剧化结局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傅斯年这位教育界泰斗不懈力争的高大形象,尽管其中使用了非规范化手段,但其争取的是能够造福教育界的集体利益,故无可非议。即便在清华的不幸遭遇中,仍无法遮蔽另一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不畏强权据理力争的身影。另外,即使那些没有留下姓名或者永远被淹没在历史烟海中的教育界无名英雄,他们也各自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地维护着神圣的教育事业。在接收期间,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组织校卫队日夜巡逻,阻止盗窃与破坏行为,并争分夺秒地与破坏势力抢夺物资。1945年底,该委员会在地下仓库发现日军存储的大量水泥后,立即用以铺筑道路,“以免被大员接收”(26)。以清华、北大接收人员为代表的教育界力量,在充满诱惑和险恶的环境中,能够始终以事业为怀,洁身自爱,忠于职守,并能无所畏惧地与强权抗争,从而有效地保护了教育资源并保障了高校复员的相对顺遂,进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延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此为战后收复区高校接收的突出特点,或称之为战后国民政府接收的唯一亮点。
注释:
①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后中国》第7编第4卷,(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65页。
②邵毓麟:《胜利前后》,《传记文学》(台北),1967年第1期。
③朱汇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台北“国史馆”1988年版,第420页。
④《复员时期之教育》,《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第三章,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4页。
⑤《郑天挺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04页。
⑥陈雪屏:《北大与台大的两段往事》,《传记文学》(台北),1976年第1期。
⑦《北大代校长傅斯年表示:做个不折不扣榜样,确保干干净净声誉》,1945年12月7日《申报》,第2版。
⑧《傅斯年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314页。
⑨《北京大学纪事》(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页。
⑩《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电》(1945年12月10日),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4—1:2—1。
(11)《陈岱孙函梅校长报告在平接收情况》(1946年2月25日),《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1页。
(12)《后方勤务总司令部第五补给区司令部代电》(1946年1月12日),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4—1:3—1。
(13)《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致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电》(1946年1月29日),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4—1:3—1。
(14)《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代电》(1946年2月11日),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4—1:3—2。
(15)《清华大学复员工作为第五补给区卫生初妨扰情形概略》(1946年4月),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4—1:3—4。
(16)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后中国》第7编第4卷,第1页。
(17)《陈岱孙函梅校长报告在平接收情况》(1946年2月25日),《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上册),第411页。
(18)《何汝楫日记(1946年4月15日—5月15日)》,《日军铁蹄下的清华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9页。
(19)《清华园之洗劫》,1946年7月13日《大公报》第三版。
(20)《如此接收——参政会旁听记》,1946年4月6日《大公报》第三版。
(21)《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等单位关于收复平津区教育机关报告》(1946年7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22)《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46年1月25日),《日军铁蹄下的清华园》,第29页。
(23)《教育部代电关于借用校舍事(1946年4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上册),第416页。
(24)余才友:《一年来的清华》,《中华教育界》,1947年第4期。
(25)陈剑恒:《战后教育的三大问题》,《教育杂志》,1947年第2号。
(26)陈封雄:《劫后燕园的第一篇新闻报道》,《燕大文史资料》(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