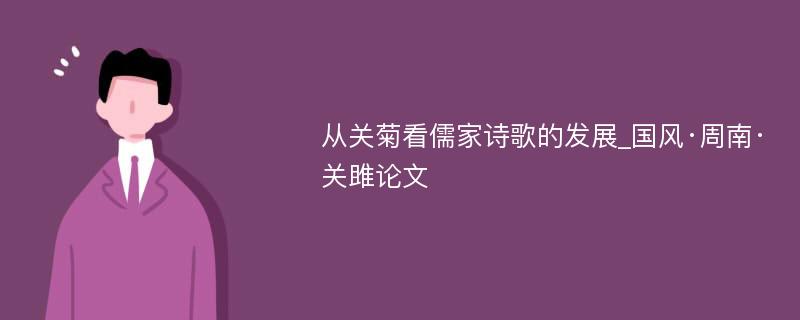
从《关雎》看儒家传诗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关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09)01-0045-05
皮锡瑞先生在《经学历史》一书中,对早自孔子之前直到西汉这一段经学历史,根据经学的发展特点给予分期和命名,即:经学开辟时代、经学流传时代、经学昌明时代。西汉作为经学昌盛时代,因为有经典的留存,儒家传诗的情况可以通过研究加以了解和掌握。但是之前经学开辟时代与经学流传时代的儒家传诗是怎样的?汉代儒家经学传诗是否继承了之前的儒家传诗特点?这些疑问因为史料和相关著作的缺失,学者们的研究也往往只能半猜想、半推测地勾画出依稀的面目。
上博馆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论》(以下简称《诗论》)的公布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可能。《诗论》是一部战国时期儒家传授、解说《诗经》的著作,透过其内容中对《诗经》的解说与评论,能够了解战国时期儒家诗学传授的大致面貌。《关雎》作为《诗经》的首篇,是儒家经典中非常重要、也是最为常见的一首。《论语》、上博楚简中的《诗论》以及汉初的经学著作《韩诗外传》、《毛诗故训传》,都曾评论过这首诗,但各书对这同一诗篇的讲解却各不相同。对此加以对比、研究,或能清理出儒家《诗经》传授的发展轨迹。
《关雎》一诗在《诗论》中出现的次数多达四次。在《诗论》零散、片断的语句中,一般诗篇多仅见一两处提及,仅有两首诗有四处提及,另一首是《甘棠》。《诗论》中与《关雎》有关的竹简文字如下:
第十简 《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盖曰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1](P263)
第十一简 《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1](P263)
第十二简 ……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1](P264)
第十四简 两矣。其四章则俞(愉)矣!以琴瑟之悦,嬉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1](P265)
《诗论》这四简对《关雎》的评论中,“改”字出现三次,训为“改”(用李学勤先生说)。第十简论“《关雎》之改,……《关雎》以色喻于礼”,是指这一诗篇以人对美色的爱慕、追求,晓谕人对礼的追求。由辗转反侧、寤寐求之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由自然而发的男女之情转向依礼相待,因此可称之为“改”。第十一简“《关雎》之改,则其思益也”,是说《关雎》由情改为礼,其思想有所进益。第十二简“……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反”前仅余一“好”字,但明显看出是一个上下文转折句,“礼”与“好”相对应。这里的“好”无论作动词还是形容词解,都从属于感性的思维,而“反纳于礼”则是对于前文的转折,指最后仍归于礼义。由此,《关雎》一诗的义旨正可谓“改”,可推知“改”字取《关雎》一诗本于情感上的爱慕与追求,而最终归于礼乐之义。第十四简集中讨论《关雎》第四章,认为以“琴瑟”、“钟鼓”表达对意中人的爱慕之情,其感情基调可谓“愉”,即“快乐”。句中仍有一“则”字,表示对上句的承接转折,可知上一句中对于三章的评论当是“愉”的相反之义,这从《关雎》三章诗句“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一句可以得到确证。悠字义为“忧思貌”[2](P2),正与四章所含之“愉”义相反。
《关雎》原诗的内容表达的是男子爱慕、追求意中女子之义。结尾处“钟鼓乐之”一句别有深义,钟鼓之乐正是古代的庙堂之乐,是举行仪式时所用,暗示着举行婚礼、成就仪式。因此,一般认为,这首诗虽写男女之情,但却能发乎情而止乎礼。联系《关雎》一诗原义,可知《诗论》中以“改”论《关雎》一诗,其着眼点有二:一是《关雎》由好色而动情,再使情归顺于礼,前后的变化显示出“改”情为礼之义;二是《关雎》虽有美色之思,但能够以礼相待,可见其人之贤。评论基于《关雎》一诗的本义,但有所归纳和生发,即以儒家礼乐观论诗。此外,第十四简中对于《关雎》第四章的评论为“愉”,反映出《诗论》对诗的情感体验和把握,虽持儒家之义理,但仍不失为真正的文学评论。
对于《关雎》一诗的讨论由《诗论》上溯到《论语》,可以看到孔门说诗的一贯性。《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泰伯》: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论语》一书早于《诗论》,两书对于《关雎》一诗的评价也有承袭之迹可辨。《论语》中两处出现《关雎》一诗,都是对《关雎》整首诗的阐述,并未单独列出诗句加以论说。这与《诗论》中对于《关雎》一诗的整体评价形式是相同的。此外,《论语》中两处评价《关雎》,分别从情感基调和乐声之美两方面加以论述,前者注重对《关雎》中所体现的情感加以把握,认为“乐”“哀”之情皆有,然而不失其度,即情感的表达适度,言外之意,其情感虽有乐有哀,却合于礼仪节度,终不失范。而《诗论》在对《关雎》的评价中,也对诗歌有深入的情感认识,所谓“其四章则愉也”,正是对于《关雎》一诗“乐”的情感基调的准确概括。《诗论》中对于《关雎》的情感基调的评论,透露出《诗论》对《论语》中情感体验论诗的继承。并且,《论语》中对于《关雎》中乐、哀之情合于礼仪的判定,在《诗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表现为多处明确的评论:“《关雎》以色喻于礼”,“反纳于礼”,“重而皆贤于初者也”。“礼”、“贤”的诗义判定,将《论语》中还处于一种潜隐状态的道德评判明朗化,儒家理念由潜在转为显在,并且在重要性上也被置于首位。这从《诗论》中“改”和“礼”在短短不足百字的篇幅中的出现频率上,也可以得到确证。
从《论语》到《诗论》,对《关雎》一诗的评价表现出孔门说诗的承袭与新变:最初对诗歌的情感体验仍被接续,但是在论诗的地位和作用上已经沦于次要,成为对于个别章节的体验。孔子论诗、传诗侧重于“义”,《论语》中在评价语言背后起着潜在支配作用的儒家理念,在《诗论》中已经成为论诗的主要出发点,毫不掩饰地在论说中起主导作用,表现出儒家说诗在《诗论》中对义理生发的侧重。
《论语》与《诗论》中对《关雎》一诗的论述在大致趋向上相同,但在具体的论述上仍有差异。《论语》中的论诗条目只是孔子言谈中偶然涉及,并不是专门的论诗之作。在对《关雎》一诗的论述上,《论语》只有寥寥两句,简略而注重义理,这只是孔子论诗的一个侧面反映,由此可知孔子论诗的一些思想原则。《诗论》作为记录孔门说诗、传诗的著作,因其专门性和体系性,有足够的空间展开论述,因而在论述《关雎》时,既有情感体验,同时兼顾儒学义理。可以说,对孔子论诗研究而言,应将《论语》与《诗论》结合来看,前者从侧面反映了孔子论诗的大致思想,并且在引诗中也体现了孔子对于《诗经》一书的理解和论说方式,后者则正面地、系统地阐述了孔门对《诗经》的理解和论述,在结构、方式上更加严密和体系化。
《诗论》之后,西汉初期的儒家说诗文本《韩诗外传》中存有《关雎》一诗的诗句。
陈澧曰:“今本《韩诗外传》,有元至正十五年钱惟善序云,‘断章取义,有合于孔门商赐言《诗》之旨。’……盖孔门学《诗》者皆如此。其于《诗》义,洽熟于心,凡读古书,论古人古事,皆与《诗》义相触发,非后儒所能及。”[3](P107)正如在《论语》中孔门以对《诗经》的义理解说、生发为主要的说诗方式,汉初今文经学对《论语》中孔门说诗方式持认可态度,将微言大义的解说方式作为主要的解诗方法,并且认为,将诗句背后可能蕴含的道德礼义挖掘出来,才是对诗句的真正理解和掌握。就诗本身而论说诗义,则失于拘谨与肤浅。
正是在这种解诗原则及方式的统领下,《韩诗外传》中卷五第一章和卷一第十六章中分别出现了对《关雎》一诗的解说。
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诗》曰:“钟鼓乐之。”[4](P453)
这一章以《关雎》中的诗句“钟鼓乐之”结尾,但整章内容却是对于《关雎》一诗何以作为国风首篇的解释。这当中涉及对于《关雎》一诗的评价,并没有任何关于诗歌内容、风格以及情感的语句,整个篇章对于《关雎》的诗歌本质是漠视的,只是把经师理解的诗中道义的价值作了论述,认为“天地”、“生民”、“王道”,都在“关雎之道”中。《论语》、《诗论》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或暗或明地将《关雎》与儒家的道德礼义观念相联系,但仍旧对《关雎》一诗的情感性因素及诗歌本义有所兼顾,而在《韩诗外传》对《关雎》的论说当中,已经见不到与“诗”本身相关的内容,《关雎》已经完全成为儒家理念的承载。这里与其说是对《关雎》一诗的论说,不如说是《诗经》之道、儒家之道的价值宣告。
《韩诗外传》对于《关雎》的解说还有一处值得注目,即对于诗篇价值及意义的夸张、玄幻之说。以“幽幽冥冥”、“纷纷沸沸”、“如神龙化,斐斐文章”等令人无从想象其实际形貌的词语来形容人,使整个篇章的解说充满神秘色彩的夸饰、推崇。与《论语》及《诗论》相对平实的风格、内容相比,《韩诗外传》带有明显的虚饰、夸张成分。
再看《韩诗外传》卷一第十六章对《关雎》同一诗句的解说:
古者天子左五钟,将出,则撞黄钟,而右五钟皆应之。马鸣中律,驾者有文,御者有数,立则磬折,拱则抱鼓,行步中规,折旋中矩,然后太师奏升车之乐,告出也。入则撞蕤宾,以治容貌,容貌得则颜色齐,颜色齐则肌肤安,蕤宾有声,鹄震马鸣,及倮介之虫,无不延颈以听,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声,然后少师奏升堂之乐,即席告人也。此言音乐相和,物类相感,同声相应之义也。诗云:“钟鼓乐之。”此之谓也。[4](P53)
这一则以《关雎》诗句“钟鼓乐之”结尾的篇章,内容上以叙说古礼中天子的钟鼓之乐为主,对整个仪式情景进行描述,突出其中乐的重要作用。结尾诗句“钟鼓乐之”的解说完全脱离了诗本义,侧重于介绍与诗义毫不相干的古代天子之乐。究其目的,不外乎以描述古礼之乐突出儒家学说中礼乐文化的重要性,借解说“钟鼓乐之”诗句,宣扬古代天子之礼乐的威仪、功效。可见,在汉代经师的传诗中,诗句已经成为经师阐述儒家礼乐的承载体,思想内核则由经师依据相对固定的经学内容和理解加以阐释。
《韩诗外传》以上两则对《关雎》诗句的阐述,与《诗论》相比,外在形式上的差异十分明显:前者文中多出现诗题,对整首诗作简略评论,后者文中多出现诗篇中的具体诗句,叙事内容成为对诗句的阐述;前者简略,只用一两句话甚至一两个字加以评论,后者相对详细,往往以短则几十、长则数百的篇幅叙事或议论,以阐释一两句诗。这种形式上的差异还只是表面的,对于相同诗句的不同处理方式才是两书真正的不同。《韩诗外传》中,解说与评论的内容与诗篇及诗句的本义不再有任何联系,而是脱离了原诗的语境,借说诗的形式,宣扬经师所要传授的儒家经义。这意味着汉初儒家今文经师的讲经已经脱离了经典本身的限制,而是借经典的传授,使儒学得以光大。
《毛诗故训传》作为汉代儒家古文经学,对诗的解说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字词训诂,二是疏通诗句意义,三是儒家经师的义理阐发。对《关雎》一诗也不例外,如对第一句“关关雎鸠”的解说即是例证:“兴也。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这种解释虽然在内容上与《韩诗外传》不同,增加了对诗句本身的训诂与解释,并标明了诗句所用的文学手法,但在义理阐发上却都侧重于儒家的德教,并没有本质的差异。这表明,在西汉时期,儒家经师的传诗正是以儒家义理的生发为主,对于诗本身的文学性及诗学评价,已经逐渐趋于消失。
这一儒说传诗的基本内容与方法,在经学极盛时代的东汉,仍然被完好地继承下来。东汉韩诗传人薛汉,《后汉书》记载:“字公子,淮阳人也。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其所著《韩诗薛君章句》中对《关雎》一诗的论说为《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所引,得以辑佚如下:
薛君《韩诗章句》曰:“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5](P112)
在韩诗第六代传人薛汉的解说中,《关雎》一诗已经被完全作为刺时辅政之用的工具,其内在意义也被理解为君王处理后宫之事的准则。在手法上与韩婴一脉相承。韩诗传人的解说再次证实了韩诗学派以义理讲经说诗的传统。
由《论语》到《诗论》,再到《韩诗外传》、《毛诗故训传》、《薛君章句》,《关雎》一诗在儒家的传诗体系中,讲解内容逐步儒学义理化,在风格上则表现出由平实、引申到夸张、渲染,甚至在今文经学著作中变得带有玄幻色彩;对于《诗经》基于切实情感体验的诗学讲解逐渐消失,代之以儒家义理的阐释和宣扬。这正是经学开辟时代到经学极盛时代,儒家学说在逐渐强化自身的过程中,对《诗经》解说所作的经学化处理。
《孔子诗论》之论诗,着重于固定诗篇意义,使诗义渐趋稳定,从而形成对于《诗》贴切的、艺术的,但又带有儒学特征的理解与评论。这种既注重艺术感受,又关注内容意义的论诗方式可以称之为对《诗经》的儒家诗性评论。如果沿着《孔子诗论》所开辟的诗学传统走下去,那么,今天的《诗经》学史当是完全不同的面貌。然而,对于汉初经师而言,这种着眼于诗歌本身的说诗方式却成为解说《诗经》并借以传播儒家学说义理的障碍。渐趋固定化的诗旨必然使诗学缺少活力和新变,更无法胜任承载经学之说的任务。汉初经师以传授儒家学说、争取政教地位为首要目的,《孔子诗论》中诗性论诗传统自然被经学家漠视,而义理说诗之途,则大放异彩。《韩诗外传》之论诗,着重于对诗句的阐发,诗义的解释往往对传统学说有所突破,事与论凡经师的述说,无不可与诗句形成经学意义的阐释,纳入经学体系。这种道德性的论述使诗学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诗句与事、论的遇合即可激发出对儒学道德礼义的阐说,因而诗学获得了无限的阐释可能与无尽的创造活力,“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汉初经师对于《诗经》论述方式的选择,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道路选择。道德既凌驾于诗性之上,则《诗经》之学也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以道德、说教为第一要义的道路,与《孔子诗论》中儒家诗性论诗之道渐行渐远。
标签:国风·周南·关雎论文; 儒家论文; 韩诗外传论文; 国学论文; 毛诗故训传论文; 孔子论文; 诗经论文; 论语论文; 诗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