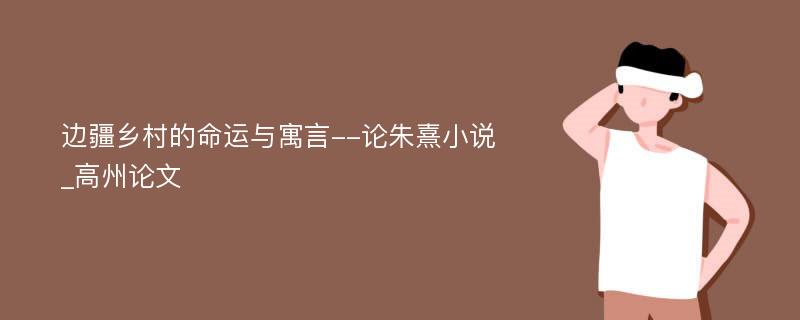
边地乡村的宿命与寓言——朱山坡小说漫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地论文,山坡论文,寓言论文,宿命论文,乡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乡村命运的深切关注,是朱山坡小说创作的核心所在。在城乡的交错地带构造独特的想象空间,其矛盾丛生的、异质混融的空间结构为叙事带来了多样的审美可能性。朱山坡有这样的表述:“我对高州有复杂的感情。一边是广西的米庄,一边是广东的高州城,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交接处是一个使人着迷的地方,总会有很有意思的东西等待我的挖掘。我试图把一座村庄和一座城市建立某种联系,让它们产生冲突和戏剧性。高州之于米庄,米庄之于高州,在时空上有时很近,有时却很远;里面存在着主从和支配关系,有时关系紧张,有时关系缓和,有时关系是物质的,有时关系是精神的,纠缠不清。”① 乡村与城市、落后与发达、精神与物质的交互冲撞,在他的笔下编织成一幅幅斑斓的画面。高州的强势渗透与米庄的被动应对,使乡村在步步退缩中成为一种附庸。高州既给米庄带来了机会,也通过对乡村沉睡的欲望的激活而催生了幻灭的痛苦和灾难。“高州贩子带来了改革开放”(《米河上面挂灯笼》),高州——这个鱼龙混杂的空间既生长着活力和希望,也为懵懂的米庄人准备好了代价和陷阱,“所有的一切高州城都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高速公路上的父亲》)。
在朱山坡的多数作品中,都会出现“高州贩子”的身影,像大耳强、香港脚、高州人贩子等等,这些外来者打破了偏僻乡村在长期封闭中的平衡状态。他们揣着金钱收购乡村的芭蕉、灯笼椒等农副产品,但其唯利是图、奸诈成性、背信弃义的作风,以异质的冲击瓦解村民古朴善良的生存法则,撼动乡村的道德秩序。《山东马》中的阙三兄弟想当然地认为“高州佬”偷走了他们的老水牛,于是就从一群迷路的精神病人中挑选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山东马”,将他关在牛栏里,用鞭子逼他拉犁拉车。意味深长的是,这种偏执的、非人化的、充满怨恨的报复与反抗,如同飞蛾扑火一样,在毁灭的冲动中自取灭亡,除了播种仇恨,并没有改变现实中不公不义的一面。《米河上面挂灯笼》的阙大胖面对阙三兄弟的讹诈,欺软怕硬的他在屈辱中将怒火转移到无辜的阙鸿禧的头上,杀死了他全家九口人。在阙大胖潜在的冲动中,闪现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吁求,曾经和他一样饱受歧视的阙鸿禧因为有五个在深圳的女儿而扬眉吐气,这种再没有分享艰难的同伴的被抛掷感,成了压垮阙大胖的最后一根稻草。作者在不无隐喻色彩的书写中,与五四以来的国民性批判传统有了模糊的呼应。不无遗憾的是,作者对于底层小人物的悲剧的难以抑制的同情,逐渐冲淡甚至淹没了潜存于文本深处的人性反思与批判理性。朱山坡试图从城乡交错地带切入,挖掘乡村在面对以城市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的压迫性侵入时的挣扎与阵痛,但是,其内在的复杂性还是被先设的戏剧化的二元结构所遮蔽,散落于字里行间的“缺德的高州人”,“高州佬就是霸道,和他们永远没有公平的交易”,“高州贩子坏得很”,作品的叙述并没有与这些米庄人情绪化的言论所营造的氛围保持足够的距离。当作品叙述所呈现的复杂性不足以摆脱外在框架的束缚时,高州就似乎应该为米庄的衰落承担责任?
朱山坡说:“农村是我的乡土,是我心灵的故乡,是文学的草根,是底层人物最集中的地方,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多触目惊心和使灵魂震颤的现实,那里繁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原生态。一个作家决不会放弃能使自己的灵魂发生里氏9级地震的题材,因为它会让你的写作变得神圣、亢奋、快感和无坚不摧。”② 正因为急剧转变的边地乡村社会失去方向的震荡,在作家的笔下呈现为具有强烈的戏剧性的场面。《米河上面挂灯笼》的叙事背景是近年乡村基层政府惯用的把戏,总是通过推广规模种植来炮制形象工程,什么好卖时就大规模地种什么,结果往往是上演了一出出物贱伤农的闹剧。这篇作品展现的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阙大胖从希望到幻灭的过程,割掉了正在吐穗的水稻,栽上椒苗,从而“获得了和别人一起憧憬未来的资格”,期望“不再当猪郎公”以重建卑微的尊严,但膨胀的希望反而成了他跌落深渊的强力推手。《我的叔叔于力》的主人公从乡村的抬棺人变成高州城医院里的背尸人,他和一个捡来的女精神病人生了儿子,为她治好病后却被其丈夫领回了上海。《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中坐卧铺汽车回老家的表妹因反抗嫖客调戏而跳下高楼,失去了一条腿,想不到躺在她身边铺位上沉睡的男人居然是一具累死了的农民工的尸体。中篇小说《感谢何其大》表现一个出身米庄的越战英雄何唐山逐渐坠入生活虎口的戏剧人生。朱山坡的这些作品让我联想到莫言的一些作品,以泥沙俱下、一气呵成的语流横冲直撞,纷繁复杂的信息碎片犹如在波澜中沉浮的枯枝败叶,而那些卑微的底层面孔犹如狂风中明灭的灯火,闪烁不定,暧昧不明,像连环炮一样试图激活五色目盲、五音耳聋的人们已经麻木的神经,通过反抗艺术成规的束缚,在现实与审美的包围中杀出一条小说的生路,用凌厉的、彪悍的、野性的冲击力来扫除弥漫文坛的闲适、奢靡、慵懒、颓废的小资情调和消费趣味。铆足了劲的朱山坡颇有奋不顾身的意味,这种戏剧性有时难免过火,在不辨方向的突围中陷入自己构造的迷魂阵,在呈现复杂性、悖论性的叩问中无所适从,在马不停蹄的奔突中被“前方”的诱惑所操控。也就是说,朱山坡还缺乏莫言驾驭情感、文字的气度与力度,就像骑着烈马的骑手一样,驾轻就熟的掌控能够带来奔腾的自由;另一方面,当没有驯服的烈马尥蹶子时,也能把骑手掀翻在地。过度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容易使作品在夸张中失真,密集的行动与琐碎的对话也容易使人物的性格呈现出平面化的特征,叙述静不下来,节奏失控。《我的叔叔于力》中高州火车站芭蕉堆积如山等情节,与《米河上面挂灯笼》灯笼椒滞销的情景异曲同工。而于力从高州捡回一个女精神病人做妻子的情节也与《山东马》中阙三兄弟捡回一个精神病人当“人头马”亦有雷同之处。
在作品的氛围和意蕴方面,朱山坡始终无法对荒诞和反讽忘情。像《山东马》中“人头马”的寓言,《鸟失踪》里人变鸟鸟变人的充满诡谲色彩的变形与再生,《喂饱两匹马》对两兄弟与两匹老马之间同构的生命轨迹的演绎,这种叙事模式给作品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魔幻色彩,但更让作者着迷的应当是呈现现实与人性的荒诞意味。知道现实背后隐藏着独特的逻辑结构与意义体系,但是却难以发现它们,知道追根究底的探索只会徒劳无功,又始终无法放弃内心的冲动与希望。朱山坡对卡夫卡式的希望与绝望的致敬,使其作品对现实的追问具有了别样的视野。朱山坡对精神病人形象的反复书写也传达出类似的艺术趣味。精神病人艰难挣扎的身影成为其作品中一道残酷的风景线,譬如《我的叔叔于力》中的田芳、《两个棺材匠》中的沈阳、《山东马》中的“山东马”、《空中的眼睛》中的麻丽冰、《中国银行》中的冯雪花、《响水底》中的桂娟等等。疯子的身份成了周围的人群蔑视、损害、践踏他们的当然理由,而逼迫他们陷入疯狂状态的苦难与社会根源也就被堂而皇之地遮蔽、抹杀,这种现实一方面加剧了这些被损害者的苦难,另一方面使苦难成为透明的尘埃,自以为健全的人们对之熟视无睹,不仅无法激发任何同情心,而且将其视为消遣的作料,甚至将这种苦难当成了佐证自己的生存价值的必要背景。朱山坡有这样的坦白:“我们都生活在精神病患者的身边。我对精神病人题材特别迷恋。……在我的眼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有病’的人,而这些人是需要怜悯的。”③ 不难感觉的是,朱山坡在文字背后隐藏着一种困惑的追问:究竟是这些疯子疯了,还是别的什么在失控的状态中疯狂奔跑?其叙述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疯子都有不愿委曲求全的个性,然而这种在屈辱中爆发的反抗最终都归于失败。难道反抗本身就隐藏了诱发疯狂的精神基因?在这一精神脉络上,从魏晋名士阮籍、嵇康的佯狂到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先知先觉,疯子形象在中国文学中成为具有丰富蕴含的象征符号。显然朱山坡也试图在浓缩混乱的现实经验之余,开掘出其中潜在的反讽性的、复调的意义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朱山坡在反复的表述中充满了无奈,找不到答案和回应的追问难免带来叙述的疲惫。面对这些不断重复的苦难,作家本人是不是也像听到“狼来了”的呼救声的村民呢?是不是也对沉甸甸的压迫感开始感到麻木了呢?如果是这样,对苦难的呈现本身也是一种遗忘的仪式啊!阿达莫夫认为:“知道存在着一种意义但却永远无法发现是悲剧性的。任何认为世界完全是荒诞的看法,便缺乏这种悲剧性因素。”④ 当朱山坡用荒诞来解释那些无法理喻的混乱时,这种举重若轻的反讽是不是也会掩盖事实的本质,甚至成为一种难以承受的轻逸?像《大喊一声》中胡四的命运就弥散出浓重的黑色幽默的意味,这个下岗的守门人紧绷的职业化神经不仅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烦恼,还让他丢掉了老命。但是,作品最后让这个以抓贼为职业的人被当成小偷活活打死,这种情节的反转以及对荒诞性的过度渲染,反而削弱了作品的冲击力和艺术含量。
应该承认,朱山坡2007年以来的作品跃升了一个台阶。作为其推荐人的张燕玲认为这和他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的选择有直接关系:“放慢急切的脚步,甘于寂寞,勇于探索,读书思考与良师益友对话赋予了朱山坡沉潜的力量与文学的翅膀,便有了他的重生之作。”⑤ 确实,像《高速公路上的父亲》在题材、结构上和《我的叔叔于力》、《米河上面挂灯笼》等一脉相承,但作者开始重视开掘人物人格与内心的渐变过程,进而追问其背后隐藏的复杂的文化根源,而不是浓墨重彩地凸显情节的陡转、人物性格的突变和人物命运的急转直下。让在施工中死于意外的父亲暴尸于高速公路上,借此向高速公路公司追索高额补偿,无恶不作的阙锋不仅利欲熏心,最终因为其父亲的补偿比拥有城镇户口的李细少了两万元而举起了屠刀。这篇小说的场面依然火爆,依稀地闪现着传统的侠义公案小说与晚清以来的黑幕小说的文化面影。值得重视的是,小说不再像《我的叔叔于力》、《感谢何其大》等作品呈现出斑驳的碎片化状态,叙述也摆脱了多头并进、枝蔓丛生的游离感,写出了可恶、可恨的阙锋性格与命运中的可怜、可悲,他的毁灭固然是自取其辱,但一个曾经充满正义感的少年在其人生的险途上似乎是别无选择。通过在相对平静中的叙述中呈现一种内在的矛盾,一篇类似于法制新闻的作品具有了深沉的反思意味,生发出意味深长的阐释空间。这个剧变环境给人的心理、人格、情感与灵魂带来的撕扯、挤压、分裂,比情节的曲折与事件的巧合具有更加强烈的表现力。
耐人寻思的是,《跟范宏大告别》、《陪夜的女人》、《鸟失踪》关注的都是乡村老迈人群孤独而凄凉的晚景。这些作品之所以受到关注和好评,恰如张燕玲所言:“面对死亡拷问人性与世事的寓言《跟范宏大告别》,其中的临终自我救赎一直延续到《陪夜的女人》,幻化成颇具人性的临终关怀……而且通过表达人性,表达人的复杂性,表达乡村新的伦理,表达时代的存在,包括自己内心的感动,显示了作品里的智慧、力量和温暖。”⑥ 我个人除了欣赏作品在阴暗的背景中涂抹人性亮色的关切外,还对其中不无巧合的象征意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偏远乡村的青壮年都像《陪夜的女人》中的厚生一样进入城市讨生活,留守老人的暮年一如乡村寂寥的现实,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老人就成了乡村本身的一种隐喻与符号。范宏大对诺言的信守,方正德对走失的妻子李文娟的愧疚与痴情,《鸟失踪》中曾经是猎手的“父亲”对山林的迷恋,这些品质似乎都是越来越物质化的现实所鄙弃的传统。当旧传统像破败的房屋一样只留下荒凉的废墟,在一茬茬老人消失的背影之后,贫穷的幽灵四处游荡,它所唤醒的对于财富的变态的渴求,以及被失衡的权力结构所支撑的新的乡村等级制度,往往会加剧人性的扭曲与欲望的膨胀。朱山坡唱响的是落寞的边地乡村的深沉的挽歌,尽管范宏大、方正德、“父亲”身上都有在严酷现实压迫下的种种卑微甚至卑鄙,但是附着在他们身上的那些被普遍指认为“过时”的价值,难道就必须同他们的身体一起被彻底埋葬吗?在这一层面上,方正德反反复复的死而复活也就有了意味深长的象征意蕴。中国的乡土社会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复杂性,生存环境的多样化催生了文化的多样性,不同形态的文化是人们适应不同环境的重要手段,然而一体化的城市化、工业化、物质化进程裹挟它们汇入统一的进程,传统的边地文明想当然地被打上“落后”的标签。在诱人的整齐划一的、现代化的乌托邦构想的参照下,这些民间的、边缘的文化本来就是一种隐性的、被压抑的、被遮蔽的文化,难道彻底湮灭是它们难以摆脱的宿命?事实上,这些脆弱的、原生态的文化就像深藏的地下水一样,滋养着一方土地上的一方人群,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犹如遗传基因一样,塑造了濡染其中的民众的独特气质。或许朱山坡对此并没有表现出清醒的自觉,但他在含混、朦胧状态中传达出的喟叹,那种面对故乡无法说明缘由的、十指连心的痛感,因摆脱了主题先行的理念化套路而具有了一种混沌的魅力。
在《跟范宏大告别》、《陪夜的女人》、《鸟失踪》等作品中,原来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惨烈和血腥的气息开始淡化,也没有赤裸裸的控诉,在表现固执的老人们滑稽可笑、荒诞不经的作为时,升腾起如烟似雾的感伤与无奈,在戏谑的笑涡里闪耀着沉痛的泪影,甚至隐含着一种锐利的悲愤。如果说《我的叔叔于力》等作品的风格接近于高举板斧横冲直撞的莽李逵,那么,近期的朱山坡开始从暴烈走向温柔,开始学习像一个医生一样,手执一把灵巧的柳叶刀,试图轻轻一挑,就如解牛的庖丁一样,游刃有余地揭开了这个时代背后掩藏着的底层真实的苦难。但是,朱山坡还是不甘平庸,总想寻找一个独树一帜的角度,想和古龙笔下的小李飞刀一样例不虚发,见血封喉。正因这样,他的作品总是散发出奇巧的光芒,将读者引入崎岖的羊肠小道,总是按捺不住一种制造阅读陷进的冲动,时不时在文字的草丛中打埋伏,在叙述的转弯处让野兔甚至老虎突然显身,令人惊魂失色。《跟范宏大告别》中阙天津老人的愿望最终落空,逃跑的“范宏大”只撂下一句:“他妈的什么米庄?五毛钱竟把老子的美梦吵醒了!”而《鸟失踪》在结尾用模糊化的笔法将失踪的鸟与在越战中战死的“喜宏”之间联系起来,确实出人意料,但这种急转弯在带来新奇与陌生化的同时,似乎也遗落了一些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的东西。《论语班》对反讽手法的运用也不无过火之嫌。对于过度迷恋反讽手法的作家,布斯有这样的忠告:“这使他能够描写人而不必使自己直接对人表态。……作者是在用反讽保护自己,而不是在揭示他的主题。”⑦ 外在的戏剧性就如百变的魔术一样,仅仅是一种障眼法,而那种潜入时代深层的内在的戏剧性,于无声处听惊雷,直逼人心,对“看不见的生活”进行深度开掘,往往具有更加持久的艺术魅力。杰出的小说叙述往往在描写外部行动时,通过暗示性的语言裸露内心思想;在推动情节的绵延时,也多方位地揭示性格的复杂内涵;在展现社会现实时,也挖掘出被遮蔽的心理现实。
朱山坡的小说叙述还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充满了对“事件”进行深度解剖的激睛。对“香蕉事件”、“灯笼椒事件”等等的观照,都试图从事件抵达本质,用显微镜式的观察与X光式的透视对标本进行病理分析,既照亮沉积在生命与人性深处的黑暗,也像寒夜里迷路的孩子一样追寻荒野里每一簇不起眼的光明,感受每一缕轻微的暖意。他在直接来自真实故事和新闻的启示的《喂饱两匹马》的后面,附有这样的自白:“这与传统的伦理道德无关,与人的生存哲学有关。有些现实我们甚至永远无法抵达,因此,我们不能用传统的伦理道德去看这个现象,更不能用简单的想当然的可信不可信去看待小说。《喂饱两匹马》看似荒诞,实满怀温情,充满了关怀和隐喻,我试图把它写成了一个寓言。”正如张大春所言:“如果我们希望新闻是真的,有时却宁可希望它像小说一样假;如果我们相信小说是假的,有时却宁可希望它像新闻一样真。”⑧ 这种真与假、常与变、事件与寓言之间的变幻,吸引着作家拓展自己的想象空间,去探索潜在的审美可能性。但是,事件化或新闻化手法对急速转换的时代的刻录,在接近真实的路途上,也容易因为浮泛、表面和猎奇而偏离。只有始终以守护记忆的独立意识来进行持续的发问,事件才不会在繁复的堆积中阻断反思历史与眺望未来的视野。
朱山坡是一个有抱负的写作者,这种持之以恒的艺术信念推动着他不断超越自我。他说:“每一个作家都拥有自己的神圣的领地,那里就是作家的‘原乡’,它与作家的情感血肉相连,也是作家记忆中水草最丰满的地方。还比如福克纳的杰弗生、马尔克斯的马贡多、余华的海盐、苏童的香椿树街。高州城也许就是我的马贡多。”⑨ 朝着这个目标,朱山坡会以更加开阔的视野不断地挖掘下去,发现地层深处独特的艺术矿藏,使他笔下的米庄和高州变得更加鲜活,更加丰富多彩,具有更强的浓缩性与概括力。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作家笔下的“原乡”真正具有其无可替代的独特性,而不是大同小异、似是而非的高仿品,它才可能真正在文学与艺术的谱系上占有一席之地。
注释:
①②⑨ 孤云、朱山坡:《不是美丽和忧伤,而是苦难与哀怨》,载《花城》2005年第6期。
③ 朱山坡:《自述:我所能表达的世界》,载《花城》2005年第6期。
④ 阿达莫夫:《自白》,见马丁·艾斯林的《荒诞派戏剧》,79—80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
⑤⑥ 张燕玲:《从鬼门关出发——崛起的玉林作家群》,载《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⑦ W.C.布斯:《小说修辞学》,94—9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⑧ 张大春:《张大春的文学意见》,10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