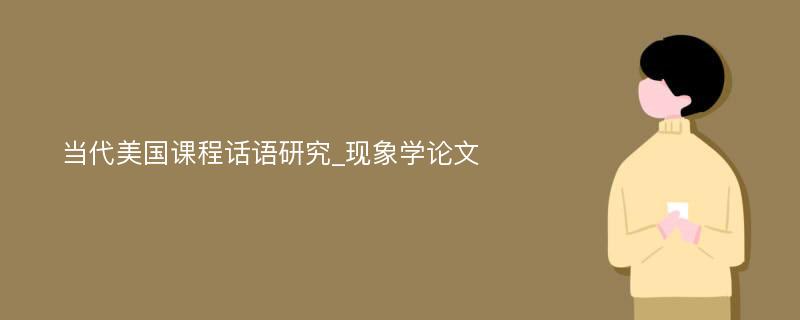
当代美国课程话语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话语论文,当代论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美国课程研究领域关注符号的潜能,提升语言的价值,采用多元的视角和方法,突破传统的课程领域过于重视普适性原理的单一格局,出现了多元的课程话语。一般而言,课程话语指的是,在课程研究领域,通过对特定主题展开言谈,推论性地形成课程意义的语言。[1]当代美国课程话语反映了美国课程研究的学术前沿,隐含丰富的课程内涵,体现了课程研究的本体论取向。对当代美国课程话语进行研究,无论是对我国课程研究进行前瞻,还是提升对课程内涵的理解均有积极的意义。
一、课程话语的主题
当代美国课程研究呈现出生机与活力。一方面,课程研究向外扩展,把课程置于广泛的社会场景中,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视角理解课程,建构课程的意义,促成了政治性课程话语、种族性课程话语、女性主义课程话语和后结构主义课程话语。另一方面,课程研究向内深入,即课程研究不仅深入儿童的教育生活,也深入课程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工作,还深入师生内在的精神和心灵。课程学者通过对这些教育生活、研究工作以及内在的精神和心灵进行反思和探究,达成理解和建构课程意义的目的,开辟了现象学课程话语、自传性课程话语。多元的课程话语架构了当代美国课程的学术领域。
课程话语是围绕一定的主题而展开的。政治性课程话语从微观政治的角度来谈论课程,力主反思性实践,视课程为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利器,其精致的主题有:“意识形态”、“霸权”、“再生产”、“抵制”、“文化资本”等。而从种族的视角言谈课程,以揭示教科书乃至日常教育生活中的种族主义动力,培育了种族性课程话语。“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理解”、“文化能力”、“文化解放”、“边缘”、“身份”构成其主题的家谱。女性主义课程话语则把持女性天然的养育经验,以女性轻柔的气质谈论和理解课程,孕育了“关爱”、“声音”、“空间”、“安宁”和“女性的自我认识”等关键的主题。借助现象学的方法,以一种原初的声音表达对儿童真实生活的体验,催生了现象学课程话语,其精微的主题为:“教育机智”、“教学智慧”、“教学沉思”、“秘密的地方”等。吸取后结构主义思想的精髓,组织隐语挑战传统的课程理论,发展了后结构主义课程话语。“恰当的距离”、“恐怖主义”、“虚无主义”、“通道”、“舞台表演”、“重写文本”、“重建自我”等是其萦绕的主题。而把学生或研究者置于课程的中心,运用自传的方法,将主体性的生成、个性的解放作为首要的目标,体现的正是自传性课程话语,其标致的主题有:“身份的建构”、“存在体验”、“梦”、“中间通道”等。
由上可知,当代美国课程研究领域的话语多元,主题繁茂。分析起来,这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当代美国课程研究强调课程的多元理解,倡导释放各种思想,力避课程研究领域出现话语霸权。其二是,课程研究着眼于培养教育者、受教育者和研究者的感悟能力及洞察能力,努力发展多种视角,导致多元课程话语的产生,而多元的课程话语是紧紧围绕某些主题而展开的,因而出现了主题繁茂的现象。
二、课程话语暗含的课程观
(一)课程是意识形态和负载价值的
政治性课程话语隐射的课程观是:“课程是意识形态和负载价值的”,换言之,“课程是为统治集团服务的观念体系、价值体系和表象体系。”[2]这有三方面的缘由,其一,课程的主体生活在特定的语言、文化、种族和不同社会层级的环境中,很难做到完全自主和客观,均带有主观偏见,所以,在选择课程内容时,不同的课程主体,其价值取向自然存在差异。其二,部分课程内容是从各种文化中精选而来,而文化选择的范围过于宽泛,这意味着文化选择必有侧重,即便有些意义被选中,它们可能会得到重新解释,或淡化某种意义,以保持同主流文化谐和。因此,课程内容的选择势必反映统治集团的意愿。其三,课程实施者把意识形态化了的课程内容教授给学生,并以此作为客观的现实而使其合法化,促成了统治集团对社会实行有效的控制。正因为课程是意识形态和负荷价值的,所以,当代美国政治性课程话语强调,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力避强化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弱化人的主体性的现象。因此,作为教育者,一方面承认课程是意识形态的,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性,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课程知识是客观、中立的观点;另一方面,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又要保持高度的警醒,对之进行适度的批判和反思,以弘扬人的主体性,唤醒人内在的自由、创造和超越的维度。
(二)课程是身份的建构
“身份”(identity)是当代西方教育理论中的一个中心概念,也是当代美国课程话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在教育中,身份往往引发对教育行为的质疑,触及教育者显现的和潜在的价值,如何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中进行协商的问题。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教育中对身份的关注,也就意味着对教育行为的关注。譬如,教师在思考学生该做些什么的时候,不仅会涉及到他认为学生是怎样的人这一问题,还会涉及到,在学生面前,教师认为他自己又是怎样的人这一问题。在当代美国课程话语的谱系中,种族性的课程话语代表了一种现实的建构,能反映和建构代与代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各种权力关系,其所隐含的课程观是:“课程是身份的建构”。种族性的课程话语表明,学校课程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自我的问题,即身份的问题,更清楚些,课程是关于自我的知识的建构,即身份的建构。诚如美国课程学者派纳所言,“认识自己现在是谁,以及自己将要成为怎样的人,这些都是需要建构的故事或文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同年轻人展开对话和交流,通过对话和交流而建构知识的过程就是课程。”[3]
(三)课程体现关爱伦理
欧洲的教育学涵盖教育和儿童养育,具体而言,它包括课程、学习方法、成人对儿童的教育责任等问题,指向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各种关系。由于受欧洲教育学思想的影响,当代美国女性主义课程话语所表达的课程,更多地反映了教育者与儿童之间的关爱关系。这里的“关爱”不局限在一般意义上的关心,或者一种个人的品德,它更多反映的是一种关系,即关爱关系。关爱关系由关爱者和被关爱者双方共同构成,在这一关系中,被关爱者与关爱者对这一关系的贡献相当,而且,只有当被关爱者承认受到了关爱时,这一关系才算成立。关爱关系是形成有道德的人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因此,道德教育过程应以道德关系的建构为中心,而不是将关爱仅仅作为人的一种美德。
(四)课程是探索生活体验的过程
现象学课程话语把持特殊的教育本质观、目的观和知识观,主张教育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反思的,而非控制的。作为事件的教育实践先于教育理论,而教育理论则是教育实践事例的启发性展示。值得关注的是,现象学课程话语把“生活世界”作为其探询的起点,认为教育植根于生活世界,并要求一种基于生活世界的对话形式的教育,旨在获取意义而不是知识的堆砌。因此,只有通过体验、理解和能动地建构,个体才能形成知识。这要求儿童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形成问题的能力,建立自己的判断,学会理性地思考。由此,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递知识、掌握技能,更应该致力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通过自身的建构而获得发展。
现象学课程话语谈论生活体验,所暗含的课程是“探索生活体验的过程”。“生活体验是人们在生活中直接的、先于反思的意识,是一种反射性的自发的意识。”[4]现象学课程话语作为人文学科,取之于生活,并以反思的形式表达着生活,因此,生活体验是现象学课程话语言谈的对象,要求在教育的实际中探寻教育的意义,目的在于唤醒人们对世界的体验,使人们重新认识生活世界。所以,对生活体验的关注就是对事物本身的关注,有了这种关注和深切的体验,才有助于在理解中培育教育实践的智慧。因此,现象学课程话语要求研究者融入生活,参与到生活关系和共同的情境中去,在生活世界中寻找生活体验的原材料,并对之进行反省和对话。
(五)课程是流动变化的,具有动态和建构的特质
后结构主义课程话语所暗含的课程具有流动和建构的特质。比如,在“舞台表演”这一话题中,生活成了文本,要求阐释和再阐释,这隐含课程的创造性和动态生成性;“重写文本与重建自我”这一话题所隐含的课程,不是预定知识的封闭式传递,而是由互动、交流、转换、对话构成的一种开放和流动的过程;“获得恰当的距离”强调教师身份的建构过程,把课程隐喻为一个建构的过程。后结构主义课程话语提倡意义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对文本而言,读者不仅要揭示其客观的含义,更重要的是揭示其所隐藏的东西。
(六)课程是“经验的履历”、鲜活的生活文化
自传性课程话语谈论师生经验的履历,换言之,它们是师生教育性经验的创造和展示。因此,教学是师生基于个人的经验而展开的活动,也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学习经验的交汇与碰撞、融合与辉映的过程。由此,教学过程是师生认知多重文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受社会、政治和伦理的影响过程。上述的教学观念挣脱了传统课程的目标、设计、实施、评价等公共框架的束缚,体现了师生基于经验而展开的创造性活动。这样,教师可以根据自身的想象力去构思课程,表达教师自己的个性化经验;“学生也可以关注自己的学习经验,而这些经验不仅具有教育的价值,还具有伦理的价值、艺术的价值等等。”[5]自传性课程话语反映的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自身鲜活的生活文化。
三、对课程话语的评价
当代美国课程话语是对传统课程话语的超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元的以叙事为基础的描述性话语,超越单一的以科学为基础的“范式话语”,二是以理解为基础的复合性课程,超越单一的以操作和技术为基础的控制性课程。当代美国课程话语不仅拓宽了课程研究的视角,而且丰富了课程的内涵,使课程研究出现了本体论取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但其局限性也很显目。
(一)当代美国课程话语是对传统课程话语的超越
美国传统的课程话语,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范式话语,具体而言,它们是以生产工程技术学、建筑工程学与开发学、农业技术、艺术表现为隐喻的术语。[6]以生产工程技术学为隐喻的术语包括:目标、生产、技术、制度、规划、程序、评价等;以建筑工程学与开发学为隐喻的术语主要有:开发、构建、结构、基础等;以农业技术为隐喻的术语为:调节、成长、组织、整合、生活;以艺术表现为隐喻的术语包括:设计、表达、表征、故事、展示、批判等。而当代美国课程研究领域,逐渐割去表现程序的工程技术学话语,使课程话语发生了根本的转换。课程研究从过去侧重对教育内容的选择、编制、评价等,转向了探讨课堂中师生文化的、政治的、伦理的意义。当代美国课程话语超越了传统的学科框架,淡化了学科界线,出现多元的以叙事为基础的描述性话语。
当代美国课程话语所表达的课程,是以理解为基础的复合的课程,超越了单一的以操作和技术为基础的控制性课程。传统的课程被理解为跑道,这是一种预设好的严密的计划,也是一种控制性的课程,具有程序性和操作性的特点。而当代美国课程话语所隐含的课程,既是一种批判性的文化,着眼于人的解放,也是师生共同跑的行动和过程,还是建构知识的过程。显然,当代美国课程话语所蕴含的课程,是以理解为基础的复合的课程。它超越了单一的以操作和技术为基础的控制性课程,有利于受教育者从僵硬的计划、单一的目标和标准化的考试中解救出来。
(二)当代美国课程话语反映了课程研究的新趋向
当代美国课程话语反映的是充满活力的本体论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重视人的存在;二是重视语言的存在。
传统的课程研究偏向认识论的研究,重视对课程和教学进行抽象的分析,以寻找稳定不变的教学的本质和规律。因而传统的课程研究,强调严密的结构和逻辑,在方法上重视归纳、测量和思辨,而研究的具体目的在于,为课程实施者寻找最佳的操作样板,研究的结论可用来证实学科内的其他理论,或用作其他理论的基础。所以,传统课程研究所得出的理论具有工具性的特点。当代美国课程话语所反映的课程研究,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本体论研究,并非对课程和教学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从典型的教育事件中获得启发,从对儿童的希望、爱和激励中导出教育的意义,还从对儿童的精神和心灵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导入教育的意义。由此,本体论的课程研究成果,所表达的正是解释所经历的意义,这种意义能够在特定的教育时刻中发生,也能在教师、家长和管理者同儿童的特定关系中发现。因而它是反思性和解释性的,而非控制性的。
当代美国课程话语提升人的自我意识,弘扬人的主体性,关注活生生的学习者这一本体的存在。此外,当代美国课程话语提升语言这一本体的价值。这是因为,语言能描述主体间的生活世界,促使个体发现自己内在的经验,并能回忆和反思生活中的各种经验。由于个体的生活世界由不同的经验领域组成,而这些经验相互联系和渗透,所以,通过语言探讨这些经验成为可能,人类经验的传承也成为可能。由于语言如此重要,所以,当代美国课程研究者试图以文本的形式来表达各种经验,强调学习者的主体性及其对文本的不同理解,以促成课程从传递中心走向对话中心。
(三)当代美国课程话语的局限
当代美国课程话创造性地融入解释学、符号学和现象学的理论和方法,激活了课程工作者对课程的思维,拓展了课程研究的视界,使课程研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是,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又显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当代美国课程话语特别关注语言的提炼和隐语的使用,而缺乏专业知识背景的人不易理解复杂的课程话语。过多地关注语言,容易诱发课程研究成果游离日常的课堂教学实践。此外,由于语言本身也存在先天不足,很难企及个体心灵深处的东西,所以,语言在表达个体内心感受的时候,会出现表现乏力的现象。因此,课程话语的作用是有限度的。
第二,当代美国课程话语,试图挣脱传统课程理论的工具主义、操作主义,推崇课程实践者的教育智慧,包括反思能力、洞察能力和感悟能力,有助于拉动教育者反思其原有的工作,进而改善其原有的工作,但却难于直面学校内具体的问题。此外,当代美国多元的课程话语,尊重各种异质的课程声音和价值,但在课程实践者中能达成共识的不多,因而在众多的课程价值面前,许多教育实践工作者由于缺乏判断、选择的能力而难于作出取舍。
第三,当代美国课程话语容易诱发课程研究的泛化问题。课程研究自然不能忽视课程理论体系自身的建设,需要不断加强理论本身的内在功力。而当代美国课程话语反映了课程研究的多元视角、方法和分析框架,但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这不利于课程研究形成强大的合力,也容易出现课程研究的泛化问题。此外,当代美国多元的课程话语丰富了课程的内涵,一方面体现课程的发展和进步,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潜伏着课程的身份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