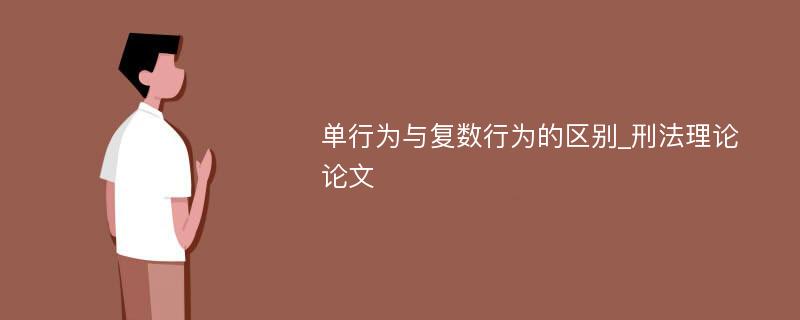
单一行为与复数行为的区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043(2011)-1(上)-0006-11
一、概说
实行行为是刑法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刑法中具有各种各样的机能:(1)通常认为,刑法分则所规定的行为是实行行为(当然存在例外),如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就是“杀人”行为,盗窃罪的实行行为就是“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刑法分则主要通过行为的描述规定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实行行为是使各种犯罪构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最主要的构成要件要素。实行行为不同,犯罪的性质就不相同。(2)一般来说,实行行为的开始就是实行的着手,如果已经着手实行犯罪,则不再属于犯罪预备,即使未得逞也应以未遂犯处罚(以未遂犯具有可罚性为前提)。实行行为是否终了,也影响犯罪形态的认定。(3)因果关系论所要判断的是能否将某种结果归属于某种实行行为,即因果关系是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而不是预备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4)在共同犯罪中,实施实行行为的人属于实行犯(正犯),没有实施实行行为的人属于狭义的共犯(教唆犯与帮助犯)。①除此之外,实行行为的数量对区分罪数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例如,倘若只有一个行为,即使侵犯了数个法益,也只能以一罪论处(想象竞合犯)。
与之相应,明确刑法分则的某个条文对某一犯罪所要求的实行行为,是单一行为还是复数行为(所谓复行为犯),也具有相同的重要性。例如,如果分则条文规定的是复数实行行为,而行为人仅实施了其中一个行为,就能够认定该犯罪已经着手实行,②但不可能认定为既遂犯。再如,如果二人以上参与的是分则条文规定为复数行为的犯罪,那么,只要行为人参与其中一个行为,就可能成立共同正犯。譬如,甲以抢劫故意对丙实施暴力且压制了丙的反抗,乙知道真相后与甲共同强取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抢劫罪的共同正犯。又如,如果分则条文规定的是单一行为,而行为人实施的是复数行为,那么,就有可能成立重罪或者构成数罪。
问题是,如何判断刑法分则的某个条文对某一犯罪所要求的实行行为,是单一行为还是复数行为?
诚然,通过法条用语、表述方式等得出结论是可能的。但是,单纯根据形式的标准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是妥当的。因为语言总是模糊的,有时难以准确地表述真实含义。所以,需要进行符合刑法真实含义的实质判断。
二、分析
刑法分则条文的表述,大体上为区分某种犯罪的实行行为是单一行为还是复数行为提供了线索。例一:如果刑法分则条文在两个行为之间使用“或者”一词,就表明本罪的实行行为不是复数行为,只是选择性行为。例如,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显然,只要行为人实施“或者”前后的行为之一,即可成立本罪。例二:如果分则条文在行为之间使用了顿号,就表明本罪不是复数行为,而是选择性行为。例如,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本罪的行为显然不是复数行为。但是,也存在难以得出合理结论的情形,下面仅就刑法分则使用的相关概念进行分析。
(一)“并”
从语法角度来说,当刑法分则条文在两种实行行为(动词)之间使用了“并”或者“并且”时,一般而言,该罪就要求复数行为。但是,在刑法分则条文中,这种情形很少见。例如,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据此,单纯盗窃信用卡的,不能适用该款规定认定为盗窃罪;反之,单纯使用他人信用卡的,也不能适用该款认定为盗窃罪。③但是,本文认为,不能认为本款规定的是复数实行行为,因为盗窃信用卡的行为并不是盗窃罪的实行行为,只能视为预备行为。再如,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如果行为人单纯伪造货币或者单纯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就不可能适用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但是,本款所规定的并不是独立的罪名,只是对包括一罪的处罚规定。
反过来的情形反而值得研究。亦即,即使刑法分则条文在两个行为(动词)之间使用了“并”或者“并且”一词,也不一定意味着该罪是复数行为。例如,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单纯从字面含义来看,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实行行为是复数行为:捏造虚伪事实与散布虚伪事实;似乎单纯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不可能成立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也有学者明确指出本罪属于复行为犯。④但本文不赞成这种结论。
第一,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故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没有侵害法益的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当然也不可能成其为实行行为。不仅如此,即使某种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性,但这种危险性非常微小时,刑法也不可能将其规定为犯罪,这种行为也不可能成其为实行行为。正如前田雅英教授所言:“所谓‘杀人’行为,并不包含偶然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一切行为,而必须是类型性地导致他人死亡的行为。例如,希望他人死于新干线事故而勉强使他人乘坐新干线,即使碰巧实际上发生事故而死亡,也不能说使他人乘坐新干线的行为是‘杀人’行为。只是意欲、意图发生结果,还不能说实行了杀人罪。”⑤换言之,实行行为并不意味着只是形式上符合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而是“具有发生结果的一定程度以上的危险性的行为”。⑥或者说,实行行为只能是发生了危险结果的行为。但是,单纯捏造虚伪事实的行为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法益侵害危险。例如,甲在纸条上写着“A啤酒厂的啤酒罐里有一具尸体,大家不要买A啤酒厂的啤酒”,然后放入抽屉。这种行为不可能侵害他人的商业信誉与商品声誉。既然如此,就不可能成为实行行为。
第二,具有侵害法益危险或者能够造成法益侵害的是散布虚伪的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事实的行为。例如,甲某日在地上捡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A啤酒厂的啤酒罐里有一具尸体”,甲明知这是虚假的,但仍然向社会公众散布“A啤酒厂的啤酒罐里有一具尸体”的虚假事实,导致A啤酒厂遭受重大损失。不难看出,单纯散布虚伪事实就能够侵害他人的商业信誉与商品声誉,使他人遭受重大损失。对这种行为不以本罪论处,明显不当。这也说明,捏造虚伪事实本身,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即使就一个人实施本罪而言,通过比较所谓“捏造并散布”这种复数行为与“散布虚伪事实”这一单一行为,也会发现二者没有任何区别。例如,甲事先在纸条上写着“A啤酒厂的啤酒罐里有一具尸体,大家不要买A啤酒厂的啤酒”,然后在大庭广众中宣读的,无疑成立本罪。乙事先并没有在纸条上写上这句话,却在大庭广众之中直接大声喊叫“A啤酒厂的啤酒罐里有一具尸体,大家不要买A啤酒厂的啤酒”的,不可能无罪。然而,如果说甲是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话,乙则是散布捏造的事实,二者完全相同。可是,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用什么标准判断,乙实施的只有一个行为,而不是两个行为。既然如此,就表明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并没有规定复数行为。人们可能会说,乙不仅散布了虚伪事实,而且捏造了虚伪事实。但是,这只是极为表面的区别。因为如前所述,单纯的捏造行为根本不是侵害和威胁法益的行为,所以,要求散布者必须实施一种没有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行为,是不合适的。
第四,不可否认的是,从文理上说,要将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中的“捏造”解释为修饰“虚伪事实”的形容词,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语言是不准确的,其含义也可能是不确定的。在这种场合,需要通过使用用语的语境与目的揭示用语的真实含义。一方面,某个事实是否属于“捏造”,是需要对方或第三者判断的,没有向对方或第三者传达的事实,也难以被判断为捏造。所以,捏造本身就包含了向外部传达的意思。另一方面,在笔者看来,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使用“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这种极为重复的表述,实际上只是为了防止将误以为是真实事实而散布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亦即是为了防止处罚没有犯罪故意的行为。
倘若坚持认为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实行行为是复数行为(即捏造虚伪事实并散布虚伪事实),就会产生诸多消极后果。
第一,如果说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实行行为是复数行为,就意味着捏造行为是实行行为的一部分,于是,开始实施捏造行为时就是着手实行行为,这是难以被人接受的。根据这种观点,甲在纸条上写着“A啤酒厂的啤酒罐里有一具尸体,大家不要买A啤酒厂的啤酒”,然后放入抽屉,就是已经着手实施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实行行为,即使没有散布,也可能成立犯罪未遂。这明显不当。而且,这种观点会导致在日记本上写日记、在私人电脑上写文章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的实行行为。但是,我们必须吸取“文革”的历史教训,对于这种没有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绝对不可能以犯罪论处。与对其他复行为犯的认定相比较,也会发现将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视为复行为犯的观点存在疑问。例如,就单个人犯罪而言,如果行为人仅实施了抢劫罪中的暴力行为,即使没有强取财物,也成立抢劫未遂。如果认为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是复行为犯,那么,只要实施了捏造行为就成立本罪的未遂,但这一观点并不成立。这从另一角度说明,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不是复行为犯。
第二,或许有人认为,如果行为人以散布为目的开始实施捏造行为,就是本罪的预备行为。但这种说法也存在问题:一方面,既然认为捏造行为是实行行为,就不能认为为了散布而捏造是预备行为。如同暴力、胁迫是抢劫行为的实行行为的一部分一样,不能认为为了强取财物而实施暴力、胁迫的行为只是抢劫罪的预备行为。另一方面,即使将捏造行为认定为犯罪预备行为,也不利于保障国民自由。因为这种观点导致的结局是,写日记、在私人电脑上写文章,都可能成为犯罪的预备行为。由此看来,将单一行为解释成复数行为,并不一定有利于保障国民的自由。
第三,认为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实行行为是复数行为的观点,不利于保护法益。在网络发达的时代,有时可能根本查不出虚伪事实的捏造者,而只能查明虚伪事实的散布者。例如,2008年3月,被告人甲开办了一个家教信息网站,因为删帖结识了另一名被告人乙。2008年8月,乙出钱并指使被告人丙,让甲在网上发布一些攻击竞争对手——某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的帖子,而且越多越好。于是,甲将严重损害某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商业信誉与商品声誉的帖子发到了20多个网站上,造成某高新技术有限公司12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但是,司法机关无法查清这些帖子内容的具体来源,换言之,不能查明谁编写了帖子的具体内容。倘若认为只有查明了虚伪事实的捏造者才能认定犯罪,则本案的几名行为人的行为均不成立犯罪,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法益。
基于同样的理由,对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的实行行为也应作相同解释。该款规定:“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虽然法条使用了“并且”一词,但笔者认为,本条中的编造并不是实行行为的一部分,由此得出的结论的是:一方面,单纯编造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的行为,并不是本罪的实行行为,不成立未遂犯。另一方面,明知是他人编造的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而传播的,即构成本罪。“编造并且传播”的规定,只是为了将没有故意的传播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
刑法分则还有几个条文虽然没有使用“并”与“并且”一词,但可能给人们的印象只是“并”与“并且”的省略,因而需要分析。
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条没有“并”的表述,但人们可能认为,本条罪状的第一句实际上是“捏造事实并诬告陷害他人”,于是,诬告陷害罪在客观上也有两个行为,一是捏造事实,二是诬告陷害。刑法理论上也有学者认为诬告陷害罪是复行为犯。⑦其实,本罪只要求一个单一行为,即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虚假告发。例如,甲事先在纸条上写着“某A于2010年10月24日盗窃某公司笔记本电脑一台”,装入信封后,递交给公安人员,该行为无疑属于诬告陷害(不考虑情节是否严重的要求)。乙事先并没有在纸条上写上这句话,却直接向公安人员说“某A于2010年10月24日盗窃某公司笔记本电脑一台”的,不可能被排除在诬告陷害之外。同样,丙在地上捡了一张写着“某A于2010年10月24日盗窃某公司笔记本电脑一台”的纸条,明知纸条的内容是虚假的,仍然将该纸条交给公安机关的,依然属于诬告陷害。
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诽谤罪的罪状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这一规定可能给人们的印象是,诽谤罪必须是“捏造事实并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其实,诽谤罪也不是由复数行为构成,亦即不意味着行为人必须先捏造、后诽谤。一方面,单纯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的,不可能成为本罪的实行行为;另一方面,明知是损害他人名誉的虚假事实而散布的,也属于诽谤。
反过来说,当刑法分则条文仅使用了捏造、编造等动词时,必须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揭示出真正的实行行为。例如,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规定:“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对本条中段所规定的“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不能作形式的理解,而是要作实质的判断。例如,甲在私人电脑上输入或者在笔记本上书写“某大型商场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晚8时发生特大爆炸事件”的文字时,不可能成立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只有将这种虚假恐怖信息传达给他人时,才可能成立本罪。否则,将意味着写日记之类的行为也成立犯罪。换言之,虽然本条规定的“编造”行为侧重于捏造虚假恐怖信息,“传播”行为侧重于散布虚假恐怖信息,但仅有捏造事实的行为不可能成立本罪。那么,法条为什么分别规定编造与传播行为呢?本文的回答是,在行为人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场合,即使只向特定人或者少数人传达所编造的虚假恐怖信息,就有可能成立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则要求行为人故意向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传达虚假恐怖信息。例如,甲在某大型商场突然大声喊叫“商场即将发生特大爆炸事故”时,认定为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即可。
再如,刑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在本罪中,并不是只要编造就成立本罪,而是要求发布了编造的虚假内容的招股说明书、认股书或者债券募集办法。发布之前,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或者债券募集办法中填写虚假内容的,并不构成本罪的着手。
又如,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里的编造显然不是在私人电脑或者日记本上编造,而是向受骗者(处分人)提交虚假理赔文书。
还如,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所规定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行为,也是指向保险公司提交虚假索赔原因或损失程度,而不是指单纯的编写、捏造行为。
(二)“和”与“及其”
在汉语中,“和”虽然一般表示并列,但有时仅表示“或者”。所以,不能将“和”一概理解为复数行为的文理根据。由于刑法分则条文并没有在动词之间使用“和”一词,故只能对类似条文略作说明。
例如,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前段规定:“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重金属或者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中的“和”表达的是“或者”的意思。
再如,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行为是“盗掘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同条第二款规定:“盗掘国家保护的具有科学价值的古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两款中的“和”表达的都是“或者”的含义。详言之,对于盗掘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或者盗掘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或者既盗掘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又盗掘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都应当适用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于盗掘国家保护的具有科学价值的古人类化石的,或者盗掘国家保护的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的,或者既盗掘国家保护的具有科学价值的古人类化石,又盗掘国家保护的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均应适用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及其”与“和”基本上起着相同作用。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前段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行为人故意掩饰、隐瞒他人犯罪所得的,或者故意掩饰、隐瞒他人犯罪所得产生的收益的,或者既故意掩饰、隐瞒他人犯罪所得,又故意掩饰、隐瞒他人犯罪所得产生的收益的,都符合本条规定的构成要件。
(三)“以……方法”与“以……手段”
在刑法分则条文中,“以……方法”与“以……手段”的描述,存在两种情形:其一,表明犯罪的实行行为是复数行为;其二,只是描述实行行为的具体方式,而不意味着其所规定的犯罪为复数行为。
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前段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法理论几乎没有争议地认为,抢劫罪的实行行为是复数行为,既暴力、胁迫等是手段行为,强取财物是目的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抢劫罪的成立,不仅要求取得财物的行为违反了被害人意志,而且要求行为人造成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状态,进而取得财物(特定的因果关系的发展过程);单纯利用他人不能反抗的状态而取得财物的行为,仅成立盗窃罪。正因为如此,日本学者一般认为抢劫罪是结合犯,⑧而结合犯是典型的复数行为。对于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以及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劫持船只、汽车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船只、汽车”),也可以作相同解释。
但是,即使规定方式与抢劫罪相同的犯罪,也可能不是复行为犯。
例如,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两个条文的规定方式与抢劫罪相同,现实发生的某些强奸案件与强制猥亵妇女案件,也可能的确表现为两个行为,即先实施暴力、胁迫等行为,再实施奸淫或者猥亵行为。但是,如果进行体系性的解释,就会发现,强奸罪与强制猥亵妇女罪的成立,既包括行为人压制被害人的反抗后实施目的行为的情形(复数行为),也包括利用被害人不能反抗的状态所实施的奸淫行为与猥亵行为。因为强奸罪与强制猥亵妇女罪,所要求的是行为人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实施奸淫或者猥亵行为,而不要求特定的因果关系的发展过程。在后一种情形下,显然不是复数行为。例如,乘妇女熟睡而实施奸淫行为的,没有争议地成立强奸罪。再如,在不少案件中,暴力本身也可能是猥亵行为;反之某些猥亵行为本身也是暴力行为。例如,违反妇女的意志,强行将手指插入妇女阴道的,其暴力行为本身就是猥亵行为。⑨再如,乘妇女站在墙边无法反抗时,突然强行与妇女接吻的,其猥亵行为本身就是暴力行为。⑩又如,强行剥光妇女衣裤,或者乘妇女不注意时突然触摸妇女阴部,或者在妇女难以脱身的场所直接强行用生殖器顶擦妇女臀部等行为,既是暴力行为,也是猥亵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认定为强制猥亵妇女罪既遂,而不能认为行为人仅实施了暴力行为,从而认定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未遂,更不能认为行为人仅实施了猥亵行为,从而否认强制猥亵妇女罪的成立。(11)在强奸行为与强制猥亵妇女行为表现为单一行为时,只有开始实施该单一行为时,才可能进入着手阶段。单一行为之前的行为不是实行行为,因而不能在单一行为之前认定着手。例如,就乘妇女熟睡而实施奸淫行为的强奸案而言,行为人进入房间等行为并不是强奸罪的着手,开始实施奸淫行为时才是强奸罪的着手。
其实,刑法分则条文关于“以……方法”、“以……手段”的规定,大多都是对行为本身的描述,而不表明犯罪具有复数实行行为。
例如,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正在依法执行职务时,行为人对之实施暴力、胁迫的,就成立妨害公务罪。也正因为如此,旧中国与国外刑法对妨害公务罪的罪状采取的表述是“在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时,对其实施暴力或者胁迫”。(12)
再如,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并不意味着本条所规定的犯罪行为是复数行为,而是旨在说明,放火、决水、爆炸等都是危险方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险方法,必须是与放火、决水、爆炸等相当的危险方法。
又如,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第二百九十八条规定的“扰乱、冲击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依法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款后段规定的“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等,都不表明相关犯罪的行为是复数行为,而是对相关犯罪行为的具体描述。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人的身体活动的行为,离不开一定的方法或手段。方法事实上是对身体活动内容的描述,方法不同,行为也就不同。例如,以暴力、胁迫等方法压制被害人反抗而强取财物的,是抢劫行为;以恶害相通告导致被害人产生恐怖心理进而交付财物的,是敲诈勒索行为;以欺骗方法使对方产生认识错误进而交付财物的,是诈骗行为。因此,抢劫行为、敲诈勒索与诈骗行为之间的关键区别可谓方法不同。不仅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方法或手段与行为甚至是同义语。例如,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将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称为危险方法,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是危险行为。当某些犯罪的成立要求特定的方法或手段时,是对行为本身的要求,而不是对行为之外的其他要素的要求。由此可见,犯罪的时间、地点、状况、方法与行为不可分离。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刑法分则中有大量条文使用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表述,许多论著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视为独立的一个行为,其实并非如此。下面以受贿罪为例展开讨论。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呢?这可能要分别就索取贿赂与收受贿赂来讨论。
索取贿赂时,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所以,在索取贿赂时,意味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贿赂。但问题是,这是指索取贿赂行为本身必须是一种职务行为,还是说国家工作人员就职务或职务行为索取贿赂?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在司法实践中,索取贿赂一般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在他人有求于自己的职务行为时,利用他人的困境或者需求,要求、索要乃至勒索财物;如果他人不交付财物,就不满足他人的要求。例如,乙有求于国家工作人员甲,期待甲通过职务行为为自己谋取利益,甲则提出交付财物的要求。显然,要求对方交付财物的行为本身,就是索取贿赂。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以权换利的行为,国家工作人员所索取的财物,是其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即财物与其职务行为的对价关系非常明显,因此,刑法规定索取贿赂的从重处罚。但是,如果他人请托的事项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没有关系时,利用他人困境或者需求,要求、索要或者勒索财物的,则不成立受贿罪。例如,中学校长抓住小偷后,小偷请求校长不报送司法机关,校长乘机要求小偷交付5000元给自己,否则报送司法机关。将盗窃犯人报送司法机关不是中学校长的职务行为,因此,校长的行为不成立受贿罪,只成立敲诈勒索罪。由上可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贿赂时,只是要求基于职务而索取贿赂,并不意味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本身是一个实行行为。
因收受财物而构成受贿罪的,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干什么?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收财物(指单纯接收财物的行为)?还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抑或接收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都要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刑法理论一直不探讨这一问题,司法解释也只是说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本身是什么含义。(13)这样一来,就更难理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了。
如果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收财物,则难以理解,也不利于对受贿罪的认定。因为并非只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才能接收财物。例如,甲向乙交付财物,要求乙为其子女安排工作,乙接收了财物。我们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乙接收财物本身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实践中存在公务人员的家属帮助接收财物的现象,这更清楚地说明了接收财物本身无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如果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也难以令人赞同。因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是一种许诺即可,而许诺本身不需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基于上述理由,我们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不能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同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收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益。
那么,能否说在收受贿赂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是构成要件呢?回答也是否定的。众所周知,收受贿赂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行贿人事前主动交付财物,以期国家工作人员为其谋取利益,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实施某种职务行为的过程中,行贿人主动交付财物,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三是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某种职务行为之后,行贿人主动交付财物,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三种情况的共同点是,国家工作人员接收财物并许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或者正在或已经实施了某种职务行为,使财物成为其(所许诺的)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司法实践中,往往需要注意区分的是收受贿赂还是接受赠与的界限,其关键在于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人们虽然从许多方面提出了区分的标准,但其核心标准应当是:交付财物者是否有求于收受贿物者的职务行为;所交付的财物是否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这表明,收受贿赂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许诺实施、正在或者已经实施(包括放弃)职务行为,而收受行贿人交付的财物,该财物成为其(所许诺的)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由此可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只是意味着国家工作人员所收受的财物与其职务行为具有关联性(财物是职务行为或所许诺的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而不意味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本身是一个实行行为。
诚然,在不同的犯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但都不意味着相关犯罪属于复数行为。例如,就贪污罪而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盗窃或者骗取,意味着盗窃与骗取行为是基于行为人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职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意味着行为人将基于职务占有的公共财物据为己有或者使第三者所有。但这些行为都不表明贪污罪是复数行为。概言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只是对特定实行行为的一种描述,也可谓实行行为的特定方式,因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实行行为。
(五)“违反国家规定”
刑法分则条文中的“违反国家规定”、“违反……法规”所表达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在此需要讨论的是,“违反国家规定”之类的要求,是否意味着必须存在复数行为?
例如,一种观点认为,“走私罪的违反海关法规和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是并列的实行行为”。(14)其实,违反海关法规并不是走私罪中的一个实行行为,只是判断行为是否属于走私的法律依据。符合海关法规的行为,不可能成为走私行为。(15)
再如,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前段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私分国有资产罪不是由“违反国家规定”与“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两个行为组成。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是判断是否“私分”的法律标准。如果行为符合国家规定,就不可能属于本罪的“私分”行为。所以,私分国有资产罪也不是复行为犯。
概言之,在以“违反国家规定”、“违反……法规”为前提的犯罪中,“违反国家规定”、“违反……法规”本身都不是一个实行行为。
三、问题
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在单一行为与复数行为的认识与处理方面,存在一些疑问,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将独立的犯罪行为视为前一行为的后续行为
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某行为是某行为的延伸”等说法相当普遍,但这种说法对定罪产生了不利影响。例如,对盗窃或者捡拾他人存单后从银行骗取存款的行为性质存在不同看法。例如,鲍某系某企业职工。一日,鲍某与同事程某、林某到隔壁办公室打扫卫生,程某发现办公桌底下有一张存折,鲍某随即捡到该存折,接着鲍某去另一办公室接电话。接完电话在上厕所的路上,鲍某掏出存折,方知是同事王某的活期存折,存额为15000元。回到办公室后,鲍某将存折锁在自己的抽屉里,没有声张。当天下午,王某找到鲍某问其是否见到她丢失的存折时,鲍某称,在接电话时,把存折扔到桌子上,不知被谁拿走了。几天后,鲍某持此存折到储蓄所提出现金15000元,并到另一储蓄所把所提出的款项存入自己的名下。关于鲍某的行为性质,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鲍某的行为是不当得利,应由民法来调整。理由是:存折落在地上是由于所有人保管不善造成的,与鲍某无关。第二种意见认为,鲍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理由是:鲍某是以捡取的方式掩盖了秘密窃取的本质,秘密窃取是针对财物所有人、保管人而言的,只要行为人采取自认为不会被财物所有人、保管人发觉的方法,暗中将财物取走即成立秘密窃取。第三种意见认为,鲍某的行为既不属不当得利,也不构成盗窃罪,而应成立侵占罪。(16)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7日《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中规定:盗窃“活期存折、已到期的定期存折……按票面数额和案发时应得的利息……计算。”上述第二种观点与司法解释的基本理由是,盗窃存折的行为是主行为,骗取存款的行为是后续行为,或者是盗窃行为的延伸。但上述观点与司法解释存在疑问。
本文认为,不管行为人通过何种非法途径取得了他人的银行存折,其使用他人银行存折通过银行职员骗取存款的,均应认定为诈骗罪(三角诈骗),而非盗窃罪。第一,存折本身的财产价值并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所以,不可能对存折本身成立盗窃、侵占等罪。第二,如果只是盗窃存折而并不持存折提取存款,被害人不会遭受实际的财产损失。换言之,造成财产损失的行为不是盗窃、侵占存折行为本身,而是后来的取款行为。因此,应根据取款行为的性质确定行为的性质,而不能根据取得存折的行为性质认定为盗窃、侵占等罪。第三,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储蓄机构若发现有伪造、涂改存单和冒领存款者,应扣留存单(折),并报有关部门进行处理。”盗窃或者拾取他人存折后向银行职员申请支取存款的行为,必然属于欺骗银行职员的冒领行为;如果银行职员发现属于冒领行为,必然扣留存折而不会支付存款;银行职员之所以支付存款,是因为行为人的冒领行为导致银行职员误认为其征得了存款人的同意。所以,银行职员支付存款的行为,是基于认识错误将存款人的存款处分给行为人。与此同时,银行职员又具有根据存折支付存款的权限与地位,因此,行为人盗窃或者拾取他人可以即时兑现的活期存折、已经到期的定期存折而冒领存款,导致他人遭受财产损失的,也属于三角诈骗,应认定为诈骗罪。同样,行为人骗取、拾取、抢夺、敲诈勒索他人存折或者银行存单后,通过银行职员骗取存款的,均应认定为诈骗罪。(17)显然,在类似案件中,将后面的诈骗行为视为前一行为的延伸,就使得盗窃行为包含了诈骗行为,明显不当。
再如,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0日《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被盗物品的数额,按照下列方法计算:……(二)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按下列方法计算:1.不记名、不挂失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不论能否即时兑现,均按票面数额和案发时应得的孳息、奖金或者奖品等可得收益一并计算。”据此,对于盗窃印鉴齐全可以即时兑现的支票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盗窃罪。但这种做法至少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只要支票可以挂失,单纯盗窃支票的行为,不能造成他人财产损失。换言之,在盗窃并使用支票的场合,造成财产损失的行为是后来的使用行为,而非先前的盗窃行为。所以,将该行为认定为盗窃罪有本末倒置之嫌。其二,将这种行为认定为盗窃罪,会造成不协调现象。根据司法解释,如果是已填写金额并能即时兑现的支票,按票面数额计算盗窃数额;如果票面价值未定,但已经兑现的,按实际兑现的财物价值计算;尚未兑现的,可作为定罪量刑的情节。这意味着,盗窃印鉴齐全可以即时兑现的支票后根本没有使用(即没有造成财产损失时)的行为人,因为按票面价值计算,可能比已经使用支票(造成财产损失)的行为人受到更严重的处罚。这违反了刑法的公平正义性。其三,根据司法解释处理也不现实。例如,行为人在盗窃其他财物的同时盗窃了某公司金额为100万元的支票,但并不使用该支票。按照该司法解释,对于行为人应以盗窃价值100万既遂处理。这既不现实,也会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其实,行为人盗窃可以即时兑现的记名支票的,无论在挂失之前或者之后使用,均应认定为票据诈骗罪。因为记名支票记载了收款人名称,所以,行为人盗窃印鉴齐全的记名支票后使用的,属于冒用他人支票,当然成立票据诈骗罪。
由此看来,在认定(广义的)财产犯罪时,首先要确定被害人,并确定被害结果的内容,然后判断什么行为造成了被害结果,再判断该行为是何种性质。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前面的行为就是主行为,后面的行为就是从行为,也不能动辄认为后行为是前一行为的延伸,或者动辄认为后行为是前行为的一部分。
(二)在法定的实行行为之前添加实行行为
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刑法分则条文原本规定的是单一行为,司法机关却在此单一行为之前添加了另一行为,使单一行为成为复数行为。表面上看,增加构成要件要素会限制处罚范围,但实际上却是明显扩大了处罚范围,甚至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例一: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仅规定了贩卖毒品罪,而没有规定购买毒品罪。易言之,单纯购买毒品的行为并不属于刑法的规制对象。那么,“贩卖”毒品是否意味着必须先购买毒品再出卖毒品呢?显然不能对贩卖作出这种要求。例如,行为人拾得一公斤海洛因后出卖给他人的,肯定成立贩卖毒品罪。再如,出卖祖辈留下的鸦片的,也成立贩卖毒品罪。既然如此,贩卖毒品就是指出卖毒品。但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普遍认为,贩卖包括出卖以及为了出卖而购买。于是,为了出卖而购买的行为成为贩卖毒品罪的实行行为。可是,购买毒品的行为原本根本不成立犯罪(购买后非法持有达到法定数额的成立非法持有毒品罪,则是另一回事),现在却成为贩卖毒品罪的实行行为,甚至以贩卖毒品的既遂犯论处。这种观点与做法明显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例二:开设赌场罪其实也只是单一行为,即经营赌场的行为。但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做法是,对于内地人员以营利为目的,承包或者参股经营澳门赌场或者境外其他赌场,组织、招揽内地人员赴他人承包或者参投的赌场赌博的行为,也按照刑法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刑事责任。其基本理由是,开设赌场行为属于复合行为,包括在内地发生的组织、招揽参赌人员等行为。可是,单纯组织、招揽他人前往境外赌博的行为,并不是开设赌场罪的实行行为。即使从客观上看,在境外开设赌场的人员常常在内在招揽赌徒,这也只是事实。但不能将客观事实强加于刑法规范。当刑法分则条文仅将开设赌场作为犯罪的实行行为时,不能将招揽赌徒的行为作为本罪的实行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将招揽赌徒的行为作为开设赌场罪的实行行为,那么,那些在境内开设了赌场,但没有组织、招揽赌徒的,其行为就并不完全符合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但这种结论既违反刑法规定,也难以被人接受。
不可否认,一般来说,在法定的构成要件要素之外添加要素,会缩小犯罪的成立范围,因为要素越多外延越窄。但是,添加犯罪的实行行为,并不一概意味着限制了处罚范围。这是因为,在法定的实行行为之前添加一个实行行为,就意味着将预备行为或者某种附随行为,被认定为犯罪的实行行为,结局必然扩大犯罪的处罚范围,进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三)在法定的实行行为之后添加实行行为
再以受贿罪为例。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受贿罪包括两种行为类型:一是索取贿赂,二是收受贿赂。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贿赂,而没有收受贿赂的行为,都没有认定为受贿罪,或者仅认定为受贿未遂。原因在于,司法实践上将索取贿赂类型的受贿罪理解为索取并收受贿赂,使索取贿赂类型的受贿罪成为复行为犯。之所以如此添加实行行为,实际上是因为司法实践将受贿罪当作财产罪对待了。
其实,受贿罪的保护法益不是他人的财物,而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也可以说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宗旨是为国民服务,具体表现在保护和促进各种法益;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报酬,故不能直接从公民或者其他单位那里收受职务行为的报酬,否则属于不正当的报酬。国家工作人员理所当然要合法、公正地实施职务行为。但权力总是会被滥用,没有权力的人也会期待掌握权力的人为自己滥用权力;一旦滥用权力,将权力与其他利益相交换,权力就会带来各种利益;因此,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正行使权力的最起码、最基本的措施,就是防止权力与其他利益的相互交换;古今中外的客观事实表明,职务行为的合法、公正性首先取决于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如果职务行为可以收买,可以与财物相互交换,那么,职务行为必然只是为提供财物的人服务,从而损害其他人的利益,进而导致公民丧失对职务行为公正性和国家机关本身的信赖。因此,为了保护职务行为的合法、公正性,首先必须保证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不可收买性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本身;二是国民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具体到受贿罪而言,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是指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或者说职务行为的无不正当报酬性。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因为其职务或职务行为获得了不正当报酬,便侵害了受贿罪的法益。公民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是一项重要的法益。因为这种信赖是国民公平正义观念的具体表现,它使得国民进一步信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信赖国家机关(在我国还应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下同)本身,从而保证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开展,促进国家机关实现其活动宗旨。如果职务行为可以收买,或者国民认为职务行为可以与财物相互交换、职务行为可以获得不正当报酬,则意味着国民不会信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而不信赖国家机关本身;这不仅会导致国家机关权威性降低,各项正常活动难以展开,而且导致政以贿成、官以利鬻,腐败成风、贿赂盛行。因此,国民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是值得刑法保护的重要法益。
由于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所以,在索取贿赂的情况下,即使行为人没有取得贿赂,但其索要行为已经侵害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换言之,就索取贿赂而言,应当以实施了索要行为作为受贿既遂标准,而不应在索取行为之后添加收受贿赂这一所谓实行行为。或许有人认为,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所规定的“索取”就是指索要并取得,因此,只有收受了贿赂才能成立受贿罪既遂。但是,这种观点是离开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得出的结论。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是保护法益为指导,只要承认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或者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就不可能在索要行为之外另要求收受行为。
不难看出,在法定的实行行为之后不当添加实行行为,必然使犯罪的既遂标准推迟,因而不利于实现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
注释:
①参见[日]前田雅英著:《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4版,第114页以下。
②其实,对于复行为犯着手的认定,并不存在绝对统一的标准。因为着手不只是形式的判断,而且需要实质的考察,亦即,只有造成了法益侵害的紧迫危险时,才能认定为着手。另一方面,虽然刑法总则规定原则上处罚未遂犯,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换言之,就某些犯罪而言,即使认为其行为已经着手实行,也不意味着要将该行为当作未遂犯处罚。例如,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前段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可以认为,本罪是复行为犯,前行为是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行为是高利转贷他人。应当认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时,就是本罪的着手。但是,如果没有高利转贷他人,就不可能符合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条件,因而基本上不可能认定为本罪的未遂犯。此外,不排除在个别复行为犯中,以行为人开始实施后行为为着手。例如,刑法第三百五十一条所规定的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的第三种行为类型是: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抗拒铲除。这种类型的犯罪,也可谓复行为犯。但在本文看来,只有开始实施抗拒铲除的行为时,才是本罪第三种行为类型的犯罪着手。
③按照笔者的观点,拾得、骗取他人信用卡后,从自动取款机中取款的,直接成立盗窃罪,不应适用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④参见陆诗忠:《复行为犯之基本问题初论》,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6期,第171页。
⑤引注同①。
⑥[日]前田雅英著:《刑法的基础·总论》,有斐阁1993年版,第92页以下。
⑦引注同④。
⑧见前引①,第496页;参见[日]山中敬一著:《刑法总论》,成文堂2008年第2版,第718页。当然,这种结合犯,并不是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单纯结合,而是要求手段行为压制了被害人的反抗进而实现目的的行为(参见[日]山口厚著:《刑法各论》,有斐阁2010年第2版,第216页)。
⑨参见日本大审院1918年8月20日判决,载日本《大审院刑事判决录》第24卷,第1203页。
⑩参见日本东京高等裁判所1957年1月22日判决,载日本《高等裁判所刑事判例集》第10卷第1号,第10页。
(11)在日本,个别学者认为,当暴力行为本身就是猥亵行为时,不成立强制猥亵罪,只成立强制罪(参见[日]中义胜著:《刑法各论》,有斐阁1975年版,第85页)。但是,通说认为这种行为成立强制猥亵罪(参见[日]大谷实著:《刑法讲义各论》,成文堂2009年新版第3版,第112页;[日]曾根威彦著:《刑法各论》,弘文堂2008年第4版,第65页;[日]山口厚著:《刑法各论》,有斐阁2010年第2版,第107页;等等)。
(12)参见旧中国1935年刑法第135条、1928年刑法第142条、日本刑法第95条、德国刑法第113条、奥地利刑法第270条、韩国刑法第136条。
(13)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11月6日《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指出:“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权或者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8月6日《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指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
(14)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第445页。
(15)参见王明辉:《复行为犯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16)参见缪军:《捡拾他人存折拒不交出并提款如何定性?》,http://www.jcrb.com/zyw/n85/ca52816.htm(访问日期:2005-04-03)。
(17)当然,如果盗窃、拾取存折后在自动取款机上取款的,则成立盗窃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