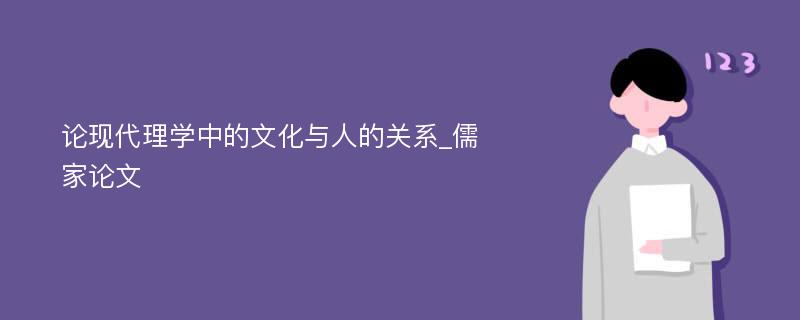
现代新儒家论文化与人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化与论文,关系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9-0028-03
文化与人是现代新儒家热烈讨论的两个话题。对前者而言,因为痛切地感到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危机实质是文化的危机,故而他们根据传统儒学资源,系统反思全球背景下的文化现象,以全面复兴儒学为根本理念,建构起新儒家的文化哲学;就后者而言,他们继承了儒学以人为本的传统,并结合时代特征和西方理论,发展出新儒家的人生哲学。尽管二者各成一理论体系,但由于文化与人的关系是如此紧密,所以使新儒家的文化哲学与人生哲学具有极强的沟通性和相关性,成为它们共同的立论基点。
一、文化定义与人的生活
文化定义是文化哲学的逻辑起点,它不仅决定了哲学体系的建构方向,而且决定了哲学体系的理论限度。大多数的现代新儒家都对文化作了规定,虽然界说和表述各有不同,但论证策略和精神主旨是一致的。如梁漱溟认为文化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注:梁漱溟:《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0页。)或“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注:梁漱溟:《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7页。)徐复观提出“文化是由生活的自觉而来的生活自身及生活方式这方面的价值的充实与提高”。(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23页。)钱穆“认为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的生活”(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中),第562页。)或文化“指的是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中),第562-563页。)这些文化定义尽管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用人及人的生活来规定文化。这样就突出和强调了人作为文化主体的地位,把文化看作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发动、凝结、确证和实现,从而深刻揭示了文化与人的内在相关性。
所谓的“人”并非指单个的人,而是一个类概念,主要指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对于面对西学挑战,急于调动、整合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新儒家来说,文化主体首先是民族主体,钱穆明确指出:“文化必有一主体,此主体即民族。”(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中),第569页。)文化危机实际是民族文化的危机,因此必须凸显文化主体的民族性。中国古代就以文化作为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准,严格夷夏之防。现代新儒家也秉持了这个精神,虽然由于文化的强势和弱势的换位造成文化自信的不足,但他们希望藉着民族文化的重建来延续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人的生活”或“民族生活”是一个富有弹性和包容性的概念,它既包括精神文化,也包括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梁漱溟析之为“精神生活方面”,“社会生活方面”、“物质生活方面”。(注:梁漱溟:《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7页。)钱穆称之为“精神的”、“集体的”、“物质的”。(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中),第565-566页。)但文化之所以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志,并使民族自成其为民族的关键在于,在民族生活中孕育、涵养、生成的民族精神。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在1958年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指出:“照我们的意思,文化是各民族精神生命之表现。”民族精神一方面贯穿、渗透于文化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在塑造、凝聚民族上起着重要的范型和纽结作用。故而现代新儒家从人的生活来规定文化的逻辑结论最终落实到民族精神上来了。
二、文化类型与人生态度
文化类型是历史形成的各种文化共同体最本质的特征。现代新儒家的文化类型理论试图通过给中外文化“别类定型”,肯定文化的平等性和独立性,挽回民族文化自信,并为中外文化比较和走向融合提供理论准备。其文化类型确立的标准乃是各民族的人生态度,由此对中外文化作出总的评判。
按照徐复观看法,文化的最根本意义“在于形成人们所共同保持的健全的人生态度”。(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22页。)梁漱溟在其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首次以人生态度的不同提出了文化的三路向学说。西方文化是第一种路向,人生态度为人对于物的问题,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是第二种路向,人生态度为人对于人的问题,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第三种路向,人生态度为人对于自己本身的问题,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要求。由于人生态度的殊异,西方文化的科学和民主最为发达,印度文化则发展了宗教,而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国文化以其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比起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要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要好,也甚于反身内求的印度文化,故而是现在最优异的文化。这三种人生态度并非悬隔,而有共生的关系,各为三种文化之基本人生态度。
这种共时性又体现为历时性,即三种人生态度是按照一定的次第在历史进程中得到重现并发展出相应的文化。“照我的意思人类文化有三步骤,人类两眼视线所集而致其研究者也有三层次: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则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再其次则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其所用是现象;初指古代的西洋及其在近世之复兴,次指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再次指古代的印度及其在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而此刻正是从近世转入最近未来的一过渡时代也”。(注:《梁漱溟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这样梁漱溟就从人生态度出发,在纵横两个维度上建构起文化类型理论,显示了现代新儒家在文化与人的基本关系上另一解释视角。
三、文化价值与人生境界
文化价值是指文化的价值构成,它是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核心。在有关文化哲学的论述中,人生境界成为一个重要的论证环节。如冯友兰说:“人对于宇宙人生底觉解的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底意义,亦有不同。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底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境界。”(注:黄克剑、吴小龙编《冯友兰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04-305页。)可见,这里的境界是指由人对于宇宙人生的悟解而获得的关于宇宙人生的意义及其由意义构成的世界。冯友兰将客观世界之外的这个意义世界——境界,按照层次的高低划分为四等,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呈现为由低到高的动态发展过程。
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才顺行的,对于所行的事的性质并无清楚的了解,而且他所行的事对于他没有清楚的意义,他的境界似乎是一个混沌。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为自己的利。虽然动物也为自己利,却是出于本能的冲动,而他自觉他有如此的行为,是出于心灵的计划,或是求增加他自己的财产,或是求发展他自己的事业,或是求增进他自己的荣誉。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即是为社会谋利益。求自己的利的行为,是利的行为;求社会的利的行为,是行义的行为。功利境界中的人以“占有”为目的,道德境界中的人以“贡献”为目的。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人不但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是宇宙的一部分,可以“与天地参”。
人生境界的次第既然在于它对于人生的意义大小,那么它也必然反映了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文化的价值高低。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是最主要的两种人生境界。与此相对应,现代新儒家区分出“形而上文化”和“形而下文化”。科学被认定为“形而下文化”,在认识大自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科学方法和技术工具改造自然,为人类谋取物质利益,因而是求利的,表现在人对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的物质生活领域。艺术、宗教、哲学和道德等被认为是“形而上文化”,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道德原则。故道德境界高于功利境界,“形而上文化”也优于“形而下文化”。方东美指出:“这个自然界是形而下的境界,我们站在形而下的里面,各方面的要求都满足了,……还要提升向上,向上去发现形而上的世界的秘密。”(注:《东方美先生演讲集》,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第20页。)文化价值停留于功利境界的形而下文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超越这个文化,达到道德境界的形而上文化。中国文化的价值就在于这种超越后的形而上的文化,尤其是心性之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本原和大道。牟宗三痛感现代人对道德境界的淡漠,导致了形而下文化的独尊,“近人以科学知识为唯一标准,以为最首出,最显明,而德行反成为最辽远,最隐晦,最不显明之事,其实这是支离歧出,逐流而忘本。”(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26页。)唐君毅亦批评曰:“顾中国近百年来之人,对于西方文化价值之肯定,实太偏于专从功利点着眼。”(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17页。)现代新儒家由人生境界而推导出文化价值,以意义说明价值,认为相对近代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不仅可以救治其重科学轻人文的价值危机、意义危机和道德危机,而且显示了儒家文化价值结构的坚实和优越。
四、文化发展与人的创造
人类文化自产生以来,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而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人的创造。冯友兰说:“文化是人的文化,是待人而后实有者。宇宙间若没有人,宇宙间即没有文化。”(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中),第146页。)徐复观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细致考察了文化发展与人的创造的关系,第一,是把感观所得的材料,通过心的构造力与判断力,以找出这种材料的条理、意义及其关联;第二,把客观化为主观,又将主观投射、印证到客观上,循环往复,使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联系在一起。人生逐渐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扩大,因而能把人与人、人与物作有意义的连接,并向有意义的方向前进。“人类的文化生活,便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人类自然地生命,便是在这样文化生活中而生存发展”。(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29页。)正因为文化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产物,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本能的活动。现代新儒家虽然肯定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但对创造主体的论证却走向了圣贤创造文化的历史观。唐君毅认为:“人类虽然都在文化社会中生活,然大多数的人,常只能享受历史传下来的丈化成果,而不能创造文化。”(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45页。)总之,是那些先知先觉者在创造文化,而广大人民群众则被描述为文化的传播者和寄生者。
文化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先进,有落后,有发达,有消亡,中国文化曾经兴旺发达了数千年,成为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但在欧风美雨、坚船利炮的震撼中,中国文化落伍了,陷入危机,失去生命力了。唐君毅叹之曰:“花果飘零”,“所谓中国文化已衰微,不足应付时代,是什么一种意义。是否中国文化精神,在现在全不存在了?”(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04页。)在这样的文化危亡中,现代新儒家勇于担承历史使命,因为“人在有创造文化的精神时,人必须以他的生活之一切实际经验,以他的精力,他的生命,为文化创造而用”,(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46页。)所以他们以强烈的学术信心和执着精神,成为20世纪文化运动中颇为活跃的一群。文化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心,逃避责任,在危机中总蕴涵着希望,“大时代中的一切灾难,皆所以促成大时代中我们最伟大的创造”。(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中),第575页。)文化的更新与发展,在现代新儒家看来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途径,“保种救国只能文化自救”。(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中),第575页。)而文化自救则在于“返本开新”,“从老根上发新芽”,决不能割裂传统的文化胶带。钱穆的说法较有代表性:“在今天纵使我们的生活的观念已经改变了,但还只能文化自救,不能脱胎换骨的要另来一套新文化。只有我们自己来救我们自己。换言之,即是从各自的旧文化中求再生长。”(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中),第576页。)
同时,文化的共性与个性也与人的创造有关。“人的共性与个性,一与多,当然会反映在其所创造的文化上,而成为文化底一与多,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34页。)而我们应当欢迎这种共性与个性,因为它们对文化的发展是极有裨益的。文化的共性与个性之间,个性与个性之间,由不断地接触、吸收,将使某些个性的若干原有部分,发生一种解体现象。“但这种解体,并非个性之消减,而是个性新的凝集。个性之不断上升与凝集,正是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34页。)中国文化要像过去吸收佛教那样,努力吸收西方文化,在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建设和发展更有民族性的中国文化。
由上可见,现代新儒家的文化哲学与人生哲学的全幅建构落足于对文化与人的基本关系的考察,尽管他们的分析、评判囿于民族本位的局限,带有很大的不足和偏颇,形成了上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干,但他们力图挖掘古代儒学资源,接续传统,调整民族文化的路向,在融合会通中回应西学的挑战,其胸襟是魄大的,其研究是深刻的,其精神是真诚的,其教训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值得反复探讨、认真汲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