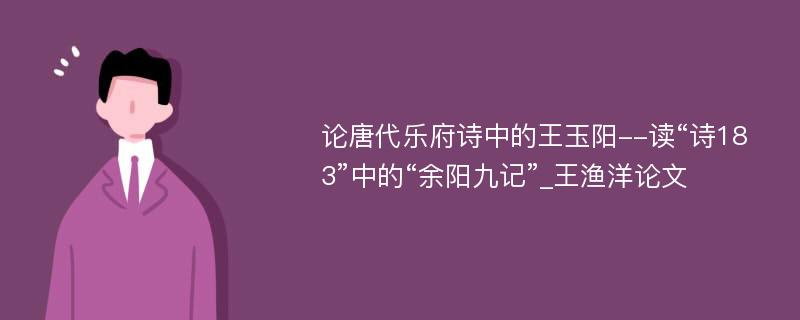
王渔洋论唐代乐府诗——读渔洋《论诗绝句#183;其九》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乐府诗论文,绝句论文,札记论文,唐代论文,论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渔洋《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其九论唐代乐府诗,云:“草堂乐府擅惊奇,杜老哀时托兴微。元白张王皆古意,不曾辛苦道妃豨。”称道唐代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乐府诗都写得好,具有古意,而不是机械模仿古乐府。其言颇为简括中肯。
王氏此论,在其诗话中有较具体的阐述,可供读者参证。王氏门人何世璂《燃灯纪闻》(《清诗记》本)第十九条述王渔洋论乐府诗有曰:
古乐府原有句有音。在当日句必大书,音必细注。后人相沿之久,并其细注之音而误认为句。附会穿凿,至于摹拟剽窃,毫无意义,而自命为乐府,使人见之欲呕。如南中某公作乐府,有“妃呼豨,豨知之”之语。夫“妃呼豨”三字皆音也,今乃认妃作女,认豨作豕,一似豕真有知,岂非笑谈?唐人乐府,惟有太白《蜀道难》《乌夜啼》、子美《无家别》《垂老别》以及元、白、张、王诸作,不袭前人乐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真乐府也。后人拟古诸篇,总是赝物。
这段话可说是对上引《论诗绝句》的最佳解释。这里称道唐代李、杜、元、白、张、王诸家所写乐府,能得到古乐府的神理,即《论诗绝句》所谓具有古意。所记南中某公把古乐府“妃呼豨”三个记音字实解为女呼豨,视为笑谈,即《论诗绝句》末句所讥嘲之对象。按汉乐府《铙歌》中之《有所思》篇有云:“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妃呼豨”实为表声的字。汉《铙歌》十八首中特多表声的字。故宋刻本《宋书乐志》(四)末尾馆臣校语有曰:“《汉鼓吹铙歌》十八篇,按《古今乐录》,皆声、辞、艳相杂,不复可分。”王渔洋《古夫于亭杂录》有曰:“沈约云:乐人以音声相传,训诂不复可解。凡古乐录,大字是辞,细字是声,声辞杂写,故致然尔。此言甚明白。故今人强拟《汉铙歌》篇,必不可也。”(《带经堂诗话》卷一引)可见他对汉乐府中声辞相杂的情况颇为注意。上引《燃灯纪闻》中前面数句,指出古乐府声辞相杂现象,即本诸沈约的言论。(王渔洋所引沈约数语,见《乐府诗集》卷十九《宋鼓吹铙歌》三首题解,今本《宋书乐志》不载。)渔洋认为应当理解汉乐府体制,区别音声和文辞,不应机械模仿,这意见是中肯的。
王渔洋《池北偶谈》又有论乐府一则,亦可资参证。文太长,节录如下:
郑渔仲曰:继三代之作者,乐府也。乐府之作,宛同风雅。……后世文士如李太白,则沿其目(指题目,即沿用乐府古题)而革其词,杜子美、白乐天之伦,则创为意而不袭其目(指制作新题乐府),皆卓然作者,后世有述焉。近乃有拟古乐府者,遂专以拟名。其说但取汉魏所传之词,句模而字合之。中间岂无陶阴之误,夏五之脱,悉所不较。或假借以附益,或因文而增损,蹐蹐床屋之下,探胠滕箧之间,乃艺林之根蟊,学人之路阱矣。以此语于作者之门,不亦恧乎!夫才有长短,学有通塞,取古今之人一一强同,则千里之谬,不容秋毫;肖貌之形,难为靓面。若曰乐府,则乐府矣,尽人而能为乐府也。若曰必此为古乐府,使与古人同曹而并奏之,其何以自容哉!李于鳞曰:“拟议以成其变化。”[①]噫,拟议将以变化也,不能变化而拟议,奚取焉?余知其不可而不能不为也,第命曰古乐府,而不敢以“拟”称云。
右蒙阴公文介公孝与(原注:公鼐字孝与,谥文介)乐府自序也。虞山钱牧翁尝亟取东阿于文定公论乐府之说,不知文介此论与文定若合符节。予尝见一江南士人拟古乐府,有“妃来呼豨豨知之”元句,盖乐府“妃呼豨”皆声而无字,今误以妃为女,呼为唤豨为豕,凑泊成句,是何文理?因于《论诗绝句》著其说云:“草堂乐府……”亦于、公二公之绪论也(《带经堂诗话》卷一引)
这里前面引录了公鼐论乐府之说,肯定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古题、新题乐府诗,批评明代中期以来拟古乐府的弊端。接着王渔洋对此深表赞同,又一次提到江南士人误会“妃呼豨”的可笑现象,并说明了他写作《论诗绝句·其九》的由来。由此可见,王渔洋对乐府诗的看法,系受到公鼐的启发。
郎廷槐编《师友师传录》,有一则记渔洋论唐以来乐府诗流变,也值得重视。节录于下:
故乐府者,继三百篇而起者也。唐人惟韩(愈)之《琴操》,最为高古。李之《远别离》、《蜀道难》、《乌夜啼》,杜之《新婚》、《无家》诸别,《石壕》、《新安》诸吏,《哀江头》、《兵车行》诸篇,皆乐府之变也。降而元、白、张、王变极矣。元次山、皮袭美补古乐章,志则高矣,顾其离合,未可知也。唐人绝句,如“渭城朝雨”、“黄河远上”诸作,多被乐府,止得风之一体耳。元杨廉夫、明李宾之各成一家,又变之变也。李沧溟(攀龙)诗名冠代,祗以乐府摹拟割裂,遂生后人诋毁。则乐府宁为其变,而不可以字句比拟也亦明矣。
这里王渔洋指出,唐代李、杜、元、白、张、王诸家,以至元代杨维桢、明代李东阳诸家、写作乐府诗,都有发展变化和创新,故能成就卓越。他不满意唐代无结、皮日休所作之补古乐章,当是由于它们机械模仿雅颂,缺乏创新变化。他不满意李攀龙的拟古乐府,因为它们对古乐府是机械摹仿,以割裂古辞字句为能事。渔洋论唐代及以后的乐府诗,肯定创新变化,反对机械摹仿,其见解是可取的。从上引诸条和诗《论诗绝句·其九》结合起来看,可见他屡屡肯定唐代李、杜、元、白、张、王诸家的作品,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的。
关于《论诗绝句·其九》,尚有两点须说明一下。一是首句所谓“草堂乐府”,究竟是指何人的作品,二是关于“辛苦道妃豨”的历史背景。至于第二句赞美杜甫“三吏”“三别”等篇感时伤事,托兴深微,第三句赞美元、白、张、王乐府注意反映民生疾苦,具有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古意,意思都颇明白,无烦细说。
首句“草堂”借指何人,旧注有两说。惠栋《渔洋精华录训纂》以为指李白。注曰:“《唐书·艺文志》有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阳冰录。首载乐府。”金荣《渔洋精华录笺注》则以为指杜甫,注曰:“胡宗愈《成都草堂先生诗碑序》:草堂先生,谓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号之曰草堂先生。”按惠注是,金注非。首先,句中以“惊奇”称道草堂乐府,此乃李白乐府诗之最大特色。考孟棨《本事诗·高逸》载:“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诗及焉。……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所称杜甫赠诗,指其《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有句云:“昔年有狂客(贺知章自称四明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汨没一朝伸。”又殷璠《河岳英灵集》评李白诗有曰:“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后代诗家论李白乐府、歌行,也常从惊奇角度指陈其特色。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评曰:“太白《蜀道难》、《远别离》、《天姥吟》、《尧祠歌》等,无首无尾,变幻错综,窈冥昏默。”渔洋诗中“惊奇”二字,正从杜诗、殷璠评语概括而来。又上引渔洋诗话言及李白乐府,总是提到《蜀道难》、《乌夜啼》,正与《本事诗》所记贺知章所叹赏篇章相合。渔洋利用前人评语,以“惊奇”二字称道李白乐府,可谓得其要领。再则,从上引渔洋诗话,可见渔洋论唐代乐府,总是李、杜、白等诸人并提,此诗不会独遗李白。再从全诗结构、行文看,前三句每句说唐代一人或数人,假如第一、二句均说杜甫,于文理亦不顺。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首句草堂乐府是指李白作品。李阳冰为李白编录《草堂集》,并为作序,其本不传。后来所编的李白集,改称《李翰林集》、《李太白集》等名称,《草堂集》一名遂不再受人注意,而杜甫成都草堂为人们所熟悉,因而在这方面易滋误会了。
王渔洋讥讽江南一士人摹仿汉乐府《铙歌·有所思》,把记声字“妃呼豨”误解为女唤豕。这虽出自个别士人之手,实际反映了明代中期以来部份诗人机械摹拟汉乐府、割裂字句、生吞活剥的流弊。在这方面,李攀龙起了不好的带头作用。他写了百余篇古乐府,对汉乐府铙歌、相和曲、杂曲歌、南朝吴声歌曲和西曲歌、北朝鼓角横吹曲等,一一加以摹拟,大抵因袭古辞字句略加变化,缺乏新意。(见《沧溟先生文集》卷一、卷二),李攀龙是后七子的领袖,因而对诗坛产生明显影响,形成了一种机械摹拟古乐府的风气,流弊滋深。渔洋讥讽江南一士人辛辛苦苦摹仿汉乐府,误“妃呼豨”为“女呼豕”的笑话,乃是这种拟古创作风气中的一个突出例子。对于李攀龙的带头摹拟古乐府,后人包括王渔洋多有訾议。上引《池北偶谈》一则,公鼐抨击李攀龙“拟议以成其变化”之说。据《师友师传录》所记,则渔详更是直接批评李攀龙“只以乐府摹拟割裂,遂生后人诋毁”。《池北偶谈》又曰:“乐府古诗不必轻拟。沧溟诸贤病正坐此。”说“诸贤”,可见机械摹仿古乐府者不止一二人,由于李樊龙是这方面的领袖人物,所以只是提他的名。与渔洋同时的冯班,对这种现象也多所指摘:
近代李于鳞取晋宋齐隋乐志所载,章截而句摘之,生吞活剥,曰拟乐府,至于宗子相之乐府,全不可通。今松江陈子龙辈效之,使人读之笑来。
《钝吟杂录·古今乐府论》
酷拟之风,起于近代。李于鳞取魏晋乐府古异难通者,句摘而字效之,学者始以艰涩道壮者为乐府,而以平典者为诗。吠声哗然,殆不可止。
《钝吟杂录·论乐府与钱颐仲》
乐工采歌谣以配声,文多不可通。《铙歌》声词混填,不可复解是也。李于鳞之流,便谓乐府当如此作。今之词人,多造诡异不可通之语,题为乐府;集中无此辈语,则以为阙。乐志所载五言、四言,自有雅则可诵者,岂未之读耶?
《钝吟杂录·正俗》
这里冯班除着重批评李攀龙外,还指责了宗子相(宗臣)、陈子龙等明代复古派文人。冯班还指出汉乐府“《铙歌》声辞混填,不可复解”,而李攀龙等偏偏喜爱摹拟这类不可通的语句,以此求奇,其风气至清代初期不绝。所以说,王渔洋所讥嘲的某江南士人误“妃呼豨”为“女唤豕”的可笑现象,正是当时不少文人刻意摹拟古乐府的创作风气中的产物。
综上所述,可见王渔洋《论诗绝句·其九》论乐府诗,主旨有二:一是肯定唐代李、杜、元、白、张、王的乐府诗写得好,它们学习古乐府,但能变化创新,获得古乐府的精神。二是通过对“妃呼豨”三字误解的例子,批评明代中后期以至清初乐府创作方面机械摹拟古乐府的不良倾向。
最后,要补充说明一下王渔洋对唐代乐府新歌的评价。唐人所作乐府诗,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古题乐府,其题目自古乐府鼓吹曲、横吹曲、相和歌、清商曲,杂舞曲、杂曲歌等沿袭而来,但内容往往能有所变化创造,推陈出新。二是新题乐府,体式和古题乐府相近,但根据所反映的内容,自制新题。李白擅长古题乐府,白居易专写新题乐府,杜甫、元稹、张籍、王建诸人,则古题、新题都写。这两类乐府诗,在体式、技巧上都蒙受古乐府的深刻影响,在当时为文人案头之作,大抵不合乐。三是乐府新歌,则为配乐(燕乐)演唱的歌词,《乐府诗集》称为近代曲辞。其歌词一般篇幅短小,多用绝句(七绝尤多)。这类歌词在当时大抵在宴席上歌唱,其内容多为日常抒情送别一类,不似前两类歌词多反映社会现实。王渔洋对这类乐府中的佳作也颇加肯定,其《唐人万首绝句选序》有曰:
考之开元、天宝已来,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尔。故王之涣“黄河远上”、王昌龄“昭阳日影”之句,至今艳称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传尤众,好事者至谱为阳关三叠。他如刘禹锡、张祜诸篇,尤难指数。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绝句擅长,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
王渔洋编选《唐人万道绝句选》,在很大程度上即表现了对这类乐府新歌的赞赏和肯定。在该书凡例中,渔洋又把上述王之涣、王昌龄、王维三绝句和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四篇推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更可看出他对这类新歌的崇高评价。唐代元结从狭隘的教化观念出发,对这类乐府新歌颇为不满,在《箧中集序》中指责道:“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在《师友诗传录》中,郎廷槐曾举元结的这几句话征询王渔洋的看法,渔洋回答道:
风化所起,《关雎》托始于房中;《乐录》(当指释智匠《古今乐录》)所载,清商亦存乎西曲。小伎容参法部,双鬟亦奏旗亭。周郎所顾,识者艳之;凉州之歌,君子所采。唯其无伤于雅道,或亦不见鄙于通人。
这里所谓凉州之歌,指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篇)。据薛用弱《集异记》记载,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某日在旗亭饮酒,诸女妓所唱绝句,均为王、高等三人作品,一双鬟女妓歌王之涣《凉州词》。此处王渔洋又一次肯定了《凉州词》等唐人乐府新歌。他不但不像元结那样鄙薄那些乐府新歌,而且认为那些多涉男女风情、由女妓歌唱的乐府诗,滥觞于《诗经》,“无伤于雅道”,其见解是相当通达的。
注释:
①李攀龙所作古乐府小引末尾曰:“《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日新之谓盛德。’不可与言诗乎哉!”(《沦溟先生集》卷一页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