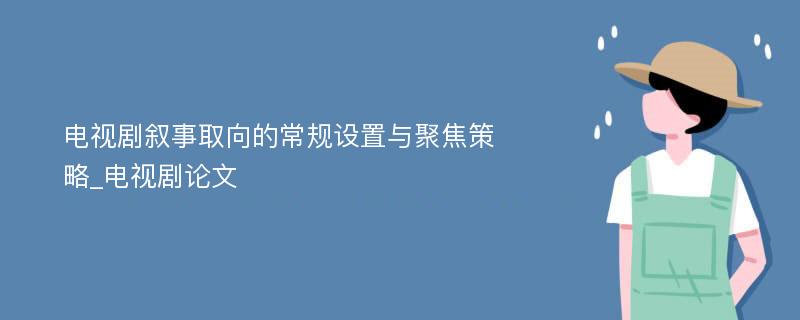
电视剧叙述方位的常规设置与聚焦谋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谋略论文,常规论文,方位论文,电视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登·怀特在《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认为,每一种叙事话语都包括了复杂的符码,作者把它们相互交织起来,从而生产出富于无限启示意义和多种影响的故事,并检验艺术家作为符码的主人而非奴仆的才能。① 俄国文本学家J·洛特曼也谈到虚构叙事话语方式、话语技巧的重要性,“艺术家的文本比科学家的文本负载更多的‘信息’,因为前者比后者设置了更多的符码和更多的编码层面。与此同时,与科学文本相对立的艺术文本既要注意在创造过程中使用不同符码传递的‘信息’,又要注意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娴熟技巧”。②
本文所努力探寻的故事述行规律,首先便出于这种对叙事话语的复杂多面性、意义阐释多样性的认识。电视剧的叙事话语,不仅仅是传达某种外在指涉物的信息工具,更是产生意义的母体。以简单的景物、事物为例,电视剧的画面语言不仅仅告诉观众这是一棵树、那是一张摇椅,《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那棵无奈却倔强生长于陋室的树、靠树搭建而起的家是坚忍生存的象征;而在《浪漫的事》的片头,被烘托在暖色调里的那张摇椅,则隐喻了起起落落聚散离合、弥散着怀旧气息的世俗生活。同时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当话语的语境和自身形式发生变化时,该指涉物的信息也许不会随之改变,但它的意义指向却可能已有很大不同。比如,“阳光”作为一种特殊含义的象征符码,在充满理想主义气质的主旋律电视剧语境中,阳光灿烂通常意味着希望、光明、美好前景等等,但在颇有些后现代味道的电视剧《给点阳光就灿烂》里,阳光的传统意指却被置换了、颠覆了,从女主角的一系列搞笑经历中不难看出,“给点阳光就灿烂”,无异于“给点色儿就开染坊”、“给根竿儿就爬”,“阳光”与“灿烂”变成了对传统爱情向往的反讽、调侃和消解。“阳光”在传递指涉物的信息时,虽然都呈现给观众“日光”这样一种客体景观,但由于电视剧语境的不同,阳光作为象征符码却有了天壤之别的意义编码。同理,如索绪尔的那个著名说法,改变一词的字母位置将构成另外一词,在电视剧叙事中,调整、改变叙述方位,往往也会影响着意义的不同生成。总之,话语形式不仅建构着不同的故事形态,且也关涉意义的不同生产、影响价值情感的不同流向。
在电视剧的编创过程中,如何自觉设置更为可观的符码和编码层面?如何使用丰富的符码传递“信息”、娴熟地演练话语技巧?本文拟通过正负价值较为鲜明的典型电视剧本文,尝试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抽象出埋藏其中的话语规律,而“叙述方位”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维。
一、电视剧叙述方位的常用聚焦
叙事学理论多采用“叙述视角”这一术语,较早也较有代表性的当推托多罗夫的三分法,即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③ 若对应电视剧的文本分析,即,当电视剧编导享有至高的话语特权,对他镜头下的各种人物和事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地加以表现时,谓之“全知视角”,放眼望去这该是长篇电视剧普遍选用的叙述方位;“内视角”,即编导大致等同于故事中的人物,其所见、所感、所思均附着于剧中的特定人物身上,如日剧《阿信》、《铃兰》;“外视角”,则意味着编导仅限于局外旁观,无论镜头话语还是人物话语,只见环境、外貌、行为、音响与人声等可视可听的实况,鲜有剧中人物思想感情的表露。显然,这种自甘局限的“外视角”恰好处于无所不能的“全知视角”的另一端。就艺术实践的可行性而言,在具有先锋气质的文学文本中可以比较自由地尝试“外视角”,以便让小说爱好者们在反复阅读中品味书写者存心掩藏的深意、体悟其良苦的美学用心,一如潜心揣摩海明威的那篇不动声色的《白象似的群山》。但把长于文学叙事的“外视角”硬往视听媒介上套,恐怕就有悖于电视剧的叙事特性。电视剧的文体特点和大众传媒平台对电视剧叙事话语的种种规约,都使得“外视角”的实施有犯忌之嫌和丢失观众之危。镜头也是观众之眼,其观看欲望不止于电视剧人物的表层外观,因而将故事中人物的内心景观遮挡起来、仅在外围上描述,恐怕是对接受者审美欲求的不敬。而法国新小说笔下、新电影镜头中的“外视角”,以“窥伺者”方式,“以物之眼观物”,深入剖析起来,则是一种极端方式的隐喻手法,其潜台词在于作者的缺席甚至死亡,意味着人的彻底被物化、人与物界限的消失殆尽,应是一种深藏意义而非埋葬意义的美学行为,与电视剧叙述方位的讨论关系不大。事实也证明,在电视剧实践中“外视角”的应用确实也凤毛麟角,即便有也只限于局部上的叙述。
在对叙述方位的种种学术探究中,米克-巴尔和热奈特的见地表现得深入而清晰,对电视剧叙事话语的探讨也更具启示意义。米克-巴尔在其叙事学著作《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用“聚焦”说代替“视角”说,并对“聚焦”这一特定概念加以强调——“我将把所呈现出来的诸成分与视觉(通过这一视觉这些成分被呈现出来)之间的关系称为聚焦”,“‘聚焦’就是视觉与被‘看见’被感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④ 在她看来,通行的“视角”说显得含混不清,而“聚焦”术语则将叙述角度细化到了“谁看”与“谁说”,并表明了它们之间的区别。这一分析,与此前热奈特已注意到的“叙述眼光”与“叙述声音”之分不谋而合。延伸到电视剧文本上看,日剧《阿信》、《铃兰》尽管都采用了“内视角”叙述,但在“叙述眼光”与“叙述声音”的关系处理却有所不同:《铃兰》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叙述者即剧中的核心主人公,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合二为一;《阿信》则采取了第三人称叙述,故事中发生的一切虽是阿信在看、在回忆,但该剧的叙述声音却由不断穿插的旁白、由故事外的叙述者担当,虽然同为“内视角”,但叙述眼光和叙述声音呈分离状。倘继续分析还可发现,同是以第三人称旁白的方式讲述故事、同是叙述眼光和叙述声音各行其是,但电视剧《阿信》和电影《红高粱》在叙述声音的功能显现上却又有所不同。《阿信》的叙述声音由一位超然事外的旁观者发出,冷静客观地引领观众鉴赏;《红高粱》的叙述声音虽也在故事之外、叙述人在剧中也不曾出场,但作为核心人物的后代,叙述声音的发送者却与故事存有一种亲缘关系,且那段故事经由了时光的积淀与过滤,因而具有潜在的情感诱导和感悟生发。
电视剧的话语载体毕竟不同于经典叙事学理论锁定的文学话语对象,因此,在“聚焦”等叙事方位问题上,需要立足于媒介特性予以探求。同时本文也注意到,叙述方位问题,上可追究到与文学叙事学通约的意识形态向度,中可触及形式美学层面的叙述角度,下可具体兑现为机位摆设。这些问题恐怕都是当下电视剧实践对叙事理论的吁求之一。
电视剧的常用聚焦方式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为“非个人化”的叙事,即以第三人称方式间接进行的叙述,借用热奈特1991年问世的重要著述《虚构与行文》中颇具叙事学色彩的术语,即“异源故事叙述”。另一类则是以“个人化”面貌、以第一人称方式直接进行的叙事,热奈特将其称之为“同源故事叙述”。较之先前众说纷纭的“叙述视角”说,笔者以为,热奈特的这一新界说显得更为明晰纯熟、也更切近包括电视剧艺术在内的叙述方位上的聚焦实践。⑤
异源故事叙述,即讲述者不在故事之内、而以第三人称的局外身份向观众叙述故事。应当说,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叙述模式,也是电视剧叙事通常采取的基本叙述方位。沿着热奈特针对聚焦问题的这一新思路,立足于电视剧的文本实践,笔者拟将其深入细化,继续划分为任意视角上的“异源故事叙述”和特定视角上的“异源故事叙述”两种情形。
任意视角上的“异源故事叙述”,意味着电视剧编导以第三人称形式置身于故事之外,手中握有一张随意进入任何一位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获知任何个人隐私的许可证。这种绝对的叙述权力,无疑给编导带来极大的讲述自由。当然,倘再深入分析下去,我们还可以剥离出更为细致的层面并从中发现新的问题。一般叙事学在研究“全知视角”时,常用“全知全能”一说加以阐释,事实上我们发现该说法更适宜文学叙事,且因比较笼统普泛,用作电视剧的叙述视角分析显得不够甚至不妥。
电视剧作为视听艺术直接诉诸观众感官,无须像文字载体的文学文本那样经由读者的大脑进行一番“制式转换”、将文字符号在想象世界中译成视听图像。在电视剧文本与文学文本的诸多不同之中,仅就时空处置、视角开辟而论,文学文本的确享有天马行空的自由,瞬息之间可上天入地,一句话便能并列出不同时空的不同事件。相形之下,就此而言,电视时空展现的具象性,镜头乃至屏幕的局限性,使得电视剧叙事难以企及前者的那般“无所不能”。如《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一书中提到的《战争与和平》里那句“这天晚上法军与俄军都开始准备进入会战”,着实“全知全能”、出于不折不扣的全景视界。⑥ 然而,倘将这一文学的话语制式转换成电视剧的叙事话语制式,用视觉语言、在同一画面中表现托尔斯泰的那句概述,恐怕就变得比较困难,除非采用抽象的旁白方式加以传达;除非分别拍摄法俄两军然后加以蒙太奇组接。然而,一旦分别拍摄问题也就冒了出来:由一组镜头完成的那句概述,其实变成了每拍一个画面相应也就变换一个角心,于是我们也就不能再将这种叙述方位处理说成是“全知视角”了,比较合理的说明应是“不同角度叙述”,再由不同角度的不同所见集合成为“全知”。由此也可以看到,正宗“全知视角”上那种权威性的叙述眼光,在影视中其实很难用镜头加以实现,这也印证了自麦克卢汉主张“媒介即信息”以来,人们为何倾向于认为一种重要的新媒介将改变话语的结构。经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电视剧叙述方位的探讨中,对文学叙事学的借鉴需慎重从事,需从电视剧话语的本体特性出发,因此,本文在分析电视剧故事的镜语呈现中,采用任意视角上的“异源故事叙述”来取代文学叙事学当中谈论较多、流行甚广的“全知视角”界说。
综观电视剧的艺术实践不难看出,任意视角上的“异源故事叙述”,是电视剧叙述方位的主流形态。以《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核心人物石光荣的塑形为例,当编导透视石光荣那种一意孤行燃烧着光荣与梦想的内心时,通常没有取“零聚焦”方式、置身事外地向观众做中立描述,而多从次核心人物褚琴的嗔怨目光、从配角石林的怨恨心态,通过经常变更切换的一个个任意视角加以表现。换言之,该剧编导更多时候并非用自己的全知眼光观察剧中的人与事,而是尽量转用剧中人物的特定视角去表现故事世界。总之,采取任意视角上的“异源故事叙述”,剧编导可从不同角度、借不同时空展示故事,可以熟稔人物的从前、也可预知角色的未来,能够不存顾虑地深入审视人物的内心。
在某些为数不多、传记色彩浓郁的电视剧叙事中,虽也保持了与任意视角上的“异源故事叙述”相同的第三人称叙述,但剧编导并不经常转换视角,而多从剧中特定人物的角度出发讲述故事,采用的是特定视角上的“异源故事叙述”,显现出叙述视角相对稳定的特点。日剧《阿信》就比较典型地起用了这一叙述视角。剧中几乎所有的事件、人物、形象、景致,均透过阿信的眼睛与心灵去观察、感受,无论核心人物阿信的漫长一生亲历了多少悲欢聚散、沧桑变故,均经由了阿信的情感过滤和观念筛选,而剧编导则以第三人称旁白形式发出叙述之声。电视剧《月亮背面》亦然,也采取了这种特定视角上的“异源故事叙述”。故事基本上以第三人称画外音形式贯穿,从主人公牟尼因犯重罪被关进死囚牢、在死前一日的追忆里展开。
这种特定视角上的“异源故事叙述”,特别有助于叙述过程中悬念的形成。视角上的局限性,反而可以转化为一种从积聚到释放的美学势能,可将原本早该大白于天下的真相、将早该告知观众的谜底自然而然地搁置起来,当人物在场时、当故事展示水到渠成时,再让牵动观赏兴致的那张底牌水落石出。如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晶与胡达凯深深相爱而天各一方,剧编导有意从石晶的有限视角去写对方的突然下落不明,将观剧注意吸引到石晶爱而不能的痛楚上来。这种视角上的有限性,自然地将胡达凯战场归来、无法以残缺之躯面对完美的爱情,不惜以消失人间的方式逃避石晶的遭遇悬置起来,变成了观众心头一个焦灼的谜团,一种揪心的悬想,变成了“欲知后事”的观剧期待,为7年后旅途上二人的意外相遇做足了铺垫。
从自我的视角出发、以第一人称方式进行的回顾性叙述,可谓之“同源故事叙述”。同源,即指叙述主体处于故事之内,充当着剧中的某个角色,且大体上既属于故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又是故事本身的叙述者。在这种叙述语境下,绝对的公允叙述是不存在的,因为置身其中,叙述自会夹带叙述人这样或那样的褒贬好恶。倘深入观察还可以发现,目前在“同源故事叙述”类型的电视剧文本中比较普遍的那个“我”,通常担当着核心人物之职。就是说,第一人称“我”即剧中主人公。换言之,在小说实践中常见的第一人称“我”出演次要角色的情形在电视剧实践中则比较少见。如阿城的小说《棋王》中,“我”不过是故事中的一个配角,仅以一个思者、一个讲述人的角色去打量那个神秘主人公。电视剧中“同源故事叙述”的典型个案可推《大明宫词》,全剧的叙述声音基本上以太平公主的第一人称旁白贯穿,以自传形式和回忆语调讲述情感与权力纠葛的一生。
二、叙述方位的聚焦谋略
上述常规聚焦方式,在电视剧实践中其审美功效自是各有短长。如特定视角上的“异源故事叙述”方位,其长在于叙述视角相对稳定、故事展示清晰易懂,但所长亦所短,若把叙述视角钉死在某种特定方位,观众一集集看下去不免单调。在动辄二三十集的电视剧叙事流程中,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叙述方位是不可取的。反之,虽处于较为灵动的“任意视角上的异源故事叙述”方位,尽管享有莫大的讲述自由,但第三人称毕竟是局外人身份,毕竟缺失了第一人称的亲和之感。若要摆脱上述叙述视角上的局限,不妨有意识地破一下成规、自觉尝试叙述视角的多重设置和自由切换,甚至走出叙述权力的自我限制进行越位实验。
笔者设想,倘在第一人称“同源故事叙述”的基本叙述流程中,根据故事所需,得体地转移聚焦、阶段性地将其切换到第三人称的特定视角上去,故事景观当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故事叙述将变得富于弹性,人物塑型也会因注视目光的变迁而愈显生动。倘对日剧《铃兰》施以类似处理,从故事传达的丰富性上考虑,叙事效果将有可能更上层楼。换言之,从原先的第一人称跨到第三人称、从颇多局限的“同源故事叙述”移向游刃有余、自由伸展的“异源故事叙述”方位,可使故事的讲述更具弹性。反之亦然,在绝大多数的电视剧叙事中,尽管在整个故事叙述流程中基本坐定“异源故事叙述”方位、基本上以第三人称讲述故事,但为了同观众缩距、调节叙事效果,不妨也尝试换位策略,以第一人称的“我”之身份,从“个中人”的经验视角,以更具亲和力的方式,零距离、富于情感色彩地呈现故事。
在聚焦谋略的具体实施上,电视剧《青衣》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个案依据和文本启示。
从叙事方位这一维度上看,《青衣》中一个十分抢眼的特征,就是在电视剧审美实践中走出了一条超常规路线。该剧基本上采用了特定视角上的“异源故事叙述”方式,从核心人物筱燕秋的视角将故事一一抖开。由于《青衣》以展示不同的内心世界见长,为了达成这一叙述目的,编导在叙述方位上,超常规地兼容了多重视角设置和不同视角转换的叙事策略,即从一个个特定视角不断向第一人称有限视角逐一转移,由“他”而“我”,由“我”而“她”,从而形成了复杂多变的聚焦效果。在《青衣》的故事讲述过程中,编导虽然把人物展现的主机位对准了剧中核心人物筱燕秋、但在组织故事时并不拘泥于这一特定视角,正如我们在剧中看到的,编导不时地将叙述眼光和叙述声音交给另外的几位重头形象、或者说次核心人物,比如,交给在艺术和现实的纠葛与撕扯中矛盾重重的京剧团长乔炳璋,由乔炳璋之眼去看四代青衣的心性与命运;比如,时而又把叙述视角托与那位在追忆梦想和追逐红尘中灵魂分家的烟厂老板郑安邦,从他的经验视角、以迥然不同于筱燕秋、乔炳璋的观点和口吻看世间的男人和女人,看人的幸与不幸。从修辞实效上看,当第一人称叙述者以“我”的真切目光和“过来人”的心态传达故事时,观众可零距离地触摸人物细腻、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而保持审美接受上的亲和感。
《青衣》中对核心人物筱燕秋的处理尤见出编导的聚焦匠心——从古典气质的第一代青衣柳如云的视角看去,筱燕秋是个百年不遇的青衣、是她柳如云夭折的艺术梦想的传人;在功利世俗的第二代青衣李雪芬眼中,筱燕秋则是她在名利场上的克星、是阻碍她欲望达成的天敌;在第四代青衣春来那个到处是实用算计、美与灵魂没有位置的小小世界里,她的筱燕秋老师是个除了舞台什么也不懂的怪物、一个不明智的落伍之辈;而在丈夫“面瓜”心里,筱燕秋则是近在身边、远在天上的嫦娥、是他生活中永远的谜。可见,不断转换的视角有意将筱燕秋的形象打散,抛洒在《青衣》的整个叙事时空当中,观众在观剧时再将这不同视角上的印象散片一一收集起来,凭借自己的审美想象、审美判断将其完整组合。而视角的这种频繁转换与组合,基本上依照了美丑对照、彼此反差,以提升审美张力的原则。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一剧中龙小羽死前的重场戏,也有很好的视角转换处理。在回放龙小羽与祝四萍贫困而温暖的爱情时光时,导演有意从律师韩丁的视角去展现,由一个与其有爱情纠葛的当事人、一个曾从枪下救过对方性命的律师、一个纯情、浪漫、慷慨的性情中人,由这样一个人去想象当初的一幕又一幕,如此处理,既打破了幻象构织与实景再现的分界,又通过观众可以接受的渲染与夸张表现了龙小羽的悲剧命运。
如果说上面的聚焦谋略侧重于视角的腾挪变化,那么下面着力探讨的问题则是视角的越轨行为。视角越轨是经典叙事学理论较少触及的一个课题。就是说,为了克服既定视角上的局限性,为了意义传达的深度化和美学传达的高品质,剧编导不妨以更为超常规的叙述魄力,让原本不在场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理直气壮以目击证人的身份去展示那种并未亲眼目睹的事件,让第一人称的“我”适时地摇身一变为无所不知的“他/她”,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的违规叙述,“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借助大胆的叙述行为吁请观众留意电视剧文本的虚构性,诱导观众成为编导的艺术同谋,一起从新的界面上注意文本的意义内涵,从而实现审美价值的最大化。
《青衣》的视角越轨行为表现得甚为鲜明。那位在剧中偶尔现身、筹划拍摄青衣故事的编导“大胡子”,在剧终时突然闯上前台,从先前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上跳脱出来,堂堂正正以第一人称“我”之身份、颇具元叙事意味地亮出了《青衣》底牌,对全剧、对剧魂进行点化和升华。视角越界恰恰表现于此,因为故事中的诸多事件发生之时,诸多人物行动之时,那位胡子并不在场,他并不是一位真实的目击者,他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故事评点其实是一种叙述上的越权行为。或者说,胡子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其实采用了上帝的眼光,他站在颇多局限的第一人称有限视角,但他的所见所闻所知却分明出于自由自在的任意视角。该剧编导的这种视角越界行为是对叙述通则的忽视还是无视?显然,从修辞实效上观察,这是《青衣》的有意为之,是叙事上的绝妙之处。透过这一特意设计的视角越界行为,编导既可以利用第三人称的任意视角自由地洞悉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又可借助第一人称的传达优势同观众缩距。而观众呢,在突然变化的新视角刺激下,则可强化对《青衣》意蕴、对命运人生的领悟。可见视角越界又是实现“陌生化”审美接受效果的一种修辞策略。
总之,如前所述,叙事方位的选择、调整抑或越界,不单建构着不同的故事形态,且也关涉意义的不同生产、影响着价值情感的流向。就像我们在观看描述动物世界的大量纪录片时所感受的那样,当编导和摄像从狮虎等生物链高端的动物族群的视角拟人化地描述它们时,随着叙述进程观众开始了解它们,在审美接受上也逐渐会产生情感认同,于是,当出现狮虎捕杀弱小猎物的镜头时,观众更关心的常常是它们能否捕获成功、嗷嗷待哺的小狮虎能否有食物果腹,而在此时,被它们吞食的弱小动物一方却往往不大引发观众的恻隐之心;与之相反,当描述视角转换到弱势的动物族群一边,从处于生物链低端的弱小动物的感受角度去记录、去呈现时,透过镜头看它们如何被狮虎追逐、撕裂,看弱小动物的母亲明知不能、却仍拼死救助自己的幼仔时,此时也处于弱势动物视角上的观众则会产生出不忍之感。可见,作为话语方式之一的叙述视角的选择,对意义的生成具有明显的催化作用。换言之,叙述方位的常规设立乃至聚焦谋略,包含了述行与意义的双重建构。
注释:
①②[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48页。
③兹维坦-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叙述学研究——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④[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⑤[法]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11—112页。
⑥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标签:电视剧论文; 电影叙事结构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阿信论文; 叙述视角论文; 铃兰论文; 第三人称论文; 青衣论文; 叙事学论文; 第一人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