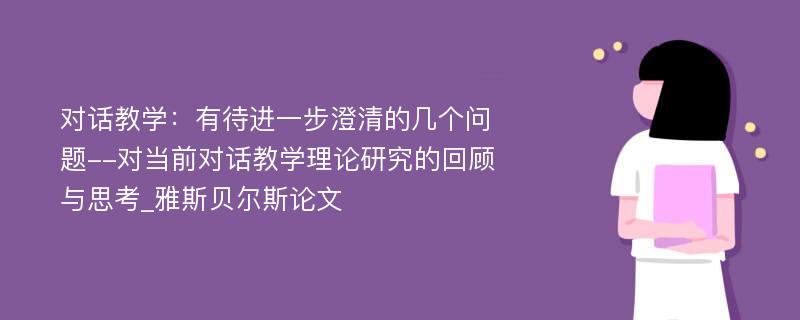
对话教学:有待进一步澄清的几个问题——对当前对话教学理论研究的审视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0)07-0026-05
近年来,对话教学成为教学论关注的焦点。人们一方面猛烈地批判传统的“独白式”教学,另一方面则极力倡导和主张对话教学,并对对话教学进行了全面的、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教学论有关对话教学的研究当然有助于我们深入地思考和理解教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然而,现有有关对话教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以及试图将对话教学普遍化的理论旨趣,有把对话教学神化的趋势,仿佛教师只有在课堂中进行了对话教学或者教学对话,则有关教与学的问题就能够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现有的有关对话教学的研究并没有意识到,任何一种教学范式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都有其有效运用的前提条件。超越了这个适用范围和运用的前提条件,则这种特定的教学范式就可能会走向人们所期望的反面。对话教学也不例外。不弄清楚对话教学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就有可能导致人们在教学实践中对对话教学的误用,从而引发更多的实践问题。
一、对话教学研究的非辩证性问题
任何一种新的教育主张都是针对特定的教育现实及其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对话教学当然也不能例外。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对话教学是针对独白式教学所存在的弊端而提出的。现有的研究表明,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文化和观念:或是把教学过程主要看作是教师“独白”的过程;或是把教学过程看作是师生“对话”的过程。前者把教学看作是单向的关系,后者则把教学看作是双向和互动的过程,师生对话是教学过程的核心环节,对学生学习实践产生重要的引领作用。[1]与独白式教学相比,对话教学体现了介入的态度、平等的关系,既是认知的方式,也是生活的方式。“对话”式教学通过“商谈”,通过共通感的获得或理解能力的养成,使教学中的人共同面对与承受生活的艰辛与苦难,共同分享生活中的愉悦与悠闲。[2]各种有关对独白式教学的批判以及对对话教学的提倡包含着对诸如师生平等、自我实现、共同分享、主动参与、双向互动等特征的推崇。在对话教学的提倡者看来,独白式教学环境下的师生关系一定是不平等的、强制性的、被动性的,因而都是需要加以清除的;反之,就一定是好的,是能够促进学生的自我发展的。
从思维方式上看,上述有关对话教学和独白式教学的阐述都秉持一个思维方式,即对教学问题的思考呈现出非辩证的思维特征,而没有看到,无论是对话教学还是独白式教学,都有其可取之处,也都有其力所不能及之处。当雅斯贝尔斯把教育的类型划分为经院式、师徒式和苏格拉底式三种时,[3](7)作为哲学家的雅斯贝尔斯已经看到了不同类型的教育各自具有的优势与独到之处。经院式教育的传授知识、师徒式教育的提高自我意识以及苏格拉底式教育的唤醒学生的内在自动力量,都各有其适用的对象与范围。相比较雅斯贝尔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对话教学理论研究上所存在的片面性与非辩证性。
我们不能不承认独白式教学存在弊端和不足,尤其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及教学参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能不承认独白式教学环境下的学生呈现被动学习的特征。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在我们看到独白式教学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和弊端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独白式教学所具有的长处。倘若独白式教学毫无益处可言,那么我们就很难解释这种教学范式作为一种传统而被延续至今,同时也很难解释在极力主张对话教学的理论语境下,独白式教学仍然盛行于我国课堂教学实践中。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对话教学在拥有它的优点与长处的同时,它是否也有其内在的不足?其不足又是什么?倘若人们看不到对话教学内在的不足,那么对话教学极有可能被神话化,这既不利于对话教学的开展,也不利于人们在教学实践中把握独白式教学的合理内核。
独白与对话,有形式意义上的,也有内容意义上的。无论是基于交往行动理论还是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对话教学的形式与内容是密不可分的。诚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教学中的对话有三个层次:学生与客观世界(文本)的对话,其目标是建构文本的意义;学生的自我对话,其目的在于重建自己的内部经验;学生与他人的对话(师生对话和生生对话),其目标在于关系的建构与理性的发展。[1]仅从形式的角度看,唯有第三个层次的对话,我们才可以看作是对话教学,因为只有在学生与他人的对话中,我们才观察到真正的互动关系的出现。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而否定第一第二个层次的对话特征。实际上,即使是在独白式的教学中,学生对于教师独白的精神与心理的参与,往往是旁观者所无法观察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由此否定说学生就没有参与到与教师的对话之中。就人的精神塑造而言,一种内隐的对话往往远甚于直接的语言对话。当某人在倾听一场学术报告,并且不断思考着报告者所提出的学术观点时,报告在形式上是独白的,然而这不能由此而否定听报告者确实与学术报告者在进行着一场对话。在日常的生活中,电视观众与电视节目的关系,可以说是典型的单向的、独白式的关系。而电视观众之所以能够热衷于某个电视节目,恰恰在于因情与心的投入而产生的内隐的对话关系。没有这样一种对话关系,观众是不可能长时间地关注某节目的。
好的独白式教学内隐着对话,而不好的对话教学可能不过徒具对话的形式而已。真正的对话是心与心的沟通,而不仅仅是直接的语言“对白”。在现代教学组织形式的环境中,师生在课堂里的任何对话都有可能使得其他人成为旁观者,从而使得所谓的对话教学只是在教师与少数几个学生之间展开。即使如有的研究者主张在学生之间展开对话,这种对话的范围与对象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否则对话教学就极有可能演变成无主题的“七嘴八舌”。
二、对话教学研究的理论取向问题
对独白式教学的贬低以及对对话教学的褒扬,暗含着某种特定的教育价值观念。独白式教学基于理性传统,注重知识传授。在独白式教学中,知识乃是终极性的价值载体。受教育就是要获取知识,并由此而实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而对于对话教学来说,人成为最终的目的。人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发展、人的生命意义而非人生意义成为根本性的追求。就两者各自价值追求而言,对人的现实生活来说,两者各有其合理性,也各有其适用的对象。就服务于特定的教育价值取向而言,不管对话教学是作为一种教学策略,还是作为一种教学原则,甚而如一些研究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教学精神,其本身的性质即设定了其发挥作用的范围。然而,从对话教学的理论取向来看,目前对对话教学的教育价值取向莫衷一是,从而使得对话教学的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时面临含糊性和多义性的问题。大体而言,有关对话教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涉及两种,即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和交往行动理论。
存在主义哲学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以人的选择自由为归宿。个人作为一种存在,通过作出通向真实性的选择来创造其生活的意义,人不应该是沦为他人的客体或工具。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不应该是“我—他”关系,而应该成为“我—你”关系。其基本内核是“选择的自由”。在这样的前提下,对话成为人们交往的首要选择,并且成为教育的核心元素,“教育中的关联是一种纯粹的对话”。[4]对话不仅是说与听的方式,而且还是寂静中相互接受的一种方式。在各种有关对话教学的理论研究中,“我—你”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什么是“我—你”关系?布伯说,“我—你”创造出关系世界,这种关系世界呈现了三重境界:人与自然相关联的人生,人与人相关联的人生,人与精神实体相关联的人生。三重境界都与语言或言说纠缠在一起:第一重关系居于语言无法降临的莫测深渊;第二重关系具语言之形,可公开敞亮;第三重关系则无可言喻但创生语言,“在这里,我们无从聆听到‘你’,但可闻听遥远的召唤,我们因此而回答、构建、思虑、行动。我们用全部身心倾诉原初词,尽管不能以口舌吐出‘你’”。[5]这已经不是在思考现实中的“我—你”关系,而是本体的意义上的“我—你”关系,是在一种神学的立场上来讲“我—你”关系了。然而,持这种立场的对话教学的理论研究者们大概没有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即作为“我—你”关系倡导者的马丁·布伯,究竟持一种怎样的哲学立场,并且布伯为何要主张人与人之间的“我—你”关系。在并没有弄清楚布伯哲学思想的内核的情况下,就将他的“我—你”关系移植到对话教学中来,这本身是否意味着一种望文生义或者是武断呢?雅斯贝尔斯也同样主张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不过这种对话的目的意在唤醒学生,促进学生的自觉发展,其最终的取向仍然是人的自由。
基于交往行动理论基础的对话教学,以交往行动理论的交往理性为出发点,以理解与对话为中介,以共识和社会秩序的整合为归宿。尽管哈贝马斯将人类的行为划分为四种类型:目的性行为、规范性行为、戏剧性行为和交往行为,但只有交往行为才是合理性行为。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有四个功能:一是理解的功能,有助于把握知识;二是合作的功能,使社会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实现社会的目标;三是社会化功能,即能够使个体认同社会规范和价值取向,从而有助于形成某种价值导向;四是社会转型功能。然而,必须要看到交往行为是基于两个基本的前提而存在的,第一个前提是交互主体的概念而非主体的概念,第二个前提是文化多元主义,即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的个人和团体所接受的不同的观点”[6]。当哈贝马斯从独语的反思走向对话的转换时,这种转换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在中国的教学实践语境中是否能够得以保持,显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由此,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即不同的哲学理论所提倡的“对话”有着不同的含义。主张对话的存在主义与交往行动理论实际上有着不同的旨趣,是为了实现各自不同的理论目的而提出的哲学主张与社会主张。对于古典哲学来说,对话如苏格拉底的对话意在发现真理和认识自我。就存在主义教育哲学而言,对话教学的核心追求在于通过确立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从而使得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不至于沦为他人意志的工具,成为一个自由的存在者。而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交往行动理论,其对话或商谈的目的在于人们就公共生活的重要问题达成共识,从而促进一种和谐有序社会的形成。现有的对话教学的理论研究,将各种不同理论前提的“对话”概念引入教学之中,不仅没有促进教学范式的改革,促进教学由独白走向对话,反而使得对话教学陷入庸俗化的理解之中,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的理论体系所主张的对话教学,是基于不同的主体概念而派生出来的教学主张。“存在”的概念与“交互主体性”的概念,并不同于与客体相对应的主体概念。由于不同的理论主张预设了不同的主体概念,而在日常的教育生活中,居于客体地位仍是学生的真实存在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虚假的对话教学之出现甚至是流行便不难理解。
三、对话教学研究的适用范围问题
在有关对话教学的理论研究中,人们赋予了对话教学太多的意义和价值,并尽可能地将美好的词汇归于对话教学。有学者指出,对话教学的认识论基础是知识的探究性、社会性与个人性。三者的融合即为“尊重个性差异的合作性探究”。这正是对话教学所追求的境界——知识、教学与民主彼此重合且化为一体。[7]并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系统确立的“主体哲学”及相应的“主体教育学”有助于突破神祇膜拜和专制统治。但是,启蒙理性的主客二元对立性又使“主体教育学”产生强制性和压迫性,使得人的解放的任务并未完成。有鉴于此,20世纪以来的诸多教育思潮和改革运动,旨在超越启蒙理性,实现教育“新启蒙”。“关系教育学”和相应的“对话教学论”因而成为教育中的时代精神。创造与变革、丰满人性、批判性民主等关系价值是对话教学的价值追求。在此时代背景下,我国“学生主体说”、“教师主导说”、“讲授教学论”三位一体的教学观需要根本超越。[8]这样的取向单纯地从价值的立场看并无问题。且不论对话教学是否能够真正地实现知识、教学与民主的重合,单就“合作性探究”是否能够做到“尊重个性差异”,也有待作更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在整个社会都注重共性与同一性的背景下,单单依靠学校教育的努力是否就能够实现这种对个性差异的尊重,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对话教学所欲超越的对象也确实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思考对话教学的适用范围,需要认真研究和确定对话教学的前提条件。
第一,对话教学有其独特的价值追求。雅斯贝尔斯是倡导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教育的教育家。但恰恰是雅斯贝尔斯就对话教育所发表的观点,对于我们反思对话教学的价值追求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全部教育的关键在于选择完美的教育内容引导学生面向事物的本源,因而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不是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通过教育使具有天资的人自己选择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由此雅斯贝尔斯提出,“对话是探索真理与自我认识的途径”。为什么“探索真理”和“认识自我”需要以对话的方式来实现?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真理”与“自我”是无法用语言来直接传达的,而只能通过对话这种形式间接地传达。换言之,教学中的对话是借以传达无法用语言直接传达的东西的。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可以用语言来表达。而某些事物的语言不可表达性正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了独白式教学的不足。雅斯贝尔斯进而阐述这样的主张,即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可以传递的,“如果将知识分类,则可分为现行的知识与原初知识……这两种知识方式的可教性与传递性却不相同。数学、天文学及医学知识的内容与熟练的技能都可以以简单的、直接的方式传递给学生。但是,关涉人的存在本源和根本处境的哲学却无法传递”。[3](8-17)不能直接传递的哲学,就只能通过间接传达的方式来实现。这就是雅斯贝尔斯极力推崇苏格拉底的理由之所在。恰恰是苏格拉底所主张和实践的辩证法,赋予哲学教育以现实的可能性,从而也使得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成为人类教育追求的最高境界。
第二,对话教学以知识的不可传递性为前提。如果对话从根本上是要解决知识的不可言传性问题,如果我们承认对话教学有着独白式教学所无法替代的优越之处,那么,知识的语言可表达性是否也意味着独白式教学的独特优势呢?从根本上讲,对话是一种不断地追问与面对追问的回答与回答过程中的困惑。然而,追问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教师对学生的追问以及面对追问者的尝试性回答;另一种是学生的追问以及学生追问后的教师回答。苏格拉底式对话立足于求知与真理,教师不断地追问,揭开对真理的遮蔽,从而引导学生走向真理的本源;而孔子的对话式教学则立足于践行与道德,学生向教师的提问意味着道德实践中的困境与困惑;唯有学生在行动中遇到困惑时,教师的解释或提示才能够发挥直接的实践指导作用。
第三,对话教学设定了主体要求。根据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本真的传达仅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这种传达并不向所有的人敞开,而是选择那些具有敏感性质的人作为传达者。”[3](19)倘若我们承认这个论述的某种真理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真正的对话教学并非是所有的教师都能够胜任的,是否意味着真正的对话教学并不是能够在所有的学生中间展开的?而课堂教学的现实似乎也在或多或少地验证着这样的论述——无法真正有效展开课堂对话教学的教师以及在对话教学中的部分学生参与。理论的洞见以及实践的经验都在昭示着一种对话教学的困境,即教师与全体学生进行教学对话的实践可能性问题。对话教学的理论研究者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对话教学”上,而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考虑到对话者这个根本性的条件。柏拉图在《美诺篇》中叙述了苏格拉底通过反复追问质询引导一个奴隶获得对几何问题的解决,[9]尽管这个事例表明了用对话的形式可以辩明真理,但同时也暗示了通过对话辩明真理所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对话的个体性以及对话者的敏感性——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的存在。同时,我们还必须要看到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及其对对话教学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教学可能面临的困难。正如伯姆所说的那样:“总有些人试图表现自己,……其他人则没有如此优越的自我感觉,他们倾向于退避三舍,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已经有人在唱主角的时候。”[10]
第四,对话教学在“我—你们”的关系中的无意义性。对话教学的后一种困境不仅与对话教学所指涉的内容与目的追求有关,而且也与当下的教学情境密不可分。必须要注意到,在班级授课制下,师生之间所谓的“我你”关系乃是一种理想的师生关系。从事实的层面看,课堂教学中真正的师生关系乃是“我”与“你们”的关系,或者是“我—你们”的关系。就前者而言,所谓的对话不过就是意义的传达与交流。如此,则对话教学不过是独白式教学在形式上的一种转换,而其精神与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就后者而言,教师所面对的,是一个学生集体,是一个集合体,既非存在主义哲学意义上所谓的个体,也非苏格拉底或孔子所面对的独特的个体。在“我—你们”的情境中,所谓对话教学的有效性,对话教学所要实现的目标,不可能不受到相当大的约束和限制。现代对话教学的提倡者只是看到了存在主义哲学所确立的“我—你”关系,而没有看到这种“我—你”关系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的难以确立。当然,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而使教师所面对的“你们”转换成“你”,而实现这种转换,最为根本的,乃是关注学生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