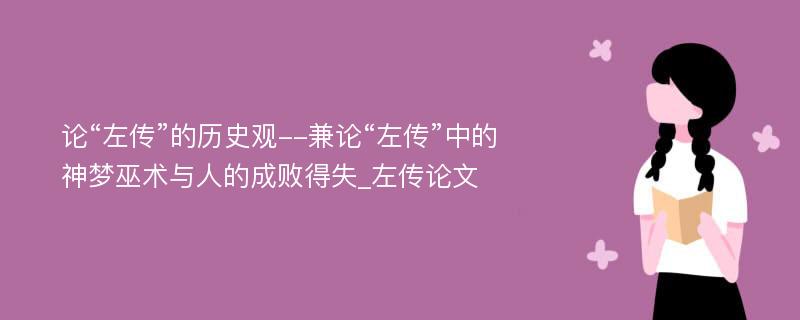
论《左传》的历史观——兼论《左传》神梦巫卜及以成败论人的本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传论文,历史观论文,本质论文,成败论人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以“天德合一”为基础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历史观
凌稚隆云:“《左传》为文章之冠,……而说者往往病其诬,……其所纪妖祥梦卜鬼怪神 奇一一响应,似属浮夸。然变幻非可理推,古今自不相及,安知事果尽诬,非沿旧史之失耶 ?惟是专以利害成败论人,故先为异说于前以著其验,此朱子亦得以大病訾之尔。”[1]按凌 说 提出了《左传》历来最受人病訾的两点:一是妖祥梦卜皆验;二是专以成败论人。但同时又 指出,其妖祥梦卜之事未必是作者所自创,可能沿诸前史;作者所以取之,乃作为成败论 人的证据。笔者以为,凌说有理。详考《左传》就会发现,神梦巫卜与以成败论人,实是作 者对其以“天(神)德合一”为基础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历史观诠释的必然结果 。
详析《左传》可见,其历史观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是历史变易论。认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历史就是不断的改朝换代史。此思 想代表言论见于《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谈鲁季氏出其君: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 ,何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 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 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 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於今为庶,主所知 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爱子也 ,始震而卜,卜人谒之,曰:‘生有嘉闻,其名曰友,为公室辅。’及生,如卜人之言,有 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 业,不废旧绩。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嫡立庶,鲁君於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 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史墨在评论季氏出其君之事时,不同情君,反赞许臣,其根据主要有五:1.“季氏世修其 勤”、“鲁君世从其失”的道德。2.“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自然法则。3.“三姓之后, 于今为庶”的历史依据。4.“雷乘乾曰《大壮》”的天道原理。5.季友生而有文在手及“为 公 室辅”等神学预言。即无论从天道、地道、神道、还是人道讲,季氏出君都是合情、合理、 合义、合法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历史就是不断的改朝换代史。
二是历史不变论。即虽然朝代更替,江山易主,但统治思想和制度——德礼却是永久不变 的。代表性论述见于《昭公二十六年》晏婴与齐侯论德礼保国:
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敢问何谓也? ”公曰:“吾以为在德。”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有施于民。……陈氏而 不亡,则国其国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对曰:“唯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 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礼之可以 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 …”“……先王所禀於天地,以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这段话中“礼之可以为国者久矣,与天地并”说明,晏婴(亦即作者)认为,无论历史怎样 变迁,但都是万变不离其“礼”的。过去的先王遵循此理(“是以先王上之”),今后也将永 远如此,礼将与天地并存。
三是神学目的论与道德目的论统一。即认为历史是天命神意为实现其“美善”道德而进 行的有意识的活动。以季氏出君论,其行为既是“雷乘《乾》曰《大壮》”的“天道”认可 的, 也是“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的道德决定了的;还是在母腹中就被神灵指派“将为 公室辅”的神意早就定下了的。即鲁国历史的发展,君弱臣强的局面的形成,是天命神意与 人之道德一致合力作用的结果。
总之,《左传》这一历史观认为:历史上没有固定不变的君臣关系,没有永保天下的社稷 之主,天命依德立君;历史就是不断的改朝换代史。但“德礼”是永世长存的。谁守德礼, 谁就会得到天命的眷顾,历史的青睐,自然的赐予,人民的支持;就会保天下,得国家, 即上引文说的礼可以防止政权被颠覆(“唯礼可以已之”),可以使社会安定、人际关系和谐 (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反之,不守德礼,将迟早会被赶下历史舞台。
显而易见,《左传》这一历史观,必然导致对既成历史事实的肯定,否则,他便无法解释 历史是怎样按照天(神)德合一轨道运行的。这就是凌稚隆说《左传》“专以利害成败论人” 的真正的、本质上的原因。
《左传》所记历史为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68年。这一段历史时期中,虽然以下僭上已极 为普遍,弑君夺位屡见不鲜,但权力转移尚只是在宗族内部甚至家族内部进行,社稷易姓尚 未有之。不过这种主弱臣强的时代大势已经拉开了不久的将来诸侯之国江山变姓的序幕。以 “天(神)德合一”愿望看待历史、社会、人生的《左传》,必须对导致这一历史巨变的春秋 时代种种有关历史现象及整个过程作出合乎其历史观念的理性解释。“妖祥梦卜鬼怪神奇 一一响应”,以及“是以成败论是非”[2],实乃是《左传》历史观导致的必然结果。
《左传》说:“左氏有绝大线索,於鲁则见三桓於鲁终始,而季氏尤强;於晋,则三晋之 局蚤定于献公之初;于齐,则田齐之机蚤决于来奔之日,三者为经,秦楚宋卫郑许曹邾等纷 纷皆其纬也。”[3]“春秋之局,凡三变:隐桓以下,政在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 哀以下,政在陪臣。”[3]这些议论可谓抓住了《左传》(也是春秋历史)的神髓。季氏、三 晋 、田齐,僭诸侯者也;齐桓、晋文,霸主之事,僭天子者也。所以,抓住《左传》对季氏、 三晋、田齐这些“僭主”的看法,就是抓住了《左传》历史观的关键。
二、为“僭主”提供神学依据
韩赵魏三家瓜分晋正式成为诸侯,是在公元前403年,乃作者亲睹之事实。当时魏最强大。 魏文侯师事孔子弟子子夏等,用西门豹治邺,以著名军事家吴起守西河、拒秦韩,用李悝作 尽地力之教,鼓励耕作,“贤人是礼,国人称仁”[4]。魏是《左传》成书之时天下最强国 之一,战国前期曾一度霸诸侯。就《左传》作者所眼见形势看,魏当是诸侯中最有光辉前途 者,因此他对魏抱有很大期望,所以分晋的三家中,预言主要指向了魏。
《左传》关于魏的神谕有两条,第一条是:“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毕万为右,以 灭耿、灭霍、灭魏。还,……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 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 ,其必有众。”人名地名,都成了毕万之后必将昌大的谶语。卜偃认为,“万”是个满数; 魏,是高大意。天子统治百姓之数称兆民;诸侯统治百姓之数称万民。封地高大与象征着诸 侯之民的满数相随,所以毕万之后必将得众。第二条是追记毕万始仕晋时的占卜:“初,毕 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 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 ,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辛廖认为,毕万筮得的《屯》变成《 比》之卦是公侯的卦象,因为屯坚固,比,进入,而屯卦震下坎上,比卦坤下坎上。震为车 、为足、为长男,坤(即土)为马、为母,坎为众。所以,从卦象上看,震变成了土,就是车 子跟随着马,两足踏于其处,有兄长的抚育,母亲的保护、大众的归附,能集合众民固守之 ,有惠有威,能生能杀。因而是预示着毕万之后代将来必将回复到其祖先毕公高的地位,成 为 诸侯。
此二则预言均记于公元前661年,距魏分晋的公元前403年尚有258年。即《左传》暗示:毕 万 子孙必将成为诸侯的命运是早在两个半世纪之前天命就定好了的。若参照《庄公二十二年》 的“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对田氏未来取代齐 国的卜筮结果,再参照《闵公二年》的“季氏亡,则鲁不昌”,“同复于父,敬如君所”等 对鲁季氏的神学预言,便不难见出,《左传》为“僭主”制造神学依据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 。当然,这些预言不一定就是作者编造的,或许有原本就在历史上流传的,但作者把它们郑 重其事地写进史书,并且让它们与未来的历史发展形成因果对照,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英 国历史学家卡尔说:“过去有这样的说法,‘事实本身就能说话’,这一点当然并不真实。 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 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5]《左传》让战国时代先后取代了或背 叛了自己国君的僭主的祖先以种种天命预言登台表演,并对此进行渲染和夸张,其主观意 图无非是:这些僭主行为是上承天命的,他们不过是执行“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上 天命令而已。而这也是作者以“天德合一”思维解释历史的一个必要步骤。
三、为“僭主”提供道德依据
《左传》为三家分晋提供的道德依据主要是从三方面进行的,一是晋公室德衰;二是诸大 族强横自蹈覆辙;三是三家德盛。
下面分而述之:
1.公室德衰。《左传》首先认为,晋公室之衰主要在于公室自身的道德缺失。昭公三年作 者借叔向之口云:“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 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政在家门, 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谗鼎之铭曰:‘昧旦不显,后世 犹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这里,叔向提出了晋公室卑微的原因:君主道德堕落、腐 朽不堪;不知恤民,只知享乐;军备废弛,民不聊生;“民闻君命,如逃寇仇”,已失去统 治基础。
为了表现公室德衰,作者在写国君为收回权力而与强卿权臣的矛盾冲突中,采取了贬君扬 臣,将不义归于君的作法。最明显者是对晋厉公被弑的态度。《成公十七年》载:“晋厉公 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杜注:“外嬖”为“爱幸大夫”, 所言甚是。观下文“胥童以胥克之废也,怨郤氏,而嬖于厉公。”“郤犨与长鱼矫争田 ,执而梏之,与其父母妻子同一辕。既,矫亦嬖于厉公”等,厉公外嬖系指胥童、长鱼矫等 人。晋厉公时,执政之中军将为栾书,然此时大族尤其是三郤等亦横甚。童书业说:“晋 厉公为一颇图自强之君主,晋国霸业至厉公时已发展至顶点,然衰运亦萌芽于此时。”并认 为,所谓“厉公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是欲集权于君,“使是计划告成,则晋国可能于 此时逐渐转入中央集权官僚制度。”[6]童说有理。鄢陵战前,范文子不欲战,屡发警惧之 言:“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7]鄢陵战胜, 范文子又使祝宗乞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惟祝我,使我 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7]因范氏亦为强族,范文子想以自己的死来免除全族之 难。即他已看出晋厉公在外靖楚患之后,有内图卿族之志。故而试图以楚牵制厉公与群臣和 睦相处。盖范文子亦是以卿族大夫立场出发,欲维持若干大族轮流执政局面。但在外事上 已大获成功的晋厉公不满于长期受强卿大族控制,急欲收回权力。“用其外嬖”是欲建立新 的权力结构,以改变栾郤等大族由于长期处于权力中心而造成的势强逼君的局面。但《左 传》对厉公此举的非议和不满溢于言表,用“侈”、“骄”等词描状,而对弑君之栾书、中 行偃则未多加指责。实际上是把君臣矛盾的责任都归之于国君了,以此作为公室衰微的一个 道德原因。其实,晋厉之所以集权未成反遭杀身,就是因为卿族势力强大。诸强卿利益攸关 ,他们之间虽也有矛盾,但在反对国君削权问题上利益是一致的,故而共同反对厉公。所以 后来悼公改变了方式,提拔一批新人,同时重用旧卿族以安其心,在卿族间搞平衡,分散强 族权力,是以有所成就。总之,晋厉公集权的失败,究其实质说不是道德上原因,而是策略 上 兼认识上原因,使集权未能贯彻到底。面对尚有栾氏等权重势横大族之逼,先自“不忍” 除之[7],结果反遭杀身。
这种贬君扬臣倾向在赵盾与晋灵公的矛盾中亦可见出。《左传》极赞赵盾的德能才干,极 斥灵公之骄奢,对赵盾蒙弑君之名极口称冤等等,都表现了作者为晋公室衰落而终至被分所 寻找的君主所应负的责任。
2.某些强族过于骄横自蹈覆亡之辙。韩、赵、魏三家的对手不仅仅是国君,还有为数不少 的大族。春秋初年,晋献公感到“亲以宠逼”,用残忍手段全部消灭了桓庄之族,终于集权 中央。骊姬之初,又于神前诅畜群公子,自此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又“宦卿之嫡而为之 田,以为公族;又宦其馀子,亦为馀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馀子、公行。”[7 ]正因为此,晋文公之后再无公室之乱,但异宗异姓大夫渐强。这些大族多立于春秋前期, 主要有狐、先、郤、胥、栾、羊舌、范、中行、知、韩、魏、赵等。随着历史的发展,大 族数量渐次减至十族、九族、七族、六族、四族、三族。大约每二三十年有一次灭族。《左 传》在叙述诸大族之亡时,除个别者外,都较充分记录了他们道德上的过失。以栾氏之亡为 例 。《襄公十四年》记:
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郑司 马子蟜帅郑师以进,师皆从之,至于棫林,不获成焉。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 ,唯余马首是瞻!”栾黡曰:“晋国之命,未是有也。余马首欲东。”乃归,下军从之。… …伯游曰:“吾令实过,悔之何及,多遗秦禽。”乃命大还。晋人谓之迁延之役。栾针曰: “此役也,报栎之败也。役又无功,晋之耻也。吾有二位于於戎路,敢不耻乎?”与士鞅驰 秦师,死焉,士鞅反,栾黡谓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来,是而 子杀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将杀之。”士鞅奔秦。
按:栾氏是晋靖侯之后,晋公室远宗疏族。晋文公时有栾枝,城濮战中将下军。晋景公十 三(公元前587)年,栾枝之孙栾书将中军执政。晋厉公六(公元前575)年,栾书指挥晋楚鄢陵 之战,大胜,次年,厉公欲杀三郤,栾书对郤至的构陷对厉公下决心诛杀三郤起了推波 助澜作用。三郤死,栾书荀偃又共弑厉公。由此可见,栾书在厉公朝之专横。栾书死,子 栾黡为公族大夫。从上段引文可见,此时栾氏虽不居正卿位,但依然专横。此次伐秦之役 ,荀偃为中军将执政,栾黡仅将下军,他竟违抗中军之命,擅自率下军东归,迫使荀偃不 得不命全军撤退,使这一集合多诸国的战争毫无结果。事后,栾黡又将弟栾针单骑入敌而 死的责任嫁祸于士鞅,逼迫士匄驱逐其子。作者认为,栾黡的骄横是栾氏灭亡的主要原因 。故而在同一年(鲁襄公十四年),通过逃亡到秦的士鞅之口,对栾氏灭亡之因作了总结性论 证:
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 ?”对曰:“然。栾黡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 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黡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 没矣,而黡之怨实章,将於是乎在。”秦伯以为知言,为之请于晋而复之。
武子即栾黡之父亲书;栾盈,即栾黡之子。士鞅认为,栾氏必先亡,因其太骄横暴虐了 , 但同时又认为,栾黡虽然骄横,但却可以免于祸难,祸难要在栾黡那德行无缺的儿子栾盈 身上产生,其原因是栾黡尚承受着他父亲栾书布于百姓恩德的余荫,而栾盈则要蒙受他父 亲栾黡恶德所招致的怨恨。这显然是事后对骄横的栾黡没遭祸难,而具备“好施、士多归 之”[7]美德的栾盈却灭族身亡的纯粹的道德上解释;或者说,是道德决定论运用栾氏灭亡 时的自圆其说。作者详录了这个对话,其赞许和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
3.挖掘三家美行,与未来得国联系。如《昭公二十九年》记: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 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 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 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 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 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按:在铸刑鼎问题上,《左传》表现了明显的保守性。《左传》与孔子、叔向等人的立场 一致。《昭公六年》“郑人铸刑书”,叔向就发了一大通议论:“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 辟 ,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 可为矣……”认为把刑法公布出来破坏了西周以来的法度。按叔向说法,西周是本无固定刑 法的,即“临事制刑,不豫设法”[8]的;或即使西周后期有“九刑”,也“似不公布之于 民”[6]的。因老百姓知道刑法内容后,就会丢弃礼义而征引刑书了,对上边就不恭敬了, 就不好治理了。所以,这里《左传》把铸刑鼎当作无德之事与家族的兴亡联系起来,认为主 其事者范氏中行氏将亡。显然,这种联系是牵强的,且不说铸刑鼎公布法律对贵族具有一 定程度的限制作用,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进步措施,只能有助于家国之兴。单单说《左传》所 联系的人上,也有问题。此次晋铸刑鼎时正是魏献子执政,铸刑鼎此等大事,正卿焉能不知 道,蔡史墨不说魏氏将亡,何也?另外,直接“赋晋国一鼓铸,以铸刑鼎”的是赵鞅、荀寅 ,范氏没有参与,只不过刑鼎的内容是早已死去的范宣子所定的,死人应负什么责任呢?史 墨说范氏将要灭亡有什么道理呢?赵鞅、中行寅在铸刑鼎问题上责任一样,为什么偏偏“中 行氏其亡乎”,而赵氏则是“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呢?显然,蔡史墨之言,均是根据 事后的历史结局而重新建立的道德联系。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为赵氏、魏氏开脱的明显用心 。
这种挖掘三家美行以作将来得国依据的事例还有不少。如《昭公二十八年》记:晋祁胜与 邬臧通室。祁盈……遂执之。祁胜赂荀跞,荀跞为之言于晋侯。晋侯执祁盈。祁盈之臣曰: “钧将皆死,使吾君闻胜与臧之死也以为快。”乃杀之。夏六月,晋杀祁盈及杨食我。食我 ,祁盈之党也,而助乱,故杀之。遂灭祁氏、羊舌氏。上文中祁胜、邬臧,杜注:“二子, 祁盈家臣。”即祁盈家臣祁胜与邬臧相互与对方的妻子通奸,对此淫纵行为,祁盈欲以家法 惩治。祁胜通过贿赂荀跞向晋侯讲情,不但没有被讨,相反却使想整治他们的祁盈被杀,并 使 祁氏灭族。羊舌氏之叔向之子杨食我因与祁盈同伙,也遭灭族之运。
这件事处理的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此时正是韩起执政。据《左传》上面的叙述似乎韩起 未参与此事。但《左传》接下去则云:“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 县 ,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 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人,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大夫,赵朝为 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又可见,韩宣子,魏献子实是此事件的策划者和参与者。《 史记·晋世家》云“晋之宗家祁傒孙、叔向子、相恶于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 其族 ,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益大。”笔者以为,《史记》之说颇得 韩魏及其他四家之本意,颇中这次灭族事件之实质,即这是韩魏借祁氏家族内乱发难以翦除 公族势力而走向篡国夺权的一个有计划步骤。
但《左传》却不这么看。作者说,魏献子举荐上述县大夫的依据是:“谓贾辛、司马乌为 有力于王室,故举之。谓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余子之不失职,能守业者也。其四人 者 ,皆受县而后见于魏子,以贤举也。”依《左传》所记,魏献子非但没有欲弱公室之意,相 反却有尊崇、强大王室之心,有举贤为国之义。在诸被举者中,有一人叫魏戊,是魏宗族中 人,为了表明魏献子举魏戊亦出于无私,作者还大段征引了关于此事的对话,为见出作者的 倾向性,这里将其全部引用如下:
魏子谓成鲟:“吾与戊也县,人其以我为党乎?”对曰:“何也?戊之为人也,远不 忘君,近不逼同,居利思义,在约思纯,有守心而无淫行。虽与之县,不亦可乎?昔武王克 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夫举无他,唯善所 在,亲疏一也。《诗》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 克君。王此大国,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心能制义曰度 ,德正应和曰,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 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无悔,故袭天禄,子孙赖之。主之举 也,近文德矣,所及其远哉。”
把魏戊说成忠于君主、友爱同事、居利思义、贫而守操之美德之人;赞誉魏献子举荐得人 ,其业绩可比之于周文周武。对魏献子之颂美之至,无以复加。最后,又引了一段孔子的话 :
仲尼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曰:“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又闻其命 贾辛也,以为忠:“《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 ,其长有后于晋国乎。
用具有权威地位的孔子来赞美魏献子并对其未来进行美好的预言,把魏氏的道德与将来的 得国紧紧联系到了一起。
由此可见,《左传》作者对魏氏取国作了充分的道德解释。大概魏氏在历史上也没有什么 特殊美德值得歌颂,《左传》作者只好在这里大作文章了。正因为《左传》对魏氏推崇得太 露骨了,所以有人怀疑,作者一定与魏国关系密切。其实,这倒未必,作者只不过是为他全 力建构的那个道德得国的理论作历史论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