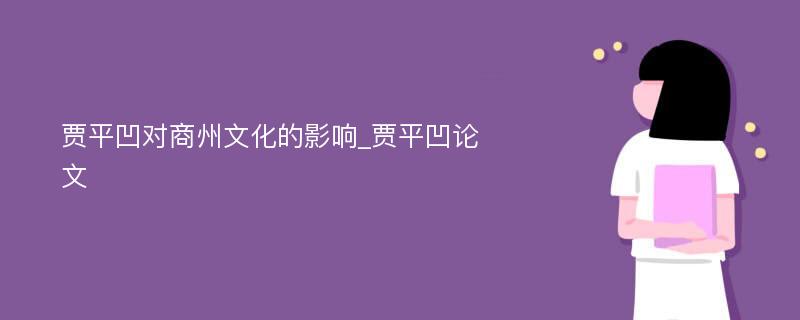
贾平凹的商州文化濡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贾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贾平凹的小说被称为商州文学久矣,贾平凹同商州文化的关系也时有论者提及,然而,商州的地理和人文如何形成商州文化特质,贾平凹何以能如此敏锐地感受商州文化特质,以及在感受中具有怎样的心理特征?本文尝试进行这方面的分析,以揭示小说创作同地缘文化的深层联系。
(一)商州文化特质
商州即今商洛地区,略有区别的是,古商州除州城外,只辖路南、镇安、山阳、商南四县;解放后重新划定,增丹凤、柞木二县,整体区域并未增加。古代或称商州,或称商洛;解放后定名商洛地区,首府为商县,今改商州市。
在陕西省的陕北、关中和陕南三大板块中,商州居关中和陕南间的秦岭南麓。这是一个过渡、交叉性地带,因为秦岭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是南北两大自然形态的过渡区,气候、物象、川流等都呈过渡性状;秦岭还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分野,以北水入黄河,以南水入长江。这就形成商州有趣的现象:商州与黄河近若比邻,纵贯商州的丹江却南入汉水,商州属长江流域。商州群山环抱,北有关中平原,南有江汉平原,西有安康——汉中盆地,东是中原大地,四面合围,形同骨节,其气象比关中灵秀却不及江汉潇洒,比安康——汉中厚朴却不及中原通达。总体看来,又兼具四方气脉,自然形象别具气韵。
商洛地区以商县——丹凤一带川道为中心,环环相连,构成神奇瑰丽的景观,其中商南、丹凤、商县(今商州市)南北一线是古代交通要道,也是现在312国道的主要经过地段。 这是商州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区。贾平凹恰恰生长在商州要冲区。他的家乡棣花镇距商州市不过35公里,距商南县城近百公里;龙驹寨是本县县城,仅距15公里,风水宝地商洛镇则近在咫尺。贾平凹受着最浓郁的商州文化濡染。
商州的通道作用,沟通着古代两大文化体系:秦文化和楚文化,从而形成两种文化的交叉。这一点大同于它的母体三秦文化,不同的是,商州文化中楚文化的韵味更浓郁。这不仅缘于地理环境,而且缘于社会历史沿革。早在战国时期,秦楚两国便在这里展开拉锯战,后来秦国采用商鞅新法,国力大增,破楚掠地,将商州封给商鞅,故名商州。楚人项羽和刘邦灭秦争天下时,均入商州。传说项羽的乌骓马得于商州黑龙潭(丹凤城东),龙驹寨由此得名,丹凤民间至今颇多项羽和龙驹寨的传说;刘邦入武关,过商州,长驱直入汉中,最终称王。秦末,四位德高望重的秦博士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避居商山,采商芝以充饥,饮朝露以润喉,持节操以终年,深得后世景仰;西汉以降,州官士人年年祭扫“四皓墓”,凭吊、咏赞四皓的诗文浩如烟海,录于《商洛古诗文选注》的达50篇。这一切,成为商州历史文化的一大景观。
汉以后的几个世纪,商州一直发挥着通道作用。明末李自成从陕北起义,几番失败,损失殆尽,退居商洛山林,招兵买马,养精蓄锐,终得东山再起,挥戈北上,摧毁明王朝。历史上还有几次大移民,如《商州志》载:“汉高祖发巴蜀伐三秦,迁巴蜀七姓居商洛,其蜀多猎山伐木,深有楚风。”这一切,都强化着商州的过渡性和交叉性。
商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形成其独有的文化特质。其一,丰富的包容性。单就语言而言,秦楚两大语系的交汇使得商州语言驳杂多变;既有秦腔的粗犷、俗重,又有楚语的柔和、婉转;既有属于某种语系的变体,又有“四不像”的杂交。细究之,语言变化又有规律可寻:从南往北,由楚语而秦腔;自北向南,由秦腔而楚语。洛南话最接近关中秦腔,商县次之,然后丹凤,到商南楚豫腔占上风,秦腔渐弱;无论声腔音调,还是表达的习惯方式,都显出明显的递变性。商县至丹凤川道一线,变化不大,相对一致,是商州方言的代表地区,它正是贾平凹的语言根基。其二,古拙的浑朴性。《商洛古诗文选注·前言》云:“收入本书中的作品可谓古朴粗犷的秦文化、柔媚清丽的楚文化与雄浑、辉煌的汉唐文化相互融合所生出的‘商洛亚文化’的丰硕果实。”这种丰硕的果实不仅物化为文人墨客的诗文辞赋,而且沉厚地积淀在民俗民风、社会心理之中。虽然商州有着并不寂寞的历史,但因四面环山,远离都城,终是偏僻闭塞,即使繁华通达的龙驹寨,也是山夹水挤,加以历史的闲置,也未脱离蛮荒封闭的境况。长期的小农经济生活,山民们的生产方式虽由刀耕火种发展到锄垦镰收,终是发展缓慢,这使得商州的社会生活保持了更多的古朴性。浑厚而古朴,成为商州文化的鲜明特征。其三,进取的开拓性,商州作为地域上的过渡地带,历史上也是政治、军事的胶着点和重要经济走廊。在各种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伸延的同时,也把文化意识渗透进来。历史上几次南民北移,也把其风俗习惯和民间文化艺术带到商州。这就形成各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在竞争和删汰中,形成攀比进取、推陈出新的民风。其实,秦文化和楚文化本身便是推陈出新的文化:商鞅变法精神作为原型意识不可避免地沉积在商州人的心理结构中,楚人的进取精神也影响着一代代商州子孙。其四,奇幻的神秘性。商州有神秘奇妙的八景十观。八景是:龙山晚日、熊耳晚霞、三台叠翠、四皓古陵、仙娥削壁、丹木环城、商山雪霁、秦岭云横;十观是:武关胜塞、仙子神湫、秀阁书声、灵喦松舞、溪岸桃花、龙潭瀑布、昙花胜地、水月洞天、鸡冠插汉、龙涎吐珠,加之板桥、龙山、棣花、商镇、龙驹寨、桃花铺、富水、竹林关等厚积着文化气息的地名,构成商州极富魅力的景观。这些景观在历代诗人的妙笔下进一步升华,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遥闻旅宿梦兄弟,应为邮亭名棣花。”“秀眉老父对樽酒,蒨袖女儿簪野花。”“历历山川连楚豫,纷纷贾客杂樵渔”。“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横空绝磴晓青苍,楚水秦山古战争。”更兼楚文化的影响,商州民间有较浓的巫文化意识,奇妙的景观演化出众多神异的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于是,商州的景观和风俗史充满着奇妙的神秘感。
(二)贾平凹的艺术思维特征
生长在商州腹地的贾平凹天然地接受着商州文化濡染,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更敏感地接受地域文化濡染的心理基因,这使他成为表现商州文化的典型代表。
1952年春,贾平凹诞生在陕西丹凤县农村,“一个22口人的大家庭里,自幼没有得到什么宠爱。长大体质差,在家干活不行,遭大人唾骂,在校上体育,争不到篮球,所以便孤独了,喜欢躲开人,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坐地。愈是躲人,愈不被人重视,愈不被人重视,愈是躲人,恶性循环,如此而已。”(注:《贾平凹性格心理调查表》,《丑小鸭》1982年第2期。)
“文革”中,当教师的父亲被诬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平凹也中断学业,回家务农。这个孱弱瘦小的“书生”,无论如何也干不好农活。正如他在《自传》中记的:“老农们全不喜欢我作他们帮手,大声叱骂,作践。队长分配我到妇女组里去作活,让那些三十五岁以上的所有人世的忌妒、气量小、说是非、庸俗不堪诸多缺点集于一身的婆娘们来管制我,用唾沫星子淹我。我很伤心,默默地干所分配的活,将心与身子都弄得疲累不堪,一进门就倒柴捆似地倒在坑上,睡得如死了一样沉。”这一切,使贾平凹在受过创伤的心灵上又蒙上一层阴翳,孤独感更加深一层。
精神创伤和心灵孤独,虽是平凹人生的不幸,却造就他作为作家的超常认知。
贾平凹那种影单形只的孤独,与各种强烈的感情体验如自卑、忧伤、失意、挫败感等相联系,形成心理失调状态。摆脱失调状态成为他强烈的愿望和要求。但是,这种由客观情势造成的孤独,是难以通过现实的活动摆脱的,正如鲁迅无法挽回家庭的不幸,贾平凹也难以改变自己矮小的身材和赢弱的身体,于是,阅读和欣赏文艺作品往往成为一种补偿性活动。贾平凹打发孤独的办法,先是到光棍楼听故事,稍大一点便酷爱读书,偌大的棣花镇,能找到的书全读了,还让父亲到朋友处借。他初中母校有个小图书馆,造反那阵,书被偷光,他打听到下落,常用帮工去换读,久之,渐渐对文学艺术产生兴趣:一段时间,他苦练毛笔字;一段时间,他又背诵唐宋诗词,手抄《古文观止》。白天累断筋骨,夜里秉烛苦读,颇有大器初铸的躁动。贾平凹谈到读书的感受时说:“能识天地之大,能晓人生之难,有自知之明,有预见之先,不为苦而愁,不受宠而欢,寂寞时不寂寞,孤单时不孤单,所以绝权欲,弃浮华,潇洒达观,于嚣烦尘世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畏不俗不谄。”(注:《好读书》,见《人迹》第39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贾平凹在文艺作品中“给自己找到了一个逃避人生忧患苦难的庇护所”,“转而又使得日常的现实世界成了痛苦的源泉。”(注:毛姆:《人性的枷锁》。)这不仅是贾平凹的痛苦,而且是古今中外文学家、艺术家的痛苦,因为大多数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是孤独者。如此,贾平凹在读书中便将自己的孤独同古往今来的孤独者融会在一起,他不仅为自己的孤独而痛苦,而且为杰出的前人的孤独而痛苦,他承受的痛苦具有时代和历史的巨大包容性,是深刻的艺术家的痛苦。贾平凹是痛苦的,也是充实的,他因孤独而参与了不同于现实生活的另一种生活,并且在与艺术的接触中重塑了自己。正是因为阅读大量文艺作品,培养了他成为未来作家的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将他的生命活动和审美活动联系在一起,愈到后来,其联系愈紧密,乃至在大病之中因艺术想象而忘记痛苦,带病写作感到是一种幸福。
生命活动和审美活动的结合,标志着贾平凹已获得作为文艺家的独特的思维方式——超常认知。认知指包括想象、联想以及幻觉因素在内的实际的知觉活动,超常认知指认知活动的奇异性和非常态。个体创伤造成的孤独感疏离了他同群体的关系,却割不断他与群体感情沟通的希望。这种希望虽在艺术接受如读书中得到补偿,那毕竟是虚幻的世界,他还需要现实的补偿,于是,他对现实中与“人”的面貌有相似之处的自然物便格外敏感,并产生将某些自然物人格化的现象。正如古语说的:“乡无君子,则以山水为友;里无君子,则以松竹为友;座无君子,则以琴酒为友。”贾平凹在《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中写道:“社会反复无常的运动,家庭反应连锁的遭遇,构成了我是是非非、灾灾难难的童年、少年生活,培养了一颗羞涩的、委屈的甚至孤独的灵魂。慰藉这颗灵魂安宁的,在其漫长的20年里,是门前那重重迭迭的山石,和山石之上圆圆的明月。这是我那时读得很有滋味的两本书,好多人情世态的妙事,都是从那儿获知的。山石和明月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在我舞文弄墨挤在文学这个小道上后,它始终左右着我的创作。”对自然景物的格外敏感,并通过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去认识“人情世态的妙事”,便成为贾平凹的超常认知。这种超常认知注定:他的政治、社会意识较弱,而历史、文化和生命意识异乎寻常的强烈。
与超常认知紧密联系的,是贾平凹的感应式思维。源于《易》的感应思维是强调人与自然、人的内在精神和外界事物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思维方式,著名的“天人感应”说便包含这种方式。在诗学领域,感应思维是一种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形象思维,它受启发于禅道,与禅道中的“妙悟”、“感悟”紧密联系在一起。感应式思维要求创作主体在思维时实现对客体和主体自身的双重超越,达到“寂寞一念无”的虚静态。这种虚静是暂时的杂念离异,使主体以明镜似的虚静之心去迎接汹涌奔腾的艺术想象世界。它以无载动有,以静追求动,以平如大漠的情怀去拥抱勃郁奔腾的大千,去迎接腾挪不绝的美和喷涌而至的灵感。其实,感应便是感悟。贾平凹称作“悟”,“悟道”,认为,“世上所有的艺道皆有悟性”。在《浮躁·序二》中,他写道:“我欣赏这样一段话:艺术家最高的目标在于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发掘最动人的情趣,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可视为他的“感应式思维宣言”。
贾平凹的超常认知和感应思维,使他能在别人司空见惯的景观上悟出生命、文化和历史来。走在陕西乡间的田野上,他能同这里的山川风物发生着强烈的情感,在黎明或者黄昏的时分,一个人独独地到田野里,远远看见天幕下一个一个山包一样隆起的十三个朝代帝王的陵墓,细细辨认着田埂上、荒草中那一截一截汉唐时期石碑上的残字,高高的土屋上的窗口就飘出一阵冗长的二胡声,几声雄壮的秦腔叫板,我就痴呆了,感觉到那村口的土尘里,一头叫驴的打滚是那么有力,猛然发现自己心胸中一股强硬的气魄随同着胳膊上的肌肉疙瘩一起产生了。”(注:《秦腔》,见《人极》第376页,中国文艺出版社1992 年版。)西安碑林,户县、安塞的剪纸和刺绣等,他也极感兴趣,说:“每过一段时间,我就去那如林的石碑下,我总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启示,每见到民间那剪纸、剌绣一类,总是爱不释手,虽然我无意要去做书法家和美术家,古老艺术竟合了现代人的心境,这使我吃惊。”(注:《平凹文论集·无题——〈心迹〉序》。)
(三)贾平凹的审美心理图式
由精神创伤所形成的超常认知和感应性思维,显示了贾平凹艺术思维的超常性和敏感性。这种超常的艺术思维能力虽然提供了敏锐地感受商州文化特质的可能性,却难以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能与地域文化特质发生“同化”作用的“心理图式”。
寻找和揭示作家固有的心理图式并非一件易事。我们拟以“人文象”描述一下贾平凹的艺术心理图式。贾平凹在《静虚村散叶》中说:“说鲁迅的人文是什么象?猫头鹰。苏东坡的人文是什么象?水。郑板桥的人文是什么象?瘦石。我是赞成这种说法的。”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在于:外在的物理世界和内在的心理世界存在着异质同构关系。可以作一番探寻。其方法是:首先寻找他艺术创作中的意象元件系统,然后确定主导意象即是。贾平凹的审美意象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扒梳起来,在他的散文、小说、诗歌乃至绘画中,出现最多的意象元件是月、水、石等。他对月特别钟爱,他的散文集《月迹》几乎全是咏月散文,精彩的篇目便有《月迹》、《月鉴》、《对月》等;在小说中,他钟爱的并着力描绘的女性形象常以月命名,如满月、小月、月清、柳月等;谈自己创作道路的文章便命题为《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认为明月和山石是“读得很有滋味的两本书”。他甚至认为,“我们这个时代该是一个月亮的时代呢”。贾平凹也特别爱水,他自称水命,以水命题的作品便有《一个有月亮的渡口》、《在池塘边》、《四月二十三日游太湖》、《溪流》、《溪》、《玉女山瀑布》、《高观潭》、《温泉》、《未名湖》、《荷花塘》、《白浪街》、《河西》……他常常描写的那条州河简直成为他作品的图腾。他甚至觉得,“我的生命,我的笔命,就是那山溪哩”。山石的意象,在贾平凹的作品里可谓俯拾皆是。在《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中,他写道:“山石和明月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在我舞文弄墨挤在文学这个小道上后,它始终左右着我的创作。”他的散文《读山》,从山石、山路、山光、山雾、山雨这些无情物中,读到了它们无限丰富的生命情调,他同山石进行着心物交感:“我坐在一堆乱石之中,聚神凝思,夜露就潮了起来,山风森森,竟几次不知了这山中的石头就是我呢,还是我就是这山中的石头?”《丑石》中那块“丑到极处”又“美到极处”的丑石,也是贾平凹的夫子自道。在为人称道的绘画《梅妻石夫》中,他再次以“石夫”自况。
月、水、石作为贾平凹笔下出现最多的审美意象,彼此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不在于它们的客观属性,而在于它们在贾平凹心理透镜上的折光。众所周知,贾平凹在他的小说中最擅长描写的而且描写最为成功的是青年女子形象,他不但把一些女性形象命名为月,在描写中还常将月亮意象同女子形象叠合:《月鉴》中,月亮同自己的妻子叠合,《天狗》中,月亮在天狗心目中同师娘的脸叠合,《佛关》中,兑子在“我”的心目中同月中嫦娥叠合……月亮既与女人叠合,月下便有爱情,黑氏和长顺在令人心性勃发的月光下涉入爱河,月光下作爱的还有“我”和兑子……在贾平凹的笔下,水的意象也往往同女人、爱情联在一起,州河、丹江、汉江等河流上便飘满了情歌。水和月,往往通过女人和爱情,发生密切的联系。《天狗》中,月食在即,女人们来到汉江边祈祷,保佑丈夫吉祥,古老的乞月歌,和着江水缓缓地流。天空挂着月亮,天狗和师娘以乞月歌袒露相爱之情。在这里,月、水、女人、爱情浑然天成地融合到一起。
平凹笔下的山石,常常象征大器,象征朴拙的力之美。他常以石自况。《梅妻石夫图》可窥见石和月的关系。该图的画面上,二三枝条,似带似缨,临风垂拂;枝条环护下,一团浓墨,如石如盘,状作襁褓;细瞧,原是一介书生,乱发纷披,平地而卧,枕下有竹简散开。其题词云“……献给俊芳三十六本命年。本丈夫以此为寿礼乞大吉大利。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牺牲者的妻子,然而成功的男人皆呆如石头矣,原来是刚强而美艳的梅,已枝干似柳了。若纯梅不行,若素柳不行,梅柳之妻,愚夫可成石。石则涵玉,玉则上补青天,下镇黄土,是吗?人间妻不好做矣。”作为成功者——可上补青天、下镇黄土的涵玉石夫,终究要置身梅柳之妻的环护之下,梅妻石夫的关系自明矣。前文已述,月与女人常常叠合,梅妻石夫的关系亦喻月和石的关系。同月和水的联系相比,月和石是一种矛盾和谐,你看,石夫顽劣,梅妻似梅似柳,刚柔相济,才形成对石夫的征服。
在贾平凹作品的意象系统中,月、水、石以女人为媒介达到了和谐统一,月和水是相辅相成的和谐,月和石是相反相成的统一,整个系统成为动态平衡的有机体。其中月的意象出现的频率最高,包含的意蕴更深刻;它不仅牵连着“水”,而且制约着“石”,是主导意象。据此,贾平凹的人文象当确定为“月”。
月象的原型意识可追溯到远古神话“嫦娥奔月”。从审美心理看,月的凄清,嫦娥的寂寞,人类的某种清幽心理,形成了对应关系。嫦娥作为凄清心理的表征,形成一种遗传因子,一直影响到现今人的审美心理。
月象作为贾平凹心理图式的表征,并不能以“凄清”作简单解说。因为平凹的月象不可避免地带时代特征,更何况这个月象是以月为主体、包括水、石在内的有机整体。贾平凹的月象中,既有月的幽静、凄清,又有水的轻柔、神秘,更有石的坚韧、顽劣,是一个复杂统一体。他称自己的性格类型是:内倾+独立。“这种气质的人,表面上是冷漠的,内心是热烈的,他永远使人看不透。以此引伸入文学,必然有一种神秘色彩,变化莫测,有不可学得(模仿)的特点,他不善于打正面攻击战,却极会选择角度进入中心地带。”(注:《贾平凹文集》第127 页。)据此, 我们可对贾平凹心理图式——月象的特征做一梳理。(1)空灵的诗性。这与他的超常认知和感应思维有密切联系。他的心理图式如忧柔的月光,空灵、恬淡、凄清、寒冷,朦胧而安静,虚空而平和,是一种诗意充溢的境界。他将生命活动与审美活动结合起来,形成生命的审美化,明显带有婉约词人的气质。(2 )孤寂的韧性。他如同笔下那块丑石,在地上“一躺就是二三百年时光”,有着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他评价川端康成时说:“孤苦凄凉的生活使他性格内向:受尽了人世的歧视,却不肯屈服,便只有孤独、虚无、颓废,官能的压倒。但只有这种人,其内心才最龙腾虎跃,才最敏感,才最神经质,才善于有瞬间纤细的感觉和细致的微妙的心理活动。”这也是夫子自道。(3)莫测的神秘性。 平凹被称为文坛“鬼才”,显示着他心理结构的神秘性。这种神秘性像他笔下的水:“平静的水面是温柔的,却深不可测;河面上翻一片雪浪花多么好看,那下面是有一块绊脚的石头的;漩涡里的空心轴儿银亮亮的,若走进去,或许会绞肉机一样将你吸拉进去……”(注:《心迹·后记》第338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又像他笔下的山:山上的路,看得见两头,又终觉难于走尽,令人不解;山上晨雾暮霭,浓浓的滚动,片刻间又匀匀地轻笼着林木,一眨眼又会倏忽尽散,无踪无影;山间的光明和黑暗一样,使人看不清任何东西,使人久久迷惘,大惑不解。(4 )隐逸的禅性。平凹室内挂达摩面壁图,将居处题名“虚静”,作品也命名为《静虚村散叶》,心理中的禅性也常常流露到作品中。观东山魁灵的画《冬花》,天上一轮虚虚的月,地上一株圆圆的树,别无他物。他感到“朦胧而又安静,虚空而又和平”,惊呼:“这是什么缘故儿呀,画儿,我一见到你,我就想哭呢。”想哭,不是伦理的认同,不是人道的悲悯,而是禅意共振的颤栗。
(四)走向商州文化
将商州文化特质同贾平凹的心理结构(图式)相比较,便可以明显看出,二者的特征虽有不少的沟通,如神秘性和进取性;也有一些差别:月象属阴柔意象,表现出婉约、空灵、清丽、秀逸,而商州文化特质则表现出沉厚、雄浑、大涵大度。在贾平凹的生活和创作中,贾平凹按照自己的心理图式吸收外来刺激,进行着“同化”过程,而商州文化亦按自己的特质对贾平凹的心理图式进行着“顺化”,促其地域文化化,在复杂的矛盾中构建着动态平衡,其结果,贾平凹的作品逐渐商州文化化。贾平凹的艺术思维方式(超常认知和感应思维)从中起着催化作用。加速着心理图式的“同化”和“顺化”进程。
贾平凹创作伊始,主要表现为心理图式的同化过程。创作始于模仿,他寻找着同自己气质相类的作家作为参照系。他首先找到孙犁,对孙犁的潜心师承使他创作大进,受到孙犁赏识;他还借鉴冯文炳和沈从文。于古人,他最早学习的是李清照和蒲松龄;于国外作家,他酷爱川端康成……在同这些作家的神交中,贾平凹的超常认知和感应思维像一只无形的手,推波助澜,强化着他对这些文学大师的理解和妙悟,同他们撞出心心相印的火花。贾平凹初登文坛,就把握住自己的创作基调,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风格:清新自然,凝炼含蓄,富有浓郁的诗意。其结构,行云流水般和谐、畅达;其语言,质朴而清新,含蓄而抒情;其艺术表现,简洁凝炼,有整体感;其审美效果,如梨花带雨,优雅醉人。这一切,使他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2年。
这一时期,贾平凹的作品并非没有商州文化意蕴。商州文化精神的遗传,商州自然人文景观和社会风尚的影响,使他的心理图式中早已带有了商州文化基因。如写爱情,他都是以自己的妻为模特儿去描写女人的神和韵,而妻子则是商洛的水土出脱而成的,加之平凹心理中的商州文化基因,自然带有了商州的神和韵。但是,毕竟平凹的心理图式同商州文化特质不无差异,初登文坛的稚嫩使他笼罩在名家大师的风格之下,他的创作处在心理图式的“同化”过程,对于图式之外的刺激,尚无暇顾及;更何况,他独特的思维方式的兴奋点也在“同化”方面。因此,读者感受到的是平凹的鲜明的艺术个性与风格,而商州文化意蕴并没有引起关注。其实,初登文坛便达到这样的高度,已属罕见,无须苛求。
贾平凹涉世渐深,眼界逐渐开扩,商州乃至三秦的景观和世事一次次冲击他固有的心理图式,他独特的超常认知和感应思维强化着这种冲击,他在田野上听到秦腔叫板而“痴呆”,见汉代瓦罐而“震惊”,见霍去病墓前的石雕而“傻呆”,见关中画派修军的木刻而想起“家乡的山脉水势”,见西安碑林,安塞、户县剪纸和剌绣而“吃惊”。这都是他与商州及三秦文化进行的心物交感。最使他激动的还是霍去病墓前那只石雕卧虎,他专作《“卧虎”说》,写道:
前年冬日,我看到这只卧虎时,喜爱极了,视有生以来所见的唯一艺术妙品,久久揣赏,感叹不已,想生我育我的商州地面,山川水土,拙厚,古朴,旷远,其味与卧虎同也。我知道,一个人的文风和性格统一了,才能写得得心应手;一个地方的文风和风尚统一了,才能写得入情入味。从而悟出要作我文,万不可类那种声色俱厉之道,亦不可论那轻靡浮艳之华。“卧虎”,重精神,重情感,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正是我求之而苦不能的啊!
之后,贾平凹开始了心理图式的顺化过程。 他选定商州作自己的开发“特区”,对商州进行着全方位的勘察。他的超常认知和感应思维促使他同商州的山势水形、社会风尚进行着强烈的心物交感。于是,商州文化特质激活了平凹心理图式中的地缘文化基因,平凹的心理图式也以开放的姿态吸纳着更多的外来刺激,获得大幅度的丰富与发展。贾平凹的创作进入辉煌的“商州文化”期。他首先以《商州初录》拉开序幕,继而陆续创作了《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商州》、《天狗》、《远山野情》、《冰炭》、《黑氏》、《商州世事》、《古堡》、《浮躁》、《妊娠》、《美穴地》、《五魁》、《佛关》、《晚雨》、《龙卷风》、《瘪家沟》等一系列中长篇,构建起“商州小说”大厦。
贾平凹心理图式的“顺化”过程,是其固有心理图式和商州文化特质的进一步融和的过程。贾平凹的个性不仅没有失落,却获得强化和发展。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商州文化特质经过贾平凹心理图式的变形和折光,带有了贾平凹的个性特征。约略说来,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走向浑朴。浑朴者,浑厚而质朴也。在贾平凹最初的个性中,质朴是早已有之的,浑厚却明显不足,他心理图式的“顺化”过程,主要是走向浑朴的过程。可以说,贾平凹是在三秦文化遗存的影响下走上浑朴的。如前所述,他见到汉代瓦罐而“震惊”,见到霍去病墓前的石雕而“傻呆”。他感到,这些遗存“其作风的浪漫,造型的夸张,其寓于厚重的幽默,其寓于稳定的强劲的动和力,太使我羞愧自己的浮浅与甜腻”。(注:《平凹文论集·无题——〈心迹〉序》。)与此同时,他钟爱的作家由李清照等转向充溢着三秦雄风的司马迁。他在一篇文章中比较了冯文炳和沈从文之后自诫道:“吾则要拉开距离,习之《史记》,强化秦汉风度。”他反复品读《史记》,着意感受司马迁身上的雄风,追求司马迁写人论事那种全局在胸的史家气度。在《腊月·正月》中,他用史记笔法写韩玄子同王才的斗争,使这部中篇带有了历史的深沉感。长篇小说《浮躁》既是贾平凹走上浑朴的标志,又是他的一个创作高峰。其浑厚性,表现在艺术宽度和深度的双重推进。在艺术构思上,《浮躁》带有相当的综合性,包含着作者对历史、文化、民俗、时代、生命、艺术等方面的思考,却又能浑为一体;在人物塑造上,追求人物性格的丰富与复杂;在艺术提炼上,突破了实际的生活原型的限制,实现了整体性艺术思维的解放;在艺术结构上,几条线索交叉渗透,有历史的纵深感,金狗的命运线又是贯串始终的主线,繁复而集中。整部作品如贾平凹笔下的卧虎石雕,“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
其二,走向神秘。由于贾平凹心理图式中包含着较强的神秘性基因,作品中的神秘因素要比浑厚性来得快,来得强烈,乃至后来过多地描写神秘事物而冲淡了作品的现实感,甚或有神秘主义之嫌。贾平凹的“商州小说”创作伊始,便开始了对神秘性的探讨。《商州初录》便记载了老医生给狼治病及狼的报德故事。1985年10个中篇的大部分如《天狗》、《黑氏》、《人极》、《远山野情》等通过各种性爱故事探索乡村社会潜在的性意识,这本身便带神秘性;更何况这些篇什还或多或少地描写了乡村的神秘文化现象。1986年的《古堡》描绘了各种神秘文化现象,透出荆楚神秘巫风的影子。它还赋予神秘事物以象征意义,如耸立于烛台峰之巅的古堡,以其古老、威严、神秘统摄着村民的精神世界,作品的“古堡”命名,便是一种神秘象征。那神秘出没的白麝,同张老大的事业和爱情进行着神秘的比照,也引起读者不尽的思索。长篇《浮躁》可说是非常写实的作品,却也设置了许多混茫之笔。如民间对阴阳风水的讲究,韩文举卜卦观天象,夜梦土地神,和尚谈玄讲空,小水左眼跳金狗果然到……那贯串全书的州河,发几次水、涨几次水“都是有一定讲究的。”它成为人民斗争浪潮和金狗命运的神秘象征。从1986年的《龙卷风》、《故里》、《瘪家沟》开始,贾平凹甩脱现实改革题材,步入参悟神秘文化、表现山民混沌思维的“形而上”层次。到《太白山记》,运用“巫化思维法”,以魔幻之笔写山民虔信神巫文化的魔幻心态,浑浑茫茫,恍兮惚兮,进入一个幻象世界,因而被称为“新志怪小说”。90年代发表的《白朗》、《美穴地》、《五魁》、《烟》、《佛关》等,同《太白山记》相比,少了浑茫之气,多了写实之笔,但神秘性仍然炽烈存在,甘愿为女性奉献的五魁后来竟娶了11位押寨夫人,白朗由得胜的英雄一下子变成颓废的隐士,目睹人生三世的石祥对古赖耶识充满困惑……形成作品整体意蕴的神秘感。
其三,艺术的开放性和进取性。开放性和进取性,既包含于贾平凹的心理图式,又见之于商州文化特质,因而形成平凹艺术创作的不断进取与开拓。他在读到马尔克斯和略萨时说:“他们创造的那些艺术形式,是那么大胆,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什么都可以写进小说,这对我的小家子气简直是当头一个轰隆隆的响雷。”(注:《静虚村散叶》第164页。)勇于剖析自己的“小家子气”, 正说明他艺术胸襟的开阔。他以开放的艺术胸襟吸收着多种信息和营养。他的古典文学修养为人们所称道,这方面的老师有司马迁、陶渊明、柳宗元、苏轼、李清照、施耐庵、蒲松龄、曹雪芹、苏曼殊等。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他吸收着传统美学精神:从志怪小说中学会了以平实的神秘感抓住读者的向往心,从《世说新语》学会简炼、隽永和传神,从《山海经》、《水经注》和地方志学会对大小空间的鸟瞰和统摄,从《浮生六记》悟出叙事写情的高超本领。(注:黄秉勋:《贾平凹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他主要学习和借鉴的是废名、沈从文、孙犁、周立波等;外国作家,对他影响大的是川端康成、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泰戈尔、略萨等。他学习沈从文对自然山水的感悟,他借鉴孙犁被称为孙的“金童”,他效法略萨被誉为“结构现实主义”者……他兴趣广泛,“喜欢观鱼,看美术杂志大胜过看文学杂志。爱看杂书:建筑、医药、兵法、农林、气象、佛学……”这一切,造就了他从事创作的艺术“底气”,这种“底气”成为艺术不断创新的基础,鼓荡着他的艺术之舟破浪前行。
贾平凹认为,“创作之所以是创作,创是第一位的,作是第二位的,一切无定式,一切皆‘扑腾’。”(注:《战胜自己——〈贾平凹小说选集〉序》。)他确实是一个不断“扑腾”、不断突破的作家。以《山地笔记》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奠定了他美学风格的第一块基石,表现的意蕴是清新、明丽;以《商州初录》、《商州世事》、《商州》为代表的那批作品奠定了他美学风格的基本格调,表现为透露着文化生命意识的犷野隽丽;以《浮躁》为代表的作品又增加了风格的雄健和朴厚;之后的作品又追求着空灵与浑茫……他的作品从不重复自己,每有新作,都会引起文坛的兴奋和关注,进入一个自觉自由的商州文学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