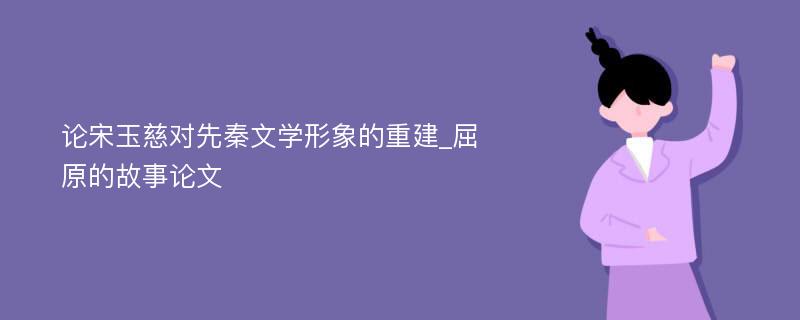
论宋玉辞赋对先秦文学意象的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辞赋论文,先秦论文,意象论文,重构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5)06-0156-06 历代批评家对于宋玉的批评,可分为批驳与褒扬两派,但以批驳居多。对宋玉辞赋的批驳,始于汉代,以扬雄和班固为代表。扬雄在《法言》中说:“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1]班固的批驳承继扬雄而来,措辞更加尖锐。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馋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2]从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批评家对宋玉辞赋的批驳,大多基于扬雄和班固之论而进一步发挥,不再赘述。 那么,为什么历代批评家指责宋玉辞赋为“淫”文之首?“辞人之赋丽以淫”和“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的批驳背后,隐藏着何种文学变迁?本文从宋玉辞赋对先秦文学意象的继承与改造入手,探讨这些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先秦文学意象的建构,并非始于宋玉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政教意象、日用意象转换为文学意象,最初始于《易经》,此后,《诗经》、诸子著作,以及屈原作品等先秦典籍继而为之。宋玉辞赋在前人基础之上,又对先秦文学意象进行了重新建构。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研究的宋玉辞赋作品,以学界公认和确考为宋玉所作的辞赋作品为准,主要包括《九辩》、《高唐赋》、《神女赋》、《讽赋》、《登徒子好色赋》、《钓赋》、《御赋》、《风赋》、《笛赋》、《大言赋》、《小言赋》,共11篇[3]1。 一、宋玉辞赋意象的分类 关于“意象”一词的含义,学界有众多解释。袁行霈先生认为,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4]。蒋寅先生则说:“意象是经作者情感和意识加工的由一个或多个语象组成、具有某种意义自足性的语象结构,是构成诗歌本文的组成部分。”[5]无论是哪一种解释,“意象”都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文学作品中的客观物象。二是作者使用客观物象所承载的主观情意。 宋玉辞赋作品中的意象,均是对先秦文学意象进行加工和改造的结果,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人格追求和情感变化。宋人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对《九辩》的比兴寄托之旨进行了探讨:“秋者,一岁之运盛极而衰,肃杀寒凉,阴气用事,草木零落,百物凋悴之时,有似叔世危邦,主昏政乱,贤智屏绌,奸凶得志,民贫财匮,不复振起之象。”[6]明人胡应麟亦说:“宋玉赋《高唐》、《神女》、《登徒》及《风》,皆妙绝今古。”[7]总体而言,宋玉辞赋作品中的意象主要可分为三大类:政教意象、人格意象和情感意象。 (一)政教意象。 政教意象是宋玉表达其政治理想的客观物象,可细分为以下两小类。 1.治国意象,包括“钓”、“御”和“风”,是宋玉阐释其治国理念的意象。 (1)“钓”意象,出自宋玉《钓赋》。“钓”,本指鱼钩或以钓具获取水生动物。《诗·卫风·竹竿》云:“籊籊竹竿,以钓于淇。”[8]94《庄子·田子方》云:“文王观于臧,见一丈夫钓,而其钓莫钓;非持其钓有钓者也,常钓也。”[9]720在宋玉之后,“钓”喻指用手段谋取或治理国家,如《鬼谷子·反应》云:“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其张罝网而取兽也。多张其会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网也。”[10]26又如《淮南子·说林训》云:“无饵之钓,不可以得鱼。”[11]《淮南子》中“钓”的意象,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宋玉辞赋的影响。 (2)“御”意象,出自宋玉《九辩》和《御赋》。如《九辩》云:“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见执辔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远去。”[12]189“御”,本指驾驭车马,周朝时为六艺之一。《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13]314后泛指驾驭一切运行或飞行之物。《庄子·逍遥游》云:“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9]17后引申为治世或治民。《鬼谷子·忤合》云:“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10]90 3、“风”意象,出自宋玉《风赋》和《笛赋》。《笛赋》云:“美风洋洋而畅茂兮,嘉乐悠长俟贤士兮。”“风”,本指空气的流动。古人认为,风是因天地阴阳变化而生成。如《庄子·齐物论》云:“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9]45后来,“风”喻指良好的风化。宋人吴箕在《常谈》中指出了宋玉辞赋以“自然之风”寄寓“教化之风”的策略:“风,阳中之阴,物藉之以发生,亦由之以摧谢,故风之为言,亦多不同。宋玉《风赋》有大王、庶人之分,虽曰托物以见意,而所以名状乎风者抑至矣。人君之化所以谓之风化,而诸侯之政,其是非得失,形于诗歌者,亦谓之风。风之名虽同,而所以谓之风者则异,是亦取其有发生、摧谢之别尔。”[14] 2.礼乐意象,主要包括“美人”和“笛”,是宋玉表达其礼乐文化理想的意象。 (1)“美人”意象,出自宋玉《高唐赋》、《神女赋》、《讽赋》和《登徒子好色赋》。“美人”,本指容貌美丽之人,多指女子,后喻指君上或品德美好之人。如《楚辞·九章·抽思》云:“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12]137《诗·邶风·简兮》云:“云谁之思?西方美人。”[8]57宋玉辞赋中的“美人”,多取其本义,即容貌美丽的女子。在此基础上,宋玉以“美人”的故事,阐明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礼乐文化思想。如《神女赋》和《高唐赋》中的君王与美人之遇合,《登徒子好色赋》中登墙而窥的东家之子等。 (2)“笛”意象,出自《笛赋》。“笛”,亦称“篴”,本为管乐器的名称,最早出自《周礼·春官·笙师》:“笙师掌教龡竽、埙、籥、箫、篪、篴、管、舂牍、应、雅,以教祴乐。”[13]737宋玉《笛赋》是第一篇以笛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从制笛、吹笛、笛声引申至对礼乐文化以及个人恪守礼制的讨论:“八音和调成禀受兮,善善不衰为世宝兮。绝郑之遗离南楚兮,美风洋洋而畅茂兮。嘉乐悠长俟贤士兮,鹿鸣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隐志可长久兮。”[3]102 (二)人格意象。 人格意象是宋玉标举其高洁人格的客观物象,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凤”和“骐骥”。 “凤”,本指传说中的神鸟,古代比喻有圣德的人或贤才。《诗·大雅·卷阿》云:“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8]455《论语·微子》云:“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15]191“骐骥”,本指骏马,如屈原《离骚》云:“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12]7后亦喻指贤才。 宋玉在其辞赋作品中,往往将“凤”与“骐骥”相提并论。如《九辩》云:“谓骐骥兮安归?谓凤凰兮安栖?变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举肥。骐骥伏匿而不见兮,凤凰高飞而不下。鸟兽犹知怀德兮,云何贤士之不处?骥不骤进而求服兮,凤亦不贪餧而妄食。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独悲愁其伤人兮,冯郁郁其何极!”[12]190凤和骐骥独立于浊世之外,保持自身品性的完美,不因俗利而违心屈志,象征作者不趋时媚俗,随波逐流。 (三)情感意象。 宋玉辞赋的情感意象主要为“秋”。“秋”,本指各种作物成熟或秋季时令。《诗·卫风·氓》云:“将子无怒,秋以为期。”[8]91古人以五音配四时,商为“秋”,因此,古人又以“秋”指商声。又因“秋”主肃杀,古人因此指称与律令、刑狱有关之事为“秋”。如此,“秋”便成为宋玉辞赋作品中传达悲伤之情的典型情感意象。 二、宋玉辞赋处理先秦文学意象的策略 先秦文学的意象多是由神话形象演化而来,以寓言的形式出现,表达作者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具有学术性和文学性共存的特质。面对先秦文学意象,宋玉辞赋是如何处理的呢?主要有以下两个策略。 (一)在意象的内涵方面,顺承的同时加以引申。 无论是政教类意象、人格类意象,还是情感类意象,宋玉辞赋作品基本上遵循了先秦文学意象的基本内涵,用以表达自己的情思,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含义加以引申。 1.政教类意象。宋玉赋予其治国理想与礼乐文化的内质。在宋玉之前的先秦文学中,“钓”、“御”、“风”、“美人”和“笛”等意象,基本维持其本质涵义。但在宋玉的辞赋中,这些意象的含义得以引申,被赋予了治国之道和礼乐文化的内质。 例如“御”这一意象,本指驾驭车马,后被辗转引申为治世或治民。如《韩非子·外储说》记载了“造父善御”的典故,并说:“且寄载,有德于人者,有术而御之也。故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16]韩非子在这个故事中,指出人君掌握御国之术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宋玉《九辩》和《御赋》将“御”的信含义进一步引申和发挥。其《九辨》强调人君要善御,即知人善任,不能使用强策。其《御赋》则在《韩非子》“造父善御”典故的基础上,以御术为发端,层层递进,专篇讨论统治者的御人之术和御国之道。 2.人格类意象。宋玉赋予其游离于入世与逃世之间的矛盾心态。在宋玉之前的先秦文学中,“凤”和“骐骥”的形象,仅是贤德之才的代名词。再如《荀子·劝学》:“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志在不舍。”[17]宋玉在其辞赋作品中,则将“凤”和“骐骥”意象置于楚国末年的乱世背景之中,象征具有贤德之才和济世之志,却因昏君佞臣当政而不被重用的失志之士。他们一方面渴望获得施展才志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因面对浊世而试图逃离,希望藉此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与高洁。 3.情感类意象。宋玉赋予其贤士失志不遇的悲怆和无奈。在宋玉之前的先秦文学中,“秋”本指各种作物成熟或秋季时令,如《尚书·盘庚上》云:“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18]因秋主肃杀,先秦文学作品便将秋天物候的变化与人之感情波动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宋玉将“秋”之意象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化,赋予楚国乱世失志贤士的悲伤之情,完成了“秋”意象之涵义从纯粹的季节时令到悲时伤世的定型。 (二)在意象的表现形式方面进行改造和重构。 在顺承先秦文学意象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宋玉又对意象的外在表现形式进行重构,具体方法有以下三种。 1.政教类意象故事化。在宋玉之前,先秦文学中的此类意象往往出现在诗歌或说理散文中,用以辅助说明哲学思想。如“东家处子”一词,出自《孟子·告子下》:“踰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19]在孟子笔下,此典虽然具有一定故事性,但是情节过于简短笼统,主要人物形象“东家处子”也面目模糊。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则借助《孟子》“东家处子”的典故,又虚构楚襄王、宋玉、登徒子三个人物,不仅加强了故事的复杂性和生动性,进而引出“好色与否”的话题,探讨人类情欲与礼乐大防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君子应当恪礼自持的结论,而且形象地塑造了“东家之子”这一人物形象,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美女形象的经典代表。 宋玉对先秦文学意象进行加工,使其故事化,大致可分为三种方式:一是借用现实人物,围绕中心意象虚构故事。如《钓赋》虚构楚襄王、宋玉、登徒子三人论辩“钓道”;《风赋》虚构楚襄王、宋玉、景差三人,探讨“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的异同;《御赋》虚构楚襄王、宋玉、唐勒讨论“御理”。二是借用神话人物,对已有神话故事加以改造。如在《高唐赋》、《神女赋》中,宋玉借用“巫山神女”这一神话形象,对其神话故事进行改造,加入楚襄王这一角色,讨论“礼”与“色”的关系。三是以第一人称角度讲述故事。如《笛赋》,作者以“余”为观察者和讲述者,从竹子生长、伐竹、制笛、奏笛到笛声,讲述“笛”的故事。 2.人格类意象具象化。在宋玉之前,先秦文学中的“凤”和“骐骥”意象,虽然意义非常明确,但形象却很笼统。如《诗·大雅·卷阿》:“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8]455宋玉《九辩》在塑造“凤”和“骐骥”意象时,着重凸显其在浊世的孤独与彷徨,带有强烈的情感特质。“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遑遑而无所集。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12]189-190 3.情感类意象精细化。此类意象主要以《九辩》中“秋”为代表。在宋玉之前的先秦文学中,“秋”这一词汇屡有出现,但均未把“秋”景及由此引发的情思联系起来,进行细致入微地描写。如《诗经·小雅·四月》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奚其适归?”[8]347又如屈原《离骚》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12]6 宋玉《九辩》将描写对象主要集中于“秋”景及以此引发的悲秋之情,从一系列动物、植物、山川、地理、天文等物象入手,赋予其因失志而哀伤的情感内涵。因此,明人陆时雍评价《九辩》说:“万物懔秋,人生苦愁,彼生不辰者,直百岁无阳日耳。屈原之于怀王,始非不遇,卒以忧死,君子哀之。宋玉作《九辩》衍述原意,兼悼来者,故语多商声。其云‘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所寄慨于千载者多矣!”[20] 可以看出,通过以上改造和重构,宋玉辞赋意象与先秦文学意象相比,弱化了其学术性的特点,强化了其文学性特点。这样做所造成的客观结果便是,宋玉辞赋意象的文学之价值超越了讽谕功能。 三、宋玉辞赋意象建构的文学史背景:楚国文学与学术渐趋分离 先秦时期,“文学”是指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战国晚期,楚国屈原和宋玉辞赋作品的出现,虽然不能说明此时文学与学术全面性地渐趋分离,至少说明楚国的文学与学术逐渐趋向分离。所以,宋玉辞赋意象的建构,当是在楚国文学与学术渐趋分离的文学史背景下完成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作家身份的转变。 作为先秦文学创作主要群体的士,其社会地位和个人心态,在战国前期与后期有着天壤之别。战国前期,各国诸侯争为天下霸主,士因其成为他们争相礼聘重用的焦点,士人心态有着为王者之师的自信。战国后期,士人随着自身政治地位的下降,其职责便转向为调笑娱乐的娱宾自伤,促使他们由学者型之士转向文人型之士。章学诚在《校雠通义·汉志诗赋》中指出战国后期文人之士与战国前期学者之士的渊源流变关系:“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对问,《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21]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指出屈原之后楚国之士在议政方面的尴尬局面:“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22]1940 作为文学侍臣的宋玉,其创作只能是在娱悦君王的前提下适度地讽谏。对此,吴广平先生认为:“从屈原的直谏发展到宋玉的曲谏,反映了楚国政治日趋黑暗的历史背景下君臣关系的变迁轨迹和文人话语方式的调适历程。而宋玉运用曲谏正是其地位卑微和生存艰难的体现。”[23]赵辉先生在《屈、宋创作身份结构的差异与创作的异同》中也指出,宋玉以文学侍臣这一职官身份为当下身份的创作,言说的对象为楚王,目的在于娱乐,故既不可能像《九辩》那样去诉说不遇的愁苦。文学侍臣,职掌以话语或文字取悦君主。故这一身份的言说,虽然在其他场合也可以像优旃就政治问题进行言说,但在娱乐场合,目的在于取悦君主,故自然不可能如同其他的职官那样,去言说法令制度或者如何治理国家,改善政治。而是采用由隐语为主干发展而形成的赋体,以恢谐、幽默、滑稽去搏君主一笑[24]。 (二)作品功利性的消减。 战国时期,周朝的礼乐制度进一步衰落,文学的教化功能亦受到削弱。尤其对于本身较少受到中原礼乐文化影响的楚国而言,其本土文学的教化功能更加颓弱。文学教化功能的削弱,在客观上反而促进了文学审美功能的加强。楚国文学呈现出与学术逐步脱离,由杂文学向纯文学转变的趋势。对此,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论述到:“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飚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蠢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衡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25]671-672刘勰尤其推崇宋玉辞赋在极尽文章修辞之能事方面的先导意义,比如夸张、铺排、对比等等。对此,他在《文心雕龙·夸饰》指出:“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25]608而在《文心雕龙·谐隐》中则指出,由于宋玉所处时代与个人身份的双重原因,宋玉辞赋的诙谐娱乐功能,在客观上要大于其直言讽谏功能:“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讌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25]270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刘勰强调文章需要美饰,但刘勰没有纯文学的观念,所以其文体论将辞赋和其它实用文体放在一起加以论述。这也从侧面说明,宋玉赋实际上依然具有较强的功利目的,只是相对而言,其娱乐性质也得到了极大地增强。 (三)辞赋文体的嬗变。 宋玉的辞赋创作,正处于辞体向赋体的嬗变时期。“辞”,为诗人之赋,承载了诗教功能。“赋”,为“辞人之赋”,因丽而淫。宋玉在屈原之后别开生面,创立赋体文学,成为赋体文学的开山祖师,在楚辞、楚赋和汉赋之间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22]1940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兔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25]135明确把宋玉列为荀子之后,枚乘、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班固、张衡、王延寿等人之前的一位辞赋大家,可知宋玉在辞体向赋体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许结先生曾在《论宋玉赋的纯文学化倾向》中指出:“宋玉赋首次将赋”作为自觉的文体脱离诗的襁褓,标示中国文学由《诗经》而《楚辞》到“汉赋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26]自南朝任昉《文章缘起》把赋的创始人归功于宋玉之后,历代批评家大多应声而和,如清人程廷祚在《骚赋论·上》中说:“或曰:骚作于屈原矣,赋何始乎?曰:宋玉。”[27]清人张惠言在《七十家赋钞叙目》中评价宋玉赋时说:“及其(屈原)徒宋玉、景差为之,其质也华,然其文也纵而后反。”[28]张惠言在《七十家赋钞叙目》中,不仅肯定了宋玉在赋体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明确指出宋玉赋崇尚文采,与荀卿之赋的尚质风格迥异,然而后世赋家大多以宋玉赋为宗法,因此可知,宋玉对于赋体的发展演变有着不可忽视的开创性功绩。 (四)文学自觉意识的加强。 战国中晚期,文学的自觉意识逐步提升,从屈原到宋玉,辞赋作品逐步显示出对文学独立审美性质的追求。宋人李纲在《文乡记》中说:“下逮战国,文乡浸衰,深醇雅正之风变,而为纵横捭阖之俗。独屈原、宋玉之徒崛起其间,颇有古意,博辩瑰丽,未免有感愤谲怪之作。识者谓体慢于三代,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不其然欤!”[29]宋玉在屈原的基础上,实现了辞赋文学性的进一步张扬,因此遭到了以汉代儒学家的斥责,认为宋玉辞赋是对诗学正统的背离。对此,刘刚先生指出,两汉学者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儒学规范之上的,他们对文学虽有了初步的认识,但仍把文学看作经学的附庸,他们还不能以文学观的价值取向评论文学家及其作品。因此,在汉代文学批评中,汉儒极力贬低宋玉现象的发生就不可避免[30]。李炳海先生也认为:“辞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纯文学阶段的开始和文人群体的生成,辞赋关于作家的创作又经历了从屈原到宋玉的转变。如果说屈原的作品还没有完全和现实政治脱钩,还处于半自觉状态,那么,宋玉等赋家已经把文学创作当成人生娱乐的重要方式,在作品中表现出明显的唯美倾向。”[31]后世的辞赋作品也由此而更加注重辞采,表现出对文学之美的自觉追求。 宋玉对先秦文学意象进行改造,一方面是辞赋文学自身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庙堂讽谏的需求。与前贤如屈原对国事的肆意批评相比,宋玉涉政言论的发表则极其不自由,不得不借助于纡徐婉曲之笔,以避灾远祸。对此,明代陈第论述极为详尽:“愚读《九辩》,其志悲,其托兴远,其言纡徐而婉曲,稍露其本质,即辄为盖藏,以此伤其抑郁愤怨之深,亦以此知楚王之终不悟,而党人接迹于世,故恐有不密,阶祸而波及于罪也,不亦悲乎?夫原,介而不屈,忠而见逐,其设心本以死自誓,故其出词,直致而无复讳忌。……玉即殉其师以死,亦何益成败之数乎?虽然北郭骚以头白托晏子,亦感其分粟养母已耳。师弟子之恩,故不止此。太史公曰:‘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愚谓宋玉诸赋,大抵婉雅之意多,劲奋之气少,律以北郭骚,难矣哉!难矣哉!”[32]不仅道出宋玉辞赋创作的复杂政治背景,亦点出宋玉故意隐藏于其辞赋作品中的抑郁愤怨之情与婉言讽谏之意,更指出后世批评家对于宋玉及其辞赋的批驳的确有失公允。 赵辉先生在《先秦文学主流言说方式的生成》中提出:“先秦礼乐政治形态的言说都是一定时空的限定场合的言说。先秦的文坛隐含于神坛和政坛,同是‘限定时空’的言说。先秦‘文学’既隐含于礼乐政治形态的‘限定时空’言说中,礼乐政治形态的特定言说场合就自然转换为‘文学’的言说场合,其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就自然转换为‘文学’的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从而在赋予‘文学’言说‘限定时空’言说特征的同时,将‘文学’言说主体始终置之于特定场合、主体身份和言说对象关系的规定之下,使其丧失独立和自主性,必然沿袭礼乐政治言说的伦理原则。”[33]由此可知,宋玉辞赋对先秦文学意象的改造,也属于“先秦礼乐政治形态‘限定时空’的言说产生的伦理原则支配下维护等级之间‘和而不同’的‘讽喻’言说方式顺理成章的置换”[33]。 宋玉辞赋对先秦文学意象化用重构之后,形成具有审美价值的纯文学意象,促使文学与学术逐步走向分离,但在客观上也弱化了辞赋的讽谏教化作用。历代批评家并非意识不到宋玉辞赋的文学之美,但是他们将宋玉辞赋纳入到儒学统序中加以考察和评价,从而得出宋玉辞赋“丽以淫”的负面结论,从而造成对宋玉辞赋的有意误读。当然,宋玉辞赋讽谏功能的实际效果,相对于儒家六经而言,的确是微不足道的。与此同时,以汉儒为代表的后世批评家对宋玉辞赋的批驳,不仅说明了自汉代开始,宋玉及其辞赋的政治地位得到逐步提升,影响范围也逐渐扩大,也意味着从汉初司马迁开始,辞赋已经不再囿于楚地文学和宫廷娱乐文学,其学术地位也逐渐得到提升,成为汉代学术领域重要研究对象之一。标签:屈原的故事论文; 宋玉论文; 文学论文; 登徒子好色赋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屈原论文; 神女赋论文; 高唐赋论文; 楚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