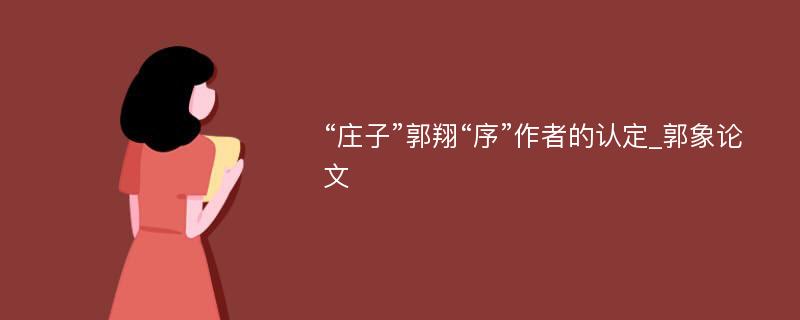
所谓《庄子》郭象《序》作者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专家点评:1978年王利器先生依据《宋会要辑稿》的相关史料,在《哲学研究》发表论文《〈庄子序〉的真伪问题》,认为该序不是出自郭象之手,引起了中国哲学史界的关注,但并未得到认可,原因有二:一是文献证据力度不够,二是没有举出有力的“内证”,说明《庄子序》与《庄子注》之间的思想差异。因此,学术界仍将《庄子序》视为郭象《庄子注》的纲领。博士生黄圣平的这篇论文,在前人基础上取得了新进展。尽管在文献方面做了更细致的梳理,并对真实作者的时代和身份作了推测,但是该论文最突出的特点,是从“内证”角度对所谓郭象《庄子序》证伪,指出了该《序》与《庄子注》在义理方面的抵触之处,证据有六条之多,尤其是对两者“方外”观念差异的分析,准确到位,可备一说。
避开当代前辈名家已反复讨论的重要课题,在相对冷僻的领域拓荒,对后学者来说不失为好经验。但富有首创精神青年学者积极参与正面进攻学术重镇,却是学科发展的希望所在。犹如在魏晋玄学领域无法回避郭象那样,研究郭象则无法绕开《庄子序》的真伪问题,它关系到对郭象玄学理论主旨的理解。我长期在郭象哲学外围俳徊,近二年试图进入其内部(注:拙作《从〈庄子注〉看〈庄子序〉的真伪问题》(《文史》2002年第4期),尽管早于黄圣平的论文发表,且观点基本相同,但所持论据各异,是各自独立研究的结果。),深知这个论题的份量。读黄圣平文赞赏其勇气和敏锐,“后生可畏”。
王晓毅(注:王晓毅,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国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魏晋思想和中国思想史研究。)
所谓《庄子》郭象《序》(下简称《庄子序》),文辞宏丽,义理精微,提要精当,是一篇好序文。但关于此序文之作者,却有一桩公案以待解决。
一、史料的剖析
问题出在北宋景德二年崇文院开雕《庄子》时。《宋会要辑稿》之《崇儒四·勘书》记载道:
景德二年二月,国子监直讲孙奭言:“诸子之书,老庄称首,其道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逍遥无为,养生济物,皆圣人南面之事,故先儒论撰,以次诸经。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三十卷,内《老子释文》一卷,《庄子释文》三卷。今诸经及《老子释文》共廿七卷,并已雕,即颁行;唯阙《庄子释文》三卷,欲望雕行,翼备一家之学。《庄子》注本,前后甚多,率皆一曲之才,妄窜奇说,唯郭象所注,特会庄生之旨,亦请依《道德经》例,差官校定雕印。”诏“可”。仍命奭与龙图阁待制杜镐等同校定刻板。镐等以《庄子序》非郭象之文,因删去之。真宗尝出序文谓宰臣曰:“观其文理可尚,但传写讹舛耳。”乃命翰林学士李宗谔、杨亿、龙图阁学士陈彭年等,别加雠校,冠于篇首。
赵宋在朝庭秘书省设有会要所,《宋会要》即依当时国史实录院之实录与日历,及其它史料,就史实之性质区别并加以归纳而成。官修原本宋时从未刊行,且其后早已流散殆尽,仅余后人所辑之《辑稿》(如上段引文即出自《辑稿》),但赵宋政府容许臣民自由传抄,故或有旁的资料能够进一步予以说明?
查南宋程俱所撰之《麟台故事》卷二,其曰: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崇文院检讨杜镐校南华真经摹刻版本毕,赐辅臣人各一本。……(景德中朝)二年二月诸王府直讲兼国子监直讲孙奭言《庄子》注本,前后甚多,唯郭象所注,特会庄生之旨,请依《道德经》例,差馆阁众官校定,与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三卷雕印。诏奭与龙图阁待制杜镐等同校定。……至大中祥符四年又命李宗谔、杨亿、陈彭年等雠校《庄子序》,摹印而行之。盖先是崇文院校《庄子》,本以其非郭象之文去之。至是,上谓其文理可尚,故有是命。
南宋江少虞所撰之《事实类苑》卷三记载道:
景德二年诏国子监直讲孙奭、龙图阁待制杜镐等同校定《庄子》。镐等以《庄子序》非郭象之文,因删去。
真宗尝出序文谓宰相曰:“观其文理可尚,但传写讹舛耳。”乃命翰林学士李宗谔、杨亿、直学士陈彭年龙图阁待制等别加雠校,冠篇首。
《玉海》卷四十三写道:
景德二年二月甲辰,校定《庄子》,并以《释文》三卷镂版。后又命李宗谔等雠校《庄子序》。
又卷五十五写道:
祥符四年十一月丙子,命李宗谔、杨亿等校《庄子序》摹版。
将以上史料予以整理和分析,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其一:在宋真宗时期,对《庄子》及其序文的处理是有一个过程的。其过程是:
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国子监直讲孙奭奏请开雕《庄子》。同年二月,诏命与龙图阁待制杜镐等一同校刻;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历时三年,孙、杜等人校刻《庄子》毕。杜镐以《庄子序》非郭象所作而删之;
同年六月,真宗赐辅臣人各一本孙、杜二人校订定稿、并删其序的《庄子》;
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2年),真宗谓宰臣曰《庄子序》“文理可尚,但传写讹舛”,并命李宗谔、杨亿和陈彭年等予以校订。三人校订后,冠《庄子序》于《庄子》篇首。
显然,在以上过程的罗列中,有两点值得引起注意:(1)孙、杜二人校订后,其《庄子》版本随即被真宗“赐辅臣人各一本”,亦即在社会上开始流行;(2)真宗提出《庄子序》“文理可尚”应该重加校订是在大中祥符四年,也就是说是在杜镐删《庄子序》三年之后。这两点很重要,有助于我们解决《庄子注》作者之公案。
其二:《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无误。其关于《庄子序》之处理过程的记载,经过《麟台故事》、《事实类苑》和《玉海》的佐证,能够完全得到证实。据三书之《四库提要目录》,《麟台故事》是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由程俱所上,其“所记皆宋初馆阁之事,典章文物,皆灿然可观”,“作是书时得诸官府旧章最为详备”,盖程俱其时正为秘书省之少监也;《事实类苑》则书成于绍兴十五(公元1146年)年,其作者江少虞以“宋代朝章国典见于诸家记录而畔散不属,难于稽考,因为选择次之”,“北宋一代遗闻逸事略具于斯”而“所引之书悉以类相从,全录原文,不加增损”,应甚为可信;至于《玉海》,乃(宋)王应麟所撰,据该书《提要》,“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其可为有力之佐证亦无疑矣。
其三:孙、杜等对《庄子序》的处理依据无误。如此论断,原因有二:(1)依上所言,孙、杜二人所校订并删序之《庄子》在社会上流行了三年,但并未有人提出异议,说明社会是认同二人删弃《庄子序》之行为与理由的;(2)宋真宗三年后旧案重提,要重新校订《庄子序》,对孙、杜二人的删序行为提出了意见,但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反对孙、杜的删序依据。其说见下。
其四:宋真宗的旧案重提是有道理的。原因在于,孙、杜二人,尽管他们删弃《庄子序》的理由是无误的,但并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充分的。因为,《庄子序》,作为《庄子》之序,并不需因为《庄子注》为郭象所作其序就亦须非郭象所作不可,更何况与《庄子》同版刻雕的除了郭象之《庄子注》外还有陆德明之《经典释文》,也就是说此《庄子》版本实乃庄周之本文、郭象之注文和陆德明之释文三者的混合体,并非郭象之注文的独行。故,作为其序文,以其非郭象所作而予以删弃,本就理由不充分,其删弃的行为也就是不必要的(其实,即使是为郭象所著之《庄子注》作序,也并非郭象本人不可)。至于其存在的问题,如宋真宗所言之“传写讹舛”,则可通过校订予以清除,而作为其优点之“文理可尚”,则理应可作为此混合之《庄子》版本序文得以流传下去的主要依据。真宗出该序文谓宰臣曰“观其文理可尚,但传写讹舛耳”,并诏命李宗谔等人校订之,其此举动对于保存此篇序文是有功劳的(至于他所言之“但传写讹舛耳”,其中的“但…耳”之语气,乃是针对“文理可尚”之优点而发的,是指从作为《庄子》之序的标准的角度看,此序所存在的唯一问题就是这“传写讹舛”了,故构不成真宗认为此序乃郭象所著的一个依据)。
其五:李宗谔等人的处理并不构成反证。依据《宋会要辑稿》等所载,李宗谔等人在校订《庄子序》之后将之“冠于篇首”,则他们在清除《庄子序》中存在的“传写讹舛”的问题之后,依据宋真宗的意见,将《庄子序》重新作为《庄子》之序文,这是无疑问的,但所有的史料都没有载明他们认为此序文乃郭象所撰,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直接否定了孙、杜二人的删序行为,但还是没有否定二人的删序依据。《庄子序》应该冠于《庄子》篇首,但不应该冠子郭象名下,这应该是分析以上史料后我们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
其六:以《庄子序》为郭象所撰的观点难以立足。原因在于它难以回答以上史料中的几个问题:(1)孙、杜二人对《庄子序》的处理措施和其依据;(2)社会对孙、杜二人处理措施长达三年的认同而不提异议;(3)宋真宗作为“近世好学之主”,在否定孙、杜的处理措施而为《庄子序》的存在辩护时,只强调其“文理可尚”,却并没有直接否定他们的删序依据。也就是说,依此观点无法把以上的史料都统一起来,但如上所分析的,倘以《庄子序》非郭象所撰,我们是可以把这些史料都讲通的,它们是可以都统一到后一种设定上的。
其七:后世以《庄子序》为郭象作品应属误传(注:如王雱在其《南华真经新传·拾遗》之“卮言”部分即写到:“此周之为言,虽放纵不一而未尝离于道本,故郭象以庄周为知本者也,所谓知庄子之深也。”由此也可见王雱决不是《庄序》的作者了。)。误传之因,推测起来,一方面,可能还是因为李宗谔等人在将《庄子序》冠于篇首时,由于史料的缺乏,他们也没有考证出真正的作者,故令后世仍然能够以讹传讹,将此序文冠于郭象名下;另一方面,则应该与此序文的内容有关。通观此篇序文,我们能够发现其与郭象《庄子注》之间确实存在内在而又紧密的关系,而这正是需要我们在后面给出解释的。
二、思想的比较
在上面,我们从史料分析的角度得出结论,认为《庄子序》不是郭象所作。下面,通过比较《庄子序》和郭象《庄子注》中的思想,找出二者间存在的思想差异,应该更能够从内证的角度说明我们在上面得出的结论。为了比较的方便,先将《庄子序》原文抄录如下:
夫庄子者,可谓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虽无会而独应者也。夫应而非会,则虽当无用,言非物事,则虽高不行;与夫寂然不动,不得已而后起者,固有间矣:斯可谓知无心者也。夫心无为,则随感而应,应随其时,言唯谨耳;故与化为体,流万代而冥物,岂曾设对独遘而游谈夫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经而为百家之冠也。
然庄生虽未体之,言则至矣: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绰,其旨玄妙,融微旨雅,泰然谴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义之所适,猖狂忘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淡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仁极夫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夫已能,忠信发夫天光,用其光则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也。
故其长波之所荡,高风之所扇,畅夫物宜,适夫民愿,弘其鄙,解其悬,洒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观其书,超然以为已当,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恍惚之庭矣;虽复贪婪之人,进躁之士,暂而揽其余芳,仿佛其音响,犹足旷然有忘形自得之怀,况探其深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绵邈清遐,去离尘埃而返冥极者也。
经过仔细的比较,我们认为,在《庄子序》和《庄子注》的思想之间存在如下的差异:
其一,二者对《庄子》的认识和态度有别。
看《庄子序》,可知《庄序》作者认为《庄子》通篇都是“狂言”,是“设对独遘而游谈夫方外”,因“应而非会”、“言非物事”,故“虽当无用”、“虽高不行”,正所谓空谈阔论、不切实际,与无心者之圣言大有其别。那么,郭象在《庄子注》中是否也这样认为呢?看《庄子·天下注》中有关庄子的注释:
累于形名,以庄语为狂而不信,故不与也(注“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句)。
庄子以平意说己,与说他人无异之,察其辞明为汪汪然。禹拜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再看《大宗师注》:
是故庄子将明流统之所寄以释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称仲尼之如此,或者将据所见以排之,故超圣人之内迹而寄方外于数子,宜忘其所寄以寻述作之大意,则夫游外冥内之道坦然自明,而庄子之书,故是涉俗盖世之谈矣。
显然,在《庄注》中,郭象与《庄序》作者对《庄子》的认识和态度是判然有别的。在他看来,阅庄者以庄言为“狂而不信”,那是其自身“累于形名”的缘故,怪不到庄言本身的头上,而倘他能“忘其所寄以寻述作之大意”,则能看得很清楚,能够看得出所谓“庄子之书,故是涉俗盖世之谈矣”,又哪里认为《庄子》是“虽当无用”、“虽高不行”之“狂言”了呢?能“察其辞”者,则“亦何嫌乎此也”,也就是说对庄子特有的表述方式自然就能够理解,又哪里会因为其“设对独遘”而认为他只是“游谈夫方外”而不切实际呢?郭象之看法,仔细品味,不仅与《庄序》有别,且倒似乎是正针对与后者类同的观点而发的,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其二,二者对儒门经典的认识和态度有别。
在《庄序》中,其作者以孔和庄、无心者和知无心者、谨言和狂言,以及六经和百家(“非经而为百家之冠”)并列,说明在其眼中,儒门六经仍然有着崇高的位置,位于诸子百家之前,就象孔子在人格上即位于老庄之前一样。这大概是自王弼以来魏晋玄学的传统观点,而郭象也是承认孔子的圣人地位的,但对于儒门六经,他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如他说:
非以此言为不至也,但能闻而学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则虽闻至言,适可以为经,胡可得至哉!(《庄子·庚桑楚注》)
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则六经也。(《庄子·天运注》)
夫与化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经以说则疏也。(《庄子·天运注》)
从上面的几条引文我们可以看出,郭象对待儒门六经,其态度与《庄序》大有区别。在他那里,“六经”是“迹”,圣性是“冥”,二者间尽管有“迹冥圆融”的一面,但为了批判名教之治,他的注文重点往往是放在对二者之别,放在“迹”对“冥性”之遮蔽与板结的论述上。从这一认识出发,他认为“六经”乃“迹”而非“所以迹”,“为经”则“不至”,故“若播六经以说则疏也”。显然,这里没有半点对儒门六经的尊崇态度,这与《庄注》是很不相同的。
其三,二者对“方外”的认识和态度有别。(注:此论点经由导师李中华教授的启发而成。)
“方内”与“方外”之别出自《庄子·大宗师》中“子贡问礼意”一段,其中以孔子为“方之内者”,而以子桑户等三人为“方之外者”,其“方”之意涵乃是方位上的,正所谓世俗社会(庙堂)与世外自然(山林)之别。在这一意义上,“方内”和“方外”正如孔子所言乃“外内不相及”,也不可能相及。观《庄子序》,其对“方外”的使用显然还是在《庄子》原义上的,也就是说是以“方外”为“世外自然(山林)”。
但,我们看郭象的《庄子注》,能够发现他的思想在这里较《庄子》有了很大的发展。他说:
人哭亦哭,俗内之迹也;齐死生,忘哀乐,临尸能歌,方外之至。
其所以观示于众人者,皆其尘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
以方内为桎梏,明所贵在方外也。
所造虽异,其于由无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内,然后养给而生定,则莫不皆然也。
在郭象的注文中,显然,尽管“方内”的含义仍然是“世俗社会(庙堂)”,但“方外”的内涵则已经发生了改变,已经是“齐死生,忘哀乐,临尸能歌”,是“冥物”,是“无心”和“无事”,也就是说已主要是指一种超越的精神境界。与这种高邈的境界相比,沉入世俗之方内者当然是层次甚低的,以“方内”为“桎梏”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圣人,有了这种高邈的精神境界,无事以得事,无可无不可,自方外以共内,自然是能够游外冥内,外内相及,与《庄子》和《庄子序》所言大有不同了。可见,二者在这一方面也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其四,在《庄子序》中,我们能够看到佛学影响的痕迹。
此一观点也许有些奇怪,但让我们看《庄子序》中的如下两句:
夫心无为,则随感而应,应随其时,言唯谨耳;故与化为体,流万代而冥物,岂曾设对独遘而游谈夫方外哉?
用其光则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也。
显然,在此二句中,“流万代”的主体是“无心者”,“独化”且“源流深长”的主体乃是“神器”。依《庄序》,“无心者”是能够“流万代而冥物”的,但依郭象《庄子注》,我们知道,由于“圣不世出”,圣人要想“冥物”而又“流万代”那是不可能的。在后一句中,“神器”的含义或可商榷,但个人以为,《庄序》是转引郭象《庄子注》中对“神器”一词的用法,其含义乃是指天下万物(注:郭象对“神器”一词的使用,在《庄注》中有二例,分别是《秋水注》“惑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机而伤其神器也”和《天下注》“巧者有为,以伤神器之自成”,二者中“神器”之含义均是指天下万物。);而万物,依《庄注》思想,乃是各有其极的。“终始者,物之极也”,物尽其极为“全”,进而“生者独化而生”且“死者独化而死”。这样,在物之“独化”的过程中,有始有终,有生有死,乃至于死生且不相关,哪里会有“源流深长”的可能?个人以为,这种认为人之存在可以“流万代”而“冥物”和“独化”且“源流深长”的观点应该是受到了佛教神不灭思想的表现,而我们知道,在郭象《庄注》中,尽管有“一气而万形”的观点,但神不灭的思想是无论如何都没有的。
其五,《庄序》与《庄注》的文章风格有异。(注:此论点经由导师李中华教授的启发而成。)
郭象注《庄》,随文而行,故多短句小文,但也有一些较长篇幅的注文,如《齐物论》中之注“天籁”与“罔两问景”段就是很好的例子。观此类注文,可以发现郭象的文章风格是带有辩说特征的散文体裁,与《庄序》之带有骈俪化特征的赋体风格有明显的差异。《世说新语》等古籍中对郭象才能的记载很多,多言其清谈时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但却未见到其有关文学才能的记载,倒是说及他的受困于裴遐的“音辞清畅,泠若琴瑟”,这也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当然,从魏晋以来,论体文骈俪化的倾向就已经很明显,“自两汉末叶以来,已经有骈体为论说之趋势”(注: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中国文学三论》第三种,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5页;转引自彭玉平《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嵇、阮之文,艳逸壮丽,大抵相同”(注:《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转引自彭玉平《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而进入东晋,名士如谢安、王羲之、支遁等都是“才藻新奇,花烂映发”、“叙致精丽”而又“才峰秀逸”的。可见,依《庄序》之骈俪化的文章风格,或可推断其非郭象所作,但倘由此将《庄序》之时代过于推后,那也是不太恰当的。
其六:二者对庄子其人的认识和态度是有差异的。
让我们看《让王》篇中郭注中的一段:
此篇大意,以起高运远让之风。故被其风者,虽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犹时慨然中路而叹,况其凡乎?故夷、许之德,足以当稷、契,对伊、吕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虽不俱为圣佐,不犹高于蒙尘埃者乎!其事虽难为,然其风少弊,故可遗也。…
我们再看《庄序》之最后一段所言:
故其长波之所荡,高风之所扇,畅夫物宜,适夫民愿,弘其鄙,解其悬,洒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观其书,超然以为已当,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恍惚之庭矣;虽复贪婪之人,进躁之士,暂而揽其余芳,仿佛其音响,犹足旷然有忘形自得之怀,况探其深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绵邈清遐,去离尘埃而返冥极者也。
两相比较,应该说意思基本一致,句式也基本一致,但一用以言夷、许,一用以言庄子。对于夷、许之德,郭象认为是“居山谷而弘天下者”,故“其事虽难为,然其风少弊,故可遗也”,但对于庄子其人,就《庄子注》中的记载看,郭象的态度应该说是有不同的:
庄子清高,笑彼名利。(《庄子·列御寇注》)
夫庄子推平于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毁仲尼,贱老聃,上掊击三皇,下病痛其一身也。(《庄子·山木注》)
可见,对于庄子,郭象的态度是很尊崇的,在《庄子注》中也没有象《庄序》首段那样对其人略加贬斥,而是有推崇,有解释,也有打圆场的地方(其打圆场,目的应该说还是为了使庄子避免受到当时士人的攻击,是为了维护庄子的声誉),这与其直接批评夷、齐的态度是有区别的。看《庄序》,很明显,其作者把庄子看成了夷、齐一类的人物,认为他们都是“居山谷而弘天下者”,而在郭象看来,庄子之言,倘正确理解,倒实在是“涉俗盖世之谈”的。二者的认识和态度,细加比较,应该说确实是有一点差别的。
总之,通过以上的史料分析和思想比较,我们发现《庄序》和《庄注》之间有着不少的区别,同时以郭象为《庄序》之作者也不能够将有关的史料统一起来,故《庄序》的作者不应该是郭象。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问,既然《庄序》的作者不是郭象,那么,从正面加以论说的角度,我们能够作出什么样的分析呢?
三、《庄序》作者略探
仔细分析《庄序》之内容,结合郭象注庄的背景,对于《庄序》的作者,我们能够作出如下的分析:
其一,《庄序》作者是对《庄子》极为熟稔的庄学士人。
如此论断,可以从《庄序》对《庄子》较多的原文征引中得到论证。突出的,如“含哺而熙乎淡泊,鼓腹而游乎混茫”显然是对《马蹄》篇“赫胥氏之时”一段中“含哺而熙,鼓腹而游”的直接转引;“不知义之所适,猖狂忘行而蹈其大方”则是源于对《山木》篇“建德之国”文“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忘行,乃蹈大方”的引用;至于“经昆仑,涉太虚”两句,则应该是出自《知北游》篇之“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一句并对其加以反引了。类似的例子还有。总之,从《庄序》对《庄子》较多的原文征引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庄序》作者应该是对《庄子》极为熟稔的庄学士人。
《庄序》作者,在其写作《庄序》时,应该是在为《庄子》而不是郭象之《庄子注》作序。《庄子序》是《庄子》之序,而不应该被认为是《庄子注》之序,原因在于:一方面,我们已经在上面证明了《庄序》的作者不是郭象,因此以郭象为己注作序的看法就可以休矣;另一方面,我们看《庄序》,分析其内在结构,能够看出其第一段是论庄子其人和其书,第二段是论庄子之学,第三段则是论庄学之用,总合而论,《庄序》之内容和主题都是关于庄子其人、其书和其学,而不是关于郭象其人、其注和其学的。因此,得出《庄序》乃《庄子》之序,而非《庄注》之序的观点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当然,比较《庄注》与《庄序》,我们可以看出《庄序》思想受到了《庄注》很大的影响,《庄序》中对庄子其人、其学和其用的观点都是玄学化了的,但这可说明《庄注》对《庄序》有影响,却构不成《庄序》是在为《庄注》作序的依据。
其二,《庄序》作者是对郭象《庄注》极为熟稔的玄学士人。
如是论断,原因有三:(1)在这篇不到四百字的简短序言中,郭象《庄注》中所特有的范畴大量地出现,如“应”、“会”、“冥物”、“寂然不动”、“不得已”、“与化为体”、“至”、“当”、“独化”、“玄冥之境”、“冥极”和“兼忘”等等,它们或在《庄子》中出现过,但却是在郭象《庄注》中方才成为独立的哲学范畴,故对它们的应用突出地表现了《庄序》作者对郭象《庄注》是极为熟悉的;(2)《庄序》中也有一些内容是对《庄注》原文的直接引用,如“至仁极乎无亲”句是对《天运注》中“至仁在乎无亲”的引用,而“独化于玄冥之境”句则是对《大宗师注》中“况乎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句和《徐无鬼注》中“意尽形教,岂知我之独化于玄冥之境哉!”句的直接引用;(3)《庄序》对郭象《庄注》中的思想作了精要的概括。这种概括,我们知道,它是以对庄子本人思想进行总结的形式出现的(正是为此,我们认为不能视《庄序》为《庄注》之序),而这种总结,由于其作者眼中的庄子已被完全玄学化,乃至郭象化了,故也相应地是对其时玄学中庄学(尤其是郭象庄学)思想的精要概括。这种概括,如“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如“至仁极夫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夫已能,忠信发夫天光”,如“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等等,可以说是对郭象思想的摄魄与勾魂,是以简短之语将郭象庄学凝结在了这篇小序之中。郭象是西晋后期的思想家,其《庄子注》流行于西晋末期,故我们可推断出《庄序》之撰作应该是在西晋之后,盖西晋后期正当社会动乱之时,而思想之传播与消化亦应有一个时段也。
其三,《庄序》作者极有可能是东晋前期的一位玄学名士。
如是论断,原因亦有三:(1)《庄序》中所概括之“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个人以为,因其是对郭象《庄注》中“神器”和“独化于玄冥之境”思想的总结,故能够成为对郭象逍遥观的精练理论表述,同时它也说明《庄序》作者犹然是服膺于郭象之逍遥义的,而我们知道,在东晋后期,当佛学大量进入思想界后,郭象的逍遥义就为支遁的逍遥义所代替了,故《庄序》产生之时代应是在支遁逍遥义流行之前;(2)《庄序》中除了有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神灭论思想影响的痕迹外,其主导思想可以说完全是玄学的,因此其产生的时代应该是在玄学普遍流行的晋朝,而不应该是在更后的南朝、隋唐乃至北宋时期;其后几个时期的思想都表现出很明显的儒、释、道三教并行和互补的特征,这与《庄序》中以老庄为本,在玄学的基础上融合儒道的思想是大有不同的;(3)《庄序》的思想和风格与东晋前期的时代精神完全吻合。我们知道,东晋前期,士族名士们清谈成风,名流辈出,如开国之君元、明二帝和王导、庚亮等大臣,以及其后的简文帝、谢安等君臣,还有殷浩、刘惔、王濛、王羲之、孙绰、许询等等,都正是其中的清谈领袖。在他们的带领下,整个清谈场上人才辈出,盛况空前,但在义理上却以继承为主而少有发明,在庄学上以向、郭《庄注》思想为本而难出其外,至于论到庄、孔关系,他们则多坚持王、何的传统观点,以孔为圣人而以庄为大贤,二者之别且是所谓“有者”和“无者”之别;他们重义理、鄙章句,重神韵、崇清虚,注重语言的清朗和文辞的华丽,要求文章“掷地应作金石声”,认为如此方是其辈之语。这样的一个时代及其精神,倘我们将《庄序》移入其中,实在只能见有之吻合而不见其有冲突。至于所谓“又一个郭象却不见其作品传世”的问题,说来很简单,那是因为玄学名士们好清谈但不好著述,以前者为作乐而以后者为妨人作乐的缘故。向秀欲注庄,嵇康曰“此书庸讵须注,徒妨人作乐耳!”嵇康的这一回答可说是对名士们心态的极好反映了。
总之,《庄子序》的作者,由于史料的缺乏,尽管无法认定到个人,但我们层层追问,层层剥落,认为他应该是庄学士人,应该是玄学士人,但不是西晋后期的郭象,却极可能是东晋前期清谈名流中的一位名士。这,就是我们这篇文章最后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