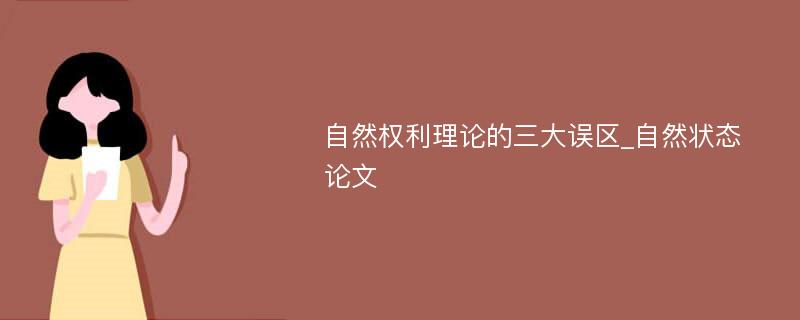
对自然权利理论的三个误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解论文,权利论文,理论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182(2006)03-0038-04
在西方思想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证人权的是近代西方自然法学派,该学派以自然法为依据,将人权理解为自然权利。正是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潘恩等自然法学家们的努力,自然权利的观念才深入人心,并成为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等伟大人权法典的原则和灵魂。但十九世纪以后,当自然权利理论所追求的人权不断转变为现实的法定权利的同时,自然权利作为一种理论却受到学术界,尤其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质疑和批判。其中,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质疑和批判有三种:其一,自然权利理论认为,人权就其性质来说是自然的,但人权能脱离社会关系吗?没有社会性的自然的权利存在吗?其二,就人权的适用性来说,自然权利理论认为,人权是普遍有效的道德准则和政治法律规范,但人权能超越于人的多样性,和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条件而成为普遍有效的规范吗?其三,就人权的理论依据来说,自然权利理论断言,人权以理性或自然法为依据,但是,人类行为领域中的价值判断存在确定不移的理性原则和自然公正吗?
人们通常认为,以上三种质疑切中要害。但笔者认为,这些质疑和批判并没有针对自然权利理论的本意,而是存在某些曲解或误解,因而并没有对自然权利理论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和挑战。下面具体分析为什么这些质疑是对自然权利理论的误解。
一、“人权的自然性”释义
近代西方自然法学家坚信人权的真实价值和有效性,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权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自然权利,这些权利是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需要,具有强大的现实基础和力量。在还没有公共权威和政治法律制度的自然状态中,人权就存在。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在自然欲望、自然需要和自然情感的驱动下享有自然的平等和自由。政治法律规范不仅不能违背这些自然的权利,而且要以对自然权利的尊重作为自身的合法性基础。政治力量和法律规范存在的全部理由就在于更有效地保护自然权利,从而使自然的权利转变为法定的权利。
随着自然权利理论的传播,人权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主流话语,但人权的自然性论断却遭到质疑,早在十八世纪,孟德斯鸠和伯克就强调权利和法律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因素和历史文化传统,而十九世纪的马克思更是对权利做出社会学分析的最杰出代表。正是他们的理论努力使法律、政治和道德的社会性观念几乎变成了常识。
通常人们认为,如果人类脱离任何社会政治关系,彼此之间独立生存,那么,作为传达和保存信息的语言与文字就不可能产生,人类的思维能力无法提高,科学与文明无法出现,人类的道德、人的价值与尊严等社会性的情感与观念也不可能产生,这种丧失了社会关系的人类只能是纯粹的动物之群,动物之群存在权利的调节原则吗?它们难道不是受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物自然法则的盲目支配吗?显然,权利与义务作为道德规范和政治准则不可能是自然的,它们是在社会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方式。自然权利理论的错误正是在于,不懂得人及其权利的社会性,它把人权理解为社会状态之外的自然状态中就已经存在并发生作用的自然法则,这是对人权性质的误解。
看来,人以及人权的社会性观念给自然权利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但是,我们要考察的是,它真的击中了自然法理论对人权性质的论断吗?
不可否认,自然法理论在字面上强调人权的自然性,而不是社会性,该理论将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对立起来,试图从自然状态或人的自然本性中寻求适用于社会状态中的道德准则。但需要指出的是,自然法学家所理解的自然状态真的是没有社会关系的人按照纯粹动物式的生存规则而生活的状态吗?我们可以看看洛克对自然状态的描述:
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1](p5)“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1](p6)“罪犯在触犯自然法时,已经表明自己按照理性和公道之外的规则生活”。[1](p7)
显然,洛克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存在财产权的、理性、文明和公道已经得到培植的社会状态,人们彼此之间存在着财产关系、财产纠纷和处理纠纷的道德准则,只不过还没有出现政府、法律,没有公共权威和共同的裁决者,此时,当人们彼此之间出现了权利纠纷时,当事人按照理性和公道来裁决自己的案件。可见,自然法学家心目的自然状态并不是没有社会关系的动物式的生存状态,而是还没有结成政治权力关系的社会状态,即一种无政府状态。洛克的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之间的关系实则为市民社会状态与国家状态之间的关系,这反映了洛克这样一种论证思路:他想从市民社会的自由生活中找出国家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
霍布斯所假定的自然状态也是一种无政府的社会状态,他对自然状态之下的人性作了极端利己主义的描述:
“当他外出旅行时,他会要带上武器并设法结伴而行;就寝时,他会要把门闩上;甚至就在屋子里面,也要把箱子锁上。他做这一切时,自己分明知道有法律和武装的官员来惩办使他遭受伤害的一切行为。试问他带上武器骑行时对自己的国人是什么看法?把门闩起来的时候对同胞们是什么看法?把箱子锁起来时对自己的子女仆人是什么看法?他在这些地方用行动攻击人类的程度不是正和我用文字攻击的程度相同吗?”[2](p95)
孟德斯鸠看出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的人并不是真正的自然状态的人,而是具有利益意识的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所以,他指出:霍布斯“是把只有在社会建立以后才能发生的事情加在社会建立以前的人类的身上。自从建立了社会,人类才有互相攻打和自卫的理由”。[3](p4)
所以,当人们通过人权的社会性攻击自然法学派的人权的自然性观念时,实际上是用有力的武器攻击了虚假的靶子。自然法学家并没有否认人的社会性,只是不承认人的政治性,他们认为,政治权力和法律规范并非从来就有,这些设施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创造的,自然法学家力图在非政治领域寻求政治领域必须遵从的规范。
直到今天,思想家们仍然从政治法律之外寻求法律规范和政治合法性的道德原则。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和诺齐克的“无政府状态”(或“自然状态”)的假设仍然是论证人权的理论模型。
可见,自然法学家所讲的人权的自然性并不是指人权具有脱离社会关系的性质,而是指人权不依赖于任何政治法律条件,因为在没有公共权力、政治和法律的条件下,人仍然存在作为人必不可少的自然情感和欲望,这些情感和欲望正是权利的直接基础和来源。人权作为基于人性的要求先于并高于政治权威和法律规范,并成为建立政治权威的理由和制订法律规范的依据。
二、道德与法治在于普遍和抽象
近代西方自然法学家在人权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上,坚持的是普遍主义的原则。他们认为,人权要求并不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法律状况,而是来源于人性的需求。所以,他们撇开了任何具体的社会文化特征和政治法律制度而抽象出自然状态这一概念,人权在自然状态中即存在,它是一种自然权利,追求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尊重他人的权利是一种自然法。
“自然状态”、“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等表述本身就是一种适用于任何人的普遍性话语。正如洛克指出:“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1](p6)
自然权利理论的这种普遍人权论受到种种质疑,其中最有力的质疑来源于人的社会性学说和文化相对主义。
坚持人的社会性观念的学者认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具体的,凡是具体的都是特殊的。现实中怎么可能存在普遍性的、抽象的人?既然没有普遍性的、抽象的人,也就没有普遍性的、抽象的人权。
不可否认,从存在论上说,每个真实存在的个体都是具体的,他们的自然特征和社会性的品质不同,甚至有优劣之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存在差异,但这一事实并不说明我们应该从道德上承认每个人的生命价值有高下之分。存在论并不等于价值论,没有普遍性的、抽象的人并不意味着没有普遍性的、抽象的人权。生活中的不同个体千姿百态,品质各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道义上撇开每个人的具体自然特征和社会身份而将他们视为无差别的存在,享有无差别的价值和尊严。真正的道德恰恰要求我们抽象,要求我们无差别地、平等地对待每个人。没有抽象就没有道德;没有抽象就没有法治。法治的精髓就是抽象原则和普遍性原则,公正合法的审判只能是撇开被告的性别、种族、肤色、受教育状况、财产状态、社会政治地位、宗教信仰、政治见解及其它见解等具体特征,而把他(或她)作为一个抽象的人对待,抽象是实现公正的保证,公正的司法并不关注被告是谁,只依据法律与实事。自然法学家们并非不懂得在存在论上个体及其观念的特殊性,但他们所处理的是人权价值问题。如果缺乏普遍性,如果每个人的权利得不到平等的尊重,也就丧失了人权的道德价值。存在论不能混同于价值论,我们不能根据人是千差万别的这一事实来论证不同的人应该受到不同的对待。自然权利理论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并不是对人的具体性和多样性的否定,而是通过普遍适用和平等对待给人权寻求道德基础。
文化相对主义对自然权利理论的普遍主义原则的批判更引人注目。文化相对论者认为,任何权利和价值都是由特定的文化观念孕育和决定的,而不同民族的文化总是特殊的。既然世界上不存在统一的普世性文化,也就不存在普遍的人权。事实上,自然权利观念并非“自然”,普遍人权并不“普遍”,它不过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将自然权利普遍化反映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文化的相对性是否意味着一个民族创造的任何文明成果(如科学技术和某些道德价值)都只能由该民族享用而无法适用于其它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否意味着不同文化毫不相容?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现实上看,自然权利理论所捍卫的基本人权已成为跨文化的共识。
从逻辑上看,自然权利理论确立的人权是生命权、人身安全权、自由权、财产权、反抗压迫的权利,这些人权是最低限度的、消极的权利,它是确保人的身体、情感和精神的完整性所必需的权利,没有哪一种文化会构成蔑视这些权利的充分理由。正如美国学者唐纳利指出:“禁止任意虐待,要求公正审判,看来已经被所有文化承认是具有约束力的。……在几乎所有文化中,生活、社会秩序、家庭不受专制统治、禁止非人的和侮辱性的待遇、保证在共同体生活中的一席之地、有机会平等地享有生活资料都是核心的道德追求”。[4](P131)普遍人权并不会导致文化多样性的丧失,相反,对基本人权的普遍尊重是保护和繁荣文化多样性的最有效方式。
从现实来看,对国际人权规范的广泛共识是人权普遍性的具体体现。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承认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禁止奴役、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人人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等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由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古巴、智利、黎巴嫩等)和新兴独立国家(如尼日利亚和加纳等)共同制订,而当《宣言》投票通过时,48个国家投赞成票,8个国家投弃权票,但没有一个国家投否决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自然权利理论曾经捍卫的基本人权越来越成为不同文化的价值共识。
当然,不同文化对人权有着特殊的解释,但人权文化的特殊性并不是对基本人权的拒绝,而只是表现在人权范围上的分歧和实现基本人权方式上的差异。
三、价值判断和经验分析仍然离不开理性
权利、自由和正义等价值领域向来充满争议,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自然科学却具有确定性和逻辑必然性。为了给人权确立牢不可破的基础,近代自然法学家“完全沉浸于唯理论的科学理解之中”,[5](p78)他们深受自然科学中的理性研究方法的启发,力图把理性在自然科学中的权威引入法理学领域。在他们看来,既然人类具有理性,人类行为领域必定存在作为正义准则的自然法,正如自然事物的运动必定存在自然规律一样(事实上,在西方语境中,作为道德法则的自然法与作为物理法则的自然规律用同一词“natural law”表达),而尊重和保护人权即是自然法。人权是可以通过理性严谨地论证的,所谓理性论证,即是以人性的事实为前提,进行合乎逻辑的推导,由此可以得出与自然规则一样真实可靠的人权原则。但是,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家休谟以经验论对抗自然权利理论的理性原则。休谟将人类知识分为数学逻辑学、经验科学和人类行为三个领域,他认为,在数学和逻辑学中,运用的是演绎推理,只要前提是真,结论必然为真,只有这样一个必然性的领域才可称为理性的领域;而经验科学只能提供或然性知识,却不能提供理性的真理;至于人类行为领域,包括人权和自由在内的任何道德目标和价值判断更不可能是理性的原则,“道德规则并不是我们理性的结论”。[6](p497)当我们断言某种行为方式正当或合理的时候,我们所指出的不过是人类的某种意向、愿望或偏好,而不是确定不移的理性真理。人权作为一种价值只是反映人权主张者的道德偏爱和道德情感,而思想家以一种欺人的方式表达的个人偏好并不比其他人的偏好更有效和更值得尊重,所以当代学者麦克唐纳(Margaret Macdonald)指出:“说‘自由比奴役好’或‘一切人具有平等的价值’并没有陈述一种事实,仅仅是作出了一种选择,它宣称这即是我的立场”。[7](p49)
休谟等经验论者还认为,被自然权利理论用于推演出人权结论的人性前提也是可疑的,不考虑实际条件而只是从某种人性中推导出正义准则是一种武断的先验论。休谟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将事实与价值分开,使人们认识到价值领域并不是一个科学、理性的领域,从而开启了功利主义法学的新时代,并启发了实证主义法学。
经验主义者正确地认识到,人权作为一种价值不可能以自然科学中的那种技术理性为基础,但是,当他们进而将理性完全归于技术理性一类,并断言价值判断只是一个非理性的情感问题和经验问题时,却是一种误解。除了技术理性之外,社会生活和人类行为领域中也存在价值理性,也就是说,作为人类行为准则和法律依据的价值不完全是人类主观情感和欲望的放纵,不完全是偶然的、任意的,而是存在理性的选择,即在利益冲突中寻求某种平衡点。因为毫不妥协地放纵反而威胁各方的安全,有损各方的利益,要想自利必须同时利他,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p98),所以,只有理性确立的价值,才是正当合理的。价值分歧和利益冲突并非排斥理性,相反,它是运用理性的理由。在人类行为的价值领域,理性的作用不在于寻求“科学”的价值,而在于确定“合理”的价值。合理的价值来源于各方达成的公平协议和不同价值的平衡,它可以通过民意表达和公民立法的过程来实现。自然法学派的契约论正是反映了理性在价值领域中的运用。正如科殷指出:价值倾向和正义原则“涉及的不是一些非理性的论断,而是任何原理都必须理性地从某一种价值分析和从现有的经验进行阐述”[8](p162)。
此外,自然权利理论根据人的自然本性来论证人权也不完全是先验主义的武断方法,该理论所描述的人性同时也得到了人们的生活经历和心理事实的支持。霍布斯和洛克都认为,自然法不能超越真实的心理感受,不能脱离人类对快乐、痛苦和世俗需要的直接体验,生命、自由和财产等权利正是他们基于自己所观察的人性事实而提出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对人性的描述包含了某种价值倾向,但价值的存在本身也是一种事实,事实既包括自然事物的事实,也包括具有目的和价值的人事的事实,正如新自然法学家富勒所言,在人类行为研究中“事实(是)与价值(应该)之间的区别消失了,价值因素是有目的活动本身所固有的事实”。[9](p127)可见,因自然权利理论基于人性进行理性论证而断定该理论完全缺乏经验和事实,是一种误解。
收稿日期:2006-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