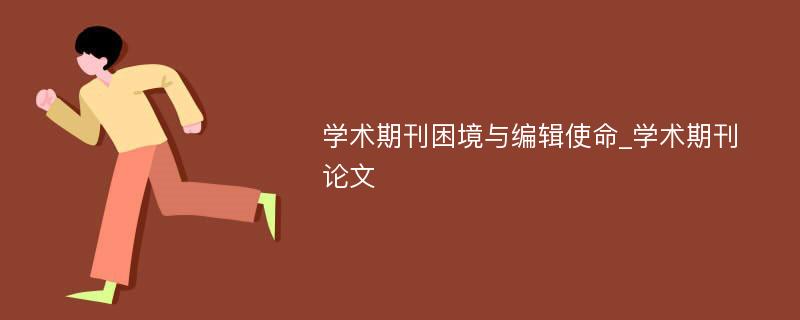
学术期刊的困境与编辑的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使命论文,学术期刊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在目前的中国出版界和学术界,学术期刊的困境已经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出版广角》去年第11期专门做过一个“特别策划”,栏目的名称就叫“学术期刊路在何方”。可见,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确实面临着许多问题。作为长期从事学术期刊编辑和研究的学者,您总体上如何看待中国的学术期刊?
孙景峰:如果要概括中国学术期刊界现状,可以套用一句俗语叫“成绩不小,问题不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学术期刊从整体来说已经初步形成了种类齐全、层次多样、编排规范、精品凸显的格局。这20多年学术期刊的发展在中国期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学术期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数量的增加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根本无法相比的;另一方面,学术期刊在出版理念和导向方面也逐渐成熟;同时,期刊的规范化、网络化、国际化和市场化开始启动并取得初步进展。目前,中国学术期刊的数量约占全国期刊总数的近二分之一,即4000多种。这是“成绩不小”。至于“问题不少”,在我看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学术期刊如何适应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学术期刊在遏制学术腐败中应该担当什么责任,学术期刊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如何与国际接轨。影响到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的这三个问题尚没有很好地解决,是导致学术期刊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
主持人:学术期刊已经成为我国出版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社会转型期,学术期刊如何实现与市场经济的接轨,这在实质上牵涉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期刊的功能定位问题。有学者提出,市场化是学术期刊的坟墓,您如何看这个“危言耸听”的命题?
孙景峰: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从宏观上讲,学术期刊在当下的责任担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反映时代精神,记录文明成果,为文明史册积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成果的“素材”,这是学术期刊事业发展的历史动力,是学术期刊的社会效益所在。这就要求我们把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文化成果记录下来,而不能把一大堆文化垃圾充塞其中。二是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研究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为决策层充当“智囊团”和“思想库”;还有些学术期刊要解决的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对提高社会生产力有直接的效益。这就要求这些期刊与经济建设的现实实践建立起密切联系,努力疏通理论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换渠道。
当然,这两方面的使命是对整个学术期刊阵营而言的。具体到每一家期刊个体,不同类型的期刊的使命担当各有其主要方面。以反映基础研究成果为主的学术期刊在记录传承优秀文化成果方面发挥作用;而一些工科学术期刊和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科学术期刊则与经济建设和当下的社会发展联系紧密一些。我们说,只要在其中一方面做出了贡献,这家期刊就生存得有意义,就获得了发展的理由。不能要求每一家学术期刊都对经济建设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学术期刊也是一部分侧重于学术、文化的积累,另一部分侧重于应用研究,对经济发展能够起到直接的推进作用。
不要一谈到与市场经济接轨,就要向学术期刊要直接的经济效益,要发行量,要“以刊养刊”。学术期刊作为向社会提供高层次精神食粮的基地,自有其独特的市场构成和运行规律。如果把社会经济的市场化等同于学术期刊的市场化,恐怕学术期刊离坟墓就不远了。
主持人:现在有些学术期刊实际上是为一些人评定职称、完成业务工作量而创办和生存的,看起来,这批期刊对社会就没有多少价值。
孙景峰:您说的这类期刊还为数不少。这实际上是学术期刊功能的异化,直接导致了学术期刊困境的出现。目前的学术失范也与此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主持人:您引出了学术失范这个话题。近年来,学术研究失范的个案不断涌现,从大学生、一般研究人员到博士生导师、院士,都有涉嫌抄袭、引用他人研究成果不注明等情节,个别案例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为减少甚至杜绝这种现象,学术期刊出版界谊做些什么?
孙景峰:学术失范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研究主体个人学术道德水准不高所致,实际上涉及科研管理、职称评定、工作量考核等一系列体制和制度。我认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在编辑出版这个环节上没有把好关。虽然学术界的有识之士近年来为遏制学术腐败做出过一些努力,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要想从根本上杜绝学术研究失范恐怕还任重道远。编辑出版环节是学术研究成果在形式上由文稿到正式出版物的闸门,是保证学术研究规范的最后一道关口。建构学术研究规范化的编辑出版机制对于学术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我认为,学术研究规范化的编辑出版机制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示范机制,或称引导机制,即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对作者的示范作用,通过刊发启事、所发文稿的示范、编辑主体的以身作则,为作者做出表率。第二是强制机制,或称把关机制,通过审稿这一关键环节,学术期刊编辑要尽可能地把那些不遵守学术规范的成果拒之于门外。第三是追究机制,或称善后机制,即学术期刊要运用法律武器和舆论力量,让作者为因其不遵守学术研究规范给期刊带来的名誉损失和物质损失负责,对那些因失察而使期刊蒙受损失的编辑人员予以追究。这三个机制的运作分别可在不同的阶段和层面上减少以至杜绝学术研究失范的发生。
从本质上说,学术研究规范与编辑出版规范是一致的。不规范的学术研究成果能得以公诸于世,其根本原因在于编辑出版这个环节失范。可以肯定地认为,学术研究规范化的编辑出版机制的建立,既有助于学者的他律,也是编辑自律与他律的利器。
主持人:在我看来,这三个机制的建立只是理论上的设想,要真正建立并付诸实施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孙景峰:确实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就像反对学术腐败是个漫长的过程一样,上述三个机制的建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就目前来讲,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就是提高学术期刊编辑的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当然,提高学术期刊编辑的素质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先现实一点,就是把带头搞学术腐败的学术期刊编辑清除出编辑队伍;同时,还要把具有较高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的人充实进编辑队伍,让他们切实担负起遏制学术腐败的使命。
主持人:中国的学术期刊面临着困境:发行量下降,品种增加而质量相对降低,难以与国际接轨。学者们用“陷入困境”来说明学术期刊的尴尬。如何看待学术期刊目前的尴尬?
孙景峰:对于目前学术期刊的尴尬处境应当客观地看待。导致学术期刊“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也很难称得上是“困境”。学术期刊的高品位特性使它不可能像大众文化期刊那样拥有众多读者。“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如果把发行量小称为“困境”的话,那么这种“困境”是学术期刊与生俱来的。不能一谈与市场经济接轨就要求学术期刊的出版引入市场化运作方式,收取版面费、刊登广告,似乎不这样做就没有市场意识,做得不成功就是没有与市场接轨。据我了解,除一些与产业联系密切的专业学术期刊外,其余的大部分综合类和基础学科学术期刊在广告经营上步履维艰,即使刊登广告,广告来源也不是市场运作的结果,而是动用了行政手段或“关系”手段。收取版面费固然使学术期刊获得了经济效益,改善了办刊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它使得学术期刊在录用稿件时降格以求,不能把上乘的研究成果奉献给社会,进而载入史册,辜负了学术期刊记录成果、积累学术、传承文明的使命。从是否与市场经济接轨这个意义上,学术期刊还谈不上已“陷入困境”。
但目前学术期刊在整体上确实处境尴尬。在我看来,根本原因还在于低水平重复出版,学术期刊的制度性结构调整力度还不够,期刊的发展缺乏自我淘汰机制,特别是缺乏社会强制淘汰机制的真正介入,刊物难生更难灭,使中国的学术期刊结构既缺乏主管部门的主观调控,也缺乏市场的客观选择,学术期刊结构的优化自然也就难以实现。
低水平学术期刊的大量涌现,破坏了中国的学术生态。它们同一些名牌的学术期刊争稿源,破坏了学术期刊的整体质量形象,成为学术腐败的温床,浪费了社会财富和读者的时间,使高水平学术成果有可能被淹没在低层次成果的汪洋大海中。我在《中国期刊年鉴(创刊号)》中把这批低水平学术期刊称为“中国学术期刊阵营中的畸形群体”,得到了许多同仁的认同。可以说,中国学术期刊的尴尬处境正是这批期刊造成的。
要真正使中国学术期刊摆脱尴尬处境,首先的和根本的途径就是治滥治散,引进竞争机制,建立制度性的淘汰机制,对期刊实行动态优化管理。对于那些不具备办刊条件、学术水平低、编辑力量不达标者一律吊销刊号,革除事实上存在的刊号终身制,实现人力、物力、财力和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最终形成布局合理、数量适中的学术期刊结构,这样,优秀的学术期刊才能脱颖而出,中国的学术期刊才能逐步摆脱困境。
主持人:在谈到学术期刊摆脱困境时许多人都谈到与国际接轨,似乎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中国学术期刊阵营中的畸形群体”就无法与国际接轨,真正意义上的与国际接轨只是少数精品学术期刊所要努力的方向。
孙景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一种世界一流的国际性刊物实际上就是一个国际性学术信息中心,意味着最先掌握、发布世界上最新的学术信息并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中国虽然有4000多种学术期刊,但真正跻身国际一流行列的却很少。《中国期刊年鉴(2002/2003)》对学术类科技期刊的质量进行了评估:国内一流水平、有国际化前景的期刊只占学术类科技期刊总数的7%,我觉得这个结论是比较客观的。在中国期刊方阵中,入选第一层次“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的“双高”期刊是冲击国际一流学术期刊的主体力量。而我们目前学术期刊界的“与国际接轨”只是表现在技术层面,就绝大部分学术期刊来讲,在内容和质量上尚缺乏与国际接轨的实力。目前教育部正在高校学报界实施的“名刊大刊”工程会有助于一批顶尖的学术期刊跻身于世界一流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