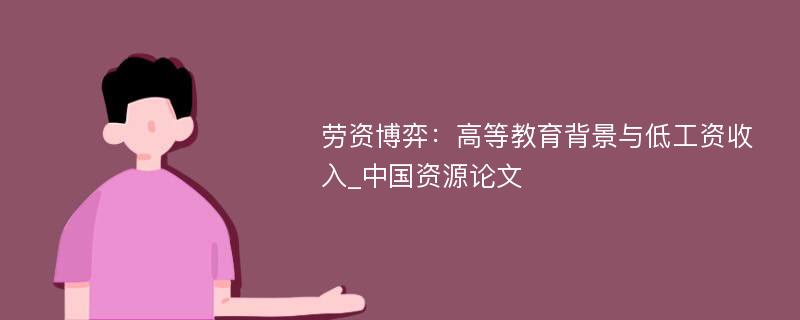
劳动与资本的博弈:高教育背景与低工资收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文,背景论文,收入论文,低工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把工薪阶层看成是劳动要素的人格化,他们的收入是工资;将企业看作是资本要素的代表,它们的收益是利润;那么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已经使得中国的劳动与资本在收益分配问题上的博弈日益引人注目。经验表明,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换言之,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即使是由自然禀赋造成的,也不占重要地位,而更多的是由制度在起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首先是数千万国有企业的职工被廉价的农民工取代,下岗、再就业、身份买断逐渐结束,或正在结束“全民所有制职工”这个庞大利益集团的安置问题。但是,有幸取代他们的农民工很快就发现,离开土地进城打工的道路并不平坦,他们不得不长期忍受低工资的困扰。当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处境被长期漠视的时候,人们逐渐发现,受到低工资困扰的绝不仅仅是农民工。大学生就业难从一个更深的层次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扭曲的问题。
一、“读书无用论”再次出现
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对当时的“读书无用论”至今尚记忆犹新。就因为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往往会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人格,相对于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更难于被愚弄,用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因此读书人被贬为“臭老九”,长期受到打压。在一个仇恨知识的社会环境下,读书显然是经济人非理性的选择,这就是当年的“读书无用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终于从那个愚昧的时代走了出来,“知识就是力量”这个早就被人类公认的法则逐渐融入我国主流社会,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精英其社会地位重新得到了认定。
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早已被抛弃的“读书无用论”似乎又卷土重来。不久前,《长沙晚报》有篇报道,说现在许多中国农村孩子已不再奢望到城里升学,就连已正在念大学的,也感到茫然。有些大学生说:“读了大学也难找工作,这书怕是读了也没什么用”。在中国农村,一种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兴起。以前作为农村孩子学习的榜样,那些希望通过求学改变自身命运的大学生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境遇甚至不如那些初中毕业就到城里打工的民工。一项1200家企业的调查表明:有34%大学生求职时,薪水只要求1000元人民币。其中更有0.8%大学生,甚至为了抢一份稍微好点的职业,更不惜选择了“零工资”,即只要能够得到希望的职位,在实习期间可以分文不取。
一方面是大学毕业后求职的艰难,另一方面是昂贵的教育支出。按照高校的正常收费,同时学生本身以最节俭的模式生活,四年的大学生活也要耗费七到八万元人民币。这种投资对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如果投资不能得到回报,那么就不如不读书,而是选择中学毕业就进城打工的生涯。这就是目前重新出现的“读书无用论”。尽管都是“读书无用论”,但是二者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前者是在一个特殊年代中,为迎合阶级斗争的需要,从政治上压抑一个社会群体,人为地贬低知识的产物;而后者则是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产物。
二、为什么高教育背景的劳动者不受欢迎
我国的大学生为什么就业困难?是否目前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已经过剩?有关统计表明,每万人口里的在学大学生数,中国28.4个人,印度54.7个人,美国528个人。显然,就高等教育的普及率来看,我国的大学生不是过多,而是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大学生的供给并非是其就业难的原因。也有的观点认为,大学生就业的障碍来自目前高等教育的扭曲,即“学非所用”。然而,用“学非所用”来解释如此普遍的就业难,显然缺乏说服力。没有证据表明,在一个GDP连续接近两位数增长的国家里,高等教育课程的设置会长时间脱离经济的发展,专门教授那些与经济发展脱节的内容。此外,用大学生过高估计自己的身价,不愿屈就解释他们的就业障碍就更站不住脚了。事实上,目前很多大学生正在忍受着低工资的困扰。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困难呢?Manatt Jones国际咨询公司的吴向宏博士的一项研究对此提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大学生就业难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资源错配”。简单地说,就是经济资源在一些人为因素的作用下,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片面流向重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知识型服务业则处于低迷。特别是2001年之后,在低利率、低汇率政策扶持下,重型产业加速发展,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近3/4来自重制造业。说通俗点,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在明显地走向“粗笨化”。这种产业结构失衡反映在劳动力需求结构上,就是知识型服务业岗位——基本上属于所谓“白领”的岗位——需求相对不足,对蓝领型岗位却产生了旺盛的需求。因此,才会出现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等新的“脑体倒挂”现象。
资源错配这个概念最早是国务院发展中心金融研究所的巴曙松博士提出的。巴曙松用它来指我国低汇率政策导致的一种现象,即低汇率造成中国产品成本被低估,造成出口“赚钱”的假象。这使得中国人把有限的资本投入到外向型产业中去,这些外向型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吴向宏还从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和过度管制的角度,指出金融产业的不发育,则是抑制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金融产业本身就是极为庞大的知识型服务业,可以创造数以千万计的白领就业岗位。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放开企业债券市场,按照企业债券数量达到美国(400万种)的十分之一、每种债券发行可创造10个就业岗位计算,这就是400万个白领就业岗位。反过来说,对企业债券市场的过分管制,就相当于扼杀了这么多的白领就业岗位。
吴向宏博士的研究不无道理,他这里的贡献在于从经济结构扭曲的角度指出了我国目前白领职位需求不足的原因。但是,我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按照新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来自于技术进步的推断,并非只有知识服务业才是技术进步的载体。相反,推动一国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重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样需要技术进步的支撑才能有持续的增长。那么,这些产业为什么就不能提供更多的白领职位呢?毫无疑问,这里一定隐藏着更深刻的原因。
三、缺乏技术创新与挤压劳动成本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0多年中,无论是国家的科研和教育投入,还是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都明显位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这种情况下,经济还能取得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压低劳动力的价格。所以,中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一国要在经济竞争中获得优势,通常有两种战略:一种是加大科技的投入,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取得竞争的优势,增加本国居民的福利;另一种则是依靠压低工资,借助传统的技术,粗放式地使用资源,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前者属于创新型的发达国家,后者则属于非创新型的发展中国家。当前,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努力寻求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即资源依赖型,如中东地区产油国家等;一些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即对外依附型,如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等;还有一些国家在充分吸收别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把促进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学术界已把后一类国家称之为“创新型国家”,目前大约有20个左右。
创新,主要是技术创新,是一种对新技术、新思想、新制度、乃至风险和失败都抱欢迎态度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一旦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广泛推崇的理念,特别是这种理念渗透于企业之中的时候(这里的企业绝不能排除重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就会激发出经久不衰的发展动力。例如,正是由于这种对创新的推崇,美国企业多年来在高科技领域始终保持领先地位,新产品层出不穷,从而推动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的诞生。
相反,在一个对创新缺乏广泛认同的国家,通常会机会主义盛行,假冒伪劣充斥。同时,在缺乏创新的情况下,知识肯定不会得到尊重。道理很简单,如果技术可以靠盗版获得,企业就没有必要进行研发(我国全部大中型企业的R & D经费,还不如一个国际大公司的投入),从而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提供白领职位;如果企业推崇低廉的劳动成本,借助血汗工资制度,依靠低端的技术、粗放式地利用资源,制造初级产品的做法获得利润,自然没有必要高薪雇佣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
在我国,尽管一些企业也追逐新技术领域的产品,但它们更青睐的是走捷径。结果新技术领域产品一旦投入市场,被仿制、复制的风险相当大。例如,企业可以雇佣少量有技术背景的人,用很少的时间和资金复制出集成电路芯片、计算机软件、激光唱盘、电影制片和原版书籍期刊、医药品等。尽管这些新技术大部分来自海外,国内的企业侵犯的是国门之外的知识产权,但是我们丧失的却是民族的创新精神;恶化的则是我国创新的宏观环境。在我国,相当数量的大型企业没有自己的研发机构,大多数中小企业几乎没有研发投入,相当多的企业既没有研发投入,也长时间不引进新技术,只是在生产“大路货”的低端市场挣扎。显然,人们不能指望这样的企业会尊重知识,会为科技人才提供就业机会。事实表明,在一个缺乏创新的国家,人们不能不忍受低工资的困扰。
四、政府在劳动与资本博弈中的角色
劳动力的价格之所以长期低下,事实上还与国家采取的竞争策略有关。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要获取竞争优势,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另一种则是以人为压低工资、放任环境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
和那些二战后迅速崛起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例如“亚洲四小龙”,我国政府并没有像他们那样,通过立法人为地压低工资,例如禁止罢工,通过立法强制仲裁劳动争议,限制工会就工资进行谈判等等。而是相反,就法律、法规来看,中国政府的劳动政策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难以为劳动者提供有力的支持。例如,《中国经济周刊》报道称:1993年就颁布的《企业最低工资规定》经过10多年后,各地的最低工资仍然低于国家标准。随后,全国总工会发给《中国经济周刊》的独家专函也认为“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尚未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40%-60%的水平”。事实表明,目前在劳动与资本的博弈中,劳动者所处的位势并不平等。劳动者自发式的抗争,例如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在资本的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五、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和途径
什么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其实,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发展经济学对此有过深刻的讨论,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是提供给国民高水平的生活。实现这个目标要借助运用劳动与资本等国家资源所得到的生产率,生产率又是每单位劳动与资金的产出价值,并且由产品的质量、特征(这两者决定产品价格)以及生产效率来决定。
生产率是人均国民收入的源泉,因此也是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生活水平的关键。资本的生产率表现在投资人的回报上;而人力资源的生产率则表现在他们的薪水上。高水平的薪金收入与高效率的劳动者共存。倘若工资只能维持劳动者最低的生活水准,指望他们输出高效率是难以想象的。国家的高生产率不仅带来高收入和更多的休闲时间,它也创造政府税收、带动公共设施,进而提高生活水平。高生产率同样也使得企业有能力达到健康保险、社会福利、平等工作权和环境保护等严格的社会标准。
靠什么来提高生产率?自然资源总是有限的,但是相对于自然资源,人类的智力资源却具有永不枯竭的特征。按照新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来自于技术进步(Temple 1999)。国家如此,企业更不例外。科技竞争越来越成为国家及厂商增强实力的主要手段,而科技竞争的关键正是对作为人类智力资源载体的科技人才的争夺。
目前,发达国家普遍加大了在全世界搜寻、吸引、利用人才的力度。统计资料表明,全世界平均每年有1.7万科技专业人才直接定居美国,16.8万科技人才通过临时签证前往美国工作,18.3万外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就读,世界科技移民的40%以上最终进入美国。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人才争夺中处境极为不利,大量在本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科技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我国为例,在1978-2003年间出国留学的70.02万人中,回归率不到30%(邓楠2005)。
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且非常脆弱的比较成本优势,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换取的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蹩脚的竞争策略。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借口避免工人失业而将劳动力价格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今天以廉价劳动力看好的国家,明天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国家取代;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往被认为不经济的、不可能的资源异军突起同样也让以传统资源见长的国家失去竞争力。
世界上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既无法在国内进行技术创新,也无力采用国外先进技术,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综合国力主导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综合国力的竞争,已明显前移并集中到了创新领域。这一领域又以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为公认竞争的关键。因此,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在劳动与资本博弈时,政府扶持劳动者,固然会减少资本的收益,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只能在“血汗工资制度”下生存的话,那么它被淘汰出局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防止生产过剩的大面积发生,消除无效供给也是必需的。那些资源配置效率低,不能通过技术提高拓展赢利空间的企业,应该被淘汰出局,这可以看作是社会技术进步的理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