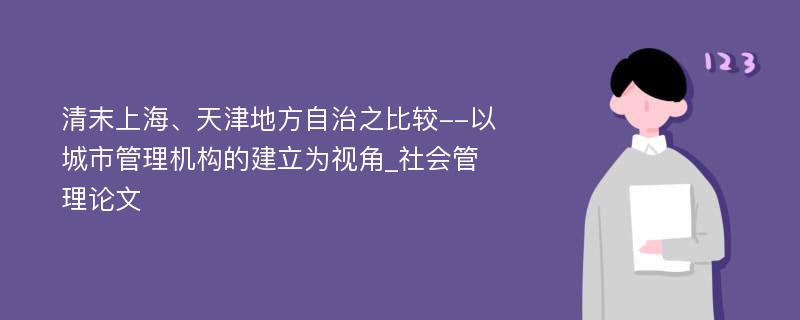
上海与天津清末地方自治的比较——从城市管理机构建立角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天津论文,管理机构论文,上海论文,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9)01-0008-07
中国以城市为单位的行政管理机制是近代以后出现的,从法律上南京政府1928年颁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是对城市行政管理机构的确认,而一个制度的形成是需要长期酝酿和实践的,20世纪初地方自治的一些措施与内容已经具有城市管理机构的雏形。本文从创建城市行政管理机构的角度,比较上海和天津推行地方自治在起因与主旨、城市理念与形制、内容与实效等方面的不同,分析各自的特点,进而探讨中国构建城市行政管理机构的路径。
一 起因主旨与创办者
地方自治的思潮出现于19世纪中叶,从最初的介绍外国政体,到戊戌维新时康梁等人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再到一时间“凡关心时局之士皆将以提倡地方自治,树20世纪新中国之先声”,①地方自治的言论“日触于耳”。上海、天津的地方自治都是在清政府谕令在全国推行之前率先兴办的,是南北方两个领风气之先的城市,但其起因、倡办者身份和目的有着明显的不同。
上海兴办地方自治的起因既有租界的影响,也有城市发展的需要。20世纪前就曾发生了因法租界筑路等引发的四明公所事件,南市马路工程局和闸北工程总局的建立都与抗衡租界扩张地界有关,1905年郭怀珠、李钟钰、姚文枬等绅商更是鉴于“租界日盛,南市日衰”,②创建了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工程局在仿效外国租界实行的城市管理模式上也较为得心应手,命名工程局、设立巡警、筑路和征收捐税,都可以看到仿效租借工部局的痕迹。南市马路工程局开征房捐时表明,此事“均系仿租界章程”,“租界之人均无异词,南市同此子民,断不致易地抗违不遵”。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推行的是中国政治制度中没有的以城市为对象的管理机构,如纳税人会议、工部局董事会,以及下属的各个部门,成为中国政府和绅商创办工程局最为直接的参照物,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设立的呈文中,明确表示是“仿行各国地方自治之制”。城市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治安、道路交通和环境景观等难以适应,逐渐恶劣的城市问题成为来华外国人讥讽嘲笑的话柄,而租界内整洁有序的秩序和环境也形成了与中国城区的强烈反差,于是上海绅商等都将修筑道路堤防、治理社会治安作为开办工程局的理由。南市马路工程局要招标修筑马路、桥梁和码头等,开设电灯房解决路灯和住宅照明,建立巡捕房沿街巡逻;闸北工程总局要“建造桥梁,兴筑沿河马路,承办一切事宜”,③意在承揽市政工程;城乡内外总工程局将城区“道路不治,沟渠积淤”作为开办的原因之一。
创办和推行上海地方自治的是城市中的绅商。南市马路工程局和闸北工程总局是绅商提议建立的,后者还由绅商自行筹措款项,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也是郭怀珠、李钟钰、姚文枬等绅商创办。从总工程局的主要成员看,有的是离职官吏,如李钟钰、郭怀珠、祁祖鎏等,更多的是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商人和长期从事教育慈善事业的士绅,如朱佩珍、曾铸、郁怀智、李厚祐、沈缦云、姚文枬、莫锡纶、叶佳棠,有的还是官商合一、绅商合一,甚至是官、商、绅士三位一体,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声誉。据学者统计,总工程局董事中商界领袖占60%,议董议员中商界领袖也占到30%以上,④这样的人员构成一直沿袭到上海城自治公所和上海市政厅。因此,代表社会力量的绅商是推动上海地方自治的原动力。当然,绅商的创举也得到了地方政府上海道的支持。如积极鼓励绅商兴办地方自治、接管绅商开办的南市工程局、将政府的南市工程局和闸北工程局统统归入绅商兴办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决定“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均归地方绅商公举董事承办”。⑤至于将这类机构纳入地方自治范畴,是政府和绅商响应预备立宪和兴办地方自治之风,即“酌收地方税,以办理地方公共事务,助官司之不及,兴民生之大利,以立地方自治之基础”。⑥
20世纪初天津的社会背景比较特殊,1900年后被八国联军组成的天津都统衙门统治二年,中国政府接收前除了有《辛丑条约》的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之外,该衙门的《有关交还天津行政权力的通牒》也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承认天津都统衙门会议的一切行为”,⑦“必须赋予这些法令以权威和效力”,“就像中国自己颁布的各项朝廷法令一样有效”,⑧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接收后必须完全承认和实行其制定的法令章程、措施。直隶总督袁世凯接收前,招募了2000名巡警,接管了都统衙门的1000名华捕,组成了管理社会治安的警务队伍;并继承了该衙门司法部、司库局、田产局、河道巡捕局、巡捕局、卫生局和公共工程局等,已经基本形成了管理城市的基础性机构;其创办的商务公所也起到了稳定市面和调解经济纠纷的作用。而且,在政府重压下反对租界扩张的举动并不突出,当时报刊中有民众反对新设租界占地等消息,却不见绅商抵制租界扩张的报道。
那末,天津为什么率先兴办地方自治呢?是什么力量倡办和主持地方自治呢?天津的地方自治完全是在袁世凯直接策划下展开的,一方面设立天津府自治局为指导机关,厘定章程,建立机构。袁世凯要求“所有章程节目参以本国风俗分别缓急妥议施行。此为他日宪政先声,至关紧要”,⑨为此自治局成立了天津县期成会,经过19次修改完成了《天津县地方自治公决草案》,袁世凯亲自划定自治应办、议协和监察事项范围,在筹办之事中加入四乡巡警、小学堂及宣讲所,“监察之事地方捐务以外,如津埠工巡事务,有何利弊,亦可随时据实纠弹”,⑩随即以《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颁布,这是全国第一部以地方自治命名的章程。成立议事会也是如此。1906年11月他面谕自治局总办,“地方自治事关紧要,饬从天津一县先行试办议事会、董事会,以备实行地方自治”。(11)随后又告诫“此次试办地方自治,为从前未有之事,凡在官绅,务必和衷共济,一秉大公,以为全省模范”;(12)并批准借用巡警各分局作为选举的办公地,(13)由天津府出示晓谕发动民众选举,翌年9月成立了天津县议事会。(14)另一方面袁世凯强调“地方自治,为我国创办之事,非先以预备,则不能实行”,要以“准备地方自治为宗旨”,(15)自治局宣称“地方自治之基础始于人人皆有普通之智识”,设立了自治研究所和宣讲处等,培训劝办人员,在全县以及全省宣传和普及地方自治的知识,“以期家喻户晓,振聩发聋”。除此之外,据《天津府自治局文件录要》记载袁世凯和后任直隶总督还有十余次批文,涉及到推行进度、规模、方式方法等。如最初有人提议改办直隶自治时,袁世凯批复道:“津郡甫经开办,尚无成效可言,近今办事之难,该绅等亦所深悉,欲速不达,不如徐步当车,可免颠踬,应俟津郡选举事毕更议扩充,毋庸求之太急也”;(16)天津县议事会成立后札文自治局:天津试办自治粗具规模,本省士民渴望已久,亟应谋及全省一律成立,期以三年遍及全省。当时,一些社会人士也对此种模式不满,有人评论道“吾人独于议事会有一极可疑异之事。盖传闻局中人颇有主张联络官府者,此真不明白自治之法理及宗旨矣”,认为议事会性质是自治的,“其一切举动虽不必与官府作反对,亦不可视官府为从违。顾名思义,要在不失自治之主权而已”。(17)《大公报》也曾连续登文讨论和批评自治与巡警关系、经费无着和董事会难产等问题;天津县议事会的不作为也使得议员心灰意冷,一年内副议长辞职、数名议员或因赴外地为官,或因病而辞职;(18)直到1920年王守恂撰写《天津政俗沿革记》时,仍然称“天津自治局时人谓之官办自治”。(19)
我们从兴办地方自治的人员可进一步分析官办自治的性质。1906年8月袁世凯委派天津知府凌福彭和金邦平筹办天津府自治局。凌福彭随袁世凯接收天津,到日本考察后创办了直隶工艺总局,深受袁的器重;金邦平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法科,是袁世凯的洋务文案和北洋常备军督练处参议,曾兼任直隶师范学堂斋务长,袁称其为“才识明通用,安详谨饬”,“志趣纯正,才识闳通”。(20)袁世凯要求自治局“招募在日本留过学者、从法政学校毕业者及官绅入局”,强调“此次法政毕业官绅即均调派任使,俾资练习,分赴各属会同地方官办事;另选学识最优者在局参议佐理”,(21)该局14名成员都是有一定功名的官绅和绅商,至少有一半曾到日本留学或考察。(22)天津县自治期成会会员包括自治局成员、20名劝学所公举的士绅、15名自治局和商会公举的商人,以及数名有功名的绅商,其中至少有十余人曾有到日本学习或考察的经历。(23)天津县议事会议员的构成,除了少数盐商、粮船巨商外,多是城乡地区有一定功名的士绅,留日和从事教育者不在少数。(24)
由此可见,天津的地方自治完全是袁世凯直接策划和操纵下进行的,并没有多少抵制外侮和为解决城市问题建立管理部门的用意,结合其积极兴办新政等行为,不难看出是想迎合预备立宪潮流,借助社会力量协助政府弥补管理体制的不足,即“非行地方自治,无以补守令之阙先,通上下之悃忱”,以得预备立宪、地方自治等方面之先机和在全国的示范性,进而为其捞取政治资本。承办与参与者多为有一定留日背景的士绅和社会名流,很少看到有经济实力的新型绅商等的自觉性行动。因此,在天津兴办的地方自治实际上是袁世凯的独角戏,绅商等社会力量只不过是陪衬而已。
二 城市理念与形制
在创办地方自治机构过程上,上海有相当的城市意识,并随着城市发展和社会力量的增强,有脱离自治机构而演变为行政管理一级政府的趋势;而天津仍没有脱离原有行政管理体制的藩篱。
在上海,从名称和行政区划上就是以上海某地冠名,如南市马路工程局、吴淞开埠工程总局、闸北工程总局,在机构设置上有一个明显的城市空间管辖范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和上海城自治公所也是如此,并没有局限于上海县的行政管辖区划,却有空间概念——城厢内外或上海城,这是有一定余地的模糊的空间范围,并没有局限在城厢以内。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有4个城区和3个城厢区,“惟北门以外为租界,自治权所不及”,各区有分派的办事处和区长、副区长。中国向来没有以城市为单位的行政管理机构,也就没有相应的区划,总工程局的空间范围与分区对建立以城市为单位的行政区划和城内分区十分重要。从机构上,在总局内设立了户政、警政、工政三科;户政科下设户籍处、地产登记处、收捐处,警政科下设巡警处、消防处、卫生处,工政处下设测绘处、路工处、路灯处,还附设有一个裁判所,这些机构皆为传统行政管理机制中缺失的,而且是城市的迅速发展亟需创立的,是以城市为对象,专门管理城市社会治安、建设,以及房地产和税收管理的专职部门,是城市行政管理机构的主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起义时自治公所总董领袖李钟钰组织数百人商团志愿军参加了起义并营救陈其美,当时地方官吏逃入公共租界,社会秩序失控,人心不安,自治公所发布告示,“昨夜城中起火,地方官他去,居民不免惊慌,本公所为维持地方秩序起见,从今日起总董常驻城中救火联合会办事,所有巡警照常站岗,其有不足由城外酌派,并请商团分段梭巡,以防土匪滋扰。凡地方官所办之事,概由本公所暂为主持,以维秩序而保治安”,(25)俨然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地方政府。随后,自治公所改为上海市政厅,市长是总工程局总董莫锡伦和议董陆文麓,议长仍然是总工程局的议长姚文枬,原自治公所总董李钟钰为都督府的民政总长,这是除了租界和殖民城市之外首次出现以“市政厅”命名的机构,“市长”的称谓也是第一次,表明了包括地方政府和上海城市社会的认同,也体现了城市管理的模式,以及从“城”到“市”这种空间理念的演变。上海市政厅作为自治机构一直延续到1914年,袁世凯下令停办各级地方自治后遂被工巡捐总局取代;1924年北京政府宣布恢复地方自治,上海市自治公所再次设立。更为重要的是,市政厅的这种城市管理模式进一步被政府肯定,不久军阀孙传芳控制了江浙五省,要将与上海有关所有行政权力都统一到“一个中心,这样才能具有改善市政府的权威性”,(26)建立了淞沪商埠督办公署,1925年成立了淞沪特别市筹备委员会,拟定《淞沪特别市公约》,遂成立了特别市政府,1927年得到南京政府的批准,从此成为特别市,比颁布《特别市组织法》早了一年。由此可见,上海的地方自治机构成立后始终以城市管理和建设为己任,以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从最初的地方自治机构演变为管理城市的地方政府。
在天津,从来没有以城市作为空间范围的理念,其各种机构都是以天津府或者天津县的名义设置各种机构,如天津府自治局、天津县自治期成会、天津县议事会等。在这些机构中也没有划定管辖范围。早在1850年编纂的《津门保甲图说》是对城厢和四乡的人口调查,并没有局限在城内,说明已经有一定的城市理念,而且1900年天津都统衙门曾经划定较为明确的管辖范围,即“将对天津市和直至土墙周围地区行使管理权”,随后又有所扩大并划分了5个区,各区以村庄为线绘制了地图,并设置了派出机关和区长。(27)袁世凯接收后,将上述行政分区纳入了警区的管辖系统,所以兴办自治时仍然是在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进行,并没有确定城市的理念。由于地方政府已经设立了巡捕局、卫生局、工程局和捐务局等,所以自治机构也没有设置专门管理城市的部门,天津府自治局仅下设负责考订章程的法制课、负责社会调查的调查课、负责编辑白话讲义和文牍的文书课、负责会计和收发的庶务课。(28)而且,创办者将地方自治始终限定在原来的行政管理体制之内,如以天津府作为指导机关,成立天津县期成会和天津县议事会,在天津府县范围内推广自治,1908年4月又将天津府自治局扩大为直隶筹办地方自治总局,而天津县城议事会直到1910年10月才出现,(29)且始终没有什么活动。1914年停办地方自治和解散议会后,无论是县议会、董事会,还是省议会均销声匿迹。1924年恢复地方自治后,仍然难以看到议会在城市管理和建设上有所作为,即便1928年天津设立特别市,从机构和人员上看不到与清末地方自治的延续性。
上海和天津都先后设立了议事会、董事会,但议事会成立的程序,以及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都有所不同。
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创立前,创办者郭怀珠等走访了曾在国外游历考察过的政法学家,制订了组织章程,也仿效国外和租界的体制,设立了议会、参事会为代议和行政执行机关,以及部分司法裁判权。在《总工程局议会章程》中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作了详细的规定,并有比较完整的选举方案,“议董由本地士绅及城厢内外各业商董秉公选举,呈请苏松太道核准”,参事会为执行机关,第一任议长、领袖总董和办事总董由上海道指定,以后由议会自行举定再呈报上海道。(30)该局第一届议董候选人未经民众投票选举,是以各善堂、书院、铺段董事和商界各行业为基础,由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士绅商贾公举后由上海道圈定的;且董事会随即成立,开始了有关管理和建设等工作。1907年总工程局打算成立一个选举局选举议董,未得到上海道批准;(31)1909年改名自治公所后开始投票选举议员,其范围包括上海城厢内外、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共计有3600余选民参加选举,投票者共计1100余人,选出40名议员,议事会和董事会成员基本是原来工程总局议董的连任。
天津县议事会是通过民众投票选举议员后产生。《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规定,议事会和董事会为地方自治机关,议事会议员以30人为限,均用复选举法选出,议长、副议长由议员公推;董事会是执行机关,会长以本县知县兼任,副会长和会员均由议事会选举。天津府自治局于1906年3月就设立了选举总分课负责推动选举,依照警区将天津县确定了8个选区,由自治研究所毕业的学员任分课员,根据选举章程规定的选举人和议员候选人资格进行调查,估计选民约有20万人,印制了调查表20万张。但民众对自治和选举的活动不甚明了,还谣传加税,故只散发了不足7万张,其中合格的选民12461人,有被选举资格者仅2572人。尽管如此,天津府自治局仍然从1907年6月起实施候选议员选举,在天津城内投票三日只有1300余人投票,自治局只好又延长二日,并登告白和广告劝导,又增加400余投票人;在四乡投票三日有7000余名投票,共计有8759人投票。投票人数不多,但当组织者开箱验票时,因好奇来参观的竟达2000余人,结果初选当选者135名;(32)遂通过复选,在参选的127人中选出30名议员,成立了天津县议事会。
另外,上海、天津自治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也有较大的不同。上海总工程局的章程中规定:“工程局以上海县知县为督办,不分派委员”,即实行官督绅办制,作为督办的地方政府不能对该局实行绝对的行政权力,“总董权限主一切应兴应革之事,会商督办,经督办认可者即由总董办理,督办不得掣肘;如督办不认可而事关重大势在必行者,邀集会议董事共决可否,其有会议董事不能决者开特别大会公共决议”。(33)对于“地方公益事件须藉地方官权力者,议会得具意见书交由领袖总董呈请地方官鉴核”,(34)即地方官只有督办和鉴核的权力。即便清政府颁布自治章程后自治公所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受到更多的监督和限制,但议员和董事变化不大,董事会总董仍然是李钟钰。在天津,自治章程中规定,议事会办理各种事务“得上条陈于地方官”,议决的各种事项,要“由议长移知本县知县及董事会并公布之”,“议事会得应地方官之咨询申述其意见”;尤其是董事会会长要由知县担任,决定了自治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且,上级地方官——知府以及总督负责监督,不仅有权追加预算和批准议事会制定的条例,总督有权解散县议事会,下令改选县董事会等,(35)使得袁世凯代表的地方政府牢牢地控制着自治机构的活动。
三 内容与实效
兴办地方自治与城市管理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诸如城市是各种力量自治活动的首选舞台,自治章程对城镇的定位表明政府确认了城市的空间理念,尤其自治章程中设定的七大类经办事项中,多涉及城市的管理和建设,诸如建筑公用房屋、修缮清洁道路和疏通沟渠等工程,开办路灯、电车、电灯、自来水等公共营业,以及建立医院、医学堂、公园、工艺厂、工业学堂、救火会等只在一定规模城市才有条件施行。上海设立自治机构本来就以城市管理和建设为主要目的,正如总工程局简明章程所言,主要办理“编查户口、测绘地图、推广埠地、开拓马路、整理河渠、清洁街道、添设电灯、推广警察、举员裁判”等,总工程局和自治公所颁布的各项章程规则也多集中在治理治安、税收和建设等方面,并在自治机构主持下努力开展城市管理和建设。如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设立了巡捕房,闸北工程总局也有自己的巡警,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设立警政科和学堂,到1911年拥有巡警455人,(36)以及“受总工程局之指挥”的商团。在城市税收和建设上也成绩斐然。据统计,总工程局的4年内财政收入折合洋元为66万余元,自治公所2年间就收入了46.6万余元,(37)不仅保证了其经费和建设有了较为可靠的来源,也推动了适合城市经济发展需要的捐税制度的形成;自1905年到1911年自治机构共投资51.7万余元,建造了大小105条道路、57座桥梁,疏浚10条河道,修筑16处码头驳岸;市政厅时期又修建46条道路、20座桥梁和4处码头驳岸;(38)自治机构还顶住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压力拆除城墙,经营的原官办电灯和自来水厂也扩大规模和改为公司制。因此,上海的地方自治重点是在城市的管理和建设上,促进了城市景观的改善和创立新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
天津推行地方自治的重点始终放在制定章程、建立机构和宣传普及上,如前述的设立期成会制定章程和开展选举,开办研究所培养劝办员,建立宣讲处和编写白话告白等。其最为突出的,除了选举候补议员成立议事会外,也就是社会调查。在《天津府自治局试办调查简章》中规定,专派法政毕业官绅分赴天津府各属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地方实况调查,其事项专在地方自治范围之内,主要包括4类:第一类为必要类,如土地、户口、生计、教育、财政、政治、土功(道路、堤防、沟渠等);第二类为推广类,如农业、工业、商业物产、社寺、宗教、交通、人事(风俗习惯,为编制民法而设);第三类为密查类,如土娼、赌场、土豪、劣绅、诉棍、吗啡针;第四类为附加类,为不属于地方自治范围而有间接关系的,如军事、巡警、刑事等。(39)从调查的内容不难看出,是以预备选举为名,进一步了解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现状,协助地方政府加强管理和控制。更为奇怪的是,天津的自治机构始终没有经费来源,一直处于经费无着的困境。天津府自治局开办经费是盐商振德黄家的报效银8万两和罚款银5500两,议事会成立后,根据章程“其经费则正赋、正税之外,杂课、杂捐皆地方自治所取资”,袁世凯也批准其经费由地方捐物即地方入款项下拨付,据估算常年经费至少需银16000两,(40)可是只得到自治局拨来5000银两罚款,没有固定的筹款规则和措施。议事会禀文直隶总督,建议“捐务科经理之一切捐款改归董事会接办”,“将捐务科并入董事会,即以酌减捐务科之常年经费化为议事、董事两会之常年经费”。但该建议遭到捐务科百般刁难和反对,也未能得到直隶总督批准,(41)致使董事会成立推迟了一年。董事会成立后,一切充公庙产成为董事会仅有的收入;1910年议事会又向地方政府建议,希望董事会接管天津各行杂税,以为自治常年经费,但藩司以这些“各属经征杂税,向系牙纪赴集抽收,交县解司”报部候拨,“其性质系在国家税范围以内”,拒绝交出;虽然引起议员反对,撰文论述此是差徭非国家税,是地方搜刮的民脂民膏,应该厉行减免,但始终没有如愿。(42)如此可以想见,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连开办费用和常年经费都难以筹集,就更无力顾及城市的管理和建设了。
综上所述,上海和天津推行的地方自治是两种模式。上海的地方自治是代表社会力量的绅商倡办和主持的,他们有着强烈的自我主体和城市管理意识,急切希望在城市管理与社会控制上有更多的话语权,体现了地方社会力量的日渐强大。自治机构也具有一定的城市管理机构的雏形,即便纳入全国地方自治轨道后也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进而很早就以市政厅命名,一度还自诩为上海地方政府,以致市政厅这样的机构一直延续到1914年,因而在以后创建城市管理机构时顺理成章,促进了中国城市行政管理机制的形成。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清末上海地方自治机构,已经演变成实际的地方权力机关,绅商对自治机构的人事又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可以说上海绅商已经成为上海政治社会的中心”。(43)
天津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状况,体现了在全国地方自治的示范性。从全国看,西方列强不断扩张,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能力衰减,巨额赔款更加重了财政入不敷出的困境,清王朝摇摇欲坠;同时社会力量和知识分子对立宪和地方自治等呼声日切,参政议政的意识增强。清廷亟需采取措施挽救时局,其推行地方自治是希图在不触动根基和财政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强对地方的控制,并无意亦无精力建立城市行政管理机制。袁世凯在天津实行的地方自治恰恰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清廷的意图。一方面能够增强各级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和协调官民关系。当时,中央政府设立农工商部、巡警部等,袁世凯也设置一系列管理部门,在政府统治权没有旁落的前提下开办地方自治,试图借机适度地发挥地方各界人士的人力财力,以重新整合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关系,即“务必和衷共济,一秉大公”。(44)另一方面当时强烈呼吁改革国体和政体的地方精英空间分布不平衡,各个城市以绅商为代表的社会力量还相当有限,也没有自觉地整合成具有社会影响和经济实力的政治团体开展目的明确的一致行动,也需要政府等给予支持、引领和指导,甚至如袁世凯那样的直接操纵。因此,天津地方自治的模式与各级统治者的目的较为吻合,即宪政编查馆在奏请核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所言,“故言其实,则自治者,所以助官治之不足也”,(45)进而得到清廷的赏识和支持,被立为全国的示范,也成为清政府制定自治章程和各地推行自治的范本。
注释:
①《东方杂志》第3年第11号,1906年。
②李钟钰:《且顽老人七十自叙》(四),中华书局1922年聚珍版,第206页;转引自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9页。
③蒋慎吾:《上海市政的分治时期》,《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2卷4期,1935年3月。
④参见周松青:《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⑤杨逸:《上海市自治志》,大事记甲编,第1页;公牍甲编,第1页。
⑥《总工程局裁判所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号。
⑦[日]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原书房1989年版,第335页。
⑧[法]Procés-Verbaux des Séances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de Tientsin:《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倪瑞英等译,刘海岩总校订,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622-623页。
⑨《天津府自治局文件录要》初编,第1页。
⑩《天津府自治局禀遵拟地方自治应办各事及权限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卷1。
(11)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8页。
(12)《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2290页。
(13)《天津府自治局文件录要》二编,第2页。
(14)《阎绅凤阁等禀请试办直隶全省自治详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卷1;《天津府自治局文件录要》三编,第2页。
(15)(20)廖一中等:《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0、998、1511页。
(16)《大公报》1907年3月28日
(17)《大公报》1907年9月27日。
(18)参见《大公报》1908年3月23日、7月11日、8月16日。
(19)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卷11。
(21)《天津府自治局文件录要》初编,第1页。
(22)《大公报》1906年9月2日。
(23)根据《天津府自治局文件录要》初编第24页整理,天津县自治期成会成员及简历表从略。
(24)天津县议事会议员及简历表从略。
(25)《申报》1911年11月5日。
(26)《申报》1926年5月6日。
(27)《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第88、170-171、809页。
(28)《天津府自治局都理凌守福彭金检讨邦平禀定开办简章》,《北洋公牍类纂》卷1。
(29)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2302、2300页。
(30)《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暂定章程》,《东方杂志》第3卷第11期。
(31)议董两会选举案《禀苏松太道瑞摄选举局与被选举办法改选总动一动半数问》,杨逸:《上海市自治志》公牍甲编,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32)《天津府自治局详开办选举各情形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篡》卷1。
(33)《上海县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3年第1号,1906年。
(34)《总工程局议会章程》,《东方杂志》第3年第12号。
(35)《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0-2298页;《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公决草案一百一十一条》,《北洋公牍类纂》卷一。
(36)杨逸:《上海市自治志·图表》,《上海警务成绩表》。
(37)杨逸:《上海市自治志》,《上海市自治会计表·收支总表》。
(38)杨逸:《上海市自治志·统计》。
(39)《北洋公牍类纂》卷1。
(40)《大公报》1908年3月19日。
(41)《天津县议事会禀督宪请接办捐务科藉议事董事两会常年经费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5,财政一。
(42)《大公报》1908年10月8日。
(43)李达嘉:《上海商人的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1909-191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辑,第187页。
(44)《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公决草案一百一十一条》,《北洋公牍类纂》卷1。
(45)《宪政编查馆奏核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并另拟选举章程摺》,《东方杂志》第6年第1期,19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