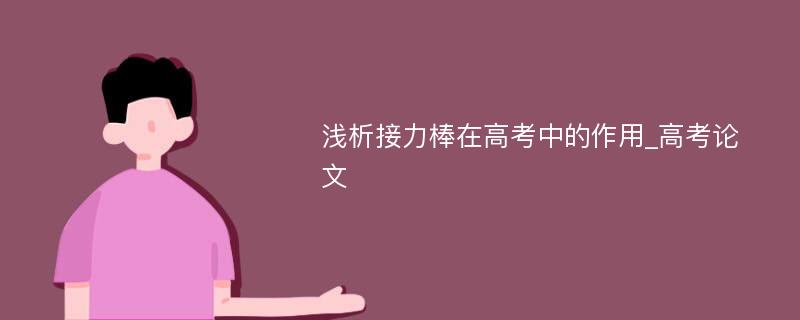
试析高考的指挥棒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挥棒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以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要对象、为高等学校选拔优秀新生的考试手段,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统一考试(以下简称“高考”)是连接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一座桥梁。由于高考密切关乎考生的前途利益,因此它始终处于教育改革的风口浪尖上,成为教育领域少有的广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自1952年建制以来,高考走过了一条崎岖风雨路,在“文革”中更是遭受重挫,一度被废止;1977年高考恢复后又经历了数次重大改革,引发的议论亦褒贬不一。多数人对高考的巨大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高考为高等学校选拔了数以千万计的优秀新生,为我国的高教事业发展、经济建设及社会文明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1997年11月的《人民日报》在纪念恢复高考20周年征文的综述中所说的,“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但随着高考竞争所带来的应试教育弊端的加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社会开始激愤地抨击“片面追求升学率”,尤其对高考的指挥棒作用群起而攻之,甚至有人指责高考是“人神共愤的考试”,号召要“炮轰”统一高考,给高考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为什么高考引发的争论有如此大的歧异?高考指挥棒作用的机制是怎样形成的?这种“指挥”是单向还是双向的?如何发挥高考对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是考试的发源地,是一个十分重视考试的国度。尤其是科举考试制度建立后,考试选才更是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澄清吏治、巩固政权、笼络民心的天下“至公”之法。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在教育和考试领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其影响已积淀为现实基因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出于培养政治人才、发展经济、实现教育民主化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等多种因素的考虑,加之考试自身发展规律使然,于1952年建立了统一高考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后,经过高考选拔出来的大学生作为国家干部的“后备役”,由国家实行“三包”(包上学、包分配、包当干部)。转轨为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高等教育逐渐由“三包”转为“三自”(自费上学、自选课程、自主择业),但在劳动力市场上,高等教育学历文凭仍是进入管理阶层或“白领”阶层的“入场券”。于是,表象上为普通高校选拔新生的高考制度,实际上成了一项上关国家和民族发展前途、下系民众个人命运,集教育功能与社会功能于一身的重要制度,因此,极易引起关注乃至引发争论。这一制度经过50年的运作,已被磨砺成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积极功能与消极影响都十分巨大和明显,引发的争论也因此歧异甚深。
在对高考的批评意见中,无论是谈及60年代开始的“片面追求升学率”,还是论至近些年的应试教育,无不将其归罪于高考的“指挥棒”作用。所谓高考的“指挥棒”作用,是指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皆以高考为中心,围绕高考来运作,“考什么便教什么学什么”,反之亦然。
其实,在教育过程中,考试只是教育教学活动这一“母体”所包含的众多“子体”之一。但身为“子体”的考试之所以能对其“母体”起到指挥和主宰作用,其形成机制乃是源于考试的竞争性。但凡考试必有竞争,尤其在选拔性考试中。而且,为达到区分与选拔的目的,竞争越激烈的考试,其难度越大。正如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文体八股文,之所以会走向“偏题”、“怪题”的死胡同,就是因为发展到清末,士子们对“四书五经”以及八股文的钻研已达到相当精深的程度,加之科举的竞争太激烈,不出“偏颇”、“怪题”不足以保持区分度来选拔人才,尽管这种命题思路已严重偏离了正轨,甚至到了非理性的地步。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长期处于“精英教育”阶段,而中等教育发展相对迅速,60年代以后,高考的竞争激烈程度和考题难度逐年攀升。近几年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竞争的激烈程度表面上虽有所缓解,但在竞争名牌或本科大学分数段上却依然如故。可以预见的是,即使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高考的竞争性依然会存在,只不过竞争的焦点将由“上大学”转移到“上名牌大学”或“读热门专业”上。这说明,竞争是选拔性考试的本质特征,而且竞争的“水涨船高”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考试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客观规律。
无论人们是渴望“上大学”抑或追逐“上名牌大学”、“读热门专业”,表面反映出来的只是一个纯教育的考试竞争问题,其背后实则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使我们不得不将高考指挥棒作用放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认识。从文化上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传统观念仍充盈于现代人的头脑;从社会地位(包括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上看,赢得高考竞争所带来的人生际遇也是中国古代观念“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现代版。因此,根植于社会背景中的高考,便成了高中毕业生面临的第一次强制性的“社会(脑体)大分工”,高考的竞争也便成为人们一生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等社会竞争在教育领域的“浓缩”。正是由于高考具有如此强大的社会功能,只要中国仍需要以高考来制约高校招生面临的人情、关系的困扰,高考的指挥棒作用便必然存在,亦实属正常。从这一意义上说,高考因激烈竞争所招致的同样激烈的社会批评,其实是“替人受过”。
与任何其他作用一样,高考的指挥棒作用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也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面影响。60年代以来,尤其是最近十几年,高考对教育教学的指挥作用已渐渐偏离正确轨道,其消极影响越来越大,并因此招致骂声一片。对高考指挥棒作用的责骂最主要集中在片面教学和学生偏科上,认为这根“魔力指挥棒”使教与学的注意力完全放在所设考试科目上,在“考什么便教什么学什么”的同时,造成“不考什么便不教什么不学什么”的弊病。例如1994年实行的在会考基础上的“新高考”制度改革,按文理分科,实行"3+2"科目组合,将地理、生物和政治(理科)等科目与高考“松绑”。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这些科目在中学的教学中很快受到冷落,大学相应专业在教学过程中则面临学生基础差的问题,师范大学的相应专业毕业生也出现分配困难的窘况。为此,有关学者纷纷上书中央有关部门,高考科目减少给相关学科带来的问题甚至被反映到全国人大的提案中。1996年8月15日,7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光明日报》上联名呼吁重视生命科学,提出:“必须立即恢复理科高考中生物学应有的地位,尤其是对报考生物系及有关医、农等科系,不得免考生物学,以保证学生来源和今后研究和教学的质量。当前,由于应试教育和取消生物学考试的影响,中学生不重视学习生物学,中学生物学教师工作不安心、教学内容落后、实验教学设备匮乏等状况,严重影响中学生物学教学质量。”
高考指挥棒不仅造成片面教学进而带来学生知识结构的偏失(尤其是非考试科目),而且带来学生偏科的问题。例如,为适应正在实行的"3+X"考试科目改革,许多学生从高中一年级起便确定"3+X"中的"X"(实际上绝大部分考生将"X"选为"1"),以便有针对性地学习。有的学生为了避难就易,便尽量不选物理或化学等难度较大的学科,而是选自己学得比较好的科目,从而导致有些科目人数相对集中,并且形成“硬碰硬”的局面。这无疑使竞争更加激烈、心理压力也更大,造成学生学习负担的进一步加重。
然而,由于人们看待高考问题往往带有较强的情绪性,对其指挥棒作用的认识也常常采取了一种“有选择的记忆”态度,高考指挥棒对教育教学发挥的积极影响经由人们的“情绪过滤”后,渐渐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其实,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高考指挥棒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与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一样,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研究价值。从积极方面看,高考可以说是统治阶级意志与教育教学活动之间的一个中介。只要高考作为选拔高校新生的手段存在,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便可以通过对考试内容的规定达到执行国家意志的目的;或者说,高考能在维护国家统治、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出积极的社会功能。而对于学生个体而言,内容科学、形式灵活、录取公平的高考,可以将学生引向身心健康发展的正确方向上,从而发挥出积极的导向作用。实践证明,只要因势利导,考试这根指挥棒就不会“瞎指挥”,以会考合格率作为评价高中教学的主要依据后,绝大多数高中由以往的“升学教育”进步到“教学面向大多数”即是鲜明的例证。如果高考科目设置合理、命题科学,就能有效解决学生因学习偏科而导致的知识残缺不全、重知识轻能力等问题,从而为高校输送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扎实、全面的合格新生。
因此,承认高考指挥棒作用的双向性并进行客观全面的研究,是高考改革成功的前提。改革的关键不应是也不可能扼杀高考的指挥棒作用,而应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的导向功能。
落实到改革实践中,可采取以下几个主要措施:一是稳步扩大招生规模,继续进行取消对考生报名年龄和婚否限制的改革,以减轻高考的竞争压力。二是改革高考的内容与形式,在将中学所有科目吸纳进考试科目的选择范围、增强命题的科学性、满足高等学校的专业差异等前提下,保持一定的考试科目与内容覆盖面,注重考察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深化综合考试改革试验。三是克服以分数为唯一录取标准的片面性,探索建立以分数为主、择优录取的综合评价体系。四是改变文凭至上的教育价值观,使人们从争过高考独木桥改为走多途径发展的立交桥,以弱化其社会导向功能。五是加快高考的社会化改革进程,变过去由学校为由教育行政部门来组织高中毕业生报名和通知录取等有关工作,使高考与学生毕业的学校逐渐脱钩,以淡化其不良竞争色彩。惟其如此,才既能从根本上纠正学生的偏科现象,使其掌握合理的知识结构,又能为高等学校输送基础知识扎实、能满足日益综合化的大学课程学习要求的合格生源,从而使高考指挥棒的运作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