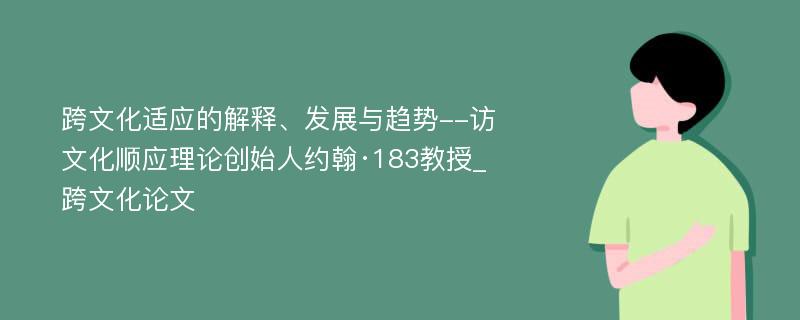
跨文化适应研究的解读、进展与趋势——访文化适应理论奠基人约翰#183;贝瑞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论文,奠基人论文,进展论文,跨文化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 边缘人、整合人、阈限人与文化适应理论解读 问:您在文化适应理论中描述了“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框架,一些学者认为跨文化传播研究者自身“边缘化”的经历是推动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动力之一,您自己是否曾经有过“边缘人”(marginal person)的经历?这些经历是否促成了您的文化适应研究? 贝瑞:“边缘人”的经典定义来自社会学家帕克,他认为“边缘人”的心理状态摇摆悬浮在两种文化世界之中,但不属于任何一种。“摇摆悬浮”(being poised)是指:他们在两种文化世界中体验着心理上的不确定性,不清楚自己是谁,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他们既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也对这些文化没有归属感。“边缘人”概念是我在建构文化适应理论时参考的经典概念之一。不过,我不认为我属于边缘人,也不认为大多数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属于边缘人。我们没有那样的不确定性,而且知道自己是谁。还有些研究者会依附一种以上的文化,我将他们定义为“整合人”(integrated person),他们从不止一个文化中获得知识给养和身份。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父母都是说英语的加拿大人,而我父亲却在加拿大魁北克省一个说法语的村庄里工作。由于我的家庭不信仰天主教,我不得不到另一个镇去上学,而那个镇有很多土著居民。这些经历让我从小就意识到了语言、宗教等跨文化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后来,我在森林里当过伐木工,在船上当过水手,在家具厂当过工人,然后才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从夜校到全日制再到研究生。这期间,我从加拿大出发,到过挪威、刚果、南非、莫桑比克、毛里求斯、苏格兰、塞拉利昂甚至北极圈,也曾短暂地移民澳大利亚,最终重新回到加拿大,在女王大学从教30年。我的研究始终处于跨国的研究之中,而且它们变得越来越重要和有意义,因此,我的学校特批我提前退休,做自己想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现在,我分别在加拿大、俄罗斯、新西兰、荷兰、斯里兰卡、中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和教学活动。 所以,有些人整个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只是一种文化,使用一种语言,和同样的人群交流,而我的经历则有些不同,这些丰富的跨文化经历当然对我建构文化适应理论有所推动。 问:您在文化适应理论中提出了四种文化适应策略:同化、分离、整合、边缘化,对这四点的措辞也从偏好(preferences)、态度(attitudes)变为策略(strategies),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措辞的变化,进而更好地理解您的文化适应策略呢? 贝瑞:我在不断积累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着我的措辞,一开始我使用的是“偏好”,之后我改成了“态度”,现在我称之为“策略”,“策略”一词中包含了态度、行为、动机、目标等。我在研究中发现,人们事实上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并且也在不断地尝试。他们想要用某种方式参与跨文化活动,所以当我分析他们时,我会考虑他们偏好的是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行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还有他们准备做什么。他们应该是也通常是相互联系的,但是态度和行为并非有必然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你的态度并不一定导致你的某种行为,还有其他的限制因素会影响你的行为。即使态度并不总是能从行为上体现出来,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理解态度来理解人们的行为。 人们在理解我的文化适应策略框架时,有时会出现偏差。我曾经用矩形来表示文化适应的四种策略,但人们总会加一些线条把四种策略放在各自的方格之中,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所以,15年前我在研究加拿大的土著居民时,改用圆形来表示策略框架,圆形是一种重要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符合土著居民的世界观,也符合我的初衷,即阻止他人将我的适应策略放入彼此区隔的方格之中。比如,关于“边缘人”的讨论,我们还引入了人类学中更新的概念“阈限人”(liminal man)。二者大致意义相同,但“边缘人”指的是个体不附属于任何一种文化,是一种消极的状态;而“阈限人”则是指个体在所有文化之间游刃有余,是一种积极的状态,这样的“阈限人”也存在于我的策略框架之中。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你首先是文化中人,然后才是跨文化中人,你必须知道你自身的文化身份,才能参与到跨文化活动中去。有时候,你不是简单的个体,你不止属于一种文化、不止拥有一个身份,此时,研究就上升到了多元身份、多种文化归属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将多元文化身份形容为“套娃式”。有时候我是单独的个体,有时候则是说英语的加拿大人,有时候又属于西方世界的一员,每一种小的身份都包含在一个更大的身份中。毫无疑问,有时候它们之间会有冲突,而你通常会赋予某种角色特权,让这个角色比其他的更加重要。比如,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如果有人问我是谁,我会告诉他我是安格鲁魁北克人;当我去欧洲的时候,我则会回答说我是加拿大人;当我来到亚洲,我会告诉大家我来自西方世界。你当时所处的地域和你来自的地方同时影响到你的身份定位。 文化适应研究的新进展与研究方法 问:自20世纪70年代您提出文化适应理论以来,很多人跟随您的理论模型进行研究,但也有些人修正甚至批评了您的研究,比如认为它过于实证主义,您怎么评价这些研究新进展呢? 贝瑞: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在引用和发展我的理论,但我不得不说,人们总是引用我的文章,但是他们很可能没有认真读过,或者,他们没有理解我的原意。1997年,布尔里(Bourhis)提出的“交互式文化适应模型”(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其实是我1974年就提出的理论框架。从1977年到现在,我在很多文章中都探讨了大社会与弱势群体的互动、交流活动,并划分了八种不同的策略,然而,人们总是忽略这些观点,还认为是其他人最先提出来的互动理论。近十年来,我反复强调这是我早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观点:文化适应是不同群体间相互的、双向的参与过程。还有一些人认为我假设只有两种文化在进行相互作用,这也是不对的。关于我的框架理论中所涉及的其他族群,指的是多元的多个族群,并不是单一的文化或是主导社会。 关于实证主义的批评则不同。《国际跨文化关系杂志》上曾有过类似的批判文章,基本上都是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他们认为,没有绝对的社会现实,现实都是在建构之中,因此,他们认为我的研究太实证主义、本质主义。我觉得,他们应该去做些实事,如果你觉得我做得不好,那你就得比我更好。从我个人而言,不能一开始就用经验工具来进行研究,通常是先进行理论研究,先进行思考,提出概念。比如,我使用了策略概念和身份概念,我用了很多的概念来构架我的测量研究,但是我一直相信真实世界的存在。 也有很多人发展了我的研究。例如,新西兰学者科林·沃德(Collen Ward)和她在新加坡的一些同事提出了文化适应指数(acculturation index)和社会文化适应(social-cultural adaptation),去年她又改进了测量表并分享在她的网站上。牙买加学者弗格森(G.Ferguson)提出“远程文化适应”,特指族群非直接接触他文化后,在文化和心理上所发生的变化。也有一些中国学者在研究农民工问题时,发展了我的研究量表。 问:那您认为,在跨文化适应研究中,怎样的研究方法才更为科学呢?比如,是否可以提供某种测量表供后来者借鉴? 贝瑞:人们总是问我“你的测量表在哪里?”我的回答是,我没有统一的测量表,因为每个文化适应的环境都由族群接触的文化所决定。例如,中国人移民到加拿大,语言是文化适应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这对本来就说英语的印度移民来说就不是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应该先从人类学开始研究,找出文化接触的具体方面,就其重要的问题再设计出测量表的内容。 我认为,目前的测量表框架已经基本确立,文化适应的很多相似之处使研究者可以借鉴、使用、调整他人的量表,而同时也需要根据不同的语境,用恰当的文化内容去填充它。尽管我的很多研究都发表了文化适应的测量表,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原版照抄,因为它们不一定适用于其他文化。当然,它们可以作为模型和参考。 在我的研究中,我曾使用三种方法去评估人们的文化适应策略:(1)针对每一种策略分别设计量表;(2)测量其中两个主要的维度,然后再将它们交叉,例如,当人们在两个维度上的程度都比较高时,他们就被认为是采用了整合的策略;(3)创造我们所说的“简介(Vignettes)”①,简单而言,就是用简略的语言描述持不同文化策略的人,例如:“我克里族出生并在那里长大。我一直认为我是克里族的一员,说克里族的语言,有着克里族人的信仰。” 此外,在我2006年出版的一部研究青年移民的书中,我还采用了聚类研究(cluster analysis)的方法,分别用四种文化适应策略量表,研究这些人的朋友是谁、他们本身的文化和接触的其他文化、他们语言和民族国籍、原文化中的身份定位等,然后把不同的变量综合起来,将这些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得到了四个群集(也就是聚类),即高度偏好整合的整合策略人群、低度偏好整合的同化策略人群、边缘化策略人群和分离策略人群。 基于这些研究经历,我提出了混合或双重研究方法(mixed method or a dual approach),即将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我做的人类学考察就是质性的,这通常是前期工作,也是最重要的部分,然后我再做量化研究。如果两者的结论不一致,我会选择质性研究的结果。 全球化与跨文化适应研究趋势 问:如今,全球化、信息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这是否会导致在将来,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之间不再有任何鸿沟?就像一些未来学家所描述的,我们的孩子们将在未来成为数字化公民,他们的生活场景将是虚拟现实,他们的民族文化观念和身份认同或许在将来会消失。基于跨文化适应的研究视角,您怎么看待这些观点? 贝瑞:我不赞同这些观点。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全球化一方面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增加了网络的复杂性。基于跨文化适应的研究视角看待全球化现象,我认为,有的人会被同化,人们变得更相似,这就是很多人认为全球化会带来的唯一产物——文化趋同和心理的同质化。然而,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全球化同时还存在反作用力——本土化,人们通过抗拒外来文化而变得越来越像自己。 我以前有一个土耳其的学生,她曾经每天使用网络和身在土耳其一个小村庄里的母亲聊天来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所以,网络不仅是一个学习新文化的工具,同时也可以保留原有的文化。用我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它就表现出两种层面的倾向:保留原文化、与他文化的交流取向。近期,将会有一本新书《流散的移民》(Diaspora Migration)出版,该书描述了世界范围内的移民现象,例如,以色列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曾移居苏联的德国人回到德国,在苏联生活了近两千年的希腊人回流到希腊等,这些年轻人回到祖国,却成为边缘人,书中把这种现象称为“逆向文化适应”,这也是文化适应的一种现象。全球化的现实社会有许多类似的新现象出现,尤其是在留学生身上。有人可能会被边缘化,有的人可能会从多元社会获益最多。 问:我们了解到,您目前正在进行一些新的学术研究,能否谈谈这些研究的新进展?这些研究是否会建构一些普遍性原则? 贝瑞:是的,我正在进行一项有关多元社会中跨文化关系的大型研究(MIRIPS),这项研究正在20多个国家进行,包括中国。我认为它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很有可能取得实际的成效,并且能够促进多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检验三种假设:多元文化主义假设、整合假设和接触假设。 多元文化主义假设指的是个体或族群对其原本文化身份和其所处大众文化中的身份都感到自信和安全,就会产生相互积极的文化关系,使得接受“他人”成为可能,这种接受方式包括容忍、接受文化多元型社会,以及接受移民和社会的少数群体。相反,当他们的文化身份受到了威胁,则会产生相互的敌意。 整合假设认为,当处于跨文化环境中时,比起拒绝其中一种或两种文化,跨文化交流策略和政策同时支持两种文化(例如传统文化和全民族文化)的参与时,个体和族群的心理输出与社会输出将达到更好的效果,有助于实现成功的双向文化适应。相反,有一些行为方式会导致较弱的文化适应,如限制移民在主文化社区的参与、限制文化遗产的维护和表达、对双方文化都进行限制。 接触假设则是指,跨文化接触能够促进跨文化关系,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文化接触的环境之下,文化族群之间接触得越多,越会相互产生更多积极的作用。这更可能在双方族群都形成安全感(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实现,机会被视为互利的。 这三种假设受到了广泛的支持,MIRIPS计划还在其他一些国家中继续进行,我们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可以论证我们假设的证据,也相信它们将成为跨文化关系和文化适应中的一些普遍性法则,为多元文化社会中的跨文化交流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问:作为一名研究者,您认为跨文化传播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目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问题在哪里? 贝瑞: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目标是努力减少跨文化传播中容易导致冲突的误解和分歧。我们要了解跨文化传播失误的根源在哪里,可能是价值取向,也有可能是历史归因,每个人都承载着历史的包袱,它是文化、社会、心理、信仰的综合体。 进行跨文化关系的基础性研究对一些多元文化国家来说,如巴西、中国、印度,是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可以为多元社会中政策与规划的实施和开发提供理论依据,并且有益于其处理跨文化关系。 可以看到,目前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确存在一些局限性,我曾提出其中九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包括使用更加复杂的模型、抛弃二元文化的观念。同时,我认为,文化适应是一个长期发生的过程,所以,我们的研究也需要长期进行,既要有横向研究,也要有纵向研究,但纵向研究的成本很高,而且总会有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 问:您多次到访中国,您认为中国在文化适应领域中有哪些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贝瑞:谈到中国,我认为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例如,很多人都认为如今的青少年变得越来越西方化,这可能是文化扩散导致的,但我认为使用文化适应策略框架来研究这一现象也很重要。当然,西方化的问题或许并不仅存在于青少年之中。我有一个同事在研究加拿大和美国的双向文化适应,他发现,在美国越靠近加拿大的地方,那里的人和加拿大人更相似。那么,在中国,这样的变化同样需要留意。中国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然而并不能完全排除西方文化对其形成干扰的可能,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介入、扰乱之中,中国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变化却没背离上下几千年的传统? 此外,中国是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也非常值得关注。据我了解,现在有很多少数民族从他们的自治区搬离出来,与此同时,汉族人开始迁入那些地区,这种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迁入迁出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与此类似,农村和城市人口的流动,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这两个问题相互交织。我们曾在重庆做过一项文化适应的研究,研究对象中就包括了从农村移居到城市的汉族人,对他们来说,种族文化和国家文化都没有村庄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大,我们将其定义为地域身份。很多人都有地域身份,他们的身份来源于生活的村子。然而,这种地域特征受到村庄的气味、规模、形状、味道、房屋类型的影响,它与城市身份形成了对比。 这些重要的文化适应问题为中国的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研究素材,值得更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①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简介法(Vignettes)是为研究参与者呈现一种假设的情境,他们会对此作出反应,从而表现出他们的感知、价值观、社会规范或事件印象等。——笔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