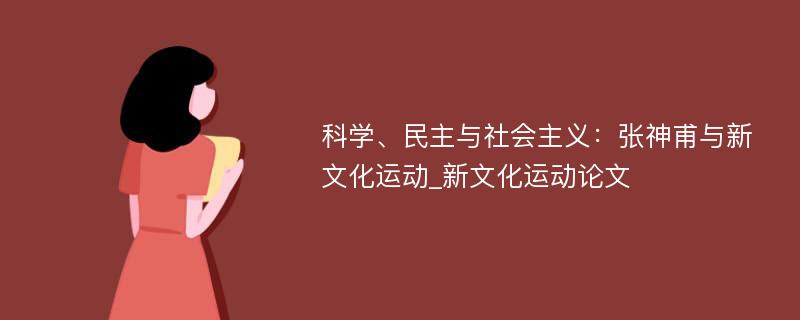
科学、民主与社会主义:张申府与新文化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民主论文,科学论文,张申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4)01-0046-07
张申府哲学思想的形成期是与1915-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相互重叠在一起的。在这个时期,张申府以哲学家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活跃于中国的思想舞台及政治舞台,由此形成了他与新文化运动的双重联系:一方面,其思想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深刻洗礼,属于这一运动的精神产儿;另一方面,其思想又给予新文化运动以积极影响,在这一运动中打上了自己的鲜明印记。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特别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经过1919年五四运动而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种双重联系的关节点也出现了变化,经历了从倡导“科学”、“民主”到主张“社会主义”的转变。可以说,“科学”、“民主”与“社会主义”是张申府哲学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相互联系的三个关节点。本文拟从这些关节点入手,根据《张申府文集》中所收的1917-1926年的著述,对张申府哲学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及其变化作一梳理和阐释,以说明其哲学思想形成的时代因素及内涵,以及对时代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以“纯客观主义”倡导“科学”
“科学”是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树立的思想旗帜,也是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观念。1915年,在标志这一运动发起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即通过《敬告青年》一文向中国青年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P135)正是从这时开始,“科学”旗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象征,给予一代新青年以深刻影响。对于这时的陈独秀,张申府十分推崇和景仰,誉之为中国革新事业里的“最干净的健将”[2](P29);对于陈独秀所树起的“科学”旗帜,张申府则成为其坚定的支持者和积极的鼓吹者。
1919年前后,张申府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表达自己对“科学”的重视和强调。1919年1月,在《每周评论》第5号上,陈独秀以“只眼”为笔名发表《除三害》一文,主张除去中国的“军人害”、“官僚害”和“政客害”。张申府随即在《每周评论》第6号上发表《兴三利》的随感录与之呼应,称:“同社只眼主张除三害,痛快得很。吾愿同时也能兴三利。”其中所兴之一“利”就是:“实行科学教育,使人人对于事物都抱着遵守科学法的态度,都是批疑之胆大而容受之心虚。”[2](P11)1920年,他在《少年世界》第1卷第3期上发表《科学里的一革命》一文,向中国人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称相对论的创立是“革命的物理新说”,认为:“影响所及足可使科学的根本概念——空间、时间、物质、能力、质量、动能等——破天荒的根本改变,自然知识的诸原理通盘再造,流行的科学的哲学完全毁坏。差不多可算安度已二百五十年的奈瑞(牛顿)吸力律既从此站不住脚,代嘉德(今译笛卡儿)以来假定为弥满空间以释万象的‘以太(孔德既曾反对此)也自此不得不退去。”[3](P25)同年,他在《新青年》第7卷第4号上发表《罗素与人口问题》一文,对科学造福人类的效用充满信心,认为科学的进步必定能使全体个人获得身心的健全发展,强调:“我们可期望以科学的发达,身心不健全的均可有处置方法,以至于这种人都没有了:这实是可能的事。”[3](P22)总之,在他看来,“科学”不仅是认识自然世界的伟大工具,而且是改造人类社会的根本手段;要改造旧中国为新中国,就必须大力推崇和积极高扬“科学”。他甚至表示:“我觉着,只替科学吹就好,不论怎么吹都好。我相信弄科学,最是中国今日根本之图。中国人坏到这个样子,中国人麻木到这个样子,中国人敷衍苟且,不耐烦,不讲理,急功贪小便宜,到这个样子,这也非拿一个非不敷衍、非讲理、非耐烦不成的科学来治他不成。中国今日实在应该多多出些科学书。”[4](P91)正是这样,他对当时的自然科学新成就十分关注,积极学习和了解。他晚年在接受美国学者舒衡哲的访谈时回忆说:“任何科学上新的东西,都是我追寻的对象。”[5](P123)
实际上,张申府所说的“只替科学吹就好,不论怎么吹都好”,只是极而言之。他对于“科学”的支持和鼓吹,并非是无原则的,而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原则,这就是立基于科学方法。他指出,“科学”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效力,实在于科学方法的作用。所谓科学方法,在他看来,就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和把握对象世界。“真”与“实”,是他在谈论和表达科学方法时最常用的概念:“吾们只求的是真,吾们只认得的是实。”[2](P31)因此,他又把科学方法称之为“实法”和“纯客观主义”。他说:“须知科学法乃是西洋文明在世界上最大的贡献。新近刚过四百年祭日、有史以来最博学多艺、思想观察极自由、亲自然而顺实的李翁柰(今译达·芬奇)始器重之,厥后百年伽离略(今译伽利略)乃大用之,实立近世科学之基。这个方法,质实说来,本不过实事求是,弃绝习传,说他非西土所专有固无不可。但是用他奏出很大的功验,确是在彼。现在他们把他越发看重,许多地方都要用他,还有好些大的果效放在眼前。吾们今要改革思想,期图自由,变风易俗,实在也缺他不可。科学法就是实法,原来没甚稀奇的。”[2](P32)“我总觉社会改造并不是没办法的。开头的办法也很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你要千万注意的那一‘真’字。申言之,便是‘说实话’。再说,就是要痛揭人类的疮疤;物物事事显出它的本来面目。我信,科学之所图,也不过如此。所以言精神,便是要‘科学法’的精神。起个主义的名字,我就叫它‘纯客观主义’。重反言之:就是要打破一切幻念迷信独断等。”[4](P75)因此,在他看来,支持和鼓吹“科学”,固然需要介绍新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成就,但更为关键的在于倡导这种作为“实法”和“纯客观主义”的科学方法。他于1925年发表《第三文化之建设——一段旧感重发》一文,批评了对“新文化”的种种空谈,认为与其空谈“新文化”,不如着力倡导“科学法”:“精神方面,中国之所最缺,乃在一种合理的态度,乃在一种逻辑的思想,乃在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样子,把西洋文明最大的贡献,科学法,拿来,切实加以培养,切实加以施用,切实加以体现,切实加以发扬,就是了。”[4](P63)由此可见,对作为“纯客观主义”的科学方法的大力强调,才是张申府积极倡导“科学”的归结点及其所理解的“新文化”的真实内核。
张申府在强调科学方法时,尤其推崇英国哲学家罗素及其科学方法,认为罗素取得了划时代的科学研究成就,形成了现代意义的科学方法,对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19年,他在《新潮》第1卷第2期上发表《哲学数学关系史论引》一文,强调哲学的发展与数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力主沿着罗素等科学哲学家的方向“进治真正科学底哲学”。他在文中引了罗素的话:“欲令哲学将来得一空前造诣,唯一必须之端实为创造一流人兼有科学训练哲学兴趣,不羁束于往日之传说,不为专抄古人糟粕者诸文字法所迷惑。”他进而解释说:“此所谓科学数学也,数理物理也,新物理学也,是其最要者。”[3](P5)1920年,他在《新青年》第8卷第2号上发表《罗素》一文称:“罗素最可注意的就是他所抱持的科学精神。他是最能实行科学法的。他真乃最切实、最重事实的哲学家。”他认为,罗素哲学的特点在于倡导一种“最有后望的科学的哲学[3](P36)。对于这种“科学的哲学”的特点以及罗素在其中的地位,他作了进一步说明:“这派的人必须娴于物理、数学与数理名学;因为欲懂得科学最关切哲学的那诸部分,非此不能。罗素便是此派的领袖。罗素哲学地位的优上又不但在英而已。今日进步的可靠的哲学者有一个不受他的影响么?论他的高深精微,论他的广大洪博,今日全世界的哲学家实没一个能比得上他的,就同现今没有一个英人能胜过他的散文能力一样。”[3](P36)正是通过罗素及其科学方法,张申府力主从“科学”出发来看待哲学的发展,认为哲学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运用科学方法来进行哲学思考,而科学的新发展又必将导致哲学的新变革。
这样一来,在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就形成了两大路向:一是胡适所倡导的以杜威为代表的实验主义方法;二是张申府所倡导的以罗素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对于杜威的实验主义,张申府也认为有其合理性;但二者相比,他更赞成罗素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早在1921年,他就对这两位大哲学家作过比较:“现代西洋哲学家最懂得科学方法最能用他的,要数罗素第一,杜威也知重之,便差远了。”[4](P22)1922年,他对这个问题作了更明确的说明,指出:“杜威实在没有多少好处。有之,只一点,胡适之很晓得。便是他的实验方法。便是他的日常主义。科学上用这个方法,日常生活上用这个方法。社会、政治上也要用这个方法。罗素的好处,吾们能知道,他是最重科学方法的。他广大,深微,而切实。他倡哲学里的科学法,开哲学的新纪元。他是晓得哲学之真意思的。他是晓得哲学之真价值的。吾们相信,哲学如果长存在,意思绝难出了罗素所说的意思,价值绝难多过罗素所说的价值。”[4](P37)张申府之所以如此看重罗素的科学方法,不仅是因为这些方法使罗素在科学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更在于其所体现的“纯客观主义”能直接通向现代唯物主义。他说:“罗素的好处,还不止此。他还有他的真理说。他说真理是与事实相应的说话。吾们尝说,真理就是实话。真理不过实话之雅名。实话以外,更无什么高不可攀的真理。吾们这个说法,小部分由于自家的体验,大部分根本罗素所说。”[4](P37)又说:“更有一个必要的常识,罗素说过。他说,对于一个东西,总是越离近,越认识的真切;越解析,越晓得清楚。吾们也说,一个主张,必越切实的试行,才越觉着有活趣。”[4](P39)后来,他在《所思·序言》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近来最常盘还于我脑际或喉头的,则尤在分析(analysis,我尤常愿名之为‘解析’),多元(pluralism),客观(objectivism),切实(realism)之四事。后二者合之,便可得流行的所谓‘唯物’(materialism)。又如最懂得这些的罗素说,二十世纪初从多方面发生起的一种普通叫作‘实在论’(即‘realism’)的哲学,其实在的特征也是以为方法则在分析,以为元学则在多元。”[2](P53)
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开展来说,最有影响力与感召力的人物当然是这一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和胡适,张申府最初也是陈独秀倡导“科学”的追随者。但张申府在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的支持和鼓吹,却鲜明地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并预示了其哲学思想在此后的发展方向。1930年代,他继续强调中国新哲学必须沿着科学化方向开展,并力主把科学主义分析方法与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3](P186)。这就使得自严复以来的科学主义思潮发生了重要分化,在以胡适、丁文江、王星拱为代表的经验论科学主义之外,形成了以张申府、张岱年兄弟为代表人物的唯物论科学主义。
二、以“新教育”与“自由”倡导“民主”
“民主”与“科学”一样,也是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树立的思想旗帜,是其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观念。1915年,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即提出了“科学与人权并重”的主张。在同年出版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他又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提出中国教育应当以“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和“兽性主义”为其方针,并在对“惟民主义”的阐释中明确强调了“民主”的意义。他说:“欧美政治学者诠释近世国家之通义曰:‘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全体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易词言之,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执政之私产也,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者也。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全体国民之权利也。伪国家者,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利,以奉一人也。……若惟民主义之国家,固吾人财产身家之所托。”[1](P144)自此以后,他对“科学”与“人权”的倡导就演变为对“科学”与“民主”的倡导,并将“科学”与“民主”生动形象地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对于陈独秀所树起的“民主”旗帜,张申府也是其坚定的支持者和积极的鼓吹者。
张申府认为,中国之所以需要“民主”,并非仅仅缘于西方的强烈影响,而在于中国自身有其深刻的根据,实是与中国社会现状相联系的。由于中国现实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不民主,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因而才产生了新文化运动对“民主”的需要和呼唤。1920年,他在《劳动界》第六册上发表《打破现状 才有进步》一文,向工农劳动者揭露社会的不平等,指出:“人生在世,必缺不了衣食与居住。但是若不种田纺棉,那里来得衣食?若不盖房筑屋,人向那里住居?种田纺棉盖房筑室的是什么人?不是农工劳动么?那个财主花百十万银盖的高楼大厦少了瓦匠能成功?那个赛过邓通的阔老缺了胼手胝足的农夫不饿死?人的世界实在由农工养活着。吾刚才说的衣食居住,不过举几个大端,此外细看看那一样好的、必须的事情,没有劳动能存在?人的世界一天没劳动,一天就会消灭。”[4](P17)1921年,他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发表《社会》一文,对现存社会给予猛烈批判:“吾知许多人虽不能晓得社会是什么,却晓得社会的代表者。社会的代表者是什么?在上者,现在占优势有权力者。现在上者占优势者是什么?资本家、官僚、皇帝、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男子;比较抽象的:习惯、风俗、从古传来的制度、先民遗留的思想、法律、禁(入国问‘禁’之‘禁’)、私有制度、婚嫁制度、国(吾信国是一种制度,但新有社会学者说国是一种结社,如寇尔(Cole)马克威(Maeiver)等)、爱国心、国旗崇拜、崇拜生殖器、上帝……在现在服从社会,能外乎服从这些东西么?”[2](P40)这种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批判包括了多方面的文化因素,但最主要的是对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平等、不民主的否定。正因如此,他在《兴三利》一文中认为,最根本的兴“利”是:“创办种种真正绝对的民本事业,成立种种真正绝对的民本制度,务令人世的确是人的人世,不再是帝王军阀的人世,不再是官僚政客的人世,不再是资本家财主的人世。”[2](P11)他在这里所强调的“真正绝对的民本制度”,也就是陈独秀所主张的“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的民主国家。
张申府对于“民主”的倡导也有自己的特点,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特点在于,张申府认为,民主制度的建设需要有一个逐渐培育的过程,不是一呼即来、一蹴而就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更是如此。在这方面,教育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切社会的改革必以教育的改革为基础”[4](P1)。1919年12月,他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新学校”》一文,宣传欧洲新出现的“新学校”,力主通过创办类似的“新学校”,以“新教育”来培养民主制度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在文章中,他对这类“新学校”作了全面介绍,特别谈到了“新学校”在管理中所实行的“学校的共和制度”的意义。所谓“学校的共和”制度,“就是由校长、教员、学生,有的且并校役,组织一普通会议,作为学校真实的管理团体,草定校法。由此校法,更为公同目的,规定共同的工作”[4](P6)。他对这一学校管理制度评价甚高:“这个学校最惹注意的一点,在他的管理会议。六岁的学生与最老的教员有平等的投票权,这是何等的精神。”[4](P8)他进而认为:“吾们简单评这种学校,可以说他的精神是自由的;他的组织是民主的;他的方法是自然的、切实的重内发不务外镇的;他对于儿童是真懂得真能尊重他,不是以儿童为工具的,是要设出种种机会,使儿童发露其所能,使其自由活泼,能想,能实现其想;他对于个人与团体能够并重,无所偏倚;重实验不忽理论,重具体不忽抽象。能使学生身心智情全部发达,能使学生得高尚的意趣。像这种学校的教育乃真是科学的教育,科学法的教育。”4](P8—9)在他看来,只有在这样的“新教育”中,才能培养民主制度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否则,民主制度是难以真正建立起来的。
其另一个特点在于,张申府主张以“自由”作为“民主”的内核,反对离开“自由”来谈民主制度建设。1919年,他在《每周评论》第30号和第32号上连载了《自由与秩序》一文,强调“自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自由本是政治营生中最伟大最宝贵的东西”;“秩序当为自由而设,妨碍自由的秩序是绝对要不得的”[2](P30)。而他所理解的“自由”,就是“合乎自然的自由”。他认为:“违背自然的制度总不会有好结果。待遇一个人、一个群、一个种族、一个阶级,如使自发自展,见助而不见阻,那个人群种族阶级便是走在正道。这条新则的势子已至是流行如火的了。凡自然都是帮忙这种待遇的,自然之中,自有法律。自然之中,自有秩序。”他进而指出:“以前人讲自由,常说什么自由于法律之中。天性少人性多的人遂就把法律为利器,一切压抑专暴之弊都从此起。须知现在世界的法律本是少数人居着强者、享乐者、统治者的地位,本是私意设的。这种东西,岂可容他约束人人应有的自由?”[2](P30)沿着这一思路,他还进一步把“自由”加以具体化,强调在中国对“自由”的追求不是抽象的高调,而有其具体的内容。1920年,他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号上发表《就来的三自由》一文,指出:“信仰自由、思想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不论实现没实现,完全实现没完全实现,许多民主‘国’总都把它们订入什么‘宪法’了。但是合理的自由、合乎自然的自由就止于此么?吾以为除此以外,还有三种自由,更加重要。但令我们肯去找它们,它们就会来。自由总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不要它的时候,它也有时会来;但是我们去找它,关系乃觉亲切。我们要找的三自由是什么?第一,就是教育自由。第二,工作自由。第三,男女关系自由。”[4](P13)这种对“自由”的重视及具体化,使得对“民主”的倡导具有了更为具体的内核和目标。
在张申府看来,人的自由精神也需要通过教育加以培养。他之所以提倡“新学校”、“新教育”,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旧学校、旧教育扼杀了人的自由精神。他在《“新学校”》一文中说:“从来的教育都是职在维持原状的,重在传衍而不重在创发。作教师的都是小霸王,总讲的是要怎么样尊严;他们本来不晓得学生的真实价值,所以总把之瞧不起。他们最怕的,最忌的,就是学生能想,所以不等他们想出,便已横加以错误之罪名。自由思想的根在这个学校的小群里便已锄了;将来到大群里,又怎么还能自由思想?”[4](P1)因此,他提出创办“新学校”,发展“新教育”,从儿童开始培育人的自由精神。可以说,他倡导“民主”的这两个特点,实有着内在的关联。
这样一来,重视“新教育”与强调“自由”成为张申府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理解“民主”的鲜明特点。他正是以这些特点深化和丰富了新文化运动中先进中国人对“民主”的倡导和理解并深刻地影响了其民主思想的开展。在他日后的民主主张中,可以看到这些特点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解,反而有时更为鲜明地表达出来。在193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中,他进一步把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与民主”口号加以完善,提出“‘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4](P190)。在1940年代前期的抗日战争中,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民主,更明确地提出:“民主本就是使人人都平等自由。平等自由的人与其自由越多,就是越民主。……根本上,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以及思想信仰研究讲习的自由,是必说不上民主的。”[4](P472)在1945年发表的《民主大纲》中,他进而把“自由”、“平等”与“合作”列为“民主的三要素”[4](P532)。在这些有关民主的主张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对“民主”的思考所留下的影响。
三、以“中国改造”倡导“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也是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主张的基本价值观念。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在发表《敬告青年》的同时,还发表了《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对“社会主义”作了专门的介绍,指出:“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1](P136)然而,社会主义作为一大思潮在中国思想界的崛起,是在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分界线的新文化运动后期。一方面,这时的世界局势已大变,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社会主义由一种思想和运动而成为活生生的新社会制度;另一方面,这时的中国形势也已大变,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使一批先进中国人开始放弃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学习,决心以俄国人为榜样,重新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而选择了以社会主义救中国。正因如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及其追随者在这时出现了分化,从中产生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张申府就是这批先行者之一。也正因如此,新文化运动经历了从倡导“科学”、“民主”到主张“社会主义”的转变,张申府的思想也与时俱进而经历了这一转变。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始终高度评价新文化运动的这一历史性变化。他在晚年回忆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给正在寻求解放道路的中国人民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2](P473)
张申府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介绍,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就已开始。1919年4月,他在《每周评论》第17号上发表了题为《威尔逊》的随感录,通过评论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欧洲之行,表达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积极支持:“威尔逊总统在欧几十天的经验,晓得永久的和平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由他这句话,可以看出三件事情。一、永久的和平并不是绝对不可能,是用政治手腕去得他,不可能。威总统若是个真实明白人,应当给俄国的改革事业以极大的赞助。二、世界有什么人为的阶级、界限存着的时候,世界绝无安宁日子。三、世界的教育若不改变方针,世界绝不会走到好的地方去。现在的教育权是握在政客、政治家的手里,他们最大的职分就是维持现状,怎肯彻底的改?怎会知道彻底的改?所以吾们可以推知深信世界的少数明白人,必不可不切实结合起来,从根本上下手,想个釜底抽薪的法子,作一群的急先锋,拼命实地的、各尽所能的去活动,万不可再想讨巧,万不可再存一丝姑息、再存一毫客气。”[2](P26)同年7月,他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题为《知识阶级》的随感录,赞扬俄国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俄罗斯之有今日,首先在世界上树出新组织,他的社会中有思想有知识的人,实在有很大的功。……要想顺着世界大道——改造——走,自必也大有赖于此样人。知识阶级是什么呢?照俄人所自解的,他就是自觉的国民。不是单单认识文字、受过教育的,乃是批评的思索家,对于现代社会总是反抗的,所希望的是解放与革命,行其所信无他顾,牺牲一切唯急于救其国人,常有自由奔放、独立不羁的态度。”[2](P36)这些都表明,张申府是社会主义思潮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崛起的积极推动者。
当张申府于1920年底来到欧洲后,进一步结合他的直接观察和实际了解,撰写文章介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旗帜鲜明地赞成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主义主张。1921年11月,他在北京《晨报》上连载长文《各地劳动运动现状》,着重介绍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劳动运动。该文开篇即指出,“劳动运动是现在世界最有力量的运动”;而作为劳动运动之一部分,“社会主义已成为不可侮的怪物”。他进而对社会主义与劳动运动的关系作了说明,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劳动人民真正获得解放,而劳动人民正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力军。他说:“社会主义是想解劳动之轭的,更切实言之,便是要使劳动居其应当居的地位。劳动运动的归趋,就在实现社会主义制,社会主义运动最靠得住的战斗员,又就是劳动阶级。”[4](P23)1922年,他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上发表多篇相关文章,着重对列宁思想和共产主义问题进行说明。他在《巴黎通信》一文中,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及思想进行了介绍,指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最富学理的价值。法译今年才出,较英译(一九一九出)为好。他去年又作了一本书,法译名《共产主义之孩子病》,英译名《左派共产主义——一个孩子病》,在战略上很重要。”[4](P41)他所说的列宁名著《共产主义之孩子病》,今通译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此后的岁月里,《国家与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读的经典文献。他在《共产主义之界说》一文中,根据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实际经验,对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环节进行了阐发,指出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应包括五个主要信念:“第一,资本制度,在世界文明上,就令可算一个必经之阶,绝不能为真文明之基础。第二,资本制度现在已处在一种极不安的状态:资本主义已不能管他自己的事;就说大混乱还未开始,实已迫在眉睫。第三,只由无产阶级的专政,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安定才能重得,秩序与进步才能再望。第四,这个变更,必须是革命性质的,必须以非宪的手段抓住权力;必须以强力扑灭反革命。第五,资本主义的推翻必须是全世界的;地方的革命不济事,非实现世界革命的计略,共产主义不能成就。”他的结论是:“简括言之:阶级战争,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全权属于‘苏维埃’(农工评议会):一切共有的共产主义舍此不立。”[2](P48)
张申府在介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时,特别强调了共产党在这一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他认为,要追求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就需要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革命。1922年,他在法国巴黎出刊的《少年》上发表了多篇文章,论述了共产党的作用和建设问题。他在《少年》第2号发表《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一文,指出:“近世以来,劳动运动之势力,已蓬勃的非到全世界社会改造,不能收拾。然劳动界的人,固未同样的觉悟,也非有同样的本领,虽有共同的利益,却非同样的知道怎样去达。在这时候,试问,若无作率导的团体,运动怎能成功?寻常战争,不能无先锋;阶级战争又怎能缺了先锋?劳动阶级的这种先锋便是共产党,有了这个机关,乃有了指路的。有了这个机关,本阶级较进步的分子乃可领着全体群众,鼓舞前进。”[4](P45)他进而以1917年俄国革命的成功和1919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为例,说明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最近俄国十月的革命,为什么成功,德国正月的革命为什么失败,主要的原因还不是一有坚强的共产党,一无坚强的共产党。”[4](P45—46)他在《少年》第3号发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一文联系中国实际指出:“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是要使人人都得其所的,是不许一人逾其分的。共产党主张的,因此绝不是少数人的利害。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劳动阶级或同化于劳动阶级的。必须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须了然于同阶级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认除此共同的利害,别无利害。必须对于现世的恶,誓死不相容。这样的人,中国是有的,必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有可为。”[4](P50)在这些文章中,他反复强调要建设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强固的共产党”,明确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一种看法,即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一个根本不同就在于具有严格的纪律性。他在《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一文中对共产党的“真谛”作了阐明:“若其真谛,还别有在。在什么?两言以蔽之,曰:纪律。有纪律,有共产党;无纪律,无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强在此,共产党之能成功在此。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不同,此其重要点之一。”“真正的共产党是一点不苟且的,是一点不姑息的,不但显然不忠,或违犯纪律的党员,为其所不容,便是一个党员,居重要职位,而作事不得法,或见解不当,也必逐无疑。”[4](P46、47)而共产党之所以需要严格的纪律,正在于统一党的思想与行动,使党在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具有坚强的战斗力。他感慨地说:“没有纪律,不能坚固,不能精神贯一,一个共产党形体不坚固,精神不贯一,又岂有能成功之理?……纪律是共产党之魂。失此,共产党是不能活的;不懂得这个的人,不配加入共产党,更不配组织共产党!”[4](P47)《少年》尽管只是一份中国旅法共产主义者的内部刊物,但集结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领袖人物。张申府后来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成立后,又发起了共产主义少年团,一时有五六十人。……我并同周恩来、赵世炎办了一个小小的油印刊物《少年》,作为机关刊。”“该刊是油印本,封面是红色的。我和周恩来经常为《少年》写稿,并负责编辑工作。刻写蜡版和油印的工作主要是由陈延年和陈乔年二位同志负责的。”[2](P542、479)由此可见,张申府的这些文章在当时尽管传播范围有限,但其影响力确是不能低估的。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张申府不仅积极介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在1921年7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他发表了《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一文,首先介绍了英国和法国共产党的情况,进而联系到中国的现实,提出了“中国改造”问题,以此作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近期目标。他指出:“吾到法后,感着欧洲一时是无望的。生于东方的人,不能不仍希望东方。”[4](P21)对于“中国改造”,他提出了具体的构想:“吾觉着中国改造的程叙应是:革命,开明专制(美其名曰劳农专政——以今日中国之一般知识阶级而言代议政治,讲选举,纯粹是欺人之谈。政治上事切忌客气。政治尤不可专模仿人。世界趋势固要晓得,但勉随趋势而忘了自己实况,必无好结果。能认事实是列宁一大长处),实行极端的强迫教育,以岁入之半办教育,其次重要的为改良农业,整理森林河渠,兴发工业交通,尤以旧有的工业为要。”[4](P22)在这里,他提出了“中国改造”的程序步骤和思想方法。在“中国改造”的程序步骤上,他既强调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又指出这个新型国家在革命后必须重视教育和发展经济。在“中国改造”的思想方法上,他主张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政治尤不可专模仿人”,“世界趋势固要晓得,但勉随趋势而忘了自己实况,必无好结果”,“能认事实是列宁一大长处”。在今天看来,张申府的这些思想无疑存在着不足之处。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在于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作了根本否定,而未看到其中所包含的历史合理性,因而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一种“开明专制”,忽视了其中所应具有的民主内容。但总地说来,这些程序步骤和思想方法,在以后九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大都得到了应验,显示出其预见性和合理性。在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的岁月里,能有此远见卓识,确实不易。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启的“中国改造”的伟大事业,张申府作为早期参与者深知其艰难,在《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一文中感叹地说:“这种话在现在只算是一个梦,但与普通的梦一样,却有应了的希望。”[4](P22)这段话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提出的“中国梦”观念。这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梦”观念早在社会主义作为一大思潮而于新文化运动后期崛起之时即已提出,可谓源远流长。今天我们在畅论“中国梦”时,不应忘记先行者张申府。
上述通过“科学”、“民主”与“社会主义”三个关节点,清楚地呈现出张申府哲学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相互联系: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以其新的价值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张申府哲学思想的形成。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其思想经历了从倡导“科学”、“民主”到主张“社会主义”的转变;另一方面,张申府在哲学思想上又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以自己的思想积极参与了新文化运动。他以“纯客观主义”倡导“科学”,以“新教育”与“自由”倡导“民主”,以“中国改造”倡导“社会主义”,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及这些新的价值观念的凸显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入手探讨张申府哲学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及其变化,对于深化张申府研究和新文化运动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
标签:新文化运动论文; 张申府论文; 科学论文; 陈独秀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新青年论文; 哲学家论文; 罗素论文; 每周评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