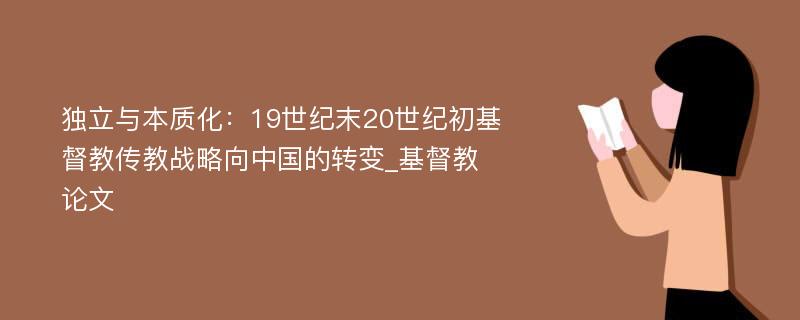
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世纪末论文,自立论文,本色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教会的自立与本色化问题成为研讨20世纪前期中国基督教史的学者愈益关注的问题。研究者多将自立教会的成长和中国教会寻求本色化的历程作为这一时期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主要成就。但实际上,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使中国教会走向自立和本色化,也是欧美在华各传教机构的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传教战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传教机构和传教士在中国教会的自立和本色化方面甚至充当了倡导者甚至组织者的角色。本文试图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立与本色化作为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作粗略考察,希望得到指正。
一
自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到广州,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曾经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艰难时期。但到19世纪末,随着环境和条件的改善,传教事业开始进入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1842年,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吸收信徒仅6人;1858年在500人以下;但到1889年,这个数字便扩大到37287人;[1](P82)1900年,信徒总数更达85000人,分属欧美在华建立的61个宣教会。[2](P89,101)这种结果,基本上是各宣教会在较为传统的传教模式下取得的。这里所谓“传统的传教模式”,是指欧美各教会之传教机构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主要运用传教机构在其国内募集的经费,从事宣教和教会教育、医疗等事业,吸收信徒,扩大影响。在此过程中,他们往往雇佣本地信徒作为开展各项事业的助手。勿庸置疑,在这种传教模式中,传教士处于基督教事业的中心位置,是教会的灵魂人物。
但从19世纪后期开始,这种模式不断受到质疑。在基督教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它并不符合传教运动的宗旨,而且将贻害无穷。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应该从以传教士为中心的时代,走向以本土教会为中心的时代;中国教会应当从依赖传教士走向自养、自治、自传;基督教应当脱离由洋教士输入、发展、控制的状态,成为融入中国社会,在中国本地的文化背景中得到表达的宗教。这种“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的教会,即所谓“本色教会”。[3](P6~7)进入20世纪以后,使中国教会走向自立,成为传教士和中国教徒的共同目标。而在1922年的全国基督教大会后,使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呼声,则渐成教会发展的主旋律。
这种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在教会内外都具有值得重视的历史背景。
近代基督教海外传教运动是一种涉及广泛地域的世界性运动。亚洲、非洲等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地区,都是传教机构开疆拓土的场所。传教士在中国所遇到的困惑和问题,其他地区的传教士也同样遇到。随着传教运动的规模日益扩大,传教机构在经济上的压力也日益彰显,这是提出本土教会应结束依赖传教士的供给而实现“自养”的直接原因。较早提出本地教会应当自养、自治、自传的,是英国圣公会在非洲的传教士亨利·韦恩(Henry Venn)。早在1841年,鉴于差会遭遇较大的经济困难,韦恩就提出’了在当地教会中使用本地牧师和实现本地教会自养的问题。[4](P3~4)此后,他逐渐将这种主张发展成较为系统的建立自养(Self-supporting)、自治(Self-governing)、自传(Self-extension)教会的传教理论。在1860年的利物浦传教大会上,韦恩的“三自”理论得到众多与会者的赞同,表明韦恩的思考并非仅仅来自他个人的独特感受,而是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4](P24)几乎与韦恩同时,美国公理会传教机构美部会负责人拉福士·安德森(Rufus Anderson)也开始阐发类似的观点。他在1841年美部会年度报告中曾提出,要注重在传教活动中选择当地教会领袖,“通过这种方法使福音很快在那片土地上本色化,使福音机构通过上帝的恩典,获得自养和自传的能力”。[5](P103)安德森的有关“三自”的理论,在他后来的著述中有更系统的阐述。
由亨利·韦恩和拉福士·安德森等人倡导并发展起来的“三自”理论,在19世纪后期不仅在新教传教运动中成为渐占主流的传教思想,而且陆续在世界各地得到实践。1900年,在纽约举行的普世传教大会上,本土教会自身的发展问题得到关注。来自印度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约翰·麦克罗伦(John McLaurin)在发言中指出:“印度、中国和其他各地教会未来的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地区的灵性生活和本土教牧人员的奉献”。[6](P275)在这次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就“本土教会的自养”举行了专题报告会。美以美会的乔治·温顿(George B.Winton)在其报告中提出了传教工作的几个原则:传教资金仅限于资助与传教士自身的工作有关的活动;从一开始就教导皈依者分担教会的负担;采取一些措施尽量使本地教会实现自养;等等。[6](P289~324)这次会议达成了包括“全世界的传教团体均已同意接受将实现自养作为基本原则”的三项共识。[6](P323)从传教士们的报告来看,“三自”在世界各地都成为一种付诸实践的传教方法。
这些,为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类似的探索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和可资借鉴的先例。同时,19世纪后期中国各地不断的反教风潮和20世纪初中国人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也为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的转变提供了外在的动力。
近代来华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就在事实上享有列强的政治保护。《中美天津条约》中的“传教宽容条款”,以及1902~1903年中美、中英商约,就传教士的特权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使传教士可以利用不平等条约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尽管如此,以各类教案为主的反教运动在19世纪后期贯穿于基督教在华扩展的整个过程,并在1900年爆发为全国规模的义和团运动。教会在这一运动中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是人们熟知的事实。八国联军和清政府对义和团的绞杀,并没有使基督教会获得更为安全的环境。进入20世纪后,经过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启蒙,中华民族在新的高度开始了民族觉醒的过程。1905年开始的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预示着新形势下的民族主义成为基督教必须面对的政治现实。英国长老会传教士汲约翰(John C.Gibson)在1907年基督教入华百年大会的主题发言中指出:“中国民族精神的觉醒在教会内外都已达到惊人的程度。这一点在帝国各处都可得到证明。这种觉醒使中国有希望在未来臻于强大,但在此刻却未必没有危险。它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于外国控制乃至外国影响的失去耐心的焦躁,这在教会内外都可以感受得到。”[7](P5)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毕来思(P.E.Price)则在文章中描绘了一幅举国上下一致排外的情景:
(中国民族主义)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时代象征就是其悄然的但持续不断的排外宣传。用骚动和攻击来反对甚或凌辱外国人的行为业已停止。那些沙文主义者学会了更好的办法。他们开始使用比较温和然而更为有效的手段。例如,很多广为传唱的流行歌曲充满了狂暴的排外情绪。许多在学校使用的教科书灌输同样的东西。……(这些都)将外国人作为一个阶层塑造成一群阴险狡诈和令人厌恶的人。[8](P21)
在20世纪早期,除了北洋政府和部分遗老一度别有用心地提倡“定孔教为国教”外,基督教并未遭遇汲约翰和毕来思们所担忧的危险。“五四”前后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在最初的阶段亦未波及基督教,直到1922年开始的非基督教运动。关于这场延续数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学界已有详细的讨论,此处不赘。这一由知识界、教育界、思想界发起和参与,并以发动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为政治背景的运动,在当时社会上发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基督教事业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之后,在各方面都呈现下滑趋势。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在华外国传教机构和传教士更饱受冲击。1927年3月,在南京发生的由几个外国人被杀而引发的“南京事件”,[9](P393~399)竟使许多传教士迅速离开中国,并在数年内难以恢复元气。
在20世纪前期民族主义运动中露出头角的还有中国基督徒。《教务杂志》在1909年3月号发表了一位中国留美学生的信。这位来自杭州之江大学的不知其名的基督徒在这封长信中表达了极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或者说是民族主义情绪。他宣称:“我的心里有三样东西”,“排在首要位置的是神,其次是人类,第三是民族”。但他接着又说,“没有民族之基础,就无法为人类服务。没有民族和人类作为一种背景,则无法为上帝服务。”[10](P149)作者还认为,尽管传教士怀有良好的意愿,无私地工作,但他们“对中国的伤害多于施惠,他们比任何西方人,无论是政客还是商人,对中国的伤害都要大”。[10](P150~151)作者宣布:“我已决定将爱国主义作为自己人生之旅的目标”;如果要在祖国和基督教之间进行取舍,那么,“我强烈地表达我的立场如下:宁可要没有基督教的中国,也不要没有中国的基督教。如果基督教不能与中国共存,或者会扰乱或遏制她的民族生机,我们,至少我们大部分基督徒,宁可不要它”。[10](P151~152)
同样的态度在20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再次显现出来。1925年6月23日,在作为当时革命中心的广州,发生了英法军警开枪射杀抗议“五卅惨案”游行队伍的“沙基惨案”。在惨案的刺激之下,广州掀起了更为猛烈的反帝风暴。仍然带有浓厚的“洋教”色彩的基督教,数年来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屡受冲击的本地教会,在这风暴中既无法幸免于波及,亦难以置身于事外。基督教会别无选择,加入到抗议列强在华暴行的行列。广州基督教界,积极行动,先后成立“广州基督徒沪案声援会”、“广州基督徒大联合”等组织,广东大会的一些领袖在其中起到骨干作用。英美一些传教机构,如美国北长老会海外传道部,也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放弃条约特权,并同情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11](P37~43)
所有这些都表明:觉醒了的中国不欢迎由外国传教士主宰的基督教会。在上述背景下,基督教在华传教的战略所实现的转变,是下文将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二
在基督教海外传教理论得到发展的背景下,来华传教士应对上述挑战的一个主要战略,就是主张确立以本土教会为中心的原则,建立“自养”、“自治”和“自传”的自立教会。
有些论者认为,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对教会自立问题的探索,可以追溯到1840年代曾以独立传教士身份在华活动的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在华南地区建立“福汉会”的实践。[4](P4)“福汉会”是郭士立在担任英国驻香港总督璞鼎查的中文秘书期间建立起来的一个基督教团体。郭氏声称,这个团体在由本地教徒管理、由中国人向中国人传教的模式下运作,在短短数年内,在中国沿海以及远至华北的广大内陆地区,发展了1000名以上的信徒,拥有100余名华人宣教师。然而,后来一项针对这个取得奇迹般的“成功”组织的调查表明,郭氏的成就基本上建立在谎言和欺骗的基础上。调查的结果一经公布之后,“福汉会”就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了。(注:有关“福汉会”的情况,参见拙著《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183页。)
“福汉会”成为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的一个笑柄。但在继郭士立而来的传教士看来,也许他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他希望提倡的传教原则含有上述“自养”、“自治”、“自传”的精神。1860年代本着此种精神尝试进行自立实践的闽南长老会、伦敦会、美国归正会传教士的努力,因为脚踏实地而不带有郭士立式的浮躁,便得到了广泛的肯定。(注:有关情况见许声炎:《闽南长老会自立自养历史》;周之德:《闽南伦敦会自养之历史》,《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期,1914年,第31-36页。)到1877年第一次全国新教传教士大会召开时,实现本土教会的“自养”,成为一个引起大家兴趣的议题。美以美会在福州的传教士保灵(S.L.Baldwin)就“本土教会的自养”作了长篇的发言。他在开篇就指出:“本土教会应尽早实现自养,而我们的责任是在权限范围内竭尽所能达致这一结果,这种主张现在已无人争议了,而且对此也不应有何争议”。他认为只有实现本土教会的自养,所谓“本土教会”才算实至名归;“一个依靠外国资金供养的教会只会受到猜疑”。[12](P283~284)保灵词锋锐利地抨击差会供养本土教会的旧模式,指出:“在这种体制下受到训练的人们的基督教无疑是发育迟滞且扭曲变形的,它没有脊梁”;“中国基督徒受到导引,觉得西方基督徒有充沛的资金,他们异乎寻常地乐于捐输,帮助中国基督徒”。[12](P287~288)保灵认为要纠正这种状况,传教士就必须在使用传教资金雇佣助手方面谨慎行事,“雇佣适当的人向其异教徒同胞宜讲福音;但一旦其成员进入教会团契,在开始时就应使他们养成习惯,依其能力支持福音事业”。[12](P287)他在演讲结束之际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使信徒在一开始就向教会捐献;要向中国基督徒表明,传教士在宣教和教育方面提供资金是暂时的,信徒必须自己捐资支持其福音机构;避免支付超过皈依者预期的薪水;不要建造花费昂贵的西洋式教堂,代之以中国风格的建筑。[12](P292)保灵的这些观点,在会上受到众多传教士的讨论,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1886~1887年,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的传教士倪维思(J.L.Nevius)在《教务杂志》上发表了总题为《传教工作之方法》的系列文章,后集为专书出版。该书在此后若干年里“被广泛阅读,并在关于传教政策的讨论中经常被引用”。它的主旨是鼓吹如何“以最小的代价使世界福音化”。[13](P109)倪维思反对其他传教士经常采用的支付薪金雇佣中国皈依者做布道员或助手的“旧方法”,提倡在不雇佣或尽量少雇佣本地助手的情况下拓展教务。他的这种做法被称作“倪维思方法”。另一位美北长老会在山东的传教士狄考文(C.W.Mateer)曾将他的观点概括为:雇佣新皈依者为受薪助手将会损害其所在的传教机构;这种做法同时也对受雇者本人造成伤害;这种“旧系统”还使得皈依者真假莫辨;养成惟利是图的风气,使基督徒贪财好货,成为“吃教者”(rice Christians);使那些原本克尽义务的基督徒望而却步;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的眼里都降低了传教事业的声誉与影响。[13](P113)倪维思声称,他在拒绝雇佣本地助手的情况下,坚持在山东烟台一带巡回布道,以自养、自传的原则,成功地建立了数十个传教站,吸引了数以百计的中国人入教。他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式的变革,在当时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使“年轻的传教士在著述和演说中大量引证这一假定的‘新方法’的成功”。[13](P109)倪维思在1890年的第二次全国传教士大会上,还专门就雇佣本地助手的问题进行了专题报告。他声称其“新方法”,即通过传教士巡回布道、以自养为原则开办新的传教站,吸收信徒的方法,具有吸引公众注意,迅速吸收大量信徒,使皈依者弃绝偶像崇拜,坚定其信仰,有利于对信徒实施有力的控制和权威,等等优点。[14](P167~177)
在1900年4月纽约普世传教大会上,“倪维思方法”成为议题之一。但他的前同事狄考文却在会上对其传教活动及其方法提出了质疑乃至抨击,指出:“他按自己的方法工作了7年之久,却没有收到一个信徒,至今在其工作的地区也没有一个通过这种方法发展的皈依者”;他曾声称自己吸收到七八百名信徒,“但今天在其原来的传教区域却没有一个自养教堂。那里确实有几个自养堂,但却没有一个是倪维思博士工作的产物”。[6](P311)狄考文在这个重要的会议上所作的这种揭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赴会之前,他就开始在《教务杂志》连载长篇文章《“传教工作方法”一书的审视》,根据他所作的具体调查,对“倪维思方法”及倪维思本人的传教工作进行了详尽的省察。他认为倪维思自己大肆宣扬的“新方法”基本上是失败的,而倪维思本人所宣称的成就则是建立在不实之词、或者说是谎言的基础上的,倪维思有意给人们在“新方法”的功效方面造成错觉。[13](P109~122,163~174,217~232)
倪维思本人已在1893年故去,没有机会为自己申辩;狄考文所指出的事实看来也是难以否认的,并且得到其他在华传教士的支持。但倪维思并没有成为第二个郭士立。这是因为,也许他的成就是虚拟的,但他所宣扬的教会“自养”、“自治”,减轻差会经济负担的“新方法”却符合基督教世界传教运动的思想潮流,亨利·韦恩和拉福士·安德森首先揭橥的“三自”原则越来越普遍地被接受。1907年基督教入华百年大会(第三次全国传教士大会)上,本土教会的自养、自治和自传,成为首要的议题。英国传教士汲约翰在会上所做的主旨报告《论中国教会》,结合自己在汕头的具体实践,就此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引起较以往更为热烈的讨论。
汲约翰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中国教会“脱离外国教会的控制而独立”。他认为这种独立的时机已经渐臻成熟,“在中国基督徒中有许多具有高尚情操和优点的人,他们对见证主的荣耀怀有真正的热情,并深爱他的教会和他的人民。这些人对其同胞和他们的宗教生活具有天然的知识。不管我们的理论为何,我们都会发现,向他们请教是甚为妥当的”。汲约翰认为中国教会的“自治”即由中国基督徒自己领导和管理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应满怀忌意地在形势所迫下让出,而是应该急切地倡导并参与这一过程”。[15](P8~11)汲约翰承认,要做到“自治”,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中国教会必须能够“自养”,即在经济上首先自立。他认为做到这一点,有赖于教徒“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双重觉醒”;而在当时情况下比较可行的一个途径是鼓励信徒捐献,以此支撑自治教会事工的运行与发展。他在报告中提出了这方面的若干原则:传教基金(即各传教差会提供的资金)只可由各传道团来管理使用;由中国教会自身的管理机构来募集和管理中国教徒的捐献资金;华人牧师等须全由中国人自己的资金供养;地方慈善事业和集体崇拜活动,须由当地基督教团体来管理;等等。[15](P11~15)汲约翰进而指出,“自治”和“自养”毕竟只是“达致目的的手段”,而作为教会主要功能的“自传”,才是应该为之奋斗的目的。他认为要中国教会实现“自传”,应该从三个方面努力。首先,应该促使基督徒在其日常生活中见证圣灵的召唤并受感动;其次,让教徒随时随地不拘形式,共同祈祷,相互激励;第三,各教会建立自己的传教组织。[15](p16)汲约翰还特别以在这三个方面似乎进行得颇为成功的长老会“汕头体制”(The Swatow Scheme)为例,来说明建立本土自养教会的基本模式。
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关于“中国教会”的共有10项。其中第4项决议规定,来华传教士应向派遣他们的母国教会正式提出如下建议:
(a)他们应当批准由他们的传教士作出的一项认可,即由他们所建立的中国教会有权根据自己的关于真理和责任的见解将其自身组织为独立教会,并就传教士在其领导团体中的地位作出合适的安排,直至这些(中国)教会能够做到完全的自养和自治。
(b)他们应当避免声称对于这些中国教会拥有任何永久的精神上或行政上的控制权。[15](P410)
在新教入华100周年的大会上通过这样的决议,无论是其实际意义还是其象征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
虽然在20世纪早期,有些传教士看上去对建立脱离差会控制的自立教会还心存疑虑,但大部分传教士对此则抱着积极的态度。美国归正会秘书科勃(Henry N.Cobb)19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不言而喻,在每一个传教区域建立具有完全的自治、自养和自传能力的本土教会,这是海外传教活动的终极目的。”[16](P172)这代表了来华传教士的普遍看法,他们普遍接受了“传教士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尽早使其自身丧失必要性”这种观念。[17](P336)所谓使传教士自身“丧失必要性”,就是使中国教会“脱离外国的控制”,实现本土教会的自治。他们在各种场合发表言论,继续构建关于自立教会的理论体系。从世纪之初到20年代,仅在基督教刊物《教务杂志》所发表的传教士关于中国自立教会问题的文章近百篇。这些文章从各方面阐述建立中国自立教会的理论根据和现实基础,并提出了各种建议和方案。1922年,美国北长老会的马德(W.A.Mather)发表题为《已经证明的自养原理》一文,再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本土教会自养与自立的理论。该文第一部分对“现行的津贴体系”即差会对中国教会的经济支持进行质疑和反省。他承认这一体系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但指出保持这一体系的后果将是很有害的。它会“腐蚀基督徒和信众的道德”;“引起贪心”;导致“伪善”行为;使志愿人员沮丧;使传教士凌驾在本土教会之上;违背西方的习俗和思想方式;最后,使中国教徒失去民族认同,从而使教会丧失影响。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论证中国教会自养必要性与现实基础。他指出,使中国教会实现自养是“最好的(传教)方法”,也是“最成功的传教方法”。同时,早期教会的历史,自古以来的传教历史,宗教改革的历史,以及现代传教史,都证明本土教会的自养是完全“可能”的,例如在中国,厦门和汕头的自养教会的建立和存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该文的第三部分主要论述实现自立的途径,包括一些具体的建议。[18](P20~28,89~95)
以上考察了作为基督教对华传教新战略的教会自立理论。1922年以后,教会自立的口号越来越被“本色教会”的口号所取代。所谓“本色教会”,或教会“本色化”,按照中国教会领袖诚静怡的解释,除了“教会一切事工,应由中国信徒负责”,即以上所论的“三自”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如何使基督教在东方适合东方人之需要?如何使基督教事业,融洽东方之习俗环境历史思想,与其深入人心不可破之数千年结晶文化?”这样的问题。[19](P9~10)诚静怡还在其他多个场合进行过类似的解释,并普遍被接受。
事实上,在提出“三自”的同时,欧美传教理论家和来华传教士就已使用“本色教会”(indigenous church)之类的说法,并常常将之与“三自”联系在一起。诚静怡主张基督教与东方文化历史环境相融合,也就是主张东方历史文化具有与基督教相容的内在价值。对此,西方宗教理论家和传教士也进行过论述。在20世纪,不少传教士和基督教思想家都从神学的角度,对东方民族及其宗教的内在价值,即丰富基督教思想的作用,进行了论述。美国奥伯林学院院长H.C.King在1906年就发表了如下观点:“我们必须承认……那些其他民族必须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具有自己的对基督教进行诠释的机会,他们同样能为世人理解最伟大的真理作出重大贡献。”[20](P173)另一位叫做丹尼尔·弗莱明(Daniel J.Fleming)的作者认为,“神的真理并没有被全部给予某一个民族,通向基督之路就是满怀感激地探索非基督教的信仰”。[20(P176)1910年的爱丁堡世界传教大会上,一个关于传教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强调:“我们所有作者都同意,传教士……应该坦诚和高兴地承认他们从当地信仰中发现了善和真”。[20](P177)因此,在东方国家创建教会的一个理想方法,就是将基督教的基本原则传播给东方民族,“并让这些灵性上的冲激在东方的民族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和联合发展之特殊的式样,这样,各国的基督教会在最初就能成为真正本色化的教会”。[21](P25)
来华传教士结合基督教在中国的情形阐述类似的思想。1924年,基督会传教士美格思(Edwin Marx)对与“本色化”相近的“本土化”(naturalization)进行过解释,指出这个名词意味着“基督教为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所同化”,成为“拥有中国精神并以中国样式表达出来”的宗教,意味着“由这个国家的人民通过对教义的陈述,通过作为其自身经验结晶而非其西方导师的教诲结果的礼仪形式、建筑和音乐,对基督教进行诠释”。[22](P97)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先后担任中华基督教会和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的高伯兰(A.R.Kepler)在阐述中华基督教会的宗旨时也说,要“使中华基督教会范围内的各教会,能有随时试验和自然发展的机会,更使他们能发见一种最完善的教会组织方式,其中不但包含千九百年以来基督教会之基本的与有益的部分,且能进一步地成为一个本色化的,能表显中国的生活和文化之教会”。[23](P32)曾任长沙雅礼大学校长的爱德华·休谟(Edward Hume)试图从更为根本的层面为中国建立本色化教会之价值作论证。他认为,东西方民族的“宗教本能”是相同的,“我们必须对东方宗教的灵性价值有新的理解”,这些宗教“追求永恒的真理”;传教士作为基督教在东方的代表,应该将东西方宗教相融和,“与其东方的兄弟在追求永恒真理的过程中合作”;而且,“必定会有来自东方的使者为西方带来宗教的消息……他们将是那些能够拓宽和丰盛我们关于基督教的观念的人”。[20](P170~171)长期担任《教务杂志》主编的乐灵生著文抨击了在对华传教运动中存在的白人种族主义,特别对那种认为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道德上较西方人劣等的观念,作了长篇的批驳。他认为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区别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基本价值的差异,而实际上中国人在道德水平和道德能力与西方人也是平等的。[24](P575~590)
这些论述,都为“本色教会”思想与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
以上探讨了关于对华传教战略转变时代的理论和思想。这些理论和思想并非仅仅停留于言论阶段,来华传教士将此落实到具体的传教活动中,从而推动了20世纪前期中国教会的发展。这里仅就欧美传教机构在华发起和推动的教会合一运动和移交传教事业的过程,对此作简略的说明。
传教士所论证的教会自立理论,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关于中国教会合一问题的讨论。所谓“合一”,是指本土教会为了克服自身力量弱小的缺陷,破除拥有不同的教派背景的西方各传教差会带来的五花八门的宗派主义,以及由此造成的教会之间的此疆彼界,在各大宗派内部超越小宗派的歧见合而为一;或是在教育、医疗、宗教教育等基督教事业方面进行实质性合作;或是以地域为中心,跨越宗派差别实现更为广泛的合一,以此消解教会的国外教派背景,通过打破宗派壁垒来减弱教会的“洋教”色彩。
传教士关于中国教会合一的论证,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以后,特别是民国建立后,则进入实际酝酿和实施阶段。汲约翰1907年在基督教入华百年大会上关于教会自立的理论阐述,就包含了本土教会合一方面的内容。曾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罗炳生(EdwinC.Lobenstine)认为,之所以出现教会合一运动普遍开展的局面,除了教会本身不断发展、交通日益便利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宣教师深觉,虽各教会宗派不同,持论互异,然大体尚无不同。不应另树旗帜,各行其是。果能联合一体,同力协作,其收效也必巨”。[25](P199)另一位传教士方约翰(A.J.Fisher)在1934年著文认为,实现教会合一已是人们的共识,“凡是教会中具有思想之士,无不承认‘宗派’为传布福音的一大障碍”。[21](P24)同时,前文所述的民族主义运动对基督教会的冲击,也是传教士促进合一运动的外在动力。美国浸礼会的传教士就表示:“我们对于在华基督徒中所表显的合作精神,和合一的感觉,深以为快。教会在过去数年内所遭遇的灾患,以及非基督教运动所给予的各种打击,反能使基督徒之间彼此放弃宗派主义,而注意于合一运动”。[23](P29)不同教派的传教士在20世纪前期一直坚持探索教会合一的问题,他们有的对全国性合一教会的名称和教会行政进行探讨;有的就教会合一的类型发表意见;有的提出一些具体的计划,等等。(注:如:G.G.Warren,"Uni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34,pp.477-483;J.B.Cochram,"The Question of Union,A General Statement",The Chinese Recorder,vol.37,pp.305~308.)这些,限于篇幅,难以一一论列。
合一事业(很多文献称为“联合事业”或“协和工作”)的实际推动者也是传教士。可以说,传教士教会自立理论的具体实践,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他们在推动中国本土教会合一方面的努力。在这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中华基督教会的成立。这个20世纪前期中国最大的、全国性的、合作型的教会,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自19世纪末开始的美国北长老会开始策动的合一工作。在义和团运动后,美国北长老会在华各传教机构全力合作,与长老宗派的其他在华传教机构一道,为全国性长老教会合一的实现进行了长期努力。从1901年开始,他们先后召开多次会议进行磋商,成立过多个临时性组织推动合一工作。1905年,他们在上海召开的委办会议上通过了“合一计划书”。1907年4月19日,基督教入华百年大会召开期间,中华长老会联会首次会议在上海召开。其后,分别于1909、1914、1915年召开了数次联会,酝酿成立中华长老会全国总会。[26](续P45~46)1918年4月17日,他们在南京成立了“全国长老会临时总会”。[27](P50)次年1月,长老宗派的传教士与伦敦会、美部会传教士在南京举行委办会议,讨论三派合一之事,起草了“信条”和“典章”[28](P1~24)。1922年4月,三会代表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临时总会。1927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正式成立于上海。它后来成为由14个教派、数百个教堂组成的教会,拥有教徒人数占全国基督徒人数的1/3左右。这是传教士推动的合一运动所产生的一个最显著的成果,也可以看作基督教对华传教新战略的重要果实。
在20世纪初年蔚然兴起的合一运动,在欧战后的一段时期曾一度遇到障碍,“就是教会内部关于信仰问题的争执。这件事的起因,是教会中人因为见解的不同,分做了‘基要主义’和‘现代主义,两派,彼此攻击非难,剑拔弩张”,[29](P5)反映到中国教会,就对合一运动形成困扰。但从总体上来说,其影响并非巨大,如参与中华基督教会的各派别,就在20年代初共同迅速地推动了这个合一教会的形成。除中华基督教会外,中华浸礼会、英国卫理宗各会的联合,也是合一事业成功的例证。就区域而言,广东、闽南等地,都是教会合一开展得较为成功的地区。
“本色教会”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以教会中心”,即中国本土教会是各地基督教事业的中心。由于历史原因,在20世纪前期,大部分地方教会还处在外国传教机构的实际控制之下。各地基督教传道团或多或少开办和管理着各级学校、各类医院和慈善机关。这种传教士控制教会事业的局面不结束,传教机构的权力不移交给中国教会,就谈不上什么“教会中心原则”,更难以使教会“本色化”。有鉴于此,各地传教机构为了实现新的传教战略,从20年代后期到抗战爆发,有计划地将其控制的各项事业次第移交给中国教会管理。这一过程需要专文论述,这里仅以美国北长老会华南传道团向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移交事业为例,对其情况略作说明。
美国北长老会华南传道团是华南地区势力最大的传教机构之一,在广东各地拥有众多的事业。1920年代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也是非基督教运动的中心之一。华南传道团在此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特别是1925年“沙基惨案”发生后,更是面对日甚一日的群众运动的大潮。在此情况下,这个传道团促使参与广东协会的各外国传教团体,将各项权力移交给由华人教会领袖管理的广东协会。经过一段时期的协商和讨论,1926年11月,该传道团与广东协会就移交各项事业的原则达成一致意见,通过了《差会向教会移交规则》等文件,就人事、财产、基金、各项事业(教务、教育、医疗及合一事业)以及其他事项的移交,和今后双方的行为规范、发展措施等,作了比较细致的规定。此后,该传道团有步骤地将其长期以来所开办和经营的各项事业,如:夏葛女子医学院、广州真光中学、培英中学、阳江医院、阳江教会学校、协和神学院、各项其他教育事业和产业,以及传教基金、学额基金,等等,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移交给广东协会和岭南大学等机构。通过这一过程,美北长老会华南传道团与广东协会建立了具有典范性的关系。广东协会在该传道团及其他传教机构的支持下,发展成中华基督教教会系统内势力最大、本色化程度最高的教会之一。(注:关于美国北长老会与广东协会的关系,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资料出处恕不一一注明。)
这些事实都表明,传教机构和传教士不仅提供新的传教战略的理论,而且也是这种理论的实践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的演变,是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这篇短文只能对其概况作鸟瞰式的考察,而未能实现有深度的研讨。不过,以上所论也许可以表明,尽管20世纪前期中国基督教史的主题,已从传教事业的发展演变为本色教事业的发展,传教机构和传教士依然在这一嬗变过程扮演着要角。“传教士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尽早使其自身丧失必要性”,这句话彰显了传教士对其使命的自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使中国教会走向自立,使其朝向本色化的方向迈进,是欧美教会颇为一致的对华传教战略。在讨论“本色教会运动”之类的课题时,记住这一点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