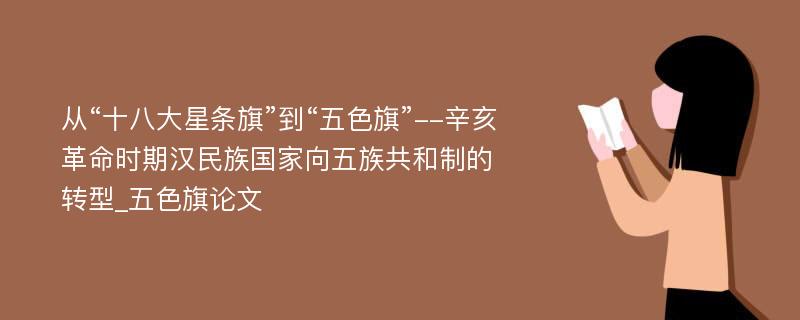
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汉族论文,国家论文,共和论文,五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2)02-0106-09
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要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尽人皆知的中国同盟会誓词,但对这八个字的解释却历来并不清晰。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1906年在日本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有这样的解释:“一、驱除鞑虏: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二、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1](P296)
这个阐释的含糊之处在于没有说清其中的地域概念,人们往往把誓词理解为推翻满清政府,在旧政府原有的全部领土范围内建立新国家,但实际上这种理解并不准确。“驱除”并不等于“推翻”,“驱除鞑虏”自然是要把“鞑虏”驱赶到某个地方去,就是要把满族赶回满洲,如当年朱元璋把蒙族赶回蒙古草原,这里就含有分裂国家领土的意味;“恢复”自然是回到原来的情形,汉族被满清灭国前的情况,大致相当于十八行省的范围,因此“恢复中华”主要是在这汉族聚居的十八行省范围恢复建立汉族国家(这个范围没有包括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只相当于当时中国领土的不到一半),而且这种思想是有着深厚基础的。
“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思想的第一个来源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孙中山一向以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的事业自勉,在1906年《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说到:“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1](P325)1912年2月12日南北议和成功,清帝刚刚退位,孙中山就决定于15日在南京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亲率民国政府各部部长及右都尉以上将校参谒明孝陵,异常隆重地祭祀明太祖朱元璋,祭文中有:“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2](P95)以共和国总统的身份,率领整个共和国政府,以如此规格祭祀一位封建王朝皇帝,其追怀崇敬之情可以想见,实际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来源于朱元璋的讨元檄文。
关于恢复建立传统的汉族国家的土地范围,虽然也有不同的说法,但还是以“十八行省”最为普遍接受。孙中山认为这就是汉族的传统疆域:“且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几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1](P223)当时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邹容《革命军》也称:“昔之禹贡九州,今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地乎?”[3](P670)武昌起义后,军政府以象征十八省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为国旗,对全国发出的文告也都以“十八省”为号召,详见后文。偶尔也有“十九省”的提法,比如章太炎写道:“自渝关而外,东三省者,为满洲之分地;自渝关而内,十九行省者,为汉人之分地。满洲尝盗吾汉土以为己有,而吾汉人于满洲之土未尝有所侵攘焉。今日逐满,亦犹田园居宅为他人所割据,而据旧时之契约界碑,以收复吾所故有而已。”[3](P97)
要之,革命派中流行的思想,是并不把满蒙等少数民族区域当作中国固有的领土,所以在革命后建立新国家时可有可无。1908年《民报》文章《仇一姓不仇一族论》中批判满清政府时称:“甲午之役,括吾民之膏血以赎其长白山之故巢,亦既无赖极矣。”[4](P43)这等于否认辽东半岛是需要保全的中国领土。1908年《民报》章太炎《排满平议》中有:“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以复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以神州之奥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东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4](P51),认为从中国版图把少数民族区域分割出去,国土面积小了,更加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
“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欧洲从19世纪开始日益发达的所谓“民族建国主义”理论,即认为民族独立建国至为正大,在民族国家竞争的世界里,惟有单一民族的国家才能强固有力,否则必然分崩离析,这种思想在《江苏》、《浙江潮》、《民报》等当时著名的革命派刊物上广为宣扬,影响很大。1903年《江苏》《新政府之建设》一文中有:“试一翻近世史,二三百年来此等惊天动地之大风潮,龙拏虎掷之大活剧,连篇累牍纷陈眼帘,何一非民族主义所激荡所演出者耶!盖自‘两民族必不能并立于一政府统治下’之精理既发明,欧洲之政局乃大变动,而所谓民族建国主义者磅礴膨胀不可消磨。”[3](P588)
当时革命派中甚至有非民族的国家不算国家的论断,1903年《浙江潮》《民族主义论》一文阐发颇为透辟,严厉批判合众多民族为一大帝国的思想:“非民族的国家,不得谓之国。……集多数人民,以公同之力之志意,向公同之目的,发公同之行为者,则曰国。而置一国于此,其内容则键结无数之异族焉,其思想不同,其语言不同,其风俗习惯不同……及政府之能力衰,而民族的反拨性起。吾证之于远,则罗马是也。彼虽能键无数民族于一国下,然一时而已,不转瞬而亡也。吾证之于近,则蒙古是也。彼能并欧亚二大族而统一之,然泡影焉。”[3](P490)清王朝的广阔疆域是在康熙、乾隆之世,由“十全武功”的征伐奠定,由上面的思想推论,大清国当然也不得谓之国,自然也难免解体的命运,革命创建的新国家自然也不应当完整继承清帝国的版图。
明确提出在“十八省”“建民族的国家”的,是1903年《江苏》《政体进化论》一文:“如吾前所举民主政体成立之四因,吾国实有其三焉:(一)十八省得天然之地势,远胜美之十三州,以地理论可独立而民主也;……(三)同胞四亿万,同文同风同利害,群策群力何事不成,以民族论尤可独立而为民主也。……二十世纪中,必现出一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耳!……以我民族建我新国,全权在我……呜呼!建民族之国家,立共和之宪章,凡我同胞,其矢斯志。”[3](P545-547)
综上,可以看出革命派中存在着以在汉族聚居的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的革命建国思想,对于满、蒙、回、藏等族聚居区,则认为在新国家中可有可无,偏激一点的甚至认为没有更好。当然,受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影响较深的只是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而且即使是这部分人后来在立宪派的舆论攻势之下,也不得不把这种对于国人来说过于激烈的主张隐藏起来。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贯反对革命派的种族革命学说,以为满汉早已融合,革命必遭瓜分,特别是杨度1907年在《中国新报》上发表的《中国新报叙》一文,论述民族革命必然引起国家分裂,至少可能分裂为汉、蒙、回、藏四国,分裂则必然遭到列强瓜分以至于亡国[5](P872),颇能言之成理,迫使革命派不得不正面回答。《民报》相继发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汪东《革命今势论》等文章,加上前一年发表的汪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算是对立宪派的回答。然而,汪精卫完全以美英“门户开放”政策立论,回避了民族分裂问题;章太炎、汪东则一相情愿地认为蒙、回、藏各族发展程度不足以自立,畏惧列强则必然依附汉族,回避了由激烈民族主义对各族的冲击而产生的离心倾向。总之,革命派的回答说服力不强,似乎只是表面上的应付,内心深处仍是以为少数民族区域的去留是次要问题,不必在革命胜利之前重点加以考虑。
二、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为日本黑龙会等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日本黑龙会1901年2月3日成立,其宗旨是:“回顾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为实行兴隆东亚的经纶,挫折西力东渐之势,目前的急务是先与俄国开战,在东亚将其击退,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6](P158)黑龙会的创建者和领袖是内田良平。
从黑龙会的宗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凶恶的侵华组织,其目标是先击退1900年庚子之变中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俄国势力,进而吞并东北三省、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这一地区有著名的大河黑龙江,所以定会名为“黑龙会”。黑龙会通过公开的舆论鼓吹和私下游说高级军政官员,对推动日俄战争的爆发起到了重要作用,日俄战争的结果终于使日本侵华势力侵入我国东北。值得一提的是,黑龙会的领袖内田良平1894年就曾经建立“天佑侠”组织,深入到朝鲜东学党起义军中,对推动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起过一定的作用,可以说是日本对外侵略的急先锋。
然而就是这个凶恶的侵华组织黑龙会以及它的领袖内田良平,却与中国同盟会以及孙中山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内田良平1898年就通过宫崎寅藏与孙中山相识,1900年到新加坡帮助孙中山组织广东惠州起义。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再到日本,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同盟会成立筹备会就是于7月30日在东京内田良平家中召开的,会上内田良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不久,当时的黑龙会会员、后来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灵魂的北一辉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内田良平在《日本之亚细亚》一书中提到孙中山1906年以来曾对日本朝野人士游说,以中国革命后在长城以南建国,满蒙让给日本,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报酬。[4](P73)1912年2月初南北议和成功的前夕,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山县有朋等通过森恪与孙中山、黄兴商谈由日本提供给革命党一千万到二千万日元的援助,换取中国以某种形式把东三省让与日本,但由于2月12日南北议和成功,这一意向无形打消。实际上,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巨大的反对力量,这一意向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但当时孙中山、黄兴并没有拒绝日本的建议,经由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和中国学者俞辛焞的考证,应该是确实的。[7](P501-516)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者,中国同盟会是伟大的爱国团体,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何以孙中山和同盟会与日本一部分侵华势力能够形成如此密切的关系呢?有些学者难以理解这一点,曾经竭力加以辩驳,但黑龙会是公开的政治团体,以黑龙江命名,有各种公开出版物宣扬其侵略主张,内田良平更是通过著述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侵略思想,如果说孙中山和同盟会不了解内田良平与黑龙会的侵略立场,那就过分牵强了。既然了解其立场,而又过从甚密,必然要对合作的基础和条件达成某种共识。
实际上,孙中山和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虽然是坚定的爱国者,但不免有其思想和认识上的局限,正是这种局限给日本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一,革命派中流行着狭隘“民族建国主义”及由此产生的在18行省建立汉族国家的革命建国思想,把满蒙置于可有可无之地。第二,不了解我国北方汉族在清代大规模扩散、因而形成广阔的民族杂居区域的国情,因此对国家和民族分裂可能给各族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缺乏认识。由于巨大的人口增长,清代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省汉族人口向东三省、内蒙、新疆等地大规模移民,形成了广阔的民族杂居区,革命派中大多是南方人,孙中山长期漂泊海外,对南方沿海人口移居海外的情形非常熟悉,而对北方人口分布的重大变化认识不清,因此对国家和民族分裂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估计不足。第三,可能还有为整体利益牺牲局部的想法,这与列宁和德国签定代价很大的布列斯特条约有些类似。
三、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
到革命大规模爆发时,上述思想局限产生的危害就会集中表现出来,造成很大的危机。1907年孙中山在南洋忙于组织两广的起义,东京同盟会本部呈现涣散状态,一部分来自长江流域的革命派为联络会党,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发展,在东京成立了“共进会”,其中重要人物有张百祥、焦达峰、刘公、居正、孙武等,共进会的革命旗帜定为“十八星旗”:“用大红色为底布,由中间辐射出来九个黑色锐角,每个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黄色圆星,内外各九个共十八个,以表示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8](P502)“十八星旗”可以说是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思想的一个具体结果。
1908年冬,共进会孙武、焦达峰、彭汉遗等先后回国,但联络会党很不顺利,而工作重点转向新军后,进展神速。1911年9月14日湖北的共进会组织与新军中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决定实行合并,发动起义的条件接近成熟了。9月24日,新军中的革命情绪已经难以抑制,意外发生了南湖炮队暴动事件,总督瑞澂开始严密戒备。革命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0月6日(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发动起义,同时议决“东京共进会预拟的国旗图样和大都督印钤,更应早日制就,以备应用。[8](P521)
可以看出,虽然后来“十八星旗”被定为陆军军旗,但当时是把它作为新国家的国旗的,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时也是把它当作与“五色旗”、“青天白日旗”并列来确定国旗的三种选择之一。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十八星旗”高高飘扬在蛇山黄鹤楼头,成为革命的象征,激励着革命军民的斗争意志。但它同时也是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十八星旗”仅仅代表十八个行省,黑龙江、吉林、奉天、新疆四个行省以及内外蒙古和西藏等广大范围的区域被排除在外,这使国家的领土完整受到重大威胁。
军政府成立不久即发出《布告全国电》,转载刊布于全国各报,影响很大,其中动辄以“十八省”、“汉族”、“汉人”为号召,痛斥满人则云“我十八行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姊妹,莫不遭逢淫杀”,号召革命则云“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之光荣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9](P100)大约同一时期发出的《布告海内人士电》则称:“为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报二百六十年之仇……我汉人四万万之生命,死活在此一举,成则与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再享万万世世之福,否则堕于地狱中永无超生之日矣……今日之举,是合十八行省诸英雄倡此义举。”[10](P138)可见在武昌起义初期,军政府完全被“民族建国主义”的狭隘思想所控制,以在十八省建立汉族国家为号召,还没有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的考虑。
共进会的排满立场在革命派中本来就较为偏激,加之两湖素以民气刚猛著称,故而当时武汉革命军中民族主义情绪甚为狭隘激烈,革命军中的两条主要军纪是“不准侵犯汉民”和“不准危害外人”[8](P311),也就是说中国汉族之外的各民族是不在保护之列的,因此武汉满人被杀者有数百人之多,虽妇孺亦有所不免。
《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收有以中华民国军统领黎元洪名义发布的《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影印件,这篇檄文产生于武昌起义之初,虽然流布不广,但可以生动地反映当时民族情绪偏激的程度。檄文的后半部分是以发表于1907年《民报》增刊《天讨》上章太炎撰写的“讨满洲檄”为底本,略加改动而成的,结尾一段的改动令人震惊,竟然是把原文只是针对满人,扩大到以满、蒙、回、藏四族为敌:“又尔蒙回藏人,受我华之卵育者二百余年……尔若忘我汉德,尔恶不悛,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乃蹀足謦欬,与外蒙响应,军政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11](P630)这一段对1907年章太炎原文的主要改动在于:(1)原文“又尔满洲胡人”改为“又尔蒙回藏人”;(2)原文“尔胡人之归化于汉土者”改为“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3)原文“与外胡响应”改为“与外蒙响应”。[12](P290)可以看出,武昌檄文的民族主义立场比章氏檄文更加狭隘激烈,简直带有与满蒙回藏四大族决裂的气味,而且满人之外特别针对蒙古族。
四川也是共进会影响较大的省份,共进会在日本成立时四川会党首领张百祥曾被推选为总理,1911年11月27日蒲殿俊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的旗帜也是“十八星旗”,不过形式和湖北似乎略有不同,英国驻成都总领事是这样描述的:“那面旗帜(我想目前中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上面有红字(汉),周围有十八颗星绕成的一个黑圈,形状象是太阳,但颜色是黑的。……旗帜上‘星’的数目是十八颗,而不是二十一颗或二十三颗,这个情况表明把东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尔)排斥在联邦之外。”[13](P247-249)可以看出,四川“十八星旗”颜色不同,还多了一个代表汉族的“汉”字,但无论如何它们向外界传达的信息是明确一致的,就是要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扩展,越来越多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进来,加上革命党中原有的温和派力量,革命开始变得温和起来,湖北黎元洪、汤化龙、湖南谭延闿、江苏程德全、浙江汤寿潜等相继进入革命领导层,特别是11月底汉阳失守和12月初苏浙联军攻占南京以后,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南京。江浙一带是立宪派实力雄厚的地区,温和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渐渐取得了能够左右整个革命形势的地位。此种转变使辛亥革命难以真正进行彻底,使得保守势力大量地保存下来,以至于后来危害民国,这是毋庸讳言的,但同时也使革命派中一部分偏激的民族主义倾向得到矫正,减少了革命的破坏性,为保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1月初江浙一带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由于当时江浙立宪派和旧官僚在社会上地位声望很高,因而转向革命后大量进入了领导层。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顺应革命形势,在苏州宣布江苏省独立,一变而成为江苏都督。同日,浙江独立,汤寿潜被推举为都督。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为都督。12日江苏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代表姚桐豫、高尔登通电全国,请各省派代表来上海,会商组织临时政府。20日,各省到沪代表议决,承认武昌军政府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也就是说此时“十八星旗”是民国中央政府的旗帜。
12月2日苏浙联军攻占南京,12月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沪军都督陈其美,以及各省留沪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赵学臣、朱福诜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开各省代表会,列席会议的还有章炳麟、赵凤昌、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顾忠琛、彭锡范[14](P248),从与会名单可以看出,著名的立宪派人物和与立宪派接近的革命派人物占有明显优势,大会议决“取五族共和的意义,决定以五色为国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8](P66)。虽然这一决议由于当时大部分代表已去武汉而并不具有完全的效力,但“五色旗”的出现标志着在革命阵营已经开始把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问题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加以考虑。
而后“五色旗”被江浙一带的革命军采用,任鸿隽12月31日搭孙中山专车去南京时,在上海车站“看见车站中人行道两面排列了沪军士兵,军队的每一枝枪上均插上一张五色小国旗(五色国旗是当时江、浙一带所采用的旗帜),大有目迷五色之感。孙中山先生的青天白日旗,竟一面也没有看见”[8](P410)。当时,“青天白日旗”被两广革命军采用,“十八星旗”被两湖革命军所采用,是为辛亥革命中影响最大的三种旗帜。1911年12月12日,在武汉和上海的各省代表齐集南京,1912年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在南京正式议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但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毫无革命历史的“五色旗”并不满意,他个人在感情上当然倾向于“青天白日旗”,1907年还曾经为“青天白日旗”几乎和黄兴闹翻[15](P113),同时认为“十八星旗”的主张也很正大。孙中山1912年1月12复函代行参议院:“贵会咨来议决用五色旗为国旗等因。本总统对于此问题,以为未可遽付颁行。盖现时民国各省已用之旗,大别有三:武汉首义则用内外十八省之徽志,苏浙则用五色之徽志;今用其一,必废其二。……至于取义,则武汉多有极正大之主张,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今日适得武昌来电,则主张用首义之旗,亦有理由,非经将来大会讨论,总难决定也。”[2](P17)
然而“五色旗”1911年12月初产生于江浙一带并不是偶然的,当时南方革命阵营里,立宪派、旧官僚和温和革命派的主张已经占压倒优势。立宪派虽然和革命派一样都是政治上的革新派,但其与革命派分歧的一个根本点就是主张满汉早已融合以及民族革命将导致国家分裂以至灭亡,这在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中表达的十分清楚,在立宪派对清政府绝望以至于参加革命以后,它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主张并未改变,而且一时极能博得舆论界的同情;温和革命派如宋教仁等原本就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比较注意民族团结和领土问题,宋教仁还著有《间岛问题》,专门论述东北中朝边境的延吉主权问题,甚至为清政府在对外谈判中所借重。[14](P39)旧官僚更是反对一切激烈的思想,认为变动越少越好。
即使激进革命派如孙中山等,也认识到共和力量已占优势,清王朝的灭亡已经不成为主要问题,开始把民族团结和避免国家分裂问题放到重要位置,因而顺应形势发展接受了五族共和以及保持领土完整的主张,并在1912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特别加以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16](P1)
既然承认五族共和为立国之本,且认为维护民族团结和领土统一为当务之急,就很难否认以“五色旗”为国旗的主张,南京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决定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标志着五族共和的建国思想已经在南方革命阵营里取得决定性胜利。
四、边疆危机及南北议和对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重大作用
然而,南京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定“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南方革命阵营达成以五族共和为建国之本的共识,并不能保证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的理想真正实现。
北方以袁世凯集团为主要支撑的清王朝还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如果坚持抗拒革命,南方的革命武力很难在短期内统一中国,受清末革命派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满、蒙、回、藏等各族对于革命都心怀疑惧,甚至北方各省很多汉人对共和革命也很不理解,加之日本、俄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势力的阴谋,假如南北战事延绵,长年不决,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将难以避免。
当时国家和民族分裂的危险是十分紧迫的。日本和俄国本来是为侵略我国东北发生过大规模战争的死敌,然而一旦经1907年和1910年密约划分势力范围,双方竟然一变成为以瓜分中国领土为目的而密切合作的伙伴,武昌起义爆发不久的1911年10月2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就与俄国总理大臣商议瓜分中国满蒙,谈话纪要中有:“根据一九○七年及一九一○年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一九○七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17](P107)10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议:“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以求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为此,帝国政府必须经常策划,不遗余力;一旦遇到可乘之机,自应加以利用,采取果断手段,实现上述目的。”[17](P109)[17](P12)1912年1月1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致电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关于清国时局问题,俄国总理大臣态度相当激越,锋芒所示,颇有一遇时机既由日、俄两国协商,一举分割满洲、蒙古之势。”[17](P134)可见日、俄两国趁火打劫的决心是很大的,中国国内动荡时间越长,它们实现阴谋的机会越大。
鞑靼长期以来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因此“驱除鞑虏”的口号给蒙古族的心理冲击不亚于满族,蒙古王公对武廷芳的质问最足以反映这种疑惧心理:“共和国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之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之乎?如诸君子欲合全国共谋组织,则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几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即使诸君子所见不远,怀挟部落思想,谓我蒙古去之不足惜……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18](P903)1911年11月30日,外蒙古在俄国的策动下,以库仑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宣布独立,而后哲布尊丹巴在亲俄派杭达多尔济等的怂恿下登极称帝,中国官员被驱逐,汉族商民备受虐待。[19](P21、23、35)1912年1月3日,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汉宣布独立。在外蒙几次派兵侵袭和日、俄两国的策动下,内蒙古也渐渐呈现不稳定迹象,1912年1月中旬呼伦贝尔盟在俄国策动下宣布独立,哲里木盟郡王乌泰也积极准备叛乱。[8](P426)1912年1月底,变乱已经蔓延到北京附近,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的策动下,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接受日本贷款,谋划发动叛乱:“关于蒙古举兵事,刻已步步准备就绪。喀喇沁王已决心于数日脱出北京(三万发子弹已于昨日领取运出)。喀喇沁王与川岛之间所订密约以及借款合同抄本,今日寄上。此项借款,约定以卓索图盟五旗内(注:指喀喇沁三旗,土默特二旗,在今天赤峰市附近)所有矿山为抵押,贷与日金二十万元整。因该区将成为举兵之根据地,故贷与款额较他项借款为多。……此次所贷款项,大部分将使其用于举兵。”[17](P88)在川岛浪速与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订立的十条契约中,规定独立后任川岛为总顾问,一切文武事宜都与川岛商量决定,未经日本允准,不得与俄国往来,这实际上是日本阴谋建立“伪满洲国”的第一次尝试。[7](P409)
国家民族的分裂往往要引发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和种族仇杀,这对各族人民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分裂意味着要在两个民族聚居区之间的民族杂居区域中,人为划出一条原来并不存在的国境线,这时杂居区中的甲族必然想要驱逐乙族以使本地划归甲国,相应的乙族也想驱逐甲族以使本地划归乙国,民族仇杀就这样难以避免地爆发,几乎每一条新划出的边境线,都是由大量的鲜血凝成。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分治,举国狂欢,但是从这一天开始,沿着一条在36天里匆匆划定的边境线,两侧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向相反的方向面对面地奔逃,1400万人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即使在英印国军队的监视下,仍有大约50万人在沿途的相互劫杀中丧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无道理最悲惨的灾难之一,而且在双方有争议的克什米尔,战火绵延半个世纪至今未熄,且不用说由敌意而产生的军备竞赛给两个国家带来的沉重负担了;最近南斯拉夫的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引发了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大的冲突,已经导致数万人丧生,几乎使这一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
辛亥革命时期在内蒙古的变乱地区,大量汉人遭到驱逐和烧杀。[21](P298、313)当动乱波及西藏时,拉萨“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22](P146),不久冲突爆发,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22](P80),西藏各地汉人处境极惨,“参赞陆兴祺及师周自印度迭电中央及川、滇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而汉商民居藏者被屠杀几尽,藏番势力遂东渐及康”,“中国难民避藏番屠杀,流亡于哲孟雄(注:今锡金)、印度各境者,为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分起资遣回国,至四年冬始毕”。[22](P139、142)如果不是全国政局很快稳定下来,灾难无疑还会蔓延更深更广。
在这样的民族冲突中没有胜利者,冲突各方都要遭受难以愈合的重大创伤,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的严重负面作用。清代三百年,汉族人口出现巨大增长,相对的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宗教(约40%男性当喇嘛)、婚俗、性病等原因,人口依旧很稀少[19](P305)[21](P221),汉族人口大量移居少数民族区域的压力虽封禁亦不能阻止,特别是晚清改封禁政策为放垦政策后,移民过程大大加快,形成了大范围的民族杂居区,因此一旦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很可能以非常大的规模爆发,给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将是不堪设想的。
不仅仅是满、蒙等少数民族,即使是很多北方汉人,由于受共和国思想影响很少,对革命极不理解,一时也是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最具危险性的是当时握有奉天军权、能够左右东北三省去向的张作霖的态度。1912年1月26日,南北和谈已接近完成,张作霖主动访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称:“目前东三省兵马实权全在本人掌握之中,断不容许革命党之类南方人任意蹂躏,如北伐军之类,何足挂齿;即袁总理,如有确实迹象证实其已附和共和,本人绝不听从其指挥……日本国如能以德相召,则东三省民众,必将人心趋向,有所依旧。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予外人更为了当。”[17](P72)1月31日张作霖再次传言落合:“袁世凯终已逐渐附和共和,皇帝退位当不可免,东三省亦将失去足以拥戴之主宰。身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宁死亦不屑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为佳。”[17](P74)2月3日张作霖第三次传言落合,称:“日昨已以统领名义致电袁世凯,阐明如下立场: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吾人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17](P77)张作霖对日本人并没有太多的好感,但对比起来,当时似乎革命党更令他感到不安。
那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形势判断颇为准确:“皇帝将早日退位并由袁世凯建立临时政府。但是这个转变可能带来严重的困难;有迹象表明,蒙古人和北方各省都不愿意心平气和地接受这项解决办法。”[13](P344)2月12日清帝退位后,东三省继续悬挂龙旗,后来张作霖在袁世凯的重金笼络之下,才逐渐改变了态度,可见作为旧官僚的袁世凯不管其动机如何,确实为说服北方各省赞成共和起到了很大作用。
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对革命党的疑惧是由革命派长期的狭隘民族主义宣传和革命初期的暴烈行为造成的,虽然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阐明了五族共和的国策,1月28日还特别致电劝慰正在策划叛乱的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其中甚至有“汉、蒙本属同种”[2](P48)的亲切表示。但是,“驱除鞑虏”载在誓词,“八月十五杀鞑子”言犹在耳,一纸宣言、几封电报怎能化解多年形成的隔阂。满、蒙、回、藏各族的取向基本上由其上层人物所左右,南北议和成功使革命军北伐得以取消,以清王朝的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使各族上层人物多少感到获得了一定的安全保障,觉得旧日的地位利益仍可保持不变。而袁世凯对蒙古问题一直极为重视,软硬兼施,充分玩弄其笼络手腕,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的蒙藏事务局总裁,晋封亲王,对其他蒙族上层人物也大量加封,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14](P425),终于使内蒙王公们放弃了分裂的图谋,而且不少逃往外蒙的蒙族也陆续返回内蒙。
清帝退位意味着将清朝政府原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范围的连续性,所以英国和俄国虽然阴谋策动西藏和外蒙古的分裂,但仍然不得不声明承认中国在这两个地区的主权,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主权。清代中央政府与各大少数民族的政治关系向来由清帝在理藩院的协助下直接处理,为此清王朝特别在承德避暑山庄行宫附近修建了外八庙,以接待各族上层人物,而理藩院历来由满蒙王公大臣主持,汉族与各族的政治联系一向很少。直到退位,清帝一直以蒙、回、藏族的保护者自居,1912年2月3日清帝“授权袁世凯与民军商酌退位条件旨”中还特别提出:“蒙古、回、藏之待遇,均应预为筹划。”[16](P71)因此2月12日清帝以退位上谕中:“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表示,正式和平退位并承认中华民国[16](P72),对抑制各族分裂倾向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不可低估,因为各族上层人物一向只承认清帝是他们的统治者。
革命爆发之后,国内外各种促使国家分裂的力量都在急速地化合作用,南北统一迟一天达成,国家分裂和由此引发的民族仇杀的危险就增大一分。所幸经过全国维护国家统一的绝大多数政治派别的共同努力,南北议和终于取得成功,使国家转危为安,顺利实现统一,当时惟一激烈反对南北议和的只有头山满、犬养毅、内田良平、北一辉等与中国革命派关系密切、来华参与革命的日本人。[7](P127)以往的论著多强调南北议和的妥协性,强调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世事向难两全,惟其妥协,惟其不彻底,才能够容纳国内多数派别的意愿,使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得以大体维持,避免了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因此南北议和的重大历史意义是应该得到公正评价的。
收稿日期:2001-09-20
标签:五色旗论文; 孙中山论文; 黑龙会论文; 五族共和论文; 蒙古军队论文; 汉族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历史论文; 独立建国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民报论文; 立宪派论文; 北洋政府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