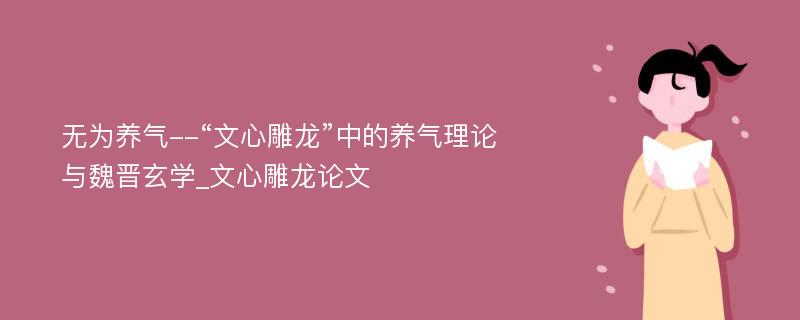
无为与养气——《文心雕龙》“养气”说与魏晋玄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玄学论文,魏晋论文,说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2)03-0083-05
一、《养气》篇“养气”的含义
《神思》篇为《文为雕龙》的第二十六篇,《养气》篇为《文心》的第四十二篇,中间隔了若干篇目;但是,《养气》篇与《神思》篇的关系却非同寻常的密切。对此,前人早有觉察。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养气谓爱精自保,与《风骨》篇所云诸气字不同。此篇之作,所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也。”[1](p.204)这就是说,《养气》篇的中心是讲如何在创作过程中长久保持作者自己的精力的问题,其内容实际上可看作《神思》篇所论述的创作思维状态与过程的一个方面,《养气》篇是对《神思》篇的补充说明,所以可以说《养气》篇是为了进一步充实《神思》篇而作的。黄先生的这种观点是符合《文心》实际的,详细考察刘勰所谓“养气”的含义及其与道家玄学无为自然观念的关系,不难明白这一点。
古代文论中的养气说往往同文气说相关,而文气说往往又直接间接地令人联想到孟子的知言养气论,唐代以后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家文论就是其典型例证。文气说中的“气”体现于文章中为文章气势,而在作者身上则表现为一种精神性的力量。《文心》的《风骨》篇提及“气”时就是这种意思。“风骨”中的“风”正是由气来规定的,所以,《风骨》篇有这样一些说法:“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2]并且,《风骨》篇还引述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气说,作为“重气”的证据,指出文章之“气”与文章之“力”直接相关。[2]甚而至于,不仅“风”而且“骨”,“风”“骨”二者的结合都以气的有无以及由之而来的力的有无为基本标志。我们提到过的野鸡(无风骨有文采)、鹰隼(有风骨无文采)、凤凰(风骨文采兼备)的比喻就证明了这一点。[2]可见,《文心》对风骨的主张实际上是对文章气力的一种强调。在这里,“重气”则是为了使文章有气势而要求作者培植聚积起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就我们所知,这种意义的“养气”说并不见于六朝文论中,大概因为当时文论家承曹丕而来,多主张“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3],以为这种精神性的“气”是先天禀受的,不可学不可致自然也不可“养”的。认为这种精神性的“气”可以“养”而且必须“养”,是唐以后孟子养浩然之气论在古文家文论中起作用时才正式出现并流行的。
因此,《文心》中的“养气”论如黄侃所说,是与文气说无关的一种文学观念。《养气》篇所讲的“气”也是一种力量,但它是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当时的人看来并非“不可力强而致”的,而是可以采用某种方式给予保护乃至培养的,刘勰“养气”之说就是提倡在作文时要注意保护和培养这种力量。让我们来看看他在这里是如何论述“气”和“养气”的。
《养气》篇开头处说:“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4]这表明《养气》篇是直接受王充启发而作的。王充《论衡·自纪》说:“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仕路隔绝,志穷无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发白齿落,日月逾迈,俦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历数冉冉,庚辛域际,虽惧终徂,愚犹沛沛。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则酒(刘盼遂以为“则”当作“节”),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既晚无还,垂书示后。”[5]这段话说明王充晚年曾经著有论“养性“的书,其内容为“养气自守,适食节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目的在于延长性命使之永不衰竭。可见,王充的书实际上是关于养生的,至于是否叫《养性》不得而知,因其早已遗佚。按王充,这本书共十六篇。刘勰记忆中的这本书好像只是一篇,名为《养气》,并且好像是因王充著述《论衡》有感而作;因此,他也仿照王充作一《养气》篇。从这种渊源关系已经可以看出,刘勰养气的思想同王充的书内容大体一致,来自道家,主要是从养生延命角度进行讨论的。
所以,《养气》篇中的“气”主要是指同个人性命休戚相关的一种要素。篇中涉及“气”的语句可以为证,一是“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二是“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三是“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四是“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五是“清和其心,调畅其气”;六是“斯亦卫气之方也”;七是“素气资养”。[4]仔细体会便不难发现,“气”就是一种维护和支持人体生命的主要物质力量,因而“气”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生命力,或我们通常所说的精力。生命力(或精力)是人生理方面的东西,因而,“气”在这里不是精神性的而是生理性的。与此相应,“养气”在这里是指培养和保护生命力,从而使人的生命得到培养和保护,“养气”实为“养生”的手段,通过“养气”达到“养生”的目的。所以,刘勰的“养气”论主要是从生理出发的,迥异于古文家的“养气”之从精神出发。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刘勰作文应该“率志委和”的说法。
二、《养气》根本途径:无为
在作文时如何才能通过“养气”达到“养生”的目的呢?《养气》篇对此有明确的说明。它一则说:“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4]它一则又说:“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而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凑理无滞。”[4]范文澜注说:“彦和论文以循自然为原则,本篇大意,即基于此。盖精神寓于形体之中,用思过剧,则心神昏迷。故必逍遥针劳,谈笑药倦,使形与神常有余闲,始能用之不竭,发之常新,所谓游刃有余者也。”[6](p.648)这一解释深得刘勰本意,它注意到《养气》篇的基本主张为创作文章时不要强作妄为而要因任自然,也即创作过程应该是一个无为之为的过程而非一个勉强造作的过程。第二,它注意到这种无为之为的主张,同《神思》篇虚静的主张一样,建筑在形神二分的基础上,主要还是对神思的一种要求。在上引一段注文之前,范注还引了两段论形神及其生命的关系的语句。其一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的话:“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6]其一为《抱朴子·至理》中的话:“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6]第三,它注意到《养气》篇由养气以养生的最终目的还是维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文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使创作永远处于游刃有余的良好状态。刘勰所谓“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凑理无滞”,不外乎这个意思。
因此,《养气》篇的根本宗旨是主张作者应该让创作过程自然无为地进行,不要进行过分的、强制性的人为干扰。篇中说,为学当积极有为、勤奋努力,就像苏秦那样锥股自厉。但为文是另一回事:“志(纪昀以为“志”当作“至”)于文也,则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4]“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这一关键语,就是从容不迫地随顺具体情况,舒缓沉着地适应当下时机的意思。它要表明的是作文过程不应是一个紧张收束的过程,而应是一个悠闲放任的过程。因循与放任是其基本特性,而造作和搅扰则是它极端排斥的,该篇赞中“无扰文虑,郁此精爽”即是此意。
在《文心》中,神思指创作过程的思维活动,而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养气的根本是在创作过程中实行自然无为原则。由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养气与神思的关系了:养气实际上是刘勰对神思提出的一种具体要求,即神思不应是呕心沥血之思而应是从容闲逸之思。《养气》篇之为《神思》篇的补充正集中表现在这里。当然,《神思》篇的某些言论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养气》篇的中心观念了。比如,《神思》篇叙及文思迟缓的几个例子时,虽未明言但对苦思竭虑的做法颇为不满:“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7]又如,《神思》篇已经明确主张:“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7]可见,《养气》篇无非是对《神思》篇的这种观点的发挥。
与此相应,像《神思》篇受到道家玄学影响一样,《养气》篇也受到道家玄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恰恰表现为它的基本观点是以自然无为要求创作过程以达到养气以至养生的目的。
三、魏晋玄学对《文心》“养气”说的影响
本来,注重人体生命,注重通过保护和培养人体中对于生命至关重要的因素而达到提高生命延长生命的目的,这种养生养气方面的学说观念,在中国文化中主要存在于道教教义中。在刘勰所在的齐梁时代,道教已经以上层社会可以接受的形态颇为流行,刘勰本人对道教的基本观点应该有所了解。现存刘勰为佛教辩护的文章《灭感论》中所提及的道家主要指道教而言,证明刘勰与道教有过很深的接触。《养气》篇很可能也确实受到了道教的影响。篇中所讲的“气”在含义上更接近道教所说的“气”,而篇中也出现了道教“精”、“气”、“神”说中的“精”、“神”概念。比如,“精气内销”,“神志外伤”,“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等等。范文澜注引及葛洪《抱朴子·至理》篇讲形神与生命的关系,也说明范文澜先生看到了这种影响。篇末“虽非胎息之迈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一语更加明显。“胎息之迈术”即胎息养生术,是道教主要养生术之一,《抱朴子·释滞》说:“故行气或可以治百病,……其大经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矣。”[8]在这里,刘勰宣称以自然无为的方式写作虽不如胎息术好,但也不失为一种“卫气”方法即养生方法。可见,道教对《养气》篇的影响理当是《文心》研究中的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这种影响的存在非常有助于解释刘勰“养气”观与韩愈、苏辙等人“养气”观的不同。
不过,我们在这里只限于研究《养气》篇所受到的道家玄学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非常复杂。一般说来。至少在玄学流行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和道教是两个基本上相对独立的发展系统,玄学作为新的道家形式与当时道教有根本区别。因此,道教对《养气》篇的影响应该不等于道家玄学对《养气》篇的影响。举一个例子。《养气》篇论作文当因任无为时提出了一种观点:作者应该永远在自己才分之内活动而不要企羡他人越出自己才分的范围。篇中称:“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缛,并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4]这就是赞美夏商周春秋时代,虽然文采一代比一代增多,但作者都是量才而行没有本无才或才不逮而勉强造作的。“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之说实际上就是作文当自足于己说,它显然与向郭《庄子注》足性逍遥论有关。这也可证之于篇中另一段话:“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或惭凫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处伤,同乎牛山之木。”[4]这段从反面说明为文当自足其性(才)的话,值得注意的是它两个地方明显出自《庄子》。一是“有似尾闾之波”之中的“尾闾之波”出自《庄子·秋水》篇;一是“惭凫企鹤”出自《庄于·拼拇》。这两个典故表明刘勰非常熟悉《庄子》,我们由此也不难推知他也很熟悉向郭对《庄子》的注释。这两个典故中“惭凫企鹤”最重要,因为它是直接用来说明刘勰足性为文之论的。《庄子》原文为:“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天所去忧也。”[9](pp.290~291)郭象注其中第一句为:“以短正长,乃谓长有余”,“以长正短,乃谓短不足”;注第二句为:“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损益之”:注第三句为:“知其性分非所断续而任之,则无所去忧而忧自去也。”[9]这却是道家玄学的影响而非道教的影响。
不过,从刘勰将向郭足性逍遥观念与养生问题联系起来这点看来,我们又必须承认道家与道教的区别并不那么绝对,它们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是有关联的。养生问题即是如此。它本来是道教的中心问题之一,但它实际上并不只是道教徒才感兴趣的问题,至少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也对它非常热衷。或许,养生问题本来就是道家与道教交叉区域内的问题。具体情况怎样不是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我们在这里只想知道玄学家们的养生观念与刘勰养生观念有什么关系。刘勰以自然无为要求创作以避免为文伤生害命、永保旺盛的创作精力,说明玄学的基本观念之一“自然无为”论对他是有影响的,现在的关键只在于能否找到更具体的线索加以具体的说明。
《养气》篇是对《神思》篇的补充,养气是针对神思而言的:养气主要是通过养神而达到的,养神的方式即自然无为(并非原始意义上的“自然无为”,而是经过玄学家重新解释的“自然无为”,即为与有为统一的无为)。这种重炼神养神而非重炼形养形的养生观,既以神形分别为基础,又以神形联系为基础。它隐含了神的状态必定影响形的状态从而神的状态与生命的状态密切相关的思想。以今天的语言说,它包含着精神的、心理的方面可以影响物质的、生理的方面的观念。只因为这样,自然无为这种对神的要求才会是一种养气养生的方法。
自然无为本为传统道家中心观念之一,玄学作为新道家继承了这种观念并作了一定程度的发挥。王弼《老子注》继承《老子》而主“无为”。比如,第二十三章说:“道以无形无为成济万物,故从事于道者以无为为君,不言为教,绵绵若存,而物得其真。与道同体,故曰‘同于道’。”[10](p.58)第五章注说:“自然已足,为则败也。”又说:“智慧自备,为则伪也。”[10]当然,王弼所说的“无为”并不是“不为”,而“无为而无不为”第四十八章注说:“有为则有所失,故无为乃无所不为也。”具体说来,王弼这种“无为乃无所不为”的自然无为说意指“因”、“顺”、“任”物之自为。这一点《老子注》中随处可见。比如,第二十七章注有:“顺自然而行”、“顺物之性”、“因物之数”、“因物自然”等语,并说:“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10]第二十九章注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物有往来而执之,故必失矣。”[10]把自然无为解释为因任事物的性理而不造作施为,也是向郭《庄子注》对自然无为的看法,只不过王弼与向郭各自所说的性理有所不同罢了。向郭所说的性理指每一物有限的自然禀赋,而他们所说的“无为”即安于自己的性分而不驰逐于性分之外,与之相反的“有为”则是不安分守己而求物于性分之外。《庄子·养生主》郭象注说:“天性所受,不可逃,亦不可加。”[9](p.428)《天道》篇注说:“无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为耳。然自得此为,率性而动,故谓之无为也。……然各用其性而天机玄发,则古今上下无为,谁有为也?”[9]同篇注又说:“夫工人无为于刻木,而有为于用斧;主上无为于亲事,而有为于用臣。各当其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当其能,则天理自然,非有为也。若乃主代臣事,则非主矣;臣秉主用,则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则上下咸得,而无为之理至矣。”[9]可见,郭象所谓“无为”即称其性分而为或足性而为而不是不为,因此,同王弼的“无为”一样,也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无为之为)。
刘勰《养生》篇主张的无为也不是不为而是无为而无不为,与王何向郭在基本点上一致,当是受到他们的影响。况且,刘勰以无为作为养生方法似乎也可以在郭象《庄子注》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庄子》本有《养生主》一篇谈及养生的正确方式,而这一正确方式恰好是无为。郭象有一段注说:“夫举重若轻而神气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胜者,虽复绝膂,犹未足以慊其愿。此知之无涯也。故知之为名,生于失当,而减于冥极。冥极者,任其所能,则忽然不知重之在身,虽应万机,泯然不觉事之在己。此养生之主也。”[9](p.103)“冥极”就是为于性分之内,即郭象自己所主张的无为。他认为这种意义的无为即是“养生之主”。结合前文所说刘勰《养气》篇本有“适分胸臆”等说法,郭象这种养生观影响及于刘勰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玄学家中谈养生最突出的是嵇康。嵇康曾作《养生论》,向秀作《难养生论》与他辩论,嵇康又作《答难养生论》,可见嵇康对养生问题的重视。嵇康论养生以形神分别及神对形的主宰作用为前提。他在《养生论》中说:“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11](p.145)嵇康这里所谓“形”直接指个人生命而非个人生命的一个组成要素,而所谓“神”则指个人的心理状态。所以他把神形关系比作君国关系,以说明心理状态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个人的生死存亡,认为一怒一哀都足以伤身侵性,调节好心理状态对养生至关重要。在同文中,他又说:“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萋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11](p.146)他在下文中更明确地把养生之方归结为“清虚静泰,少私寡欲”[11](p.156)八个字,而这八个字表达的具体内容是灭名利、除喜怒、去声色、绝滋味、息思虑,达到性气恬淡平和、意得自足。[11]嵇康的这一养生之法也可看作一种无为,但这种无为更接近少为或不为,与刘勰《养气》篇无为的含义有所不同。但嵇康由于是以无为论养生的玄学家代表,又按《世说新语》,嵇康《养生论》因清淡而颇为风行,[12]刘勰对其养生学说也应有所了解,因而刘勰的观点受到他的影响也大有可能。
最后,我们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肯定在来源上《文心》中的养气观受到过道家玄学的影响,这集中表现在为文应自然无为的主张上;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明白,刘勰是从作文的实际出发接受这种影响而不是因偏爱自然无为的玄学观点而把它推广到文论中来。文章创作中确实存在着力不胜任而强自操笔的呕心沥血现象,刘勰所举司马相如、扬雄、桓谭、王充等人的事就是例证。后世有李贺作诗呕出心肝、贾岛作诗一味苦吟的事,乃至出现“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之说,都是刘勰所谓作文伤命的例证。刘勰《养气》篇作文应自然无为的思想主要是针对这种情况而提出的,而且仅限于作文过程。至于作文前的训练积累,刘勰是非常重视的,他并不认为平日也应东游西荡、“自然无为”。所以,黄侃说:“彦养气之说,正为刻厉之士言,不为逸游者立论。”[1](p.205)我们理解道家玄学对刘勰观点的影响时,始终应该牢记这一点:刘勰总是从文学实际出发接受这种影响的。
收稿日期:2001-11-06
标签:文心雕龙论文; 玄学论文; 道家养生论文; 魏晋论文; 养生论论文; 道教建筑论文; 庄子论文; 国学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道家论文; 养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