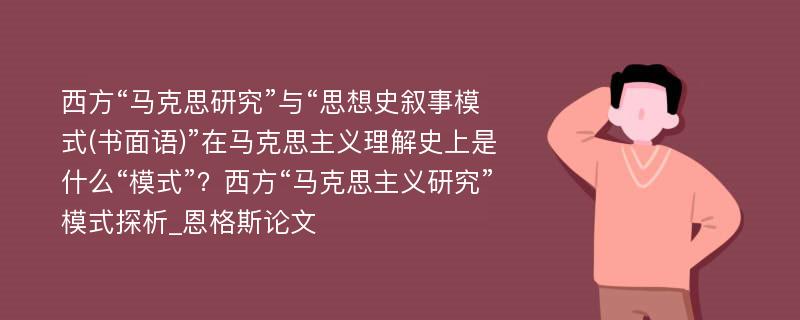
西方“马克思学”与思想史叙事的模式(笔谈)——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的“模式”?——兼析作为“模式”的西方“马克思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模式论文,笔谈论文,史上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批评话语中,“模式”一词无疑是一种晚近的发明。在1989年以前,我们通常会质问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国际国内学者的“立场”究竟是什么,言下之意,马克思主义真理只有一个,很遗憾,它恰好就在我们手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作为真实主体的个人逐渐形成,个人的主体意识也随之觉醒。学术界自然是主体意识最先觉醒的地方。具有主体意识的学者们首先因其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不同地位而经验到了存在方式的独特性与多样性,进而开始在自由而开放的国际学术市场上任意挑选自己所喜爱的、个性化的学术资源。于是,从原本是唯一的集体主体中分化出了众多个人主体,均质的“立场”由此解体。学者们开始自觉地探索、建构个性化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就像承认、尊重市场过程中其他个人的存在一样,开始承认、尊重其他学者的马克思主义观。“模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舞台。它的出现表明,国内学界已经自觉不自觉地默认了德里达的箴言,肯定马克思的继承人是复数的而不再是唯一的。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在国内学界,张一兵教授是第一个开始用“模式”去审视、评价不同学者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学者。①尽管从现在的眼光看,他的“五大解读模式”比较梗概,未能有效覆盖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但却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出发点。沿着张一兵教授开辟的道路,胡大平教授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模式及其一般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②并在此基础上对模式的一般问题进行了极富启发的论述。③依托他们的研究,我本人近年来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影响最大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的历史与逻辑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清理;二是对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的直接对立面的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初步梳理。在完成了这两个个案研究之后,我觉得,现在到了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的“模式”进行全面定义的时候了。
从诞生到现在,马克思主义已有160多年的历史。这160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恩格斯逝世是第一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断发展的阶段。从恩格斯逝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并在越来越广大的范围内得到实践,与此相对应的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基础开始破裂,由此出现了若干种不同的理解“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马克思主义既以极快的速度获得了空前广大的实践成功,又以极快的速度遭受了实践上的挫败,与此相对应,差异性的理解“模式”快速增殖,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观成了一种“不可能性”。在历史的当下,当我们超越惟我独尊的意识形态定式,重新审视那些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模式”的时候,就会看到,不管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理解是否准确、是否全面,它们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因为它们都不是凭借思想,而是凭借自己对资本主义的不同历史经验形成自己的差异性“模式”的。换言之,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决定了他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不同的历史经验必然会造就不同的理解“模式”,尽管人们要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在存在层面上具有客观的唯一性。
众所周知,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大都或直接或间接接受过恩格斯的教诲,考茨基和伯恩斯坦更是他的长期理论助手。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观终究还是无可挽回地发生分化了。这是为什么呢?归根到底是因为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发生了分化。作为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之一,伯恩斯坦为什么后来会和自己的“同学”考茨基分道扬镳、成为一个修正主义者,从而在事实上创造出了一个修正主义的新“模式”?除了过去我们经常提及的政治背叛等因素外,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作为一名政治领导人,伯恩斯坦工作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因而清楚地经验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方面的新变化、新发展。因为这些新变化、新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未曾看到、甚至未曾预料到的,所以伯恩斯坦无法直接运用原有的“正统”来解释,最终不得不机会主义地选择以修正“正统”、发明“模式”的方式来适应现实的变化。作为第二国际时期唯一产生了积极后果的新“模式”,列宁主义兴起的基础同样在于历史经验的变化:作为正在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俄国的一个革命家,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自然不同于考茨基这个德国人;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因为他与考茨基经验、观察资本主义的方式不同,因而看到或发现了一些与考茨基的理解不完全相同的东西,最终形成了新的“模式”。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模式”为什么会快速增殖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向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各种具有自身独特性的资本主义历史经验不断涌现,它们不可避免地影响并重新塑造了人们的理解“模式”。一般说来,一种历史经验越具有代表性,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模式”的理论活力就越高,理论影响力就越持久、越广泛。社会历史发展、变化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也就随之发展、变化,这时候,原有的“模式”与变化了的历史经验就会发生冲突,它的生命力就开始衰竭,“模式”的更新和再发明就成为了一种需要。
虽然“模式”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由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决定的,但在一种历史经验基础上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模式”,还和其他三个因素有关。
第一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期待。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是否能够实现?以及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人们的政治期待不同,可能形成的“模式”也就不同。在这个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模式”和西方“马克思学”“模式”的分野就很能说明问题。
第二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水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观点体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体系中的各个观点决不是均一等值的,其中只有少数具有普适性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同一性,要想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这些问题上坚持经典作家们的基本观点。还有一些观点是经典作家们基于自身独特的资本主义历史经验,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及其前景所作的基本判断。由于这些观点是以资本主义在特定民族国家、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独特发展形态有关,因此其有效性就可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而改变。最后剩下来大量观点都属于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对特定问题的个别判断,它们从本质上讲不具有也不应当具有普遍的可推广性。第二个层次是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范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只有真正掌握了这种分析范式,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三个层次是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整个学说体系的灵魂。我们只有真正领会这种精神实质,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幻象,在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形成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继续发展。毫无疑问,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水平究竟能够达到什么层次,这将对其“模式”的形成构成直接影响。例如,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阵营,“晚期马克思主义”“模式”之所以能够超越“后马克思主义”“模式”、“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模式”,赢得更多的支持者,就在于它基本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运用生产方式分析范式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给出了一种新的、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第三是理论资源。对于那些“模式”的创造者或更新者来说,他们总是在特定的理论背景中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进而创造或更新了某种“模式”的。尽管这些独特的理论资源并不会从根本上决定“模式”的塑造,但它们无疑会对“模式”特征的明确化起到某种强化作用。所谓“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就是如此。
“模式”一旦形成,就具有了自身的同一性,从而能将自身与其他“模式”有效地区分开来。而要想真正了解一种“模式”,我们就必须深入到它的内部,对它进行解剖学式的精确研究。在此,我愿意以西方“马克思学”为例进行示范分析。
首先,“模式”之为“模式”,即在于它内在地包含一种具有独特性的“理解的前结构”,这种“理解的前结构”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本提出一个“总问题”,并预先规定其回答的方式及其边界。正如20世纪解释学已经阐明的那样,绝对的客观性是一种绝对的神话。这一判词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解史。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的任何一种“模式”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再建构方式。它们通过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本提出“总问题”,在历史文本中再建构出了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模式”不同,它的“理解的前结构”就会不同,而其提出的“总问题”也随之不同。作为一种流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学院化“模式”,尽管西方“马克思学”受到20世纪马克思主义内部诸多思潮的深刻影响,尽管它始终标榜自己的价值中立性,但它的“理解的前结构”却充分暴露了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因为它的“总问题”已经先在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当代性:作为一种曾在19世纪西欧某些工人团体流行过的激进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究竟为20世纪留下了什么值得缅怀的思想遗产呢?
其次,“模式”的“理解的前结构”所提出的“总问题”通常可以分解为若干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存在的假设。例如,西方“马克思学”的上述“总问题”就可以分解为三个前提假设。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性假设,即西方“马克思学”假设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恩格斯逝世之后、甚至是马克思逝世之后就已经终结了,后来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不断发展的学说体系其实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之名(特别是对马克思之名)的一种“盗用”。第二是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性假设,即西方“马克思学”假设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与批判,而只是19世纪基于伦理道德批判资本主义的诸激进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种。第三是同一性假设,即西方“马克思学”假设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实质是一种价值观念,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不过就是这种或许在当代依旧有其功效的价值观念的线性进化过程。
再次,为了更有效地捍卫自己的“理解的前结构”、更便捷地回答“总问题”所提之问题,“模式”会寻找、运用一些独特的方法。作为一种学术潮流,西方“马克思学”内部分化严重,所运用的方法也是花样繁多,让人一时间难以归类。但仔细想来,其诸多方法大都可以归属到语境分析法和差异分析法的范畴之一。这实际上是西方“马克思学”充分吸收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一种积极结果。
最后,“模式”会运用自己的独特方法得出一套自治的观点体系。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发展到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后世马克思主义者与他们的思想关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精细发展,西方“马克思学”形成了一整套观点体系。其全部观点可以用两个词组来描述:人道主义的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
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为了“反资防修”,国内理论界即开始零星译介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观点。改革开放以后,这种译介曾达到一定的规模。与此同时,在苏联东欧理论界的影响下,我们始终把西方“马克思学”作为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严厉批判。但令人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学”并没有因此被批倒。按照我的观察,近年来,虽然几乎没有什么人公开引证西方“马克思学”的观点,但它的一些基本观点却在国内相当数量的中青年学者中得到传播,甚至是极端化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主要是对待作为“模式”的西方“马克思学”的方式出了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对西方“马克思学”“模式”的批判要么集中于它的结论,如“两个马克思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要么纠缠于它使用的具体方法。这无疑是在舍本逐末!因为对于这一“模式”而言,真正需要批判和首先需要批判的并不是它的方法和结论,而是它据以为出发点和前提的“理解的前结构”和“总问题”及其假设。如果我们不首先批判、扬弃西方“马克思学”的出发点和前提的虚假性,那么,它完全可能因其方法的先进性、观点的新奇性而俘获我们,使我们在不自觉中接受它的出发点和前提,从而走到我们自觉意识的对立面。反过来,要是我们已经彻底扬弃它的出发点和前提,那么,它的先进的方法完全可以为我所用,而其大量充满攻击性观点在经过改造后,完全可以像灭活疫苗一样纳入我们的观点体系,促进后者的完善。我以为我们在西方“马克思学”“模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具有一定的警示性,它从一个负的方面提示我们应当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模式”,尤其是那些在观点和方法层面具有较强新异性的“模式”。
注释:
①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3页。
②胡大平:《重新阐释马克思的三个理论模式》,《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胡大平:《马克思文本的解释和学派立场》,《学术月刊》2002年第6期;胡大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创新与方法自觉》,《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③胡大平:《穿越西方“马克思学”神话,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处》,《福建论坛》2006年第4期;胡大平:《从问题到模式: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理论自觉》,《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胡大平:《从问题意识到模式化的理论生产》,《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