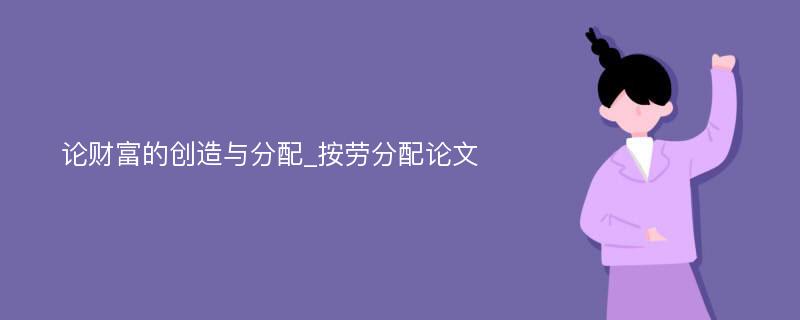
论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配论文,财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财富分配的根据之一:财富的创造
财富分配之道是财富哲学要研究的重要问题。财富哲学研究财富分配之道的目的是,通过对财富的性质、源泉及财富增长的规律性的探索,阐明财富分配的正确原则和正确途径。
如果按使用价值定义财富,世界上的财富可分为两种:“天然存在的”财富和“借人力”而创造出来的财富。(参见马克思,第1卷,第56页)天然的财富是自然界直接恩赐的财富;创造的财富是经过劳动而生成的财富,也可以说是社会财富。社会财富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对人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是指“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同上,第57页)或者说,种种商品体都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不过,由于有些天然物不以劳动为中介就对人有用,所以财富实际有三种状况:(1)“不借人力”对人就有使用价值的天然的财富,如裸露地表的煤;(2)“借人力”才有使用价值的创造的财富,如铁矿石经冶炼后制成铁,成为对人有使用价值的物;(3)两种财富的混合体,即天然对人就有使用价值的物以劳动为中介,变为对人更有使用价值的物,如处女地经开垦后使用价值大大提高,成为两种财富的混合体。
取财有道的“道”,首先就是按劳分配之道。改革开放伊始,经济学界拨乱反正,最初是从为按劳分配正名开始的。按劳分配是对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否定,是对劳动光荣的制度保障。就是在今天,我国也不存在按劳分配过分的问题,而是贯彻得不够。邓小平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对于如今出现的贫富悬殊现象,我们首先必须从按劳分配原则有没有得到正确理解和执行上去找原因。理解和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时,有以下三点特别需要正确把握:(1)按劳分配的应该是创造的财富;(2)按劳分配的个人所得之权重必须合理;(3)必须按“有用”劳动来进行财富分配。
首先,财富分配的根据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的创造。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初次分配旨在解决效率问题,讨论天然的财富如何分配是无意义的。因为这部分财富既然本来就有,所以它们必定与激励无关。如果将它们纳入分配,也就与提高效率无关。况且,天然的财富既然本来就有,这就使得任何对其拥有分配权的“私”的声称都为社会所不接受。经过劳动而创造出来的财富则不然,其多少是由创造主体的努力所决定的,因而初次分配若以它们为根据,实行多劳多得,必然会对提高效率和扩大再生产产生激励。换句话说,分配天然的财富不会产生激励,因而不会带来更多的财富;以创造的财富为根据分配财富则会产生激励,因而会带来更多的财富。由此可见,理解按劳分配原则时,光强调劳动创造财富还不够,还要认识到财富分配的根据应该是创造的财富,天然的财富不在其内。就市场经济而言,财富哲学对初次分配应该探讨的是:创造的财富如何分配。因为只有创造的财富才是劳动的产物。只有将按劳分配准确地理解为分配创造的财富,财富才获得了不竭的源泉。
应该指出,无论是按财富的创造分配财富,还是按财富的创造之增加分配财富,都要解决财富衡量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马克思,第1卷,第48-49页)例如煤处在未开采状态时,其使用价值是很低的,它的“有用性”完全取决于裸露及与人的不期而遇,且这种“有用性”的获得与分配无关,只有捷足先登这一种合理方式。但煤成为商品到了用户手中,其使用价值就大大提高,与此同时它也就成了两种财富的混合体。而煤被提高的使用价值,就是人的活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所以无论衡量天然的财富还是创造的财富,都可以用使用价值这一尺度。但是若要衡量财富的创造,则要进一步指向市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不管一种产品是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它总是财富的物质形式,是要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使用价值。”(同上,第2卷,第153页)“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一种特殊的需要,构成物质财富的一种特殊的要素。而商品的价值则衡量该商品对物质财富的一切要素的吸引力的大小,因而也衡量该商品占有者的社会财富。”(同上,第1卷,第156页)具体来讲,市场具有将天然的财富和创造的财富区分开来、将此劳动和彼劳动区分开来的功能,财富的增量就这样被抽取了出来。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衡量财富的两种尺度:衡量财富靠使用价值;衡量使用价值靠市场。第三种尺度则是:衡量市场还要靠时间,详见下文第三节。财富衡量必定是一个客观过程,绝非任何一个智者和贤人所能为。
其次,按劳分配的个人所得,应该是此劳动创造的财富,而不是彼劳动创造的财富,而且此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也并非全都拿来分配,其中的个人所得有一个权重问题。在财富分配的治理结构中,权重的合理配置非常重要。关键是要保证个人所得的增加一定以社会财富的更大增加为前提。鉴此,与低收入者个人拿大头不同,为富者个人应拿小头。现在不乏富豪慷慨解囊回馈社会,这当然值得提倡。但财富分配的义利结合不能光靠义举,更要靠制度保障。在财富分配的治理结构中,只要权重配置合理,就可以放心大胆地鼓励人们去发家致富。公平不是“均贫富”,缩小收入差距不能由动摇按劳分配原则的途径来解决。对于财富的初次分配,按劳取酬是永远都要恪守的最基本原则。搞好再分配当然是政府的职责,但这要以社会财富的充裕为后盾。如果个人所得的增加一定带来社会财富的更大增加,个人发家致富就会和共同富裕一致起来,两极分化也就会成为不可能;相反,如果在个体层面上只思分配不思创造,社会财富的充裕又从何而来?对于眼下收入差距加剧之势,我们一定要分清究竟是关于财富分配原则的理解出了问题,还是按劳分配原则的执行出了问题,或是再分配环节出了问题。
第三,劳动的形式不管如何复杂多样,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同上,第88页)但是我们不能依据这种耗费来分配财富,原因在于有“劳而无功”的情况存在。只有有效劳动才会真正创造财富。所以,按劳分配应该更准确地理解为按劳动的价值进行分配或按劳动的贡献进行分配。
马克思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同上,第195页)我们过去往往只从体力劳动去狭隘地理解劳动,所以工人农民是劳动者,知识分子不在其列,企业主由于涉及雇佣就更不在其列。现在,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财富分配的根据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的创造,那么劳动的内涵自然要丰富,外延自然也要扩大:体力创造财富是劳动,脑力创造财富也是劳动。脑力劳动创造财富的基本实现方式有两种:一是知识生产;二是合法经营。因此,现在我们应该明确,劳动是由人的创造财富的活动来定义的:一切旨在创造财富并且取得创造财富之效果的人类活动都是劳动。
二、财富分配的根据之二:财富的创造之增加
经营、技术等生产要素若作为复杂劳动加以考量,其收益是可以纳入按劳分配的范畴的。但资本就不一样了,劳动的内涵再丰富、外延再扩大,资本也不能并入劳动。正因如此,马克思称资本为“特殊的以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页)。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提出两个重要问题: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财富分配的根据何在?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也就回答了另两个问题:财富创造的源泉是否唯有劳动;取财之道是否唯有按照劳动。
论及资本当然离不开货币。在市场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资本首先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但货币并非就是资本。货币与资本的关系是:当货币有了主人、有了赚钱的目的和行动时,就成为资本。资本的本质在于增殖,这是资本从货币中提升出来的关键。既然资本旨在“下金蛋”,那么它对财富创造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马克思关于G变成G+ΔG的货币运动的阐述,揭示了资本增殖的奥秘,同时也说明,资本对财富创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不能使之可称为财富创造的另一源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简单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但与之恰恰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却是“为卖而买”(更确切地说是为贵卖而买),“在为卖而买的过程中,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都是交换价值……货币在运动终结时又成为运动的开端。……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马克思,第1卷,第177-178页)
通过G变成G+ΔG的没有止境的货币运动,资本增殖的奥秘被揭示出来了。对此加以深刻领会,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点重要认识:
第一,资本不等同于货币。因为尽管资本总是以货币为表现形态,但货币归属不清时不是资本;货币贮藏起来时不是资本,货币没有目的时也不是资本;货币只有在有了主人、有了赚钱的目的和行动时才成为资本。
第二,资本并不直接创造财富。因为“为买而卖”披露了劳动的目的是使用价值,“为贵卖而买”披露了资本的目的是ΔG。劳动的目的是使用价值,于是劳动意味着生产,劳动意味着财富的创造。而ΔG是什么东西?ΔG是交换价值,是利润,更直白地讲是货币的增加,即钱生钱。钱生钱的逻辑固然能说明资本与财富创造关系密切,但也说明资本并非与生产直接勾连,其所获增殖也并非实打实的财富,而是货币形态的财富。资本增殖是通过先△G再与财富增加发生联系的,因此△G是否真的就是财富的增加,是一个与资本增殖过程相伴随的问题。
第三,资本是财富创造的倍增器。G变成G+ΔG的没有止境的货币运动,意味着资本增殖是指数增长型的。虽然资本不直接创造财富,但是ΔG如果不是虚的而是实的,那么钱生钱的逻辑就能使财富的创造得到增加,并在总体上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的特征。原因在于资本以货币为表现形态,因此它获得了远非劳动可比的流动性和配置资源的能力。而生产一经资本这个要素有效发挥作用,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总体上变算术级数增长为几何级数增长。
综上所述,关于资本和财富创造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资本对财富创造能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越是后工业社会,资本对财富创造的作用越不能小觑。资本可以分配财富,其根据并不在于它如同劳动那样也是财富创造的源泉,而在于它是财富创造的倍增器:生产一经资本这个要素有效发挥作用,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换句话说,资本可以分配财富,其根据并不是财富的创造,而是财富的创造之增加。但是资本是按钱生钱的逻辑增殖的,所以ΔG(货币的增加)并非就意味着财富的实质性增加。这一不确定性正是财富哲学考量财富分配时需要深思的大问题。这意味着,资本参与财富分配,只有当它对财富的创造真正有提高作用时才是正当的、合理的。
三、对资本的风险控制:金锁制和金融监管
如前所述,资本从货币出发追求货币,所获ΔG并非实打实的财富,而是货币形态的财富。“即使假定借贷资本存在的形式,只是现实货币即金或银的形式,只是以自己的物质充当价值尺度的商品的形式,那么,这个货币资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也必然只是虚拟的。也就是说,完全像价值符号一样,只是价值的权利证书。”(马克思,第3卷,第575页)所以,资本的扩张往往更反映在虚拟经济之中,并有其“独特的运动”。(同上,第527页)资本的本性是逐利。但由于ΔG并非就意味着财富的实质性增加,所以资本在虚拟经济之中对利润的追逐,有做实和做空两种情况。只有做实,钱生的钱才是真金白银;如果做空,钱生的钱就是随时有可能蒸发的泡沫。这就披露了资本有损害财富创造的可能性——风险,进而披露了资本增殖的两重性。G+ΔG必须用虚拟经济的语境来表达:虚拟当然不是虚无,但是这种倍增既然存在于虚拟经济之中,不言而喻就意味着风险,而且是那种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的风险。所以,把财富创造的增加作为资本分配财富的根据,必须在有关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的条件下才能成立。
指数增长,从正面看固然意味着资本可以以撬动经济方式而大大增加财富的创造,但我们绝不能漠视或者轻视ΔG与财富的实质性增加之间的不确定性。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在指数增长之下就意味着牵一发而动全身。换句话说,指数增长的不确定性也意味着只要资本扩张过度,就一定会发生蝴蝶效应。例如,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虚拟价值不断膨胀所产生的货币幻象,吸引越来越多实体经济的资本流向虚拟经济,最终“头重脚轻”的资本格局一经形成,只要有一定数量的金融资产要求将其虚拟价值兑现成真金白银,资金链便顷刻间断裂,金融危机由此爆发。蝴蝶效应对资本扩张悖论的生动表达披露了这样一种现实的可能:只要不确定性失去控制,资本就会对财富创造起完全相反的作用,即一个微扰(如次贷危机)就可能导致系统丧失整体稳定性甚至崩溃。由此可见,并非资本而是资本的做空,才是此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应该指出,金融危机的阴霾并非真的不请自到又永远挥之不去。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建立一种风险控制机制,既能有效地遏制投机和贪婪,又不影响资本撬动经济的能力。既然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并非资本而是资本的做空,那么问题就很清楚:第一,资本收益以增殖为根据这一条仍应保持不变,价值增得多就给得多,价值增得少就给得少,价值不增就不给;第二,必须使良币淘汰劣币,使投机和贪婪失去滋生空间,这样ΔG也就能等同于财富的实质性增加。我们永远不要试图去改变资本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就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资本做实还是做空,或者说钱生的钱是否是实打实的财富,这才是风险控制的关键所在。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今天人们痛定思痛,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认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在于:ΔG并不等同于财富的实质性增加。在指数增长之下,只要这一不确定性失控,独立的金融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金融危机就将不可避免。资本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必然贪婪,所以要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无疑是必要之举。不过,监管必须是游刃有余的监管,既不能缺位,又不能越位。如果缺位,ΔG与财富的实质性增加之间的不确定性就会放大,投机和贪婪就会泛滥;如果越位,系统的活力就会大受影响。但是在金融风险的治理结构中,系统内生的自主控制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它才能收到治本的效果。监管做得再好也是他律,自主控制产生的却是自律。自主控制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是任何他律手段所无法企及的。而要使系统内生地产生一种有效的控制机制,能自动遏制投机和贪婪,首先还得着眼于市场。因为创造的财富是有还是无,是增还是减,唯有市场可以给出价值判断。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市场法则,而在于放任主义(即否定有形手起作用)。由于有形手起作用有可能越位,系统活力有可能丧失,所以新自由主义垂而不死并非全无理由。换句话说,挫败新自由主义不能仅仅仰仗强化监管,还要仰仗有形手起作用却不违背市场经济逻辑。
但是对于ΔG中可能存在的泡沫,光靠市场是挤不掉的,还要进一步仰仗时间。时间要素将短期波动平滑掉,虚拟财富中的泡沫就被挤出。时间越长,虚拟经济中的虚拟财富就越接近于实打实的财富。因此,就资本而言,如果财富创造的增加是其参与财富分配之根据的话,“推迟变现”在操作层面上就成了首选的基本原则。这样一来,既然不是靠人而是靠“市场+时间”来区分做实还是做空,“推迟变现”对金融风险的控制来说,当然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让无形手起作用的逻辑了。“推迟变现”可以使系统对风险内生地产生控制,所以比外部监管更有效、更持久。
自从2007年夏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在危机中苦苦煎熬,与此同时华尔街上的天价薪酬成了众矢之的,对金融高管限薪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但如果我们承认财富创造的增加也是财富分配之根据的话,那么无论从自控还是从他控来看,“限薪”在操作层面上都是不着边际的提法。因为贪婪不贪婪并非由薪酬高低来决定。钱生的钱只要是实打实的财富,并且个人所得在财富分配结构中有合理权重,那么个人所得越多,财富创造的增加也只会越多,社会财富也只会越丰裕。实际上,控制风险的真正有效的主张是金锁制,它的机理正是“市场+时间”:(1)个人所得以资本增殖为根据,水涨船高,水落船低; (2)报酬的变现有锁期,同时还有归零和不归零的选择。应该指出,同样是“推迟变现”,归零和不归零的区别是很大的。因为只有归零(即有起值点),才能使钱生的钱当有变无时,个人所得也化为无。所以,“锁期+归零”对贪婪的遏止不仅是自动的,也是最有力的。
金融和资本市场说到底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应处于从属地位,因为劳动实乃一切社会财富之所以能被创造出来的源泉。但实体经济创造财富要靠日积月累,挣不到“快钱”,所以股市等才变得如此“火热”,乃至出现资本强势、劳动式微之格局。破解如此分配性冲突,当然少不了政府这只有形手的作为和干预,但让经济规律有效发挥作用才是真正的出路。对于金融和资本市场,时间要素衡量财富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指短期行为。在时间展开的过程中,金融监管与金锁制相得益彰:金融监管的功能在于预防,没有监管就没有预防;金锁制则旨在长期激励,其实质是用时间约束来减少甚至消除市场衡量财富的不确定性,因而它对化解资本扩张悖论可谓是治本之术。两相比较之下,最重要的还是具有自我控制机制的金锁制:因为金锁制顾名思义,是让一只无形手在金融和资本市场中起作用,所以它对风险控制能够达到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的效果,同时可以很好地保持系统的效率、竞争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