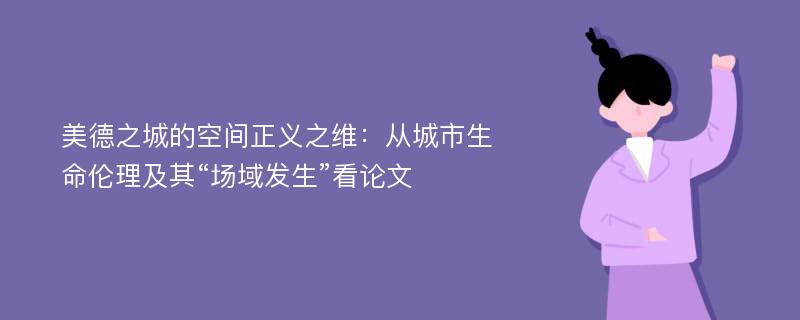
美德之城的空间正义之维:从城市生命伦理及其“场域发生”看
田海平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 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加速,“活得好”与“做得好”的实践理智不能回避“城市生命伦理问题”。城市如何以“美好生活”为目的,并使生命个体和整体在其安顿、协调、需要之满足、意义之实现等方面“做得好”?现代大城市的复杂性及其对生命的关照,体现在“理解-不理解”、“需要-不需要”的悖论性时空重组中遭遇生命伦理难题,并由此建构合理化的规范体系和价值秩序。城市,究竟是谁之生命?何种伦理?这是“城市使生活美好”一语内含生命伦理之场域发生的问题式。我们要通过对技术、文化、生态、审美、教育、政治、经济、历史、道德、休闲的生命价值形态的理解和诠释回应这一基本问题,思考大城市与美好生活之间的生命依系、伦理关联以及生命伦理的人性政治内涵,从美德之城的空间正义维度,厘定大城市的中心与边缘、生与死、文与质的紧张关系。
关键词: 城市生命伦理;美德之城;空间正义;人性政治
人类聚群而居发展到今天,以超大规模的城市和城市群的出现为之写下了文明史的现代 “序曲”。然而,关于城市生活的实践理性谋划,不能回避“城市与美好生活”论题中诸生命伦理问题。城市生活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而且必须关涉人类生命或人类生活的美好?城市规划和设计是否必须事先问一问:什么样的城市规划设计才是“好”的城市规划设计?这样的提问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我们澄清城市文明发展的思路,端正我们看问题的视角。它内含一种哲学性质的且与城市生活密切关联的生命伦理反思,推动我们在行动之前对行动本身的意义进行充分论证和全面反思。我们需要这种批判性思考的介入。唯有如此,才能真实地回应“城市使生活更美好”的城市生命伦理课题。
着眼于此,笔者想从“城市与生命伦理”的关联视阈探问:“美好的城市生活”如何应对我们生命中那些挥之不去的“不美好”?这个问题乍听起来似乎太过宽泛,不太容易说清楚。然而,抛开理论上的纠缠,我们会看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城市生活必须建立在一种合理化规范体系和一种价值秩序(或良善品质)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我们的城市既需要有足够好的品质和美德,又需要有足够合理的空间正义,才能正确应对和处理“美好的城市生活”必须面对的人类生命中诸种“不美好”。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与美好生活,既是一种生命政治学论题或生命伦理的场域关联,又总是呼唤人类美德的回归和人性政治的创建。
一、城市生命伦理:在面对“不美好”中寻求“美好”
超大规模的城市和城市群的崛起,是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正在呈现的事实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然而,作为文明史上的一种典型的现代性景观,究其实质,却内蕴一种伦理性悖论:它既充满欲望、冲突(甚至罪恶),又体现理性、仁爱的诉求;一方面似乎是“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现实版”,另一方面又似乎体现着“伊甸园”的复临或再现;它是爱与恨、生与死、开放性与隐蔽性、平等与不平等的奇特混合场域。然而,城市的个性却是由此得到了刻画, 无论人们称之为 “魔都”、“废都”、“古都”,人们都是以一种个性化的命名赋予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在面对“不美好”中以“美好生活”的憧憬。事实上,人们不论生活在何处,城市生活总会带来一种“美好生活”的乌托邦向往。然而,不可否认,在其现实性上,城市又是一个充满了欲望、压力、冲突和痛苦的地方,每一天都上演着人世间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城市的天际线或地平线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它以永不停息的运动刺激人们的“肾上腺”,尽管很多人认为它是令人厌恶的肮脏之地,但却不能否认,城市又绝对是值得居栖、回忆和庆祝的地方。我们称这种矛盾特性,是浸蕴于城市生活中的一种伦理性悖论。这是因为,它以“居栖之地”(ethos)的本原活动而铸成了人类生活的文明形态,既归属一种生命共同体的秩序规定,又不离每一个个人自由意志的自我规定。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黑格尔所说的“伦理性的实体和个人”[1](P165)的紧张关系。
问:小孩遇到考试就会打瞌睡,注意力不集中,今年6月就要高考。现在已服用补氧胶丸几天,上课犯困情况减轻,这个产品的确不错,需要增加其他的补品吗?
这样的讨论,必然会使人们面对大城市的某种气质性欠缺或不足。从一种对美好纯净的理念世界的预设或者在这种“预设世界”的坍塌中,大城市不得不面对残败、流浪或乡愁的挑战。如同梭罗和波德莱尔所表明的那样:城市并不美好,大城市尤其不美好,相较于乡村或瓦尔登湖畔的乡野生活而言,我们在大城市里找不到美好。然而,这种气质性欠缺或不足,并不能阻挡大城市的崛起,更不能阻止人们在大城市中追求 “美好的城市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抛开浪漫主义乡愁及其相关视角的城市批评叙事不论,我们面对一种日益紧张的城市生活的伦理性悖论:一方面伦理性约束构成了个人自由的前提;另一方面“美好生活”需要面对我们生命中诸种“不美好”。这种伦理性悖论虽然本质上根源于人性或人的生命本性,却不容否认,它属于“人生活于城市之中”的一种现象学实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指认,这种伦理性的悖论构成了城市生命伦理的基本问题:即,如何在面对诸种“不美好”中寻求“美好”。这是生活于大城市中的单个的生命个体和整个的生命共体必然要遭遇的一种普遍性的生命伦理问题。为此,我们需要着眼于一种“美德之城”的理念构建,采取积极的行动。
城市是人之居栖的“集置”。这种集置以空间性的“筑居”及其规模化的巨大系统,规定了一种空间正义的永久性模型:这就是,在一种“文质彬彬”的伦理的联结中,反对一切“空间性的促逼”。这是城市伦理生命的“自由”之真谛,是城市生活或城市生命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君子之德风”的古老箴言中,窥见到了“美德之城”的君子气象。
(5)政治价值。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其中,政治的力量越是强大,自由和权利的伦理诉求也就越迫切。就此而言,一种建立在效率与公平之辩证法基础上的政治价值的觉悟,是“美德之城”的意识形态根据。实际上,当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是政治的动物”的时候,主要是针对生活于城邦中的人而言的。历史上,城市空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私人性的房屋为中心展开的空间,不仅包括居住空间,还包括一些类似性的功能房屋如工厂、商店等等;二是通过公共空间提供公共性的功能,如神殿、市政厅、城门等。城市的政治价值通常是以城市的公共精神建构和公共空间布展为中心展开。
广西教育厅、财政厅日前制定了《广西高等学校助困资助经费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管理工作,规范助困资助经费的提取、使用、管理和监督工作,提高助困资金使用效益。
第一,基于“中心与边缘”的辩证法,城市空间总是在“亲疏远近”的伦理的联结中不断地得以重构,城市由此具备了某种由生命总体化的空间正义所驱动的变革的力量。
在城市文明史上,城市空间的“中心化”汇聚,使得居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中心城市(一线城市)或居于某个城市的中心区域(一线区域)成为资本竞逐的目标。例如,在100多年前,纽约的城市规划就面临 “中心区域”空间紧缺及急速增殖的困扰。“1912年,摩天大楼的出现导致这样一个问题产生:城中有1 510栋大楼是介于9层和17层之间,还有91栋是介于18层和55层之间。它们之间彼此妨碍,玩起了彼此自我毁灭的零和博弈游戏,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的摩天大楼的过度发展,最终使得彼此无法获得充足的光线和新鲜的空气。”[2]然而,“从中心到边缘”的城市空间的流动、形态变化和功能疏解,以及城市空间在活力四射的创新性构架中沿着产业、技术、贸易、金融、教育、交通、文化、政治、历史、自然等功能的再次集聚,使原本居于城市边缘的空间在“再中心”的形态重构中有可能成为新崛起的富有活力的城市空间。而原来的城市中心或中心城区可能会萧条下去。这表明,人之亲疏远近的伦理的联结,以另一副面孔呈现在城市形态的空间感知中。资本以多重样式出现在从“资源地理空间”到“文化社会空间”、再到“网络数字空间”的空间化重组以及形态学分布中。城市设计总是“从边缘切入”,进而颠覆以往的“中心结构”。那些曾经被疏远的空间由此进入城市的亲近场域,以使创新的火焰在那里被激发并熊熊燃烧。将“边缘”与“中心”进行连结的“伦理”,从边缘切入、变革和重组城市空间的构型,不断地改变着城市的地理或文化空间构架及其形态学分布。它构成了城市空间正义的结构性原理,使城市保持生机与活力,充满创造力和生命力。例如,人们熟知的广东深圳的快速发展和上海浦东的崛起,就是由边缘切入以展现城市空间架构的形态总体性及其空间正义的一种“美德之城”之构建的典范例子。
由此,我们进入城市空间的“人-人口-人群”的生命伦理论域。城市提供了人之“聚群而居”的经济而神圣的形式。不可否认,城市空间原型来自原初的居住群落,如同建筑原型来自原初的棚屋一样。无论城市与建筑如何发展,它的底色脱不了作为原型的居住群落和原初棚屋。即是说,一旦人类筑居于大地上,其栖居活动无论如何进步,它都应该扎根于大地上,而非悬于天空中。然而,当人们按照几何化造型或者功能化架构去营造城市空间时,一种深沉的担忧就会如影随形:城市空间如何“以人为本”?如何避免让过强的“空间性促逼”偏离了人之筑造于大地上的伦理本原?我们看到,这种“空间性促逼”,既以建筑技术的样式向天空做“直线”伸展,又以社会技术的样式向大地做“直线”切割。更有甚者,当这两种“直线运动”共同作用于城市空间的“人口形态”或“人群构成”时,城市就会在它发起的“拆除贫民窟”“驱逐低端人口”“改造老旧城区”的空间改造运动中丧失自己的本原。有鉴于此,面对日益增长起来的对大城市之不适宜居栖的担忧,一种“空间正义”理念是需要建基于“文与质”的辩证法基础之上的,以使得城市空间得以在一种“文质彬彬”的伦理的联结中回归人类居栖于大地上的筑居之本原。
(4)教育价值。城市是人生活的地方,我们要从创造的激情开始,将知识社会、教育城邦和智慧城市结合起来。世界各地的重要城市,无一例外地都是一些拥有著名的研究机构、大学和出色的基础教育的城市。其实,对于城市价值的理解,居于首要地位的,是对城市的公民教育的理解。城市的优秀和卓越,在于人的美好,它的根本在于美德教育。因此,一个城市如何通过发展它的教育功能来提升其美善的美德,是城市凸显其教育价值功能的最为直观的表现。所谓“君子之风”实乃有赖于城市对此教育价值的理解和领会。这从基础设施的物质形态(比如体育场所、休闲娱乐、影视购物、大学小学、艺术长廊、博物馆、纪念馆等等)的功能预设可窥见一斑。比如,向全民开放的博物馆、大学讲座和体育设施,等等,就充分体现了城市的教育价值功能。
人类对时间的恐惧,与我们终有一死的命运密切相关。一切生者,总是在死亡的临在的有限性中,而成为“向死而在”的存在者。恰如中国古代名辨家惠施所言:“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庄子亦有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死”与“生”互为前提,相互转化,无论在至大无外的宇宙尺度,还是在至小无内的心灵尺度,“死生”的辩证法是我们周遭世界和生命本身的辩证法。它是说,理解“生”或“生命”的根本是在其对立面的“死”或“死亡”那里;另一方面,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诘问,又将“死”之真谛归还到了“生”或“生命”。这是一个诠释学意义上的“解释循环”。人在“死生”之间或“生死”之内,即入此历史性的循环之内。城市亦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赋予了城市空间在“生与死”的伦理联结中成为诗与史的展现。城市通过它的建筑、街道、公园、社区和繁衍生息的人民,来实现连通“生与死”的精神上的秩序。这是一种筑居于无穷无尽的空间构架中的时间性的思与诗。牛津的天际线,剑桥剑河畔的桨影,苏州园林,北京故宫博物馆,悉尼歌剧院,墨尔本闻名于世的有轨电车体系,等等,这些体现着诗与史之永恒生命咏唱的城市空间,是人的精神能量和思想力量的历史性的凝聚和沉淀,是人之抵抗时间、死亡、有限性和孤独的命运交响曲。从城市的最初发源到现代大城市,这一命运的本质和意义从来未曾改变过。人在大地上筑居,既是人类此在性的基本的需要,又是人类面对死亡、时间和孤独而在制作(或创造)的神圣性中展示出来的“空间聚焦之形态”——此乃城市生活和城市生命形态的诞生及一再地复现。生与死,有限与无限,世俗与神圣,物之成毁与人之生死,在这里以伦理的方式相连通。“死”的“不美好”,构成了“生”之美好的前提或必要构件,而城市的俗世荣光在这里意味着人类精神战胜时间之恐惧的神圣力量之汇聚。我们的青春、爱、欢乐,包括日复一日的劳作,以及我们与生俱来的脆弱和等待,等等,……在一种精神性的自我展现及成长中融入城市生活的历史。它难道不是一种具有生命崇高感和敬畏生命之美学的 “具身化”形式的体现吗?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生活在一种人类史的意义上帮助我们对抗这种对时间性的恐惧,激发人类对永生的渴望和对死亡的超越。城市在人类的建造和筑居活动中与人在大地上的那种本原性的“连结”活动相关联、相贯通。于是,“生与死”,构成了城市生活的最为原始的一种存在论的规定。它甚至把两者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并置在了一起,使得“生与死”的意义在一种艺术化的空间构造中进入生命本身的美学和生命自身的伦理——教堂与墓地,人群聚集的广场与英雄纪念碑,安葬死者的公墓与周边的民居——城市以其独特的方式,进入“生与死”的辩证法,延续着人类对抗时间性恐惧的精神力量,从中生发出人类对不死和永恒的建造和筑居之承诺。这使人追忆《诗经·邶风》中的千古咏叹: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诗经·邶风·击鼓》)
我们今天在城市生活中仍然存在着类似的“感同身受”:“我身在何方?身处何地?我的马儿丢失在了哪里?到哪儿能觅得到它的踪影?”在此寻寻觅觅中,诗人相信:“终归有一片山间林泉之地,是它的归处和栖处”。于是,面对这种个体的偶在命运与终将会“丢失”的恐惧,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彼此的联合或连结来克服之:“我们啊,生生死死,离离合合……我与你立下誓言:从此握着你的手,与你一同老去。”(“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永恒就在这个承诺中,就在当下的生命相与之道中——就在这一超越“死生契阔”的个体之间的连结之中。一切依系关系其实都可以还原为这一本真性的伦理的连接。即是说,贯通死生的连结,既不在于架设通往天国的桥梁,也不在于寻找到永生不死之药以超越时间性羁押之所,而是在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生命相与的时间性伴随,在于当下的朝朝暮暮。这恰恰是最为本真地对抗时间性恐惧的一种精神的力量。
我们需要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文质彬彬”,在“空间正义”之义理上是指城市空间的“营构”要辩证地处理好“文”与“质”的对立统一关系,要把这两个方面协调起来、统一起来,进而使得自然与人文、城市与乡野、历史文化之展现与现代技术之建造达成一种和谐交融。据 《论语·雍也第六》记载,“文质彬彬”是孔子的教导,意指做人(尤其是做“谦谦君子”)要做到表里如一、文质均衡。“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第六》)这段话中的“彬彬”二字是一个叠字模态词,用来描绘人的表象之“文”与人的内里之“质”的谐和平衡、融合中道之相。即是说,我们“做人”,既不能“文胜质”(史),也不能“质胜文”(野),而是要做到“文和质”均衡交融。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言行恰到好处,既文雅又真实,合乎中道,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儒家“君子”。显然,如果说一个人“文质彬彬”呈现出“君子”气象,那么推而广之,一个城市也如此“文质彬彬”,就会使城市空间呈现出一种“君子之风”。
第三,基于“文与质”的辩证法,城市空间在“文质彬彬”的伦理的联结中,诠释着人类“反对空间性促逼”的文化的力量。
第二,基于“生与死”的辩证法,城市空间在“死生契阔”的伦理的联结中,延续着人类“对抗时间性恐惧”的精神的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空间正义的价值诉求在于:让每一种或每一个空间性的绽出,具备一种时间性的“停留”位置。在这种既属于一种审美性质的意义之“瞬间”生成中又属于一种伦理性质的本原之“居栖”经验中,城市的建筑、街道、桥梁、寺庙、教堂、公园等才可能被理解为凝固了的“音乐乐章”。 于是,“美”“善”得以贯通,“美”“好”的联结成为可能。唯有如此,一种越过砖瓦、木质、石头、尘埃、水泥、铁锈、雨水、油彩等物质表象而呈现出精神彩色的空间才是可能的。它的根本,就在于让城市空间进入一种人类生存的时空关联境域,从而回归人和人性之筑居根本——因为,城市空间,说到底,就是人之建造以及由此建造而实现的人类精神之秩序,是人和人性面对“死生契阔”而构建彼此之间无限时间和空间的“思”“史”“诗”。
(1)利用定义3确定各决策成员{e1,e2,e3,e4}所给决策信息的冲突水平依次为0.083,0.167,0.083,0.056。其中,需对e2的冲突水平进行调整。令交互次数g=1,已知决策成员e2所给的各项决策信息中冲突水平最大的决策信息为“s4,1”,确定的冲突水平调整参考值则决策成员e2需提升的值,给出新的的值为“{s4,s5},(0.5,0.5)”。此时各决策成员的冲突水平依次为0.083、0.083、0.056,0.056,均具有合理的冲突水平。
当我们面对城市空间的时间性表出时,我们需要问:什么是城市的“君子之风”?这显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放眼看去,那些成为历史陈迹的废墟、残墙、剥蚀的表象、粗砾的地表、长满霉斑的空间、褪色的景观,等等,似乎总是会引发人们对之进行某种改造或重建的冲动。这些“质”的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对之推倒重建,是否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所为?历史上战争、大屠杀、温疫、地震、大萧条等等灾害或灾难,对城市及其人口造成的毁灭性的印迹总是与一种致死的“残破”景观关联在一起。这使得这种重建具有了伦理正当性。然而,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不但一切历史性、时间性的消逝会引发这种修饰性或改造性的“文”之冲动,一切自然性、原始性的物质形态也会以其“粗砾”的特性引发人们产生类似的冲动;于是,在城市文明中,“设计”的偏好和将空间技艺化或技术化的呈现形式,展现出一种过度的设计技术或建造技术的“文化”,进而导致了一种背离“空间正义”理念的 “空间性促逼”在现代城市空间营构中的蔓延。它在技术的订造下,体现为“对几何形状的热爱”,出现了前面所说的通过“直线”的伸展和切割肢解城市生命及其个性的“文化”。当这种偏向发展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就会背离城市文化的本质,使得城市空间受制于技术展现的逻辑,乃至偏离了生命之纯真、历史之质感与自然之鲜活。在这个意义上,维也纳画家汉得瓦萨(Hundertwasser)指认说,现代城市建筑把使用直角和直线变成了一种设计学的教条,这是一种“道德上不能容忍”的事情[3](P233)。 因为,“让街道保持一条直线”,或者“使某一社区的所有建筑物在外观上统一起来”,以至于“让建筑插入空间、挖空地面、在远离地面的高处规划和翱翔”等空间技术,都是以计划、算计、控制和组织的理性样式来经营或筹划城市空间。如此一来,过于人工化、设计化和功能化的空间形态也就渐渐丧失了其扎根于大地上的自然质态的温度。人类文化和文明在现代技术的统治模式下发展出一种冰冷的城市空间架构。一种从“文”的本源处发展壮大的技术理性,有可能以这种方式走向“文化”的反面,蜕变成为一种新的“野蛮”。
液硫脱气效果达标后,联合装置硫磺回收单元涉及液硫脱气的设备如硫磺冷却器(E-309)、液硫输送管线等腐蚀现象大大减缓,腐蚀泄漏事件的发生率明显降低,联合装置连续运行周期增长,为装置的平稳运行提供了有效保障[8]。
因此,一种深层的反思紧随其后,它迫使我们聚焦于一种“文质彬彬”的城市空间之建构。它属于一种伦理性的联结,而非简单的功能化的展现。谈到“伦理性”的东西,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伦理性”一词有一段经典的诠释,他写道:“伦理性的东西就是理念的这些规定的体系,这一点构成了伦理性的东西的合理性。因此,伦理性的东西就是自由,或自在自为地存在的意志,并且表现为客观的东西,必然性的圆圈。这个必然性的圆圈就是调整个人生活的那些伦理力量。”[1](P165)相对于恬静乡村、莽莽群山、繁密森林、潺潺溪流、如镜湖泊等自然景观而言,城市这种人口或人群聚居之所,所具有的调整个人生活的伦理力量并不主要地在其自然之特性,虽然自然方面的特性也是非常重要,但其主导方面则是在于它所彰显的自由之特性——或者准确地说,在于一种内蕴自然特性的自由本质。如果我们把城市比做是一个“生命体”,那么城市生命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实乃取决于它以何种方式应对我们生命中诸质态的“文化”。
2.使用试灯替代这类用电设备进行诊断时,试灯的电阻要和用电设备一致,电阻差异过大,得到的诊断结果反而造成误判或误导。该故障就是最初是电磁阀开路故障,维修人员使用试灯替代电磁阀测试时,由于试灯的电阻远小于电磁阀,ECM认为电路存在短路故障,不再输出,让维修人员认为模块或电路出现了故障。如果直接替换新电磁阀就可以判断出故障。但是使用电阻不合适的试灯,反而引发误判。
二、城市空间正义与美德的回归
毫无疑问,城市空间关涉人之“筑居”活动的三类空间展现形态。它们分别与“亲疏远近”、“死生契阔”、“文质彬彬”的伦理联结紧密相关。从其美德谱系而论,它们将一种空间正义理念及原则与美好生活的美德之城之诉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从美好生活的情感的、本体的和文化的三大根源处,不难看到一种“空间正义”的理念及原则在协调城市的变革图新力量、精神超越力量和文化协调力量时,所应遵循的一些基本尺度和具体原则系统。围绕着这个论题,我们当然可以且有必要进行一种规范性探索,以揭示城市空间正义的建构原则及其应用。当然,在距离原则(基于边缘与中心的辩证法)、生存原则(基于生与死的辩证法)和文化原则(基于文与质的辩证法)的论证和展开方面,阐述城市空间正义的具体内涵及其应用,不是我们这里要做的事情。我们的重点是,要描绘城市空间正义之形态的基本趋势,以应对一种日益增长的强大的紧迫感和焦虑。
这种紧迫感和焦虑,是在城市空间的现代性构建中呼唤美德的回归和人性政治的创建。它深刻地揭示,我们的大城市文明,在大裂变大阵痛中,遭遇且必将遭遇迫在眉睫的现代性“问题丛”,以及日益紧迫的变革图新的任务。理查德·塞纳特在《公共人的衰落:论资本主义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关于城市给出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他写道:“城市就是一个陌生人(stranger)或可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4]。他所说的城市主要指现代大城市。即是说,我们的大城市,在文明底色上,是由陌生人的相遇和相与构成的;它把大规模人口或人群的聚群而居这样一件现代性的“事情”,向着一种极端化的方向推进。于是,城市不同于乡村的独特性也就得到了刻画:不同于乡村中基于亲友、近邻、熟人、远人之间的邂逅和相与,现代城市是“陌生人以适合于陌生人的方式的相遇”[5]。这种空间场域的改变,越来越使得城市以一种功能化的区隔而取代本原性的筑居。这一趋势甚至在辉煌的顶点尚未来临之际,现代城市在“远与近”、“生与死”、“文与质”的纠缠中已然遭遇到了严峻的生死危机。想像一下,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动辄2 000多万人口的城市规模,通勤高峰时段如潮汐般降临的汹涌车流或人群,它的街道如何可能像墨尔本那样保留完备的有轨电车网络——宜居性,从何说起?我们必须穿越太多的无奈、不适、混乱和精神焦虑。100多年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城市文明以它巨无霸式的能量集结,集合书写了大致类似的一个又一个“大城市利维坦”的故事。其中发生的大事,既是“人”的大规模聚合,又是“人”的空前退却,和“人之死”的一再重现或重演。这个世界需要一种大城市伦理,用以指引我们走出城市文明的“铁器时代”——前提是,我们必须真实地面对大城市遭遇的伦理悖论。
今天的大城市在空间形态上的无边无际的扩展,通过日益精准、便捷、高速的交通网络,日益智能化、人性化、加速化的物流、人流和信息流,重述了人类建造“通天塔”的故事。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预知,任何一种“通天塔”式的城市建造,其宿命,其本质,换一个视角看,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巴别塔”,或者说,是某种形式的“通天塔”的“烂尾”!维也纳建筑家、画家汉得瓦萨在20世纪50年代预见到了现代性大城市之不适于居住的命运。他以一种后现代敏感性主张通过建造废墟以凸显城市建筑的筑居本原。他认为,废墟比那些功能建筑更适合人居住[3](P235)。这其中其实隐含着大城市的另外一种伦理悖论,与前面所说的“美好悖论”(在面对“不美好”中寻求美好)相对应,我们称之为“理解悖论”。“理解悖论”,说的是某种“预定的理解”变成了“不可理解”,从而使得大城市的“通天塔”式的建造变成了“巴别塔”式的散落。它有两层含义:第一,人们在大城市寻求理解,并以理解为基础建立起彼此之间的联结,但是,这一过程却隐蔽着某种深层的不被理解;第二,大城市使一种对“不理解”的理解成为可能。我们知道,大城市把更多的人和人群在空间上联结起来了。城市就是联结的体系。而联结的本质即伦理,它以理解为前提,在促进人的联结中实现理解。然而,个人的世界性存在及其单子化散落,在现代文明体系中,却总是被淹没在大城市的大叙事中,悄无声息。今天,人的孤独和被抛,总渴望在大城市的收纳与包容中被理解。可谁是那个灯火阑珊处知冷知热又知心的存在?大城市的无根,使人们多少觉察到,没有什么比在人群中的孤独更孤独,没有什么比大城市中的“理解”更难理解。另一方面,以大叙事展现的大城市故事,使“人”居栖于相互依存的联结中,这种相互依存,预设了理解的独特类型,即一种对“不理解”的理解。大城市的异质性,使真正的理解似乎离我们远去——人们相互交淡、沟通,通过社交网络、微信平台,或街巷邻里,通过技术的共享和贸易的联系(或者壁垒),通过政治动员和资本操控(或者融合),等等,所有这些形式的联结,其实并不意味着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我想表达的是:一种理解的两难,似乎渗透进了大城市的血脉之中。对于人类的建造活动而言,如果没有爱和理解,大城市的生命也就枯萎了,或者终结了。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大城市的命运是否本质地关联着“理解”?笔者对此的回答是,尽管大城市存在无法消除的隔膜、歧异,我们仍然要借助于理解,特别是通过九种价值的理解,展现大城市与“人”的联结,回应“什么是美德之城”及“如何构建空间正义”,进而寻求“美德的回归与人性政治的创建”。
(1)文化价值。我们必须理解城市的文化价值,特别是从城市批评史的意义上,对跨越过去、现在、未来的城市文化进行提炼,达到一种文化价值形态上的理解性觉悟。事实上,“理解悖论”与人类筑居于大地上的本原活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前面提到了“通天塔/巴别塔”的建造,它即是产生于一种目空一切的“自以为是”,而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却是反击这种“自以为是”的最为有力的武器。在城市文化的构筑中,只有在人们面对彼此之间的“不理解”时,“理解”活动才能真实地、历史地发生。文化理解是“美德之城”在各种异质性的文化扇面(宗教、科学、艺术、历史、文学等等)和异质性的文化传统中坚持城市的文化性和文化价值的唯一方式。它是对城市的灵魂和个性的一种坚持。如果没有文化价值的理解、承传和创生,城市故事及其德性之构筑,就失去了精神的彩色和至为深沉的人文精神之内涵。
(2)生态价值。从城市自然史的意义上,一个城市的个性、禀赋、历史、地理、环境、人口等等诸多要素,综合构成了城市的生态价值,我们需要在城市的自然历史形态上提升一种对城市价值的生态理解和生态觉悟。山、水、城、林、动物、植物,以及历史遗存、民间传说,包括来来往往的人群和居栖于城中的世代居民,这一切多样性的联结构成了一种伦理性的普遍和自由,它是城市之进入生态理解和生态价值之自觉的契机。对于一城之人民而言,每一物都是城市生态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只在林地树间奔跑的松鼠,一只红腹锦鸡,或者一条游弋于河中的小鱼,等等,都是城市共同体中的成员。从这个意义上看,城市本身即具有博物学的价值。而从一种人文史的意义上看,一切属于人的创造对于城市生态而言都是不可剥蚀的珍宝。如果没有生态价值的理解、教育和建构,城市的自然与人文就会丧失那种内在的契合和历史的肯定。美德之城的空间正义之理念,是以生态价值的理解为最基本之善,以使城市的自然之美善与人文之美好相得益彰、相互协调。
对《导基》书本的所有章节进行解读,梳理章节内容衔接性和关联性;依据知识内容的关联性,总结归纳,化分散为统一;依据考试大纲,勾选重点考试内容。
(3)审美价值。城市的建筑、街道、人群、山川、河流、动物、植物,等等,都具有一种美学上的价值。一切美的形态都与人之栖居和人的劳动本质紧密相联。人是城市中最美的风景,而劳动者又是一切美的事物最能体现美之为美的本质存在。城市的审美价值既是“美德之城”展现的一种大美,又是“美德之城”构建的一种大德。我们需要在城市空间的筑造中创造性贯注美的理解、美的鉴赏和美的生活意蕴。城市生活既需要一双双发现美的眼睛和创造美的双手,又需要汇聚无限多样的美的呈现形式和表现方式,而只有让每个人都参与到城市之美善的行动之中,城市之审美与悦乐才会成为一种流行。
1) 经过模拟得到拉形辅助的渐进成形最大应力主要分布在板料和支撑模相贴模的位置,回弹后贴模位置应力下降,最大应力集中在渐进成形区域和贴模区域之间。
在这个意义上,主要基于“中心与边缘”、“生与死”、“文与质”三个方面的“伦理”之连结,城市生活和城市生命得以构筑一种基础性的合宜性的空间正义,以寻求一种通向“美好生活”的城市形态之展开。
(6)经济价值。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不可否认,它的活力之源,在于经济价值。一个城市的经济价值往往取决于它的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政治经济环境,如海港、工业中心、金融中心等等。更多的时候,经济价值又总是与文化的、教育的、审美的、政治的等等多重价值,构成一种重叠效应。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的经济价值体现为它的高效的通勤以及整合内外部资源的能力。什么是经济价值?在城市空间的构筑上,它是清晰表达人筑居其间的、或者以一种人口形态呈现的增值效应,欲望、热情、创造性、生命力、活跃程度,以及源自人性的创造性冲动等等,都是城市空间对经济价值的理解形式。
(7)历史价值。尽管历史并不是一定保存在城市中,但城市却因为其历史价值而获得了超越时间的永恒。城市以共同记忆的形式而成为活着的历史。我们对城市的历史价值的理解是指:当我们走过街道和城市时,我们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过去岁月留下的沧桑或见证。如同走在华沙老城区的巷道中,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世界历史的巨大灾难中,同时又能够借助于一个民族的坚韧不屈而使整个生活完成转变。城市的历史价值,并非只是对过去遗迹的知识性的摄取,相反,它联结着作为未来的过去,进而使我们现在的城市空间变得具有深厚的底蕴,并因此具有某种存在论之深度。
(8)道德价值。道德关乎城市的厚道,它的秩序和规范,它对规则的遵守,以及它以何种方式界定“好生活”和正当行为。城市的道德价值,将责任与爱、规范与正直,向子孙后代传承。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空间应该是一种“厚道”的空间,它在一种不偏倚中面向各个阶层的人民,且以最底层人群的美好做为标尺,展现其公共空间中的人性光彩。
(9)休闲价值。人们是否愿意在城市中度过休闲时光,这关乎城市的休闲价值。休闲是忙碌的对应词,如同一阴一阳的变奏和晨昏的变化。城市的忙碌需要透过它的休闲空间得以体现并得到真正的理解。在空间正义的理念上,休闲是让城市生命体进入整装待发的休整状态,类似于会场中的茶歇。它是音乐中的停顿或休止符,是绘画中的留白,是一切创造性活动必须具备的等待。理解休闲,是城市空间构筑的基本价值要求。
综上所述,一种“美德之城”总是在城市构筑者对上述城市价值的理解中,着力发展其中的一种或多种价值形态和美德品质。于是,“不可理解”的城市特性,就会进入人们理解的视野。我们应该追溯这些价值的源泉,并重新赋予它们新的诠释、新的理解并焕发其生命力。
三、美德之城的核心:一种人性政治的空间创建
“美德之城”的核心,是“人”和“人性”的回归,是人性政治的空间创建。
不容否认,一切有关城市的美好憧憬或乌托邦式的想像,总会遭遇冰冷的现实。在钢筋水泥构成的大城市里,我们去寻求城市文化的 “君子之风”,究其实质而言,就是要把地理学的“城市天际”汇合进一种“人口学”的“城市地平”,把物理形态的城市空间重叠于道德形态之上。在这个意义上,一种“自我技术的伦理”与“他者关注的伦理”使空间正义的理念聚焦于人性政治的空间创建。这里隐含着大城市的第三个伦理悖论,我们称之为“需要的悖论”。
从作业工序问题上,填埋场覆盖采取外包的形式。通过人工的方式铺设,就目前的作业量与作业面积,这是1项劳动力较多的工作,每天作业前揭膜时间和作业后的覆膜时间需要2 h以上。1 a的运营中,日覆盖材料的选择从原先的防水雨布改为0.5 mm HDPE膜,解决了膜的颜色及材料参差不齐的情况,但也使铺膜的效率减少了很多,外加负压抽吸等管道的铺设,需研究1种新的覆盖材料及作业方式,将现场设施一体化设计,配以快速接头,快速拼接与撤离,提高效率。
简略言之,“需要的悖论”是说,在一个需要的体系中,事情往往引发了一种悖谬,即以“不需要”的形式呈现为一种需要。它也有两层含义:第一,从人聚群而居的筑居本性和筑居本原中,开发出了大城市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却产生了自己的他者,即对“不需要”的“需要”(它使我们想起了核武器这种不需要的“神器”);第二,我们在相互需要的城市体系中,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至深的陌生或冷漠,而正是这种“相互需要”的系统促成一种它不需要的东西(即隔阂或冷漠)。这两个方面都在一种深层的相互解构中彼此抵触、相互拆解。需要与不需要的这种纠缠,也就衍生出了一种伦理性的悖论:对“不需要”的需要。
我们知道,伦理的本义是ethos,这个古希腊词的涵义就是“聚居地”,它基于“人居栖于大地上”的需要,是人聚群而居的本质体现或展现。大城市把人聚群而居这一回事,或者说,这样一种需要,发挥到了极致。它充分地利用了它,甚至极度地开发了它。城市就是需要的体系。而伦理,就是一种“涌现”,它以“需要”为前提,是人们彼此之间相互需要的“涌现”。我们甚至不知道,这种涌现究竟来自何方?去向哪里?我们只知道,以“安得广厦千万间”的人之安居或人之居住为直接目标的大城市,在开发出一种美善力量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之栖居的异化。大城市的 “天际线”,以其壮丽轮廓见证了这种需要的极端膨胀,以至于生产出它的反面:对不需要的“需要”。大城市展现出它的复杂性。大城市表征的就是这种“需要”的神话。这并不是说,大城市与美好生活从此无关,而是说,“美好”总是在一种悖论性质的需要中生发。这是“美好生活”的辩证法,它在空间正义的构筑上,以“作为厚道的正义”为指引。
人们相互需要,然而,在一种冰冷的现代性设置中,又彼此阻隔。大城市似乎使这种“不需要”成为必不可少的需要。“不需要”的需要,成为一种诠释空间正义的压仓石。
当前企业战略管理中的研究点,大都是追随着企业的赢收利益而展开研讨的,怎样在短期内为企业带来有效的利益,逐渐成为相关行业中研究者的探究点。继而为了实现在短期内为企业赢得最大化的利益,相关研究人士大都从快速提高市场竞争力、以创新带动企业发展,以及以流量明星推动企业进步三个方面,来提高企业的市场利益,这是当前许多有关企业战略管理相关从业研究人士的研究点。
此处只限于提出这一观点。总而言之,从一种人性政治之创建的角度看,如果有美德,人人都有足够的自律,人人都遵守规范,我们不需要警察,不需要人权,不需要制度,不需要法律,甚至不需要国家,等等。就如同人们声称,我们不需要核武器,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按照有关国际协议行动。可是,一种人性政治一直坚持:这种“不需要”的“需要”是必不可少的,原因在于,美德和美德之城有其致命的脆弱性。
5) 作为叹词well的基本意义见表2。但在翻译时,这远远不够,需要把well由原来的感叹词扩展为话语标记语来考虑。译文上下文的衔接还需要明示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做到既要语义明确,又要符合汉语句法结构特征,这样,位于认知路线枢纽位置的well有时需要译成连词(如“不过”),甚至是单部句(汉语中非主谓的单句)(如“算了,得了,话又说回来”等)。为了在原文和译文中实现人际功能、语篇功能的更好对应,完全可以跨级在单部句这一层面上去寻求对应语,这样,往往反而会使译笔生花,成为亮点。通过对《漫》剧译文进行描写和分析后发现,台词中well作为话语标记语的主要对应语如表3所示。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英)彼得霍尔.文明中的城市(第二册)[M].王志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783.
[3](美)卡斯腾·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M].申嘉,陈朝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4]Richard Sen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On the Psychology of Capi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1978.39.
[5](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67.
Spatial Justice in the City of Virtu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Bioethics and its “Field Occurrence”
TIAN Hai-ping
(College of Philosoph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
Abstract: Due to the acceleration of modernity and the practical reason of“living well” and “doing well”,we cannot shy away from the “urban bioethics issue ”.How can a city take “good life” as its goal and “do a good job” in the settlement,coordination,satisfaction of needs and realizing meaning of individuals and the city as a whole?The complexity of modern big cities and their care for life are reflected in the bioethical challenges in the paradox of“understand—not understand” and “need—not need”.Whose life should the city care about and what kind of ethics should it abide by?This is a question-type expression of bioethics reflected in the slogan “city makes life better”.We need to respond to the question through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fe value of technology,culture,ecology,aesthetics,education,politics,economics,history,morality,and leisure life,think about the life dependency,ethical relation and the human and political connotation of bioethics between the big city and good life,defin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center and periphery,life and death,form and content of the big city.
Key words: urban bioethics;the city of virtue;spatial justice;politics of humanity
中图分类号: B 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0X(2019)01-0005-09
收稿日期: 2018-11-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研究”(13&ZD066)
作者简介: 田海平,国际价值哲学学会(ISVI)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道德哲学的理论与方法、道德领域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来小乔】
标签:城市生命伦理论文; 美德之城论文; 空间正义论文; 人性政治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