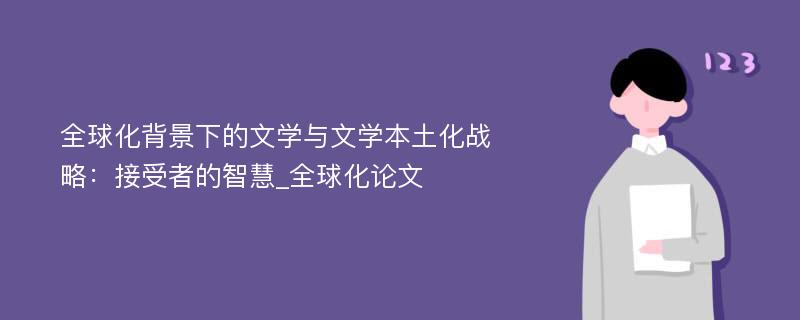
全球化背景与文学、文艺学本土化策略笔谈——受动者的智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笔谈论文,本土化论文,背景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02)05-0041-19
“全球化”已成为各个领域、各门学科都在热烈谈论的话题。这个诱人、堂皇的字眼,事实上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科技规模和经济趋势下所作的新一场调配。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自然关注这一世纪性的、波及文化学术场域的大潮。然而,如果我们越过科技、经济的层面,不难发现,“全球化”美妙的字眼背后,包含有特殊的价值论述、观念形态与文化诉求。那种假“普世”、“主流”、“接轨”之名而推行或传播的单一性与压迫性,那种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所引发的不均衡性、边缘性乃至被摧毁的可能性,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焦虑与思考。
就文艺学研究而言,那种以为“全球化”来了,世间有了文明的主流、学术的先导,中国学人只要往前靠、接上轨的看法,以为“他者”谈什么我们就谈什么的“唯名论”的念头,以为中国的文艺学没有系统体系也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观点,都使一些人陷入了受动的困境。或者说,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与学术传统的特殊性,更意味着放弃了对“自我”的肯定。
我们不妨提出一个问题:谈论、研究中国的文学(包括理论与创作),为什么不可以用中国自己的美学概念?为什么不可以发挥自身的内在性创造能力去重新解释传统观念并回应“他者”的挑战?
人类的精神、文明在其久远、在其深层,其实有着暗合、相通的方面。譬如说,西方有“移情”之说,而我们从庄周梦蝶的“物化”中,不难发现物我两忘、主客互移的影子;西方讲接受美学,中国美学早就强调“知人论世”,也可以在“清除距离”、“视界融合”上找到近义之处;“对话”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亦并非巴赫金之首创,两千多年前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墨子就曾有言:“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那也是强调了通过对话可分清是非、辨明异同,寻察自然与社会发展的道理、规律。如果我们把“他者”包容进来,又让“他者”来挑战自己、审视自己,继而在与“异”与“变”的碰撞中,把我们自身一些相对稳定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美学和学术观念重新阐释、重新解读,我想,我们也可以寻找到一些中国文学历史经验的当代表达形式,可以以一种文化与学术的自主性的姿态既切入现实的文学问题,又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普世性”体系产生反冲击,或补充其单一和匮缺。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艺学,无疑要召唤自己的民族意识,唤起学界对民族审美文化价值观的维护,使文艺理论的历史转型得以在对民族文化价值观重新确认的过程中进行,在传统文化思想与当代文化转型之间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继而产生能促进全球性文化多元和谐的有民族特色的理论范式、叙事策略与审美追求。这也是本土化策略的整体要求。
中国传统文艺学一开始就被赋予一种诗性思维——诗性往往又同美学、哲学相联系着。先秦孔子美学可谓中国古典文艺学的一大源头。沿着“思无邪”的思路而主张先善后美、以善制美;强调“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而寻求审美主客体的交融一体,衍化出“心物交感”并奠定古典文艺学的基石;提倡“中和”而发展成延续百代的审美模式、思维习惯和批评方式;从“图乐”、“知味”到“治心”、“养气”,揭示内省化的审美批评的心理过程;从“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到对倾向性的倚重,确认诗文的伦理化美学;而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诗性文心,又导向辩证地处理文质、因袭、言意、形神、道技以及多少、大小、远近、高下、浓淡、粗精等多种艺术哲学问题。况且,中国传统的思维与逻辑,一开始也没有那些非此即彼、排斥歧义的特征,相反,文艺学的表述受母语汉字“词法功能”和“字法功能”之影响,并借生义、意象思维、弹性连绵等的话语活力,既呈现了一种文明传承的命脉跳动,又提供了意味与创造的智力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古典文论有其内在性和连续性——把诗学(狭义的和广义的)视作自主的行为、人性的修炼和审美的投射,而且以特殊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一种历史的连续性。我们今天谈论自己的文论传统、谈论本土化策略,并不仅仅是一个重视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性问题,而是对这种特殊性内在的普适性价值和启示性意义的确认与自信。应当说,尽管斯人远去,但在今人眼里,纸“泛黄”了就有一种温暖,那里面有先贤的智慧和灵性在。
自然,“本土化”策略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回到传统的文本、规范,而是要重建自身文艺学历史的连续性。以批评语言而论,现代文艺学自新文化运动始,用白话代替文言,实际上更换了批评的语言系统。从批评观念上讲,不仅“汲古润今”——吸收了古典文论的养分,盘活与翻新(有的是沿用)了古代思想术语、美学概念,同时又“汲洋润中”——吸收西方文论的优长,产生了新的批评范畴与论述方式。这样,现代文艺学形成了一种新的场域、语境,既不同于古典,又不同于西方。的确,我们的一些批评家借助了古典文论的许多精华性理念,但古典思想并非以整体的、系统的、不加调适的方式进入现代文艺学,而多以“碎片”的形态在当今文论及叙述过程中闪射光亮。同理,我们一些有成就的批评家,也不是把西方文论拿过来照抄照搬,而是通过翻译——在追求信、达、雅的同时已经融入了自己的、属于中国现代人的理解与阐释。“汲古润今”与“汲洋润中”的交汇,使中国现代文论以至整体的现代文化,发生了从语境到批评概念、范畴、范式的重大嬗变,形成了不“古”不“洋”的、姑且称之为“第三种”文化、文学、文化,而且,也可以说,集百年之功,已酿成了一种“近传统”。
应当说,我们现在的文艺学已经结合“现代性”的解读而寻找着新的生长点。然而,如果我们获得“现代性”的代价只是认知“现代性”的命名而并不落实到自己的文学世界,仍然是件可悲的事情。中国有中国的文学问题,而且有些问题可能也是这个世界上许多人的问题。也因此,我们运用本土化的策略,不能采取拣一些别人的命名系统中的选题用汉字来操演辞藻和话语作派而是切切实实地从“中国问题”出发,对自己的理论境况作出反思,对自己的文学现象作出新解,对自己的叙述方式加以推进。在这方面,我们不是没有特长和优势可言。至少我们可以做下列的探索:
——发掘、整理我们丰富的古典文论资源,取其有益加以翻新,由当代激活而自铸新词。
——考察、研讨属于“母题”性质的、带有历史连续性的理论话语及其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变奏”,探究是如何“穿越历史”而获得生命力和净化力的。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生命情调入手,研究中国文艺学在历史进程中的合目的性与合理性,以及自然形成的理论思维习性与基本品格。
——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不满足于解剖学式的细读,而是把“局部”的文艺学研究与文学史、思想史、社会批评、文化批判、思想批判等“大问题”整体地结合起来研究,既“小题大做”又“大题小做”,将会造成有中国特色的大气象、大手笔,而不是纯学院式的或“占山为王”式的学术生产。
——“本土化”不是“守土有责”的代名词,而是对超出本土范围的相关性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对“世界联通”的概念体系提出质疑或修正,使西方学者不得不引以为参照。
“本土化策略”应当是文艺学有活力的策略。它的活力,既取决于对传统文论的当代解释,也取决于在与当今时代的正面碰撞中“穿越西方,接续传统”。中国的文艺理论家应当有勇气和力量深入当代,扩大而不是缩减母语的功能和语型,在对当代文艺学问题的复杂性的发现与探究中,更多、更广泛地拥有词语的命名权,而不再受动,不再被任何即时的、外在或外来的东西所赐予和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