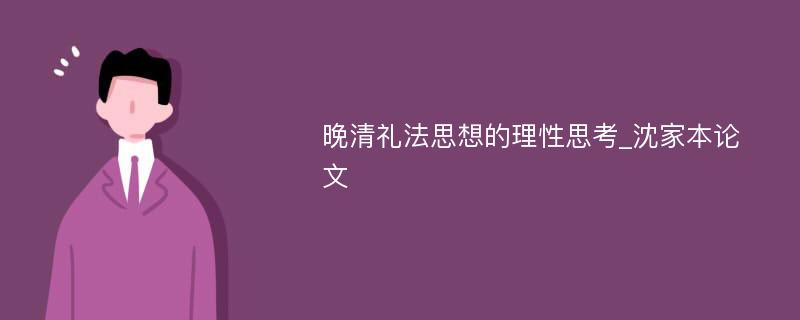
清末礼教派法律思想的理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教论文,清末论文,理性论文,思想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1-0062-04
1906年秋,清朝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遵清廷“参酌各国法律……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谕旨,“模范列强”、“斟酌编辑”,制定中国历史上首部《刑事民事诉讼法》。该法采用公开审判、陪审和律师制等西方审判制度,遭到以张之洞为代表的部院督抚大臣的强烈反对,被清廷宣布作废。次年,沈上奏《大清新刑律草案》,遭张之洞等的反对,清廷将该草案、学部及部院督抚大臣的反驳意见连同新颁布的修律“谕旨”交修订法律馆和法部,要求对刑律草案进行修改。在修订法律馆对草案作出修改的基础上,法部尚书廷杰在正文后加《附则五条》,命其为《修正刑律草案》。1910年,宪政编查馆核定该草案,编查馆参议、考核专科总办劳乃宣著《修正刑律草案说帖》批驳之,要求把旧律有关伦纪礼教各条修入新律正文,遭到沈家本等的激烈反驳。此后,以沈为首的一派和以劳为代表的一派就新刑律之条文展开辩论。宪政编查馆考核人员综合双方意见,改《修正刑律草案》为《大清新刑律》,《附则》为《暂行章程》。交资政院议决时,双方争论达到最高潮。劳乃宣与杨度就中国立法应遵循传统家族主义原理还是西方国家主义原理进行争论,后双方就“子孙对尊长之正当防卫”和“无夫和奸”问题爆发针锋相对的辩决。
法史学界称这场争执为“礼法之争”,涌现的两派为“法理派”和“礼教派”。其具体细节在人们记忆中已然模糊,它扬起的尘嚣却远未落定。反思当时辩决的实质,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仍是“乍新还旧”:如何处理中国法律传统与西方法律的关系,中国立法的根本等依然是当代法治建设不容回避的核心问题。在法治秩序的建构屡试不成,改革目标迟迟未达的今天,有必要“检讨一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的把握是否正确”①。由于过多受激进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过去对“法理派”和“礼教派”法律思想的“检讨”缺乏客观、公正与理性,对双方评论厚此薄彼,过于褒扬“法理派”,贬抑、斥责“礼教派”。前者被誉为“先进”、“文明”、“适应时代潮流”,沈家本被赞为“中国法制现代化之父”,其思想也被论者们全面、系统地阐释介绍②;后者却被冠以“反动”、“落后”、“顽固”等贬义评价,其法律思想极少受人关注,更遑论系统介绍、理性的评介。哲学家(思想家)是时代的制度、政治和社会环境之果③。“礼教派”是清末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其思想与“法理派”一样,是“深思熟虑”的理论体系,决非“疯狂叫嚣”、“令人啼笑皆非之说”④,它体现了“礼教派”对法律变革、文化传统、西方法律吸收等问题的深层思考、设计,值得我们冷静、客观地介绍研究,批判借鉴,不能仅仅用情绪性的语词加以斥责。本文先介绍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的主要法律思想,然后对其作出客观评价。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立基于对国内外时势的清醒认识,“礼教派”反对因循守旧,力主“变法”。张之洞是最早提出修律的地方实力派⑤。反思甲午战争失败原因,张提出“西人政事美备”,“十倍精于”其军事技术⑥,这远超当时认为西方先进仅在枪炮制造等器物的看法。《劝学篇》承认西学先进和学西学的必要性,坚定地表达采用“西政”、“西律”修改中国“旧律”的变法主张:“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⑦“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其器”,“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王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趋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⑧。张在与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穷而不变,何以为图?”“立法贵在因时,变通惟期尽利。”在后来的会奏中更强调修律。“我如拘守成例,不思亟为变通,则……权利尽失,何以为国?”“遐稽德、法,考日本,其变法皆从改律入手。而其改律,皆运以精心,持之毅力,艰苦恒久而后成之。”⑨“礼教派”后期人物劳乃宣被称是“十分顽固的封建卫道士”,“以反面人物入史”⑩,他也支持变法。他说“穷则变,变则通”,“今天下事变亟矣,……官司无善政,士无实学;刑不足以止奸,兵不足以御侮,而数万里十数国之强敌环逼而虎视。创闻创见之事,月异而岁不同。”如“犹拘于成法以治之”,则“鲜不败矣”。故,“法不得不变者,势也。”(11)
但是,张氏反对只知西学,不通中学。“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12) 他鄙弃“虑害道者守旧学”的愚顽,讽刺“旧者不知通”,“因噎而废食”,批判抛弃根本的“图救时者言新学”的激进派,指责“新者歧多而羊亡”,这两种极端片面的思想将造成严重后果:“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习。”(13) 张提出“博采东西诸国律法,详加参酌,从速厘订”,又反对“一意模仿外国”,要求修律“仍求合于国家政教大纲”。因为“立法固贵因时,而经国必先正本”,而且“盖法律之设,所以纳民于轨物之中,而法律本质,实与经术相表里,其最著者为亲亲之义,男女之别,天经地义,万古不刊”,所以,修律首先要“正本”,保持“法律本质”,“窃维古昔圣王,因伦制礼,凡伦之轻重等差,一本乎伦之秩序,礼之节文,而合乎天理人情之至者也。《书》曰‘明五刑以弼五教’。《五制》曰‘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此我国立法之本也,大本不同,故立法独异。我国以立纲为教,故无礼于君父者,罪罚至重”。新定《刑事民事诉讼法》和《新刑律》草案“于中法本原似有乖违者也”,“隐患实深”(14)。它们盲目引进西方制度,不知“西国以平等立教,故父子可以同罪,叛逆可以不死,此各因其政教习俗而异,万不能以强合者也”(15)。劳乃宣鼓吹,形而上者谓之道,道原天理,道者古胜于今,故道则从古从旧,万古不变;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成于人,器者今胜于古,器则从今从新,可变也。他批评“以新学为诟病”的“守旧之徒”,他们的“群起附合”使“有志之士亦劫于众论瞻顾而不敢涉足”新学。他激烈反对“偏于新说”,如一味“醉心欧化,貌袭文明,而千圣百王之大义,四子六经之微言皆弃之如遗,不稍措意”,“修律而专主平等自由,尊卑之分,长幼之伦,男女之别一扫而空。不数年而三纲沦、九法败、纲纪法度荡然无存”。新学是国家富强根本,纲常礼教之道又是新学根本。“农之利”、“工商之利”、“军械之强”皆“有待于新学”,但假如“无旧道以持之”,如将帅无忠君爱国之志,士卒无亲上死长之心,即使“甲兵坚利训练精良”,大敌当前,结果只能是“委而去之”,或“倒戈相向”,何谓国富兵强(16)?在劳氏看来,礼教纲常是道,器包括法律制度。由于“法而无所变,则道之不变者将为法所穷;法而轻于变者,则道之不变者将为法所累”,故“王者有改制之名,而无变法之实”,“不变者道,而不能不变者,法也”(17)。
“礼教派”承认社会发展的不可逆转,主张“立法固贵因时”,“法不得不变”,同时强调保持社会的稳定、连续性,坚持审慎变法,“持久毅力”。沈家本等“折冲樽俎”,“模范列强”,快速制定的《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却遭主张“博采东西诸国律法,详加参酌,从速厘订”的张之洞等的激烈反对。张等的反对原因在于该草案引进的西方法律制度在中国“扞格难行”。中国诉讼法制的改革,包括刑事民事诉讼法的制定、西方诉讼法律制度的引进等不应骤然进行。“外国法学家讲法律关系亦必就政治、宗教、风俗、习惯、历史、地理,一一考证”,法、德、日等国“变法者,皆从改律入手,而其改律也,皆运以精心,持以毅力,坚苦恒久,而后成之”,因为“惟是改定律例,事纂繁重,既非一手一足之烈,亦非一朝一夕之为”。所以,中国变法修律,“必须将中国民情、风俗法令源流,通筹熟计,然后量为变通。庶免官民惶惑,无所适从。”(18) 他主张从国情民俗出发,“运以精心,持以毅力”,再“期于民情风俗一无阻碍而后可”的渐进变法,反对“不察情势,贸然举行”、“过于西制”的激进变革。劳乃宣也提出了“不可妄变”的主张。他提出,虽不能“拘于成法以治之”,然而旧律基本精神、思想已深入人心,不可骤然改变。“欲举一世之法而悉变之”者,其意虽善,但偏激导致的危害甚于不变法。他指责这些人“欲以一时之力尽矫天下之失而不知风气当以渐开”,他呼吁“变法必以道为本,以时为衡”,“新学在所必兴,而不可因而废儒术之旧”。劳还从法律与道德之紧密联系的角度进一步论证法律“不可妄变”:“法律与道德诚非一事,然实相表里,必谓法律与道德教化毫不相关,实谬妄之论也”,“外国之俗重平等,而中国之俗重伦常,周孔之教,深入人心者,已数千年。所谓久则难变也。骤以外国平等之道施之,其凿枘也必矣。”他希望,不仅“刑律之修”而且“地方自治之规”、“国民代表之制”皆能“次第发生”,“假以岁月”,“加以提撕”,国民爱国爱家之心“不期然而然”产生,变法修律根本宗旨也即达到(19)。
劳乃宣不是“愚昧无知的阿Q”,不“拒绝对新学的了解和研究”,“常援引外国法律抨击法理派”。劳超越前人将法律起源与生计、风俗、礼教、政体联系起来思考,“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基本上是科学的”(20)。他以为,人类“生计”不同,法律有异。“法律何自生乎?生于政体。政体何自生乎?生于礼教。礼教何自生乎?生于风俗。风俗何自生乎?生于生计。”人类有农桑、猎牧、工商三类不同“生计”,就有三种风俗、礼教和政体对应,产生家法、军法、商法三种类型的法律。在农桑之国,人们耕定田,居定所,男耕女织,听命父兄,故家法以立。“家法者,农桑之国风俗之大本也。”农桑之国的礼教政体由家法生,法律以维持家法为旨归。“家家之家治,而一国之国治也。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是也”。在猎牧之国,人们择水草之处而居,依兵法维持有序生活,其礼教政体由兵法生。在工商之国,“人不家食,群居于市……人人服从于商法”,其礼教政体由商法生。“风俗者,法律之母也,立法也不异其俗,其凿钠也必也。”法律“不能与风俗相违”,作为农桑之国的中国,不能用兵法和商法,只能“从家法”。对“中国之坏,就由于慈父孝子悌弟太多”,“四万万人都是对于家族负责任,并非对于国家负责任”的指责(21),劳辩解说,中国人只知爱家不知爱国,不应归咎家族主义,应在于秦后的专制制度。“春秋之世,正家法政治极盛之时也,列国之民无不知爱其国者”。“国人莫不毁家以护其国,家法政治之下,民何尝不爱其国哉”?西人爱国,非不爱其家。西国“行立宪政体,人人得预闻国事,是以人人与国家休戚相关”,西人“深明家国一体之理,知非保国无以保家”,“其爱国也,正其所以爱家也”。中国秦以后的专制使“一国政权悉操官吏之手,而人民不得预闻”,人民但知爱家不知爱国。如“今中国已预备立宪也,地方自治之规、国民代表之制,次第发生也,假以岁月,加以提撕,家国一体之理渐明于天下,天下之人皆知保国正所以保家,则推广其爱家之心而爱国之心将油然而生”。不能借口“家法政治之不善”,以欧美“尚平等,重权利之道”代替“家法之治”(22)。而且,中国的家族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除了“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的狭义家族主义,还有“事君不忠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尧舜之道孝悌而矣”的广义家族主义。他主张,“保存伦理上之狭义之家族主义,以弥政治所生缺陷,提供广义之家族主义以为国家主义之先驱”(23)。总之,劳乃宣主张,“变法……本乎我国故有之家族主义……以期渐进于国民主义,事半功倍”(24)。
有学者认为,“法理派”代表“新文化进步思想”,“是资产阶级法律思想,以维护‘人权’为号召,进而达到维护资产阶级所有权、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礼教派”“体现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图”,“反对用西方法律改造旧法,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保护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垄断资本主义”(25)。其实,“礼教派”和“法理派”都倡言变法,试图拯救清廷。沈家本“是忠实执行清廷‘变法新政’的典范”,“在修律方针上,他与清廷完全一致”,他“受封建法律文化影响很深”,对传统法制和律学的理解深刻而全面(26)。两派在变法旨归、法律作用和地位等认识方面无本质差异。沈家本指出“中重而西轻者为多”,要求行“仁法”,张之洞赞“西法以省刑养民为先务”;沈主张“新亦当参,旧不俱废,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张也讲“变中国旧法从西法,非泛泛改革整顿之谓也”,“以西法为主,抱定旨中‘采西法补中法,深化中西之见’二语作主意”;在沈家本看来,“为政之道,首在立法典民……刑法乃国家惩戒工具”,张之洞视法律为“纳民于轨物之中”,须“与经术相表里”;沈强调法律“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劳乃宣提出立法“本乎我国故有之家族主义”。双方无根本冲突,其争论“是采行‘西法’多一点或少一点,照顾中国礼教风俗多一点或少一点之争,是激进或渐进之争”(27)。
“法理派”相信列强放弃治外法权的诺言,强调外人对修律的态度,深惧列强悔约不能收回治外法权(28)。修律中,“所谓‘参考古今’,‘考今’是实,‘参古’是虚;‘博稽中外’,‘稽外’是真,‘博中’是假”(29)。修律“专以折冲樽俎”,“模范列强”。“会通中西”变成“专力翻译”,“继则派员调查”,比较法律条文,找出符合列强“法制完备”标准的条款,把它们囫囵吞枣般地嵌入中国法律躯体。这些“后出最精确法理”,“世界通行之法规”使中国法律“在规范制度的层面上具备了近代化的形态”(30),但此“理性的目标,不理智的过程”(31) 的激进修律“不是翻译即为抄袭”,“依照本国情形而为创制之法律,可谓极少”(32),因而“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割裂传统的不归之路”(33)。“一切法规的形式和内容,直接模仿日本,间接效法西欧。中国旧律,在起草者的心目中毫无存在的余地……传承数千年的旧律,随着成为历史上的名词”(34)。直接后果是“基本西化而非中西融合”(35)。这是百年中国法治艰辛曲折的根源之一。“最精确”、“最先进”的法律制度得以引进、健全,中国人的法律意识、法律价值和“主体精神”依旧,国法与人们心中的“活法”产生矛盾、冲突。因为“先进未必合适”,“法律的价值之一在于它必须与特定的国情、民情相适应”(36),与社会现实、国情民俗及人们观念背离的法律制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生命力。这种断裂传统、盲目移植西法的激进变革,导致近代中国社会独有的制度与精神、条文与现实之疏离隔膜的二元主义现象,但因其“先进”、“符合历史潮流”倍受后人喝彩。“礼教派”之考量国情民意、循序变革的主张却屡屡遭人诟病。
“中体西用”是“礼教派”法思想的理论基础,后人从激进意识形态出发对之采取驳斥、贬低的态度,认为它主张只学西方的器物技艺,不学西方的政治法律;认为它冥顽不化,死抱封建专制的伦常纲条。其实,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用”并非仅指西方的技物,还包括西方的政治制度。其“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艺”的主张,体现出“中学为体,西政为用”;而其“体”,也非君主专制之体,而是“文化价值系统之体”,“中国人……主体精神……含有对人类根本之道和中国国情的深刻思考……张之洞主张的是要识本,固本,把握大道”。“礼教派”坚守“主体精神”,“本、体、大道”,主张变法要保持、坚守中国法律之根,要对中西“政治、宗教、风俗、习惯、历史、地理进行一一考证”基础上,再“通筹熟计,量为变通”。萨雅尼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初期,法律如同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语言,生活方式和素质一样,就具有一种固定的性质。这些现象不是分离地存在着,而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机能和习性,在本质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我们看得到的明显属性。这些属性之所以能融为一体,是由于民族共同信念,一种民族内部所必须的同族意识所至,任何偶然或任意原因的说法都是错误的。”(37) 罗斯科·庞德更具体指出,“因为人民并不为法律而存在,法律是为人民而存在,用以维持并促进他们的文化……关于发展及适用中国法典的技术,必须是适应中国的技术,而非从普遍适合于全世界的观念中移植过来……只有中国精神才能使中国法律有效地治理中国人民。”(38) 礼是中国传统法的精神和灵魂,也是“中国精神”和“民族共同信念”。礼外现为具体的礼制(礼仪),“礼法一体化”就是礼制(礼仪)与法的融合;礼的内在本质是礼义,礼义根源于“家族主义”的“亲亲”、“尊尊”的伦理道德。礼的外现形式可随时代变迁修正;礼义乃亘古不变的原则,是衡量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制度的价值标准。在中国传统法观念中,法必须体现这种礼义之精神,即“家族主义”的“亲亲”、“尊尊”为核心的人伦道德,否则,法“就失去了价值,违背了礼义……就成了不详之物”(39)。
在时不我待的激进变革中,人们关注快速引进“最先进”、“最精确”的制度,“礼教派”的呼吁被视为“抱残守缺的鼓噪”,“礼”、“德”、“教化”皆被看作传统的包袱,无情地斥责和抛弃,结果是“割断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脐带”。“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而发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真正的法律不是用墨水写在纸上,而是用道德写在人的心中。未能“发乎人间,合乎人心”,没有道德作支撑,移植来的法失去了“大本”、“主体精神”,就成了“无血肉的枯骨”(40)。依美国人柯文“代际逻辑”的观点,历史上每代人都受到其时代的限制,其思想、眼光和事功不可能超越时代(41)。我们不能站在今人角度,苛责百年前的“法理派”,他们竭力将法律与道德分离,让法律成为独立、专门的社会规范,直接引进“最精确法理”、“世界通行之法规”,过于幼稚激进,精神用意却良善可嘉;我们不能苛责“礼教派”,果诚如“礼教派”主张在坚守根本基础上,“徐图自强”,“随着时间推移和变革范围扩大,这些小变革和效果显现起来,就足可以带来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社会变革既没有人去刻意赞美,也不会引起恐慌,……生活于中的人们就可以有机会调整自己”(42),那么,中国百年法治之历史是否会被重写呢?
注释:
①季卫东:《宪政新论——全球化时代的法与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序》。
②参见纪念沈家本先生诞辰150周年学术会议论文集《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法学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台湾地区“中国法制史学会”编《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回顾与前瞻——纪念沈家本诞辰152周年》,台湾大学法学院出版,1993年。
③Bertland Russeau,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London.George.1968,Preface.
④罗志渊:《近代中国法制演变研究》,正中书局1976年版,第215页。
⑤有论者认为甲午以后的清末,“师夷”的重心转向夷制和夷文化,目的都是为了“制夷”即改变中西竞争中中国的劣势地位,实现自强并超越西方,而这一转向首先起于张之洞、刘坤一之奏折。见赵娓妮《清末中西竞争语境下的刑律修订》,《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⑥此为谭嗣同转述,见《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8页。
⑦⑧(12)(13)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2002年版,外篇“设学”第三,“变法”第七,内篇“循序”第七,“序”。
⑨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会保熟悉中西律例人员沈家本等听侯简用折》,载廖一中、罗真容主编《袁世凯奏议》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75页。
⑩张国华、饶鑫贤编《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2页;李贵连:《近代中国法制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页。
(11)《桐乡劳先生遗稿·谈瀛漫录》。
(14)(18)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遵旨核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北平楚学精庐刊本,民国二十六年。
(15)《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四年六月。
(16)《桐乡劳先生遗稿·论古今新旧》。
(17)(19)(22)《桐乡劳先生遗稿·新刑律修正案汇录序》。
(20)(25)(28)李贵连:《近代中国法制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129-131、43页。
(21)《资政院议场速记录》,第二三号。
(23)《桐乡劳先生遗稿·江氏刑律争论评议》。
(24)《桐乡劳先生遗稿·修正刑律草案说贴》。
(26)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页。
(27)邱远猷:《张之洞与清末法律近代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9)(33)李晓明:《清末礼法之争及其法哲学解析》,《河北法学》2001年第4期。
(30)张生:《从沈家本到孙中山——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1期。
(31)(36)朱勇:《理性的目标与不理智的过程——论“大清刑律”的社会适应性》,载张生主编《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295页。
(32)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44页。
(34)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河北第一监狱印刷,1947年,第58页。
(35)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
(37)[德]萨维尼:《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26页。
(38)翟志勇主编《罗斯科·庞德:法律与社会——生平著述及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页。
(39)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85页。
(40)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41)郑定、扬昂:《还原沈家本:略论沈家本与晚清司法场域之变迁(1901—1911)》,《政法论坛》2004年第1期。
(42)[美]拉齐恩·萨丽等:《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秋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