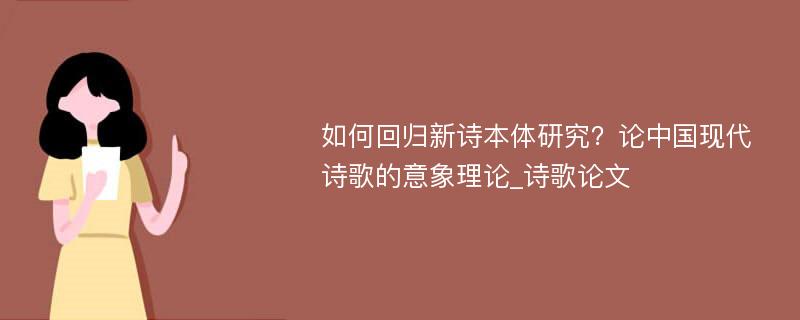
如何重返新诗本体研究?——从《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意象论文,本体论文,中国论文,现代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9)05-0097-05
一
中国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无可避免地置身于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两大传统的阴影”(黄灿然语)之中。在看待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问题上,大致有三种观点和态度:一种观点认为,新诗对古典诗歌造成了“断裂”,“和传统及历史相呼应的品质在新诗创作中消失了……是新诗显得单薄、落寞、无传统支撑的原因”,而那场催生了新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被视为一次“对母语的弑母行为”①;另一种观点刚好与此相对,论者提出,“从现代性的角度看,新诗的诞生不是反叛古典诗歌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②;还有一种观点持调和论,主张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具有某种共通性,研究者甚至从具体的元素如词汇、句法、意象乃至情调入手,看到了新诗在某些方面对古典诗歌的“继承与改造”③。
实际上,迄今为止包括上述观点在内的众多关于新诗的论述,无论是思潮、流派的梳理,还是对诗人、作品的探究,一个很重要的主旨就是围绕新诗的“合法性”进行辨析。研究者力图在与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的区分中廓清新诗自身的边界,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和层次,勉力勾画新诗发生、发展的曲折历程,寻索新诗之为新诗的“特质”。在这样的勾画和寻索过程中,必然要对新诗史上的某些问题和现象不断进行重述。
从研究角度和方法来看,1980年代以降的新诗研究,经历了从政治(阶级)、社会文化角度和主题分析方法,到本体、审美角度和形式(语言)、文本分析方法,再到近年的报刊、出版以及更为宽泛的文化角度和综合分析方法的转变过程。当然,这样的描述,并不意味着每个时期的新诗研究在角度和方法上是绝对单一的(如此上述过程就成了一种单一对另一种单一的替换),而仅仅试图表明某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研究风尚。不过,总体来说,近30年的新诗研究经历了从批评到学术的转变。
如果对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新诗研究略作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显著差异:与1980年代诗歌和思想文化的理想主义氛围相呼应,此际的新诗研究多为充满锐气的批评,表现出强烈的追寻历史“真实”、探求诗歌“本体”的姿态,具有浓郁的“自律”色彩和审美主义气息;而1990年代诗歌的“边缘化”处境和某种规范化学术机制的确立,则为更多内敛稳健的学术探讨提供了可能,新诗研究逐渐成为一种知识化的运作,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例证是1990年代新诗史论著的大量涌现。最近几年,由于受强势的文化研究的影响,新诗研究出现了以考察新诗与历史、文化环境之关系等“外部”研究,取代审美、形式研究和文本分析等“内部”研究的趋势。于是,新诗研究中始终未曾消隐的“内”与“外”的纠缠再度凸显出来。
在如此情形下,新近出版的王泽龙教授的专著《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③,可谓一个颇能映照当前新诗研究特点与趋向、引发一些相关议题的典型案例。该著似乎找到了一条对新诗之“特质”进行“重述”和重新解析的可靠路径,那就是以“意象”为探讨的核心,“通过现代诗歌意象的研究,引起人们对现代诗歌以及其他现代诗歌本体性问题的更多关注,共同把中国现代诗歌研究引向深入”;在该著作者看来,“诗的文体、诗的节奏、诗的韵式、诗的结构,包括诗的语言与诗的意象问题,它们构成了诗之为诗的本体属性”,“现代诗歌研究最薄弱之处突出反映在有关诗歌本体或诗歌形式方面。作为文学门类中的诗歌,相对其他文体形式而言,是一门更加形式化的艺术,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到诗歌本体艺术层面的各个环节,不然就会制约我们对现代诗歌其他层面的研究”。[1](p.3)
二
“走向本体”在1980年代的文学和诗歌研究界曾经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在文学性和诗意逐渐消失或弥散,文学和诗歌本体被种种传媒、网络、影音和大众文化所围裹的今天,提出重视诗歌本体研究无疑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不过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究竟应该如何重返诗歌本体及本体研究?
的确,《意象论》对新诗意象理论、意象艺术和意象文本所作的条分缕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本体研究。从全书的结构来看,该著以诗学论、发展论、比较论三个方面为基本线索和框架,试图通过逻辑严密的论证,建构一种关于新诗意象理论嬗变和意象艺术发展的体系。立足于新诗意象诗学的历时性考察,《意象论》从中提炼出具象论、幻象论、兴象论、意象象征论、恶美意象论、象征意境论、意象联络论、体验意象论和意象的诗质化、意象的智性化、意象凝合论、意象结构论、意象沉潜论、意象凝定论等命题,并讨论了意象的全感官性、情趣与意象、显意象与隐意象以及意象人格化等诸多议题。
在此基础上,《意象论》借助于对不同时期代表诗人作品中意象艺术的剖析,力求把握不同历史阶段新诗意象艺术的规律性特征。在作者看来,20年代是新诗意象的诞生与转换期,此际的新诗意象艺术以古典诗歌意象艺术作为对照物,与后者经历了一个纠结、突破、回应与反叛相交叉的过程;30年代意象探索表现为对古典诗歌意象和西方现代主义意象艺术的兼容,在意象的生成方式、审美理想、思维特征、形态选择等方面,显出更全面、更自觉的建构意识,体现了新诗意象艺术的发展与深化;40年代的新诗追求意象内质的充盈与丰厚、意象内涵的深沉与内敛,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度的意象象征模式,特别是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诗歌,实现了意象从感性形态向智性形态的转变,以意象视域的日常性、意象取向的都市化、意象思维的现代性生成等方面,全面推进了意象艺术现代化的深层发展,体现了新诗意象艺术的基本成熟。[1](pp.5~7)
应该说,《意象论》实现了作者预期的某些理念:“在现有的个体诗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起一个较为系统的宏观研究的意象体系,从意象论的视角较全面深入地透视中国现代诗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本体性特征,从而形成某些关于现代诗歌意象诗学的理论思考和创作实践中意象问题规律性特征的认识。”[1](p.3)
那么,当这一集结着高度本体意识的“意象”,被作者用来观察新诗历史和现象时,其效力究竟怎样?这里有几方面的问题值得辨析。一方面可以看到,《意象论》在对新诗意象诗学的历时性考察和对新诗意象艺术嬗变过程的线性梳理过程中,始终葆有一种建构诗歌史的抱负。作者显然意识到,并没有一种本质化了的稳固的新诗“本体”,因而他把新诗意象的生成看作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将之放到新诗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分析。不过,前引《意象论》所描述的新诗意象探索的规律性特征——从“诞生与转换”到“发展与深化”再到“基本成熟”——如此线条分明的嬗变轨迹的勾勒,实则是一种带有理想化色彩的递进、整合新诗史观的产物。这样会给人带来某种印象:新诗历史就是新诗意象艺术演变的历史,作者以对意象的分析替代或涵盖了对新诗其他因素的分析。其实,这种新诗史观及其引导下的建构新诗历史的方式,在1990年代以来的新诗史论著中颇为常见。较典型的如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便把新诗历史划分为草创、奠基、拓展、普及和深化等阶段,这些阶段之间的标志性更迭来自以郭沫若、戴望舒、艾青为代表的三次整合,该著作者将这一过程称为“循环着由合-分-合的规律,即肯定-否定-肯定的辩证发展过程”④。这无疑是舍弃了许多枝蔓的建构新诗历史的方式,其所造成的对历史复杂性的遮蔽和简化,正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和检讨。
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意象能否担当对整个新诗历史、现象和问题的剖解?虽然作者的本意只在于把新诗意象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而非以意象来整合甚至涵盖全部的新诗现象和问题,但当他试图勾勒一条线索清晰、具有鲜明“史”之倾向的新诗意象发展脉络时,他的描述难免遭到如此质询。意象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它应用于新诗后所产生的古今之变,并不能仅从意象自身获得解释,其间还关涉古今汉语的语汇、语法、句法和诗人思维的差异等因素。
由于新诗所用的现代汉语,在性质上属于分析性语言,在来源和风格上偏于口语化、散文化,在句法上较少古代汉语中省略了关系词的并置与叠加方式,而更强调语义和句子结构的完整性,因此,相对于古典诗歌而言,新诗对意象的态度以及意象在诗中的位置和表现,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一,新诗的意象超越了传统意义的意象,不复有相对稳定的内涵和指向,从而变得繁复、零碎和充满歧义;其二,意象的营造似乎不再是诗歌的重心所在,诗歌中的“意”胜于“象”,感性的直观让位于理性的思辨;其三,有别于古典诗歌“物我同一”的思维观念、“目击道存”的构思和表达,新诗的诗思多表现为矛盾丛生、“物”“我”分离、有很强的透视意图,这使得新诗意象的生成颇为隐蔽、多变和难以把捉。这也就是说,意象对于新诗来说并非一个孤立的问题。
诚然,《意象论》将意象从新诗历史和现象单独析出进行梳理,自有其合理和新颖之处,却因其题旨的限制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意象与新诗其他因素的诗学和历史相关性。
三
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看,《意象论》所倚重的“意象”这一范畴,其本体意识和观念的确立,或者说其作为本体得到确认,主要建基于1980年代的诗学氛围。尽管新诗历史上有不少对意象的关注和言述,比如胡适受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启发而提出的“八事”[2],李金发所宣称的“诗之须要Image犹人身之须要血液”[3],施蛰存在《现代》杂志上打出的“意象抒情诗”旗号,李健吾对1930年代现代派诗人运用意象的解析——(意象)“从各方面来看,光影那样匀称,却唤起一个完美的想象的世界,在字句以外,在比喻以内,需要细心的体会,经过迷藏一样的捉摸,然后尽你联想的可能,启发你一种永久的诗的情绪”[4](p.113),但是,这些关注和言述并不具有明确的本体意识。只有在本体研究和审美研究盛行,同时也是观念热和方法论热十分高涨的1980年代,随着以意象为重要技巧的新诗潮(“朦胧诗”)的兴起,随着一些对这种诗歌现象进行阐释的理论表述应运而生,意象才显出真正的本体意味和特征。
1980年代关于意象的论述中,除难以计数的研究论文外,尚有多部专门性的论著出版,如陈植锷的《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初版)、吴晓的《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诗学新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初版)、汪耀进主编的《意象批评》(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初版)等。其中,吴晓的著作可以被视为在理论上对新诗潮的直接回应,正如曾经作为新诗潮主要辩护者的谢冕在为该著所作的序言里开篇写道:“新诗潮的崛起是自有新诗历史以来就艺术层面而言较为纯粹的一次革命”,“新诗潮除了变革和拓展传统诗歌内涵而向着精深沉厚方向挺进外,其在诗艺革新方面的最大贡献即在于大幅度引进意象化方式而为新诗注入了鲜活的生机”[5];该著“内容简介”中所说的“作者从‘诗是意象符号系统’这一本体论观念出发,系统介绍了诗歌意象产生、运动、组合的内在规律及诗歌情感空间构成的基本方式”,正是吴著的宗旨和特色所在。
与1980年代应运而生的关于意象的论著相比,《意象论》的取向迥然不同:其一,虽然该著作者的视野里也有1980年代新诗潮这一背景,但他的立意在于追溯新诗历史上的意象传统。作者注意到,1980年代后期“第三代”诗人为了抵制“朦胧诗”,主张“要从诗中放逐意象,并将消解意象、抛弃意象作为彻底告别朦胧派诗以及中国诗歌传统的一个标志,让诗回到自足的语言本体”。这一现象引发了他的追问:“这种非意象化的新诗潮提出来的具有挑战性的命题,是否代表了当代新诗潮发展的某种趋势呢?一向被我们视为诗歌生命之内核与灵魂的意象的现代性意义何在?”在此作者的意愿是明确的:“必须认真研究诗歌意象的传统,特别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诗歌意象传统,并作出理论的阐释与回应。”[1](p.2)其二,正如作者也认识到的,在当前无论创作实践还是学术研究中,意象的绚烂景观早已是明日黄花,人们对于意象的种种理解和诠释本身也已成为诗歌“知识库”的组成部分,当他执意重拾这一渐渐被尘封的范畴时,时代境遇的变迁使他的研究与当下纷繁变幻的创作场景形成了某种脱节和错位,因而《意象论》无法像1980年代的某些论著那样能够直接与当时的创作现象展开对话。当然,在当前,不独意象研究如此,新诗研究中任何显得孤立、封闭的知识化研究的命运大抵如此。
这一错位,导致了《意象论》中能够充分体现作者本体观念、支撑全书论述的文本分析在有效性上的减弱。该著作者格外提到:“诗歌的本体性研究应该主要是文本的研究,只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概括或规律总结才能有说服力。在具体诗人与诗歌文本的研究中,也运用了一些西方现代批评的概念与方法,涉及的主要有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新批评、现代意象批评等。”[1](p.7)众所周知,文本分析是1980年代文学和诗歌本体研究的有机构成要素,此际不少研究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譬如,康林提出“本文结构”的概念,将新诗“本文结构”划分为语言体式、语象世界和语义体系三个层次,他通过剖析胡适《尝试集》的“本文结构”,展示了新诗怎样一步步促使古典诗歌本文结构的瓦解直至建构自身本文结构的全部过程,即“汉语抒情诗的本文结构”“从古典形态过渡到现代形态”的过程。[6]1980年代的文本分析,与俄国形式主义者对诗歌中语词关系的精细剖解和英美“新批评”基于“肌质—构架”说所采取的“细读法”的熏染是分不开的。不可否认,这种文本分析曾给新诗研究带来巨大的活力,但由于研究者过于强调诗歌文本的自足性,堵塞了诗歌向外部世界敞开的通道,所以很多文本分析最终沦为了单纯的技巧分析。
可以看到,《意象论》的突出优势确实体现在其对新诗历史上一些典型文本的细致分析。不过,其所采用的方法承续的是1980年代文本分析中的某些方法,这使得该著的文本分析在凸显了新诗意象艺术特色的同时,会出现一定的论断上的不足。比如,该著在阐述新诗中的“感物兴思”的诗思模式时,举了陈敬容的《律动》、郑敏的《金黄的稻束》和穆旦的《春》为例进行分析,其中关于《春》作者论析道:
《春》一开始起兴之物就是托比兴思,比中寓思,“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接下转向“花朵”,“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再由花朵引出暖风,暖风吹醒“满园的欲望”,由春天里自然欲望的苏醒流转到二十岁青春的“禁闭的肉体”被点燃,却无处归依。最后升发出春天里一切生命苏生中的渴望:“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意象层层递进,思维随物婉转,所感之物与所兴之思高度融合,给人兴会无穷的感受,诗的意象思维不是单线直进,也不是平面平行展开,而是一种曲线流转,随物婉转,容涵了更为丰富的人生体验。[1](p.179)
这里所论断的《春》的“意象思维不是单线直进,也不是平面平行展开,而是一种曲线流转”,是十分准确的。不过,《春》的独特魅力和价值,除感物兴会(思)的意象思维外,还在于其语词与主题之间以及诗句内部的张力所显示的现代感。倘若对一首诗的解读仅限于从意象角度进行论析,或仍然沿袭1980年代文本分析的某些方法,那么,这样的解读多少会留下一些尚待拓展的空间。
当然,这并不是说,从1980年代本体研究浪潮中涌现出的文本分析已经过时。近年来,在新诗文本分析方面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著作,如唐晓渡的《中外现代诗名篇细读》(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洪子诚主编的《在北大课堂读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孙玉石主编的《中国现代诗导读》(三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蔡天新主编的《现代汉诗100首》(三联书店2007年版)等,这些各具特色的论著深化了新诗文本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新的时代境遇提示着研究者应该以新的方式进入诗歌文本。如前所述,1980年代文本分析的主要局限在于其自足性和封闭性。笔者认为,突破这一局限的可行途径在于,在文本分析中重新引入历史语境、制度策略、文化心理等“外部因素”,并将新诗文本与这些“外部因素”的关系,从一种依附、对峙或反抗的格局,调整为穿越、渗透乃至包容的情势,讨论种种“外部因素”渗入新诗文本中的复杂印迹,及其对新诗文本样态与体式形成过程的塑造和影响。或许,重返新诗本体研究,不是重新回到某个局部或总体的本体概念,而是重新找到本体研究得以生根的语境及二者的新的紧张关系。
收稿日期:2009-06-07
注释:
① 参阅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② 参阅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见《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第89页以下,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③ 王泽龙:《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意象论》。
④ 姜涛恰切地指出了龙著的“历时性的线性发展眼光”和“对某种内在演进、辩证发展的逻辑的强调”。见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第5、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