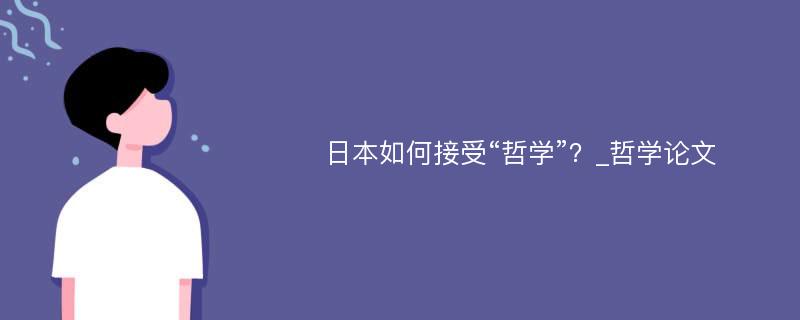
日本如何接受“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2)01-0006-07
一、最初的“哲学”教学
日本最初的哲学教学究竟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或许不少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线索、模糊不清的问题,不过幸好过去的基督教研究可以解答它,也就是距今420多年前的1583年(天正11年)。1580年,耶稣会高等教育机构——天主教神学院(Colégio)首次在丰后国府内创办,并开始了人文课程的教学。1583年10月21日,人文课程教学结束之后,神学生们开始接受哲学课程的教学。哲学课程采用的教材乃是在罗马诺神学院(Collegio Romano)教授哲学与神学的托雷多(Francisco de Toledo)所编撰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解说。但是,这一课程是以拉丁语来进行的,而且,只有5名葡萄牙的神学生选择了这一课程①。就此而言,或许我们不能将之视为日本哲学教学之开端。
日本第1次出现“哲学”(philosophy,philosophia,filosofie)的记载,也是在与基督教相关的出版物之中。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耶稣会第1次将活字印刷机带到日本,并印刷了基督教版的书籍。现存最为古老的资料,就是1591年在岛原加津佐出版印刷的《サントス[聖人]の御作業の内抜書》(圣人桑托斯工作之记载)一书,该书之中多次出现“ヒイロゾフイア”[philosophia、哲学]、「ヒイロゾホ」[philosopho、哲学者]等一系列词语。不仅如此,该书还出现了这样的记载:塞内卡[Seneca]赞美斯提尔朋[Stilpon]这位哲学家[philosopho、哲学者]所讲述的话语,这位哲学家的居住地在被敌军打败之后,大将德梅崔厄斯[Demetrios]遇到了哲学家,提到经历战乱之后什么都会失去。对此,哲学家却回答什么都不会丧失,也就是如果将此身拥有的财宝换为哲学的话,那么就绝对不会失去了②。在此,日本人并没有翻译“哲学家”这一概念,而是直接使用了葡萄牙语的[philosopho、哲学者]的表述。这也就是日本最早的使用例文。
以日本语来展开哲学的教学,西周大概是第一人吧。1862(文久2)年至1865(庆应元)年,西周留学荷兰莱顿大学。回国之后的第2年,西周就得到了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召见,而后随侍左右。在这一时候,西周开设私塾,为众多的弟子讲授西方学问,也就是可能在这一时期展开了哲学教学。但是,西周究竟在这一时期——京都时期究竟从事了什么样的教学,却是难以了解细致。
明治维新之后,西周担任新政府(兵部省)的官员,同时还开设私塾——育英舍,并自1870(明治3)年开始以“百学连环”为标题进行了教学。所谓“百学连环”,乃是Encyclopedia一语的翻译,它并不是唯以哲学为对象,而是涉及整个学问;不仅如此,应该说西周也没有就哲学而展开详细的教学。但是,西周却进行了“致知学”(Logic)、“理体学”(Ontology)等哲学各个领域的概述,而且也概述了“哲学的历史”。尽管西周的教学极为简单,但却是日本最早的哲学概论,同时也可以说是日本最早的哲学史教学。
我们如今所使用的大多数的学问术语,事实上就是西周在这一教学以及1871(明治4)年至1873年期间执笔的《生性发蕴》所使用过的。“几何学”与“地质学”这样的学问称谓,“立法权”与“元素”这样的学术用语,“概念”、“命题”、“演绎”与“归纳”这样的哲学术语就是一个范例。而且,“哲学”这一概念本身也毫无例外地来自西周。
二、philosophy的翻译语
1862(文久2)年,幕府派遣使者赴外订购两艘军舰,西周与蕃书调所的同僚津田真道(1829年-1903年)一道随行赴荷兰留学。西周一行抵达海勒武特斯莱斯[Hellevoetsluis]之后即进入荷兰莱顿大学,师从中国学——日本学教授霍夫曼(J.J.Hoffmann)。在赴荷兰的船中,西周写下了一篇荷兰语的文章——这篇文章也交给了霍夫曼教授。在这篇题为“致有关人士”的文章之中,西周就自己的留学意图进行了这样的阐述:“不管是致力于改善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还是为了进行内政或者设施的改良,皆需要更高一层的学问。这样就必须要向统计学、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外交学等领域进行求索。这样的学问在日本还不为人知。……除此之外,我还想学习被称为哲学或者爱智学的学问,它与我国法律严格禁止的神学不同,乃是笛卡尔、洛克、黑格尔、康德等大力宣传的学问。”③霍夫曼收到该文之后,就向西周介绍了同事、经济学教授西蒙·卫斯林(Simon Vissering)。卫斯林就在自己家中为西周、津田开设了自然法、万国公法、经济学等课程。
在这篇文章之中,西周强调自己要学习日本需要的法律学、经济学,并将它视为自己的首要目的。同时,西周也表明自己对于学习哲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在留学荷兰之前,西周就对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并且有所了解,这一点通过其留学之前寄给友人松冈的信函即可一目了然。西周写道:“小生最近得以了解西方之性理学、经济学等学问之一端,大为惊叹其乃公平正大之论,而觉悟到与以往所学汉说存在大相径庭之处。只是其所言ヒロソヒ之学,阐述性命之理不轶于程朱之学,本于公顺自然之道……”④
根据这一文章表述,我们可以了解到,西周将哲学理解为儒学,更为确切地说是理解为宋学所谓的“性理之学”,并以理气、心性之学作为基础来理解它。与那一时代开始关注哲学的大多数人一样,西周也借助儒学的各个概念来作为理解哲学的支撑点。但是,西周同时还注意到了二者之间的差异。不仅如此,他还强调在探索事物、人类的根源与本性这一方面,哲学凌驾于宋学之上,乃是令人惊叹的“公平正大”之思想。日本在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曾经出现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立论⑤,且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但是西周的这一论断却显而易见地超越了它。究其背景,可以说正是缘于西周直接接触到了欧洲的学问,也直接地认识到欧洲学问所具有的决定性的力量。
西周在赴荷兰之前,或者说在赴外途中传闻曾撰写西方哲学史的课程教案。在这一教案之中,西周亦曾记载:“这一时期从事此学之人(贤者),皆自称ソヒスト[sophist],意为贤哲。尽管这一语意不失夸耀之意,但是,西方的苏格拉底却以谦逊的态度自称为ヒロソフル[philosopher],意为爱贤德之人,应该等同于希贤之意。”
由此可见,西周在留学之前即对哲学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给霍夫曼的文章之中,西周列举出笛卡尔、洛克、黑格尔、康德等人的名字也并非是什么偶然。与此同时,我认为还需要注意的是,西周提到philosopher之意“等同于希贤之意”。如前所述,“哲学”这一翻译语来自西周,但是西周一开始并不是就将它翻译为“哲学”。1861年,津田真道执笔《性理论》之际,西周为它撰写了跋文。在这篇文章之中,西周将philosophy表述为“希哲学”。“西土之学,传之既百年余,至格物[物理学]舍密[化学],地理器械等诸学科,间有窥其室者,独至吾希哲学(ヒロソヒ)一科,则未见其人矣,遂使世人以为西人论气则备,论理则未矣。(故希哲学一门,译者附)独自我友天外如来(津田真道号“天外”)始。”
“希哲学”这一翻译语,正如西周在《百学连环》、《生性发蕴》所阐述的,乃是来自周濂溪《通书》志学第十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这一段话。津田真道亦在被推断为自1860(万延元)年至1862(文久2)年期间撰写的《天外独语》之中,也使用了“求圣学”这一表述,并标示出“ヒロソヒ一”的假名注音;在《性理论》之中也采取“志道希贤者”[1]73的表述。就此而言,应该说津田也是从周濂溪的《通书》获得灵感而采取了这样的表述。顺便强调一点,正如之前西周写给霍夫曼的文章所示,荷兰人不仅借助外来语philosophie来表述“哲学”这一外来概念,而且同时也在使用“爱智学”(wijsbegeerte)这一概念,或许这也是西周与津田在翻译philosophy之际会联想到《通书》的缘故之一。
“希哲学”或者“求圣学”这样的翻译,并非是西周或者津田各自思考的产物,应该说是二者之间彼此交流讨论的一个结果。不过,西周在《百学连环》之后基本采用了“哲学”这一翻译语,与之不同,津田在1874(明治7)年的《明六杂志》第3号出版的《论推动进化的方法》一文之中,依旧使用了“希哲学”这一翻译语。[1]20这或许是由于津田认为这一翻译语保留了哲学原意,更为贴切合适吧。
从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在“希哲学”、“求圣学”这样的概念之外,日本人还尝试了“究理学”、“性理学”、“理学”、“理论”、“玄学”、“知识学”等各种各样的翻译。在这之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是“理学”这一概念。这一时期,大多数的语言学辞典将philosophy翻译为“理学”⑥,明治初期的流行读物——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之理》(中村正直译,1871年)之中也将它翻译为“理学”。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日本人是将哲学与宋学糅杂在一起加以理解的。
宋学的开山之祖周濂溪(1017年-1073年)强调“太极”,朱子(1130年-1200年)将它视为“理”,也就是理解为各个现象(气阴阳)的存在根据,或者各个存在的普遍原理,并以这一概念为基础来谋求儒学的新发展。正是因为这一学问重视“理”这一概念,因此宋学才被称为“性理学”或者直接称为“理学”吧。因此,将philosophy翻译为“理学”的人,大概是找到了“性理学”或者“理学”与哲学的共同之处,故而选择了这一概念吧⑦。
但是,西周却没有采用这一翻译,而是始终遵循“爱知”的本意,将philosophy翻译为了“希哲学”,而后不久就翻译为“哲学”。根据现存资料推断,西周第1次采用“哲学”这一翻译是在1870(明治3)年所写的《复某氏书》。西周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传闻是为了批判国学家大国隆正(1793年-1871年)及其弟子的立场。大国隆正与西周一样来自津和野,且活跃在幕府末期至明治维新时期。这篇文章之中,西周记载道:“大概孔孟之道与西方之哲学相比大同小异,犹如东西彼此不相因袭而彼此相符合。”同年,西周开始讲授《百学连环》,尽管他也提到“亦可从事希贤学”,但是基本上开始使用“哲学”这一概念。
西周在正式的出版物之中第1次正式将“哲学”公之于众,是在1874(明治7)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之中。所谓“百一”,就是西周主张的“考究百教之趣之极意,归于同一之趣意”。在此所谓的“教”,并不是指宗教,而是指作为“治身之道具”的“人道之教”,也就是道德。西周认为,这样的“教”存在着国家的差异,但是其核心则是一致。到了《百一新论》的最后,西周提到:“参考个样(“物理”、“天然自然之理”),征于心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之方法,即为ヒロソヒ一,翻译之名为哲学,乃西方自古既有之论。”⑧
“哲学”这一概念不断传播,而后被确定下来。在这一过程中最终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则是1877(明治10)年东京大学创立之际,文学部设置“史学、哲学及政治学科”。之所以选择“哲学”这一概念,乃是为了区别于同时设置的“理学部”⑨。
井上哲次郎(1856年-1944年)编撰的《哲学字汇》(1881年)一书为哲学术语的确立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这部辞书的标题所示,“philosophy”基本上被翻译为“哲学”。但是,令人感兴趣的是,“理学”这一翻译术语也同时并用。“Critical philosophy”被翻译为“批评理学”、“Practical philosophy”被翻译为“实践理学”⑩。在这之后,中江兆民于1886(明治19)年出版了费歇尔(Alfred Fouillée,1838年-1912年)《哲学史》的翻译——《理学沿革史》与哲学概论《理学钩玄》。在此,“philosophie”依旧被翻译为“理学”,由此可见,理学与哲学的两个翻译语长期以来一直是并存的。
三、区别于儒学的“哲学”——西周理解的“哲学”
之前提到,西周没有将philosophy翻译为“理学”,而是始终遵循“爱知”的本意,将它翻译为“希哲学”,而后确立为“哲学”。不过,就日本的儒学传统,而且就西周本人的知识素养而言,西周应该说也有极大可能会选择“理学”这一翻译。那么,西周为什么会选择“哲学”这一翻译呢?
西周的意图究竟何在?为此,我认为《生性发蕴》的这么一段话可以成为我们思考的线索。西周提到:“尽管可以采取直译的方式将之翻译为理学、理论之类,但是由此却会过多引发与他者之间的混淆,故而如今翻译为哲学,与东洲之儒学一分为二。”也就是说,西周尽管承认将之直译为“理学”、“理论”比较合适,但是却认为这也容易产生混淆,故而选择“哲学”这一概念。所谓“混淆”,也就是西周考虑到它会与儒学混同在一起(11)。
那么,西周为什么要避免与儒学混同在一起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来了解一下西周究竟是如何来理解西方的哲学。
承前所述,西周在《复某氏书》之中提到:“大概孔孟之道与西方之哲学相比大同小异,犹如东西彼此不相因袭而合乎符节。”在此,儒学与哲学之间尽管没有什么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是基本上拥有了同样的内容。西周的《开题门》一文,亦被推断为这一时期撰写的作品。在此之中,西周也强调了这一旨趣。“东土谓之为儒,西洲谓之为斐鹵苏比,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12)也就是说,在明确一切存在的理法、树立道德之原则这一方面,哲学与儒学完全是一致的。
但是,到了1870年开始的《百学连环》的教学之际,西周强调哲学区别于儒学,乃是西方自身的学问。他提到:“正如此编(神理学=神学)所述,乃是按照和、汉、西方的顺序来加以阐述,而到哲学这一章节,则是以西方为先。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我国尚无可称之为哲学的存在,即便是中国(汉),也无法与西方相比。”在宗教这一部分,西周以日本为先开始了阐述,但是与此不同,到了哲学这一部分,西周认为,东方没有可以与西方之哲学相媲美之物,故改变了叙述的顺序,转而以西方为先。
不言而喻,西周应该说也意识到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通之处。西周承认,在被翻译为“名教学”的伦理、道德的学问,也就是Ethics这一领域,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容的重叠,“所谓名教学,汉称之为儒学,与西方大处皆是一致,小处则略为存在差异。”之前曾述,即便是在《百一新论》之中,西周也提到“人道之教”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其内容皆“归于同一之趣意”。就伦理学而言,尽管东西方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但是西周认为其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到了其他的领域,西周认为东方却没有什么值得与西方可比较之物。宋学所谓的“理”,是探讨一切存在的根源或者依据,我们也认为它与西方哲学完全具备比较抗衡的可能性。但是,为什么西周会提到“无法与西方相比”呢?
西周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异。在《百学连环》之中,西周对此进行了如下的阐述:“哲学在东洲称之为儒学,此儒学之根本在于邹鲁。自邹鲁以来的学者们形成孔孟学派,连绵不绝,更无变革。西洲之学者,尽管亦是自太古以来连绵承续其学问,但是却依照各自之发明,讨伐前人学者之学说,唯采纳其不可动摇者,故而得以逐渐推陈出新。”
西周认为,儒学的特质在于将“真理”置于儒学之起点的孔孟之说,进而追求代代相传,永以为继。儒学的这一特质,在此我们可以援引伊藤仁斋(1627年-1705年)的一段话来加以论证,伊藤提到:“论语一书,万世道学之规矩准则,其之言,至正至当。”(13)一语道破了儒学的真理观。
与之不同,西周认为,西方的学问之中,“真理”的获取与东方的儒学处于截然不同的立场。西方也强调历史传统,没有历史传统,学问也无法得以成立,但是,西方学问的根底却并不是以遵循传统作为前提,倒不如说它的真理观念乃是通过施加批判与检验,由此才能把握事物的真相。也就是说,真理始终是存在于发展之中。
在将东方与西方的学问观念对比之际,西周认为儒教的根本问题在于墨守前人之学说。西周认为,“汉儒”最为不良之处“即在于泥古二字”,也就是以“泥古”二字来强调“汉儒”将真理的基准置于祖述学说的态度,并指出它与学问的精神不相兼容。西周之所以在哲学与儒学之间明确划出一条线,将二者截然区别开来,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也正因为如此,西周没有采取“理学”这一固有概念,而是创造出了“哲学”这一新语。
尽管如此,西周也并非是要全面否定儒学。西周提到“汉儒”最为不良之处“即在于泥古二字”。但是,在这一段文字之后,西周提到:“因此若是在其顶上施以一针,则必然开化,足以与西方一较高下。”也就是说,西周确信,儒学无须墨守祖宗之言,而是批判性地去加以探讨,由此找到新的真理,只要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努力,就有可能成为足以与西方哲学相匹敌的思想。
在此,顺便也要提一点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即西周并不是针对西方所有的哲学皆给予同等的评价,而是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之前我们提到《开题门》,西周写道:“宋儒与理性主义(rationalism)之间其学说尽管有所出入,但所见则颇为相似。唯至晚近,实证主义思想论据确实,辩论明哲,将大有助于辅助后学,是我亚细亚未曾见者也,奥古斯都·孔德(Auguste Comte)实为首倡之人。”[2]54
西方近代自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合理主义哲学或者观念论哲学,被称之为了nationalism(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宋学可以与之并列。二者皆非是基于“实物”来加以检验,注重积累“实知”,正因为如此,西周认为“其论虽大,其语虽详,而其裨究竟几何?”
西周留学欧洲之际,在荷兰占据重要地位的哲学思想,就是孔德的实证主义与边沁(Jeremy Bentham)、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西周留学之前,尽管接受了笛卡尔、黑格尔的若干知识,但是最为深刻的影响却是来自孔德等一批人的新思潮。西周在1875年发表的《人世三宝说》之中提到:“孔德之实理学(positivism)兴起,颇多令世间耳目一新之见识,诸位大家之说大多逐渐基于实理。”在《百学连环》之中,西周也阐述道:“到了当今的穆勒氏,乃至一切学问大为开启。”
西周反复强调孔德的3个阶段的发展规律,同时也代表了其对于奥古斯都·孔德所作出的高度评价。《百学连环》的“总论”之中,西周还进行了如下阐述:“近来法国的Auguste Comte所发明的术语之中,所有一切事物不管如何最初皆是不大顺利的,其后逐渐登上stage——翻译为舞台或者场,这样的场包括了3个,可以说是从一开始的第一个过渡到第二个,最终抵达第三个。第一个场就是theological stage,即神学家;第二个是metaphysical stage,即空理家;第三个是positive stage,即实理家。总之,不管涉足第一、第二的时间长短如何,或者抵达实理之场是慢还是快,若是没有涉足第一场、第二场,则断无抵达实理之第三场之途径也。”
《百学连环》之中,西周首先排斥了一种非学问的态度,也就是“臆断(prejudice)”与“惑溺(superstition)”。所谓的“合理论者”与“宋儒”的学说正是因为它们是以“臆断”与“惑溺”为基础的“空理”,故而遭到西周的排斥(14)。“空理”不足以成为“真理”,只有基于确切的论据与明快的推论的“实理”(positive knowledge)才值得赋予“真理”之名,这也正是支撑西周百学连环的思想源泉。
不仅如此,针对“空理”与“实理”之间的区别,西周还分别强调了“演绎”(deduction)与“归纳(induction)”——西周翻译的术语——的思维方法来加以对应。所谓“演绎”,就是从唯一的一个根据来引导出所有事物的方法。西周批评指出,正是因为演绎之方法,故我们难以脱离这一框架,容易陷入到“固陋顽愚”之中。而且,这一方法以文献为线索,也就容易为文献所禁锢。作为改革之方法,西周注意到穆勒提出的“归纳”。西周指出,我们通过五官来把握具体的经验,以此为出发点,也就是通过经验的方法才是走向“实理”的有效手段,才有可能开启新的学问。这一方法也就构成了西周的学问观念的基础。
不过,西周在《开题门》之中也提到:“穆勒之名冠盖一时,唯此学之兴,时日尚浅,故若是张扬规模,详悉目次,以致其盛,其任将在后人。”也就是说,西周认为,确立了这一发现真理的新的方法,在此之上构建学问,乃是现代性的课题。之前,我们提到西周认为儒学也需要“在其顶上施以一针,则必然开化,足以与西方一较高下”。应该说西周正是考虑到实现这一现代性的课题的可能性,故而才会提到儒学的“开化”的问题吧。
四、作为“理学”的哲学——中江兆民理解的“哲学”
无论是在《理学沿革史》或者《理学钩玄》之中,还是在去世之前出版的《一年有半》或者《续一年有半》(1901年出版、明治34年)之中,中江兆民皆一直将“philosophie”翻译为“理学”来加以使用。三宅雪岭(1860年-1945年)在《哲学涓滴》(1889年、明治22年)之中曾经提到:“哲学这一术语如今成为了普通词语,即便是商贾之人亦称哲学如何。”[3]也就是说,到了明治20年前后,“哲学”这一概念也已成为“常用词语”。那么,为什么中江兆民却还一直使用“理学”这一翻译语呢?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就是中江兆民的学问观念,与西周、津田真道等所代表的、以“明六社”为中心而聚集在一起的、一批明治初期启蒙思想家们的学问观念之间存在着截然的不同。
承前所述,西周采取“空理”与“实理”的表述方式来突出东方与西方的学问特征。儒学“鲜有可引导至真理者”,只是重复于文献的解释,乃是欠缺“实验”(观察与体验)的“空理”。而且,津田真道也在《论推动进化的方法》之中以“虚学”与“实学”的概念来区分二者的特征,“夫论高远之空理虚无寂灭,犹如五行性理,或良知良能之说,虚学也。征之以实物,质之以实象,专说确实之理,犹如西方之天文、格物、化学、医学、经济、希哲学,实学也。此实学国内普遍流行,各人明达道理,可称为真文明界。”[1]306西周与津田皆是具有高深的汉学素养之人,其思想也是在这一基础上来接受西方思想。但是,他们却将东方的佛教、儒学的世界观、道德论视为缺乏具体经验的空论,而将西方的学问视为立足于确切论据之上的“确实之理”,从而将二者区别开来。其根本,大概就是考虑到只有对二者进行明确的区分,才有可能真正地“推动进化”吧。
与之不同,中江兆民则只是评价了其中之一,或者说没有将二者的区别加以绝对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学问并不能以“虚学/实学”这样的二分法来加以区别或者归类。西方与东方的学问,不应该在二者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来加以区分,而应该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来将它们视为为了学问的发展应该做出贡献的资源来加以对待。
中江兆民留学法国期间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思想,通过将它们介绍到日本,从而为过去将穆勒与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自由论、代议政治论为理论出典的民权运动家们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尤其是经过中江兆民而介绍到日本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为不断高涨的民权运动带来巨大的影响。正如其《社会公约论》第1编第1章的起始部分“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5)这一段话所示,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之根本,也就是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以这样的“自由”观念为核心,中江兆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1881(明治14)年,《东洋自由新闻》发刊之际,中江兆民作为其主笔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论说,其第1号《社评》之中,中江兆民针对“自由”指出它是由libertè morale与libertè politique所组成的,而且,libertè morale才是人类活动整体的“根基”(16),中江兆民提到:“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17)这一理解无疑是以卢梭的“自由”为基础的,但是同时,中江也尝试对于儒教式的伦理加以解读,提到孟子所谓的“配义与道之浩然一气”(《公孙丑篇》)也是libertè morale。不是为欲望所驱使而展开行动,而是自己制定法律,且自我顺从于它,这样的人心之“余裕”,中江兆民认为它与“浩然一气”彼此相通(18)。
中江兆民为了让“自由”这一概念在日本扎根,因此不得已才采取了一个便捷的方式来阐释它,即通过传统思想来予以解读。但是在此,我们必须提示的一点,即中江的确坚信东方与西方思想之中存在着彼此相通之处。中江在一篇被推断为1875年撰写的草稿(《策论》)之中记载:“西土的道学,以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为根本,进而论述贤德之道,不外仁义忠信,兆民在欧地阅读其书,诚知斯道古今远尔,确乎不易。”在此,中江尽管只是阐述了道德的观念,但是他却认为东西方共通之处绝不止于道德论。《一年有半》之中,中江指出民权思想也绝非是欧美独有之物,“民权是至理也。自由平等是大义也。反对此等理义者竟然能不予受罚。……虽为帝王之尊,而敬重此理义,兹可得以保其尊也。此理在于汉土,孟轲、柳宗元早已一语道破,非欧美之专有也。”
中江兆民的思想特征之一,即在于他并没有将东方与西方的思想放置在各个不同的文脉之中来加以理解,倒不如说是关注到了贯穿二者的普遍性的思想[4]9。就中江而言,关注西方思想并不是一味地接受西方思想,同时也意味着要关注到贯穿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同时也还是作为特殊而存在的、带有了普遍性的西方思想。
中江兆民采取这样一个态度,并不是意味着他认为西方没有什么值得学习之处,倒不如说中江兆民同时还深刻地认识到东方思想的不足之处。之前引用的《策论》之中,中江提到:“父子相爱,兄弟相亲,英法贤于我乎,无贤也。有上下尊卑之礼,英法贤于我乎,无贤也。彼所贤于我者,只有技术与理论而已。”不仅如此,中江还留下了一段名言,“我日本自古至今无哲学”。所谓“无哲学”,可以说同时也反映出日本在经验的理论化这一方面存在着不足之处。
中江认为,正是在克服理论的缺失这一方面,欧洲的哲学应该成为日本的典范。他之所以翻译维隆(Eugène Véron,1825年-1889年)的《美学(L'esthétique)》(19)与费歇尔的《哲学史》,也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但是,中江并不是无前提地、对于欧洲哲学皆采取肯定的态度。西周高度评价“论据确实,辩论明哲,将大有助于辅助后学”的实证主义哲学,兆民在《续一年有半》之中对它进行了批判,指出:“该派看起来依据极为确切,但是过于拘泥于现实,即便是皎然明白之道理,若是未能通过实验以确证,皆予以抹杀,因而其自身日益狭隘,陷入固陋,其弊将大为歪曲吾人精神之能力,乃至自减声价。”换而言之,中江认为,即便是未经科学论证的东西,被视为不可动摇的东西,或者在道义上应该被加以认可的东西,皆应该是存在了的事物。若是将它们一概排除,那么就会不恰当地矮化我们人类自身的能力。
就这样,中江兆民对实证主义哲学提出了批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不曾利用“虚学/实学”的二分法框架将东西方的思想加以区分,并采取排除一方的态度。倒不如说,正是在排斥这样的框架这一点上,中江兆民始终坚持着自身的立场,就应该做出评价之处展开了自己的评价。对于他本人而言,可以说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虑是否会“与他者混淆”,进而言之,也就完全没有必须去创造“哲学”这一新的术语了。
注释:
①Hubert Cieslik:《府内のコレジヨ——大友宗麟帰天四百周年によせて(府内的神学院——大友宗麟归天四百周年)》、「キリシタン研究」第27辑、第101页。
②《サントスの御作業》印影篇(勉诚社,1976年)第2卷,第328—329页,翻字篇(勉诚社,1979年)第2卷第318—319页。《日本哲学思想全書》第1卷“哲学篇”之“解説”(三枝博音)第3页。参考茅野良男:《近代日本の哲学とドイツ観念論》(茅野编《ドイツ観念論と日本近代》、ミネルウア書房、1994年)第12页。
③高坂史朗:《新しい世界を求めて——西周と才ランダとの出会い》,岛根县立大学西周研究会编:《西周と日本の近代》,ぺりかん社,2005年,第62—64页。原文收录在Gerhart Vissering,De Troonbestijging van den Keizer van Japan.De relatien in ouden tijd van Holland tot Japan.Amsterdam,blz.6—8.
④西周的著作引用来自《西周全集》(宗高書房,1981年)。
⑤西周为津田真道《性理论》撰写的跋文之中,提到“西人论气则备,论理则未矣”,触及了世人针对西方学问的评价。所谓“论气”,是指探索具体的各个事物或者与之相关的学问;所谓“论理”,则是探索整个存在根本原理或者伦理道德的原则,或者与之相关的学问。参考《西周全集》,第1卷第13页。
⑥以堀达之助等人编撰的《英和对訳袖珍辞書》(1862、即文久2年)为例,philosophy被翻译为“理学”、“Natural philosophy”被翻译为“究理学”。柴田昌吉、子安峻编撰的《附音挿図英和字彙》(1873、即明治6年)之中,也罗列了“理学、理论、理科”等译名。顺便提一下,“science”一语的翻译,前者翻译为“学问、技艺”;后者翻译为“学艺、学问、智慧、知识、博学”,还没有采用“科学”或者“理学”的译名。
⑦中国最早详细介绍西方学问的人,则是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著述的《西学凡》。不过,他所提到的“斐録所費亜”被翻译为了“理科”或者“理学”,参考斋藤毅:《明治のことば——東から西への架け橋》,讲谈社,1977年,第317页。
⑧西周自荷兰回来之后,第2年就在京都开设了私塾,讲授西方学问。在这一段时间,后人推测西周撰写了《百一新论》的讲义。但是,西周在这一时期是否开始使用“哲学”这一概念,则无从知晓。
⑨东京大学的前身——大学南校设置了理科,且与法科、文科、兵科一同对待,而后,“理学部”这一名称作为它的继承者而被确立下来,大学南校之中的文科设立了“性理”这一领域,也就是相当于“哲学领域”的学问。
⑩《哲学字彙》之中,“science”被翻译为了“理学、科学”。
(11)西周在《生性発蘊》之中原本也将theology翻译为“神理学”,将metaphysics翻译为“超理学”,并非是不曾使用“理”这一概念。
(12)西周在此没有翻译philosophy,而是直接标记为“斐鹵蘇比”,由此可以推断,西周大概是在留学荷兰之际就开始撰写《開题門》一文。参考莲沼启介:《開题門の成立事情》,《神戶法学雑誌》,第30巻2号、3号、1980年。
(13)伊藤仁斋:《論語古義》,佐藤正范校,六盟馆,1909年,总论第6页。
(14)西周在明治15年执笔撰写的《尚白劄記》之中,针对宋学进行了这样的批判。“宋儒不管什么皆谓之天理,认为自天地风雨之事至人伦之事皆存在了一定不变的天理,与此相违背者,则确定为背离天理,实可谓是书生之见也。由此而陷入疏谬之中,徒生妄念之想,以为日月之蚀、旱魃、洪水灾害皆与人君之政治密不可分。”
(15)Jean-Jacques Rousseau,Du Contrat Social et autres oeuvres polotiques.Paris 1975:236.
(16)中江兆民的著作引用,参考《中江兆民全集》(岩波書店、1983-1986年)。
(17)Rousseau,Du Contrat Social et autres oeuvres politiques,Paris,1975:247.
(18)中江兆民究竟是如何来理解这一概念,可以参考拙文,《“日本古ょり今に至る迄哲学無し”——中江兆民》,藤田正胜编:《日本近代思想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世界思想社、1997年,第45页。
(19)该书标题为《维氏美学》(上、下)在1883、1884年经文部省编辑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