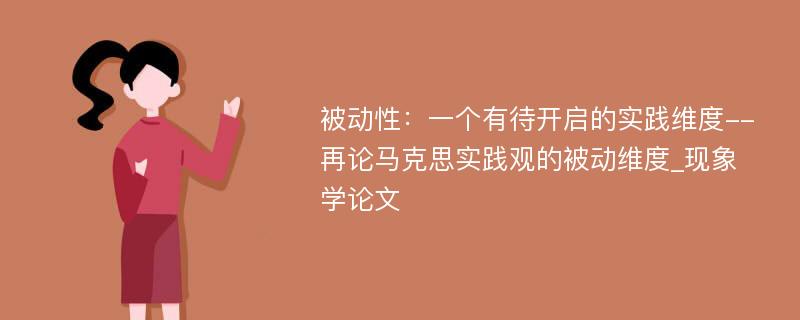
受动性:一个有待开启的实践向度——马克思实践观的受动性之维的再揭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受动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0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245X(2010)06-0062-06
一、“受动性”的“隐”与“显”
长期以来,就实践理解为“一种体现着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客观过程”[1]或“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2],业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从中也充分体现了人们对能动性的重视程度及其在实践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就其对“受动性”的忽视(如上述两种理解)或误读(如“受动性是指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受外界自然和社会制约”[3]),进而导致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内在分裂,笔者则不敢苟同。这种要么将受动性“附属于”能动性(从动于能动性),要么将受动性“庸俗化”为“消极性”(相对于能动性的积极性),无疑是传统“主客二元”范式的现代“隐喻”。现代性的风靡似乎是这一范式的现实:理性主体在启蒙运动的大潮中高歌凯进,为自身建构起现代的“合理化”的社会的同时,却以感性主体的压制为代价,进而将其“宰制”其中,使“人变成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变成“无家可归”的“牢囚”。殊不知,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就深中肯綮地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但是,这些对象是他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4]。可见,在马克思那里,受动性与能动性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的特性,二者不但被赋予同等的重要性,而且被须臾不可分离地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原因在于,在实践活动中,能动性与受动性是一种互动、协同的关系,并且,受动性作为人的不断增长着的“本质力量”(能动性)的“策源地”,因而亦具有了“根源性”和“积极性”的意蕴。
二、马克思实践观的受动性内涵
在《手稿》中,马克思将实践活动理解和表述为“感性活动”。而感性活动最本质地表现为感性对象之间的对象性活动。这种感性对象性活动并不是“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通过对象性的产物“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4]105。因此,它是感性的自然存在物之间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对象性活动。同时,也正是在这一活动中,受动性的本真内涵才得以显现。
(一)受动性——感性(活动)的客观现实性之源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站在新实践观的高度,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予以彻底地批判和清算,找到了二者的共同症结在于使“活生生的、具体的”感性(活动)丧失了客观现实性的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在《精神现象学》中,实践(劳动)是黑格尔的核心概念,但囿于意识哲学的思维范式,仅将其理解为“一种观念的外化和回收的对象性的活动”[4]111。并认为这种外化和回收就是“和自身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即感性的现实,从而认为自己的活动就是感性的现实活动”[4]111。殊不知,这种外化和收回并不具有现实性的内容,“对象对于它来说已成为一个思想的环节,所以对象在自己的现实中也被它看作思维本身的即自我意识的、抽象的自我确证”[4]112。费尔巴哈不满意这种“观念”(唯能动性)的活动,而诉诸“感性”的活动。但是,在他那里,人与对象的关系仅仅是一种“直观”(唯受动性)的感性关系,而非对象性活动的感性关系,即“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5]16。
为了克服黑格尔感性活动的“观念”性和费尔巴哈感性活动的“直观”性,马克思将感性活动奠基于感性对象之间的对象性活动。马克思指出:“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这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对象。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是说它是受动的”[4]10。正是因为人“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4]107。可见,在马克思那里,“感性”已不像在传统哲学中那样,或是人的一种先验的认识能力,或是人的一种机械的感官功能,而是人的一种对象化的本质力量。它并非源于先验的“认识形式”,或直观的“镜像图式”,而是源于客观现实的对象之间的对象性(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并且,“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4]107,而是在这种不断地对象性活动中顺应(受动于)对象而(能动地)设定自身。因此,感性作为感性对象性活动的“本质力量”,不但具有客观现实性,而且具有“历史的目的性”[4]90。
(二)受动性——人的本质的丰富性之源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18。但是,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终将遭遇“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武器的批判”。因此,人的本质既受动于社会关系,又在社会关系的批判中完善自身,兼具主体属性和客体属性。
一方面,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类存在物,更重要的是社会存在物,并且,“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4]83,“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4]83。因此,人的本质表现为客体属性,它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但是又并非是费尔巴哈式的自然属性——“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5]18,和黑格尔式的社会属性[根据美国学者威廉姆斯的分析,在黑格尔的“相互承认”的思想中,确证的并不仅仅是一种不平等的主奴二阶关系,而是一种包含了我——你主体间出现的第三者——我们的三阶关系。这个“我们”是这种双向承认过程的产物。作为具体的普遍,它包括它的成员的联合行动,也是这个联合行动(双向承认)的结果[6]。]——“抽象的、形式的、思维着的本质,即自我意识”[4]113,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客体主体化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中不断生成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这种对象性活动中,对象的性质之所以能成为人的性质,首先在于人与对象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因为迄今为止,无论是五官感觉,还是精神感觉、实践感觉,即“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4]87。并且,对象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对象,则在于对象的性质与人的本质力量的性质之间的适应性(受动性与能动性)的发展程度,就像对于没有音乐感的人来说,美丽动听的音乐与他毫无意义。正是在这种相互适应(对象化)的过程中,作为人的本质的客体属性才不断成为自然的和社会的。
另一方面,“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4]107,“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4]83。正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生成”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中,作为人的本质的另一属性——主体性方得以彰显。在感性对象性的活动中,“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成,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5]77。并且,这种“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它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对象成为它自身”[4]83。但是,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在对象性活动的过程中,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4]105。人之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4]105。正是在这种相互设定(受动与能动)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中,作为主体属性的人的本质才不断得以丰富起来。
(三)受动性——人类社会自然性的源泉
在马克思看来,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还都不是人类“社会”的历史,都不过是人类社会的“史前史”,这一史前史的结束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终结为标志。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是财产私有制,只有“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4]82。
但是,这种“扬弃”又不是“粗鲁的共产主义”和“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那种“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4]79的扬弃,而是对产生它的世俗基础的扬弃。而私有财产源于异化劳动[4]79,异化劳动源于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异化关系[4]50-63,异化关系源于感性异化,感性异化源于对象之间受动性的物化[4]85-86。也即是说,“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4]82。因此,物化的感性关系(受动性)正是私有财产最本质的世俗基础。而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统一于能动性和受动性的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4]105。因此,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中,人的能动性应当统一于自然存在物的感性对象性关系的受动性,而非统一于物化的感性对象性关系的受动性,活动本身对人来说应当是一种享受,而非强制。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自然、社会之间的感性关系正是这种“自然存在物的感性对象性关系”的异化(物化)。因此,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运动看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否定的否定的肯定”,所肯定的正是这种扬弃了异化的“自然存在物的感性对象性关系”。
正是在这种肯定中,“人同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4]80。正是在这种肯定中,“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良上对他说来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4]80。正是在这种肯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正是在这种肯定中,“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81。
三、受动性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体现
面对西方近代自然(主义)科学对哲学领地的“蚕食”,及其基础的非科学性的困境,将哲学构建为一种“严格的科学”成为20世纪欧洲哲学的“憧憬”。在胡塞尔看来,要使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即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根本的任务是拒绝自然主义(态度)的科学观念,“面向事情本身”,以回溯到传统科学及其逻辑工具在直接经验中的“前意识”根源。即将一切“自然态度”和“逻辑观念”予以“悬置”,将意识还原至“纯粹意识”这一“彻底经验”状态,并以此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哲学基础。基于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才是作为基源性的“包含着一切感性的丰富性的‘知觉’王国,它无一遗漏、不带偏见地将感觉、表象、想象、信念、苦乐体验、情感、意志等等,总之将一切直接向我们呈现出来的东西尽收眼底,并将它们都看作具有‘意向性结构’、因而具有自己的‘意向对象’的意识现象”[7]。这样,胡塞尔通过以直接经验(感性)的“现象”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通过对意识活动中的“意向性”与“意识物”之间的互动(受动与能动)关系——感性活动中的对象性与感性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揭示,以及在直接经验的直观中对人类意识和精神现象的内在本质结构的把握,不但与传统科学主义(自然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也与唯心主义(唯受动性)和旧唯物主义(唯受动性)划清了界限。但是,由于胡塞尔的上述现象学“活动”仍然是在意识哲学的范式内展开的,他所谓的“悬置”后的直接经验依然带有浓厚的“先验”色彩,所谓的“事情本身”并非“本来的事情”,而是一种柏拉图式理念的超验本质的设定。尽管胡塞尔晚年认识到科学的最初前提应该在科学之外的“生活世界”,但是经过“历史的还原”所得到的生活世界的经验仍然是先验的。这样,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依然落入了先验哲学的窠臼。
这一窠臼的“缺口”首先是由海德格尔来打开的。虽然海德格尔依然把“面向事情本身”视为现象学的根本路标,但它的内容却是存在主义的,即“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8],也即这个显现事情本质的任务是由“此在”来完成的。并且,“此在”的存在是一个在“时间”上连贯显现自己的过程,是一种从“顺应”世界(沉沦态)到“规划”世界(生存态)的无限过程,也即是一种“受动”与“能动”相统一的无限过程。这样,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就是用“此在”这种“感性”的存在者来展现曾经被遮蔽的、“祛身性”的存在,从而实现了从胡塞尔“祛身性”的先验现象学向“具身性”感性现象学的转换。然而,海德格尔囿于西方个人主义的偏执,虽然将“此在”视作是一种“在世之中的存在”,但认为日常生活的“共在”只能带来“此在”的异化和沉沦,因此他更执迷“此在”的本己性和向我属性。可见,海德格尔的感性现象学虽然走出了先验现象学“祛身性”的阴影,却依然没能使其摆脱“独白”的命运。但是,就其现象学的感性生命之维,无疑成为现象学运动的“路标”和后现代主义的“先锋”。之后的存在主义(如萨特、马塞尔、梅洛·庞帝和雅斯贝尔斯等)、解释学(如伽达玛尔和利科)、宗教—伦理学(如列维纳斯)及美学(如茵加登)等无不是沿着这一路向对现象学进行拓展、深化和运用的。之后的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对“性”、“癫狂”等的非理性的肯定,利奥塔对通过“元叙事”的方式而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主义的批判,波德里亚对“物体系”符号化本质的揭橥,无不是对理性(能动性)的“越俎”而招致现代性悖论的痛斥,无不是对感性(受动性)的“召唤”而向后现代性的回归。此外,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囿于受动性和能动性的偏执而形成的对抗,又无不体现了中国儒道两家“践行”观的差异。
中国古代实践观是一种生命“践行”观。儒道两家兼以现实的感性生命为前提,展开身体的思考与实践,以标举理想生命来克治实存之负累。但在具体“践行”的路向上,又迥然有别。儒家重生厚生,崇尚“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当厚德载物”(《易经》)。生命操行,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践行”之路,以追求“内圣外王”、“游方于内”的德性生命。它着重于实践活动的能动性。道家重天性本然,推崇“无为”、“无待”的自然生命境界,通过“徇耳目而内通”的“践行”路径,以实现“游方于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自然生命。与儒家相比,道家的“践行”观着重于实践活动的受动性,
在道家看来,实存世界是一个“异化”的世界,处身其间的人“受动”于之而悖道失性,官能知觉因之而对形躯、情欲和心智之身的迷执,进而陷入了“为身所累”困境:“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姆》)。
为了摆脱“为身所累”的世俗困境,道家选择了“以道观之”的路向,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的“回归”之路。这是一种逆向、反致和虚化的过程;是一种实存之身自然化,自然之道身体化的过程;是一种“与物同理”、“与物终始”(《庄子·则阳》)的过程。通过对“世俗之身”进行“存而不论,宽而不迫”,进而使其“效法自然,顺应自然”,以至于“知止其所不知”(《庄子·齐物论》),“至于无为”(《老子·四十八章》)的“自然之身”。即庄子通过“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庄子·大宗师》)的“坐忘”功夫,“外天下,外物,外生”(《庄子·大宗师》)的“撄宁”功夫,以及“耳止于听,心止于符,唯道集虚”(《庄子·人间世》)的“心斋”功夫,进而臻于一种虽“视乎冥冥,听乎无声”,但“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庄子·天地》),自然之身与自然之道相感通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一种想象和联想的创造之物(源于感性受动性基础之上的能动性之物),而非柏拉图式“模仿”和“分有”的必然之物(源于理念能动性基础之上的受动性之物),即胡塞尔的“意向性”之物,萨特的“前反思的我思”之物,梅洛·庞蒂的“前语言学的或前逻辑的野性的感觉”的创造之物。这种境界是一种“无为”的境界,但并非是一种消极遁世的“无所作为”,而是一种“顺性而为”、“顺物而为”、“顺世而为”的“无为而无不为”,即庄子所谓的“内直而外曲”的处事原则,也即感性活动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原则。它象征了一种顺应、柔弱的女性化(受动)精神,即列维纳斯的“异域”之境,而与征服、刚劲的男性化(能动)精神相对应,是一种对唯理性主义的反叛和纠拨。这种境界又是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庄子·逍遥游》)的天、地、人相互“感通”之境,即现象学在“纯粹意识”中消融对象的“直观”之境,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之境,是一种对传统西方哲学主客、身心二元论的克服与消解,但又与唯心主义“抽象思辨”和旧唯物主义“感性直观”的消解方式判若有别,而是在生命“践行”(感性对象性活动)中所实现的主客、身心的和解,并且与儒家“下学而上达”、“日用即道”的实践精神共同铸成了中国哲学“显微无间”、“体用不二”的实践存在论特质。然而,囿于价值取向的不同,儒道两家的“践行”之路又各有所重。但是,这种差异,甚或对立,又无不是一种互补,无不潜藏着中国《易经》思想的“阴阳两仪、创生道”的玄妙。诚如钱穆先生所言:“惟道家原其始,而儒家则尤能要其终”[9]。
四、受动性“彰显”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哲学通过对一切唯心主义“观念实践论”和一切旧唯物主义“机械实践论”的批判,对实践予以“感性活动”的理解和阐释,对能动与受动关系的感性对象性关系的本质揭示,对受动性的积极性和根源性的彰显,无疑“把握了它的时代”,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的受动性的彰显,开启了现象学方法论之维。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现象学》“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4]101,成为黑格尔《哲学全书》的诞生地。然而,这种“辩证法”却是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自我意识的抽象精神”结束。它虽然“已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但是它“那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却始终以潜在的方式存在着。这样,整个历史不过是“思想的生产史”。感性的现实与抽象的思维的对立不过是“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人和自然界不过是“抽象思维的外化”,而终将作为“异化”而被“扬弃”。可见,这种非彻底性的“意识的经验科学”并未真正地触及到“事情本身”,而只是以颠倒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对事情本身的抽象意识和概念。而“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4]89-90。因此,马克思主张回到感性的对象性活动这一最基本的事实,以还原“事情本身”的本来面目。正是基于此,使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4]89-90——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意义,无不具有现象学“彻底经验”意义上的第一性的含义,但已是超越了胡塞尔意义上的“先验性”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封闭性”,而具有现实性和开放性。使感性活动的“对象性”与“感性对象”之间的受动与能动的关系,无不具有现象学的“意向性”与“意向物”之间的“交遇”与“构造”关系的意义,但已是超出了现象学意义上“意向性”的“意识性”和“意向物”的“意义性”,而具有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尽管如此,然而就“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在马克思实践观中的应用而言,则又是无可置疑的,这似乎也应验了现象学研究的前辈罗姆巴赫的话:“胡塞尔不是第一个现象学家,海德格尔不是最后一个现象学家。现象学是哲学的基本思想,它有一个长长的前史,并且还会有一个长长的后史”[10]。
其次,马克思哲学感性实践观的受动性的彰显,开启了现代性批判之维。现代性的理论基础是意识哲学,其精神实质是弘扬理性和主体性,其社会基础是技术的强制和资本的泛化。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作为近代意识哲学的完成,标志着主体性原则的确立。而黑格尔的主体就是“自我意识”,所以“在《现象学》中出现的异化的各种不同形式,不过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4]100。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作为自我意识的化身而具有独立的生命且掌控着人的思想和行动,资本逻辑作为理性逻辑而成为一切行动的原则和旨归。而资本不过是私有财产的抽象形式,同样源于感性的物化,即“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4]85。这样,这种物化的感觉(感性)作为资本逻辑的“本质力量”而成为资本增值的源泉,资本在这种“同一化”的逻辑中扮演着能动与受动的双重角色,从而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一种从属与奴役的关系,他人对我而言,变成了“从属于自我的他我”[11],变成了我的“商品”;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一种征服与掠夺的关系,单一的拥有感加速了人的“自然性”的泯灭,进而将“人类中心主义”奉为圭臬,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而对自然界豪取强夺,对“自然主义”堵截封杀;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规训和服从的关系,社会作为一种独立于人的“物体系”,商品的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等“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12],人的存在变得“整齐划一”,进而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因此,马克思指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4]85-86,从而使“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4]86,而“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4]81。由此可见,马克思对黑格尔意识哲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但击中了现代性的要害,而且为现代性的存在论转向开启了新的向度。
第三,马克思哲学感性实践观的受动性的彰显,开启了中西马对话之维。立足于感性对象性活动之上的马克思哲学实践观,不但厘清了能动性与受动性之间的内在关系,彰显了受动性的积极性和根源性的“特性”,而且似乎形成了一种“效应”。它不仅引发了西方现当代哲学革命的“风暴”,而且也与中国古代哲学发生了“共振”。究其根源,则在于共同的问题意识——理性主义执导下的社会的异化,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致力于异化了的感性的救赎与解放的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让我们领略到了马克思哲学感性实践观,与现象学“回到事情本身”的憧憬“志同道合”、与道家“以道观之”的进路“遥相呼应”、与后现代主义“人文关怀”的诉求“不谋而合”、与20世纪法国哲学“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趣味相投”的胜景,相互之间的“共鸣”、“对话”和“联袂”,共同编织成了一曲穿越时空(中西马)的和谐之声。
[收稿日期]2010-03-25
标签:现象学论文; 能动性论文; 社会属性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胡塞尔论文; 科学论文; 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