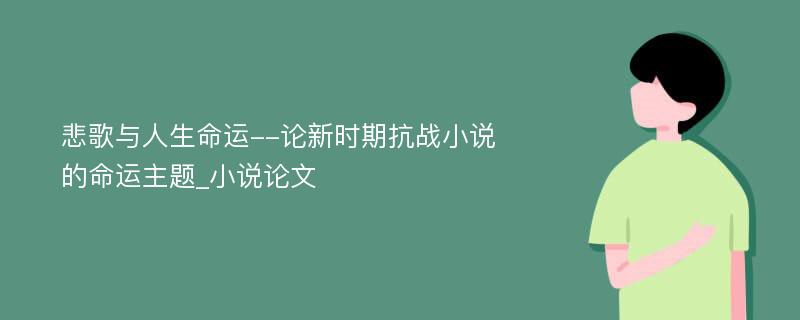
战争与人生命运的悲歌——论新时期抗战小说的命运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运论文,悲歌论文,新时期论文,战争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不充溢着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说,人道主义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而描写战争的文学,更应该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战争虽是一种社会群体行为,它的发生自有其深刻复杂的原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管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他们都必须面对战争,无法自我选择。因此,战争对群体社会来说,是一个至关重大的社会历史活动;对个体人生来说,却是一种生存困境。战争作为一种人生遭遇,从对个体生命形式、价值和意义的影响来说,都是一种损害和不幸。因此,战争文学应当把战争中的人、人的命运作为自己的重要表现内容。正如前苏联战争文学作家邦达耶夫强调的那样,“人——这就是永恒的、永远不会陈旧的、永远不变化和不受任何影响的主题。”(注:转引自陈敬泳《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小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这种人道主义的战争文学观,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小说的历史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苏联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出现了《一个人的遭遇》等对人的命运给予深切同情和理解的小说,以后又产生了《生者与死者》、《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继续这一人道主义主题探索的优秀小说,引起了世界性的反响。但是,在我们的抗战小说发展史上,却很少看到这种战争主题表现。即使个别作家偶有尝试,也都受到严厉批评。对许多人来说,我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却让主人公那样悲哀、痛苦,这是不可想象的。自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的。首先,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作为资产阶级哲学和文学思想,一直是思想界和文学界批判的对象,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还出现过大规模的批判运动,这自然影响了作家从人道主义立场上对人的探索。其次,战争的爆发,固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3500万人的死亡就是明证,但战争毕竟使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特别是由于战争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最终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独立、统一、自主的新中国,实现了无数革命先辈为之奋斗了百年的理想,因此,战争对中国人民来说,既是一场灾难,更是“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3页)。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来说,它对我们民族的重新崛起不无积极的意义。这就必然地使胜利的喜悦与战争的痛苦变得不平衡起来,人们更多地看到了群体成就的一面,而对个体的不幸相对漠视了。这和苏联的卫国战争有所不同。战前的苏联是一个新型的、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的生活和平而幸福。战争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一场意外的灾难,战争没有给他们带来一点有益的影响,所以人们有理由为自己的不幸而鸣不平,作者也更有理由对战争受害者给予理解与同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曾长期以苏联的战争文学为我们创作的范本,却几乎没有接受他们这种战争文学观念的原因。再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群体与个体,社会与个人是不平等的,有着主次之分的。在现实的社会利益和抽象的正义原则面前,作为人的存在、人的不可重复的生命,往往变得微不足道,也无可陈述。连极富胆识和批判精神的司马迁,写秦人坑杀赵卒40万,也不过一笔带过。因此在中国的战争文学中,个体的悲剧性遭遇,总是能够融化到民族和国家的喜剧性历史命题中。很少有人去关注一个普通人为战争所吞噬而造成的无可挽回的人生悲剧,更没有人为他们身后亲人悲* 的命运而伤心。
但是,随着战争历史的逐渐远逝,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以及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冲击,尤其是苏联战争文学的大量翻译介绍,作家们终于认识到,战争小说不能没有人道主义的精神观照。只有用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贴近战争中的人,去感受、体验、理解和同情他们的真实遭遇,才能够真正理解战争,理解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思潮推动下,关注人在战争中的悲剧性命运的抗战小说出现了。
2
命运主题小说首先关怀的是战争中普通人的不幸遭遇。
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社会活动。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战争的性质、目的、手段各种各样,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也自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战争,对普通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因为在战争环境里,人们无法把握自己,悲剧性的命运随时都会降临头上。这种源于外部强力而非自身因素造成的人生悲剧,不仅是个体的不幸,也是人类自身的悲哀。因此,对普通人悲剧命运的同情,不仅是对战争暴力的反思与批判,也是对人类自身生存方式的思索与关怀。
尤凤传的《生命通道》是一篇沉重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小说。小说中的苏原医生,似乎被一只冥冥之中的巨手所操纵,总也逃不脱命运的捉弄。他有自己的事业,还有新婚不久的妻子,却不幸被日军抓去,作了日军的随军医生。他不愿作汉奸,却无法不为日军服务;他为抗日事业秘密工作,却导致了妻子的误会出走;他杀死了日本军医,自己却永远背着汉奸的耻辱。小说以对其生存困境和人生选择设身处地的理解,真实地表现了一个被迫为敌人做事的人的身心痛苦和挣扎,为这个被迫卷入战争漩涡的小人物的不幸命运鸣了一声不平,如果苏原有知,他在地下也会向作家说一声“谢谢”!
战争带给人们的命运灾难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女人,她们的命运比男人更不幸。战争所施加给她们的不仅仅是死亡,血泪,更有不尽的屈辱和永生难忘的阴影。叶楠的《花之殇》、莫言《红高梁家族》以及贺景文的长篇小说《孽狱》都对被迫作了日军军妓的中国妇女的悲惨遭遇进行了真实的反映。然而战争所给予女性的痛苦并不仅仅是肉体上暂时的痛苦,更有精神上永远的伤痕。高建群的《大顺店》中被迫作了日军军妓的女子“大顺店”,虽侥幸活了下来,但在性变态的侵略军的非人折磨下,却“成了一个类无生物,一个白痴,一个被世人以轻蔑的口吻谈到的那种尤物”。抗战胜利了,她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于是,她成了伤兵、土匪、赌徒、烟鬼、乞丐等人组成的部落群共有的女人,一个女巫式的人物,热闹而又孤独地忍受着失去真正女人资格的自暴自弃、痛至心灵的苦恼与悲哀。叶兆言的《日本鬼子来了》中阿庆嫂,本来也是村里受人尊敬的妇女,却因一个叫三良的日军将她强奸以后,便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一辈子都没能卸下。“因为和日本兵睡过觉这一事实让人忘怀决不容易。”
这些命运主题小说,将普通人的命运展现出来,目的首先是为了暴露侵略战争的不义和侵略者的残暴,从而激发人们对战争的谴责与对和平的热爱。因为这些人的悲剧命运,无不来源于罪恶的战争。正是战争使无辜的中国人成了敌人解剖刀下活的“木头”(《生命通道》、《殇》),甚至成了日军用来练胆的活靶子(《漠野烟尘》、《白太阳 红太阳》);战争使无数的中国平民大片地死于敌人制造的鼠疫病菌(《法西斯菌》),又是战争,使中国清白的少女与母亲,受到法西斯军人残酷、变态的性折磨(《红高梁家族》、《大顺店》、《孽狱》、《花之殇》、《日本鬼子来了》);更有无数的中国男人被侵略者残忍地割下生殖器,为的是使中华民族种族灭绝(《天镇老女人》、《风》)。这一切都是这样触目惊心,每一个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人,面对这些战争罪恶,面对这些人生悲剧,怎么能够不对战争与和平进行冷静的思考呢?
然而这些小说,并未仅仅为了道义的目的而展览战争的不幸。在这不幸命运描写的背后,也蕴含着作家对人的真诚的关怀。因为从战争本身的要求来说,这些人都是相当被动的受害者,大都未对战争作出什么贡献,从国家民族的意义上来说,并无多大价值。但是,从人的意义上来说,任何个体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与价值,任何个体的无意义毁灭,都是人生的悲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命运主题小说显示出了与过去抗战小说的不同。过去的一些抗战小说也写普通人的不幸遭遇,但仅仅是为了表现侵略者的残暴,而这些小说,则对这些不幸者表达了由衷的理解与同情。比如腊梅、“大顺店”、阿庆嫂等,尽管只是些普通人,但她们都有着人的权利。然而她们的权利却被战争粗暴地干涉和剥夺了。这在战争中也许是极普通的事,但对这些个体来说,却是她们人生最大的不幸。这些小说没有漠视她们的痛苦,而是对她们不幸的命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应该说是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的精神的。不仅如此,小说还对特殊环境下的人格弱点也给予了人道关怀。比如《生命通道》并未对苏原医生的一时的懦弱大加抨击。当敌人以当面强奸他的妻子、肢解妻子、将妻子活埋并从不同角度将刺刀捅入他的身体等相要挟时,对这个手无寸铁的医生的任何苛求,都是不说合理的。而宗璞在《南渡记》中,甚至对做了伪华北文艺联合会主席的大学教授、著名戏剧家凌京尧,也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凌京尧并不是主动去当汉奸的。当日本人找上门时,他当即就拒绝了。只是由于连续不断的、越来越残酷的折磨,他终于挺不住而屈服了。对此,作家当然进行了谴责,但作者同时也表示了理解。经受不住肉体的痛苦,这当然不能成为当汉奸的借口,但“经过地狱的煎熬还能有完整的灵魂么?让每个人来试试!”对人的这种透视和认识,显然是来自于人的意识的觉醒。
当然,这些命运主题小说,在表现主人公的不幸命运时,也并非一味同情,它们同时也写出了这些普通人面对不幸命运却不甘屈服的抗争,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坚韧不拔的生命意志。正是这些因素的介入,使得这些小说有了一种刚性。比如苏原医生身在狼窝,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当需要他为国家和自己的同胞出力时,他还是克服了心中的懦弱,而走上了危机四伏的道路,最终献出了生命。农家孩子李金锁(俊然.《殇》)在险些成了731部队试验用的“木头”,费尽千难万险回到故乡后,又投入抗日部队,作了一名勇敢的士兵。腊梅以坚强的毅力支撑着自己的生命等待鬼子的投降,即使生命的最后,还拉开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大顺店”在经历了无尽的辛酸与摧残之后,却不向命运低头,当她发现自己重新“来红”之后,人的尊严又再次苏醒,从此告别女巫般的生活,重新走上了人的新生之路。阿庆嫂虽然象羊脂球一样忍受着屈辱,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艰难前行。那个为抗战失去丈夫和两个儿子的无名老女人(魏人:《天镇老女人》也没有被不幸的命运所压倒,而是忍受着屈辱与情感的折磨,坚韧地生活下去。正是这种敢于抗拒命运、不向命运低头的积极精神,使这些不幸的弱者,同时又成了令人敬佩的强者。
对战争中普通人命运的人道关怀,使抗战小说从历史走向了人。
3
命运主题小说不仅将人道主义的关怀奉献给战争中的普通人,也对爱国者不幸的命运给予了深深的关注与同情。
以爱国者不幸命运为主题的小说,与以普通人不幸命运为主题的小说有所不同。后者的悲剧命运主要来源于战争中的邪恶势力,而前者的悲剧命运则主要来自于抗日队伍内部对人的不信任。
爱国者不幸命运小说的出现,显然受到了苏联卫国战争小说的影响。1990年11月11日至13日,《牧童与牧女》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访问我国南京,当我国学者问及对卫国战争的独特看法时,阿斯塔菲耶夫以亲身经历说明:“战争中重大失误的根源都是不尊重人,不珍视人的价值。”(注:余一中:《阿斯塔耶夫访谈录》,《当代外国文学》,1993年第3期)这种见解不仅是阿斯塔耶夫的看法,在五十年代末以及其后的作家中间也流行。他们中间的一些卫国战争小说家在描写人的命运遭遇时往往与人不被重视联系起来,或者描写人不被关心而产生的命运悲剧;或者描写人不被关心而出现的凄凉生活。如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别洛夫的《这样的战争》、拉普京的《活着,可是要记住》等。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这种抗战革命队伍内部群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悲剧,很少成为抗战小说的主题。五十年代末诗人郭小川的叙事诗《一个和八个》曾作过有益的探索,但却遭到了严厉批评。
管桦的《龙争虎斗》是新时期较早对战争中人的信任问题进行探索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民兵队长古佩雄不幸陷入日伪军魔掌,被关进了据点。敌人为了让古佩雄当汉奸,搞了一个离间计,放风说古佩雄已经叛变了。县委书记不问青红皂白,就下达了逮捕之后立即枪决的命令。于是古佩雄侥幸逃出敌人据点后,受到了一系列不公正的待遇,直到古佩雄在战斗中有了突出表现以后,才结束对他的审查,并委以重任。尽管在战争这种特殊环境下,为了整体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自有其合理性,但这却不应该成为随意造成不幸悲剧的借口。
苏策的《寻找包璞丽》对爱国者的悲剧问题,作了更全面、更深入和更严肃的探索。小说以一个青年爱国者的悲剧命运,对历史的失误,对人的漠视进行了沉重的反思。小说中的主人公包璞丽是山西抗日前线部队的一名宣传员。一次伏击战中,包璞丽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引走敌人,保证了战斗的胜利,自己却不幸被俘。为了帮助被俘战士逃走,她听从营长安排,进了敌人的宣抚班。后又设法逃回了抗日根据地。但是,这段经历却成了她必须背在身上的沉重的十字架。先是参加教导队学习,接受保卫部门的审查,后侥幸未被就地枪毙,却被送到太原去作地下工作。让一个既不会山西话、又不熟悉太原环境的广东人到那里去,无疑是保卫部门对她“既不敢杀又不敢留”的最圆满的解决办法。自然,她也只能以悲剧而告终。包璞丽的悲剧命运是令人同情的。毫无疑问,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对被俘过的人进行审查是必要的。但不少人对人的价值的淡漠却是可怕的。他们仅仅考虑到被俘者可能对群体利益造成的危害,却完全忽视了可能造成的个体悲剧命运。人是最宝贵的。即使是在战争中,也不能忽视人的价值。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事过四五十年,包璞丽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青春热血,却至今还不被理解与公正评价。那些当事人依然相信自己的感觉,对包璞丽之死毫无点滴忏悔之心。历史的真实面貌或许永远被掩盖了,但包璞丽一腔热血空洒的人生悲剧所留给人们的教训却是不应忘记的。
一合的《未婚妻》也写了一个爱国青年被误伤的不幸经历。吴希是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受到县长蔡俊风的影响,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并在他的介绍下入了党。谁知蔡俊风被捕叛变了,吴希也莫名其妙地成了审查对象,遭受了极大的心灵痛苦。王泽群的《集合》和马加的《血映关山》则对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的错误作法,给予了一定的描写与批评。
尽管这些小说,在描写爱国者悲剧命运时,对群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对不相信人,不尊重人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但却十分注意处理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首先,小说真实地表现了这些身遭不幸命运的爱国者忍辱负重、不忘民族大义的高贵的献身精神。如包璞丽面对种种误解、不公正甚至有辱人格的处理,虽然也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与怨恨,并向上级进行了申诉,但她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并不后悔。当她被派往太原去作地下工作时,她清楚地知道这是对她最严厉的惩罚,因为她既无地下工作的经验,又没有地下工作者的联络接应,完全是单枪匹马的个人奋斗,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但她明知危险,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荆棘之路。在无奈的困境中,她放弃个人尊严,毅然当了舞女,通过自己特殊的身份和敌伪人员交往,从而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并设法送给地下组织,直到被敌伪发现,失踪而不知去向。这种爱国热情,是丝毫也不逊色于战场上激烈的拼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她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生命的危险,还有个人尊严和人格的失落,这对一个年青女性来说,是比生命的牺牲更为痛苦的。如果没有一腔报国之心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集合》中的一群所谓的阶级“异己分子”,虽然正受到审查,但面对日军,却英勇不屈,最后全部牺牲。其次,小说也没有将个体命运和群体命运对立起来,在充分尊重个人价值的时候,也同时表明,个人命运只有服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局,才能最终得到根本改变。古佩雄、吴希和周云(《血映关山》)等人在被审查期间,虽然对某些作法不理解,甚至有些恐惧,但却信念不失,坚信自己的问题终会搞清楚的,所以并不消沉。古佩雄不顾自己被审查的身份,在危急时刻,带头冲杀,救出县委机关,使偏听偏信的县委书记终于相信了他的清白,当即宣布撤消对他的审查,并委以新的重任。吴希在受审期间,也没有闹情绪,而是依然默默工作,最终得到组织的信任。周云在“抢救失足者”运动深受打击,但当事实证明他的无辜时,他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由于这些小说比较好地处理了战争中群体与个体的关系,既批评了对同志的不信任,表达了尊重人的现代意识,又赞赏了个体命运服从群体命运大局的自觉性,因此,它们既唤起了人们深切的同情心和人的意识,又对战争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命运主题小说除了对普通人和受到委屈的爱国者的不幸命运给予了人道主义的关怀以外,对抗战中的民族英雄,也给予了人的意义上的理解。如辛实的《步入辉煌》、《雪殇》,周梅森的《大捷》、《日祭》,刘金忠的《故渎》,倪景翔的《龙凤旗》,黎汝清的《皖南事变》等。这些小说,不仅从国家民族的视角上充分肯定了这些抗日英雄的价值意义,也从人的观念上对这些英难不幸的命运给予了深切的同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英雄们的悲剧,几乎都是由中国人自己造成的。比如将军(《步入辉煌》)实际死于一个无耻的告密者;林启明(《日祭》)死于自己的国军部下;宋景周(《故渎》)死于自己的同宗兄弟;孔昭棠(《龙凤旗》)死于心怀野心的地方武装势力;顶英等人(《皖南事变》)则死于国共相残的内战。这就使小说在人的价值视野上,又增加了文化的参照系。
新时期命运主题小说的出现,将抗战小说的目光从历史的喜剧性的结果,转移到了个体的悲剧性遭遇,从无数的仁人志士杀身成仁报效祖国的壮烈行为,转移到了永远失去亲人、家庭甚至生命的不幸者悲哀的脸孔,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这些小说主题表现的深广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探索爱国者不幸命运的小说就比较少。是不是我们战争年代很少出现这类现象呢?并不。“抢救失足者”运动就曾经造成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很多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另外,类似于《一个人的遭遇》中的主人公安德烈·索科洛夫式遭遇的人,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也着实不少。他们为民族、国家、社会承担了应有的责任,付出了没重的代价,但社会却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他们作出相应的回报。但这种小说却几乎没有。而历史和现实,都期待着更有深度的作品出现。
本文所评论到的主要作品出处:
(1)尤凤伟《生命通道》,《当代》,1994年第4期
(2)叶楠《花之殇》,《十月》,1995年第4期
(3)贺景文《孽狱》,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
(4)高建群《大顺店》,《小说家》,1995年第1期
(5)叶兆言《日本鬼子来了》,《中国作家》,1991年第4期
(6)魏人《天镇老女人》,《青年文学》,1987年第11期
(7)管桦《龙争虎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
(8)苏策《寻找包璞丽》,《中国作家》,1992年第1期
(9)一合《未婚妻》,《中国作家》,1995年第4期
(10)王泽群《集合》,《山东文学》,199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