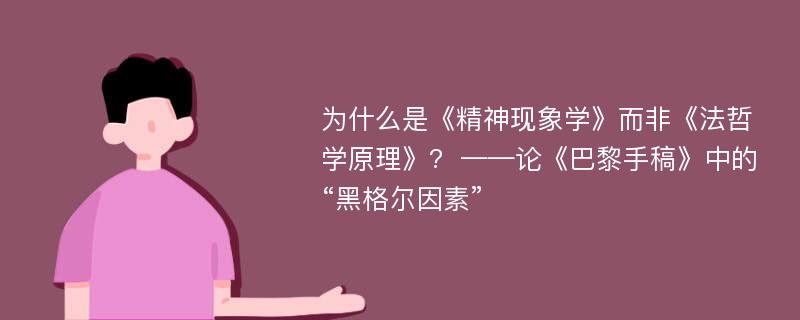
[摘 要] 正如阿尔都塞所言,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曾破天荒地求助于黑格尔.无论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文本相关性,还是从推进法哲学批判的写作任务来看,这一“求助”都应当指向《法哲学》,但实际上马克思却出人意料地援引了《精神现象学》.为了解答这一“舍近求远”的难题,有必要重新聚焦异化劳动的主题——贫困问题,有必要重新考察异化劳动与《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辩证法、《精神现象学》主奴辩证法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市民社会的三重辩证法既表明了黑格尔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传承与分歧,又揭露了作为其断裂点的贫困问题的复杂性.而贫困问题恰恰是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批判中一条为人所忽视的潜在主线,也是其迟迟无法破解的理论困境.正是借助主奴辩证法中被黑格尔所忽略的“劳动的消极方面”所体现的主体间对抗性,异化劳动理论才推进了对贫困问题的阐释效能.可见,在异化劳动理论中,马克思用“翻转版”的主奴辩证法超越了市民社会辩证法,用“升级版”的青年黑格尔超越了老年黑格尔.
[关键词]市民社会辩证法;主奴辩证法;异化劳动;贫困;黑格尔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指出,他在完成对黑格尔法哲学中国家观的批判之后,为了继续解剖市民社会而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而写作了《巴黎手稿》.因此,无论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文本相关性,还是从推进法哲学批判的写作任务来看,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理应继续探讨的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以下简称《法哲学》),特别是其中的市民社会辩证法,但马克思却出人意料地援引了充满形而上学意味的《精神现象学》(以下简称《现象学》)辩证法.而阻碍这一“舍近求远”的难题得到合理解答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些研究者过多地将人道主义而非贫困问题当作了异化劳动的主题.实际上,贫困问题恰恰是沟通市民社会辩证法、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批判、主奴辩证法与异化劳动之间的一道桥梁.有鉴于此,本文将以贫困问题为线索来探讨《巴黎手稿》中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这段复杂的思想姻缘.
一、“舍近求远”的难题:为什么是《现象学》而非《法哲学》?
尽管阿尔都塞曾激进地宣称“广为流传的所谓青年马克思是黑格尔派的说法是一种神话”,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在其“意识形态哲学时期”的最后一部著作即《巴黎手稿》中“却破天荒地向黑格尔求助”.[1](P.16)遗憾的是,阿尔都塞并未言明这一“求助”究竟指向黑格尔的何物.不过,按常理而言,这一“求助物”应被理解为黑格尔的《法哲学》,因为在《巴黎手稿》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宣称自己的出发点仍然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只是鉴于主题与材料的多样性,才暂时仅仅局限于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并且,在正文中马克思还明确地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2](P.320),而在黑格尔的所有著作中,与国民经济学最为紧密相关的便是深刻阐释市民社会与需要体系原理的《法哲学》.然而,令人颇感诧异的是,事实上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却极少言及《法哲学》,反而大量引用黑格尔的《现象学》,并称赞它曾“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2](P.220);另外,从具体文本语境看,马克思关于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家立场的判定,也是针对描述“意识的经验科学”的《现象学》而言的.
也就是说,明明是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为何不直接借鉴黑格尔饱含经济学气息的《法哲学》,反而借用其充满形而上学色彩的《现象学》?这明显是一条“舍近求远”的道路.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当马克思在1844年开始围绕着劳动主题而对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进行一种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批判时,他却牢牢地抓住了《现象学》,而几乎完全没有提到《法哲学》与劳动主题直接相关的部分.考虑到《法哲学》还直接论及国民经济学的地位和性质,考虑到马克思1843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这种情形就显得尤为奇特.”[3]如何对马克思这种“不合常理”的行为给出合理的解释,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其中,vR(f)为频率为f的瑞利面波的相速度。根据式(1)即可求出不同频率f的相速度vR,即vR-f频散曲线(见图1)。
供应链金融的风险管理是现阶段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核心,也是金融贸易阶段性发展的产物。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不仅提高了其整体评估速度,更提高了金融管理精度,可以预见,未来供应链金融管理势必会与金融大数据进行更深层次的数据整合。
那么,法哲学批判时期的马克思究竟是如何批判黑格尔市民社会辩证法的呢?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评了市民社会的第三辩证法,即批判了黑格尔对贫困问题的解决路径.在马克思看来,“具有各自的细微差异的商业和工业,是各种特殊的同业公会的私有财产”,因此,同业公会会为了自己的行业利益而反对社会和国家的普遍利益,甚至勾结政府官僚去打压其他公会,“单独一个同业公会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希望官僚政治去反对别的同业公会,反对别的特殊利益”.[2](P.135,59)在这样一种恶性竞争的状态下,黑格尔所构想的同业公会的自身生存都成问题,更别提有余力去解决贫困问题了.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批判了市民社会的第一辩证法,揭露了利己的个人所创造的“普遍社会财富”与个体的恶所成就的“社会的善”的虚伪性.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在政治上的对应物就是法国和北美的政治解放运动.他们所标榜的以私有财产权、平等、安全等为核心的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这使得“citoyen[公民]被宣布为利己的homme[人]的奴仆”.[2](PP.182~185)在市民社会的分工与交换基础上实现的所谓“社会的财富”“社会的善”只是利己的个人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与工具,甚至只是经济学与法律上自我美化的遁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判了市民社会的第二辩证法,重新解读了贱民与无产阶级的产生原因.与黑格尔的贱民一样,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也处于“完全丧失”的一无所有状态,也属于“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也是由近代的工业运动“人工制造”出来的.但是,与黑格尔强调贱民在主观上好逸恶劳不同,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贫困与堕落是因为遭受了社会的普遍苦难,受到了“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的待遇,因此,不是无产阶级想游手好闲,而是他们发现越劳动越贫困,最后甚至连劳动机会也被剥夺掉.[2](P.213)也就说,黑格尔将贱民产生的原因归咎于个人因素(能力的不足、正直情绪的丧失等),马克思则从社会制度的层面(社会的压迫,私有制的不公等)阐释无产阶级的悲楚处境.
此外,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即使有研究者关注到异化劳动的贫困主题,但却只是从一种孤立的视角切入,仅仅就《巴黎手稿》来谈论异化劳动,而没有立足于早期马克思法哲学批判的整个体系来评估异化劳动对于阐释贫困问题的新作用与新意义,如此一来,也就无法给出马克思“突然”从《法哲学》转向《现象学》的内在缘由.比如科耶夫、马尔库塞等人认为异化劳动本身的内在逻辑是与《现象学》的主奴辩证法,而非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相一致的,进而直接从主体间的对抗性维度阐发贫困问题.马尔库塞直言:“1844年,马克思通过批判地分析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完善了他自己理论的基本概念.他借鉴黑格尔关于主人和仆人论述的观点,描述了劳动的‘异化’.”[4](P.104)还有学者将《现象学》与《巴黎手稿》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从前资本主义强调人身依附的“显性主奴辩证法”到体现资本家、劳动产品和工人之间间接统治的“隐性主奴辩证法”的一种创造性转换.[5]这种解读方式存在两处偏颇:其一,它貌似可以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剥削论相勾连,但却是以一种带着“前见”的方式介入的,根本没有澄清马克思此时突然转向主奴辩证法的机缘,毕竟马克思在大学时代早已阅读过《现象学》;其二,忽视了主奴辩证法与异化劳动的方向性差异,主奴辩证法的侧重点在于,处于从属地位的奴隶通过劳动完成了对自我积极而非消极的塑造,若遵循这一逻辑,黑格尔会认为“就工人的自我实现来说,即便在剥削的生产关系中劳动的教育意义也是充分的”[6].
有鉴于此,为了更好地解答马克思这一“舍近求远”的难题,我们既要重新聚焦异化劳动的主题,使其从人道主义回归到贫困问题,也要突破《巴黎手稿》的狭隘视野,力图在马克思早期作品的“整体像”中考察异化劳动与《法哲学》市民社会辩证法、《现象学》主奴辩证法之间的复杂关系,重估异化劳动对于澄清贫困问题所带来的新的理论贡献.
二、作为《法哲学》市民社会辩证法断裂点的贫困问题
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第一个在术语层面上提出了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概念系统,把国家这一政治领域与‘市民社会’区别了开来”[7](P.44).也就是说,市民社会是一个既适应于现代社会又区别于古典政治学说的新概念框架.在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古代世界中,经济(或者说家政学)是从属于政治的,共同体是优先于个体的,而在现代社会中,经济从政治中独立出来,个体从共同体中挣脱出来,由普遍商品交换和自由私有者所建构的市民社会有着与官僚化的国家不同的相对独立的运行轨道.这一建立在近代商业社会基础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既是黑格尔自法兰克福时期起便不断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取得的成果,也是黑格尔以哲学家的敏锐洞察力力图超越斯密、李嘉图、萨伊等人的尝试.在市民社会辩证法中,黑格尔正视了为古典经济学家所忽略但却极为重要的贫困问题,并提供出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案,而正是沿着黑格尔的新视角与新方案,马克思才进一步推进了自己的批判性研究.
我们结合工作岗位设计相应的药学服务情景,根据项目内容,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情景设计,编写用药咨询、药患沟通等剧本,由专业教师指导,并进行扮演排练演出。另外,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学院医药学社等社团活动走进社会药房,观摩药师工作程序,并进行合理用药知识宣传等。通过有目的地组织各类活动,顺利地完成课程教学目标,更重要的是促进学生了的综合素质发展,获取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一)黑格尔市民社会辩证法的三重含义
从被黑格尔忽视的奴隶劳动的“消极方面”中,马克思看到了突破法哲学批判困境的希望.而之所以强调其中体现出的阶级对抗维度,是因为它对于深入分析贫困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前文所述,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斯密在《国富论》中都看到了近代大分工与机器化条件下的工业劳动带给工人的负面作用.但是,他们仅仅看到的是以机器为代表的物对人的压迫,而没有看到掩盖在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关系,没有看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与压榨.在他们眼中,工人与工厂主都是平等的市民,都以自愿、公平的方式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体系进行生产、交换,而之所以产生贫困只能归因于个人能力禀赋的不足、个人际遇的不幸.在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就不满于黑格尔的这种分析方式,进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私有制、指向了社会压迫,可是他未能言明贫困与私有财产、社会等级等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为此,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借用了奴隶劳动的“消极方面”进行了进一步阐释.
针对学生的难点问题,做成微视频,有针对性地去帮助学生,主要对数学学科中难以理解的概念、公式的推导以及考试的重难点知识,分割成简单的完整的知识点,用微课程的方式来展现,使学习者加深对重要知识点的掌握和研究,并将短时记忆的内容加工进入到长时记忆中,以便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可以随时将知识提取出来进行解决.
在日本市民社会派看来,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市民社会辩证法的认识有一个由“误解”到澄清的过程.他们认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是英国市民社会像与普鲁士市民社会像结合的产物,当马克思先前借助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逻辑来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主要针对的是普鲁士市民社会像而非英国市民社会像,其原因在于当时的马克思并不具备“黑格尔已经掌握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素养”[18](P.20),也就不能理解市民社会的“需要体系”所蕴含的积极的等价交换和社会分工的逻辑,并且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穆勒评注》.但是,上述的论证已经表明,并非如他们所批评的那样,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辩证法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他充分了解市民社会辩证法的积极与消极方面,并且深刻理解作为其内在断裂点的贫困问题.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至少达到了黑格尔的高度.因夹杂着同业公会等内容而被讥讽为散发着“普鲁士体臭”的市民社会像,这并非是黑格尔落后、保守的证据,而是他试图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所在.黑格尔的贡献在于,正视了为古典经济学家所忽视的贫困问题,并且设计了一系列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分歧不在于对贫困现象与危害的揭示方面,而在于对贫困根源的判定与解决方案的选择方面.黑格尔将贫困归因于个体的主观因素,试图在私有制的框架内修补这一问题.也就是说,他在私有财产的保护与贫困的救济之间小心翼翼地游走.而马克思则将贫困归咎于社会制度层面,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人的解放”运动.
第三层含义是指“需要的体系—司法—警察与同业公会”的结构性辩证法.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由需要的体系、司法、警察和同业公会组成,这三部分是“主导着《法哲学》市民社会阐释之结构与进程的辩证法”[12](S.114).依靠彼此相依赖的需要,孤立的个体组成“需要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个人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根据劳动与获取财富方式的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等级;“司法”保护每个人的人身财产免受非法侵害;而鉴于“司法”只是以赛亚·伯林意义上的一种消极保护,无法顾及个体间合法竞争等因素导致的特殊福利受损问题,此时便由警察和同业公会来实施一种积极保护.在笔者看来,结构性辩证法的落脚点就是贫困问题,就是要解决上述“巨富与赤贫并峙”的辩证法难题,为此,黑格尔曾研究过个人慈善、警察的物质救济、就业援助、海外殖民等诸多措施.事实上,对于“黑格尔究竟是否解决了贫困”的讨论,已成为学界的一桩公案,而近来的一些新研究成果[13][14]表明,黑格尔最终将解决贫困问题的重担放在同业公会肩上.黑格尔所构想的同业公会,与中世纪封闭保守的旧行会截然不同.它尊重个体基于自我选择的自由流动,注重培养会员的技能并为其提供就业机会,重视培育会员的行业共同体精神,同时作为一个不同于国家的市民社会自主组织,它也可以适度地调控生产规模,避免生产过剩.如此一来,在尊重劳动所有权和自食其力精神的前提下,同业公会既可保证现有会员不致陷入贫困的泥潭,又可吸纳外来的贫民进入,从而有效阻止贱民及其贱民精神在市民社会的产生与蔓延.
诚如诺伯特·瓦泽克(Norbert Waszek)在其名作《苏格兰启蒙运动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描述》中所指出的那样,“通过研究和吸收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先进的经济理论,黑格尔将他们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解提升到了综合性政治哲学的水平”[15](P.230).从上述的三种市民社会辩证法中,可以看出黑格尔对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持有的借鉴、分歧与超越三个不同维度的态度.而正是贫困问题构成了二者分野的关键点.在处理贫困问题的过程中,黑格尔重新发现了等级与同业公会的意义,并由此建构了以代表制为基础的“现代立宪君主制”[16].在黑格尔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追求的自由市场经济逻辑只表达了市民社会辩证法的第一层含义,而作为市民社会辩证法断裂点的贫困问题,尚处在他们的视野之外.那么,法哲学批判时期的马克思是否意识到黑格尔市民社会辩证法的真实要旨了呢?
(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辩证法断裂点的初步批判及其理论困境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主题往往被定位为批判黑格尔的逻辑神秘主义,确立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新范式.诚然,这两条主题内容是正确的,但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主题范围却绝不仅仅局限于此,尤其在考虑到以下两个文本事实的情况下.其一,马克思进行法哲学批判研究的初心是什么呢?按照马克思自己的回顾,是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为了回答《莱茵报》时期遭遇的“物质利益难题”.[17](PP.411~412)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曾为莱茵省因捡拾枯枝而被定性为盗窃的贫困民众鸣不平;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也曾替摩泽尔河沿岸贫困破产的葡萄种植者辩护.但当时除了诉诸于“正义的法”的早日实现以外,他还无法对这些贫困现象产生的根源与解决的方法作出更多的理论分析,这令他苦恼不已.其二,在完成法哲学批判草稿之际,马克思为其写了一份“导言”(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从理论上讲,相对于正文来说,“导言”对于正文应该具有概括性与导引性,可是,马克思在“导言”中却几乎没有提及上述的两条“主题”,反而关注的是无产阶级的诞生与政治使命问题.其实,如果联系到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对贫困与贱民问题的分析,那么,马克思这一貌似“从天而降”的无产阶级概念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
鉴于马克思进行法哲学批判的初衷与结论都涉及贫困与穷人问题,笔者以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另一条主线是围绕对市民社会辩证法的断裂点——贫困——的探究与批判展开的,不过这条主线过去往往被人所忽视.同时,如此一来,《莱茵报》时期、法哲学批判时期、甚至《巴黎手稿》时期的主题便可以由贫困问题“一以贯之”起来,这会为之后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与异化劳动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阐释路径.
事实上,长期以来阻碍这一难题得到有效澄清和解决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很多研究者偏离了异化劳动的主题——贫困问题,而将关注点过多地集中在了人道主义问题上.异化劳动理论的出发点是要阐释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即理论上要求“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实践上却要求“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2](P.230)马克思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相异化这四个维度来试图解读现实中“越劳动越贫困”的这种悖论性现象.也就是说,贫困问题才是异化劳动理论的初衷与旨归所在.因此,评估异化劳动的重要指标在于,考察它如何看待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解释贫困的形成机制,同时也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异化劳动与《法哲学》辩证法和《现象学》辩证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实际上成为研究焦点的却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而非贫困问题.由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2](P.273)这一人的类本质的设定,使整个异化劳动被当作一种抽象的人本主义.如阿尔都塞“从意识形态阶段到科学阶段”的认识论断裂说和广松涉“从异化逻辑到物象化逻辑”的飞越说,都认为《巴黎手稿》主要笼罩在费尔巴哈的阴影之下,而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微乎其微,只有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种境况才获得了根本性的改变.在这种解读范式的强烈影响下,异化劳动对于贫困的推进作用、《现象学》对于异化劳动的借鉴意义等问题都被遮盖起来.
第二层含义是巨富与赤贫的并峙.“市民社会的这种辩证法(ihre Dialektik……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这里就显露出来,尽管财富过剩,市民社会总是不够富足的,这就是说,它所占有而属于它所有的财产,如果用来防止过分贫困和贱民的产 生,总 是 不 够 的”.[8](PP.245~246)[9](S.390~391)如果说第一层面的市民社会辩证法描绘了利己个人创造普遍社会财富的美好景象,那么此时黑格尔却展示了市民社会的另一种悖论性现象,即一方面社会财富过剩,另一方面贫困遍地.实际上,此处便显露出了黑格尔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歧.众所周知,斯密始终沉浸在市场经济的光明前景之中,在他那里贫困不会成为一个恼人的问题,因为他坚信发达的分工与交换体系会创造出充裕的社会财富,进而“引起了一般的、普及于最低阶级人民的富裕”[11](P.6).而黑格尔却把贫困问题看作是市民社会的癌症,认为它没有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与社会财富的增加而消退,反而愈演愈烈,以致“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8](P.245).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一辩证法被伊尔廷(Karl-Heinz Ilting)在《市民社会辩证法》一文中称为“阶级对立辩证法(Dialektik des Klassengegensatzes)”[12](S.114),但是,黑格尔并没有从阶级对抗的角度剖析贫困问题,而是在私有制框架内对其进行诠释.在以私人所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个体在禀赋、技能、资本、偶然的际遇等方面的差异必然会导致贫困的产生,而且最糟糕的结果是穷人进一步退化为“贱民”,即丧失了自食其力的精神、把恳扰求乞当作权利的穷人.黑格尔承认,市民社会的贫困是体系性与悖论性的,仅仅依靠斯密那种扩大生产进而做大社会财富蛋糕的方式,反而有可能增加失业率和加剧贫困.
不过,在批判黑格尔市民社会辩证法的过程中,或者说在超越黑格尔的贫困观时,马克思尚存在一些不足.他只看到同业公会之间的相互竞争,但尚未分析行会内部成员之间的对抗关系;他主张无产阶级受到了无情的压迫,但尚未阐明受到了哪种力量的压迫,经历了怎样的压迫过程;他提出要废除私有制,但尚未言明私有制与贫困之间有怎样的必然联系.因此,马克思在批判市民社会辩证法时,事实上也遇到了一个理论瓶颈,迫切地需要“外援”来帮助突破.而这一“外援”就是《巴黎手稿》中貌似“突兀现身”的《现象学》主奴辩证法.
三、《现象学》主奴辩证法对于阐释贫困问题的突破性意义
虽然马尔库塞等人坚称《巴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深受《现象学》主奴辩证法的影响,但是他们并没有为马克思这一出人意料地“引援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本文的第二部分展示了马克思批判市民社会辩证法的过程及其遇到的困境,即无法深入阐明无产阶级陷入贫困的内在机理,而事实上正是这一困境成为了马克思转向《现象学》辩证法的内在契机.
(一)主奴辩证法中被忽视的“劳动的消极方面”
可见,在主奴辩证法中,黑格尔从劳动过程、劳动产品以及与主人的关系三个维度都描述了奴隶劳动对于奴隶的积极意义,尤其凸显了劳动塑造奴隶的自我意识、促使奴隶陶冶为自由人这一“积极方面”,但是,他却没有强调劳动过程对于奴隶的摧残、劳动产品被主人的无偿占有、对主人的恐惧的无法彻底根除等“消极方面”.而隐藏在这些“消极方面”背后的是起主导作用的主人与奴隶的二元阶级对抗关系,马克思正是从这种对抗性关系中发现了进一步推进市民社会辩证法批判的突破口.
目前学界关于“劳动的消极方面”大致有三种解读方式.在第一种解读看来,这完全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误读.洛维特认为,在黑格尔耶拿草稿等文献中存在着对劳动的机械化、工人意识的迟钝等“消极方面”的大量描述,而马克思当时却无法看到这些著作,故而误解了黑格尔,“如果马克思能够领会耶拿讲演中的批判阐述和对斯图尔特的国民经济学的评述的话,他就会比在对《精神现象学》的研究中更直接地从黑格尔的问题提出发展出他自己的问题提出”[19](P.365).第二种解读认为,马克思在《法哲学》中是能够看到机械化导致机器替代人等现象的,但他仍批评黑格尔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是因为“黑格尔把这些消极方面归根结底看作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们最终成全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普鲁士国家和黑格尔的哲学,因而其消极性已被精神、意识所扬弃、所抵消”[20](P.212).第三种解读将劳动的消极方面理解为这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劳动”,也就是说,相对物质实践劳动而言精神劳动是消极抽象的.[6]
显然,前两种解读都仍局限在《法哲学》的框架之内,都围绕工业给劳动者带来的不利方面展开,只是后者指出了黑格尔仍把劳动的消极方面当作成就其法哲学体系的积极媒介.但是,从文本语境来看,马克思此处的讨论对象明显是《现象学》,故而直接用《法哲学》的工业劳动来阐释便有“偏题”之嫌.而阿瑟(Chris Arthur)的解读是基于《现象学》的,他把此处的劳动理解为贯穿整部《现象学》的“精神劳动”,但是,如此一来,却难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家立场.毕竟,“一部《精神现象学》实质性地讨论劳动,只有 ‘主奴关系’章节”,《巴黎手稿》中的劳动概念虽然汲取了“精神概念的内涵如活动、自我创造、异化和超越等等,但其根底还是同‘主奴关系’中的奴隶劳动密切相关”.[21]笔者认为,这里的劳动是指用国民经济学棱镜透视后的奴隶劳动,是借用费尔巴哈哲学去除“神秘精神”后的奴隶的物质劳动.
那么,黑格尔究竟有没有看到奴隶劳动的什么消极方面?在《现象学》的“自我意识的独立与依赖:主人与奴隶”一节中,黑格尔认为,仅当获得另一个自我意识的承认时,自我意识才能成为自我意识,于是双方爆发了争取承认的生死斗争,由于一方的怕死与妥协,结果形成了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其中,主人处于统治地位,把奴隶放在物和它之间,让奴隶对物进行加工改造,自己则尽情享受;奴隶则处于依赖性地位,它开始时基于恐惧而被迫为主人服务,但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它逐渐意识到“它特有的否定性、它的自为存在是它的对象”,并能够在劳动产品中直观到自己的这一本质,因为奴隶陶冶事物的劳动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亦即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22](PP.130~131)也就是说,在劳动中奴隶压抑了促使他“‘直接’‘消费’‘原始’物品的本能”,克服了自己的直接自然性(物性),完成了自我的教育与升华.[23](P.26)此外,这一劳动过程,对于克服奴隶对主人的恐惧也具有积极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现象学》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并且“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2](PP.319~320)可见,《现象学》中辩证法的贡献就在于展示了劳动的积极方面,展示了劳动可以生成人、可以塑造人的本质,而不足之处在于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可是,“劳动的消极方面”究竟是指什么呢?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一指责是否确切?回答这一问题对于判定《现象学》中辩证法的性质及其与马克思异化劳动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事实上,个体的利己心与社会的普遍财富之间的这一辩证法,是黑格尔沿袭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借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结果.在最早的“1817/18年法哲学讲义”中,黑格尔将上述的“需要的体系”与“国民经济学(staatsökonomie)”并列在同一个小标题中.[10](S.118)也就是说,把二者等同视之.与欧陆思想界注重思辨理性、提倡从个体的良心与理性建构理想的社会(如康德)不同,英国的思想家们深谙商业社会的习气,依据经验观察提出从“个体的恶”亦能生发“社会的善”.比如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认为,是私人的恶德而非美德最终会导致公众利益的产生;斯密在《国富论》中亦强调,“看不见的手”能使追逐私利的个体不自觉地创造出有益于社会的普遍利益.
(二)“翻转版”的主奴辩证法与异化劳动
依据对《法哲学》的考察,黑格尔市民社会辩证法主要具有下述三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利己的个人创造普遍(利他)的社会财富.“在劳动和满足需要的上述依赖性和相互关系中,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这是一种辩证运动(dialektische Bewegung).其结果,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正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得.在一切人相互依赖全面交织中所含有的必然性,现在对每个人说来,就是普遍而持久的财富.”[8](P.210)[9](P.353)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中存在着两大原则.其一是特殊性原则,即每一个市民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他的劳动、交换、消费等活动都围绕这一原则展开;其二是形式普遍性原则,利己的市民如果不同他人发生关系,那么他最终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他必须首先通过自己的劳动和他人的劳动使他人的需要获得满足,然后方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普遍的社会财富也被创造出来.而这一“需要的体系”只能建立在近代工业的基础上,需要与满足需要手段的殊多化与细致化引起了分工乃至机械化的产生,现代社会的普遍分工与交换又好似一张大网将利己的市民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呼……看样子他们没敢跟过来,你先在我家写作业。别怕,这种找事儿的人你越怕,他越欺负你。”王施凯拍拍赵明月的肩膀安慰道。
在《巴黎手稿》开端部分,马克思摘录了斯密等人关于“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来源的分析,从中看到了现代社会阶级的具体划分状况,并且预判到地主阶级将会被吞灭,“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2](P.266).两大阶级的对立构成了主奴关系的基本框架,为阐释异化劳动和贫困问题奠定了主基调.同时,这种二元阶级划分的模式也大大突破了《法哲学》的等级结构:土地等级(农民和地主)、产业等级(手工业者、工业者和商人)和普遍等级(官僚、教师、军人).黑格尔除了强调繁复的等级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外,根本没有分析他们彼此之间的对抗性关系.
与贫穷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财富问题及私有财产问题.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说法,劳动创造财富(私有财产).但当前的经济事实却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2](P.267).这样一个“越劳动越贫穷”的悖论,就是在工人和资本家对抗性的主奴关系中产生的.在这种对抗性的主奴关系中,工人劳动成了奴隶劳动、成了异化劳动,并且是劳动的“消极方面”而非“积极方面”占主导.
从劳动产品的维度看,它变成不依赖工人的异己的存在物,工人在其中消耗的力量越多,工人自己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属于工人的东西就越少,同时劳动产品生产的越美,工人就越畸形和愚钝,而在《现象学》的积极性描述中,奴隶反而应该感激主人将物的独立性一面让给自己,使自己在替主人劳作、加工改造物之后,在劳动产品中能够直观到自我的本质;从劳动过程的维度看,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自由发挥体力脑力而是折磨肉体摧残精神,甚至会像逃避瘟疫一样躲避劳动,而在《现象学》的积极性描述中,劳动使奴隶成为纯粹的自为存在,陶冶出它的自由意识;从与人的类本质的关系来看,劳动仅仅变成了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这违背了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类本质,而在《现象学》的积极性描述中,奴隶可以从在为他人的劳动、归他人所有的劳动产品中陶冶、直观到自己的独立意识,找回自己的潜在本质;从与他人的关系来看,前三种异化导致工人以异化的态度去对待周围的一切,进而发生了人与人的全面异化,而在《现象学》的积极性描述中,劳动却是有利于奴隶克服对主人的恐惧,进而构建二者“和谐”关系的.
我写此文不是自己有什么育儿高招,这些不是我的成果。我家蛮蛮号称放养,但显然我没有完全清楚放养的真正意思,good manner方面差得远。但我希望自己遇到了好的方式好的现象,能思考并能正面地学习点啥,也带给国内很积极上进的家长们一些参考。国内不管是节目《保姆911》的火爆,还是现在“正面教育”的流行,我发现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教育孩子,首先是调整好自己。父母带头做到了,孩子才可能跟着做到。
取患者新鲜中段尿液,混合后分为3管,分别给予患者单纯尿液干化学法、单纯尿沉渣镜检法和干化学法联合尿沉渣镜检法进行白细胞检验。尿液干化学法:实验前对干化学分析仪的仪器进行空白矫正和实验室质控,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将试纸充分浸入尿液标本1 s后取出,使用滤纸吸出多于尿液,使用干化学分析仪进行检测。尿沉渣镜检法:将患者尿液标本10 mL,离心(1500 r/min,5 min)后,取0.2 mL的尿液沉渣,混匀后滴在载玻片上,先使用低倍显微镜来对分布情况进行观察,然后再使用高倍显微镜对10个镜下视野的白细胞依次进行计数并做好记录,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可见,在对异化劳动的阐释中,马克思补上了黑格尔《现象学》中缺失的一环——主奴辩证法中劳动的消极方面,不过已将奴隶劳动置换为国民经济学语境中的工人劳动.在描述完四种异化之后,马克思又再次突出了其中的对抗性关系.他指出,在异化劳动中,劳动为之服务、劳动产品为之享受的那个异己存在物,不是神也不是自然,“只能是人自身”,“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Capitalist)——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 的 名 字——对 这 个 劳 动 的 关系”.[2](PP.276~277)[24](S.243~244)至此,马克思不 再 空 洞地谈论市民社会辩证法中的贫困问题,他将“无产阶级遭受了社会的不公”明确为“无产阶级受到了资产阶级的剥夺”,并给国民经济学的信条“劳动创造财富”加上了双重定语——“工人的异化劳动创造资本家的私有财产”.
结语
围绕《巴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苏联教科书体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双方虽然对异化劳动的思想价值作出了非常悬殊的评价,但却都认为异化劳动属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逻辑,主要受费尔巴哈人道主义而非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而要回答“马克思为何求助于《现象学》而非《法哲学》”这一舍近求远的难题,恰恰要将研究的视野从人道主义问题拉回到贫困问题,并将后者确立为异化劳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也要立足于马克思早期整个法哲学批判的新坐标来重审异化劳动对于阐释贫困问题的新突破.
《法哲学》市民社会的三重辩证法既表明了黑格尔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吸收、对市民社会特殊性原理与普遍性原理的继承,也表明了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对贫困问题的忧思.而在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批判中,一条易被忽视的主线就是他对贫困问题的持续关注.马克思之所以一再批判市民社会“人对人是狼”的“特殊性原理”,是因为他认为所谓的在分工和交换基础上“人与人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普遍性原理”是极其虚伪的,维护的只是利己的私人财产权这样的人权,不仅无法解决贫困问题,甚至掩盖对贫困产生根源的揭露.从这种意义看,将《穆勒评注》中商品交换基础上形成的“交往异化”[18](PP.79~99)视为马克思第一次发现“普遍性原理”进而超越异化劳动的标志,恐怕是对马克思的一种误解.事实上,正是通过借助“翻转版”的《现象学》主奴辩证法中“劳动的消极方面”所体现出的阶级对抗性,而非市民社会辩证法中的普遍性原理,马克思才突破了法哲学批判的困境,推进了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在《巴黎手稿》中存在着一场“青年黑格尔超越老年黑格尔”的运动.
1.心理测评普及。2012年至2017年,仅进行量表测评61次,而2017年7月至2018年7月,通过每月新入矫集中心理测评和每季度各司法所集中心理测评,工作人员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绘画投射测验总计1430人次,是前五年测评量的23倍。
[参考文献]
[1]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吴晓明.《精神现象学》的劳动主题与马克思的哲学奠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4]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M].程志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5]刘同舫.从显性到隐性的主奴辩证法——《精神现象学》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系注解[J].哲学研究,2014,(1).
[6]Chris Arthur.Hegel’Master-Slave Dialectic and a Myth of Marxology[J].New Left Review,1983,November-December.
[7]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9]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M].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70.
[10]Hegel.Vorlesungenüb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Heidelberg 1817/18 mit Nachträgen aus der Vorlesung 1818/19[M].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83.
[11]斯密.国富论(上)[M].郭大力,王亚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2]Karl-Heinz Ilting.Die Dialektik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A].Aufsätzeüber Hegel.Herausgegeben von Paolo Becchi und Hansgeorg Hoppe[C].Frankfurt am Main:Humanities Online,2006.
[13]梁燕晓.黑格尔:个体与共同体冲突的成功和解者?——基于市民社会中贫困问题的考察[J].哲学分析,2018,(4).
[14]Stephen Hudson.The Problem of Poverty and the Rabble:Against the Neo-Marxist Critique of Hegel[J].Hegel-Jahrbuch,2014,(1).
[15]Norbert Waszek.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Hegel’s Account of“Civil Society”[M].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8.
[16]梁燕晓.马克思误解黑格尔王权理论了吗?——由《法哲学》版本问题所引发的新争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8]望月清司.马克思的历史理论[M].韩立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9]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M].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20]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1]王金林.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概念之重构[J].哲学研究,2017,(4).
[2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3]科耶夫.黑格尔导读[M].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24]Marx-Engels Gesamtausgabe,Band I/2[M].Berlin:Dietz Verlag,1982.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9)04-0049-08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9.04.007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编号:201806210408);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黑格尔法哲学中的自由困境”(编号:16ZXB007).
[收稿日期]2019-04-26
[作者简介]梁燕晓,男,清华大学哲学系与海德堡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冯军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