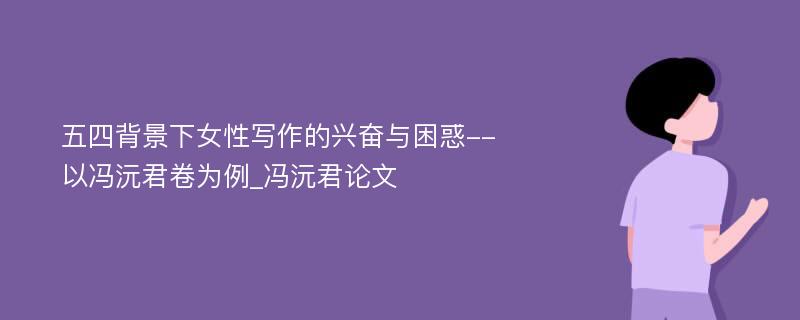
“五四”背景下女性书写的兴奋与迷茫——以冯沅君的《卷葹》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迷茫论文,兴奋论文,女性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5)01-0124-03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陈独秀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以文化批判为主要内容,为随后的“五四”运动以及文学革命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辛亥革命以降,革命话语逐渐成为转型时代初期的主流话语。中国主流文化中的儒家传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抨击,以至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过程中,知识分子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废除汉语、汉字”的口号,将文化激进主义推向了巅峰。这股激进主义思潮以其在新文化运动后期观点的超越性最终以压倒性的革命话语权取得了“五四”以后中国思想领域、文化领域乃至政治领域的领导权。在那个狂飙突进式的“五四”新时代里,“激进主义”成为众多年轻人的精神信仰,并成为他们反抗社会、反抗传统、反抗命运的有力武器。在这种时代氛围之下,女性写作应运而生。20年代初,以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苏雪林等代表的中国第一个现代女性作家群落粉墨登场。这批受惠于现代高等教育并接受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双重熏染的知识女性在“五四”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开始“我手写我心”,试图用文学创作的形式在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发出了她们的声音。 冯沅君的《卷葹》是奠定了其文学史地位的代表性作品,曾被鲁迅亲自编选列入《乌合丛书》。此小说集初版于1927年,收录了作家1924年前后以“淦女士”为笔名创作、发表于《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的四篇小说《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1928年《卷葹》再版,增收了《写于母亲走后》《误点》两篇小说。这一系列小说诉说的其实是同一个母题的故事:婚约在身的新知识女性与已有妻室的知识男性两情相悦、自由恋爱,曾共同外出“旅行”,共处一室却未发生实质关系,在“慈母”面前勇敢反抗家族包办婚姻未果,被“隔绝之后”双双殉情。除了小说的主题出于反封建需要将结局做了悲剧性处理而作者本人却尝到了自由恋爱的果实之外,按照作家“处女作即自传”的创作惯例,再结合冯沅君本人的人生经历及亲属的回忆文章,不难发现这些小说具有强烈的自叙传色彩。这一点也得到了一些文学研究者的认可:“年轻的五四作者大多长于抒情,拙于描写,呈现在他们作品里的,往往不是对精神世界的准确细致的刻画,而是真实心态的披露。”[1](P208)因此,这几篇极具有写实色彩的小说就成为折射当时新女性心路历程的文学载体,也为后人研究此时期的女性创作心理提供了第一手详尽的材料。 就写作风格而言,许多读过《卷葹》的读者都会被作品中的“大胆”而震撼。在展现情侣之间的亲密关系时:热烈的爱情宣言、亲昵的肢体描写、微妙的心理暗示等极具有隐私性的情节都会让经历过爱情的过来人感同身受。而在描写女主人公同家庭的对立冲突中所发出的“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隔绝》)的战斗呐喊同样让人感慨不已。可以说《卷葹》就是一部沉浸于爱情之中的新女性真实的成长记录。无怪乎沈从文会做出这样的评价:“淦女士具有展览自己的勇敢,她告给人是自己在如何解决自己的故事,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为了对于‘爱’这名词有所说明,在1923年前,女作家中还没有这种作品。在男子作品中,能肆无所忌的写到一切,也还没有。因此,淦女士的作品,以崭新的趣味,兴奋了一时代的年轻人。……淦女士所得到的盛誉,超越了冰心,惹人注意与讨论,较之郁达夫鲁迅作品,似更宽泛而长久。”[2](P210-211)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社会文化氛围让一个出身地主家庭、从小读私塾长大、系统接受过四书五经教育的女青年面对普罗大众如此“肆无忌惮”的敞开心扉? 时值1923年,冯沅君结束了在北京女高师5年的学习生涯,顺利考取北京大学国学门攻读古典文学硕士学位。早已到适婚年龄的作家也遭遇到“五四”时期极为普遍的封建包办婚姻问题:“有爱情而不得爱,强不爱以为爱。”面对这一问题,在“五四”激进主义思潮中久经熏染的新女性们坚定地表明了自己激进反抗的姿态。联系作家自身,早在1920年4月,冯沅君还是北京女高师一名普通本科学生时就曾在学校内部刊物《文艺会刊》上发表了《今后吾国女子的道德问题》的评论文章,署名冯淑兰。在文章中,作家从学理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旧式女性所奉行的“三从四德”道德准则,并逐条加以分析和批评。文章中,作者提出了她理想中的女性是“独立”“博爱”与“自强”。而这些思想的来源显然与作家平日所受到的进步思想熏陶不无关系。 “五四”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转折时期,它彰显了现代知识分子同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壮志与豪情,破“旧”立“新”成为这一时期遍布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关键词。在随之产生的轰轰烈烈的激进主义文化思潮中,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氏兄弟等启蒙者所倡导的民主、科学、劳工神圣、男女平等、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等现代观念已然获取了广大新青年们的广泛认同。仅以新文化运动中和女性相关的论题为例:早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陈独秀就通过《敬告青年》呼吁女子参政,自第2卷第6号起开辟了“女子问题”专栏。继而胡适的《易卜生主义》、鲁迅的《我之节烈观》等文章相继发表,引起了《新潮》《少年中国》《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晨报》《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妇女评论》等国内众多报刊在“妇女解放”这一问题上的呼应。具体到女性的婚姻问题,一些思想先驱们也发表了一些影响力甚大且极具针对性的文章,如恽代英的《结婚问题之研究》、鲁迅的《随感录·四十》、胡适的《李超传》、俞平伯的《现行婚姻底片面批评》等。《妇女杂志》甚至在第8卷第12号刊发了若干关于女性贞操观的文章,就当时奉行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制度展开强烈批判。除此之外,20年代初“男女同校”“社交公开”等理念的提出以及瑞典爱伦凯、日本厨川白村、美国高曼的“爱情至上”理论的传播也给予了当时新青年们反抗旧式婚姻、追求自由幸福的莫大勇气和力量。 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就不难理解冯沅君们在面临文化抉择时的激进姿态,“五四”提出的所谓“个性解放”其实就是在个人利益和他者利益发生冲突时皆以个人本位主义为先,这一点在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中得到了极力的肯定。因此,当新女性在试图用文学作品描摹人生、人性时不约而同地显现出激进的一面,而女性文学出现的历史条件便是新知识女性独立诉说意识的觉醒。“文艺之可贵,即在其能抒写人之难言的痛苦与欢愉,苦闷而发出的叹息号泣,由喜悦而发出的欢欣的呼声,这就是‘文艺的原质。’”[3]当作家借助创作来发泄自身的愤懑、书写对自由幸福的向往之时,无疑她是兴奋的。正如当时青年人的精神导师胡适所言:“伟大作家的文学要能表现人生——不是那想象的人生。是那实在的人生: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情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4](P186)而作为“五四”时期畅销一时的小说集《卷葹》之所以在那个时代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响应,即和它主题的时代性休戚相关。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作为新生代的知识分子志趣相投、两情相悦。他们为了自由、爱情毅然决然冲破旧枷锁甚至不惜牺牲性命的行为,正是体现了“五四”精神中对正常、自然的人生权利的追求。正如有论者指出:“五四激进主义张扬的思想启蒙构成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根本动力,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核心,在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中显示了自身的文化风采和历史价值。”[5](P3) 然而,正像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五四”激进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其姿态的决绝也让新女性们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上产生困惑和迷茫。毕竟“五四”新文化是一种以西方理性精神否定传统伦理学的启蒙话语,其所推崇的新道德的核心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体现的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正义伦理[6]。而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所承袭至今的家族伦理、关怀伦理依然在众多新青年尤其是女青年中影响深远,这一点在《卷葹》中也体现得非常鲜明。作品中女主人公苦闷的根源便是个人自由与家族权威之间的矛盾冲突,当她为了个人幸福以莫大的勇气对抗以慈母为代表的家族权威时,心情无疑是痛苦且纠结的。“我爱你,我也爱我的妈妈,世界上的爱情都是神圣的,无论是男女之爱,母子之爱……我这次冒险归来的目的是要使爱情在各方面都满足。不想爱情的根本是只一个,但因为表现出来的方面不同就矛盾得不能两立了。”(《隔绝》)而在作家随后创作的《慈母》《写于母亲走后》《误点》这几篇小说中,对于母亲之爱和情人之爱的矛盾铺陈得更加淋漓尽致,对慈母的眷恋之情更是溢于言表。母亲与爱人、旧角色与新伦理时刻在困扰着这些善良、勇敢但又无法同过去彻底说再见的新女性们。在冷冰冰却又不乏公正、客观的正义伦理面前、面对母兄殷切的目光,得知儿时婚约对象迟迟不婚的消息,想到爱人的发妻被休后凄惨的未来,这些都无疑会触动新女性们脆弱而又敏感的神经。毕竟她们是在浓烈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代女知识分子,又恰逢一个新旧更迭交替的大变革时代,当母亲和情人在她们身上幻化为两种力量的争夺和撕扯,其思想上的游离和摇摆在所难免。因此,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学者们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卷葹》是‘五四’激情的余音,是走出封建家门而又徘徊于家门内外的勇敢而又脆弱的‘五四’女儿们的心理写照。”[7] 时至今日,当再次回顾“五四”那段历史,当在历史语境中再次品读《卷葹》,不由得让人思考:当一种风靡一时的文化思潮以极其具有感召力和蛊惑性的思想影响人民大众的时候,当它试图以“矫枉过正”的言论和行为改变社会各个领域现行秩序的时候,作为时代精英的知识分子应当作何抉择?诚然,时值20世纪初中国的大转折时期,“五四”激进主义思潮以其决绝的反帝反封建态度极大地鼓舞和启迪了众多知识分子投身于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之中,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深入民心,并成为新青年心目中的精神旗帜。它体现出的启蒙色彩和现代意识使之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毋庸置疑。在此种文化背景下,随着现代知识女性的出现以及她们作为独立个人的性别意识的凸显,女性文学创作逐渐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思想倾向抑或艺术风范,女性文学都与新文学主潮趋于一致:或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摇旗呐喊,或为社会进步、人的解放热烈呼唤。当女性作家们自觉地将反封建、妇女解放作为自己创作主题的时候,她们的书写无疑是兴奋而又沉重的。在“五四”女作家的创作视域内,她们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始终裹挟于一种巨大的焦虑感和迷茫感中。在“五四”这个既是思想解放的自由时代亦是文化批判的激进时代里,女性与激进主义思潮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特殊关系,激进主义思潮一方面给新女性们提供了独立言说的机会和实践理想的平台,另一方面也让新女性们遭遇到了来自家族伦理、关怀伦理的矛盾和纠结。这种矛盾心理促使她们以自身独特的女性经验和意识展现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面貌,以女性细腻的笔调真实地勾勒出新青年在理智与情感、亲情与爱情之间犹疑徘徊的心境。她们笔下塑造的那些游离于事业与家庭之间,彷徨于自我实现与妻性、母性矛盾中的时代女性形象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群落,有着它独特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在诸多文本的字里行间,透过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隐约地传达出女作家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思考:即便自由之爱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淫威,即便出走后的娜拉在社会上谋得了生存的权利,这些所谓新女性们依然无法摆脱传统的文化心理带给她们心灵上的系绊。面对未来,她们充满了迷茫和困惑。 究其根本原因,社会文化因素是女性创作个性中心理矛盾冲突的根源。如做具体深入分析,造成彼时女性创作这种矛盾的心理特质主要来自于西方现代文明同中国传统伦理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其实,每一种文化建构都有它独特的理论视野。传统与现代也好,东方与西方也好,它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和维度。依照黑格尔“存在即合理”的哲学体系,每一种文化都拥有其他文化永远无法僭越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毕竟“一个民族在长久的生命中要经过好几回这一类的更新;但它的本来面目依旧存在,不仅因为世代连绵不断,并且构成民族的特性也始终存在。这就是原始地层。需要整个历史时代才能铲除的地层已经很坚固,但底下有更坚固得多,为历史时期铲除不了的一层,深深地埋在那里,铺在下面。”[8](P347)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求同存异式的共存互补,而非剑拔弩张式的相互取代。当一种思潮以文学革命、伦理革命、文化论争等言论或行动的方式急剧、迫切要改变现存事物的时候,它的立场、态度难免失之公允。被启蒙的青年一代面临着在激进与中庸之间非此即彼的抉择,他们的彷徨犹疑在所难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摇摆构成了“五四”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普遍的矛盾心理:她们既享受着新思潮带给她们能够独立言说的兴奋与狂热,同时在传统文化的长河中又倒映出她们频频回首的倩影。基于此,对于“五四”激进主义思潮中所大力提倡之“新”与带有浓烈人伦色彩的传统文化之“旧”,当代学人们似乎应当以更为客观、理性的视角审视二者的关系。 收稿日期:2013-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