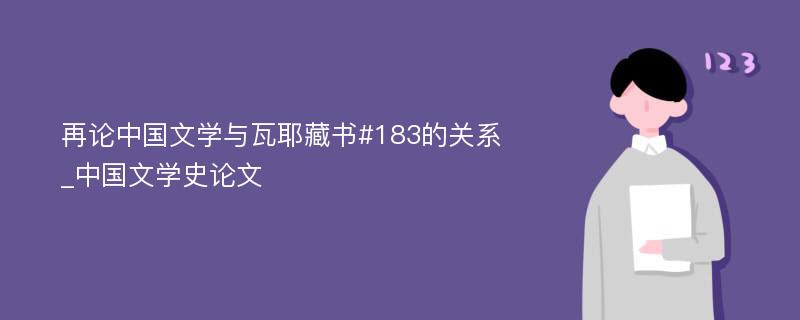
中国文献与《万叶集#183;相闻》关系之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献论文,关系论文,万叶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闻》是《万叶集》中三大分类名之一(注:四千五百余首万叶歌的三大分类为:《相闻》、《挽歌》、《杂歌》。其中《相闻》中有和歌1700首以上。除不足百首歌之外,其余皆为恋歌。)。它在日本和歌史上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万叶集》以后再也没有被使用过。就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特别是《相闻》的出典与语义,众多的研究者从各个方面、各个视野进行了探讨。在漫长的研究史上,对于《相闻》的研究,笔者以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七大学说:
1.仙觉、契冲的“恋爱说”
2.雅澄、岸本由豆流等的“文选出典说”
3.五味智英的“炫学说”
4.武田祐吉的“先行说”
5.山田孝雄的“往复存问说”(间接出典论)
6.伊藤博的“私情说”
7.小岛宪之的“法帖尺牍说”
从13世纪的仙觉,到20世纪的小岛宪之,七百年间,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的争论。其中山田孝雄提出“往复存问说”的《相闻考(补改)》一文(注:山田孝雄:《相闻考(补改)》,《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学研究会1950年5月。), 被誉为《相闻》研究史上具有转折点意义的论文。伊藤博的“私情说”几乎成为现在日本学界的通说(注:伊藤博:《相闻的意义》,《万叶》第五号1952年10月。)。
然而,通过回顾迄今为止的《相闻》研究史,我们看到对于《相闻》这一分类名的出典、语义以及被采用理由的论述,均还存在着问题。例如,山田孝雄和伊藤博两氏认为:“相闻”一语是“隋唐的惯用语”(山田孝雄)。“‘相闻’是中国一般的俗语、实用语、带有个人间的亲密感、融通度极高的词语”(伊藤博)。《万叶集》的编者依照中国当时的用法,设立了《相闻》这一分类名。问题是至今发现的二十余“相闻”的例句中,除《玉台新咏》有三首诗之外,其余全部为散文。表现男女私情的隋唐诗歌一首也没有。不仅如此,就笔者的管见所及,以口语唱出的汉乐府民歌、南北朝乐府民歌中也没有使用“相闻”之例。于是乎对于这种“惯用语”“俗语”“实用语”的说法,自然要产生疑问。对其语义,山田孝雄释《相闻》的“相”,为“交互之意”,“闻”为“以闻之闻”,即“往复存问”的意思。他认为把《相闻》解释为“恋之歌”,是错误的。《相闻》中的恋歌,是因在《相闻》这一极其广泛的范围内自然导入的。伊藤博则认为《相闻》“是以男女的恋爱为中心,相互传达个人间私情(包括亲爱、悲别、思慕等)之歌”。两者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分歧。使我们感到对于《相闻》的出典与语义,有结合中国文献进行再探讨的必要性。
一、万叶编撰者的困惑
《万叶集》的三大分类,受《诗经》的影响,三大分类名也来自中国,这已经为众多的日本研究者所赞同。他们认为:以宫廷诗等为中心的《万叶集》的《杂歌》与《毛诗》的《雅》,收集着与死相关联的《挽歌》与《毛诗》的《颂》,以男女的恋爱为中心的《相闻》与《毛诗》的《风》,内容分别相类似。《万叶集》的编者把和歌分成三大类,无疑是学习《毛诗》的结果,而分类名则利用了《文选》中的名称(注:伊藤博:《万叶集的表现和方法》上,塙书房昭和1975年。)。
诸如此论,其问题的焦点则在于《万叶集》的编者为什么采用了《文选》的分类名,而没有直接使用《毛诗》的《风》《雅》《颂》?尤其是《杂歌》《挽歌》直接从《文选》中借用,《相闻》却是《文选》没有、中国诗歌中也没有的分类名呢?在这里,前者与本论没有直接关系,姑且不论。笔者想讨论的是后者,即《万叶集》的编者为什么特别设立了《相闻》这一分类名,《相闻》到底是什么意思的问题。
其实在中国,《文选》以及其他正统文学里,没有与《万叶集》恋歌相当的诗歌分类名。古来中日两国的文学观存在着很大的相异性。正统的中国文学是与政治、理想密切相关的文学。日本文学、日本和歌的一个最主要的精神则是表现恋情。这是我们从奈良时代成书、日本最早的诗歌论著《歌经标式》以及后来的《古今集》序中可看到的。前者把和歌的本质定义为:“原夫歌者,所以感鬼神之幽情慰天下之恋心者也。”后者则宣称和歌以表现“心”为己任。《古今集》真名序中说:“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华于词林者也。”而用日语假名写成的假名序则更鲜明地指出:“和歌是以人之心为种子的。”由此我们看到,悲愤的文学表现的是志,爱的文学表现的则是心(注:参阅山口博:《闺怨的诗人小野小町》,三省堂1979年10月。)。由于文学观念的相异,当然,万叶编撰者在正统的中国文学中,找不到与和歌的恋歌相适应的分类名。在昭明太子萧统的主持下编撰的《文选》,体现的也是正统的文学观念。其中与《万叶集》的《相闻》最相近的《赠答》,也如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是对政治、道德、文学的关心的综合体。是些标榜人间善意的、公正的观照的诗”。仅有四首情诗的《赠答》,显然与拥有1600首以上万叶恋歌的分类名是不适宜的。
但中国文学的另一系统,即同正统文学相对立的中国民间歌谣,却从诞生时起,就是率直地歌唱心声的文学。《诗经》中民歌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代乐府的感其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早已为前人所指出。在民歌中,男女恋情这一人类诞生以来被表现得最多的主题,占有压倒多数的地位。以《诗经》的《国风》为首,汉乐府民歌、南北朝乐府民歌、明朝民歌等,形成了与正统文学相异、以歌唱爱情为主的文学体系。那其中大量的情歌,都是热烈、大胆地吐露心声之歌。表现男女私情可以说是中国民歌系统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在正统文学中找不到与万叶恋歌相类似分类名的情况下,《万叶集》的编撰者只有从中国民歌,具体地说,只有从乐府民歌中才能找到与日本和歌之恋歌相适应的文学。笔者以为所谓《相闻》,是从作为乐府情歌象征的《相和》及与《相闻》的歌唱方式有关联的《欢闻》中出典。这样大体以公的立场为主的《杂歌》《挽歌》,直接借用《文选》的分类名,而表现个人间、主要以男女恋情为主的恋歌,则从乐府民歌中出典,形成了《万叶集》的三大分类。
二、乐府民歌《相和》、《欢闻》的出典
(一)《相和》
“相和”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班固的《汉书·礼乐志》中:
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童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
南北朝时期,沈约的《宋书·志·乐三》中有:“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澈好声,善倡此曲,当时特妙。自晋以来,不复传,遂绝。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到了唐代,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又说:“……以上乐府相和歌。按相和而歌,并汉世街陌讴谣之词,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之。”对于“相和”的意思,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曾指出:“所谓相和,是一种演唱方式,含有‘丝竹更相和’和‘人声相和’两种意思。”沈约的《宋书》中将《但歌》和《相和》一并论述,这对于我们理解《相和》之意非常有利。两者原本民歌,它们的区别则在于《但歌》“无弦节”,即无伴奏,“一人唱、三人和”或“一人唱余人和”。而演唱《相和》时,与之相唱和的不仅仅是人,又伴有“丝竹”。这即《中国文学史》上指出的“人声相和”与“丝竹更相和”的两种意思。
汉武帝时代,设立乐府机关,采集了许多民谣。宋朝郭茂倩《乐府诗集》中说:“晋书乐志曰:凡乐章古辞之存者,立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鸟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其后渐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这些被采集来的民谣,在乐府机关“被于管弦”,成为能歌唱的乐歌。于是原本民间歌谣“演唱方式”的“相和”,一变为这类歌谣的曲名。从西汉开始,音乐机关分为太乐和乐府两个部分。将雅乐和俗乐分别进行管理。雅乐主要指周王朝以来统治者、上流社会的音乐。俗乐则为各地的民谣。采诗的目的,固然有历史学家指出的“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一面,而一些统治者对民歌、特别是其中的恋歌甚为喜欢的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视。下面的史料,就很能说明问题。
魏文侯最为好古。而谓子夏曰:寡人听古乐欲寐,及闻郑卫,余不知倦焉。子夏辞而弁之,终不见纳。 (《汉书·礼乐志》)
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
(《南齐书卷四六》)
魏文侯听古乐(先王之雅乐)则欲睡,而听郑卫之乐则“不知倦”的记载,表明了民歌或俗乐的魅力。汉乐府的设立与汉武帝爱好文学,喜欢俗乐有着很大的关系。据历史记载,武帝不喜欢雅乐,宴会、郊庙上演奏的都是些俗乐:
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
《汉书·礼乐志》)
这里的“非雅乐”即所谓郑卫《相和》之类俗乐。在中国历史上,“郑卫之声”被经学家们斥为“淫诗”、“淫声”。《论语》中有“子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朱熹的《诗集传》则说:“郑卫之乐皆为淫声”。其实这些被他们大加斥责的“郑卫之声”都是些大胆、率直、热烈的情歌。只不过他们没有勇气承认这个现实罢了。只好一方面从经学的立场把《诗经》中的情歌歪曲为“美后妃之德”“先王之化”“朋友之义”,一方面将它们视为“淫诗”“淫声”加以批判。这种歪曲的解释,也是《万叶集》的编撰者不能直接采用《风》作为分类名的一个重要原因。
曹魏时代,依照前朝,仍然是雅乐与俗乐分别管理。由于俗乐清商曲的飞跃发展,又设立了清商署。清商曲又叫清乐,它是汉魏六朝时代俗乐的总称。王运熙在《乐府诗论丛》中指出:“在文学方面,配合清乐歌唱的歌词便是汉魏六朝的一些乐府歌辞,主要是相和歌辞和清商曲辞。这些歌辞是乐府歌辞中最精采的一部分。”经过了南北朝的动乱,以及隋朝的洗礼,清乐仍占有一定的地位。到了唐贞观年间,使用十部乐,清乐为其中的一种。
综上所述,可见《相和》的特点之一,即来自民间,几乎都是民歌。《相和》是继《诗经·国风》之后的《国风》。有关这一点,中国研究者已明确指出过:
拿诗经相比,相和歌正是国风一类的歌谣。故郑樵《通志乐略》将相和歌例入《风雅正声》。清朱乾《乐府正义序》也说“以三百篇例之,相和杂曲,如诗之风”(注:王运熙:《乐府诗论丛》,中华书局出版1962年10月。)
其特点之二,则在于大多数为恋歌。像有名的《子夜》《欢闻》都是这一类。《子夜歌》四十二首中有:
夜长不得眠 转侧听更鼓 无故欢相逢 使侬肝肠苦
气清明月朗 夜与君共嬉 郎歌妙意曲 侬亦吐芳词
自从别欢来 奁器了不开 头乱不敢理 粉拂生黄衣
上面所引的三首恋歌,用词如日常口语,表现情感率直、大胆。这正是民歌作为民间文学的特色,与正统文学截然不同。对此后世文人曾这样赞叹道:
歌谣数百种 子夜最可怜 慷慨吐清声 明转出天然
丝竹发歌响 假器扬清音 不知歌谣妙 声势出口心
的确,歌谣的出色之处,就在于它的“出天然”“出口心”(注:郭茂倩:《乐府诗集·大子夜歌》。对于这两首诗,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这样指出:这是说,歌谣,不是假丝竹,而出心脱口,自然成妙音的。《大子夜歌》只有二首,似即为《子夜》诸歌的总引子。未必是民歌的本来面目,大约是当时文人们写来颂赞《子夜》诸歌的。其赞语的可靠性,是无可怀疑的。)。
我们可以说《相和》是《诗经》之后,乐府中恋歌的象征。这些表现人类永恒主题的恋歌,也得到封建时代统治者的喜爱,曾响彻于宫廷内外。而深受大陆文化影响的日本宫廷又是如何呢?关于这个问题,待第三部分一并论述。
故而,《万叶集·相闻》的“相”,不是“交互之意”,而是从如《诗经·国风》的民歌《相和》中出典。原本歌谣演唱方式、“郑卫之声”的《相和》,是乐府恋歌的象征,因此《相闻》的“相”不仅是唱和之歌,也包含着恋歌之意。若如山田孝雄氏所云,《相闻》没有恋歌之意的话,那么编撰者便没有特意设立这一名目的必要。像《挽歌》《杂歌》一样,直接使用《文选》中的《赠答》不是更为合适、方便吗?
(二)《欢闻》
《万叶集·相闻》的“闻”,应与乐府民歌中的《欢闻》有内在关系。陈朝释智匠(也叫智丘)在《古今乐录》里指出:“……《吴声》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凤将雏》,四曰《上声》,五曰《欢闻》,六曰《欢闻变》,七曰《前溪》,八曰《阿子》,九曰《丁督护》,十曰《团扇》。”宋朝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又有:“《吴声》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就是说《欢闻》等歌最初也是民谣,被乐府机关采用后,才“被之管弦”的。关于曲名的形成问题,梁朝沈约的《宋书·志·乐》说:“《阿子》及《欢闻歌》者,晋穆帝升平初,歌毕辄呼‘阿子,汝闻不’,语在《五行志》,后人演其声,以为二曲。”《古今乐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欢闻歌》者,穆帝升平初,歌毕辄呼‘欢闻不’,以为送声,后因此为曲名。”两者都说《欢闻歌》为晋朝穆帝时所作。这里的“汝闻不”和“欢闻不”作为送声之语,最终则成了新曲名。
据郭茂倩的《欢闻歌》“其始皆徒歌”的说法,我们可以想见这种情景:当初,在民间唱和《欢闻》等歌的时候,一唱完,便向听者兴奋地喊道:“阿子,我的歌你听见了吗?”其欢呼沸腾之场面可想而知。
这种民间的演唱方式,随着歌谣被采入乐府,“被之管弦”,则被上流社会所接受,继而成为这类歌谣之曲名。这样从民间到上流社会,当时知道这些《欢闻歌》的人一定不少。现在被保存下来的《欢闻歌》并不很多,但全部是恋歌。像下面的《欢闻歌》,表现的就是男女间的恋情:
遥遥天无柱 流漂萍无根 单身如莹火 持底报郎恩
艳艳金楼女 心如玉池莲 持底报郎恩 俱期游梵天
南有相思木 合影复同心 游女不可求 谁能息空荫
于是我们是否可以说,《相闻》的“闻”不是“以闻之闻”、“以复存问”之意,而是从《欢闻》出典,取的是“你听见了吗”的意思。《相闻》则为“我的恋歌(我的歌)你听见了吗”这样男女间充满浪漫气息的、带有亲切之感的、亲戚友人间的唱和也可包括在内的分类名。
三、推论之证据
A.日本著名民俗学家折口信夫曾指出:“《相闻》是对唱之歌”(注:《折口信夫全集》第一卷,中央公论社1972年版。)。我们如将这一性质,与《万叶集》中歌垣的对唱情景,以及在当时日本宫廷大为流行的踏歌一并考察的话,就会更加坚信这种出典之可能性。
所谓歌垣,是指春季或秋季,在山上、水边等地举行的唱歌大会。男女通过相互对唱表达爱情,寻求配偶。在唱完表达爱的恋歌后,向对方叮问:我的恋歌你听到了吗?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诸如此类的光景也是可以想见的一般常套。对于歌垣,史书的《日本书纪》、《古事记》及《风土记》上都有记载。而《万叶集》中更有诗描述了在那青年男女对唱传情之时,已婚男女则“他人之妻我相交,我之妻与他士欢(一七五九番歌)”的场面。
至于踏歌又叫蹈歌。是一种众人手拉手,以足踏地而歌的集团歌舞。原本中国古代的风俗习惯,现在可见的最早资料是晋朝葛洪的《西京杂记》。上面记载了汉代的宫女们“以十月十五日……相与联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之事。《旧唐书·睿宗纪》中也记有:
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蹈歌。
中国都市的踏歌风俗,传到奈良时代的日本后,与古代民间歌垣相合流,被宫廷化、艺能化了,成为宫廷的风流文艺。这一点早已为日本学者所确认。日本史书中也有许多关于踏歌的记载。
天武天皇,三年正月朔,朝大极殿诏,男女无别,暗夜蹈歌。
(《伊吕波字类抄》所引《本朝事始》)
晚头移幸皇后宫,百官主典以上陪从踏歌,且奏且行,引入宫里,以赐酒食。
(《续日本纪》圣武天皇七三○年)
这种踏歌在演唱中途,或结束时,也像《欢闻》一样有呼喊之举,反复喊出“万年春”“千春乐”等语助兴。
如此,日本民间的歌垣对唱、众人在音乐的伴奏下,且唱、且舞,欢呼雀跃的宫廷踏歌,与前面谈到的《相和》的“人声”“丝竹”相唱和,《欢闻》结尾时呼喊“阿子,汝闻不”“欢闻不”的情景相当类似。可见《万叶集》编撰者将乐府《相和》《欢闻》合二而一地出典设立《相闻》,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并非凭空而造。
B.关于《万叶集》成书的具体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学者们也说法不一。一般则认为一卷到十六卷为745年前成书, 余下的十七到二十卷,即《万叶集》的最后完成大约在770—780年之间。其实在万叶时代,中国的乐府等乐歌,伴随着大量的大陆文化早已传入日本,并已开花结果。在当时的日本,“礼”和“乐”的作为儒教的政治措施,受到极大的重视。为学习“礼”的大学寮与为学习“乐”的雅乐寮(也叫乐府),分别在天智朝(661—671年)、天武朝(686—697年)间创立。而这“二寮”已被制度化之事,在701 年成立的《大宝律令》中可以得到验证。同时大学寮467人、雅乐寮429人的职员队伍,也可见被重视之程度。其后从孝谦天皇(749—758年)统治时期的敕令:“敕,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乐所兴,惟在二寮”(《类聚三代格》)中,又可见礼乐繁盛之一斑。
正如日本学者所说,既然设置了这样的机关,那么其中也理所当然应该有大陆音乐。据折口信夫的研究:雅乐寮实际上是由外国音乐部和日本音乐部两部分来分别掌管的(注:《折口信夫全集》第一卷,中央公论社1972年版。)。其中的外国音乐部有唐乐、朝鲜三国之乐、吴乐,也为学者们指出(注:获美津夫:《通过古代艺能看日本和勃海的交海》,《环日本海论丛》第八号,1995年9月。)。 就是说乐府歌的《相和》《欢闻》等也应在其雅乐寮之中。并且日本的《令义解职员令》还明确记载着雅乐寮有唐乐师之事。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唐朝的音乐频繁地在日本朝廷上演奏的记载。例如,《日本书纪》持统七年(693 年)正月:“汉人等奏蹈歌。”持统八年正月又有:“唐人奏蹈歌。”在这里,汉人、唐人演奏的“蹈歌”当然应该是中国的乐曲。《续日本书纪》圣武天皇天平七年(735年):“入唐回使及唐人奏唐国·新罗乐。 ”入唐回使及唐人一起演奏唐乐、新罗乐,反映了当时音乐交流之盛况。又称德天皇神护景云元年(767年):“奏唐高丽乐及内教坊踏歌。 ”如上,足见大陆音乐在日本之繁荣。不用说以表现恋情为和歌主要精神之一的日本民族,对于《相和》《欢闻》之类恋歌,更容易产生共鸣。
C.《相和》和《欢闻》分别在《汉书》、《宋书》、《古今乐录》及《玉台新咏》等典籍中有所记载。而这四部典籍在宽平三年(891 年)以前成书的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均被收录。就是说在891年以前,这些典籍确实传到了日本。 万叶时代的人们读到这些典籍是可能的。不言而喻,在雅乐寮中《古今乐录》之类书籍,是不可缺少的。而在那个任用官吏采用唐代的科举制,学问和仕途一体化的时代,除了《大宝律令》中明确规定必学的《毛诗》《论语》《周礼》等经典外,所谓的“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也很受重视。至于《玉台新咏》对于万叶人的影响,在日本学者中论述极多。比如著名学者中西进在论及大诗人大伴家持的望乡歌(四一四二)时,曾指出:可以判定家持是否知晓《折杨柳》诗的资料,我们没有。然而《玉台新咏》是与《万叶集》最相近的诗集(注:中西进:《万叶论集》第三卷,讲谈社1995年7月。)。 著名学者小岛宪之曾就日本上代歌谣与中国歌谣具有哪些影响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许多考察(注:小岛宪之:《上代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上,塙书房1986年版。)。在论述日本上代歌谣的《歌返》时,列举了中国乐府的《欢闻歌》、《欢闻变歌》、《子夜歌》、《子夜变歌》,指出一些学者认为日本上代歌谣的《歌返》,是由中国的《变歌》的命名而来的说法值得重视。并进一步论证了日本的记纪歌谣(注:记纪歌谣是指《古事记》与《日本书记》中所载日本歌谣。)、《琴歌谱》以及文献中可以见到的歌谣名(某振某歌)等,有很多是参考了中国歌谣命名方法而诞生的。先学的这些研究成果,已为我们验证《相闻》的得名,提供了极为有力的佐证材料。
如上所述,《万叶集》的编撰者之所以自己设立了《相闻》,就在于中日两国文学观的相异,中国没有现成的可以借用的分类名。毋庸赘言,既然是自己创作,就要考虑到与这类歌群的特点相适应。而在中国学问的大热潮时代,编撰者不肯勉强了事,特意设立的分类名,既没有出典,又不能表现其恋歌的特色,只是单纯地借用一个名词,这是很难想像的。正如日本学者已指出的那样,《相闻》的设立有知识阶层的“炫学意识”(注:五味智英:《万叶的分类与支那文学》,《国语与国文学》1938年4月)。 编者意欲炫耀汉籍知识渊博的一面我们也必须考虑到。
《万叶集》分类名的设立之初,可以说编撰者们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在内容上追随《诗经》的三大分类,形式上适合于和歌的分类名称则借用,不相适应的也不过于牵就。《相闻》这一分类名应该说是独特的创造。它含有那个时代知识阶层的“炫学意识”,同时也表明了那个时代知识阶层对于汉学的精通。它的值得称道之处,则在于不仅具有一定的出典,而且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万叶恋歌的实态及日本民族的文学观念。
标签:中国文学史论文; 万叶集论文; 诗经论文; 子夜论文; 挽歌论文; 玉台新咏论文; 汉书·礼乐志论文; 民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