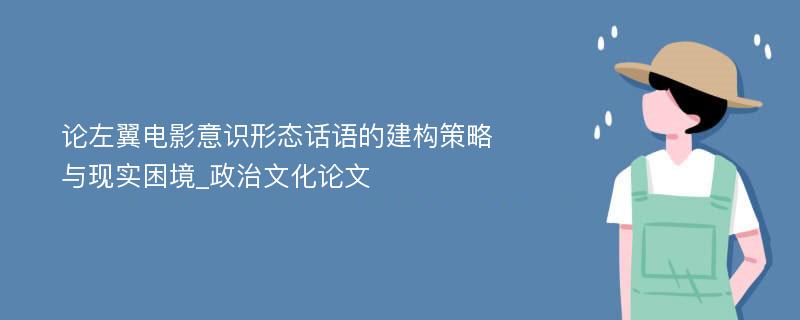
论左翼电影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策略及其现实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困境论文,话语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9)05-0103-05
作为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一场新兴电影运动,左翼电影特指进入电影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电影文化人士参与制作的进步影片。概括起来说,左翼电影具有如下基本思想内涵:阶级意识是左翼电影的内在特质;批判性地介入现实是左翼电影的主要目的,揭露和反抗是其两大主题;反帝、反封、反资是左翼电影的主要历史使命。就创作主体而言,参与制作左翼电影的人士既有作为共产党人的左翼作家如夏衍、阿英(钱杏邨)、阳翰笙、田汉等人,还包括一批思想向左转的电影界文化人士(我们可以称之为左翼作家的同路人),如郑正秋、蔡楚生、孙瑜、吴永刚、欧阳予倩等。从题材来看,左翼电影突破了20世纪20年代电影的狭隘圈子,将镜头对准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聚焦于农村农民、城市工人与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妇女乃至儿童。从主题来看,左翼电影文本大致有如下几种表现形态:(一)左倾意识非常突出,主要意图在于宣扬阶级斗争与革命反抗;(二)具有一定的左倾观念,但阶级意识表现得不十分明显,侧重于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现实社会;(三)抗日救亡电影,目的在于宣传民族救亡图存意识,因而包括1936-1937年的“国防电影”。上述几种表现形态有时还相互交织在一起。
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中,左翼电影人挖掘新的现实题材,灵活运用了多种策略,基本实现了其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但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左翼电影也遇到了诸多的现实困境,从而使得其文本呈现出了异常复杂的面貌,这也许是左翼电影人士所始料未及的。
一、社会聚焦: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多声部变奏
如前文所述,左翼电影具有大致趋同的意识形态内涵,这是其“共性”,但由于创作主体(主要是编剧与导演)电影观念的差异与政治立场的一些分歧,加之电影生产受到电影审查机关、资本家以及市场的制约,相当一部分左翼电影文本又带有明显的独特“个性”。关于这一点,在以现实社会为主要题材的左翼电影文本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为中共党人的夏衍、阿英、阳翰笙等左翼作家,他们进入电影界正值宣扬阶级斗争、鼓吹革命反抗的红色30年代,当时中国共产党带有左倾思想的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了国内的形势,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处于阶级对立十分严重、人们生活普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因此要求文艺发挥战斗作用,为政治服务。作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回应,1931年9月,“左联”在《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对于电影作出了明确的要求:“……目前为取得映出底公开性以深入各大小都市各市民层起见,剧本内容暂取暴露性的……同时,为准备并发动中国电影界的‘普罗·机诺’运动与布尔乔亚及封建的倾向斗争,对于现阶段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加以批判与清算的必要。”①由于夏衍等左翼电影剧作家基本上都参加过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并加入了左联,“左倾”政治观念本来就比较浓厚,加之“左联”对电影的明确要求,因而从1933年开始,左翼作家采用暴露性策略创作了大量直接表达阶级斗争或者民族救亡的影片:《狂流》(夏衍编剧,1933)《盐潮》(郑伯奇、阿英编剧,1933)《压迫》(洪深编剧,1933)《民族生存》(田汉编导,1933)《肉搏》(田汉编剧,1933)《时代的儿女》(夏衍、郑伯奇、阿英编剧,1933)《上海二十四小时》(夏衍编剧,1933)《母性之光》(田汉编剧,1933)《铁板红泪录》(阳翰笙编剧,1933)《中国海的怒潮》(编剧阳翰笙,1933)等等。左翼作家创作这些电影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意图。夏衍曾经毫不避讳地直言当时搞电影就是为了革命和左翼文化运动;钱杏邨(阿英)将电影视为宣传工具;席耐芳(郑伯奇)认为电影应该赤裸裸地暴露现实的矛盾与不合理,把它摆在观众的面前,使他们深刻地感觉社会变革的必要,使他们迫切地找寻自己的出路;阳翰笙希望中国电影向着反帝反封的方向前进;田汉则强调用革命的世界观来把握电影创作。因此,这些电影以先在的阶级观念和革命意识为指导,结合当时农村的灾荒与破产、城市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小市民生活贫困以及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等社会现实来挖掘题材。为了强化主题,它们往往将人物放在特定的阶级范围内,展示他们之间在阶级和道德方面的二元对立与激烈冲突,通过他们的个人或家庭命运、男女两性之间的爱情悲剧来展示当时社会的严重阶级对立或者民族危机,号召人们起来奋起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激进的左翼作家大多采用了暴露性策略来建构其电影政治话语,但他们的创作个性并未得以消除。比如,夏衍的电影剧作立足于真实的生活,以鲜明的主题与深刻的思想来反映中国农村和城市的阶级压迫与社会矛盾,叙事结构讲究精练简洁,表现手法极具概括性,是一种具有深刻理性的现实主义;阳翰笙的电影剧作则充满了鲜明的战斗色彩,几乎直接将阶级斗争或民族救亡斗争搬上银幕,表现出明显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特点,流露出一种直率、粗犷、明朗和高昂的艺术格调;而田汉这一时期的电影剧作带有突出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人物塑造方面理想多于理性,观念多于写实,粗疏的写实与战斗的浪漫是他这一时期电影剧作的风格基调。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暴露性的左翼作家电影大多命运多舛,尤其是那些直接反映阶级斗争的影片更是如此。自1933年底“艺华”公司被捣事件、1934年明星公司解除夏衍等人的编剧职务之后,左翼作家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随着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加剧,为顺应社会发展的大情势,左翼作家将电影创作主题重心转移到了抗日救亡上,如《同仇》(夏衍编剧,1934)、《夜奔》(阳翰笙编剧,1937)、《青年进行曲》(田汉编剧,1937)等影片。
作为左翼作家电影创作的同路人,郑正秋、蔡楚生、孙瑜等人在拍摄一些带有一定左倾观念的社会批判电影时采用了与左翼作家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方式。比如郑正秋编导的《姊妹花》虽然在其中灌注了一定的阶级意识,但他并没有为了前进的“意识”而放弃自己的平民视野,更多地是采用一种大众化策略以达到煽情的效果。蔡楚生强调电影的“写真”,但反对把电影作为纯粹政治宣传的工具。在他导演的《都会的早晨》、《渔光曲》、《迷途的羔羊》等影片中, 蔡楚生严格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纪录,尽管这些电影也流露出了一定的阶级意识,但显然没有左翼作家电影那么激进,他力求在电影中实现思想性、艺术性与娱乐性的综合平衡。孙瑜电影关注现实,并将其对现实的感怀与憧憬投射到影片的人物、情节和细节之中,以丰富的镜头表现“诗化”的人生与理想化的社会,体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他的影片中也具有社会批判与革命主题,但却通过“诗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使得其电影美学风格既不同于左翼作家电影那种过于沉重的基调,也与郑正秋、蔡楚生等人的苦情戏拉开了距离。正因为如此,石川认为:横亘在孙瑜文本与主流政治话语之间是一道永远也无法弥合的深深裂痕。“孙瑜电影既折射出作者自身的美学趣味,也叠映着孙瑜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政治。它虽然努力向着时代靠拢,却不能最终融入时代政治的主流”。②
面对国民党的电影审查与电影资本家的压力,袁牧之、沈西苓、费穆等人在一些社会批判影片中采用隐喻方式来暗示其政治理念。在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中,用一个摩天大楼摇至柏油路下的底层然后切到贫民窟的镜头组合来表述贫富之间的巨大差异并隐含了阶级冲突的主题。沈西苓的《十字街头》中,影片在开头就以一个大俯拍的全景镜头来以十字大道表现人们的迷惘与彷徨之感,而结尾的长镜头下,宽阔大道上四个青年坚定勇敢的步伐,喻示了他们的出路。费穆导演的《狼山喋血记》则通过寓言式的隐喻来表达共同抗日的主题。即使作为左翼作家的夏衍,在他编剧的《压岁钱》中,最后出现的大批银元被外国货轮载走的镜头,暗示出影片中描写的一切罪恶现象,都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压榨中国人民所造成的。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上述电影以隐喻的策略来建构意识形态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渗透策略。
二、女性电影:流行文化/意识形态化改造/政治观念符号
自19世纪晚期开始,女性由狭小的家庭步入了社会舞台,以月份牌的现代女性形象为肇始,到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上海通过印刷文化的文字和图片以及电影的影像为现代妇女提供了很大的形象展示空间。在文化公共空间的强力推动下,女性形象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在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与电影、关注女性命运的人道主义电影以及第一次商业电影浪潮中,女性形象一直是读者与观众的关注热点。同时,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下,女性的命运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因此,三十年代的上海电影界出于商业利益和现实社会环境的考虑,拍摄反映女性命运影片,通过女性形象来获得市场卖点乃是必然之举,左翼电影也概莫能外。
左翼拍摄的女性电影中,都一致批判了黑暗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反映了一定的阶级意识。但由于意识形态观念的分歧,这些电影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具有明显的差异,如《飞絮》(邵醉翁编导,1933)、《飘零》(高天栖编导,1933)、《海棠红》(欧阳予倩编剧,1936)、《小玲子》(欧阳予倩编剧,1936)、《神女》(吴永刚编导,1934)、《船家女》(沈西苓编导,1935)等影片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达对社会的批判,展示了女性所受的封建专制制度或者阶级压迫,基本上遵循了20年代以来郑正秋等人关注女性命运的人道主义电影的创作思路,但这些电影已经突破了以前的电影将女性命运放在狭小的家庭生活背景下来加以展示的局限,社会背景更为广阔,有的已经具备了较为明显的阶级意识。由于严格遵守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这些电影只揭示了女性的悲惨命运,表达了社会批判,没有给女性指明出路。夏衍编剧的《脂粉市场》(1933)、《前程》(1933)、《自由神》(1935)表达了在黑暗的社会背景下,小知识分子女性在职业和爱情方面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挫折,只有自强自立、积极投入社会才有真正的出路。而由田汉编剧的《三个摩登女性》(1932)、沈西苓编导的《女性的呐喊》(1933)、孙瑜编导的《天明》(1933)、孙师毅编剧的《新女性》(1935)则在批判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对女性进行了新的意识形态的规劝:即女性要摆脱阶级压迫只有投身于革命事业。《三个摩登女性》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肯定和歌颂了热爱劳动、为大众利益英勇奋斗的女接线生周淑贞,批判了资产阶级女性虞玉和小资产阶级女性陈若英;《女性的呐喊》以小知识分子女性叶莲依靠个人奋斗追求幸福生活失败而最终投入革命的洪流,来传达只有社会解放才能实现个人解放的革命观念;《天明》中的菱菱从被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而破产的农村来到上海,却又受到资产阶级的身心摧残,终于觉醒起来为保护革命者而勇敢献身;《新女性》塑造了两个命运不同的女性:小知识分子女性韦明、觉悟了的女工人李阿英,面对残酷无情的社会,韦明在个人婚姻和事业上都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最后自杀,而李阿英不仅依靠自食其力,而且领导女工为保障权益进行斗争,影片的最后,一群女工唱着《新女性》歌曲,从印有“摩登女郎”照片的报纸上踏过,向初升的太阳走去。
左翼反映女性命运的电影是在三十年代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上升的中国现实社会环境下出现的,因此这些电影通过女性形象来批判社会和对女性进行意识形态规训带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左翼电影人及时将中国社会的现实搬上银幕,借助女性的命运喻示民族的命运,巧妙表现了中国社会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关系的变化,使得左翼电影犀利的反帝反封建锋芒与之前影片温情的‘移风易俗,针砭社会’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和人道主义取向’形成鲜明的对比。”③但像《自由神》、《三个摩登女性》、《女性的呐喊》、《新女性》等女性电影文本基本上都是以先在的政治观念为出发点,借助女性形象作为流行文化的特点来传播阶级或者革命意识,使得这些电影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成为了一种政治观念符号。左翼女性电影所遵循的这种流行文化/意识形态化改造/政治观念符号的思维模式消除了人物个性的丰富性与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对人物的思想转变进行了过于简单的处理,因此,尽管这些电影表面上给女性指明了出路,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仅仅只是为女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出路,并不见得可以真正解决女性命运问题。
三、电影歌曲:作为传达意识形态观念的第二文本
左翼电影运动开展时期正是音乐进入电影的高潮时期,面对电影歌曲在流行文化中的巨大影响力,加上电影歌曲在当时的电影审查中不那么严格,左翼电影人自然想到了利用电影歌曲作为构筑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第二文本。一些左翼作家和音乐家创作的电影歌曲在影响力方面甚至超过了电影文本本身。比如人们现在对许幸之导演的影片《风云儿女》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但这部影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到后来还成为了新中国的国歌。参与制作电影歌曲的左翼电影人包括田汉、聂耳、冼星海、孙师毅、关露、安娥、贺绿汀等人。他们创作的用来传达政治观念的电影歌曲有:《开矿歌》(《母性之光》中的插曲,田汉词、聂耳曲,这是左翼电影第一次唱出工人阶级要求解放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影片《桃李劫》主题歌,田汉词、聂耳曲)、《大路歌》(影片《大路》主题歌,孙瑜词、聂耳曲)、《春天里》(影片《十字街头》插曲,关露词,贺绿汀曲)、《自由神之歌》(影片《自由神》主题歌,孙师毅词、吕骥曲)、《夜半歌声》(影片《夜半歌声》主题歌,田汉词、冼星海曲)、《黄河之恋》(影片《夜半歌声》插曲,田汉词、冼星海曲)、《青年进行曲》(影片《青年进行曲》主题歌,田汉词、冼星海曲)等。这些电影歌曲所表达的政治观念主要是反帝、反封与反对阶级压迫,其介入电影叙事文本的策略则具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歌曲内容与叙事文本的主题基本保持一致,如《开矿歌》、《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春天里》、《四季歌》、《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等。这些歌曲或通过直白或通过暗示与象征,与电影画面完美结合,成为了抒情和提升主题的重要手段。第二种类型为歌曲内容与叙事文本的主题保持分离。如《毕业歌》、《自由神之歌》、《黄河之恋》等。如影片《桃李劫》、《自由神》、《夜半歌声》明明都是批判社会黑暗的,但其主题歌或插曲宣扬的却是抗日内容。在音乐题材的来源方面,左翼电影人一方面自己动手独创歌曲,另一方面对传统民歌与流行歌曲加以适当的改造,以符合自己的政治意图。在表达政治观念时左翼电影歌曲大多采用对比的直白的语言,强调呐喊和激情,注重一种火山爆发式的艺术风格。作为当时民族矛盾上升时期的社会情绪的一种表达,左翼的这些火山爆发式电影歌曲意在激发观众抗日救国情感,通过影片在社会上广为传播,鼓舞了很多青年热爱祖国的激情,使他们勇敢地奔赴民族解放的战场,这在当时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
四、左翼电影所遭遇到的现实困境
左翼电影人在电影中不遗余力地采用了灵活多样的话语建构策略,以达到其意识形态图谋,但遇到了诸多的现实困境,并不见得真正实现了其政治目的。以左翼作家的暴露性电影作品为例,首先,南京国民政府对这些暴露性作品大为恐惧,同样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考虑,他们一方面通过电影检查的手段对一些左翼电影予以禁演、删减或窜改,《上海二十四小时》、《中国海的怒潮》在电影审查中被剪去将近三分之一并被禁映将近两年,像《铁板红泪录》、《香草美人》、《民族生存》、《压迫》等影片都遭到“电检会”的大加删改。这样一来使得上述影片的原初意识形态观念出现了变异,影响了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当局采用武力威胁和恐吓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制作所谓“赤化”电影的影片公司以及电影从业人员,1933年底“艺华”公司被捣事件、主演《盐潮》的女演员胡蝶遭到人身威胁就是明证。迫于当局的强大压力,1934年,明星公司被迫解除夏衍等人的编剧职务,这些左翼电影工作者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这就出现了夏衍所谓的“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里潜行”的左翼电影文化运动局面。左翼作家这些影片在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采用过于外露政治锋芒的策略是有深刻的教训的。其次,这类暴露性电影在市场上也遇到了挫折。1933年左翼作家参与编剧的一些反映农村破产与灾荒的电影作品如《狂流》、《铁板红泪录》、《春蚕》、《盐潮》等陆续上映之后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市场效应。《春蚕》首轮映期为五天,《铁板红泪录》则仅仅只有三天。对此结果,明星公司《明星月报》1934年1月的新年题词不无忧虑:“这一年中,制作者采用最多的剧本是以农村破产为题材的,为什么不约而同的采用了这一种剧本?对于观众的影响如何?在另一方面,这一年中,国产影片的营业渐见衰败,为什么会得到这样恶劣的结果?这些,我们都当仔细的估量一下,以来决定未来的路线。”④这些左翼电影票房不理想,除了电影本身的缺陷之外,与观众的兴趣也不无关系。大多数观众买票进影院不是为了受教化,而是想获得视听愉悦,况且早期的电影观众大多为小市民、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他们对农村生活不熟悉,自然就对这类影片没什么兴趣了。这说明,即便“意识正确”,左翼的这类电影如果不考虑观众的俗趣与身份特征,是很难获得市场的,其进行革命宣传与教化的政治意图当然也就无法实现。
第三,一些暴露性的左翼电影作品还遇到了来自左翼内部影评人士与“软性电影”论者的批判。左翼电影人士柯灵在论及一些暴露性的左翼电影的主题解决手法时说:“用了凑巧、逃避的方法”,又给影片“加上一条‘光明的尾巴’”的所谓“指示出路”,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的欺骗”。⑤另一位左翼人士铭三在批评“暴露主义”时说:“暴露只是一种游击,只能动摇个人底意识而不能变更社会底制度。”“真正的艺术底作品应该是储满的”,“燃起了未来之光的,不单单只是暴露。”⑥左翼作家的同路人,包括同为暴露性的左翼电影剧作家,他们在是否应该“暴露”,以及如何“暴露”上亦存在着分歧。1933—1935年出现“软性电影”论者则明确反对突出电影的宣传作用,认为电影的主要作用是娱乐,要重视艺术性,淡化政治性。这些人在遭到了左翼电影界人士的大规模批判后,反而攻击左翼电影和理论是“垃圾”、“毒素”,“是受到了主义或某派的宣传遗毒的结晶”。并且他们还拍摄了一部分“软性电影”来与左翼电影争夺市场。因此,暴露性的左翼电影在内部和外部都承担了众多的压力。
最后,左翼作家这类电影还有来自于自身的创作困境。左翼电影剧作家大多来源于小资产阶级阶层,他们很多人对农村与工人生活状况并不是十分了解,多数影片过于偏重思想意识,在艺术上则显得粗糙,以至夸张、失真,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概念化、雷同化、简单化的弊病。《丰年》、《民族生存》、《盐潮》、《肉搏》、《母性之光》等影片都缺乏人物性格的具体刻画,对人物的思想转变过程也作了非常简单的处理,实际上是违反现实主义精神的。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左翼电影剧作家们在参加左翼文学运动时就受到了日本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苏联“拉普”的唯物辩证法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新写实主义、唯物辩证法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强调写“真实”,但都把先进的世界观摆在首位,导致无法真正地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最终摆脱不了左倾机械论观念与庸俗社会学偏向。左翼作家也把左翼文学思潮中的这些创作方法带入了电影,由于过分地遵循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以先进的世界观为前提,面对现实题材不是以感性情感来烛照社会生活与人物形象,而是以理性的集团话语来概念化地宣扬阶级斗争与民族救亡,故而很难激活观众的情感。
与左翼作家的暴露性电影作品一样,左翼的一些女性影片由于带有鲜明的阶级意识与革命观念的话语建构,也遭到了国民党“电检会”的删改,《三个摩登女性》、《女性的呐喊》就是如此。而与此同时,由于女性形象是作为一种流行文化而出现在“公共空间”中的,观众对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关注更多的是看能否满足自己的感官视觉,比如,为了批判那些沉溺于都市享乐的女性,左翼电影在反映女性命运的影片中塑造了一批反面女性形象,像《三个摩登女性》中的虞玉、《女性的呐喊》中的爱娜等,左翼电影本来是想以她们来突出进步、独立女性形象,但她们在具有好莱坞风格的柔光和感性光源映衬下,被镜头情色化、性感化了,激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而那些旨在体现阶级意识与民族救亡等左翼思想观念的觉醒女性形象,由于在镜头中以非情欲化、非性别化的面貌呈现出来,反而难以引起观众的共鸣。为了迎合观众,左翼电影人尽管启用了一批青春美貌的女演员,如黎莉莉、王人美、周璇、白杨以及老牌明星胡蝶与阮玲玉,但也未获得预期的市场效应。这说明左翼电影的意识形态观念对观众的教育和改造作用极为有限。方岩在《〈自由神〉与中国妇女》一文中不无失望地指出:“看了《三个摩登女性》、《新女性》、《女儿经》,以及将公映的电通的《自由神》,不能不说中国的文化进步之速,尤其是电影,可是大多数的妇女们,在这世界浪潮的袭击下,文化运动的推进中,好像没有感觉似的,仍旧重温着‘贤妻良母’,‘回到厨房’去的旧梦。”⑦
此外,由于个人政治观念的差异,左翼电影创作者与左翼影评人士之间对女性电影的思想主题存在着分歧。大部分左翼女性电影都遭到了左翼影评人士不同程度的批评。比如,王尘无批评《新女性》反帝反封的程度有限,没有真正表现大时代中的新女性。苏凤认为《女性的呐喊》对于女性出路的指示含混而空虚,事实上没有真正的呐喊。陈鲤庭认为《脂粉市场》人物身份定位不当,爱情穿插无聊,思想内容不深刻,不简洁。苏凤、鲁思批评《三个摩登女性》讽刺的方面多余、指示的方面空虚。
五、余论
左翼电影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的政治情势下兴起的,左翼电影人试图通过电影的意识形态化来鼓动人们起来革命(反帝反封反资),是一种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奋斗的理想化想象在文化运动上的反映。左翼电影人那种不屈不挠反抗专制、压迫和黑暗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既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同时也体现出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与时代感。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中,左翼电影挖掘新的现实题材,借鉴和创造新的电影语言,灵活地运用多种策略,力图实现其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为中国电影步入新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⑧左翼电影将人们从二十年代早期电影武侠神怪片和个人情感片所导致的麻木钝化的审美感觉中解放出来,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在实践中,电影本身不能变革现实,但电影能够从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革命中,吸取灵感和发展它自身的艺术形式。左翼电影意识形态话语所展示出来的那种社会与时代氛围,即左翼电影在其中被创造并对之诉说的、规定了它的功能和意义的独一无二的历史性情境,是任何其它电影所无法表现的。尤其重要的是,左翼电影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模式对于之后的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革命进入电影的滥觞。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电影”、“文革电影”中的革命政治话语建构均可以从左翼电影中找到源头。
但是,毋庸讳言,大部分左翼电影是在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出现的,其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带有明显的左倾观念。它们将电影作为对大众进行革命启蒙的工具,不懂得艺术的社会政治作用与它的审美形式功能始终只能保持着辩证的关系,在电影的艺术形式与政治革命以及娱乐功能的关系上存在着一些观念误区。比如,它们颠倒了艺术与政治功用的关系,把电影这种艺术加以意识形态压制性使用,结果使之与社会现实相脱节。“艺术不能为革命越俎代庖,它只有通过把政治内容在艺术中变成元政治的东西,也就是说,让政治内容受制于作为艺术内在必然性的审美形式时,艺术才能表现出革命。”⑨大部分左翼电影运动者仅仅立足于政治领地,试图让电影屈从于社会革命的完成,削平艺术与激进革命之间的张力,以致使艺术丧失了自身的变革层面。这种认为艺术在变革世界中必须成为一个因素的这种基本观点,就会很容易变成它的反面。因为直接吁求政治的艺术尽管具有反抗性但往往会由于其表现形式的粗糙直接性而被市场吞没和变形,变得无甚棱角。大部分暴露性左翼电影遭到观众的冷遇就是一个现实的例证。
大部分左翼电影力图对苏联革命电影和美国好莱坞电影模式进行本土化的“重写”,以期达到政治目的,但在文本中由于它们并未能将上述两种电影语言很好地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性,忽视了电影与生俱来的商业性与娱乐功能。⑩因此,尽管左翼电影人颇为努力,而所取得的成效却十分有限。而少数左翼电影艺术家,比如蔡楚生、袁牧之、沈西苓的一些影片在思想、艺术与娱乐方面实现了很好的结合,获得了市场的轰动效应。他们这种综合平衡电影各要素的艺术观念也许更容易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大部分左翼电影在试图对现实加以意识形态改造时却反而被现实所改造。因此,与其说它们在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时采用了灵活的策略,倒不如说是一种被现实改造的结果。
收稿日期:2009-06-08
注释:
①陈播主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第18页。
②石川:《孙瑜电影的作者性表征及其内在冲突》,《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第56页、52页。
③赵小青:《左翼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当代电影》2002年第5期,第42-43页。
④《前题》,《明星月报》1934年1月。
⑤席耐芳:《电影罪言——变相的电影时评》,《明星月报》1933年5月。
⑥铭三:《中国电影的检讨——从表面的转变到今后的趋势》,《明星月报》1933年8月版。
⑦陈播主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第562页,原载《电通画报》1935年第5期。
⑧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载《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⑨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162-163页。
⑩姚建新:《蒙太奇与电影的逼真性、假定性》,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女性的呐喊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青年进行曲论文; 铁板红泪录论文; 夏衍论文; 夜半歌声论文; 田汉论文; 盐潮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爱情电视剧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