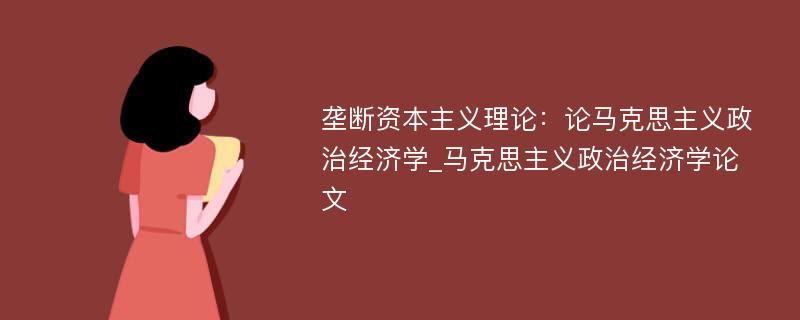
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垄断资本论文,主义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在思想形成期的有机产物。对我来说,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以下主导性事件所构成:反对帝国主义的事件,特别是越战和美国支持的智利政变;以及在1974-1975年危机中达到顶点的经济风暴。我第一次读到了巴兰(Paul A.Baran)和斯威齐(Paul M.Sweezy)的《垄断资本》一书是在1974年,当时我正在华盛顿奥林匹亚的常青州立学院(Evergreen State College)学习经济学。就像当时与我有来往的其他激进学生(最引人注意的是罗伯特·麦克切斯尼)一样,巴兰和斯威齐的分析当时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同时如时间所证明的,这种影响也是长久的。在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其他作品能在左翼政治经济学家内部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我看来,《垄断资本》的历史深度和广度令人惊叹。 我们把《垄断资本》与新古典经济学文本放在一起阅读,同时也阅读了其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品,如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亨特(Emerson K.Hunt)和舍曼(Howard J.Sherman)的《经济学:主流和激进观念》,舍曼的《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的《帝国主义时代》,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国家的财政危机》,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劳动与垄断资本》。 我们当时还阅读了阿瑟·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颇具影响力的《新左翼政治经济学》,这本小册子旨在反对美国出现的激进经济学——后者与1968年成立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URPE)有密切联系——并将其批判集中于《垄断资本》。 之后,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作为多伦多大学主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我更加专注于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在一段时期内被某些思想家更为原教旨主义的分析所吸引,如本·芬(Ben Fine)、劳伦斯·哈里斯、大卫·雅非(David Yaffe)和保罗·麦提克(Paul Mattick)。所有这些作者都批判了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因为后者否定了马克思“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意义。在此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利润率下降的理论并没有居于如此核心的地位,但到了70年代却逐渐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资本主义发展所有阶段的经济危机理论的绝对真理。①当时,在一篇试图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当下经济现实分析的论文中,我认识到,由于存在许多理论、经验和历史问题,这一理论根本无法应用于20世纪晚期的垄断资本主义。虽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依然是对资本主义进行透彻分析的必要起点,但如果要对20世纪的经济进行现实主义的评估,就需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境况重新进行分析,否则就不可能有对“作为历史的当下”的分析。 在那段时期,历史学家加伯雷尔·卡尔考(Gabriel Kolko)——我跟随他学习美国政治经济学史——向我介绍了有关美国过剩产能数据的争论,并将这一争论与约瑟夫·施泰因德尔(Josef Steindl)的《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停滞》联系起来。我在施泰因德尔以及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中发现了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中大多数论述的真正基础,同时我也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大传统植根于马克思,但是却与当下的垄断资本主义境况紧密相关,这一传统可以称为危机的“过度积累”理论。我和卡尔考为课程写了100页的手稿,标题为“美国和垄断资本:产能过剩问题”,然后寄给了斯威齐。他热情地回复了我,很快我就频繁向《每月评论》投稿——那时的编辑是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81年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幻象吗?》。在2000年,我终于与斯威齐、马格多夫和麦克切斯尼一道成为《每月评论》的编辑,直到现在。 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对经济剩余概念的分析是他们最具原创性的贡献。这个概念基于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但是,其目的是深化分析,以便能更好地解决垄断资本主义中的浪费问题。②正是这个话题——部分受到波兰经济学家斯拉基弗(Henryk Szlajfer)的启发——成为我在80年代早期的著述的焦点,由此就有了《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这部著作。 当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他方面也有发展,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地对垄断资本主义概念进行原教旨主义批判,其实这一概念很早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可以追溯到希法亭、卢森堡、列宁,并且奠基于马克思本人对资本集中的分析。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越来越多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宣称,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任何基础,竞争也没有任何缓解,甚至作为资本主义不可破坏的前提的价格竞争也是如此。据说,生产和垄断利润的集中趋势被夸大了。与此相关的是将巴兰和斯威齐错误地批判为粗糙的“消费不足论者”。这种批判乃是源于对如下两个要素的系统性忽略:对这一术语发展历史(其主要用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有所改变,不再包括熊彼特所谓的“非支出”类型)的忽略,以及对巴兰和斯威齐后来的分析演变的系统性忽略。正如斯威齐早在50年代就指出的,他们后来转向了“过度积累”论。另一个常见的批判是,巴兰和斯威齐在发展经济剩余概念的同时,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其他不同意见与某些左翼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所发起的批判有关,有些批判甚至针对最为成熟的依附理论,如巴兰和阿明,他们质疑处于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剥削和阻碍边缘国家的理念。最后,还有一些论战涉及国家的财政危机,以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国家和阶级的作用。所有这些问题在本书中都有所涉及。 30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让本书的再版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对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的学术研究也有了很大的拓展,最值得注意的是《垄断资本》两章遗失内容的出版——一章论及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内涵,另一章论及文化和传播——以及对他们的往来书信的研究。金融危机和再度出现的经济停滞滋生了对这一思想传统的新兴趣。在历史的推动下,这一理论用来解决最新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尤其涉及对停滞、金融化和垄断资本全球化的理解。同样重要的是与《垄断资本》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向其他领域的扩张,如传播、环境和再度浮出水面的阶级斗争。所有这些都可以被视为对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的历史分析,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时期。 遗失的章节 当《垄断资本》于1966年出版时,斯威齐指出,由于巴兰在1964年3月的逝世和没有解决的手稿问题,最终的书稿遗漏了两章内容。在2011年8月,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这些遗失的手稿终于找到了。《一些理论启示》在《每月评论》2012年7—8月号上发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品质:文化与传播》也发表在同一期上。③ 《一些理论启示》表明了巴兰和斯威齐如何将他们的“经济剩余”这一核心概念(他们将其定义为“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联系起来。更为具体的是,该文解释了垄断资本下工资与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而解决了《垄断资本》中“剩余的吸收:销售努力”一章所提出的理论难题:如果非生产性劳动/浪费在垄断资本主义下渗入生产过程,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以及“经济剩余”这个巴兰和斯威齐所引入的另一概念)产生怎样的影响? 巴兰和斯威齐在《一些理论启示》中的主要理论创新就是利用马克思“利润扣除”(profits by deduction)的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其作品的很多地方都使用了这个范畴。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解释说,垄断价格部分可以由资本“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但是工资只不过是要高于身体上的最低限度。在这种场合,垄断价格就要通过对实际工资(即工人靠同量劳动而得到的使用价值量)的扣除和其他资本家的利润的扣除来支付”④。 根据巴兰和斯威齐在《一些理论启示》中的观点,马克思对“因扣除而产生的利润”这一范畴的使用为我们提供了在垄断资本下理解工资与劳动力价值之间关系的基础。工人可以部分通过经济垄断部门的工会行动使工资提高到劳动力价值以上——或者在现有历史条件下达到保证劳动力供应的水平。但是,工资增长到超过劳动力价值很难说是一种进步,主要因为这一趋势将非生产性劳动或浪费(即旨在吸收剩余的资产主义使用价值)纳入工资品(wage goods)的生产中——用削减工人真正所得的方式。 事实上,垄断资本主义下的所有工资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两个组成要素:Wv反映了工人所需要的真正使用价值,并且相当于历史所决定的劳动力价值(构成了工人所需要的真正使用价值,用来补偿扩大的劳动力);WS相当于吸纳了工资品的具体的资本主义使用价值,并因而构成只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的浪费形式。⑤在这些情况下,真实工资(为避免通货膨胀而受到控制)可能会增长,但同时也可能会从Wv转向WS,让工人的境况较之从前更加恶化。 在《一些理论启示》中,巴兰和斯威齐表示出他们对剑桥经济学家斯拉法(Piero Sraffa)的广泛认同,即工资包含了剩余的要素。但是,他们是从马克思那里得到这个结论的,这个结论以将浪费系统地吸收到工资品中或以WS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这个观点来看,是Wv而非作为整体的工资,与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使用价值相等同,因此我们就有了劳动力的真实价值(以使用价值来衡量)。⑥同时,工人也无法让自己脱离内化在工资品中并构成WS的具体的资本主义使用价值。这就提供了一个更深刻的批判视角,强调了经济剩余范畴作为剩余价值补充的不可或缺的角色。⑦ 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工人工资的所有上涨都采取WS相对增长的形式,那么就可以认为工人遭受了更严重的剥削,并且实际剩余或社会积累也可以认为是在增长的(其中包括这种将浪费内化的生产)——即便工资份额保持稳定,甚至有所上升。在垄断资本的体系中,原本被算作生产成本的要素日益成为销售努力的一部分,如汽车模型改造、包装设计和广告。这些都是工人在购买商品时需要支付的被浪费的剩余的形式——他们只想得到构成真正使用价值的那部分。正如《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所说,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如下事实:“在垄断资本主义下,从事生产的雇佣工人比例日益增长,借用马克思的话就是:‘他们只是由于社会关系的缺陷,才成为有用的和必要的,他们的存在,只能归因于社会的弊端。’”⑧ 事实上,《垄断资本》的概念体系最初所提出的最棘手问题是如何在经济过程中考察各种浪费形式以及体系中非生产性劳动的作用(那些并不为资本家直接生产剩余的劳动对垄断资本依然是“有用的”,因为它们有助于吸收生产出的部分剩余)。正如斯威齐在1956年写给巴兰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 对我来说,真正的问题如下: 1.提出关于剩余的有效概念,就此来说,最为根本的是去理解它与普通的收入分配数据只存在间接的联系。很多工资都来自剩余,也就是说,工人作为整体范畴吸收剩余。同理,广告和金融等“产业”也是如此。问题在于,这也会产生非常棘手的问题和悖论。我们需要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观念上去,让其适应现代的境况和(如果可能的话)数据。这是凯恩斯主义和其他新古典经济学所缺失的关键一环。 2.对生产部门的分析(剩余的创造)。体制性资本家(institutional capitalist)——运行规律、与阶级结构和行为的关系等。价格政策、工资政策、技术性强制等。 3.对非生产性部门的分析(剩余的吸收)。“吸收者”的不同范畴:奢侈品消费者、非生产性“产业”、政府等,包括复杂的转换关系。 4.生产性部门和非生产性部门的相互作用——有很多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在欠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内,我们可以假设非生产性部门的工资和利润由(更大的)生产性部门决定。但是,这显然不适用于像今天的美国这样的经济体,在美国,非生产性部门或许比生产性部门还要大。 5.决定性的矛盾,即此类体系“运转良好”意味着如下境况:就福利来说,日益远离获取体制性资源(在人力、自然和技术方面)的可能性,消灭剥削,让文明摆脱财富拜物教的侵蚀,等等。我们所面临的是文明的日渐堕落,而非不断进步。⑨ 《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关注的正是巴兰和斯威齐分析中的核心概念结构,即如何对待经济剩余和浪费问题,同时试图纠正对他们作品的错误阐释。他们将经济剩余理解为理性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可以使用的全部社会积累基金,而这部分基金很大一部分在垄断资本主义下被系统地浪费了。我在拙著的最后部分指出:“只有巴兰和斯威齐(在凡勃伦之后)将浪费的概念扩展到‘工资品的消费’当中。这似乎是理解垄断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关系演化被遗失的环节。”但我并没有能解决谜题,基本的问题依旧存在。 《一些理论启示》的发现肯定了《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对他们作品的阐释,同时也为他们拒绝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以及另外一个紧密相关的批判,即他们的分析“缺乏工资理论”——提供了明确的答案。⑩当我们了解了巴兰和斯威齐对垄断资本下因扣除而产生的剩余的分析时(他们明确地将自己的分析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部新的、富有潜力的分析路径就打开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巴兰和斯威齐将垄断资本下的浪费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批判结合起来。 《垄断资本》的另一章“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品质:文化与传播”的问世,解决了与该书相关的另一个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新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文献在许多国家的大学中涌现,如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斯麦兹(Dallas W.Smythe)在其思想成型期所著的文章《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中特别对《垄断资本》进行了批判。 然而,这个聚焦图书出版和广播的有关文化的遗失章节被发现——当我们将其与他们论述广告的作品以及休伯曼(Leo Huberman)和斯威齐对联邦传播委员会和广播的批判结合起来时——让我们原本的看法有了颠覆性的转变。在这个遗失的章节中,巴兰和斯威齐介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文化机器”的批判,这一批判源于对布莱希特和法兰克福学派(巴兰与之有联系)的分析,同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性著作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如赖特·米尔斯、雷蒙德·威廉斯和拉尔夫·米利班德。在这方面,巴兰、斯威齐、米尔斯、威廉斯和米利班德的目标显然是围绕文化机器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在60年代早期,一般还没有将这个问题视为“学术”问题。今天,当包括数字革命的技术革新以及媒体的集中化将激进的传播革新带入大众视野时,这些作品再度彰显了它们的重要意义。 劳动和垄断—金融资本 如果说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似乎忽略了劳动价值论和工资的问题(这一问题直到《一些理论启示》发表才得到澄清),那么他们对劳动过程本身的忽视却是他们明确承认的,是他们在“论文概要”中自己设置的边界。他们这样写道: 我们并不主张,把注意力集中于剩余的形成和吸收就能给这种社会或任何其他社会提供一幅全面的画图。我们特别意识到,像我们所使用的方法,几乎是完全忽视了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一个题目:劳动过程。我们强调技术的概念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但并没有试图去系统研究作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特征的某种技术的改变对于工作的性质、工人阶级的构成(和分化)、工人的心理、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的形式所造成的后果。所有这些显然都是重要题目,在任何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详尽研究中都是必须探讨的。(11) 在巴兰逝世之后的10年内,这个缺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布雷弗曼的《劳动和垄断资本》(1974)所弥补的。布雷弗曼的作品完美地再现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分析,将其置于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和垄断资本所造就的新语境下。巴兰和斯威齐在其著作的结尾指出,历史中的革命动力已经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产业无产阶级转向边缘国家正在不断涌现的无产阶级。当时,中心国家造反的主要希望似乎会发生在那些边缘人物身上,尤其是有色人种和学生的造反,大部分工人阶级却退出了斗争。对巴兰和斯威齐来说,中心国家的工人阶级问题依然非常关键,是他们进行长时段分析的核心,虽然当时的工人阶级的确处于不活跃状态。(12) 布雷弗曼的作品开启了一个漫长的进程,将工人阶级的分析纳入对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中心。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在70年代至90年代发表在《每月评论》上的那些探讨不断升高的失业率问题的文章也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迈克尔·耶茨(Michael Yates)的作品起到了更大的作用,他撰写了一系列与垄断资本传统相关的批判性分析文章。耶茨的作品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其政治经济视角的清晰性,而且也因为其对真实的工人阶级的展现(包括他们的种族、性别、族裔和性取向在他的分析中占据中心地位)以及对工人阶级斗争所处国际舞台的考量。 然而,对斯威齐来说,《垄断资本》在理论方面的致命弱点在于无法将该体系的金融结构整合到吸收经济剩余这个核心主题当中。正如他在1991年(即他与巴兰合著的这部作品出版25周年之际)所说的,该弱点是传统的资本积累理论所产生的后果。 为什么《垄断资本》未能预见到资本主义体制的结构和功能(就金融化来说)在过去25年中所发生的变化?我认为,答案主要是,该书对资本积累过程的理解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在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已有传统中,我们将资本积累从根本上视为增加资本品的存量。但在现实中,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积累也事关增加金融资产的存量。这两个方面当然是彼此相关的,但相关性的本质却是成问题的。事实上,处理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是将其弃置一边:例如,认为购买股票和债券(金融资产的两种简单形式)只是购买实体资本品的间接方式。这从来就是错误的,而且可能非常具有误导性。 这里,我们无法就资本积累过程给出更为令人满意的概念。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问题,老实说我现在也没有解决问题的答案。但是,我可以比较自信地说,只有基于更完备的资本积累理论,并且关注实体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才能够获得对当今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更好的理解。(13) 《垄断资本》并没有完全忽略金融部门的角色,而是在“销售努力”一章的结尾做了简要论述,该章探讨了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问题,它们是“利用剩余的方式”。事实上,早在1956年,在我们之前所引用的给巴兰的信中,斯威齐就认识到将金融整合进论述的问题。而在1965年为《社会主义年鉴》撰写的文章中,马格多夫强调了美国经济中不断增长的债务问题。 因此,我在某个场合向斯威齐表示过,他对《垄断资本》没有能够解决金融化问题的自我批评过于严厉了。先于历史的发展而指出趋势——正如他们在“销售努力”一章所做的——本身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他没有进行更全面的论述。他关心的并非著述本身,而是基本理论,就此来说,他认为还不够完善。他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其他任何人都是如此。正如他所说的: 我有时有这样的感觉,经济学现在需要一个普遍的理论,就像物理学需要普遍的理论一样,有很多运动中的事物都不符合标准的物理学理论。物理学家正在探索一个可以包容所有现象的普遍场域理论。他们还没有找到。在经济学领域,我们需要一个较之传统理论能更好地整合金融与生产、金融资本周期、生产性资本周期的理论。就我所见,没有人这么做。有些人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是非常复杂的。我年纪太大了,无法再思考这些问题。我也许会有些零碎的想法,但却无法将其汇成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体系。我认为,会有人从其他地方开始,不会执着于M-C-M′这一工业周期,并且将金融周期视为附带现象,而非根本问题。(14) 所有这些都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停滞趋势再度出现之后的政治经济史紧密相关。最初,70年代的经济危机看起来完全印证了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的论断。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在为《每月评论》所写的文章中将危机解释为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垄断化和产业成熟对积累的影响而造成的滞胀,或增长缓慢、失业率上升以及产能过剩。这就使得扩大资本品的部门变得愈发困难。这个体系由于过去的资本积累和产能的大量聚集(这些产能大都处于闲置状态,遏制了新的投资)而随时有崩溃的危险。军事开支可以吸收一部分过量剩余,但却缺乏真正划时代的、能够使得整个资本积累进入新阶段的创新,结果也就不可能摆脱这一根本性的困境。 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总结道,如果该体系没有进入深度停滞,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剩余以悖论性的方式流入了经济的金融上层建筑领域中,因为金融部门的就业和资本家阶级的开销,特别是奢侈品消费所产生的财富,间接地促进了生产(有时也被称为“实体经济”),从而改善了这个体系。自70年代开始,《每月评论》在经验和理论方面所进行的主要政治—经济考察就是金融爆炸,而这在80年代日益成为编辑们关注的焦点——斯威齐在1997年将其称为“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最为根本性的分析出现在马格多夫和斯威齐1987年的著作《停滞和金融爆炸》中。 在《垄断资本》出版20周年之际面世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并未提及这个问题,只是指出,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在投资停滞的状况下可以将金融视为经济剩余的一种“转移”形式。我参加1975年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会议时,马格多夫和斯威齐的《如履薄冰的银行》一文刚刚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80年代早期,当我更为直接地参与这些讨论时,我强烈地感受到金融爆炸这个关键问题及其对积累的意义所在。马格多夫尤其鼓励所有与《每月评论》有联系的年轻政治经济学者集中关注这个研究领域,斯威齐也是如此。 我自己的回应有所不同。就当时提及的金融爆炸来说,主流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没有提供理解这个问题的真正基础。除了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关于这方面的著作之外,我还研究了明斯基(Hyman Minsky)关于金融不稳定性的作品。我也尝试去了解如何将金融爆炸与施泰因德尔的理论结合起来。但是,我在1984年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找不到有效解决爆炸的金融问题及其与垄断和停滞之间关系的方法。因此,与其提出站不住脚的假设,我索性将这些问题抛至一边。我没能完全理解分析这个问题所面临的挑战,虽然这是真实的问题,但却是无法解决的——起码当时如此。因此,我对讨论金融爆炸的基本反应和我当时的大多数同辈一样:这只意味着金融泡沫,随之而来的是金融危机或崩溃。这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已经屡见不鲜。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提出的作为经济趋势的金融化所引发的更深层问题以及这个问题与资本积累过程的转变之间的关系,在当时并未引起我的重视。 当这些问题进入我的思考时,我没有想出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从80年代早期到中期,个人债务的巨大积累以及金融创新的迅速增长看起来依然像是新的历史发展,将其视为历史的当下(除了当时所知的金融周期)的具体分析基础在那时尚不存在。 直到1987年的股市崩盘,金融化所导致的体系变化才变得清晰起来。就在这时,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开始阐述因为金融爆炸而导致的资本积累过程的变化,并提出了第一个真正的理论分析提纲。斯威齐在1994年的《金融资本的胜利》中更为明确地指出: 过去20年左右的发展相对独立(相对是从与之前对比的意义上说的),金融上层建筑凌驾于世界经济及大部分国家之上。这个上层建筑由银行——中央的、地区的和当地的——各种各样的资产和服务行业的经销商所构成,这些都由市场网络所连接,有些得到组织和调节,有些则是非正式的,没有正规的调节机制。这样一个实体是多维度的,但是还没有一个概念性的整体来衡量其范围。不过,它是非常巨大的,其增长趋势不仅一目了然,而且清晰地反映在与整体的可衡量方面相关的数据中。 我认为,金融上层建筑是过去20年的创造。这意味着金融膨胀与20世纪70年代经济停滞的回归几乎同步。然而,这种现象是否违背了以前的经验呢?就传统来说,金融膨胀与实体经济的繁荣并行不悖。现在的问题则是,在20世纪末期,相反的情况是否成为了现实:当下的金融膨胀不再依靠健康的实体经济而是停滞的经济?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事实很可能如此,它已经发生且仍在继续。不仅如此,我还坚信,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转化关系是理解世界经济新趋势的关键。(15) 在斯威齐看来,金融化的一个结果是资本家阶级内部的权力转移。“伴随着金融资本的崛起,经济权力的中心也转移了。长久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尤其是激进分子,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处于几百个巨型跨国企业的董事会的会议室内。”但是,情况在90年代后期却有所不同了:“真正的权力与其说在企业董事会的会议室,不如说在金融市场。”(16) 让马格多夫和斯威齐的分析与其他关于金融不稳定性的讨论区分开来的正是如下事实:他们认为金融化是因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结构长期停滞所造就的趋势,而非在该体系的历史中——通常是在生产繁荣期的顶点——偶尔出现的金融泡沫或危机。从80年代开始,随着停滞的积累过程日益被金融化的增长所主导,该体系的性质也转变了,同时还改变了生产与金融周期的关系,而这种改变的方式难以识别。尽管如此,金融化也有其自身的界限和危机,会导致金融内爆,然后又会反弹到实体经济。 当我在2000年成为《每月评论》编辑中的一员时,我负责起草的第一篇文章涉及“工人阶级住宅和债务负担”问题,主要关注人口中低收入群体日益为债务所累的现实,其结果可能导致“层叠违约”(cascading defaults)和严重的金融危机。次年,我与马格多夫和麦克切斯尼合写了《新经济:神话与现实》,指向与高科技扩张相关的金融投机的结构性缺陷。当我们写作这些文章时,高科技股票市场崩盘了,之后是更严重的停滞和工人阶级违约。在接下来的时间中,我们回到了这个问题,早在2002年就提及房地产泡沫可能破灭。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我在2006年(即《垄断资本》出版50周年)撰写了《垄断—金融资本》。在这篇文章中,我回到了基本的理论问题,试图去整合在过去40年中主要由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所发展的关于停滞和金融化的论述,并且将其阐述为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新时期——我称其为“垄断—金融资本主义”。 这篇文章的核心概念是“停滞—金融化陷阱”(stagnation-financialization trap)。尽管在很多方面金融化是对始于70年代的长期经济放缓的一个回应,但它无法克服“实体经济”内积累的萎缩,而是创造出了一个更不稳定、更难以预测、也更难以控制的体系。这个基础性的概念是马格多夫文章的基础,在2007-2008年经济泡沫破灭前后关于金融化和危机的作品之后,就有了2009年1月《金融大危机》的出版,那是在雷曼兄弟破产的几个月之后。 三年之后,也就是2012年,我和麦克切斯尼合写了《无尽的危机》,试图说明停滞显然已经危及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核心,但同时又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本身就是基础性的问题,而新出现的金融化则是抵消性的要素。结果就是,目前除了与金融泡沫相伴而生的金融化并可能导致更大的崩溃之外,还看不到有任何解决方案。根据这种解释,今天我们所了解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了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主导性政治—经济策略。货币向金融部门的流动以及金融资产的保存和强化在很多方面都比生产或就业更加重要,同时也要求国家日益臣服于富豪的需求。 《无尽的危机》在这一理论传统之内还有其他三方面的创新。首先,它探讨了美国和国际经济的持续集中化和中央化趋势,证明了垄断权力在美国和全世界的经济中都在持续增长。这可以由斯威齐所说的主导整个经济的“寡头垄断共同体”的扩张所证明。新千年伊始,美国的200强企业占据了经济总利润的30%(1950年则是13%),而在全球范围内,全球500强企业的收入占据全球总收入的40%(在1960年则不到20%)。其次,基于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的早期著作(其中包括在《每月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无尽的危机》揭示出,垄断资本的国际化通过全球劳动仲裁的“分而治之”体系将生产国际化。它以最低的单位劳动成本将生产转向了全球出口平台,进而剥削巨大的全球劳动后备军,这支后备军远远超出活跃的、正式的劳动大军。最后,对垄断—金融资本霸权下生产全球化的分析被扩展至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及其不断激化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与中国国内对劳动力剥削及其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不平衡整合相关的。(17) 帝国主义:连续性与转变 毫无疑问的是,世界形势转变了,更为全球化的生产体系出现了,这使得《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对帝国主义和依附的解释看起来早了30年。但是,就帝国主义来说,与过去的连续性要比当下的转变更加巨大。自从资本主义出现以来,国际范围内的主导语境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关于帝国主义的章节主要处理的是更为传统的(有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的批判,前者的批判理由基于如下断言:(1)“第三世界主义”;(2)关注交换而非生产;(3)缺乏阶级分析;(4)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无法取得发展。当时,大多数批判都聚焦弗兰克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我在《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中提出的论断是,虽然弗兰克的作品在这方面提出了有力的论述,并在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并非马克思主义有关帝国主义和依附性积累理论的最好版本。更为成熟的分析可以追溯到巴兰和阿明更早、更具奠基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代表了更具动态性的方法,并且扎根于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积累理论和对经济剩余的分析。就那些与巴兰和阿明的才能相当的思想家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和依附理论的教条性批判有些言不及义。 在写作《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时,我倾向于认为,更广阔的依附视角主要源自拉丁美洲,巴兰和阿明(前者来自俄国和德国的争论语境,后者则植根于非洲的情况)作为异类在这个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我并不知道帝国主义论中的依附理论以及巴兰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还有阿明)在何种程度上源自这条路线——这条路线源自列宁领导下的早期共产国际的尝试,即提出了可以描述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剥削的所有维度的理论。正如印度孟买的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所表明的,巴兰的视角可以追溯至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和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上列宁和其他边缘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所提出的论题。毛泽东于1926年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20年代加入这些辩论的其他人物还有印度的罗易(M.N.Roy)和秘鲁的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巴兰在俄国出生并接受教育,自然对这些辩论了然于心,这也影响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依附(或依附性发展)理论的体系化。巴兰对这个辩论的独特贡献是,他的分析关注对真实的、潜在的和有计划的剩余的利用——这一源自社会主义计划的视角为第三世界革命确立了理论基础,同时也影响了像切·格瓦拉这样的人物。 从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早期,阿明以类似的方法独立地发展了自己的分析,并提出了世界范围的积累理论,以探索不平等交换/过度剥削、帝国主义下垄断资本的作用、自主性积累和脱节性积累、去依附以及后革命社会中经济上的自力更生等问题。在我看来,这是20世纪后期最为本真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并非从空洞的公式推导而来,而是历史分析和历史偶然性的产物。斯威齐晚年有关帝国主义的著述受到了阿明很深的影响,强调边缘地区高得多的剥削率。同时,马格多夫为源自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关系的演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分析,并且还结合了对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理解——其中包括对强加于边缘国家的不断增长的债务的批判。 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不断出现新兴经济体的时代,这些到底还有多大的相关性?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不是已经开始了吗?这里我们需要直面事实。尽管出现了新兴经济体,且主要出现在东亚地区,这些国家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较高的增长率,但作为整体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却毫无疑问地依然存在。在20世纪最后1/4的时间里,全世界最富裕地区与最贫穷地区的经济差距由13︰1变成了19︰1。从1970年到1989年,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年人均GDP只是七国集团的6.1%。从1990年到2006年(金融危机前不久),这个比例下降到5.6%。同时,48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与七国集团人均GDP的比例从1970-1989年的1.4%下降到2000-2006年的0.96%。考虑到在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时代,几乎全世界所有地区的不平等都在加剧发展,世界等级制下的顶层和底层的收入和财富差别有如天壤之别。2008年,全球10%的最富裕人口消耗了全球59%的产出,与之相对的是,全世界10%的最穷人口只消耗了0.5%的产品(50%的最穷人口消耗了7.2%)。 事实上,表象很可能具有欺骗性。21世纪更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世界中心国家的巨型企业将其生产转移到边缘国家(生产出的产品绝大多数都返运到中心国家进行销售)——改变了全球经济的形态,其结果看起来与全球北方剥削南方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相矛盾。但是,虽然由中国所领衔的新兴经济体在GDP方面正在追赶三巨头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但对作为整体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剩余”(或“价值捕获”)的吸收,却正在巨型跨国企业所纵容的全球仲裁体系下迅速扩张。 例如,2006年,苹果公司从海外ipod生产中所获得的毛利率为52%。这些高得离谱的利润主要源于如下事实:1.25万名中国生产工人所得到的工资率只有美国生产工人小时工资的3.2%,而且前者的工作肯定更加繁重。2009年,iphone的毛利率达到64%,这反映了如下事实:装配iphone的中国工人的工资只占手机全部生产成本的3.6%。从海外所获取的巨额剩余价值强化了核心国家的过度积累问题。 在最近几年,基于正在出现其所谓的“世界范围的价值规律”,阿明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地租理论而深化了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在解释这种分析的起源时,阿明写道: 巴兰、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在这个领域(对垄断资本的理解)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他们让我们对当下资本主义的本质有了新的理解,如停滞的趋势以及遏制这一趋势而采取的措施(尤其是金融化)。 在他们分析的基础上,我提出了如下论点,即资本集中的发达程度,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让我们可以首次谈及普遍化、全球化和金融化的寡头垄断体系——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欧洲和日本三巨头的群体帝国主义日趋形成。(18) 由美国霸权所领导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帝国主义日益依赖“全球北约组织”(global NATO),因此需要扩大军事预算,并依靠战争来强化其权力。这可以从自苏联解体之后发生在巴尔干、中东及周边地区的战争看出,一个更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正在形成。同时,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前线,同样的三巨头结构已经出现,其目标是:削弱对垄断—金融资本的一切反抗,降低全球单位劳动力成本,并向中心输送更多的利润。在这些情况下,全球南方国家持续不断的革命需求在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中体现出来,这个国家一直处于美国与当地统治阶级所结成的同盟的统治之下,但现在却可以将大量的剩余重新分配,来满足人口的需求,并形成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因此,尽管形势有变,但对边缘国家的大多数人口来说,如下论点依然正确:如果要创造出一个实质平等且人类发展可持续的社会,真正的进步必然是革命性的,这也是《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论点。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 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的民主制,实质上的富豪统治。”尽管“人民行使最高权力”,但实际上是“相对极少的富豪进行统治”。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阶级的统治是没有代理的。就美国来说,各种制度结构都被建国者们吸收到美国宪法之中,并进一步演化,以确保国家首先服务有产者的利益而非人民主权。另外,“体系内也存在着潜在的矛盾”。在民主行动领域以及人民主权行使方面所取得的任何成功——这种成功意味着经济和社会权力偏向大众——都可能滋生阶级权力的危机,而统治阶级则会迅速遏制任何有意义的变革。进步的改良运动一旦成功,就会发现自己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框架内,即不得破坏资本积累或既得利益者的政治—经济统治。 《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中对“国家经济”的讨论写作于80年代,当时主要是从里根时代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引发的辩论的角度来关注“国家的财政危机”。我的分析还指向奥康纳的财政危机理论以及巴兰与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对政府支出的论述所存在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领域的批判需从如下事实开始:税收国家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国家,它在征收高收入者和富人的税收方面存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障碍,却在对工人阶级的收入征税时倾向于增加剩余并进一步恶化了停滞的趋势。资本所不断推进的累退税政策使过度积累问题更加恶化。考虑到长期以来赤字财政的内在限制,对利润和财富进行征税,就稳定经济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税收国家在80年代迅速出现的危机可以直接归因于企业税收和高收入群体税收的长期下降。今天,这个论点与新自由主义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更为紧密相连。伴随着福利国家支出的削减和对资本补贴的不断增多,累退税削减导致了国家永久性的财政危机。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流向金融部门的现金(尤其是保险和个人养老金)、不断升高的失业(以及非充分就业)、不断扩大的军事和法律支出、缩水的教育、日益减少的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对工人阶级的进一步监管。所有这些与克莱因(Naomi Klein)所谓的“灾难资本主义”若合符节。 随后的章节涉及后革命社会的国家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如果说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家阶级伪装成了没有政治利益的经济精英,那么在前苏联这样的社会中,党的官僚或权贵阶层则伪装成没有经济利益的政治精英。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的阶级权力的性质被否定了。在戈尔巴乔夫历史性的上台仅仅几个月之后,在这个事件的历史意义变得明朗之前,《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对苏联式的社会的分析已经完成。我借鉴了斯威齐后革命社会的论题,即这些社会是“新形式的阶级剥削社会”——既非资本主义的,也不能称为社会主义,因为它们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后革命社会中,积累的内在驱动力消失了,而对剩余的利用也政治化了。但是,这并不能避免新的统治阶级的出现,虽然他们的地位比西方的资本家阶级要脆弱。这样的社会也无法避免大多数工人的无产阶级化,虽然这些工人缺乏某些关键的自由,却在就业、住房、福利等方面享受一定的保障,而这在同等发展程度的主要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看不到的。有两个方面是一目了然的:(1)20世纪80年代,苏联类型的社会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都已陷于停滞;(2)对剩余进行利用的政治化意味着只有两个选择——该体系自上而下的退却或自下而上的再生。在我看来,该体系的未来并非由经济规律所决定,而是由国家在指导经济方面所引发的斗争以及国家统治阶级的角色所决定。 除了这些,当时很难再作出进一步的论断。因此,拙著的最后部分对这些矛盾的分析并不尽如人意,处理也是仓促的。历史会给出答案。五年之后的苏联解体并非由于自下而上的反抗,而是因为自上而下所开启和实施的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今天,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一次大反抗的失败教训已经为后来的革命所吸收,并将我们引向社会主义的重生,而这是21世纪唯一的历史选择。在我看来,对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最重要的分析——这种分析既考察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也考察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代表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最为全面的理论应用——出现在伊斯塔法·梅扎罗斯(István Mészáros)于1995年出版的不朽著作《超越资本》中。 传播与环境:新的批判领域 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70年代早期的英国和美国(两国具体的时间有所不同)都出现了“批判的关键时刻”,社会的文化机器特别是垄断性的媒介体系在政治上受到了挑战。巴兰、斯威齐、休伯曼、米尔斯、威廉斯和米利班德等在那段时期都就媒介批判进行了批判性的著述,而米尔斯在这方面的贡献只是一些批判性的谈话,他关于“文化机器”的计划并没有付诸实践。 70年代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媒介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与60年代激进分子所思考的问题有所不同。其结果是某种程度上更为深刻的批判,但在当时的语境下还没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会那么具体、那么具有政治性和战略性。尽管如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物如达拉斯·斯麦兹与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所作出的贡献为后人铺平了道路。而后来的麦克切斯尼在将传播理论与垄断资本批判进行整合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整个数字领域已经进入了寡头垄断的空间,这种转变的速度会让那些盲目相信流行神话——如比尔·盖茨所预测的“无摩擦的资本主义”——的人目瞪口呆。今天,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争夺传播的政治斗争正在发生,这使得巴兰和斯威齐的早期作品以及休伯曼、米尔斯、米利班德和威廉斯的作品重获意义。正如麦克切斯尼在《数字中断》的结论中所说:“如果这个关键时刻尘埃落定,而我们的社会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如果民主没有战胜资本,那么数字革命就只是名义上的革命,只是反讽地、悲剧性地提醒我们人类社会的现实与可能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19) 对于在70年代研读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的某些人来说,在一个环境运动日渐高涨的时期,他们的作品——关注浪费,强调尽可能以更理性的方式满足人类需求——充满强烈的生态关怀。事实上,他们的作品启发了环境社会学中某些早期的批判性整合。斯威齐1973年的文章《汽车与城市》以及后来的《资本主义与环境》都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先驱之作。 1994年,我完成了《脆弱的星球:环境经济学简史》,试图为正在出现的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同时将环境问题与垄断资本理论整合在一起——如康门勒(Barry Commoner)、巴兰、斯威齐和布雷弗曼在他们的著述中所尝试的。但是,就像其他被称为第一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一样,我将唯物主义的概念嫁接到主流环境主义的“绿色”理论中。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流远离生态考量为时已久(这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此在我看来,有必要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重构全面的批判。柏克特(Paul Burkett)的《马克思与自然》和我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从不同但互补的角度完成了这一任务,开启了可以称之为第二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潮流。但是,直到最近才出现真正将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分析与垄断—金融资本的现实整合在一起的尝试(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第三阶段)。 现实与理性的革命性对抗 巴兰与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的分析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以独一无二的方式描述了当下的现实,同时又指向转变的可能。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写道: 资本主义总的发展,特别是它的最后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几乎没有表现任何与一个好社会相像的地方,但却产生了出现这样一个好社会的客观潜力。在帝国主义时期已经出现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尽管是战争、剥削和浪费的副产品,事实上为未来真正丰裕的社会打下了基础。但是在寡头统治下,大量的资源为几百家大公司的利益服务,一切为了维持现状以便进行控制,这种社会不可能产生。只有当丰富的资源由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的社会来管理时,好社会才会变成现实。(20) 正是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的潜力——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主义秩序中的浪费和不合理中发现了这种潜力——构成了他们的分析中不妥协的现实主义:消除一切异化。 本文系美国著名左翼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教授为自己的专著《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再版所写的序言,原载美刊《每月评论》2013年7—8月号。译文有删节。 ①人们通常会忽略这一点,即马克思(包括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对危机理论的贡献很少是关于下降的利润率的。事实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考茨基、卢森堡、布哈林、列宁以及一战之后的大多数理论家关注的都是不均衡性问题(从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的视角)以及价值实现危机问题。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是这一趋势的主要例外。因此,70年代重新重视马克思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与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形成了断裂。事实表明,马克思本人对自己正在创作中的有关利润率下降的作品越来越不满意,而且似乎在其最后的写作中有意与这一“趋势性规律”保持距离。 ②萨米尔·阿明言简意赅地指出:“我们需要考察与寡头垄断或垄断的出现相关的对价格系统的扭曲,并且首先要考察自一战之后,特别是二战之后,由于第三部门的不断扩张——对剩余价值的吸收——而导致的被迫扩大的平衡体系的艰难转型。巴兰和斯威齐用他们所主张的剩余概念回应了这个挑战,并深化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认为,那些拒绝承认巴兰和斯威齐贡献的人难以提出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有力批判的方法。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对马克思文本的注释性解读。” ③中译文参见《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6期,由《每月评论》杂志授权翻译。——译者注 ④《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75—976页。——译者注 ⑤我提出的这两个符号,Wv(代表工资品的构成要素,表明真正的使用价值成为了劳动力真实价值的一部分)和WS(指代构成特定的资本主义使用价值的工资品的那一部分,因此是剩余和浪费的隐蔽形式),在这里是为了指出巴兰和斯威齐在《一些理论启示》中对垄断资本主义下“因扣除而产生的利润”进行分析所产生的启发。 ⑥应该提及的是,巴兰和斯威齐认为,Wv绝不能混同于物质生存,它总是包含历史性的内容。以汽车为例,在讨论销售努力如何被纳入生产过程时,这种努力指向了汽车的尾翼和铬,包括为了市场目的而进行的表面改变等造型变化,以及产品的淘汰等。但是,在他们的分析中,没有将汽车视为基本的交通工具,当然,这并非基本的物质生存需求,因此不应该纳入被历史地决定的劳动力价值。 ⑦如果由工人阶级所承担的这种非生产性成本会根据它们是由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所生产而有所差别,那么分析会变得更加复杂。在生产性劳动条件下,因扣除而产生的利润只会增加社会总剩余。因此就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工人来说,他们被迫支付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被纳入工资品中的浪费(反映在他们的工资上就是从Wv向WS的转变),总剩余可以说有所增长。但就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工人来说,却并非如此,因为他们的劳动不会生成剩余。但是,这种劳动的确能够确保对剩余的更大吸收,让具体的资本主义使用价值得到扩大,因此,对体系的运行是有用的。但是,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工人,其生活水平却恶化了,因为他们不得不将自己工资的更大一部分用于购买体现在工资品中的具体的资本主义使用价值。因此,非生产性劳动构成了整个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中浪费周期不可或缺的基础。 ⑧J.B.Foster,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86,p.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页。——译者注 ⑨Paul M.Sweezy to Paul A.Baran,November 25,1956. 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本人的工资理论完全被忽视了,以至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个领域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当我们将巴兰和斯威齐的《一些理论启示》置于马克思本人的工资理论以及他们的思想发展的语境中时,就会看到他们的贡献是卓著的,他们根据历史变化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 (11)[美]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4页。 (12)正如斯威齐后来所表明的:“当下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革命现象对我来说如此明显,以至于我看不出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会否定这个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事态会永远如此,也不意味着革命者应该回避或忽视在工人中进行教育和组织活动。”(Paul M.Sweezy,Modern Capitalism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2,p.vii.) (13)Paul M.Sweezy,"Monopoly Capital after Twenty-Five Years",Monthly Review 43,no.7(December 1991):52-57;这里的“实体经济”(real economy)有其特殊意义,在经济理论中意指与金融/投机以及属于货币领域的其他要素相对的生产/产出。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坚持认为,金融系统事实上是“真实的”,他们通常用“生产”来指代“实体经济”。 (14)Paul M.Sweezy,"Interview with Paul Sweezy",Monthly Review 38,no.11(April 1987):19. (15)Paul M.Sweezy,"The Triumph of Financial Capital",Monthly Review 46,no.2(June 1994):7-8. (16)就权力向金融资本的直接转移来说,这可以视为资产阶级内部财富生产中心的转变。 (17)一些批评家如M.C.霍华德(M.C.Howard)和J.E.金(J.E.King)认为,国际经济证伪了巴兰和斯威齐的论点,他们写道:“考虑到战后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以及国际竞争压力的持续增长,很多产业的‘垄断程度’都应该在国际范围而非纯粹的国内范围进行衡量。基于以上论述,垄断资本只是一个幻象。”但是,我们可以说,伴随着世界经济迅速寡头垄断化的垄断资本的国际化现象首先是跨国企业增长的后果之一——这一现象在巴兰、斯威齐、马格多夫和海默的分析中早有提及。从这个角度来看,霍华德和金的批判存在的问题是,他们关于国际影响的论述还不够国际化。虽然“国际竞争不断增长的压力”这个概念从任何特定国家的经济这一有限视角来看都是主导性的现实,但实质上这是一个影响所有国家的全球现象,并且在世界范围内表明了资本的集中化和中心化。毕竟,全球范围的战争是在横跨世界的巨型企业之间发生的。结果是,越来越少的公司主导着全球经济中越来越大的领地,提高了全球垄断的程度。 (18)Samir Amin,The Law of Worldwide Valu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0,pp.28-29. (19)Robert W.McChesney,Digital Disconnect,New York:New Press,2013,p.232. (20)[美]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21页。——译者注标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市场垄断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斯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