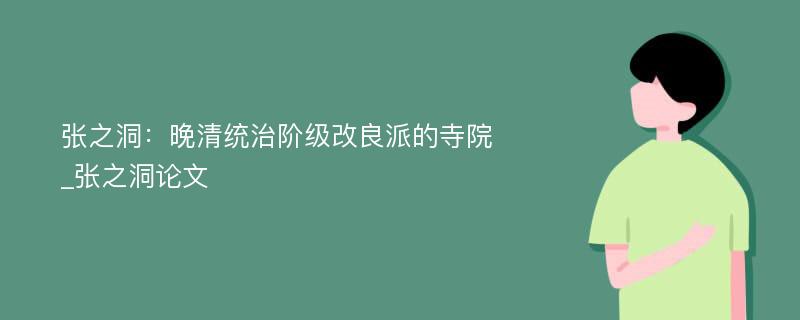
张之洞: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殿军论文,改革派论文,晚清论文,统治阶级论文,张之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常称张之洞为晚清洋务派的殿军或后期洋务派首领。说他是洋务派,主要是因为他注重学习西方,并在近30年的政治活动中,为了国家富强,在学习西方的实践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如果从政治角度去考察,把它置于晚清统治集团各个政治派别的斗争中来评论,说他是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似乎更加合适。
清朝统治到了嘉、道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面对空前深重的政治危局,围绕如何挽救危局这个根本性问题,在统治集团内部实际形成了三个政治派别:一派是看不见或不愿看见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局势,拒绝进行任何改革的守旧顽固派。其代表人物有倭仁、徐桐等;另一派是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反抗,为增强镇压人民能力而购买了大批西方枪炮,兴办了一些军民用工业的洋务派。他们虽然在推进中国近代化方面起过一定作用,但由于一贯推行妥协投降政策,从政治上考察,实际是投降派。其代表人物有琦善、曾国藩、李鸿章等;再一派是晚清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他们为了拯救清朝统治,希望通过改革和师法西方,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这就是统治阶级改革派。其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左宗棠、胡林翼等,张之洞则是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后起之秀。
一
晚清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早在嘉庆后期就敏锐地看到了社会统治危机日益深重,发出了社会进入衰世的呼吁,倡言改革。到了道光时期,随着社会矛盾激化,统治危机加深,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希望通过改革,以挽救清朝统治的政治派别——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在这一派人物之中,政治首脑是陶澍(1779~1839)和林则徐(1785~1850),提出改革理论和出谋献策的则有包世臣(1775~1855)、龚自珍(1792~1841)和魏源(1794~1857),此外还有一批力主改革的积极分子与实干家。(注:关于鸦片战争时期的改革派情况,笔者有《鸦片战争时期的改革派概论》一文可供参考。该文载《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他们以江苏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鸦片战争后又及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进一步把改革向前推进。
陶澍、林则徐等不但积极推行各项改革,而且十分注意发现和培植改革人才。晚清中期改革派的核心人物如左宗棠和胡林翼等,都是由他们敏锐识拔和着力扶植成长起来的。
胡林翼(1812~1861)从小就受到陶澍的关爱与培养,陶曾将林翼带在身边,亲自教养,并把女儿许配给他。在陶的精心培育下,胡林翼23岁考中举人,24岁高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1838年散馆授编修。1839年大考二等。但此后有一段曲折,变得意志消沉,流连于山水之间,无意仕宦。这时陶澍已于1839年去世,而林则徐深信胡林翼才堪大用,先是致信劝勉,望他不必灰心丧气。1845年,林则徐从新疆释回,半年后出任陕西巡抚。在职期间,为了促使胡林翼早日复出,他又专折奏报朝廷,由陕西捐输案为胡捐了个内阁中书,接着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胡在贵州安顺、镇远等地做知府数年,治绩卓著。后来,由于林则徐竭力举荐而一年三迁的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又把胡林翼调到湖北帮理军务。因为才华出众,没过多久,胡林翼即由按察使升任湖北巡抚,成为晚清和太平天国斗争中扭转败局的“中兴”名臣。
同样,左宗棠(1812~1885)也是受到陶澍、林则徐慧眼识拔的特异人才。左宗棠自幼聪明过人,在县、府、省三级考试中,常常名列前茅。但自1832年中举后,三次参加全国会试,却三次不中。从此绝意科考,潜心研究舆地经世之学。1837年9月,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在江西检阅营伍后回乡省亲扫墓,路过醴陵,结识时年25岁的禄江书院主讲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注:左宗棠:《与周夫人》,《左宗棠全集·附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45页。)左宗棠得到陶澍如此嚣重,感慨地说:“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惟吾诚不知何以得此,殊自愧耳。”(注:左宗棠:《与周夫人》,《左宗棠全集·附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46页。)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赴京会试落第,绕道去江宁(今南京)拜访陶澍。陶澍没有因左再次落第而轻视他,接待格外热情,留左在总督衙署里住了十多天,并且主动提议两家联姻,将自己惟一健在的儿子陶桄与左氏之长女孝瑜结为连理。1839年,陶澍病死南京,他的儿子陶桄年仅七岁。为了把陶桄培育成才,左宗棠受业师贺熙龄之托,接受陶澍女婿胡林翼的聘请,赴安化陶家教育陶桄(字少云)读书达八年之久。左氏在陶家一面教书,一面读书。利用陶家丰富的藏书,饱览了各种典籍,尤其精深研究了清代的朝章国故,为后来的事业奠立了坚实的基础。
林则徐早年从陶澍处得悉左宗棠是个杰出人才,即甚为器重。左宗棠也非常敬佩林则徐,并对林的一举一动均十分关注,自言:“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指林则徐)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注:左宗棠:《答胡润之》,《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58页。)后来林则徐调任云贵总督,拟招左宗棠入幕府充当高参。胡林翼见林非常器重左宗棠,又见林则徐年老力衰,“忧国形癯,巨细一手,勤瘁备至”,希望左能分其劳,敦促左即刻应招。(注:左宗棠:《答胡润之》,《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58页。)左宗棠也极愿陪侍左右,亲聆教诲。无奈左宗棠已于头年与陶桄约定:陶要去长沙读书,并与左女完婚。左因极盼陶桄早日成才,以不负陶澍的知遇之恩与厚望,故未能应招。1849年,林则徐因病辞官归田。回乡途中特意绕道去长沙与左宗棠一晤。林在长沙舟中见到左宗棠,两人倾谈一夜,军国大事,无所不谈,尤注重西北边防。林谈到自己在西北“办理屯务,大兴水利,功未告藏……颇以未竟其事为憾”(注:左宗棠:《答刘毅斋》,《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140页。),对左宗棠“期许良厚”(注:左宗棠:《林文忠公政书》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74页。)。这次林左会晤,对左宗棠影响很大,为后来左氏成就西北功业奠下了思想基础。
至于左宗棠与胡林翼,两家乃是世交。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与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是同窗好友,“曾共麓山研席者数年”(注:左宗棠:《与癸叟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6页。)。胡林翼与左宗棠两人也有30年的交情,彼此相知最深。早在1833年,左首次入京会试,即曾与胡林翼“彻夜谈古今大政”(注: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第1卷,第12页。)。1839年陶澍去世,胡林翼即聘请左宗棠为陶家西席,并委托帮管陶家家务。1842年,胡林翼因父亲去世,从北京回湖南益阳守制尽孝,并赴陶家料理相关事务,和正在陶家任教的左宗棠“因得连床夜话,纵论古今大政,以及古来圣贤、豪杰、大儒、名臣之用心行事,无所不谈,无所不合”(注:左宗棠:《与景乔先生》,《左宗棠全集·附册》,第252~253页。)。左宗棠生性刚介,常易引致嫉忌,胡林翼曾诚心劝导。左氏因科举失意,仕途不顺,长期倚靠教读为生,家境清贫。胡林翼又和湖南巡抚骆秉章,为左筹资500金在长沙司马桥购置住宅,使他得以安居。胡林翼深知左宗棠有济世奇才,先是荐于陶澍,再是荐于林则徐,三是荐于张亮基,因得先后入张亮基骆秉章幕府。抚署所有“批、答、咨、奏,皆(左)公一人主之”(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34页。),实际是代张、骆主持全省要政。左宗棠因得在筹饷、运饷、用兵等方面初露锋芒。此后,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抚,又多次向咸丰皇帝举荐,称赞左“才学过人,于兵政机宜、山川险要尤所究心”,“秉性忠良,才堪济变”,(注:《左宗棠年表》,《左宗棠全集·附册》,第994~995页。)实为不可多得的将才。后又经多人交章举荐,甚至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注:蔡冠洛:《左宗棠》,《清代七百名人传》(中),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1379页。)。咸丰帝见人们对左如此推重,才于1860年下达谕旨,命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从此,左宗棠才得招幕楚军,独当一面。最终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功臣。
张之洞(1837~1909)与胡林翼则有直接的师生关系。张之洞虽然祖籍在河北南皮,却生在贵州,长在贵州。父亲张瑛,道光、咸丰年间一直在贵州供职,由州县官升到兴义府知府。胡林翼在林则徐的提携下,从道光末到咸丰初,先后做过贵州安顺、镇远、思南等地知府。张之洞少时因胡是父亲的同僚好友,经常向胡林翼求道问业。道光二十九年(1849),做过独山知州的韩超,因丁父忧,张瑛曾聘请他到兴义府署教授之洞等人。韩超为人沉勇慷慨,胡林翼称赞他是“血性奇男子”(注: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一,北京天华印书馆1939年版,第3页。)。胡韩两人对张之洞都很器重,对他寄予厚望。咸丰二年(1852),张之洞15岁,在顺天乡试中成为举人第一名(解元)。喜报传到贵州,韩超正在黄平胡林翼军中协办军务。两人得悉张之洞少年高中,喜不自胜。胡林翼在致张瑛的贺信中说:“在军中得令郎领解之信,与南溪(指韩超)开口而笑者累日。”(注:张之洞:《谒胡文忠公祠二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32页。)欣喜之情,跃然纸上。胡林翼对张之洞的教导与期望,使张铭刻终生。
从上面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彼此之间的情缘不难看出,上自陶澍、林则徐,中经胡林翼、左宗棠,下到张之洞,相互之间均有深厚的情谊。他们有着忠君、爱国、恤民的共同情怀。
二
说张之洞是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当然不只是他和前期改革派有深厚的情缘,主要是他的改革主张和前期改革派基本一致,并在不少方面有所发展。
1.整伤吏治,力挽颓风。吏治腐败,官吏因循怠玩,贪赃枉法,是清代衰落的一个重要表征。统治阶级改革派深知吏治腐败严重威胁着清朝统治,都主张认真整顿,并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作出表率。晚清时期,官吏作风拖沓,有案不办,已是司空见惯。改革派力反这种拖沓作风,尽职尽责,表现出强烈的责任心。张之洞继承了改革派的勤政传统,“服官治文书,往往达旦”(注: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一,第2页。)。1882年,张出任山西巡抚,“丑正二刻即起,寅初阅公牍,辰初见客”(注: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二,第1页。),“章疏公牍,多出手稿,不委之幕僚”(注: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二,第4页。)。光绪二十一年(1895)底,他已奉命由两江总督回湖广总督本任,可是,他为了“两江吏治民生,力谋所以整饬”,竟然“乙未除夕二鼓,犹在幕府治事;丙申元旦,亦办公竟日”(注: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三,第17页。)。从旧历十二月二十六到正月初五日,十天之内,单是奏报清廷的奏折即达19件,内容涉及裁兵、浚河、练兵、筑路、购买军火、遣派学生出洋等诸多方面。(注:参看《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109~1144页。)其勤政程度,和前期改革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改革派在勤于政务的同时,十分注意廉洁自持。张之洞和前期改革派一样,一贯清廉自守。1873年,张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后,又任四川学政三年。四川学政的收入本较丰裕,但他廉洁自持,既裁去陋规银二万两,又对恩优岁贡录遗诸费重新核定,杜绝婪索,以致任满离蜀,竟然无钱治装。迫不得已,“售所刻万氏拾书经版,始成行”(注: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一,第20页。)。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敬谨率属,益发廉洁自律。自莅任始,即裁去原来各地解送抚院的公费银、藩司津贴抚院卓饭银共计26350两。藩臬两司及道府州县的公费也相应进行了裁减。合计全省为此节省银78916两。(注: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第21~22页。)此外,一应查库、门包等陋规也全行裁革。此后,在两广、湖广、两江总督任上,都是一如既往,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赠礼物。服官四十多年,家乡未造房舍,未置田产。1909年八月二十一日(10月4日)弥留之际,清监国摄政王前往探视,称赞张“公忠体国”。张回答说:“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注:张之洞:《裁革公费馈送折》,《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08~109页。)张之洞一生站在统治阶级改革派立场,不结党,不营私,处处为维护统治阶级统治、为促进国家独立富强着想。凡是他认为正确的,甘冒万难,执著做去,务求成功;凡是妨碍国家利益或统治阶级统治的,则坚决反对。“廉正无私”——张之洞临终前的最后一言,足以表达他一生的心声。
2.兴修水利,注重务本。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保障。在封建社会中,租赋是封建统治阶级财富的基本来源。从统治阶级到各级官员,无不仰赖租赋维生。因此,水利的好坏,不但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同时直接影响到封建统治的根基,以及社会的安定。正是基于这种情况,统治阶级改革派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几乎做官到了哪里,哪里就留下了他们兴修水利的足迹。
张之洞和前期改革派一样,也是每到一处,即大兴水利。汾河纵贯山西南北,关系山西全省利害最大。1882年汾水盛涨成灾,知府周天麟请求筑堤,以期一劳永逸。张之洞即刻亲自“详为规划,饬增宽培厚,一律如式,不可惜费”(注: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二,第3页。)。此外,又制定维修章程,拨专款设河防队负责,规定每年均要对汾河堤堰进行培修,以防水患。(注:卢学礼:《记述有关省政的一段故事》,《山西文献》第9期,台北山西文献出版社1977年版,第46页。)广东的西江和北江,由于水利失修,数十年来几乎无年不发水灾。1886年,广州府与肇庆府又大水成灾。张之洞随即“筹款二十五万余元,修筑围堤数十处,同时又筹款十六万余两,修筑潮州府属韩江各堤”(注: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二,第17页。)。后来他在湖北任湖广总督十七年,兴修的水利更多。如1899年,兴修武昌城南北江堤:北自望山门外鲇鱼套至金口龙口矶五十余里,南自武胜门外红关至青山木兰庙二十余里。这年5月重修工竣后,有些地方不够坚固,几经翻修,“卑者益之,冲刷者补之,建闸以泄内湖之水。每于出险时,亲往督率抢护”,至1902年10月全工稳固,凡用费十多万两。由此“民田涸出数十万亩,在通商场以内者三万余亩”(注: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四,第1、19~20页。)。汉口后湖一带,靠近铁路和租界,原来全是沼泽地区,蚊蝇滋生。1901年即提议筑堤,因没有筹到堤款,无法兴工。1904年德商愿意承揽,张之洞因怕损害国家主权,以自办却之。于是秋天水落时,即亲往履勘兴修。决定拆去原有城墙,以城墙砖石用于筑堤,堤外面开筑一条引河,“上通汉水,下达滠口,即以开河之土筑堤,凡得可居可种之地十余万亩,地价日昂,人民日富,人呼之为张公堤”(注: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五,第12页。)。这些水利的兴修,都产生了长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改革派在兴修水利的同时,对发展农业生产也很重视。与前期改革派不同的是,张之洞在重视农业中,适应农业需要,更富改革意味。张之洞认为:“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注: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436页。)他建议在京城设农政大臣,每县设劝农局,专门负责督课农务事宜;有感于农政人才匮乏,他对培育农业人才、改良农业种植十分热心。提议凡学生有愿赴日本农务学堂学习,“学成领有凭照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官职。”赴欧美或自费者,给奖加优。(注: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436页。)在湖广总督任内,先是在武昌设立湖北农务学堂,后又将它改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培养农桑、畜牧、森林方面的专业人才。他对推广良种很热心。我国虽有种棉悠久历史,但棉种退化。为了改进棉种,他从美国引进优良棉种1000多担,分发湖北各地试种,并译刊《美国种棉法十条》等,随同棉种分发各地参考。茶叶也是中国传统产业,在国际竞争下,茶叶出口急剧下降。为了增强竞争力,他劝谕茶商讲求采制茶叶新法,鼓励富商购置机器制茶,并延请外国专家指导。为了发展湖北蚕桑,他在省城开办蚕桑局,并多次派员赴浙江采购桑苗1000多万株,分发江夏、汉阳等地种植,使湖北蚕桑业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些都表明,张之洞在推进农业发展与改革方面,都是很积极的。
3.改革弊政,利国利民。排除各种阻扰,竭力改革各种弊政,是晚清改革派的主要特色。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经过深思熟虑,毅然进行了大胆改革,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张之洞继承了前期改革派的传统,对改革弊政也十分卖力。他出任山西巡抚后,经过数月考察,“灼见晋省公私困穷,几乎无以自立”,决心表里兼治,大力整顿。经过认真梳理,提出应办要务二十事。选择其中责垦荒、清善后,省差徭、除累粮、储仓谷、禁罂粟、减公费、裁摊捐等最要八事先行整办。(注:张之洞:《整饬治理折》,《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01~102页。)他发现山西“虐民之政,不在赋敛,而在差徭。所谓差徭者,非役民力也,乃敛民财也。向来积习,每县所派差钱,大县制钱五六万缗,小县亦万缗至数千缗不等。按粮摊派,官吏朋分。”实际就是假借差徭敛钱,集体贪污分肥。他们还在交通要道,设立车柜、骡柜,强行勒收,“一驴月敛数百,一车动索数千。以致外省脚户不愿入晋,外县车骡不愿入省。远近行旅,目为畏途”(注:张之洞:《裁减差徭片》,《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05~106页。)。为了解除民困,张之洞参照阎敬铭在西南路州县制定的裁减规章,实行裁减。将每月收支钱数,一面张榜公布,一面送报上司备查。差徭一经裁减,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众情欢欣,任载络驿,南北商旅,四乡车畜,度恒霍而趋并门者,联镳接轸,渐有坦荡之乐”(注:张之洞:《裁减差徭片》,《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05~106页。)。山西藩库库款,自1849年后,三十三年未经清查。他奏请设立清源局,配备专班,分工负责,将军费、报销、善后、交代等项,一一进行彻底清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数十年尘薶丝棼之累,一举而廓清之”(注:张之洞:《清查库款完竣折》,《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205~207页。)。此外如清丈地亩、豁除累粮、裁抵摊捐、裁免科场支应等方面均取得显著的成效。他在山西任职只两年多,短时期内在改革弊政方面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显示了他是晚清一位杰出的统治阶级改革派。
张之洞在两广、湖广、两江总督任上,本着有弊即除的精神,继续改革各项弊政,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广东潮桥盐务,引地行销广东之潮州、嘉应,福建之汀州,江西之赣州、宁都,地联三省,路隔千数百里,盐场饷项13万多两。自咸丰、同治以来,引地疲坏,汀州所属宁化、归化、清流三埠,全被闽私侵占,盐课常常只能销七成。张之洞奏准先以潮州知府兼署运同,后又遴派廉干之员前往专办,改章设局,终见成效。“整顿行之一年,加课三万,次年复正杂十三万旧额。”(注: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二,第16页;《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395、604、658页。)肇庆、潮州两府税厂和梧州税关,擅立各种名目,浮收勒索很多。张之洞通过派员明查暗访,查出各种积弊,重定新章,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裁减,刻石榜示各个水陆通区,永远遵行。通过这次整顿,肇庆商民每年可省银二十万余两,梧州可省二十五万两。(注:张之洞:《查革肇、潮两府税厂积弊折》,《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409~416、418~425页。)张之洞调湖广总督后,访知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运销湖北的土药偷漏税收严重,一由于征收税卡较少,二少缉私巡勇,决定认真整顿。计南北两路增设隘卡二十多处,增招缉私巡勇500多名,派遣镇道大员分南北两路督办。行之一年,土药税收由7万余两增至31万两,成为税收大宗。(注:张之洞:《整顿土药税项筹拟办法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768~772页;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三,第2页。)1902年,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察知两淮盐纲疲弊,立即亲赴仪征调查,委派得力督办,分别奖惩,同时剔除各种弊端。经过整顿,盐课明显增加,第一年增课厘50万两,第二年增加100多万两。自从货物推行厘捐以来,“弊窦日滋,局卡繁密,司巡苛暴,查验则到处留难,浮费则有加无已,以致商利日薄,民生日艰,良懦者歇业而失生计,狡黠者驱之以归洋旗,徒召怨咨,无裨国用,体察情形,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注:张之洞:《裁撤厘金局卡试办统捐折》,《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1675~1676页;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五,第16页。)1905年,张之洞经过深思熟虑,决心在湖北境内裁撤厘金局,试办统捐。计裁去厘金局29个,保留20个。凡货物自外省来的,在入境第一卡征收统税;来自本省的,由产地运出内河第一卡统计其指运之地沿途各卡所征之数合并征收;本省销售落地之货,在最大市镇征税后转运其他地方,其落地捐概不征收。试行一年,税收增加十万缗。对商民的苛索勒征情弊,一并清除,商民称便。
上述一系列事实表明,张之洞在改革清末弊政中,态度坚决,措施得力,成效卓著,是一位实心实意、力图振衰起弊的统治阶级改革派。
4.采行西法,御侮图强。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最可贵之处,在于能适应时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改革措施,与时俱进。张之洞继承了前期统治阶级改革派师法西方、抵抗西方侵略的爱国传统,把师法西方扩充到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以至政法等各个领域,从而把统治阶级改革派师法西方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首先在军事方面,为了建设一支足以抵抗西方侵略的军队,张之洞把练兵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早在出任山西巡抚时期,他就着手筹改营制,规定“无论马步,火器概用洋枪”(注:张之洞:《筹改营制折》,《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226页。)。经过中法、中日战争,他深知救亡图强,非按西法编练军队不可,所以在署理两江总督期间,就着手按西法编练自强军。到湖北以后,经过十年努力,终于编练出一支包括步、炮、马、工、辎各兵种、称雄江南的湖北新军。他还购造兵轮,先后在两广、湖北建设起近代化的水师。
其次在经济方面,他建立的汉冶萍公司,规模宏大,乃亚洲当时最大的重工业联合企业。纺织丝麻四局则是著名的轻工业企业。湖北枪炮厂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军火工厂。此外,还建立铜币局、银元局、官钱局、江岸机车厂、白沙洲造纸厂、武昌制革厂、汉阳针钉厂、湖北毡呢厂、既济水电公司等许多近代工厂。由于张之洞的努力,湖北基本上建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再次,铁路交通建设。京汉铁路是他首倡建立的,以后又有粤汉、川汉铁路的建设,还有邮政电讯建设。武汉城市交通、长江航运的开发,无不有张之洞的功绩。
第四,文化教育建设。“保邦致治,非人无由”(注:张之洞:《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94页。)。张之洞曾在湖北、四川做过两任学政,对文化教育一向重视。后来当了督抚大员,深感人才匮乏,对兴学育才表现了空前的热心。早期他几乎在哪里任职,就在哪里建书院。后来他倡议废科举、兴学校、派游学,又使新式学堂蓬勃发展,出国游学者络绎不绝。湖北省在他的长期主持下,新式教育遥遥领先于全国各省。据湖北学务公所统计,全省在1910年共有各类学堂2738所,学生人数达99064人。湖北从1896年开始派遣出国留学生,十多年间,出国留学者达5000人,这在全国是少有的。在文化方面,他创办了湖北官报,创建了湖北图书馆,扩充了湖北官书局,还成立了江楚编译局,翻译西书,介绍西学。凡此种种,对湖北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最后,张之洞还把师法西方扩展到政治法制领域。前期的改革派,学习西方的范围,主要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编练。他们对西方的某些政制虽很赞赏,但还没敢提出要向西方学习。张之洞则对师法西方的政治法制给予高度重视。他在《劝学篇》里提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还说:“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注:张之洞:《劝学篇》,《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05、9740页。)早在山西巡抚任内,他就设立洋务局,延访熟悉洋务人才。1901年,清政府谕令各督抚司道就推行新政献计献策。张之洞会同刘坤一上奏了著名江楚会奏三折。其中采用西法十一条中,就有劝农政、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推行邮政等属于政治法制范围。这在师法西方史上也是一个重大进步。
总之,在师法西方上,张之洞继承了统治阶级改革派的传统,同时大大扩展了师法西方的领域,而且成效显著。
三
张之洞和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从表面看,有些地方是相似的。比如,张之洞主张师法西方,曾、李等人也师法过西方;在师法西方的具体实践中,洋务派兴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张之洞也兴办了湖北枪炮厂;洋务派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张之洞兴办的民用企业更多。人们把张之洞称为洋务派殿军,就是因为他和曾、李等洋务派有这些相同之处。但是,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要确定其性质,还必须透过现象看实质。因为现象常常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只有实质才能决定事务的性质。
首先,统治阶级改革派和曾、李等洋务派在对外态度上有根本性的区别,而且贯串始终。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威胁,是坚持抵抗,还是妥协求存,这是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改革派和洋务派一直不同,而且进行过不断的斗争。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等统治阶级改革派面对英国侵略,即力主严禁鸦片,坚持抵抗;而琦善等人则胁于敌人的船坚炮利,不惜卑躬屈膝,谋求妥协投降。左宗棠当时坚决赞成林则徐严禁鸦片的主张。在各省督抚会奏的禁烟意见中,他认为“少穆先生(即林则徐)折奏最好。”并强调“此乃万世利害转机”(注:左宗棠:《复周汝光》,《左宗棠全集·附册》,第29页。)。后来鸦片战争因琦善等人妥协投降,导致节节失败,他表示了无比悲愤,指斥“洋事为琦督所误,遂尔决裂,卒难收拾……宗棠窃计,夫已氏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注:左宗棠:《上贺蔗农先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24页。)。他还对议和进行了批判,指出:“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注:左宗棠:《感事四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9页。)当时正在北京翰林院供职的曾国藩,其态度则和左宗棠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竭力为清朝的妥协投降政策辩解,认为这样做是息兵安民的良策,“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注:曾国藩:《禀祖父母》(道光廿二年九月十七日),《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3页。)
1870年,天津人民发动反抗外国天主教侵略势力的斗争,造成“天津教案”。如何处理这个案件?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的态度又有截然不同。曾国藩和李鸿章先后奉命和法国交涉。他们为了“曲全邻好”,明知事件的发生“曲在洋人”,却硬是以曲为直,向侵略者“满口认错”,“事事认错”,斥责坚持正义的天津人民为“乱民”,攻击人民反侵略是“刁风”。最后完全屈服于法人的要挟,捕杀义民20人,判处军、徒等刑者25人。(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二,第32页;《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第10页;《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一,第3页。)左宗棠则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义愤于形,非乱民可比”。天津人民的反抗是正义的,应当“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不能“以仓卒不知谁何之人论抵,致失人和。”“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注: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197~199页。)同一事件,两者的处置方针如此不同,谁是谁非?不言自明。
祖国的新疆,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在英国的卵翼下、从中亚浩罕汗国窜入的阿古柏占去大部分地区,俄国乘机占夺伊犁九城。正当左宗棠平定甘肃,筹划进军新疆之际,曾、李等人为了“力保和局”,却跳出来坚决反对。先是曾国藩提出“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主张,随后是李鸿章在统筹全局的幌子下,建议停止收复新疆,腾出经费专办海防。他认为新疆是荒漠之地,每年为守卫新疆要花费三百万巨款,很不值得。而且向新疆进兵,势必开罪英俄,妨碍“和局”(注: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第10~25页。)。左宗棠为了收复神圣的祖国领土,痛斥了李鸿章等人的误国谬论,强调东南海防,西北塞防,“两者并重”。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注:左宗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188~191页。)而且从全局考虑,“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注:左宗棠:《遵旨统筹全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702页。)清廷接受了左氏的正确意见,授予他政治、军事和筹饷全权,督办新疆军务,统理收复新疆事宜。
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清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就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部疆土。1878年,崇厚奉命使俄,交涉收回伊犁事宜。昏庸的崇厚,经不起沙俄的软硬夹攻,于1879年8月和俄签订了《里瓦吉亚条约》,丧失了大量领土主权,仅仅收回一座孤立的伊犁城。消息传回国内,立刻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当清廷将条约内容通知左宗棠时,左即认为全是“损中益西(俄)”,明确表示“不可允”,必须改订新约。李鸿章又唱反调,居然认为要求收复伊犁是“好大喜功”,而今签订了条约,理应接受,“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左宗棠提出的改约之议“万做不到”(注:《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九,第6、34页;《奏稿》卷三五,第16~18页;《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十,第17页。)。左宗棠严正指出:沙俄“占我土地,诱我部落,势不至化中为俄不止”(注:左宗棠:《复陈李鸿章所奏各节折》,《左宗棠全集·卷稿七》,第431页。)。如果按李鸿章“割地议款以苟旦夕之安”方针行事,则“我退而彼益进,我俯而彼益仰,其祸患将靡所止极,不仅西北之忧也”(注: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539页。)。张之洞也站在左宗棠一边,上奏清廷,详陈俄约有十不可许,认为“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建议修武备,缓立约,治崇厚以应得之罪。(注:张之洞:《熟权俄约利害折》,《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32~36页。)同时指责“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注:张之洞:《熟权俄约利害折》,《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32~36页。)在左、张等改革派的齐声呼吁下,清政府不得不另派曾纪泽为出使俄国大臣,与俄国议订改约,终得挽回部分利权。
继伊犁交涉之后,围绕法国侵略越南,统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派之间又展开了一场新的较量。面对法国的步步北犯,李鸿章还是一如既往,推行妥协投降路线。他“始终不以主战为然”,拼命寻求与法国妥协的门道,不认真作抵抗准备。这时左宗棠已从西北调回,先是在北京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不久改任两江总督,后又督办福建军务。他看到越南局势日趋衙严重,十分焦急,特致函总理衙门,敦促放弃“主款”而确定“主战”方针,“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事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注: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796页。)并特命王德榜回湖南募集旧部,组织“定边军”,开赴越南参战。此时正在山西任上的张之洞,得知越南边防告急,朝廷和战不定,立刻上奏清廷,陈述战守事宜十七条,认为“定计宜坚,赴机宜速,自守宜固,料敌宜审,必如是而后有济”(注:张之洞:《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83~190页。)。不久,他调任两广总督,即以全力组织抗法斗争,终于很快扭转了局势,在越南战场取得抗法战争的胜利。可是,李鸿章却提出“乘胜即收”的方针,结果在胜利的形势下,却订立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改革派拚死争得的成果,竟被洋务派葬送了。气得左宗棠一病不起,赍志以殁。张之洞也为之忿忿不平。
十年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改革派与洋务派围绕和战问题,继续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李鸿章从战争一开始,就存一不敢战之心,向英美等国乞求调停,丝毫不作应战准备。结果水上陆上,处处被动挨打。李鸿章原想“避战”以保存实力,结果花了十多年功夫建起的北洋海军,在战争中全军覆没。陆军也一败涂地。张之洞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坚定主战,战争一爆发,即调遣湖北军队一万多人北上参战。奉调署理两江总督后,又马不停蹄地加强长江沿线防务,从兵力、财力上支持抗战。李鸿章在日本签订了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张之洞“愤恨欲死”,致电总理衙门,逐条剖析了条约的严重危害,斥责李鸿章卖国胜过南宋秦桧。
其次,改革派和洋务派虽然都主张师法西方,而在师法的目的上并不完全一致。统治阶级改革派从林则徐到张之洞,师法西方的目的都是为了抵制西方的侵略。魏源提出,要“以彼之技,御彼长技”,要“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在此一举。(注:魏源:《圣武记》,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391、336页。)左宗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提出了自造船炮的主张,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十分推崇。后来,他在1866年在福州建马尾船政局,自造轮船,就自认是实践魏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注:左宗棠:《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7页。)。张之洞一生,在师法西方方面用力最勤,成效最著。他把发展近代机器工业视为“富民强国”之本,因而短时期内,多方筹集资金,广泛网罗西学人才,大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在湖北建立起一个以钢铁为主、门类比较齐全的近代工业体系,无非就是希望国家早日走上富强之道,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趋。他把练兵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更明显表达了希望通过练兵,为国家建设一支足以“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近代化军队。至于兴学育才,同样是为国家富强着想,因为他认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人才要靠教育培养,有了近代化的人才,才有望建设富强的国家。
而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最初购买洋枪洋炮,惟一目的是为了镇压当时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全国人民大起义。后来兴办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虽然也常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但主要还是为了增强自身实力,为了保全自己的禄位。所以他们花了国家许多财力,建设起一支近代化的北洋海军,却在实际反抗外国侵略中毫无作为,一触即溃,全军覆没。这自然与改革派师法西方是为了抵制外国侵略,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在内政改革方面,改革派和洋务派也有很大差别。改革派为了挽救清朝的统治危机,在改革弊政上下了很大的力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洋务派本身就是一个苟安图存的政治派别,他们眼光短浅,只图目前,只图私利,除了对外妥协投降换取国家苟延残喘,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反抗,以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外,他们无意在内政上进行改革,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政绩。
综观活动于晚清时期的统治阶级中的三个派别,他们也有共性,那就是要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从维护统治出发,他们都主张对人民的反抗实行镇压。但对他们的评价以及他们在晚清历史上的作用,还是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区分,不但要把顽固派和改革派、洋务派区别开来,更应把改革派和洋务派区别开来。事实上,晚清时期的历史反复表明,统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派(正确地说是妥协投降派)在对外态度上,一直执行着两条不同的路线:改革派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一直坚持抵抗路线;洋务派为了苟安求存,在洋人的卵翼下生活,顽固坚持妥协投降路线。国家的许多利权都是由于洋务派执行妥协投降路线葬送的。两派在师法西方上虽有某些相似之处,实际上是貌合神离。过去把左宗棠、张之洞等称之为洋务派,实际上模糊了爱国与卖国的界线。把爱国者与卖国者相提并论,统称之为洋务派,是十分不妥的。
标签:张之洞论文; 左宗棠论文; 林则徐论文; 张之洞全集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清朝论文; 晚清论文; 历史论文; 胡林翼论文; 张文论文; 陶澍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八国联军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明治维新论文; 鸦片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