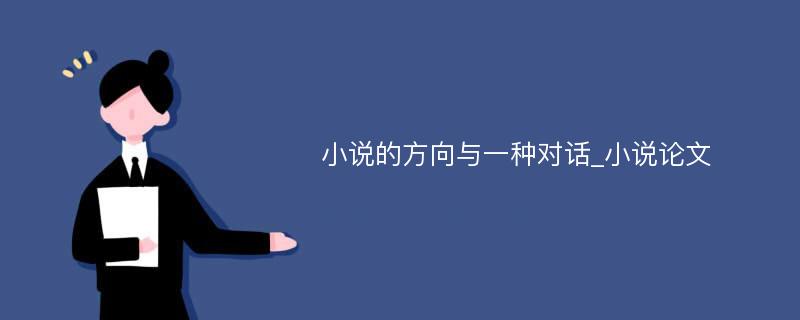
小说的方向及一种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向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在相当大意义上必须果断,甚至武断。特别是当我们回顾某段历史时,理论的姿态决不是轻描淡写所能应付了事的。它必然作出判断与裁决,没有这些,理论也就失去了它的尊严与意义。不管这种判断是否正确,它都只能作出裁决,从而表明理论家的立场与态度。在这判断面前,理论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分析,这种分析必须建立在相当可靠的事实与论据之上。理论家通过这庞大而有效的工程建筑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系,这就是理论家真实的工作。因此说,没有判断或说没有观点的理论家不是合格的理论家;而没有分析只有结论的理论家也不是称职的理论家。原因在于,前者是一种蛮干,它松散、混乱,没有建构;而后者则成了空中楼阁,只能给人印象,没有印证。
陈晓明认为,文学批评同样只能与文学史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在这点上我表示赞同,因为任何文学批评都是与文学史相牵连的,也只有与文学史挂钩,文学批评可能充分体现其意义与职能。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对文学史的建立,文学批评有职责作出判断,它不能停留于描述。只有描述的文学史是失败的,因为它弃绝了权威与批评的果断。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任何一种来源于不客观判断的文学史都容易过时。这就警诫我们时代的理论家:判断的尺度是什么?我们靠什么裁决这个时代的作品?
A.回顾一下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是必要的,特别是当我们面对新世纪小说的前途问题时,梳理与回顾都有益于我们更好地展望。新时期面临的是觉醒与吸收,经过了十年浩劫的苦痛及血腥般的记忆,文学革命的恢宏之势汹涌而来。在这样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中,迎来的是与五四精神交相辉映的伟大举措。被压抑与捆束的人觉醒了,于是小说出现了“大写的人”。而对这段奇特的历史,人们开始抚摸与反思,在伤痕与苦难带来的两面效应中穿行,有控诉有反思也有一种美好的记忆。
在小说中,随着伤痕及苦难的稍纵即逝,“知青”生活的丰富经历化成了一道道美丽抒情的小河,小说家们采用了寻找人的情感记忆的叙述方式朴素地向读者诉说。在这样一种娓娓动听的故事情调中,热情与真善美的交融把小说推向一种极美。更由于一种忧伤的情感基调的定格,读者的共鸣便更多地带上了余音绕梁的效果。显然,这种小说是成功的,它在真善美的情感中找到了立足之地。虽然此时的小说还没有借鉴什么外国小说技巧,但这种积淀已久的生活与情感一旦爆发,它的能量仍然是惊人的。就是在这一切优越条件的掩护下,“知青”小说取悦了众多的读者,许多小说家因此声名鹊起。
也就在此时,人们生活渐渐有了明显的变化与好转。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大大地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人们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温饱问题的解决带来的是人们对精神文化饥不择食的追求,小说读者的热情同时带来了小说的空前繁荣。在这种背景下,一切丰厚的记忆与经历都被廉价地展示出来,小说家们还没有认真加以思索就答应了读者呼唤。由此,中短篇小说空前繁荣,而长篇小说却凤毛麟角。从今天看来,当时的中篇小说魅力不容置疑,其优秀的素质至今令人心动。这是一件奇怪的现象:围绕着一个知青经历竟会产生如许多优秀的小说!它同时印证了一个事实:题材是写不尽的,因此小说不会轻易死亡。
另一方面,随着“知青”小说面貌的日益雷同,小说家开始尝试着朝美丽的大自然进发。由于“知青”经历带来的对大自然刻骨铭心的记忆,小说家把那一片思念的情愫放置于博大而美丽的大自然之中。在此,乡村仍然是个重要的场景,人们通过它还原到记忆的深处。张承志、贾平凹便是这个时期出色的代表。在张承志的小说中,狂热的人与大自然统一、协调,在博大的大自然背景衬托下,人被扩张、放大,从而以此完成英雄主义及理想主义的一种梦想。在这样一个间隙中,小说家都试图完成心中那片遥远而极美的回忆园地,但孤独的主人公的行走带来的却是一种深刻的遗憾与失落,更深一层的思索由此秘密地抵达了心灵的深处。
B.历史的进程再一次显示了它那厚重的份量。在一批虽然忧伤但却明丽的小说走过之后,留下的便更多了一份执著与沉郁。以刘索拉、徐星等为代表的“现代派”开始以放大的“自我”诉说激情,这是一次夹杂着个性解放与新个人主义而唤起的解放思潮。在一批年青人的狂热情绪笼罩下,这批小说脱胎换骨般地燃起了这股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喧哗与骚动的背景后面,是青年人那悸动不安的灵魂与精神。显然,小说已经在此无意识地把历史遗留下来的病症加以深化,它以重新唤起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对自我的变相欣赏来否定一切。这种非局外人的眼光证实了这种小说的“伪现代”性质,主人公的痛苦并不能排除它对“自我”的欣赏。
时代已经来到85年中期,刘再复的一本《性格组合论》引起人们奇异的热潮,而李泽厚的美学也已经深入人心。在众人捧读美学的高雅举止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成为公式被大家熟记于心,人被推向了制高点。同时,伴随着86年经济财政的衰落,地方自主权得以扩大,许多单位团体开始自负盈亏走向市场。文学由此失去轰动效应,刊物不得不重新考虑读者的地位。在读者不再迷恋于理论以求生活指南而寻求消遣的同时,形形色色的杂志、舞厅、歌厅及卡拉OK抢走了读者大量的闲暇时光。文学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它必然承受寂寞。
寻根热的又一次过去导致文学失去主题,已经没有什么庞大的题材值得小说家们倾心创作并引起读者的关注。寻根是一次文化与自然的混血产儿,它涉指了人们对文化与自然兴趣的进一步丧失。
C.失去了方向的小说开始转向自身隐蔽能量的挖掘。在人们不再关注写什么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可写的时候,小说家的智慧便体现于走到了“怎么写”身上。这种对小说本体的思考转换了人们的视野,人们发现,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而这样那样的叙述也叫作小说。由此,马原、残雪、洪峰的意义就显得非同一般,特别是马原,他在86年下半年及87年上半年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作为传统小说的可怕入侵者,马原带给我们的是对小说传统经典现实主义规范的猛烈冲击,“大写的人”至此才真正解体。在残雪、洪峰等一批后继者身上,主流已经失去,小说在真实的意义上强调自身,回到自身。这是一次惨痛而略带喜悦的背叛,也是一次渎神运动。在它们背叛与亵渎神圣的背后,精英小说以进一步对读者的反抗得以站立。
这个时候的小说已经渐渐走向了小说的反面,那就是它拒绝了相当一部分的读者。但从马原、洪峰、残雪他们身上似乎看不出这种迹象,因为马原的叙述时时刻刻都在说明,他想讨好并吸引读者。然而,他却只想把读者引上路,至于后面的路别人会不会走下去马原并没有过多的思考。马原甚至更容易被自己的叙述迷住,他只对如何写下去感兴趣,却对读者置之不理。这也许是一次有意的忽略,亦或是一次无心的失误,这一切都只有小说家本人清楚。
洪峰的《奔丧》是一篇比较典型的小说。在这样一个奔丧的题材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与加缪的《局外人》相类似的主人公形象。小说完全违背了传统经典现实主义的规范,它在每个细节上都与传统相背,从而完成了“审父”的阴晦心理与意识,并进一步对神圣加以嘲笑与亵渎。主人公那违背常规的举动与意识进一步言诉着根深蒂固的背叛欲望与仇恨的欲望,在此,谁也无法考证这种反常的举动及违背人伦道德的举动意识源于何处,我们似乎只能仅仅在那惊人的举止中看到一种无意识。
D.先锋小说的出现及旗号的铺展令人吃惊。在苏童、余华、格非、北村、吕新等一批年青人的倡导下,先锋小说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使命,这种主张至今听起来仍旧有些悲壮的力量。应当说,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在假文学与精英文学的分野下,先锋小说强调叙述与历史形式的重构。它明确地不再写宠大的政治观念与信念,也不再捕捉社会重大题材。先锋小说是个没有很明确定义的概念,包括后来的孙甘露、叶兆言以及更后的一批刚露头角的小说家都可以归在此列。应当说,先锋小说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它并不象一些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轻飘。至少而言,它提供了中国小说足够长久的理论话语,也给小说指出了可能性的方向。同时,它也代表了当代中国小说最高的艺术水准,面对它,后来者将失去欲望与冲动来构建这样的小说。无论是在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还是格非的《迷舟》与《褐色鸟群》上,亦或余华的《现实一种》与北村的《聒噪者说》,还是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它们都以一种后人无可企望的高度封锁了后来者前进的步伐。不论是在叙事方式,还是在语言、结构或风格上,这些小说都从尽可能的范围内对艺术作出了探险与尝试,而成功又同时阻隔了后来者的交流,因为它是形式的、一次性的。毋庸置疑,博尔赫斯只存在一个,而新小说亦只能昙花一现,作为中国的先锋小说自然亦只有一次机会。面临这样的机遇,我们看到了后来者的尴尬,文学便在这进退两难的境地中来到了九十年代。
E.九十年代对于今天而言并不是历史而是现实。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文学面临的两难境地,它不愿意向后退缩回到传统现实主义当中,但前面的道路又已封锁,因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已经无路可走。靠技艺的翻新来获取读者的青睐已经成为古老的神话。在这样的时刻,新写实小说成为一度被大家使用的名词,虽然它理论还欠完备,甚至在相当大程度上显示出幼稚,而且也比先锋小说的提法远为逊色,但它由于缺乏有力的抗衡对手而得以确立。新写实主义(也叫新现实主义)是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一种变形,它以还原生活的原生态作为自己的主要特征,同时,它运用了客观主义的叙述态度写生活的负面,展示了生活的琐碎与苦难,并体现出了一种审丑的立场与态度。另外,它在语言上往往不事雕琢,从而显出了一种粗鄙化的倾向。应当说,新写实小说是最后一个比较完整的小说流派概念,在它之后,小说便开始走向个人化,同时也走向了沉默。
新写实小说的主要代表应当是刘震云、池莉、方方。另外,由于先锋小说的明显转化,苏童、余华、北村也被许多评论家列入新写实的行列。同时,也包括了叶兆言等一些比较传统的但却写得相当出色的作家。应当说,新写实主义仍然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因此它的局限不可避免。再加上它源于一次刊物的策略,提出得过于草率,因此很快就销声匿迹。
F.由于个人化写作日渐明显,因而任何概念流派的提出都显得牵强附会。但理论永远不会甘于寂寞,它已经惯于为这个文坛制造一切热闹景象,加上刊物的生存需要,一个个名目繁多的流派还是被炒得沸沸扬扬。这个时期显得出奇的平静但又骚动不宁,平静在于没有什么能够深入人心引发大起大落,骚动则在于每时每刻都有各种各样的新名词新流派出现。诸如新历史小说、新体验小说、新都市小说、新状态小说、后新时期小说、后后现代主义小说等等概念都不会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因为靠“新”与“后”的旗号显然已经没有任何新意,它只会给人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与反感。我至今不明白中国的评论家智商怎么如此低下,为什么不能去发现新颖别致一点的名词,而偏偏在令人厌烦的“新”与“后”上面打主意?要知道,“新”与“后”实际上是流派理论的最大敌人,它导致的更多是人们对理论家低能的猜测。更何况,“新”与“后”本来也是一个虚浮的概念,它的范围太容易让人忽略时间的存在,因为时间的变迁必将为任何的“新”与“后”打上苍白的颜色。
在这样一个失去命名的时代里,小说家的出现已经取得相对的自由,他不再通过什么流派联展得以推出。但与此同时,它却在另一个办刊策略中得以亮相,这就是期刊联网的方式。至今为止,《大家》、《作家》、《钟山》、《山花》的“四联网”是我所见最容易推出作家的形式。虽然推出的小说家不尽人意,但还是不妨碍小说家成名。于是,一大批小说家又开始以各种面目活跃在读者面前。然而一个事实不容否认,那就是人们对这样推出的小说家更多地持一种观望的态度,也就是说并不太信任刊物的“四联网”。但我们可以知道,在这样一个没有轰动的时代中把一个陌生的小说家推到读者面前,刊物显然尽了它的职能,而且应当承认这种方法卓有成效。
G.在诗歌日益沉寂的今天,小说也迎来了相对寂寞的时光。象谁也没法再给诗歌说清楚一样,小说也让人感到了言说的困难。想要统一言之的时代显然已经过去,我们面临的更多是一种多元化的格局。也许,这同时意味着一种自觉与成熟。
陈晓明的分类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它说明了一个事实:小说已经走向多元化,但它仍有一些特征比较贴近,在陈晓明的话语中,我可以捕捉到这么几种归类或特征:
第一,非历史化的个人化立场。陈晓明认为,90年代文学出现了相对疲惫的状态,一批新出现的小说家已经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叙述。这也就是所谓的晚生代,它是相对于整个人类艺术史而言的。这一批作家有一种晚生感,他们缺乏艺术大师的想象力。在陈晓明看来,80年代末期的小说已经耗尽了想象力,艺术形式革命已经不可能。同时,他们笼罩在“知青”的阴影里,与文学史对话发生障碍,从而找不到插入点,找不到艺术创新的冲动。在他们面前,文学史已经丧失,个人的记忆强化了非历史化的个人话语。显然,这种关于晚生代的描述分析是相当出色的,但我们看到,晚生代小说家的归类同样是困难的。虽然小说家的写作有些类似,但实质却往往相差甚远,而且这些小说在我看来仍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比如说,把何顿、韩东、刁斗、述平、张旻、毕飞宇、鲁平、东西等这样一大批作家划归一类就令我有些吃惊。无论从经历还是从小说经验而言,这样归类都显得牵强,从年龄上简单地归类都是显得不那么明智。当然,作为一种谈论的方便这种名称是许可的,但若把它形之于理论就显得苍白。
不容否认,这些小说家在相当大程度上都写自己经历,他们拒绝大师们的艺术经典文本,与艺术史、文学史没有对话。他们的创作与历史也不发生联系,小说更多展示的是生活中的原生态。一个很平常的生活片断会在这批小说家手中信手拈来成为一个短篇。我不敢说它会成为出色的短篇,但它却让人耳目一新,甚至也能给人某种启示与回味。这种非深度化的表象化叙事同样具备了一种效果,虽然它往往不事雕琢,随意就写出来了,但仍不失为一种别致的小说。当然,你若要如何去追寻这小说的意义,那是没有的,它只会让你失望。我想,它的意义就在于在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中重提,从而给人一种淡淡的回味。
陈晓明同时认为,这些小说写得轻松、自如,在捕捉表象方面非常出色。这同时也就认同了一种述说:这个时代剩下的就是表象、欲望以及男女的交欢。由此,陈晓明认为这种小说是出色的。
H.在另一方面,陈晓明认为90年代的小说强调感性化,它停留在感性经验的生活样态。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是贾平凹的《废都》。至今为止,我们仍然没办法回避对它的言说。应当说,《废都》给我们提供的不是一部出色的小说,而是一部重要的小说,因为它带给时代许多重要的话语。《废都》的意义在于它指出了这个时代文化的彻底衰落与颓废,它通过一系列艺术家的事变强调说明了艺术的死亡。同时,它通过大量的性描写营造了时代的性欲史,从而力图说明在表象的背后是欲望与男女交欢,除此之外不存在真实。显然,《废都》是值得读解的文本,它给我们时代提供了象征主义的巨型代码。但同时,它又是一部失败之作,因为作家的立场在同构中没有升越到一个层次,从而引起了人们过多不怀好意的误解。当然,这不能怪读者,它只能说明作家还没有能力把自己的视点凌驾于主人公之上。
《废都》的很大程度上的失败可以引起新一代作家的警戒,特别是在陈晓明划定的晚生代作家身上,过多表象的自然刻画都容易使作家流于表象化的肤浅。
I.在第三个方面,陈晓明注意到了反男权主义的女权主义叙述,这是90年代异彩纷呈的另一侧面。在一批女作家身上,偏激的女性个人故事被空前复制。强烈的个人经验的大胆抖露,特别是包括性经验、性体验在内的个人隐私被作家自己出卖,从而强烈地诱发了广大读者的观赏欲望,特别是诱发了男性读者的欲望。不容否认,这批小说有它独特的阅读价值,但同时也出示了很多问题。作为一种隐私的暴露所带来的阅读激情到底能否长久?另外,人们对这种暴露到底能宽容到什么限度?所有这些都是值得女作家深思的。当然,女作家本身就有一种暴露的欲望,而且这种暴露同时也带给读者一种全新的阅读感受,这都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一种进步。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暴露可以没有分寸或者厚颜无耻,如果这样,那小说的悲哀也可想而知。
因此,对陈染、海男、林白、徐小斌、迟子建等一大批比较年轻的女作家而言,问题依然存在。虽然她们的小说成就突出,但大都还停留在女性经验的范畴里面。她们抒写的也大都还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当中。她们那情绪或绝望或骚动都刻画得淋漓尽致,那心理也极尽细腻与变化,从这意义上说,她们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以前任何女性作家的写作,但在另一方面,她们一直没有摆脱自己向外界世界涉足,特别是还没有比较深刻的以女性视野来描摩时代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J.在第四个方面,陈晓明认为是道德主义及理想主义的话语,并认为它的代表是张炜及张承志。在陈晓明看来,这明显是一个多元化、个人化的时代,作家都以个人化的形式谈论各种话题。但又认为,在张炜及张承志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道德主义及理想主义过于片面,特别是它容易助长某种东西的单方面膨胀。陈晓明不赞赏企图以个人化的形式强加或统合给别人的思想,并认为这是一种霸道,同时又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毫无节制表示不满,认为它过分夸大了知识分子启蒙,过分夸大了真理的绝对性,并认为它有偏执的一面,是对个人的一种强调。
在此,我不想轻易否认陈晓明观点的可贵的一面,也不想对张炜、张承志的观点作片面与肤浅的概括,我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张炜、张承志的小说远远不象陈晓明说的那么简单。同样,在提及北村这位已经相当重要的小说家时,陈晓明也提出了自己相当有见地的看法,但我也认为陈晓明对北村的小说缺乏深入与客观的把握。这牵涉到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小说的精神问题。在我们乐此不疲地谈论小说技巧(如后现代主义)时,我们是否想过,我们把小说的灵魂忘得一干二净呢?
K.这无疑是一个相当紧要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无主题”的杂乱无序的小说时代时,我们最不可忽略的就是小说的本质问题。
面对历史与九十年代的小说状况,从回顾来到现实,我们发现了一个鲜明的小说事实:中国新时期小说面临的是危机。从小说技巧上说,新时期小说在80年代末就已经走向了最后的辉煌,正如陈晓明所说,已经不存在超越的可能;而从小说内容上说,“知青”已成为历史,寻根及后来的一系列流派都已被写得支离破碎,没有人再愿意重复一遍炒冷饭的滋味。由此,九十年代的小说出现了空前的盲目与危机。从小说家对理论的失望可以看到,小说家对小说同样失去了信心。
这种状况实际上来源于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失落,那即是文学信仰精神的丧失。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文学的失落,关键在于人的失落,主体意识失落了,创作个性也便随之失落(张慧敏语)。在评论界大肆哄炒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背后,由评论家的判断尺度消失带来了小说家的迷惘,因为意义已经缺席,文学成为虚饰。这显然是最让小说家无法承受的事实,理论的前引功能一旦消失,对于这个习惯以理论为路线进行创作的国度来说,危机就实实在在地降临在每个小说家身上。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并非所有小说家地处荒原与迷惘,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小说家确实回到了小说的本质进行创作。他们面对的灵魂与精神开始了拓荒之路,这便是九十年代最值得告慰的文学现象。虽然缺乏足够的理论与之配合,但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学写作,是为心灵与神圣而抒发的诗歌。正是从这意义上说,中国新时期文学特别是小说已经走向成熟(而不是衰落),而面对新世纪,我有信心(完全的)认为:小说必将再度辉煌。
L.实际上,在谢冕、李洁非、王彬彬、陶东风、洪子诚、张慧敏、唐晓渡、蔡翔、吴亮等一大批理论批评家身上,文学的理想精神及信仰精神已经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推崇。所缺乏的是,他们没有始终一贯地形成理论的系统以引领人们的精神。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批评及理论实际上在寓示着小说的勃勃生机。只要我们面对小说的本质存在,我们就会发现:小说实际上已经孕育着极大的潜力,喷薄欲出的时候已经来临。在史铁生、路遥、张承志、张炜、北村等人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足以让我们自豪的期待。路遥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的一部《平凡的世界》给了我们沉重的分量,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一种希望。只要这个希望寄寓在任何一位年轻小说家身上,我想,小说的希望也就到来。而在史铁生、张承志、张炜、北村等人身上,小说则寓示着一种精神的力量,他们执著不二的文学追求必将带给小说以更优秀的素质,这素质是后现代主义小说无法相匹的。
当然,如陈晓明所言,这批小说家由于一种控制不住的激情导致的艺术粗糙及武断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违背了艺术的原则与美感。但是,我同时认为,作为相对空白的宗教信仰与文学相交的领域,这种不成熟是难免的,我们评论家应当以足够的宽容指出它的缺陷,而不是指责与棍棒。另外,作为开端,谁也无法认定这种文学不会走向成熟。我想,这批小说家早晚会意识到这些缺陷,从而完善自己或由后来者补上。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南帆的理论文章,它的严谨与客观至今让我心动,特别是在评论北村小说时所透出的那股慎重,它都远远超出了一般评论家的肤浅与无知。
M.应当在此重提前一段批评理论给我们带来的负面效应,那就是由于一种文化现象的效应,使得人们一言崇高便是虚伪,一谈理想便是矫情,而所有高尚的奉献却瑟缩萎琐羞于见人。无疑,当自己不言情怀便也不允许别人言情怀同样亦是一种霸道。在一批人对真诚与善良进行嘻笑嘲讽的同时,我们是否看到这是一种更为恶劣的不宽容?显然,时代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那就是再逃避神圣的追问已经不太可能。面对精神的溃散与崩败,面对文学信仰的缺席,面对爱情的消失,我们到底是逃避还是面对?是认同还是重建?
谢冕在《理想的召唤》一文中认为,商潮的涌起使人们乐于把文学定格于满足快感的欲望功能,人们因厌弃以往的仆役于意识形态的位置而耻谈使命和责任。对于世俗的迎合使文学(包括艺术)迅速地小市民化,庸俗和浅薄成为时尚。同时还认为,当前的问题并不是文学的受到羁约,恰恰相反,正因为文学的过于放任而使文学有了某种匮失。当前的文学不缺乏游戏,也不缺乏轻松与趣味,不缺乏炫奇和刺激,独独缺乏对文学来说是致命的东西。而这种缺乏导致人们追问文学到底何用?
张慧敏在《文学需要理想精神》一文中也有精采的论述。张认为,今日“理想精神”的提出,意在打破传统理想主义及价值体系被动摇而出现的“真空”状态,还知识分子使命感与责任感。并认为,这种“理想精神”再度强调艺术和生命的同构关系,艺术的选择应该是生命的选择。同时强调每一个人性,在面对人类的死亡景象,写作者有勇气喊出“谁在/我在!”的回应,并本着个人的身份去追寻、去感悟、去体验。同时,反抗灵魂不可承受之轻的零度状态,就要求写作者有勇气去直面和经验现实,从当下的经验存在延伸向未来,并通过无限的求索来达到现时的真实存在。
为了反抗长期以来“理想”与乌托邦神话的纠缠,张进一步认为,今日的“精神信念”便是以艺术“未然”的意识遭遇到每一个此在瞬间,它囊括过去、现在和未来,超越了时空的有限性。因此这种理想精神不是虚幻、假想的彼岸,而是一种以自我为终极的人类精神的远景。并且认为,今日发生“理想精神”的呼唤,不再是启蒙者振臂的倡导,而是如同沐浴在晚霞中的祈祷钟声,是一种以心受难的文化精神的创造。这里想寻求一种对话的可能性,但只有期待,并不强求。更确切地说,这里谈理想精神,只是本着一种希望的情感,想以心携自己邀同仁一起倾听,那水天深处冥冥之中文学魂灵的召唤。
N.在我看来,张慧敏的论点充满了诚恳与执著,也是自然可行的。而在这点上,我认为它恰恰点出了陈晓明另一观点的片面。那就是陈晓明认为,精神已经匮乏,理想早已成了乌托邦,因此不存在重建的希望,只有满足于现状在后现代主义身上寻找技艺的热情。实际上,这不仅仅是陈晓明的观点,它在相当大程度上代表着评论家一种普遍的方向。许多评论家认为谈论精神谈论理想与崇高都是一种徒劳,因为它都是乌托邦。今天看来,这种观点明显失之偏颇。如果它置于八十年代也许恰好点中要害,但若继续把它放置于九十年代特别是目前,那我只能说明评论家的失职。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史铁生、张承志、张炜还是在北村的身上,精神与理想,崇高与神圣都已不再是随意可以用乌托邦加以怀疑与消解的东西。以我比较熟知的北村而言,我没有理由不对他的信仰表示一种尊重与敬畏,因为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他身上的一股力量,这力量只有来源于圣、光、义、爱。不论我们采取何种态度对待北村的信仰,这信仰的神圣精神素质已经在北村的身上得以彰显,而且对于北村而言,这一切都无比真实。这无疑便是我们相当一批狂妄自大的批评家需要重新反省的地方。实际上,不论从何处而言,对信仰采取嘲讽的轻薄态度都不是一个批评家的所为,它除了说明我们无知之外并不能再有什么结论。
只有互相尊重,同时也尊重自己。实际上,在史铁生、张炜、张承志身上,虽然也暴露了信仰者精神上的优越感而导致的艺术粗糙,但并不妨碍他们前进的步伐,我们评论家更没有理由以他们艺术上的粗糙来指责他们信仰的失败。实际上,只要稍有世界眼光,我们就应当承认,艺术的希望在他们身上,特别是对于一个长期缺席信仰话语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艺术方向,它必将给新世纪的中国带来艺术的曙光。当然也不容否认,信仰者的武断曾给评论家作家带来一种言说的困难,也带来一种压力。但我认为,真正的信仰者不会给我们过多狂妄的印象,他们必将也有更多的宽容与爱。这点我在北村的小说中找到很好的印证。
O.谈到最后,我的观点就是;我们不能忽略小说的本质存在而轻言小说的形式,如谢冕所言,这对文学来说致命的东西的缺乏会导致人们追问文学到底何用。只有站立在文学精神信仰的高度上写作,我们的文学才不仅止于游戏、炫奇和刺激,而会一步步地朝崇高与神圣走去。文学也因此才获得家园的安憩,并由此获得一种动力,这动力让每一位作家有着足够的良知与责任感。这就是文学创作的意义所在。
说到底,文学就是精神的,它不给我们提供任何物质的需要。它应该是将光明投向人的内心黑暗中去的行为,是一种人对自身个性的超越性活动。文学的意义在于它给广大读者的精神上丰富的营养,指引人们向神圣崇高迈进;或者说,它是一剂良药,从而解救我们灵魂的病症。而任何技术的鳞片只不过在于增强艺术精神的效果而已。
托尔斯泰曾这样说:“如果对我说,现在的孩子们在二十年后,会因为我写的小说而哭、而笑、而热爱生活,那我愿以毕生的精力来写它。”而福克纳这样一位技巧超前的大师也认为,唯有以良知的精神建造文学的神圣殿宇,我们的小说家才能对自己的职责放心。
面对无数大师的肺腑之言,我们看到文学独一无二的方向,也只有这方向才能引发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为之献出毕生的心血,并从中引发出意义。回顾中国小说家的当下创作,我们完全有信心指正理论给我们造成的误区:文学需要的是精神与灵魂,是实质,而不是片面的技艺与形式;同时,当下小说创作已经充满希望(而非衰落与低谷),它必将在新世纪迎来灿烂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