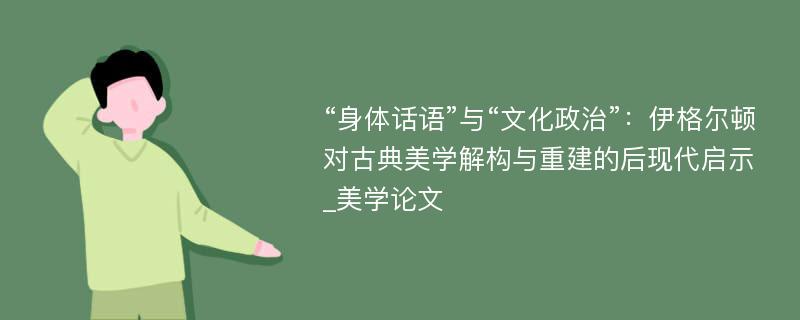
“肉体话语”与“文化政治”——伊格尔顿对于经典美学解构与重构的后现代启示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启示录论文,美学论文,肉体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2)09-0124-05
通览西方美学史论著,不难发现一个情况,在对于鲍姆加通①创建“美学”(aesthetica)学科的历史贡献普遍予以褒赞之外,还有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声音,认为这位“美学之父”乃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问题集中到一点:鲍姆加通的功劳只在于给“美学”作了命名而已,他并没有为这一新学科提供充实的内涵支撑。克罗齐这样说,“美学”在鲍姆加通手里就像一个尚未出世的婴儿受到时机尚未成熟的洗礼并得到了名称,这个名称便流传下来。“但是,这个名称并没有真正的新内容;这个哲学的盔甲还缺少一个强壮的身体来支撑它。”[1]吉尔伯特、库恩也说,“鲍姆加通所得到的荣誉,依传统而论是勉强的”,他为美学这一学科命名,但为事物命名并不意味着就创造了这个事物,因此“鲍姆加通对美学的贡献是名义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2]。这些说法以往一直未获足够重视,今天重读之,却发现其恰恰不乏先见之明。鲍姆加通当初对于这一概念的内涵界定就存在着失误,这些失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纠正,还时常造成种种弊端。现在是改变这一状况的时候了。
一、鲍姆加通的失误
鲍姆加通第一次使用“美学”(aesthetica)这一概念是在他173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诗的哲学默想录》之中,而在1750年出版有关专论时将这一概念作为该书的书名。鲍姆加通建立“美学”(aesthetica)这一新学科的初衷在于弥补德国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缺陷。当时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是以莱布尼兹、沃尔夫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莱布尼兹建立了德国近代第一个哲学体系,而沃尔夫则将莱布尼兹哲学加以系统化和通俗化,他们的理论建树吸引了大批追随者,鲍姆加通就是其中之一。然而鲍姆加通有其进一步的贡献,那就是对于莱布尼兹、沃尔夫的哲学体系进行了修补。他发现,用人的心理功能来衡量,莱布尼兹、沃尔夫的哲学体系并不完整:对应于理性认识的有逻辑学,对应于伦理意志的有伦理学,但对应于感性认识的学科却告阙如。为此,鲍姆加通致力于在研究理性认识的逻辑学之外,建立一个专门研究感性认识的学科,他取名为“美学”( aesthetica)。所谓“美学”(aesthetica)原本与“美”(beauty)无关,它的本义可追溯到希腊文aesthesis,意指感官的察觉,而与理性思维相对应。据雷蒙·威廉斯考证,aesthesis的主要意涵是指“可以经由感官察觉的实质东西,而非那些只能经由学习而得到的非物质、抽象之事物”[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姆加通也将“美学”(aesthetica)称为“感性学”[4][169]。
然而,鲍姆加通对于“美学”(aesthetica)这门“感性学”的内涵的界定,从一开始就存在种种失误。首先,鲍姆加通对于美学的讨论,只是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兜圈子,只是将美学限于感性认识领域。鲍姆加通《美学》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确认“美学”是一门“感性认识的科学”。原话是这样的:“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那么,什么是“感性认识”呢?鲍姆加通认为它是一种“低级认识能力”,具体地说包括感觉、幻想、虚构、记忆力等[4][13]。他有时干脆将其称为“美的认识”[4][35]。鲍姆加通美学的这种唯认识论倾向是在早先的《诗的哲学默想录》中就奠定了的,也可以说是其创立美学的一个理论基础。他认为,诗的哲学考察要预先假定诗人具有一种低级的认知能力。但是以往的逻辑学却限囿于一个十分狭窄的范围内,将这种低级的认知能力排除在外,因而也就无法指导这种低级的认知能力。从这一点上讲,以往的逻辑学都算不上是一种以哲学的方式把握事物的科学。他主张,根据心理学的原理,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一门有效的学科,“它能指导低级的认知能力,从感性方面认识事物”,它就是“美学”,或曰“感性学”[4][169]。
鲍姆加通将美学归于认识论,将美的问题放入认识论范围内加以审视,这是延续了西方哲学重认识论的一贯取向。西方哲学历来将哲学史当成认识论,而且这一倾向愈到晚近其演愈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认识论只是哲学的一部分,尽管是比较重要的部分,但它并不能代表哲学的全部。哲学的内涵不仅包括认识论,而且包括本体论、自然论、人性论、实践论、价值论、功能论、方法论等,中国哲学中还有天人论、知行论、体用论等,可见哲学原本就是多元素、多向度、多学科的。如果仅仅囿于认识论,那就将哲学的性质、内涵和功能大大地缩小了。关于这一点,鲍姆加通《诗的哲学默想录》英译本的译者阿什布鲁纳和霍尔特早就表示了质疑:“他明知情感在艺术中的地位,但他的理论却以强调认知为特点。因而这种观点注定不会长期为人赞同。”[4][181]
其次,鲍姆加通尽管将“美学”从以往的逻辑学中剥离出来,将理性认识归诸逻辑学,将感性认识归诸“美学”或“感性学”,这似乎是为感性争得了一片独立的空间,但说到底他仍持理性至上的立场,对于感性是加以排斥的。他这样定义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指,在严格的逻辑分辨界限以下的,表象的总和。”[4][18]这就是说,感性认识包括“感官的感受、想象、虚构、一切混乱的感觉和情感”[4][15],它们都处于理性水准之下。这就造成了它的种种缺陷:“感性认识也有同样多的丑、错误和令人讨厌的瑕疵,这些必须加以杜绝。”[4][20]因此,它必须谋求自身的完善,才能成其为美。他说:“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完善感性认识)。而这完善也就是美。据此,感性认识的不完善就是丑,这是应当避免的。”[4][18]而感性认识的完善必须在理性的照耀之下才能实现,是理性的光芒赋予它诸多优异的品质:“每一种认识的完善都产生于认识的丰富、伟大、真实、清晰和确定,产生于认识的生动和灵活。”[4][20]不难看出,鲍姆加通承续了大陆理性派的精神旨趣,强调理性对于感性认识的统治地位和主导作用。他的“美学”并不求“美”,而是求“完善”。所谓完善,正是莱布尼茨、沃尔夫美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它成为了“理性”的代名词。例如莱布尼茨说过,美的世界“最完满地体现了和谐是寓杂多于整一的原则”,沃尔夫也说“美在于一件事物的完善,只要那件事物易于凭它的完善来引起我们的快感”[5]。
由此可见,鲍姆加通在他创立的“美学”中对于感性与理性两者还是有尊卑上下之别、存厚此薄彼之意的,这种偏至与他将美学归诸认识论不无关系,因为感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本来就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这种既定的认识论立场和理性至上观念从根本上决定了鲍姆加通对于“美学”的理解,从而他将美学进一步定义为“关于美的认识的本质的理论,以及通过正确途径获得美的认识的方式方法的理论”[4][35],也就好理解了。
再次,鲍姆加通创立的“美学”还存在着一个重大失误,那就是忽视了人的肉体和官能等生物性、生理性方面。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鲍姆加通创立了美学这门“感性学”,但无论是在《美学》还是《诗的哲学默想录》中,却都很少读到对于情感、欲望、快感、生命、本能、爱情、性、潜意识等与人的肉体和官能相关的感性生活的关注,即便偶然提及,也是被纳入认识论范畴来进行考量的。例如,他说“欲望只要是源自于善的混乱的表象,它就是感性的欲望”[4][128],“既然被激起的情感决定着感性表象的产生,能激起情感的诗就比充满僵死的意象的诗更为完善”[4][138],“梦幻中的表象是意象,因而具有诗意”[4][141],“令人惊奇的表象是具有诗意的”[4][144]。这里多次提到的“感性表象”,用鲍姆加通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低级的认识能力所接受的表象”[4][128]。
按说人类的“感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感知、表象、想象、联想为要素的感性认识,这是与认识活动相关的;一是以生理欲望、原始冲动、感官快适、自然本能等为表现形式的感性生活,这是与肉体和官能直接相关的。如果说前者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后者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就是说,美学固然与感性认识攸关,但它也并不排斥感性生活。古人云:“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出自人的本能和本性的感性生活是人们念兹在兹、无日无之的事情,即便单凭常识也不能否认它们对于审美活动的重要性。然而,在鲍姆加通创建的“美学”亦即“感性学”中对此却避而不谈、存而不论,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的缺憾。
鲍姆加通所创立的“美学”或“感性学”的以上失误,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后世学者的批评,而这种批评尤以晚近为烈,其高密度地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这表达了在当今的后现代语境中对于经典美学重作考量和重新建构的普遍冲动。
二、伊格尔顿对于经典美学的解构
在对于经典美学发起的挑战中,伊格尔顿堪称领军,他在1991年出版的《审美意识形态》一书开篇便发表了一个惊天之论:“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6][1]在他看来,鲍姆加通当初创立“美学”的宗旨就出了问题。
伊格尔顿指出,鲍姆加通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将“美学”仅仅归诸认识论。鲍姆加通最初提出“美学”(aesthetica)这一概念,乃是沿用了古希腊的感性(aisthesis)一词,指的是与形而上的概念思想领域相对应的感觉、知觉等感性认识领域,从而他所关心的“不是‘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区别,而是物质与非物质之间,即事物和思想、感觉和观念之间的区别”[6][1]。如果说前者事关感性生活的话,那么后者则事关认识论,而认识论的问题并不能囊括美学的全部要义。
伊格尔顿还指出,鲍姆加通创建“美学”,虽然革命性地开拓了人的感觉领域,但他所推行的实际上仍是“理性的殖民化”。因为“对于鲍姆加通来说,审美认识介于理性的普遍性和感性的特殊性之间:审美是如此一种存在领域,这个领域既带有几分理性的完美,又显出‘混乱’的状态。此处‘混乱’(confusion)的意思不是‘杂乱’(muddle)而是‘融合’(fusion)”。其中审美表象的各种要素并不划为相互分立的单元,而是相互渗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表象是模糊的,恰恰相反,“它们越‘混乱’(confusion)就越趋于获得多单元的统一,于是也就变得更加明晰、完美和确定。在此意义上,诗歌是感觉话语的完美形式。”可见审美的诸单元“乐于接受理性的分析,美学之所以为美学正在于此”。伊格尔顿这里说的是,鲍姆加通沿袭了莱布尼兹、沃尔夫关于诗的表象的分析方法,认为诗的表象既是混乱的、模糊的,同时又是清晰的、明确的,与哲学始终追求概念的明确性迥然不同。然而正是诗的表象这种既混乱又清晰、既模糊又明确的多单元融合体现了理性的主导作用[4][128-133]。伊格尔顿指出,鲍姆加通这一带有莱布尼兹、沃尔夫意味的对于诗的表象的分析暗含着一个策略,即“理性必须找到直接深入感觉世界的方式,但理性这样做时又必须不危及自身的绝对力量”。关于“理性的殖民化”,伊格尔顿还拿鲍姆加通的一个比喻说事,鲍姆加通在《美学》一书中曾将美学比作逻辑学的“姐妹”,伊格尔顿认为,这种“次级推理”(ratio inferior)是将美学变成了“理性在感性生活的低层次上的女性类似物”。总之一句话,“美学的任务就是要以类似于恰当的理性的运作方式(即使是相对自律地),把这个领域整理成明晰的或完全确定的表象”[6][3-4]。可见在鲍姆加通那里,虽然美学从逻辑学中被划分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但仍未摆脱理性的宰制,美学仍是逻辑学谦恭的婢女。
伊格尔顿在厘定鲍姆加通创立的“美学”的边界时,发现了它所存在的一个重大疏漏,那就是对于感性生活的忽视。他说:“哲学似乎突然意识到,在它的精神飞地之外存在着一个极端拥挤的、随时可能完全摆脱其控制的领域。那个领域就是我们全部的感性生活——诸如下列之类:爱慕和厌恶,外部世界如何刺激肉体的感官表层,令人过目不忘、刻骨铭心的现象,源于人类最平常的生物性活动对世界影响的各种情况。”伊格尔顿提出了“感性生活”的概念,这是与“感性认识”同属感性但是与肉体和官能直接相关的生存状态,包括情感欲望、生理需要、本能冲动、感官快适等,这是审美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伊格尔顿甚至认为,“审美关注的是人类最粗俗的,最可触知的方面”,然而“后笛卡尔哲学却莫名其妙地在某种关注失误的过程中,不知怎的忽视了这一点。”[6][1]这就明白无误地批评了鲍姆加通,因为在鲍姆加通创立的“美学”中恰恰将人类的肉体方面给丢掉了。
三、伊格尔顿对于美学的重构
伊格尔顿有一个理论建构的宏愿,那就是在生物性、生理性的肉体的基础上,将美学与解决重大的社会、政治、伦理问题,与人类谋求自由解放的愿景结合起来。他在《审美意识形态》一书的《导言》中就开宗明义:本书“试图在美学范畴内找到一条通向现代欧洲思想某些中心问题的道路,以便从那个特定的角度出发,弄清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政治、伦理问题。”[6][1]这个途径或角度就是“肉体”(body)。伊格尔顿认为,“对肉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他愿意为这一“时髦的主题”进行辩护,希望从这一新的取向来扩展探索问题的路径,即“通过美学这一中介范畴把肉体的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更为传统的政治主题重新联系起来”[6][7-8]。进而言之,“肉体的感情不是纯粹的主观幻想,而是秩序良好的国家的关键”[6][23]。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学小而言之成为一种“肉体政治”,大而言之成为一种“文化政治”。伊格尔顿说过:“我在范畴的使用上是松散和宽泛的,几近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当范畴与有关肉体经验的观念本身结合起来之时,更是如此。”[6][3]因此他所谓“肉体”,并非仅仅指人自然的、原始的动物性方面,而且是指那些经过文化陶铸的生理性、遗传性因素,包括性别、性、身体、种族、民族、族裔、年龄等,它们之间的悬殊与抗衡事关文化,又无不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从而成为一种“文化政治”。
伊格尔顿在感性肉体的意义上讨论“文化政治”的问题,提出了考量现实政治的又一标准,不是将种种文化矛盾仅仅放在阶级斗争、党派斗争的刻度上进行计量,而是将其置于性别、性、身体、种族、民族、族裔、年龄等生理差异、遗传特点的天平上进行衡称,从而肯定性别政治、性政治、身体政治、种族政治、地域政治、生态政治等“文化政治”的重要意义。对此伊格尔顿后来作出明确的论述:“对于过去几十年间支配全球议事日程的激进政治的三种形式——革命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和种族斗争,作为符号、形象、意义、价值、身份、团结和自我表达的文化,正好是政治斗争的通货。”[7]总之,伊格尔顿是将发现“肉体话语”这条美学通向政治的隐秘幽径,视为文化研究的重大成果,从而为文化政治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伊格尔顿是最早提出“文化政治”的理论家之一,他针对“文化政治”兴起之初出现的偏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时有些“左派批评家”认为美学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须为文化政治这一替代形式所击溃和取代。伊格尔顿对此不予苟同,认为这种全盘否定美学的偏至只能导致非辩证的庸俗化倾向[6][8]。在伊格尔顿看来,上述偏见基于一个绝大的误解,那就是忽视了美学与政治之间固有的联系,从而将两者对立起来。他指出:“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的感觉上记录自己、在我们的情感里留下印记的方式而已。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只是政治秩序刺激眼睛、激荡心灵的方式。”[6][26-27]可见,美学中有政治,只不过美学中的政治往往不是以现实的、直观的模样现身,而是以潜在的、抽象的形式若隐若现。它像一座冰山的底座潜藏在海面之下,深不可测但体量巨大,正是它托举着冰山的顶端。其深层机理在于,人们对于种种事物的政治态度遭到压抑以后沉入意识底层,经过长期积累和沉淀转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一旦条件成熟,它便会以某种象征形式出现,而美学就正是这种象征形式。因此,伊格尔顿称之为“政治无意识”。与伊格尔顿并肩倡导“文化政治”并予以身体力行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于“政治无意识”也作了深入的探讨,在他看来,一切文学“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如果说文学作品可划分为直义的和描写的、形式的、神话的或原型的、神秘解释的等四个层面的话,那么只有在第三个层面即在神话的或原型的层面“才达到真正的阐释”[8]。
现代主义对于商品社会的抵制就是通过“政治无意识”干预现实的显例。自从康德将审美判断力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区分开来,审美活动与伦理实践、政治实践的相互疏离和隔绝便成为一种常态,审美成为自律的、封闭的、不及物的,它无关乎伦理实践,更无关乎政治行为。这一状况被现代主义推向了极致。现代主义以荒诞、晦涩、神秘、杂乱、扭曲的形式表达了对于商品社会、金钱世界的大拒绝,它以反审美、反形式的方式抗拒一切来自经济资本、市场机制的收买和招安,远离污浊的势利心和铜臭气,以保证艺术的本真、质朴和纯洁。于是事情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大逆转:现代主义极端的自律性恰恰成为反叛和抗击商品社会的正统秩序和流行风尚的利器,现代主义艺术创造性地故意转向自身,以自律性、纯粹性为盾牌,保持一种抵抗商品社会秩序的缄默的姿态,阿多诺将其比喻为“这是用枪口对着自己的脑袋”[6][369],从而形式变成了内容、审美变成了意识形态、艺术变成了实际行动。因此不妨说现代主义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对于商品社会、金钱世界的否定立场更是一种政治态度。伊格尔顿借用挪威画家蒙克的表现主义绘画《嚎叫》来说明这一道理,画面中的人不知性别,没有头发,鼻孔外露,眼神空洞,整个头脸像个骷髅,唯一引人注意的是尽力咧开的嘴巴和大声嚎叫的表情,而双手紧捂着耳朵的动作更加助长了这种嚎叫的力度和尖利度,但其声音再强也无法穿透画布的屏蔽,这是一个被剥去了社会特征的生物性的肉体。伊格尔顿指出这幅画带有抗拒市场权力和工具理性的政治意味:“我们现在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明显空洞的、具体化的、理性的和管理化的领域。你不能通过有组织的技术迫使其屈服,因此你不得不采取沉默的嚎叫”,从而“审美成为秘密的颠覆、沉默的反抗,以及顽固地拒绝的游击战术”。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里·伊格尔顿说:“审美的自律性成为一种否定性政治。”[6][368-369]这样,现代主义便用极端的自律性、纯粹性超越了鲍姆加通、康德倡导的美学现代性,它不是把审美活动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相互割裂开来,而是“把审美与其他两个系统合拢起来,努力把艺术与社会实践重新挂起钩来”[6][369],或者说将审美、艺术与政治实践重新挂起钩来。伊格尔顿对于美学的这一重构思路也适用于后现代审美景观,一旦条件具备,这种“政治无意识”便会从民族、人种、族裔、地域、身份、性别、年龄等各种领域和路径浮出水面,升华为一种象征性的审美文本。如今族裔文学在西方发达国家异军突起,生态批评在发达工业社会成为显学,而中国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女性主义文学独树一帜,以“80后写作”为代表的青年文学取得骄人的市场效益等,都说明这种“政治无意识”一旦升华为文化政治,便势必会对社会现实的改良和完善起到重要的制约、平衡和协调作用。
四、一部后现代启示录
伊格尔顿对于鲍姆加通创建的经典美学进行解构与重构的工作不啻是一部寓意深远的后现代启示录,它预告着当今美学面临的重大突破和重要发展。伊格尔顿的理论锋芒挑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鲍姆加通创建的“美学”(aesthetica)乃是一个将错就错近三百年的概念。如果梳理一下伊格尔顿的理论逻辑的话,那么不难发现他往往是以鲍姆加通致力证明的命题为反命题:(1)美学不只是认识论;(2)美学不应贬低感性;(3)美学作为感性学不排斥感性生活。而同时则确立了若干正命题:(1)美学是一种肉体话语;(2)美学是一种政治无意识;(3)美学与社会实践挂钩。顺着这一逻辑向前推演,最终得出的结论便是:美学是一种文化政治。而这一逻辑推演,则是以破除经典美学的唯认识论、唯理主义和反身体论为前提的,后者则是当年大陆理性派作为立身之本来加以恪守的,而“美学”自诞生之日起便陷溺其中而长期不能自拔。伊格尔顿关于美学的上述一系列反命题与正命题恰恰昭示了当今美学在解构与重构的交互作用中发生的后现代转折,以历史主义的鲜明取向为当今的美学研究开了新生面。
在美学研究中,身体、肉体问题历来是加括号、被搁置的边缘问题,然而如今却成为具有重要担当、处于焦点位置的大关节目。伊格尔顿将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怀与文化政治结合起来,他选择“肉体”的角度,由此出发寻找解决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政治、伦理问题的途径,从而使得美学成为一种文化政治。可见,伊格尔顿将美学与文化政治结合起来既是对于当下现实的积极回应,又是对于美学内涵的深入开拓。
注释:
①关于鲍姆加通的中译名,目前国内有多种译法,如鲍姆嘉滕、鲍姆加登、鲍姆加通等,本文统一称鲍姆加通。
②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曾分析过蒙克该画作的政治意义,见其《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173—1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