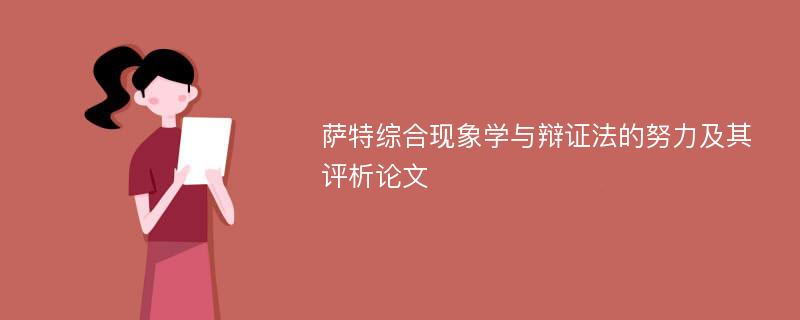
萨特综合现象学与辩证法的努力及其评析*
张立达
【摘 要】 现象学和辩证法融合的可能性及方式,是关系到哲学内在统一性的重大问题。萨特的基本经验是,自在和自为的非实体化、以包容了意识的实践作为“事情本身”、以活动和体验作为将外在的“多”转化为内在的“一”的方式。但是由于自我反思的不彻底以及急于追求理论的彻底性,他仍保留了二元论和过多的概念思辨,对现象学和辩证法以及它们的综合都造成了损害。
【关键词】 萨特;现象学;辩证法
作为哲学两大运动的辩证法和现象学,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早已毋庸赘言了。那么这两种富有意义的思潮、方法能否相融以及怎样相融,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哲学的内在统一性,进而关系到哲学的真理性和意义普适性问题。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两种方法直接呈现出来的是深刻的异质性:现象学要消融本质和现象的区分,辩证法却坚持这一区分;现象学主张无中介的直接性,以此作为明见性的保障,辩证法却要通过中介来展开矛盾,否则对立统一、自我否定无法摆脱逻辑意义上自相矛盾的窘境,无法获得实现的途径。如果这两种有重大意义和影响力的方法不能相融,自然是哲学的尴尬,哲学要摆脱这种尴尬,当然也付出了许多努力。本文就是以萨特为例,总结和反思他综合现象学与辩证法的努力及其经验教训。
一
在著名现象学家中,萨特可以说是最看重辩证法的一位,通过他的《存在与虚无》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两部书名的比较就可以看出其现象学的辩证法特色。在后者中,“时间”直接是“存在”的显现方式;而在前者中,“存在”和“虚无”直接构成对立,但虚无又内在于存在之中。因此,他对现象学和辩证法关系的处理值得我们关注。
对萨特前期来说,辩证法更多地是一种内在的学理支撑,公开的学术标签则是现象学,《存在与虚无》的副标题便是“现象学的存在论”。他的现象学出发点,是前反思的意识,当然也就是最原初的、未经任何中介的现象显现。与胡塞尔相比,萨特既不像胡氏那样重视反思的功能,也不像他那样认为意向性活动总是围绕着一个“自我”极,而是认为原初的意识根本就是无“我”的。因为胡塞尔关注的是认识论研究,为了达到结论的普遍必然性就不得不以反思为必经之途,而萨特的终极关切完全是个别性的行动及其意义,恰恰是意识的直接性才能为这种个别性提供存在论依据。同时,如果意识一开始就是以“自我”为主体的话,就意味着意识已经有了负载、有了内容,意识的纯粹性、开放性、透明性已经遭到了破坏。总之,这样一种绝对开放和透明的意识之光,就是萨特现象学的第一基石。
接下来才是内容在意识中的显现。“意识是对某物的意识,这意味着超越性是意识的构成结构;也就是说,意识生来就被一个不是自身的存在支撑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本体论证明。”(1)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21页。 因此意识必须显现自身所不是的东西,并以对对方的显现作为自身存在的方式。当然,离开意识的显现,对方也无从获得任何规定性。所以,这个对方便是除了存在一无所是的“自在存在”(being-in-itself),意识自身则显现为以轻盈的、能动的虚无化活动为规定性的“自为存在”(being-for-itself)。将自在和自为设为并立的两种本体,似乎是一种笛卡尔式的二元论,但是显然萨特的这两种存在都已经非实体化了,只能相互依存、一体化才能实际存在,自在和自为的相互否定转变成了它们各自的内在否定,进而成了现象之显现。从而萨特便以现象显现的一元论扬弃了二元论,这正是他的现象学与辩证法相统一的最集中表现。
不过,仅有非自我的意识还不足以显示自为相对于自在的优势,不能说明虚无化活动、显现活动究竟有什么意义,自为要进行有意义的创造,就必须现实化为人。那么这个跳跃是如何可能的呢?萨特认为,意识的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意向性,另一个就是自我意识。“所有对对象的位置性意识同时又是对自身的非位置性意识。”(2)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0页。 既然思必有所思,非位置性的自我意识又和对象意识互为前提,那么对“我”的确认也就是必然的了。由此,散漫的意识转化成了自觉的意义追求,非定向的虚无变成了积极的自由。同时,非位置性、非正题的意识依然是前反思的,也就是仍在顽强维护着现象的直接性、明见性。绝对虚无的自觉化是绝对自由,自由便意味着根据不在外部,完全就在当下的自身活动之中,随着活动的展开而显现。即是说,自由就等于明见性,我做故我是,我做故我可明见。既然意识是现象显现之本,虚无就是其根本规定性,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人之自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在预见中,但还是给今天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让我们见证了社会发展的流光溢彩——恢复高考、开放搞活、留学下海、创新创业……每一轮潮起潮落,都是很多人改变命运轨迹的历史机遇。
高考结束之后,爸妈决定让我放松一下,先是去北京旅游,后又到内蒙古草原,最后是大连。在大连广场,我光着脚,试了所有的脚印。晚上,住在海边一家宾馆。这天夜里,我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现付玉,她和咱们的校长王歪嘴在一起,她还挎着校长的胳膊。校长那个熊样,酒糟鼻子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只硕大无比的红色青蛙,他当着校长,却只会喝酒和千方百计扣老师的钱,老师们都背地里骂他。付玉和校长没看见我。他们住在405房间,这个婊子养的校长,竟然把付玉弄得哇哇叫。我真想闯进去宰了这个狗日的。
学生通过观察可知,在相同的时间内,在竖直方向上只做自由落体的小球和做平抛运动的小球运动的位移相同,即,平抛运动的物体在竖直方向做初速度为零的加速度为g的匀加速运动.做平抛运动的小球水平位移较理论值小,是因为小球运动中受到空气阻力.
其一,由于自为对自在的依赖,导致这两者的矛盾纠缠,其集中表现便是人的自欺。所谓自欺是这样一种态度,它“本质上是属于人的实在的,而同时又像意识一样不是把它的否定引向外部,而是把它转向自身”。(3)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83页。 萨特首先将它和说谎做了区别,说谎者完全了解他所掩盖的事情,而自欺不仅是指向自身的,而且有一种内在的真诚。就像一个咖啡馆侍者,他真诚地扮演着侍者的角色,因为他确实是一个侍者。但是,侍者何以成为侍者呢?“是侍者”恰恰要以“不是侍者”为前提、以自由为前提,一个生来注定只能是咖啡馆侍者的存在者只能进行对于侍者而言最必需的活动,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侍者”,这样的存在者不过是一台自动倒咖啡的机器而已。萨特提出,“是其所是”的墨水瓶不会自欺,“自欺的可能性的条件是:人的实在在它的最直接的存在中,在反思前的我思的内在结构中,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4)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08页。 其实他不太情愿承认的是,人要作为人而存在,就首先必须作为一个存在者,而存在者的本性就是“是其所是”,离开了最起码的确定性、稳定性,所谓的自由、超越、否定都将无所依附、无从发生。因此,人既要维系自身又要超出自身,自为既离不开自在又必须超脱自在,作为虚无和否定性的“我”和作为实在的“我”不得不是同一个“我”。只有自欺才能调和这一矛盾,它的目的就是“使我按‘不是我所是’的样式是我所是,或按‘是我所是’的样式不是我所是。”(5)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06页。 正因为两种样式只是暂时地、人为地调和了,并未真正同一,所以这种调和才是自欺。
其中COD、TN、TP作为主要污染物去除指标,其每年污染物减少量为:COD:438t/a;TN:291t/a;TP:18.3t/a;HN3-H:109.5t/a。
其二,萨特当然不承认自在会限制自由,但是由于自为存在的复数性,以他人为中介,自由显示了其内在限制和自我否定。他人,当然也是以自为的直接活动——意识到自身被注视、被对象化——来得到证明。同时,离开他者,自为就还只处于散漫的前反思状态,尚未对象化为自我;“我一下子意识到我,是由于我脱离了我……我只是作为纯粹对他人的反映才为我地存在的。”(7)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345页。 因此,自我和他人是相互生成的。这些都还体现着现象学的圆融性。然而,萨特极力强调注视这一行为的客体化效果,因为被注视,我的自由和超越性成了被超越的,成了别人的客体,这个别人却是我不能预料和支配的。“这样,我的每一个自由行为都使我介入一个新的中心,在这个中心,我的存在的质料本身是别人的一个不可预料的自由。然而,由于我的羞耻本身,我要求别人的这种自由成为我的自由。”(8)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347页。 但是即便可以在意识中完成这种被动/主动的转换,这种“我的自由”其实也不是行动的自由,只是生存体验的自由,这种自由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人在自由中丧失了对自由的理解和把握,从而遭遇和体验着异化。
市政工程本身就比较复杂,其施工和管理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影响因素,在众多影响因素的影响下也很容易出现施工和管理问题,这些问题很多都是可控的,也存在不可控的因素,要着力提高市政工程造价控制水平和管理水平就必须对这些影响因素和实际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可控的因素进行有效的控制,对不可控因素进行预防等。
人不可能消除自欺,也不可能消除人与人的交互主客体化和冲突对抗,这样的理论后果虽显得悲观,但至少从一方面看,这是萨特所需要的。因为,如果人已经本体性地具有了完满性,个体的自由行动就不是真正的“自由”行动了;正因为人之存在的不完满,所以属于个体的存在意义必须由当下的行动来创造。但从相反相成的另一方面来看,这同样也是萨特面对的尴尬窘境。因为,自由之成为自由,意义之成为意义,总是需要拥有可以把握实际内容的客观标准,如果光从形式上把“由自身(有意识地)发出”当作自由的绝对规定性,那么犹太人在奥斯维辛毒气室里片刻咒骂的自由和萨特在有暖气的咖啡馆里交谈和写作的自由还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自由和意义要富含内容,那么人在扬弃自欺方面,在化解冲突对抗方面究竟能有什么客观成果,以使这种内容显现出来呢?既然萨特承认了异化的存在,也就等于承认了这个工作的必要性。但是,他没有完成这个工作,根源在于他的整个理论都是建立在自在/自为的二元分裂之上的。基于这种本体性分裂,是其所是和不是其所是/是其所不是就不能真正统一起来,只有纠缠而没有过渡,也就无法对自欺做出更具体的意义评价,(9) 邓晓芒明确区分了自欺的负面和正面意义,就其正面意义而言,“把人从这种虚无主义中救拔出来的,仍然是自我意识的自欺结构。人类历史上,一切对人类精神生活有实质性贡献的人,都具有某种执着或片面性,即把他所追求的目标视为最终的绝对目标,这样他才能爆发出全部生命力来投身于这一理想的实现。……这种自欺的信仰为他提供了奋起的着力点。”而且,消极和积极的自欺不可严格区分,所以人的反思和忏悔是永无止境的,但只有在这个永恒过程中才能实现人性的真诚和人生意义的深刻。参见邓晓芒:《论“自我”的自欺本质》,《世界哲学》2009年第4期。这样,人的存在结构中就植入了发展、进步的维度,个体自由有了富含内容的评价标准,同时又以自否定、自批判的形式结构保证了该标准的哲学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可以说,这是他对萨特自欺理论的重要发展。 无法将“自欺”作为把握具体现实的概念工具。同样基于这种分裂,自为、自由因当下性、直接性而成了绝对个体性的单子,既然自在和是其所是从人的本质结构(10) 在此,我们不要被“存在先于本质”的字面意思误导,因为具有哲学意义的“存在”其实已经是本质了,萨特这句名言其实讲的是本质怎样显现,而不是相互外在的存在和本质的先后关系。 中排除掉了,那么单子间的沟通和统一就失去了桥梁和公共平台。
萨特现象学中的矛盾也在继续展开。一方面,意识之显现——人之自由选择维系着现象显现的纯粹性、可理解性。另一方面,这现象之流中又包含着两重深刻的分裂。
所以就像梅洛—庞蒂批评的那样,萨特的他人理论中只有交互主客体性,没有主体间性。而且我们还应该质问的是:萨特的他人理论完全符合现象学吗?意识到被注视固然有着明见性,但是“被注视—注视”难道就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基本关系吗?一切语言交流、共同活动或生活意义的共享都可以还原成这一原始关系吗?而且就算人们共享某种生活意义总要以对其它生活意义(相当于第三者)的排斥为条件,这种共享难道总会被感性个体之间的冲突轻易瓦解吗?这种向着个体二元对立的还原又有什么现象学的明见性呢?这不是正好暴露了萨特非现象学的理论预设吗?
二
萨特也意识到了,执着于某些抽象原则的绝对性、纯粹性,只是激发了对立却并未赢得统一,因为本体性存在已经是分裂的,那么统一就只能在具体的现象世界。也就是说,解决问题不能再只围绕着自为和自由做文章,必须把目光转向更具体的自在自为。自在自为最根本的存在形式,当然就是人的实践。所以萨特后期的思想转变,首先就是以社会实践部分取代了意识、自由选择的地位。实践作为自在和自为结合的具体形式,自然可以成为更富有实际内容的现象显现。其次,自在在《存在与虚无》中还只是消极支撑自为,任由自为随意表现的舞台,当自在自为被集中关注之后,自在对自为的内在否定,具体来说就是实践惰性,其辩证效应也就得到了集中考察。再次,中介问题被提升到了方法论的中心地位。因为异质、对立的因素的联系、统一必须通过中介,中介显现为中介的过程也就是事物在联系中具体地生成、运动和总体化的过程,也就是自由自觉的人投身于世界并通过自己实践活动的遭遇理解世界和自身的过程。为此,他不仅以“在总体化的视野中将所有因素中介化”作为基本研究思路,而且他提出的类似于解释学循环的前进—逆溯方法,本质上也是具体展开中介过程的一种方式。
具体来看,首先,自为和自在究竟怎样统一?实践是如何可能的?萨特所找到的统一的基础、可能性的根据,便是人的匮乏。匮乏和自为一样,都是“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都是一种内在否定性。但同时匮乏并不像自为那样具有独立自足的能动性,人需要征用自在,征用外部力量来缓解匮乏、实现自身,因此匮乏本身意味着自为对自在的依赖。消除匮乏并不等于自由,因为这是人的肉体存在所预定的内在要求,但是由此成为某种特定的“所是”,人的存在才不再像绝对自由那样轻灵飘忽、无从把捉。同时,消除匮乏的活动又毕竟切实地容纳了自由。正因为匮乏构成了自为和自在内在相互否定性的统一,所以它才成了人类历史创造的原动力,成了“人类历史可能性的基础”。(11)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64页。 同时,因为否定性和虚无性本身是同一的,否定力量依赖于所否定的东西来使自身实在化,所以匮乏也构成了萨特的历史辩证法、人学辩证法的基础。人征用物,但自身是虚无,所以自身也被物所控制;人以物为中介利用他人,同时也被他人所利用。而且这两方面正是同一过程,即,人就是在自主行动的同时自我异化。微观层面的人的异化,在宏观层面来看则是实践—惰性的生成。一方面,实践—惰性正是人的力量的实在化,“有机体若不暂时回到惰性层次,就不能作用于环境”(12)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19页。 ,同时,惰性又意味着对人的外部否定力量在人自身实践中的内在化,人们自由的实现只能是在崎岖小路上艰难行进。
其次,人怎样突破个体性的单子状态,走向社会性、现实性?萨特依靠的是三元的相互性关系,“二元的统一只有在一个第三者从外部执行的整体化内部才可能实现”。(13)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54页。 虽然《存在与虚无》已经提出了“第三者”,但是就像Flynn所指出的,此时的第三者不过是一个相距更远的他者,此举不过是让二元关系分出了层次结构,并没有让“二”走向“三”,内在于“二”的冲突性也就并没有得到解决。(14) Flynn,Sartre and Marxist Existent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93.《辩证理性批判》的处理方式,是让自我、他者、第三者的关系相对化、灵活化,“每个人对于其他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也是一个第三者”。(15)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37页。 不仅有第三者超越我和他者的对立,同样我也作为第三者超越别人之间的对立,由此,不再有哪组对立拥有绝对必然性,对立和统一在实践中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交织。这样的实践必定是多元复合性的,正因为联系中充满着异质和冲突,所以萨特才必须区分整体性和整体化,并将永不会完成的整体化看作人类现实的存在方式。
自欺理论可以说是整部《存在与虚无》辩证法色彩最浓的部分,不必多说,而其现象学方面的集中表现,就是自欺与真诚的同一化(显然这也是内在于辩证法的)。他人的谎言既是非真诚的又是非明见的,真诚便意味着意识现象的透明性。自欺必须是真诚的,因为人不得不自欺,用萨特的话说就是“因为真诚意识到它根本上是没有目的的”,(6)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07页。 即不存在特殊性、偶然性的谋划。更深一层,“不是”本身也是一种“是”,“是”也必须通过“不是”才能从混沌中现身,所以“是”和“不是”既对立,又有直接的同一性。因此,这里的辩证关系是以现象学方式显现的。
其二,现象学要避免小圈子内部的逻辑游戏,要有更强、更广泛的解释力,现象就要具有尽可能大的综合性,“事情本身”也就要从意识转向实践。意识固然可以显现自身之外的内容,但局限于意识,这些内容就不过是意识活动所把握到的偶然的东西,无法上升到普遍形式层面进行真正哲学的把握,这种意识哲学就依然显得空洞、抽象。具体来说,意识中只是自为单向否定自在,自为以及人也就因为缺乏规定而抽象化了,除了显现自身或他者的主观性、个体性、自由之外并没有更多建树。既不脱离作为明见性之基的意识,又比意识更具有综合性、包容性的是实践。实践才是自在和自为的双向否定,双方也就都可以得到具体规定,并且在直接一体性的实践活动、实践过程中显现出来。正因为如此,萨特后期才会把实践当作自己的中心课题。实践综合、统一和超越各种异质性、冲突,无疑呈现着鲜明的辩证法意蕴。
传统的直销手段存在交换效率低,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小,金字塔式拉人头,层层加价导致价格虚高,营销资源浪费严重的问题。
三
萨特在整合现象学与辩证法方面取得的基本经验,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总结。
1.3 指标判定 用MMSE量表评估患者术后认知功能,包含语言能力、回忆力、计算力、注意力、记忆力、定向力等方面,正常:27-30分,轻度障碍:21-26分,中度障碍:10-20分,重度障碍:<10分。记录其麻醉前、手术开始时、术中0.5h、手术完成时,患者平均动脉压、心率,以及术后睁眼时间、拔管时间,并比较。
再次,人究竟怎样寻找突破生存困境的出路?换言之,人之存在怎样进入历史?历史意味着一种不可逆性,不再只是诸如自由/异化或能动/受动的无限纠缠和循环。这种不可逆性,就来自于群体的共同实践对集合体的消极性,对实践—惰性的努力超越。群体的形成,当然首先需要敌对性的外在压力,这种思想在《存在与虚无》谈“我们”的时候已经表达过了,但是强有力的群体并没有因此在逻辑上形成。因此更重要的是,群体自身要有超越个体冲突的中介手段,形成自我维系和强化的内在力量。从外在压力到誓言再到制度,这就是群体的内在中介的演变,也是萨特在自己人学中展开的(准)历史维度。
其三,不掌握异质性、中介性就不能突破意识的抽象形式框架,而活动和体验就是将外在的“多”转化为内在的“一”的方式和过程,是非明见性向明见性转化的方式和过程。外在的异质性、不透明性只能通过我的活动和理解对我起作用,也就被我的活动和理解内化了,因此,多和一、间接性和直接性是以辩证的方式相互依存的,矛盾也可成为现象实情。
其一,打通对立统一和直接一体的关键,即让异质的它们以现象学的方式统一的关键,是所考察项的非实体化、虚无化。如果本体已经是自足的、完满的实体,那么抽象演绎就是了,直面现象就成了多余。正因为单独的自在和自为都是没有内容的,都不过是一种欠缺,是对对方的依赖,所以概念上的对立才能转化为现象的一体。二元本体直接依存,且通过自为的具体活动来显现,既是想保证显现方式的直接性,又是要保证显现内容的现实性、丰富性。
通过上述三条原则,萨特是否成功实现了现象学和辩证法的统一呢?这仍然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研究的。在现象学家中,萨特最特别地突出了理论上的二元张力(20) 对于萨特这种非一元存在论,汪帮琼的解释是:“现象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统一整体,而本体论存在必须是多元的。否则,现象的生动丰富最终只能归于虚幻或变成神秘的不可理解的东西,现象的总体性和统一性只能是一种毫无生气的外在强制。……所以,萨特本体论所达到的彻底明晰性并不是一元的本体论存在,而是多元的本体论存在及其内在的矛盾冲突。”参见汪帮琼:《萨特本体论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9页。笔者认为此说有一定见地,但是其中可商榷之处,其一,萨特的本体论(存在论)并不是简单的多元论,而是要在“一”和“多”之间保持辩证的张力。其二,如果说萨特反对一元论只是为了不损害现象世界的丰富性似乎理由不充分,实际上萨特并不把这当做根本目的,我们在读他关于绝对自由、人与人之冲突等论述时,感受到的并不是现象的丰富性,而是逻辑演绎力量的强大。与其说萨特是为了维护现象的丰富性,不如说是萨特在充斥着个体冲突的社会背景(尤其是二战这种战争背景)下,特意选择了以通过冲突,战胜异己力量来显示生存意义的方式。 ,这实际上是现象学对辩证法的让步,以及对概念思辨的让步。那么,为什么非要在二元论和一元论之间玩辩证游戏?为何不直接将源始的存在揭示为“一”呢?这是因为,绝对彻底的“一”只能是混沌的、死寂的、不可意识也不可言说的,“二”才是可理解性的基础,因为理解首先必须是区分。即便对胡塞尔来说,也要区分出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即使把先验自我当作独一的现象之源,若没有被先验自我建构的内容,先验自我也将毫无意义。海德格尔同样也不能摆脱“二”,例如存在和存在者、本真和非本真等区分。实在的差异性、对立融入关系的一体性才会有现象的、意义的显现,这就是现象学对辩证法的内在依赖。
那么,这套人学辩证法又是怎样体现现象学意蕴的呢?萨特很清楚,在包容了如此复杂、异质的内容之后,那种单纯、直接的明见性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他退而求其次,寻求的是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可理解性。《存在与虚无》已经把自为、自由当作了明见性的充分必要条件,由此出发,社会关系、历史运动之所以是可理解的,根本上就是因为这说到底是每一个体自由地活动的产物。“实践的辩证法的唯一实在,万物之动力,就是个体的行动。”(16)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80页。 人理解自己的活动也就是理解社会历史,因为“理解就是生存本身……是我的真实生活,也就是把我旁边的人、我自己以及周围的环境聚集到正在进行的使对象综合统一的整体化运动。”(17)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37、124页。 就算实践—惰性否定了我的自由,“能够通过一种已定型物质来限制我的实践的效率和自由的,只是以物质环境为基础的他人的自由实践。……正是自由限制了自由。”(18)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78、479页。 就是说,不透明的客观性是可以回溯到可理解的自由行动的。再具体到理解他人,则是通过实践的交互性实现的。斗争依然被看作是社会交往的原型。“我根据自己对敌人来说是对象这一点,我理解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经验的各个辩证契机都是一个过渡到另一个之中的:我根据我所知道的敌人之客观结构,通过代价昂贵的差错,通过逐步改正,就能预见到敌人眼里的我的客观性,我根据敌人先前对我的行为而预见到敌人的状况。”(19)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003页。 萨特用下棋的例子说明,每一步棋都是对整个棋局的新的整体化,也就是通过整体的联系和运动来实现着同时既对自身又对整体的理解。当然,他承认了差错的存在,也就是承认了理解只能是历史性的自我扬弃的过程。
当然,较之胡塞尔等人,萨特的二元关系更加外在,每一元在概念上更加独立,在现象上则突出表现为冲突性的结合。这又是为何呢?除了笛卡尔式二元论传统的影响之外,还可以从萨特与海德格尔的比较来理解。海氏从先于意识与物分化的“一”,即此在的生存来揭示存在,但问题是,在这种不离于“一”的现象学描述下,此在的命运却是海氏自己不愿接受的“沉沦”,因为理想的提出和实现必然是对同一性的突破。为了摆脱沉沦,就只有靠死亡的追逼这种特殊的生存情态,而且这并不一定奏效,充其量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由此可以看到萨特对海德格尔不满的主要理由。萨特渴望着人能够更加积极有为,渴望着将积极有为作为使人成为人的必然性揭示出来,当然就不能让有为依赖于“直面死亡”这种特殊情态,而必须把不受阻碍的自为提升至本体高度。但是因为自为已经纯粹得没有了内容,所以与之对峙的自在也必须获得本体性的地位。这样,一定意义上的二元论对于萨特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二元本体,本体性地突出了人之存在的矛盾冲突,昭示人们世上没有逃避纷扰的桃花源,只有勇敢面对矛盾冲突,勇敢迎接各种挑战,人之生存的意义之花才能绚丽绽放!当然,因为二元本体的抽象性和缺乏过渡,萨特也就无法揭示异化如何为自由创造条件,无法指出扬弃异化的具体道路。他回避这一难题而过于迷恋行动和自由的直接同一,也就显得过于苍白空洞,无力指导实践,这正是萨特最遭诟病的地方之一。我们不否认这是一个重要局限,但是如果对他抱有理解之同情的话,可以为之作部分地辩护:指导实践并不是哲学的任务,而且再具体的理论也不可能完全指导实践,反而依赖于存在主义对生存意义的终极澄明;正因为存在主义只提供终极根据,把“具体怎样做”的问题不是交给理论而是交给实践行动,因此它才更旗帜鲜明地自我确证为了一种行动哲学。
总之,萨特哲学的辩证法意蕴突出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突出存在的矛盾张力,二是理论的自我扬弃,即理论宣称行动高于理论。当然,萨特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即为了突出这些效果,结果使自身许多思想显得过于绝对化和抽象。其实,辩证法只要彻底,只要敢于指向自身,它本身并不会导致这些缺点,根本原因还是萨特自己的哲学思辨惯习(habitus)。(21) 惯习,是借自社会学家布迪厄的重要概念。它是指“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是一种实践策略的生成系统,既来自于社会场域,又内在于行动者个体。参见[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只要把哲学研究也看作一种实践,那么哲学旨趣和研究方式就可以看作一种惯习。布迪厄认为,人对自己的惯习既不是无意识的,也未达到理性的自觉意识,而是为了应对实践的复杂性、权宜性而必然具有模糊性。萨特的概念思辨明显体现着追求理论彻底性的自觉意图,但是熟悉现象学的他却没有对思辨的危险加以警惕,似乎又是不自觉的。这种认识上的模糊性也正好体现了惯习的特征。 既然哲学的历史传统就是思辨,就是追求绝对性、普遍性,这种传统也就容易积淀在萨特的哲学研究方式中。一旦单纯化、绝对化的理论不能把握复杂的现实,他就立刻求助于辩证法。例如,当他发现绝对自由有抽空人的现实性的危险时,就立刻引入“处境”概念,以此将反自由包容到自由内部,由此来辩证地化解难题。但是反自由的因素真能如此消解掉吗?显然他是用体验和理解的自由偷换了实践的自由,而后者其实并不能被前者替代,所以这无疑是一种论证的作弊。总之,萨特以带有过多思辨的方式对待辩证法,导致抽象化的辩证法对现象学造成了某种外在的限制,我们也就可以提出这样的反思:萨特哲学中的辩证法是否太过于勤快,演绎过多,以至于抢了一些本该现象学干的活?而现象学的弱化又会加剧辩证法的思辨化、抽象化,这不正是一个恶性循环吗?
具体来看,现象学的弱化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更加明显。随着现象学的视域从意识转换到实践,现象实情在变得复杂化的同时,现象学直观的意义也大大弱化了,乃至于只能在解释学层面探讨理解的可能性了。这本来是视域转变的必然后果,并非现象学的失败,但问题是,萨特真的成功揭示了社会实践的可理解性吗?若要完成这一任务,他就应该探究自我和他人、实践境域的同一性,探究自我是怎样在实践情境中进行意义理解,这种理解的形式和内容又是怎样建立起自我与他者的统一的。也就是说,研究可理解性,应当关注实践和理解的情境、方式及成果,而不能仅仅盯住实践和理解的主体本身,因为主体、行动者是实体化的、离散的,主体的存在方式才可能成为同一化的因素。可是,大概是为了接续《存在与虚无》的理论旨趣,萨特最关注的恰恰是行动者,由此造成了一些具体的理论困难。
第一,他以“自己的自由行动是直接可理解的”和“个体自由行动是社会实践之源”来论证社会实践的可理解性,直接便会遭遇的难题就是:就算只是“自由限制了自由”,他人的自由为什么对我也是可理解的?能够超越实践处境和个体经历而具有绝对透明性的自由一般,究竟是现象学的自由,还是概念思辨构造的自由?
第二,忽视人之生存在本体层面的被动性,完全从个体行动者的能动性出发来解释群体的形成也是很可疑的。群体之成为群体,必须要有不能还原为个体的成分,这就是集体意向性和生存意义的共享。当然萨特也谈到了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行动目标,但这最终还是以个体行动、直接地以“作为第三者的每个人的中介”为前提的他指出:“他作为第三者的原始结构,表现了在他自己的活动领域内部统一任何一种多元复合性的实际能力,也就是用向其目的的超越来对任何多元复合性进行整体化的能力。”(22)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31页。 萨特企图以这种整体化来论证群体的生成,可是,每个人的中介本身是多元的、离散的,那么,以个体为中心的体验、理解层次上的整体化,如何跨越到超个体的实践行动的整体化?即便阅读他的文本,我们依然打消不了困惑。
第三,他以实践的交互对象性论证社会实践以及他者的可理解性,这在原则上是可行的,然而,实践中的交互对象性最多只是一种半透明性,他却忘了反思人的理解能力的有限性及其社会历史效应。也许萨特觉得,既然只是探讨理解的可能性,那么实际能达到多大的可能性在理论上并不重要。但是,理解的困难绝不只是所花时间的延长这么简单,对他人的意图和行为,对所处实践境域的态势和趋向缺乏理解,会实在地影响人的生存,由此造成的挫败也会深刻影响人们后续的理解方式。假如忽略这些影响,就不能算现象学地把握了人的存在。
第四,社会实践如果是可理解的,那么无论对实践的理论把握在一般形式上多么抽象,它都要能够展开通达具体性的道路,因为只有在具体和抽象的解释学循环中才有所谓的理解。看上去,《辩证理性批判》对人的研究比《存在与虚无》具体了,但是它又在一个相对具体的层面封闭起来,重新陷入了抽象。具体来说,萨特虽然知道了以中介展开具体性的基本方法,但是在他的理论中的中介类型不过是群体、家庭等寥寥几种,地理环境、人口、生产力、具体制度类型、具体意识形态类型等等其它中介未能认真展开,(23) 笔者此处可能会遇到的一个质疑是:将生产力同其它因素简单并列,是不是模糊了生产力的基础决定性地位?笔者的回答是,先入为主地设定生产力的这种绝对地位是违背“回到事情本身”的,也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生产力的力量和作用只能在实践情境中生成,只有在和其它因素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显现为塑造历史的一个特殊的基础性枢纽环节(而不是原发的第一因、第一推动力,否则生产力就会取得类似于上帝、绝对精神的地位,历史唯物主义就会变成唯心主义)。之所以生产力具有这种基础地位,乃是因为它承载的是人类最紧迫的生存需要和最实在、最硬性的实践手段,保证了这两方面才可能解决其它各种生存问题。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基础地位只能在实践—生存活动的现象实情中显现出来。 理论也就依然显得抽象。为了兼顾个体和整体的发展,兼顾对立和统一,少数解释项要承担过重的解释任务,也就不得不以思辨的方式求助于辩证法。在他的思辨中,自我、他者、第三者、惰性、异化、自由,确实深刻地辩证统一了,但是这种辩证关系却在概念层面、社会历史哲学层面就完成了循环,阻碍了思维向具体性的深入。因为,这种辩证法没有指向自身,没有自我批判,没有给作为自身对立面的形式逻辑留出太大余地,我们也就难以把握辩证运动中的相对静止。这样,也就难以有确定的因果关系能够超脱辩证循环,进入到不可逆的历史过程。正因为如此,萨特所讲的实践群体的演变,实际上只是彰显了时间性维度,并未真正进入历史性维度。因为制度性群体及其执行机构在文明社会之初就已存在,合并中的群体至今仍广泛存在,而且未必以制度化作为必然趋势。像马克思那样揭示实在的历史运动趋向及其内在机制,萨特的理论是难以完成的。
或许,萨特的历史人学研究中受到的最大的客观限制来自自己的知识结构。他是哲学家、文学家,却不是马克思那样的社会科学家。知识结构的限制使他没有能力展开更多更具体的中介、对社会历史进行更具体的研究,也就不得不过多依赖概念思辨。而经验科学恰恰是对概念思辨去蔽的有力手段(当然,去蔽应该是双向的)。再从主观方面说,他自我反思和批判的态度还是依然不足,但又急于实现理论的彻底性,才使得对抽象思辨的危险丧失了警惕。那么他和我们面对的共同的根本问题就是:对人的整体把握既要立足于直面现实的具体经验,又要防止哲学自身被解构为实证知识的碎片,这也就是要寻求直接内在于内容的“多”之中的形式的“一”,寻求“多”和“一”直接同一化的渠道。显然,这也正是现象学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确切地说,是怎样以现象学的形式把握辩证的内容的问题。萨特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可是对待它的方式却是抽象的,结果既偏离现象学又未彻底贯彻辩证法。自然,他所留下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健康旅游的实质是基于资源整合之上的服务内涵拓展。随着“康旅联盟”等众多旅行联合体的成立,健康旅游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面临着大整合的趋势,传统的条块分隔局面正在改变,关联业态的跨界组合成为常态。各个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也是无一例外地将自然旅游风光和医药、保健等资源整合作为着力点。从总体上看,我国健康旅游的资源整合还很不足,零散状态依然严重,发展藩篱急需打破。只有加快资源整合步伐,提高综合利用效率,才能带来更多增值内容,形成多重溢出效应。
On Sartre ’s Efforts to Integrate Phenomenology and Dialectics
ZHANG Lid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 The possibility and way of integration of phenomenology and dialectics,is a significant problem that concerns to the unity of philosophy. Non-substantialization of being -in -itself andbeing -for -itself ,taking praxis which contains consciousness as things themselves ,taking activity and experience as the way to turnexternal Many into internal One ,are his three basic strategies. However,because of his halfway reflection and haste theory thoroughness,he retained dualism and spekulation,which injured phenomenology,dialectics,and their integration.
Keywords :Sartre,Phenomenology,Dialectics
*本文系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及其重构研究”(14XJC72000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B565.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723(2019)02-0089-10
【作者简介】 张立达,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永芝]
标签:萨特论文; 现象学论文; 辩证法论文;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