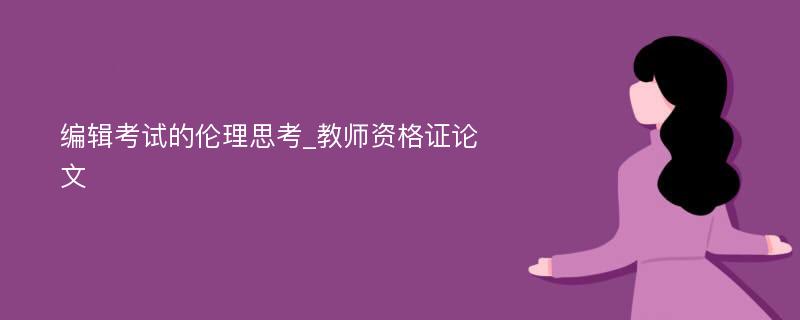
对“考编”的伦理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编”是指希望从教的大中专毕业生参加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教师招聘考试,以获得事业单位编制并在公立中小学任教。它是当前我国补充中小学教师的主要形式。相比以前国家对师范毕业生“包分配”的旧教师准入制度,现在以选拔性为特质的“考编”无疑提高了教师准入门槛,拓宽了教师来源渠道,为中小学教育事业输入了不少优秀人才。然而,改革的进程是艰难的,在新旧制度交替中暴露出的种种伦理危机,极大地影响了改革的力度和效度。因此,从伦理维度深刻反思当前教师招聘制度存在的问题,是当前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人类社会生活的和谐与幸福有赖于公正的规则及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统一而有效的贯彻执行。[1]我们对“考编”的伦理反思也就着眼于其合理性和公正问题。
一、“考编”的形式合理吗
2006年颁布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第二条明确要求“事业单位新进人员除国家政策性安置、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由上级任命及涉密岗位等确需使用其他方法选拔任用人员外,都要实行公开招聘”,从而把“考编”作为事业单位进人的主渠道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选聘新教师采用“考编”的形式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考编”必然能够选聘到合格的教师,即“考编”制度的实施与所选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这个形式是否合理?假设是否成立?如果我们从伦理的角度进行考量,这一制度本身就有不完善的地方。
那种认为“考编”制度的实施与所选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观点,来自于对科学主义范式下“技术理性”的推崇。在技术理性支配下的“考编”中,人的主体性因被遮蔽而缺失。
从根本上说,“考编”就是用一套制度为尺度去“量人裁人”。在“考编”的过程中只见制度不见人——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校长无权选择自己满意的员工;家长和学生原本是“考编”的直接“受益者”,但在“考编”过程中根本没有发言权。众所周知,教育是一种用人来影响人的活动,是一个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从未成熟的人成为成熟的人的事业。诚如学者雅斯贝尔斯所言,教育就像一棵树撼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起另一个灵魂。[2]教育是柔性的,需要情感上的投入,因此,教师的工作不可能用清晰的、刚性的、客观中立的制度、标准和指标来规约。由于现行“考编”制度只见制度不见人,那么,这样一种刚性的“考编”制度能够选择到柔性的教师吗?
同时,随着教师社会地位和职业待遇的不断提高以及师范类毕业生政府统一分配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受到了更多人的青睐,在某些地区出现了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竞聘一个教学岗位的情况。教师的门槛也相应地水涨船高,博士、硕士做中小学教师的比比皆是。但高学历未必就是高素质,高学历教师未必适合中小学教育。而且冲着待遇而去的应聘者不一定能够安心从教。
所以,当前“考编”制度的形式面临着伦理困境,存在着假设合理性不足及不够尊重教师、家长和学生权利等问题。
二、“考编”的内容公正吗
任何制度都必须体现正义、公正等伦理道德,这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对一项制度的伦理考察不仅要看其形式上是否合理,还要思考其内容上是否公正。虽然我国至今尚没有专门的中小学教师招聘法规,但是依据相关规定,各地的招聘程序是相似的,即基本上是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政审、录用。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资格审查,这实际上就规定了“考编”的门槛,决定哪些人有资格去做教师。如果这一关都过不了,则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考编”的资格审查,反思这些报名条件公正与否。
南京市2011年六城区新聘中小学教师报名条件是,报名人必须是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合格毕业生,符合学科需求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南京生源2011年师范类本科毕业生。南京生源2011年学前教育师范类大专生。南京生源2010年师范类本科毕业生,已取得教师资格,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人员。非南京生源2011年师范类本科毕业生(应是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大学、徐州师范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南京晓庄学院或国家“211工程”院校学生)。拟取得教师资格的2011年非师范类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一律为国家“211工程”院校毕业生)。拟取得教师资格的2011年硕士毕业生(1981年1月1日以后出生)。[3]
从上面的报名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市在招聘中小学教师时的三大限制,这些限制正是“考编”内容的不公正的具体表现。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首先是学历、学科限制。对中小学教师学历要求的提高是全球的趋势,但是目前尚没有研究数据证明全日制毕业生比非全日制毕业生更加适应中小学教育工作。而且,现在的教师队伍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通过在职学习的方式获得本科和研究生学历,他们的教学效果是有目共睹的。还有一些地区在招聘研究生学历教师时要求其第一学历是全日制本科,并且本科、硕士所学专业都要与任教学科一致。这样的要求不仅将许多乐于学习不断提高的青年拒之门外,而且也不符合基础教育的教育规律。基础教育的核心是要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教师具有广博的知识。而教育背景丰富的教师恰恰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其次是年龄限制。该市要求本科生是近两年毕业,硕士研究生年龄是28周岁以下,限制较严格。这样的限制其实毫无道理。
再次是生源地限制。生源地限制也就是户籍限制,说到底,就是地方保护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瓶颈的户籍政策一直为人们所诟病。从教育的角度来说,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不仅在就学方面已经成为义务教育中的最大难题,他们在就业的时候也遭受了明显的歧视。当然,随着国家对流动儿童就学问题的关心,相关的照顾性就学政策也相继出台,但是在就业时这种歧视性的生源地限制却未见松动。如果就业时的限制不去除,入学时的照顾也就失去了价值。
三、构建“善”的“考编”制度
一般来说,制度的“善”有两个基本方面:形式的“善”或技术的“善”,内容的“善”或实质的“善”。形式的“善”考量制度的技术方面,是看其是否自洽、严密、有效;内容的“善”考量制度的实质方面,考量制度所内在具有的社会成员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看其是否有时代精神。[4]从内容与形式的角度去构建“善”的“考编”制度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完善教师资格证制度,保证“门槛”的公正
表面上看,确定“考编”的门槛是规定哪些人有参加的资格,实际上是求职人员之间权利与义务的考量。在面对一个职位时,每一个求职者的机会应该是均等的,这也是社会公正的表现之一。但是给每个人相同的机会并不代表给他们相同的结果,因为结果永远只属于有准备的人。现行的“考编”政策虽然有诸多门槛,但是却缺少一条最重要的限制——教师资格证。笔者认为,“考编”的机会应该向所有拥有教师资格证的人开放,因为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也就具备了做教师的资格,即“备选教师”。而当前许多单位往往要求先考取编制,然后在工作后的规定时间里获得教师资格证。这是明显的无证上岗。
但是,现在每年取得教师资格证的人数往往是实际需要的数倍甚至十几倍,这是因为大量并不从事教育工作的“考证族”的存在。很多大中专毕业生认为教师资格证书与英语四级、六级证书以及计算机等级证书一样,只是为自己就业时多一个砝码。他们往往把教师资格证看作是自己职业生涯的备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教师资格认证形式过于简单,申请者只要通过了教育学、心理学理论考试,经过试讲或说课等教育教学能力测试,提供普通话证书、思想品德鉴定表、毕业证书等材料,在较短的时间里就能获得教师资格证书。有学者认为“实行全国统一教师资格考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实行国家统一教师资格考试制度要求所有申请进入教师职业的公民,在学历达标的前提下,必须参加全国教师资格统一考试,资格标准由国家制定并颁布实施,考试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国家要求统一组织,并且参加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面试。当考试合格、面试过关之后,再经过一年的试用期,确系具备当教师的基本条件与素质,方可申请教师资格证书。[5]这样,剔除了一部分“考证族”后,在“考编”的门槛前剩下的就是那些立志从教或已经从教者的公平竞争者,“考编”的选贤任能价值也就真正地凸显出来。
2.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试用制度,延长“考编”过程
教师的专业发展不仅体现教师在职前教育阶段对学科知识、教育理论知识以及教育教学技能的掌握上,而且更体现在他们真正走进职业生活后对教育教学工作的适应、感悟、体验以及教育智慧的积累上。因此,笔者建议将“考编”的过程延长,建立专门的评价委员会对试用教师进行评判以决定最终录用与否。
首先对应聘者进行专门的笔试,内容包括教育基本理论与专业知识,特别要关注应聘者知识的广度。然后进入一至两年的试用期。这种试用期不应该是形式主义的,对于那些通过试用后被确认为不合格的教师坚决实行淘汰制度。而我国目前的“考编”制度虽然也有一年试用期的规定,但这种试用期基本是一种固定程序,而没有实行严格的筛选制。为此应该实行“差额试用制”,即在笔试后多选几名应聘者进入试用期,最终录用人员按末位淘汰的原则择优选择。这就要求参加筛选的专门评价委员会具有公信力,可以兼顾各方诉求。因此,这一评价委员会的组成成员至少要包括校长、教师代表、政府代表、家长或社区代表和学生代表。
总之,“考编”制度的生成、实施乃至改革,都必须获得伦理道德的价值支持,必须合乎公正合理的伦理精神。构建更为符合公正、合理的中小学教师聘任制度,才能保证对教师综合素养等各方面能力的要求,同时能够将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选拔到教师队伍中来。
标签:教师资格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