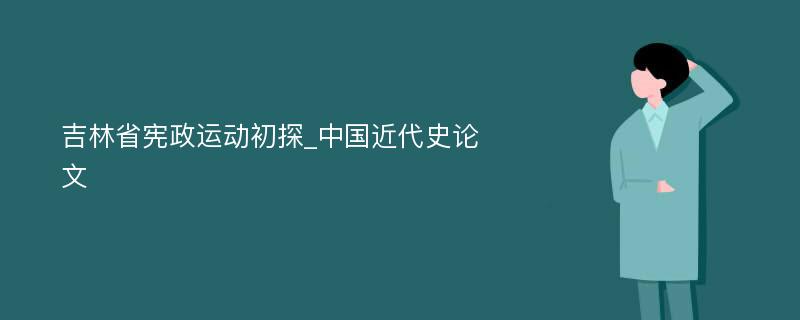
吉林立宪运动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立宪论文,吉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3)05-0109-03
立宪运动是辛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一支重要前奏。但立宪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的情况是很不平衡的,对于各地立宪运动的研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以往人们大都偏重于内地尤其是江浙等民族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省区,对于地处东北边陲的吉林则少有问津。而事实上,吉林的广大人民、民族资产阶级,以及爱国进步士绅,也以各种形式,进行了争取民主政治、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为这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本文拟就立宪运动在吉林开展的情况、特点等问题做一点粗浅的探索。
1906年9月,清廷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次年1月,吉林士绅松毓就组织成立了“吉林地方自治会”,以“预备立宪、养成公民”(1)(106页)为宗旨,希图以地方自治为基础,渐进至立宪政治。同时,主动接受政府督抚的监。督,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一些研究、宣传活动。
由于吉林地处东北中部,受到日、俄两个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当时已是“主权半丧、利权多失”,“虎口狼涎、奄奄一息”,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所以,“吉林地方自治会”一成立,立即参与、领导了保卫利权的反侵略斗争。1907年6月,日本侵略者怂使朝鲜农民越境垦荒,挑起了中朝边界争端,即所谓“间岛问题”。自治会员文元等得悉后,立即多方调查,又参考史志,汇成《中韩国界历史志》一文,证明间岛确系中国领土。然后呈给省府官员,希望“据此力争,以期保存国土,而慰黎庶殷望”[1](126页)。同年11月,自治会断然拒绝了日本领事岛川的“捐助”,使自治会保持了独立自主,而免受外人操纵控制。
1908年夏,为了收回被日本攫取的吉长路权,爱国绅商和青年学生成立了“吉林公民保路会”。自治会立即与其建立了联系,并代其向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吉林巡抚陈昭常上书,要求筹款自筑。上书痛切指出:“路之所至,即兵威权力之所至。此中得失,重关主权。……吉长二百四十里,扼满洲之中心,为交通之要点。倘此路遂为日有,则主权尽失,民命随之。”要求他们代奏皇上,“谅察舆情,抗废前约,以回天之大力,挽必要之路权”[1](78页)。同时领导各界爱国群众,掀起了保路风潮。他们集股筹款,“慨愤争先,甚有闺阁之中,典簪脱珥;童幼之子,倒箧倾囊”[1](79页),在短短几个月里,就筹集筑路股本210多万两。此外,他们还派出代表,向地方当局以至清廷政府进行请愿斗争,愤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痛陈丧失路权之祸害,表达了吉林人民“故宁为死,争做中国之鬼魂,亦不愿苟活,供外人之奴隶”[1](86页)的强烈爱国决心。
1907年10月,自治会发布第二次简章,提出一些具有民主色彩的政治要求。要“对于地方所办各事,得准上书质问及条陈之”;可以“受人民关于地方利弊之条陈,酌量议行”;“凡人民困苦不能上达地方官者,本会议事处应得酌议代陈”[1](119页)等等。随后又派代表到北京、奉天参加国会请愿活动。由于自治会脱离了“章程必定自政府,筹办必出自官家”的窠臼,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恐慌,终于在1908年11月,被当局以“与政府宗旨显相违背,……既非遵照部章,又未经奏准有案”[1](133页)为由,将其并入谘议局筹办处,名为“收小规模”,实则予以取缔。会长松毓也被强加以“把持学务,破坏政权”的罪名,开缺回籍。
“吉林地方自治会”被取缔,使吉林省的立宪运动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但形势的发展,已不是封建统治者所能完全左右。从1909年3月起,各省陆续开始选举谘议局议员,吉林省也选出议员30人。由于吉林地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较弱,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较小,所以谘议局中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比例不是很大,一部分带有很大封建性的士绅挤了进来,这与其他各省谘议局议员“大多都是立宪派或与立宪派有联系的人”[2]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吉林谘议局的出现,仍被看作是伸张民权的起点,成为吉林立宪运动的领导机关。当年6月,谘议局正式成立前,就以“议案预备会”的名义,发布公告,强调“一省之舆论,莫不待谘议局为主持,一省之民权,莫不待谘议局而伸张”;认为“我中国之所以垂败,岌岌不足自保者,莫不曰专制政体。而改造此专制政体,莫不曰开国会,建立宪政”,而谘议局就是“宪政之始基,国会之萌芽也”[1](153页)。以救国重任,自负于肩,并号召吉省父老兄弟给予支持,以尽乡人桑梓之谊。
1910年1月至10月,各省立宪派连续发动了三次全国性的请愿速开国会高潮。东三省代表表现甚为积极,甚而咬破手指,以血书上陈,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忱。与此同时,吉林省谘议局以及绅商各界爱国人士在省内也开展了上书请愿活动。1910年10月,正当中央资政院开会期间,吉林省谘议局以“代表全体人民”名义,泣血上书给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吉林巡抚陈昭常,并要求代奏皇上,请即行降旨,成立国会。上书痛切写道:“关外三省,壤接日俄,吉林适介其中。近自协约发生后,外人兼营并进,一日千里,……宗国之危亡,即在旦夕。……窃以为舍速开国会外,不止别无补救之方,尤恐人心一去,大势瓦解,三省危殆,全局随之。……吁请即开国会,以期号召人心,挽回大局。”[1](102页)但狡猾的陈昭常大耍两面派手法,一面夸奖其上书的“爱国热忱”,以讨好谘议局,一面又说“似应伏阙自陈,分途呼吁,方见全国一心”[1](104页),拒绝代奏。
随后,吉林商务总会又上书“详请速开国会”。上书特别指出:“东三省危亡之祸,已迫在眉睫,若再不亟图挽救,将不免为朝鲜之续。”要求陈昭常“垂念东省大局,即日据情代奏,速开国会,以救危亡”[1](104页)。接着,长寿县绅民王炳辰等630人也联名上书,认为“方今大计,则莫如速开国会,而成一团结莫解之大团体,庶君民一体,万众同心,尚可挽狂澜于即倒。不然,壮志顿消,时局之坏,当不知伊于胡底”[1](105页)。这些上书说明,吉林立宪运动的范围、影响已越来越大。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把召开国会、实行宪政看成是内结人心、外御强敌的唯一有效手段。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们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使吉林的立宪运动更带有爱国救亡的色彩。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派大多转向革命,推动了各省的独立,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但吉林的立宪派这时则更多地表现出他们的软弱性,对革命形势的发展缺乏正确认识,而毫无所动。当陈昭常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电令,召集政绅商学军警各界议组“保安会”,以继续维持旧的统治秩序时,谘议局议长庆康率先表示“绅界极赞成”。只有学界极力反对,倡言“非独立不可”[3],但孤掌难鸣。“保安会”终于成立,陈昭常被“公推”为会长。
由此可见,“大抵吉林士绅,心如散沙,遇事毫无所主,而先各存意见,又何怪乎各省纷张独立旗,而吉林省徒落人之后尘也”[3]。此语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吉林在辛亥革命中之所以落后于全国形势的原因。由于吉林的立宪派内部意见分歧,没有及时转向革命,而革命派则力量薄弱,在吉林的活动也不甚显著,以至使吉林省始终没有主动脱离清王朝的反动阵营。直到清帝已经退位,陈昭常才摇身一变,成为中华民国的吉林都督,就连像江苏巡抚程德全挑几块巡抚衙门的屋檐瓦以示“革命”的形式都未曾表演一下,辛亥革命的情况,从中也可略见一斑。
综观吉林的立宪运动,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立宪运动作为一场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在吉林基础薄弱。由于吉林地处东北边陲,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资本主义起步较晚,其数量和规模远逊于内地,尤其是与江浙地区相比则差距更大,因而吉林的资产阶级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似乎无足轻重,其局限性则更为突出。虽然他们同样具有改革政治的要求,但由于缺乏这种改革的社会基础,因而难有大的作为。
第二,尽管吉林的立宪运动在全国影响并不甚大,但他们毕竟还是参与了这场有利于社会进步、推动历史发展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且经历了从地方自治会到谘议局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一定规模,为立宪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三,尤为重要的是,吉林的立宪运动有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具有强烈的救亡色彩,表现了可贵的爱国热忱。内地省区的立宪运动大都是以要求清政府改革封建制度,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为直接目标,而吉林的立宪运动却时刻把这一政治要求与救亡图存紧密联系起来,甚至把后者放在更为核心的地位。这反映了立宪运动更为深刻的内涵,也真正体现了时代的中心。因此,吉林的立宪运动虽然在起步、发展规模、造成的声势与影响上,尤其是从立宪到革命的转变上,落后与内地特别是南方省区,但却以其独具特色的斗争历程,为这场运动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
[收稿日期]2003-0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