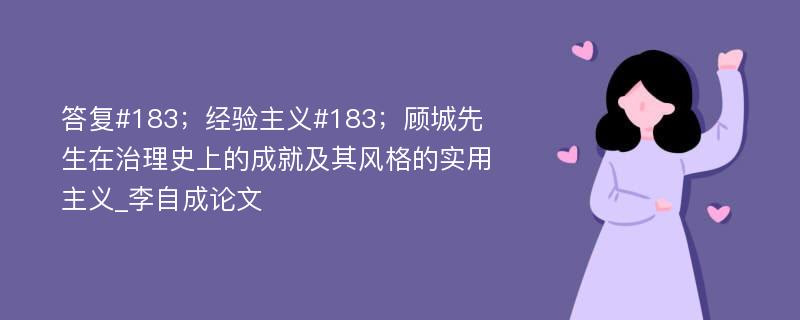
发覆#183;实证#183;务实——论顾诚先生的治史成就及其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风格论文,史成论文,顾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4)11-0223-08
顾诚先生(1934.11—2003.6),江西南昌人,著名的明清史学家。生前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先生的史学研究以史料扎实、论证严密、发覆求真、学风严谨的显著特点,引起海内外明清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笔者不才,有幸忝列师门之末。先生去世后,协助师母整理先生遗稿及论著,时时为先生以“学术为生命”的治学精神所感动。在此笔者以惴惴不安的心情,就先生的学术传承与治史之路、治学特点略加整理,以期弘扬先生的治学精神。粗陋之处,敬祈方家赐教。
一、治学之路与学术传承
1934年11月28日,顾诚先生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乳名“小六”。其父顾祖荫(1891—1969),在河南大学毕业后回江西工作,先后在南昌一中、二中任教,曾担任南昌二中的教务长;1940年至1946年间,任省立吉安 中学(今白鹭洲中学)校长;稍后,任国立中正大学和南昌大学副教授。其母高克正(189 9—1972年),多年担任班主任之职,在抗日战争期间经济最困难的日子里,在自家吃不 饱饭的情况下,帮助一批家境贫寒的学生。如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王梓坤院士即是 其中一位,他多次在文章里感谢这位“恩师”,说:“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的最高学 历可能只是初中一年级。”[1]他们夫妇二人学识兼及语文、地理、英语、历史、人文 和经济等。生活在这一个充满爱心、家学渊博的家庭里,顾先生的兄弟姊妹都受到较好 的影响。在国务院公布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顾家有包括顾诚先生在内的三人 榜上有名,这在全国也是极其少见的。
回顾先生的治学之路,出身书香门第给他提供了良好的治学潜智,其一生的学术发展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厚重扎实的学风和学术传承有更为密切的关系。
1957年,顾诚先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此前,自1951年始,他在南昌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南昌市委党校工作。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年龄与工作关系,他比别的同学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学期间,他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整理和周一良先生主持的通用教材《世界现代史》的编写工作,培养了较强的独立科研能力。[2]
顾先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在白寿彝先生的建议和指导下,开始了明史的研究。“文革”开始后,先生被分派到学校新成立的外国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工作。1971年他毅然决然地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是在“林彪事件”以后,此后五年,他一直在干“私活”——上班点卯后,偷偷找书看。为防止“意外”,他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明末农民战 争史作为研究的对象。据他讲,“在‘文革’之前我摘录的明清史资料已经不少,有那 么一堆。‘文革’初期抄家之风极为盛行……在处理抄摘的史料时我留了个心眼,把有 关农民起义的史料保存起来,即便有人看到这也是历史上的‘红线’材料,而从朱元璋 起义的、与帝王将相有关的史料都进了造纸厂。这也就是后来重理业务以探讨明末农民 起义作起点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学术界同行是在1976年四人帮垮台,甚至1978年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理旧业,我多争取五年左右的时间(尽管不是全部时间),不能不 说是一件幸事。”[3]
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勤奋积累,1977年,顾先生回到历史系工作不久就发表了著名的《李岩质疑》。这篇用力颇深的论文,奠定了他在明清史学界的地位。此后二十余年, 先生的研究主要围绕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和明代的卫所制度等来展开,取得了彪炳 史册的成就。
如果说先生早年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还带有历史烙印的话,那么对南明史、明代卫所制度和管理系统等问题的研究则与之一脉相承。明末农民战争史与南明史的密切关联勿需赘言,而卫所制度的研究也是缘于对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他说,“最初感到卫所制度值得研究还同李岩问题有关”,原因在于所谓李岩之父李精白的卫籍身份问题。顾先生从明代的卫籍入手,发现卫所制度背后竟然隐藏着非常重大的历史问题,于是他暂时中断了对南明史的研究,集中五年时间研究卫所制度及其相关问题。[3]
顾先生的治史方法,深受北师大的两位史学大师的影响,一位是老校长陈垣先生,另一位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白寿彝先生。
在考证之法方面,他说:“以前陈垣先生曾经谈过研究历史应当在收集材料上做到‘竭泽而渔’。明清史料浩如烟海,往往力不从心,但作为一种治学的律己精神,作了一种努力的方向,总是应该的。”[4]北师大另一位学史学家赵光贤先生在总结从陈垣先 生那里的收益时特别提到了培养“考证功底”的重要性。他说,既然相信史学的“求真 ”职责,求真则有赖于“史料”,由于史料本身具有局限性,就需要详加考辨;考辨要充分占有史料,有必要的科学方法,惟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5]
顾先生非常感谢白先生早年对他的指导与赏识,认为是白先生指导他走向治明史之道。顾先生多次告诉笔者,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是呕心沥血之作,是真正的“主编”,与现在许多挂名“主编”大不相同,对白先生充满了敬意。在给学生授课时,他说,治学要像白先生那样,既要注重史料的占有、考辨,又要注意宏观问题,为现实服务。顾先生秉承前辈学者的学风,践履之,传承之。白先生强调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经过考核分析才是可靠的”,顾先生则明确表示,学术讨论“不要在低水平的有材料层次上停止不前”。又如白先生说:“要注意:决不要想找材料支持我的观点。这不是个正确的态度。”顾先生则非常严肃地告诫他的学生:“如果不去研读大量原始材料,想用一些所谓‘理论’做框架,填充一些二、三手的材料就想毕业,那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多次强调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顾先生亦以此为研究的重点。[6]以下我们结合顾先生的治史成就及其治史风格详加论述。
二、发覆之作,探寻历史的真实
顾诚先生一生心无旁系,潜心治学,平均每天读书时间在10小时以上。从1978年以后,他有《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2部专著,参加撰写著作5部;学术论文计39篇,约50万字,可见其下笔之慎重。在他的笔下,一个个明清史研究领域长期错讹的观点被纠正,长期迷惑人们的问题得到了最为合理的解释,每发一覆,便接近历史的真实一步。虽然他的许多结论具有颠覆性,但由于他论证严密,立论扎实,因而又几乎不给别人留下反驳的机会。如他的《明末农民战争史》荣获北京市社科二等奖,被认为是“敢于创新,见解独特,精于考证,立论坚实”的经典之作。[7]日本明史学会会长山根幸夫在《东洋学报》第67卷的1、2号分两期介绍了该书的主要观点。《南明史》全书新意迭出,寓事于论,论史于征,语言优美,颇受褒奖,被认为是“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其丰富的史实,扎实的功底,深刻的论著,独到的见解,把南明史的研究全面地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这对于明末与清初历史研究的深入,是一个很大的贡献。”[8]该书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一等奖和北京市社科一等奖。
《李岩质疑》是顾先生的奠基之作。李岩问题因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等作品而变得家喻户晓。顾先生在研读史料时发现,这位地位仅次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将领的史料竟然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他的生平事迹均不可靠。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史料的辨伪上,逐一否定了与李岩有关的记载,并解释清楚了李岩传说的来笼去脉。[9]文章发表后,美国的明清史学者戴福士(R.V.Des Forges)寄赠了他数年研究的、与其相似的观点,即李岩确系乌有先生。他对顾先生的研究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变换了研究的思路与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先生的观点。①
在对明清之际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理论问题的研究基础上,顾先生多有发覆,澄清了许多误解。如关于大顺政权的性质问题,有学者从根本上否定历史上曾经有过农民政权, 他则认为大顺政权就是一个典型的“由起义农民建立起来的代表贫苦农民利益的革命政 权”;同时,他也认为农民政权“决不可能长期存在”,“它们不是被地主阶级的武装 所摧毁,就是在胜利进军的途中由于领导人的蜕化转变为封建政权”,但也不意味着“ 大顺政权根本不可能统一全国,成为继明王朝之后的另一个封建帝国”。大顺农民革命 政权失败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大顺政权没有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动相应地调整自己 的政策”,即没有及时从农民性质的政权转变为封建政权;二是满、汉地主阶级的联盟 通力镇压。[10]与之相一致的,他认为,李自成起义军“确实曾经长期采取流动作战的 斗争方式;但是,要说李自成奉行一种什么‘流寇主义’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他指 出,李自成起义军长期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应当肯定,在四处征战过程中,大顺政权也 在各地部署武装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权,并为巩固这些政权做出了种种努力。[11]在《 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附录的“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表”和“大西政权地方官员表”中, 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李自成和张献忠农民政权的性质和建立地方政权的情况,因为大顺 和大西政权“在每一个相当于省管辖的地区内,都有高级将领统兵镇守,战略要地一般 都部署了相当的武装力量,甚至州、县基层政权也大抵配置了专职武官带领地方武装维 持治安”,这也是对“流寇主义”观点绝好的回击。[12]
对南明时期大顺、大西农民军余部抗清斗争的评价问题,顾先生也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他认为满清入关后,当时的社会矛盾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明末和清军入关初期,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满清政权建立后,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推行了民族压迫政策,民族 矛盾不断激化,其地位逐步上升。清初二十多年连绵不断的战火,“应该说这是满洲贵 族竭力推行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所带来的直接结果”,这一矛盾也促成了抗清联合 阵营的形成,大顺、大西农民军余部与南明政权联合抗清的做法在当时是值得称道的。 [13]
也正是有了农民义军的浴血奋战,有了满清统治者倒行逆施的民族压迫政策,顾先生以坚实的立论反驳了那种认为“南明势力不过爝火余烬,苟延残喘而已”的观点,认为直到顺治十一年以后,复明运动才“逐渐化作泡影”,如果诸多反清计划觅得机缘,颠覆满清政权并非没有可能。基于农民起义军在南明史上抗击满清统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南明史》是以抗清农民军为主线来论述的。在《关于夔东十三家的抗清斗争》一文 中,先生认为,“在长达二十年的大规模抗清斗争中,真正的主力是由起义农民组成的 大顺军和大西军”,夔东十三家的抗清斗争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正是由于以农民军 为核心的抗清斗争的顽强斗争,才使清朝统治者多少认识到了蕴藏在人民当中的雄伟力 量,迫使他们为稳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采取一些有利于安定人民生活、恢复社会生产的 措施。”[14]
顾先生对清初二十余年的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评价不高,对所谓的“康乾盛世”持低调的态度。他说,他的研究“着重分析的是各派势力的成败得失,以哪一种势力取胜对中国社会生产破坏最小,最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前进为褒贬的标准。”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他用确凿的事实证明了大顺军推翻明王朝、接管整个黄河流域,几乎对社会生产没有造成什么破坏,并且扫荡或狠狠打击了那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而满洲贵族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大多实行“屠城血政”,经济的恢复发展效果相当有限。在《南明史·序》中,他说:“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
顾先生的晚年密切关注明代的卫所制度和明帝国疆土管理问题。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的《明前期耕地数新探》、《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谈明代的卫所》和《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四篇文章,在明清史学界再次引起震惊。他创造性地提出明帝国两大管理系统的论断,其基本观点是:明帝国的整个疆土分别隶属于行政系统即六部——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府(直隶布政司的州)——县(府属州),军事系统即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行都指挥使司、直隶都督府的卫)—— 卫(直隶都司的守御千户所)——千户所两大系统的……明代军事系统的都司(行都司)、 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种地理单位,负责管辖不属于行政系统的大片明帝国疆 土。明代体制的这一重要特点,为历来治明史者所忽视。他的这一研究引发了明清史学 界在诸多领域的思考。如有学者认为,他的这一理论对长期争论不休的明清两代的人口 与耕地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也进一步论证了清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相当滞后 的观点。[15]
顾先生的创新不是刻意去标新立异或哗众取宠,而是对相关问题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去探寻历史的真实,去澄清大量史籍错误或前人的误解。如在研究沈万三问题时,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从民间到学术界都说沈万三是明初人,至少认为他的主要事迹发生在 明朝洪武年间。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他断言:“沈万三是元朝人,有关他本人在明 初的一切‘事迹’纯属讹传。”[16]又如对史可法的评价,他一反传统观点,说:“史 可法的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至于 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 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 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7]对于他这 一反传统的观点,许多人从情感上难以接受,但看了他的论证,又感觉难以反驳。
顾先生每发一履,必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为目标,虽 然不乏颠覆之作,惊人之举,细读其文,惟有佩服其功力。
三、无信不征的考辨,严谨持重的学风
顾诚先生的考实功力为学界公认。他的史料运用几近“竭泽而渔”,并摸索出科学的考据方法,可谓当代考实之学的杰出代表。他谨严的治学态度和无信不征的考实学风,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史学理论家刘泽华先生把顾先生的《李岩质疑》和陈寅恪先生的“曹冲称象之事”的考证方法作为当代历史学考实的典范。[18]
顾先生在庞杂的明清史料里披沙拣金。如在明末农民战争的研究中,他对“古元真龙皇帝”的解释,[19]对子属乌有的荥阳大会和“分兵定向”策略的论证,否定了清初关 于张鼐或李双喜统率孩儿军的说法,澄清了车厢峡之困和抗击张献忠的女将军沈云英的 相关事实等,[20]对李自成起义军何时从何地入豫以及何时称帝进行了详细的考订,摆 事实,讲道理,令人折服。
在《南明史》中,全书考订出的史实及史籍错讹之处俯拾即是,既有子属乌有的“韩王定武政权”,也有李自成殉难的时间和地点、李定国病死的时间和地点以及马士英的归宿等。还有对一些重大历史疑案的解释,如李定国进军广东的举止,郑成功与永历朝的关系,以及“长江之役”的价值等,许多传统观点在顾先生笔下为耳目一新、令人信服的结论所取代。在这本巨著中,先生随手出校,把考实之法贯穿于字里行间,论证恰如其分,真真做到言不轻出,无一字无出处。如姜瓖反清时间,先生据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考得,《清史列传》卷八十《姜瓖传》载为十一月,“时间有误”(P528);对严重错误,如乾隆四十四年《甘州府志》载甘肃回民米喇印抗清事,明确指出为“大误”(P549)。而对自己无法确定又可能有错误者,也会明示之,如在考订王应熊病死的时间和地点诸书记载不一致,先生认为“刘道开为同时同乡人,所记可能较准确” ,李天根的《爝火录》所记“恐不可靠”,(P626)表明了他对不同讹误的处理态度,做 到让读者心中有数。在考订时,往往会对考辨的方法加以说明,如《清世祖实录》卷四 十五对济尔哈朗进军湖南的记载出现错讹的原因是:“济尔哈朗的奏疏是用满文写的, 实录译成汉文时,因音近致误,辰州当是郴州,杜允熙即堵胤锡。”(P579)
顾先生扎实的考辨功力源于他“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刻苦钻研精神,源于他“竭泽而渔”式的史料搜索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像《南明史》直接征引的地方志史料有二百余种,而他把明末及南明义军所到地区的省、府、州县志书全部翻检一遍,达上千部之多,仅云南一省的方志就查阅了一百余种。一些珍贵的史料,如《南明史》的封面配图出自柳同春的《天念录》中的插图,该书生动地描述了清军围困南昌城的情形,是顾先生在图书馆里首次发现并利用。他多次强调,史实考辨不仅必要而且必需。他说:“历史研究做到言必有据比较容易,困难的是要鉴别哪些记载可靠,哪些不大可靠,哪些根本不可靠。”[4]
顾先生无信不征的治史风格,源于他严谨持重的学风。先生读书很广博,知识面相当宽广,但他的学术研究一直专注于自己的领域,恪守“言不轻出”的原则。顾先生始终把培养年轻学人良好的学风当做重要的问题来抓紧落实,他说,“学风的好坏,关系到学术发展的前途”,治学切忌浮躁,树立严谨的学风是学术界的当务之急。[4]他认为,学风问题,其实是做人问题,一个人首先应当诚实守信,尊重别人的劳动,不欺瞒,不偷懒;要勇于承认自己的差距与不足,“做学问先学会做人,真理比面子更重要”。[21]在《南明史·凡例》中他说,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书中引用史料“虽在摘录时经过核对,力求准确,也不敢说绝对没有笔误”,他郑重地提醒读者:“如果有人未见原书而从本书中转引史料,请注明引自本书。这不仅是著作权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读者负责和学术上良心的体现。”顾先生以一位学者的良知以及对后学负责的态度,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忠告。
四、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密切关注重大社会问题
顾先生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导自己的研究,认为:只有尊重历史,尊重历史史实,实事求是地去诠释历史,才是历史学的治学之道。
以他所倡导的扎实严谨的学风为例,他说,史实的考辨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只有对史料深入挖掘,才能找到所谓的“理论”和“规律”。他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相信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可以认识的”,恢复历史真面目凭借的是“第一手材料”。[22]在治学方法上,他认为,历史研究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充分吸收国外科研方法和学术成果,要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看不到海外学者运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可以借鉴,学术上取得了的成果可以引进,无疑是错误的;对海外学者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发表的作品不加分析地奉为楷模,大加鼓吹,则至少是一种幼稚的表现。”[23]
顾先生是在肯定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前提下进行研究的,他说,“历史不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不要认为历史研究过于容易,历史学是一门最硬的学问,尊重客观史实的重要性非常重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学问,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相当有限,许多问题仅具一般常识,甚至毫无所知……至于在理论和观点问题上,则遵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必强求一律,既不想把个人看法强加于他人,也不想违心地迎合某种思潮或论点。”[3]正是承认历史的客观存在,所以他才不会停滞在“有史料”的低水平层面上,而是要穷尽史料,广征博引,考辨史料,务求信史,使自己的研究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先生始终坚持史学的阶级属性,认为史学研究为现实社会服务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任何一部史籍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它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产生,又反过来为作者所选择的政治服务的。”他说,像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其史学价值就不能简单地从纯史学的角度去衡量,“《甲申三百年祭》是时代的产物,又为推动历史前进作出了贡献。这正是它的优点。史学的科学性,首先在于揭示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现实斗争。”[24]
先生的考实细致入微,他的视野始终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和整个世界范围内,去洞察研究的对象。他说:“应当说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离开了微观研究成果的综合,所谓宏观研究就将失去科学的依据,变成研究者主观的遐想。”先生认为,在史学研究过程中,一个明清史学者,一定要注意到:“明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和明帝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改变就事论事,力图从更加广阔的眼界开展明史研究……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转为落后大致发生在明中期至清中期这400年间,研究中国和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并找出其原因是明清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23]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在建国以 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五朵金花”之一,是历史研究中的“显学”,它与20世 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有直接的渊源,而那场大论战又源于人们对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 关注。先生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以及发展阶段的宏观思考,体现了在与西方历史比较的 基础上,在世界史的范围内研究中国历史的意识,其学术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 谈到研究明史的重要性时,他说:“世界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落后,有时先进 。我们中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研究明史可以知道中国是怎样落后的,这是对中国 国情的研究和认识,我以为这是研究明史的关键所在。”[25]
顾先生也非常乐意对一些与自己学术研究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如近年来,李自成殉难的地点成为地方政府和明史学界关注的焦点。顾先生从崇祯十七年大顺军南撤路线研究入手,利用档案材料,考查李自成牺牲的经过和大致时间,以及牺牲后大军的行程路线后得出结论: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无可怀疑”;并对李自成归隐湖南石门县夹山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以清廷和南明政权均没有在湖北获取李自成的尸首为由,来否定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是“徒劳无功的”,乾隆年间何璘所撰《书李自成传后》一文和有关奉天玉和尚的所谓遗存史料都是不可靠的。[26]他说,对这些社会热点的争论,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第一手材料为基础分析论证,以达到揭示历史事实、服务社会的目的,这充分体现了顾先生作为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史学服务社会的自觉。
顾先生推动了新时期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以《南明史》的研究为例,何龄修先生认为,该书“代表南明史研究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只有顾诚教授《南明史》对南明史全过程和具体问题做了精深的分析、研究。也就是说,只有顾诚教授一人真正前后贯通地、比较透彻地掌握南明史。”[27]他“所提出的一些带理论色彩的学术观点,受到了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28]他对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意义、明清易代、人物评价标准以及清前期的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凝重的思考,给治明、清史者提出了许多指导性和启迪性意见。秦晖先生认为,顾先生在史学与史识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创造了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南明史》的史识史论都有鲜明特色……像这样对传统史学、改革前史学与当前流行史学范式都实现了超越的著作,应当说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南明史》本身便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的出现,这种意义显然已经超出南明史研究的范围。”[29]
顾先生的实证、求实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以及淡泊名利的身体力行,不仅成为创造学术精品的典范,也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家应有的崇高品格和科学精神。郭小凌先生对《南明史》的评价,也是对顾先生学问人生的评价,他说:“顾诚用自己的《南明史》证明,社会科学中的真理(真实),哪怕是很小的真理,也同自然科学中的真理一样,绝不是一块铸好的硬币,拿过来就能用,同样需要寻找者付出巨大的代价,需要时间、精力和才智的慷慨投入,需要长时间与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进行抗衡的勇气。那些靠一知半解、东拼西凑、媚俗媚上、投机取巧等小聪明、小伎俩拼凑学问的人,是永远同真理无缘的。”[30]
顾诚小传:
顾诚,1934年生于江西南昌市。生前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重点学科——古代史的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2003年6月25日因病于北京逝世。顾诚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明清史专家,代表著作有《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后者于1998年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代表论文有《李岩质疑》、《明前期耕地数新探》、《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等。顾先生生性秉直,深居简出,孤夜长灯,治学严谨,以学术为生命,是学术界公认的当代考实之学的杰出代表。WWXXCK
[1]王梓坤.悠悠师生万古情[J].江西教育,1985,(9):4.
[2]陈宝良.学穷本原,行追先哲——顾诚教授学行记[J].(日)明代史研究,2004,(4).
[3]顾诚.我与明史[J].社会科学评论,2003,(1).
[4]张越.顾诚教授访问记[J].史学史研究,1995,(2).
[5]赵光贤.我在史学研究中是如何贯彻实是精神的[A].赵艳国.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C].武汉出版社,1994.454.
[6]白寿彝.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A].中国史学史论集[C].中华书局,1999.348—368.
[7]诸葛计.<明末农民战争史>简评[J].历史研究,1987,(5).
[8]陈梧桐.一部将南明史研究推向深入的佳作[J].历史研究,1998,(1).
[9]顾诚.李岩质疑[J].历史研究,1978,(5).
[10]顾诚.论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6).
[11]顾诚.关于李自成“流寇主义”的商榷[A].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二)[C].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2]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50.
[13]顾诚.论清初的社会矛盾——兼论农民军的联明抗清[A].清史论丛(第二辑)[C].
[14]顾诚.关于夔东十三家的抗清斗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3).
[15]赵明.明代兵制研究六十年之回顾[J].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8).
[16]顾诚.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J].历史研究,1999,(1).
[17]顾诚.南明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184—186.
[18]刘泽华.历史研究中的考实性认识[J].文史哲,1989,(1).
[19]顾诚.古元真龙皇帝试释[J].历史研究,1979,(5).
[20]顾诚.明末史事杂考[A].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四)[C].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21]彭勇.顾恋寂寞修己志,道德文章彰其诚——怀念我的导师顾诚先生[J].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03,(9—30).
[22]顾诚.再谈李岩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2).
[23]肖黎.中国古代史导读[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1.448—455.
[24]顾诚.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与姚雪垠同志商榷[J].中国史研究,1981,(4).
[25]肖黎.在明史中辛勤耕耘[N].光明日报,1990-4-4.
[26]顾诚.李自成牺牲的前前后后——兼评石门县为僧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2).
[27]何龄修.读顾诚<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4).
[28]高翔.1998年清史研究综述[J].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3).
[29]秦晖.南明史研究与顾诚的<南明史>[N].北京日报,1997-11-16.
[30]郭小凌.文章不写一字空——评顾诚<南明史>的治史方法与治史精神[J].史学理论 研究,1998,(4).
标签:李自成论文; 明清战争论文; 元末农民起义论文; 顾诚论文; 甲申三百年祭论文; 明末农民战争史论文; 南明史论文; 明史论文; 明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