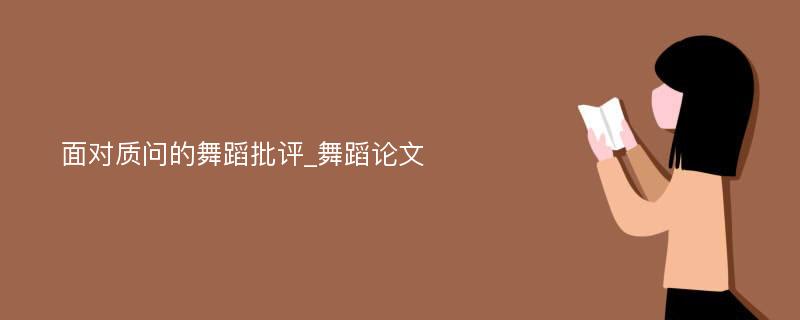
面对诘难的舞蹈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诘难论文,舞蹈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时不时地,会在《舞蹈》期刊上看到一些批评“舞蹈批评”的文字。文字虽然不是很多,诉诸文字者的水准也大相径庭,但这毕竟说明我们的舞蹈批评是被监督着的言论,它在批评对象时也就意味着向对象和公众敞亮着自己的态度和水准。按说,有对“批评”的批评的存在,对于舞蹈批评而言是一大幸事。但平心而论,这些对于“批评”的批评,大部分无益于舞蹈批评的改善和前行。比如有的批评(我指的是对“批评”的批评)居然看到了“当前舞蹈评论面对当代社会价值观的异变、游离所滋生的几分无奈、几分茫然的‘精神错乱’”;又比如有批评在为舞蹈批评的问诊把脉中,看到的是“中庸、虚伪、不关痛痒的批评在舞蹈界泛滥成灾”……一边说是“精神错乱”,一边说是“泛滥成灾”,读到这样的文字,我总在想,我们的舞蹈批评果真如此吗?那我们《舞蹈》的编辑们又干什么去了?否则何以会让“精神错乱”的批评见诸刊物,又何以会让“中庸、虚伪”的批评“泛滥成灾”?于是有一次拨通执行副主编杜晓青的电话谈了我的想法,晓青倒是快人快语地说:“这是在批评我们呢!”或许也是。谁叫你总不给人家“话语权”,逼得人家也找一个“一骂成名”的方式……
2、在那些批评“舞蹈批评”的文字中,对舞蹈批评最多的批评是说其“批评的缺席”,或者说是“没有批评的批评”。诘难者甚至认为:“当今流行的多数舞蹈评论既不能对作品的艺术价值作出恰当的判断,也不能对作品及创作中的谬误流弊予以鞭挞。”我不知道这个“流行的多数”到底多到什么数、流的什么行,值得诘难者惊呼“舞蹈批评往何处去”?事实上,我们的舞蹈批评并不缺批评。不信,你可以在《舞蹈》上随便一翻就能看到不少“批评”的文章,尽管这“批评”未必都深刻但却不乏犀利。当批评把创作作为对象时,批评者大概不会回应创作者类似的愤言——你说我不行,你编个给我看看!但对于“舞蹈批评”的批评者,提这样的要求就不算过分——你写一篇对作品的艺术价值作出恰当的判断、对作品及创作中的谬误流弊予以鞭挞的舞蹈批评给我们看看。与其发问诘难“舞蹈批评往何处去”,莫如示范—下“舞蹈批评往何处去”!
3、写下上面这段文字,我其实并不是要找谁抬扛。而是在陆陆续续读到一些批评“批评”的文字后,总觉得这些文字都有些“眼高手低”的味道。当然,你也不能不允许“手低”者可以“眼高”些,不能不允许别人批评不了创作就不能去批评“批评”。但我仔细读过这些文字后,发现这些“眼高手低”者其实并不怎么真正了解舞蹈创作的现状。他们甚至都没有怎么看过作品,就敢于狂言:“为什么每年全国各地有那么多地方官员热衷于大大小小的舞剧工程?我们的舞蹈批评又有多少能够以及敢于指出真相?”读着这样的狂言,我觉得这些起初看来的“眼高手低”者已近乎“目盲言狂”了,真给人“无知者无畏”的感觉。虽然,我们的舞蹈批评是不是需要更多、更狠些的批评,这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批评毕竟只是手段,目的仍然是有助于舞蹈创作的繁荣和舞蹈文化的建设。如果对舞蹈创作现状的事实都知之甚少,又怎么可能对舞蹈批评的存在有一个恰当的评估呢?
4、还有一些批评“批评”的文字,或被刊物编辑成“理论的尴尬”,或以作者居高临下的告诫——《舞蹈理论不要自欺之人》为题。“理论的尴尬”的一组文章,似乎谈的是理论相对于实践的滞后性,谈的是我们需要应用性更强的理论。我曾对参与笔谈的许薇博士说,不要去谈这些品之无味、读之无益的东西。因为谈这些问题就难免要给人开药方——隐匿者告诉你谁谁谁的理论才是好理论,简直者则告诉你什么样的舞蹈理论才不自欺欺人。实际上,一个进行着独立思考、追求着独立品格的批评者怎么会照这样的药方去抓药呢?我对许薇说,无论是舞蹈理论的建构还是舞蹈批评的操作,我们目前主要是“胆有余而学不足”,我们缺少的是博奥的学养、睿智的学识、缜密的学理和平实的学风。
5、在舞蹈学乃至文艺学的领域内,对于“批评”的批评其实也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你为着要实现自己的“话语权”来批评“批评”,或者要证明自己才不是“自欺欺人”的“舞蹈理论”,你起码也要懂一些舞蹈批评学甚至文艺批评学的学理。实际上,《舞蹈》杂志上让人开卷有益的关于“批评”的文字,是张中载先生的《也说“批评”》。这篇短文一是告诉了我们“批评作为一门学问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Criticism最初的词义是判断或评论”;二是告诉我们“这几年我国文化界和学术界一个有意思的变化是人们开始更多地用‘批评’取代‘评论’”。为什么已经有两千多年初义的Criticism会在近几年的中国由“评论”变成“批评”?这其间一个重要的原因无疑是批评者“主体性”的膨胀或扩张。我从不视批评为创作的附庸,但我更不认为批评对于创作可以耀武扬威、颐指气使。作为一门科学的批评,“它是以充分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刻研究典范的作用和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基础的”(普希金《论批评》);批评为什么要以“艺术家在作品中遵循的规则”为基础,是如集大作家、大批评家于一身的郭沫若先生所言:“文艺是在无之中创出有,批评是在砂之中寻到金。”我对于当下舞蹈批评最大的遗憾,不是缺少“璧中指瑕”的胆略,而是缺少“砂中寻金”的智慧。
6、为什么会缺少“砂中寻金”的智慧?就当下的舞蹈批评而言,我以为主要不是缺少某种理论的武器,而是缺少对批评对象的历史把握。也就是说,大部分批评既缺少“知人论世”,又缺少“温故知新”。事实上,就是本文提及的对于“批评”的批评,在舞蹈批评历史真相的洞察和历史脉络的梳理上,也基本上是“盲人摸象”或“痴人说梦”式的。一般的文艺批评学在论及文艺批评活动的结构系统之时,都喜欢沿用美国学者亚伯拉姆斯《镜与灯》一书中提出的“四元架构说”,也即认为一件文艺作品必然含有世界、作家、作品以及读者四个要素,这四要素的相互关系便是文艺作品的“四元架构”。批评家的批评活动由于对上述四要素的关注点不同,从而形成了相应的批评类型,即还原批评、作家批评、作品批评和接受批评。我想要指出的是,无论哪种批评类型,都要建立在洞察历史真相和梳理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否则,我们的还原批评无法通过作品与现实世界关系的考察,揭示出作品形成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渊源;我们的作品批评也无法通过作品文本的构成分析,揭示出作品的构成规律及其文本价值。如此,我们当然就更谈不上在众多的舞蹈创作实践中“砂中寻金”了!
7、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舞蹈批评本身也是在建设过程中的舞蹈文化。对于建设过程中的舞蹈批评而言,与其抱怨没有“话语权”就不如潜心提高“话语能”,与其冷眼旁观去“璧中指瑕”就不如慧眼独具去“砂中寻金”。为着慧眼独具并进而匠心独运,我们的舞蹈批评就要结合批评的实践去形成方法的自觉。多年来,我们文艺批评所奉行的是“美学的历史的方法”。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种方法的对象视野,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也就是说,只有这种“完美融合”的作品,才是我们“砂中寻金”的对象。其实,无论是“美学的历史的方法”还是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无论是系统论的思路还是整体论的理念,无论语言学、心理学的方法还是人类学、价值学的主张,都没有被我们舞蹈批评很好地掌握。我们的舞蹈批评缺的不是“真话”,而是“真话”中“真”的方法依据和“话”的理性含量。我们需要有积极意义和良好效果的真话。
8、对于舞蹈批评,特别是广义的舞蹈批评——比如《舞蹈》刊物上刊发的那些并非针对舞蹈作品、舞蹈家乃至舞蹈批评的文章,我一直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因为现在各式各样的舞蹈研究生多了,他们需要找地方练笔,而他们其中一些人的导师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舞蹈论文,对他们的苛求就有可能扼杀舞蹈批评“未来的希望”。还有许多在各式各样的高校中从事舞蹈教学的教师,尽管视野有限思考也有限,但总在为获得某一级职称而费劲地琢磨一些课题,他们之中也不乏“未来的希望”。其实这里要批评的,不完全是他们治学的浮躁心态,更是他们求学的浮躁环境。你想想,现在高校的舞蹈教材都多有“水货”,那么多舞蹈学子能不缺“干粮”吗?
9、即使在舞蹈高教界,也总能听到“(舞蹈)是干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说法。诚然,舞蹈有舞蹈的“干”法,但“写”却是人类共通的表达方式,舞蹈的高级知识分子恐怕不能以不会“写”而自豪。而且就舞蹈批评而言,“写”就是其“干”的方式。应当说,舞界能拿起笔来“干”的舞者渐渐多起来了,舞者“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状态也得到了初步的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动辄说他们“精神错乱”、“泛滥成灾”即使算不上用心险恶也总有点存心不良。这也是我对目前广义的舞蹈批评持宽容态度的一个重要缘由。舞蹈批评是写出来的,“写”不仅是舞蹈批评的“干”,而且是一种倾注着“思”的干。在这样一种“干”的方式中,过于火爆的批评可能恰恰不利于批评品格的建构和素质的提升。虽然有些舞蹈批评的文章也让人感到“吐气扬眉”,但我却更愿意读那些心平气和的文字——比如年轻后学里许锐文章中溢出的思辨色彩,比如刘春文章中闪烁的智性灵光,还比如慕羽文章中弥散的学养气息……当舞蹈批评面对诘难时,我只想说一句:我们仍然要——宁以学养心,勿使气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