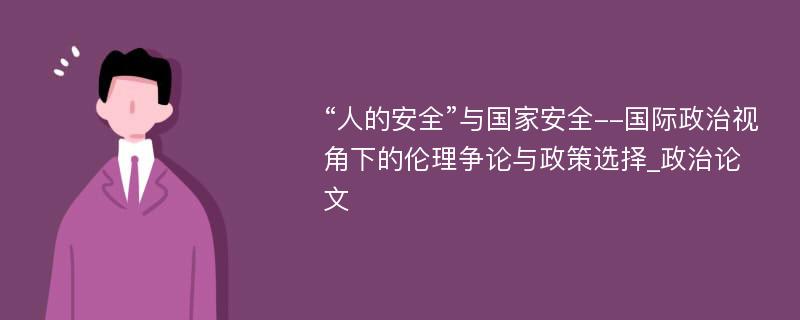
“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国际政治视角的伦理论辩与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安全论文,伦理论文,视角论文,政治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4)02-0085-26
一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人(类)的安全(human security)”问题逐渐成为当代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以及联合国等重要国际论坛,与此相关的理论探讨和政策辩论层出不穷。在其倡导者看来,国际社会的安全主体或安全关切对象已经或者应该从国家转向人类个体或整体,“人的安全”应该取代国家安全或国际安全而成为首要价值。
然而,在国际政治的语境中讨论安全问题,不能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尽管当今国际体系与三百多年前相比,在地理范围、权力结构、交往规则和价值规范等方面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国际体系仍然以民族主权国家为主体并且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在人的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等新的安全观念或安全关切日益受到重视的同时,国家安全仍然是各民族国家在交往互动时普遍珍视的一种重要价值、乃至首要价值。与此相关,作为国家在安全相互依存时代确保自身安全的一种必要的外部条件,全球以及区域层次的国际安全——集中体现为国际体系本身的存续以及国际基本秩序与交往规范的维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成为一种公认的价值。相比之下,国际社会在“人的安全”问题上所形成的共识显然要“稀薄”得多,在学术理论与政策实践两个层面都存在着许多重大分歧。因此,辨明各种安全价值之间的关系,厘清在具体情形下其合理的优先等级次序,思考进行合理价值选择的原则与途径,以避免陷入本末倒置、顾此失彼或得不偿失等各种政策误区与两难处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文的目的,是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探究“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辨析围绕这两种价值所产生的学理论争和政策分歧并探讨可能的解决途径。为此,本文首先描述和分析“人的安全”观念或概念的兴起及其背景。其次,辨析人们对“人的安全”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相关理论分歧。复次,联系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研究的各种理论观点,探究“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这两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厘清它们的合理边界与兼容范围。最后,联系当今世界政治的现实,从实践伦理的角度提出一个分析框架,以阐明应对价值冲突与政治分歧、进行伦理判断与政策选择的途径与原则。
二 “人的安全”观念的兴起
“人的安全”显然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更不是一个新问题,只是长期被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这类传统主流话语所遮蔽。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的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主要是因为以下三点:首先,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过去长期被东西方矛盾所掩盖或者由于两极格局的相对稳定而得到有效控制的一些潜在的冲突、危害或威胁很快暴露出来。其次,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各类全球性问题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安全相互依赖”的现实日益明朗,传统的安全观念与安全战略受到冲击。人们发现,这些新的因素主要是对人类个体或某些群体而不是国家构成了直接威胁。例如,对人类安全尤其是生命安全与生存质量的直接和现实威胁,不是过去一直被视为核心安全议题的传统国际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大国核对抗或军备竞赛,而是诸如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经济危机、贫困、流行疾病、自然灾害、人权侵犯等问题以及与国家治理失败和内部种族、部族或宗教矛盾有关的各类新型战争或暴力冲突。与此同时,民族国家似乎没有足够的能力或意愿去应对各类新的威胁,保护“人(类)的安全”。最后,“人的安全”概念的兴起,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与理论背景,这就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自由主义(尤其是自由派国际主义)国际政治观念的重新抬头和国际人权话语的盛行。①事实上,如果追根溯源,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安全”最初主要是一种“西方话语”,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谈论各种新安全挑战时,使用更多的是“非传统安全”这个概念。
众所周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其价值取向和出发点从根本上讲是个人的自由、福祉和尊严。在国际关系的层面,自由主义既把个人视为主要国际行为体,又把国家看做最重要的集体行为体,即以个人为开端,试图理解由个人构成的各种组织如何相互作用,因此国家是多元化而非一元化的行为体。但自由主义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十分庞杂的思想系统。一方面,分别由共和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所衍生出来的“民主和平”、“商业和平”与“制度和平”论,本质上都是以发达国家和跨国资本利益为主要关照对象;另一方面,以个人权力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派国际主义(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又是人类安全、全球安全等新观念的主要倡导者。②这在冷战结束之初还集中表现为“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相应地,“人的安全”也几乎成为“人权”的同义词,从而被赋予了比“国家安全”更高的价值。这类自由主义观念还认为,现实主义用来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主要政策工具——国际均势——远不足以应对人类个体所面临的日趋多样化的安全挑战,人类安全以及国际安全还需要诸如法治、国际制度乃至国际干涉、包括军事干涉等新的手段。③
不过,“人的安全”并非自由主义独家垄断的话语,它实际上已成为西方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众广泛关注的一个公共议题。④就学术理论层面而言,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些著名学者已开始注意到传统议题的局限性,主张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其他各种重要威胁,而不只是军事威胁。⑤研究环境安全的学者们则认为,鉴于环境恶化对人类所构成的直接威胁以及与国际冲突之间的潜在和间接联系,环境保护应该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议题之一。⑥此外,一大批被笼统称为“批判安全研究”的理论观点也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的批判锋芒所向,不仅在于否定国家是安全利益的主要提供者或保障者这一“常识”,更在于揭示一个在他们看来显而易见的道理,即仅仅着眼于国家间关系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人类“不安全”的现实。只有将注意力转向社会性别、历史、种族、族群或经济关系,才能够深刻、全面地理解不安全的根源。⑦其中,建构主义理论试图用“人的安全”概念来挑战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中心主义立场,认为它们过分专注于国家,忽视了个人、群体、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组织等其他行为体,并且过分执迷于物质主义和实证主义,没有充分考虑到安全的主观成分、心理根源与人文因素。后现代主义借助“人的安全”概念来批判主流的知识论,进而反对把国家视为包罗万象、无所不能的安全行为体。女性主义据此批评主流安全话语所蕴涵的父权制特征。新葛兰西主义则要求根本改造现有国家体系与制度,认为拥有权力与意识形态霸权的政治精英们试图确立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安全结构,从而导致个人安全的边缘化。⑧
总之,在冷战后时代,人类的安全环境与安全处境已发生若干重要变化,人们的安全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人的安全”问题逐渐走出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议题的阴影而呈现在世人面前。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了以“人的安全”为主题的首个《人类发展报告》,并预言这一概念有可能掀起21世纪的一场社会革命。一些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也开始联合起来,尝试通过灵活的多边外交方式致力于促进“人的安全”。例如,1999年5月,奥地利、加拿大、智利、爱尔兰、约旦、荷兰、斯洛文尼亚、瑞士、泰国、挪威和南非等观点相近的11国政府部长和代表齐聚挪威利松,建立了“人类安全网络(HSN)”。日本等国家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后来又陆续参与其活动。一些国家还把“人类安全”概念纳入其外交政策之中。八国集团(G8)工业国峰会、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也逐渐将人类安全议题列为讨论重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曾几次将“人类安全”列为主要议题。在2004年的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还就此做了专题发言,论述恐怖主义、传染病的蔓延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凡此种种,皆表明“人(类)的安全”问题在国际社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上述现实与思想背景之下,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社会安全和全球安全等一系列新安全概念迅速在国际社会流行起来。总体上看,这些新概念或新观念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都直接或间接地认为,安全的主体或指涉对象应该从国家转移到个人,安全研究应该从国家安全转向“人(类)的安全”,从传统安全威胁转向(或者扩展到)非传统安全威胁。当然,这也是各种“人的安全”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点和显著特征。
总之,“人的安全”概念的兴起,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范围广泛的各类新安全威胁的一种直接反应,同时也是对以国家为中心的、内容狭隘并且以军事手段为重点的安全理念与安全战略的一种替代、矫正或补充。
三 理论分歧:何谓“人的安全”?
尽管“人的安全”已成为国际政治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相关学术讨论与理论分析也层出不穷,然而,究竟何谓“人的安全”?应该如何界定安全的内容,即需要维护哪些价值?应对哪些威胁?如何确定价值的等级与威胁的性质(即优先次序与轻重缓急)?维护安全的手段、途径或机制是什么?国际社会却远未形成足够的共识。仅就“人的安全”的内涵而言,从无所不包的宽泛概念到捉襟见肘的狭隘界定,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学术界所提出的定义五花八门,其中影响较大的不下十数种。⑨虽然这些定义都把“人(类)”视为安全主体或主要关切对象,但对于其中所涉及的主要价值和具体威胁却众说纷纭。“人的安全”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之所以学术疆界迄今仍然十分模糊,思想或理论分歧相当严重,概念本身的含糊不清是首要原因。
有关“人的安全”的第一项重要论述、也是迄今为止仍被广泛引用的“最权威”⑩界定,是1994年联合国发布的首个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其中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对安全这一概念的解读过于狭隘,例如免受外来侵略的领土安全、对外政策中的国家利益保护或者免遭核浩劫的全球安全等,而“对于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安全的普通民众的合理关切则被遗忘了”。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安全意味着保护他们免于疾病、饥饿、失业、犯罪、社会冲突、政治迫害和环境灾难等威胁。随着冷战阴影的消退,人们应重点关注的是国内冲突,而非国际冲突。(11)这一批评可谓明确而有力,但报告随后提出的“人的安全”新概念却相当含混:“人的安全有两个主要方面:它首先意味着免受诸如饥饿、疾病和压迫等长期威胁的安全状态。其次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在家中、工作中还是社群(communities)当中——免遭突然和有害的破坏。”(12)
按照这个定义,任何意料之外的、不合常规的不舒适状态都可以被视为对某个人的安全威胁。报告的作者似乎也意识到这个定义过于笼统,于是又列举了七个具体要素:(1)经济安全(如免于贫困的自由);(2)粮食安全(如能够得到食物);(3)健康安全(如有免于疾病的卫生保健);(4)环境安全(如免受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的威胁);(5)人身安全(如免于酷刑、战争、犯罪性攻击、家庭暴力、吸毒、自杀甚至交通事故等威胁的肉体安全);(6)社群安全(如传统文化和种族群体的存续以及该群体的人身安全);(7)政治安全(如享有公民与政治权力,免受政治压迫)。
正如报告的题目所示,所谓“人(类)的安全”,其实就是“人(类)的发展”问题。报告不仅根本无意给“人的安全”这个概念划定明确的边界,相反还明确肯定其“无所不包”的“综合”性质,认为这正是这个新概念的主要优点。(13)这种无所不包的概念及其所体现的“泛安全化”倾向颇有代表性。学术界尽管对这种阐述并不满意,但大多仍致力于修改、完善其安全要素清单,未能摆脱内容过于宽泛、含混的弊端,无法或者无意提出一个边界清晰、重点明确、具有学术研究和政策指导价值的定义。
例如,乔治·内夫(Jorge Nef)提出五大内容:(1)环境、个人和肉体安全;(2)经济安全;(3)社会安全,包括“免于因年龄、性别、种族或社会地位而遭受歧视的自由”;(4)政治安全;(5)文化安全。(14)劳拉·里德(Laura Reed)等人则提出十大要素,其中包括心理安全(目的是创造条件促进彼此尊重、充满爱心和人道的人际关系);沟通安全(强调信息流通的自由和平衡)。(15)
一些学者也试图提出自己的定义,但都非常宽泛。例如,萨拜因·阿尔基尔(Sabine Alkire)的著名定义甚至比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内涵还要丰富。她把人类安全的目标界定为“以与长期的人类富足相协调的方式,保障所有人类生命之核心利益免于普遍的威胁”。(16)萨拜因后来成为“人类安全委员会(CHS)”(17)的首席专家,其思想直接影响了该组织的观点。
卡罗琳·托马斯(Caroline Thomas)的观点也很有代表性。她认为,“人的安全”指的是满足“基本的人类需求”,实现“人的尊严”,包括“从压迫性的权力结构(无论其根源和范围是全球、国家还是地方性的)中解放出来”。此外她还把这个概念分为物质满足的数量与生存的质量两个方面。(18)罗伯特·贝德斯基(Robert Bedski)则认为,“人的安全”是“那些能够保护、捍卫和保持人类生命存在的知识、技术、制度与活动的总和以及维护和完善集体和平与繁荣、促进人类自由的进程”。这类定义所涵盖的内容如此广泛,以至于一位批评者感叹道:“如果人的安全是所有这些东西,那么它不是什么呢?”(19)
有鉴于此,也有人试图“缩小”这个概念,使其更加精确和实用,以便研究者和决策者有章可循。例如,加里·金(Gary King)等人提出的定义仅仅包括所谓“核心要素”,即那些“对人类足够重要、人们愿意为之奋斗或不惜冒生命与财产风险”的要素。(20)根据这个标准,他们提出用来衡量个人和群体安全状况的五项指标:贫困、健康、教育、政治自由以及民主。坎提·巴耶派(Kanti Bajpai)认为,“人的安全”状况可以通过考察“威胁”与“能力”之间的关系来判定,并进而提出一套指标,用以衡量“对个人身体安全和自由的直接与间接威胁”以及不同社会“处理这些威胁——也即培育规范、制度以及决策结构的代表性——的能力”。(21)
如果说联合国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代表了“广义派”的观点,倡导的主要是“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那么加拿大政府的观点则堪称“狭义派”的代表,强调的是“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即把重点集中在暴力威胁上。尽管加拿大政府有时也笼统地宣称人类安全指的是“人的权利、安全或生命免受广泛威胁的自由”,但在实践上,却强调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致力于“提高人们免于暴力威胁的安全”,包括公共安全、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冲突预防、治理与责任以及和平支持行动。此外,对人的暴力威胁还包括贩毒、地雷、种族纷争、国家失败、小型(廉价)武器交易等。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政府还主张,应该主要运用外交、经济手段以及情报与信息技术等软权力来应对这些威胁。(22)这类观点在学术界也不乏支持者,例如安迪·麦克(Andy Mack)等人也主张把威胁限定在政治暴力上(无论暴力威胁来自国家还是任何有组织的政治行为体),(23)并且认为,尽管其他威胁确实存在,但议题过于广泛虽有宣传价值,却会丧失分析价值。因此麦克及其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安全中心”在其发表的一项重要定量与定性分析成果中,把“人的安全”明确界定为“保护个人和共同体免于战争和其他形式的暴力”。(24)
2004年,著名的《安全对话》(Security Dialogue)杂志曾就“人的安全”这个概念咨询21名学者和政策专家的意见,结果得到21种大不相同的定义。(25)面对如此巨大的概念及相关理论分歧,一些研究者也曾试图对各种观点进行梳理和分类,目的是寻绎更加有效的研究线索与理论路径。例如,萨加伦·奈杜(Sagaren Naidoo)通过追溯其国际关系理论渊源,把有关概念分为两大派别:新现实主义者认为安全的概念必须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威胁;批评理论或后现代理论则不仅主张拓展威胁的内容,还主张涵盖更多的安全主体,包括个人、族群、文化群体和非政府组织等。克劳德·多德林(Claude Daudelin)则用三个平行轴来归纳各种概念:其一,“对威胁的界定”,即人们在安全这个标签下所罗列的各种威胁或危害。其二,“新的安全对象”,即个人、群体、国家或超国家等人们各自强调的安全主体或指涉对象。其三,“新安全工具”,即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手段、途径或机制。芬·汉普森(Fen O.Hampson)概括的三种类型则有助于了解某些“人的安全”概念与“人权”、“发展”等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或者混同:一是以权利为基础的界定方式,即以国际人权法为依据,主张个人安全生存的权利可以超越主权国家的权利;二是从个人所受到的各种暴力伤害的角度来界定,既包括传统的、与国家有关的暴力,更包括内战、反叛等新型暴力。三是以可持续发展问题为核心,即强调类似于199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所罗列的那些范围广泛的、传统上被划入“发展”范畴的问题。(26)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这些分类、总结除了再次说明人们关注点和判断标准的多样性,并未真正解决问题。由于迄今为止人们未能就“人的安全”这个概念达成足够的共识,因而既没有形成一套合理的学术分析框架,也无法给决策者提供有效的政策指导。
因此,厘清“人的安全”研究的学术边界,避免“泛安全化”,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人的安全”之内涵与外延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它究竟应该包含哪些价值?主要面临哪些威胁?这些价值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各种威胁的轻重缓急是什么?澄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开展相关学术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人类安全的众多定义虽然有一些共同点,例如,都认为安全的主体应该从国家转向人或人类,都强调非国家或次国家行为者在安全实践中的作用,都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持批评态度,一般都强调不能忽视非传统安全或非军事安全问题;许多内容基本上都与联合国《千年宣言》所强调的三大领域(免于匮乏、免于恐惧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有关,但总的来说,人们对于具体安全价值和安全威胁的理解还很不一致,并且过于宽泛。上述各类观点总体上的西方价值取向显而易见(“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还令人联想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此姑且勿论,但其中所反映的个人主观偏好和“泛安全化”倾向却值得注意。“仁者见仁”或者“各取所需”,实际上是谈论“人的安全”问题时的一个常见现象。因此,本文认为,在基本概念的厘定方面,有四个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由于学术边界不明确,导致学术理论研究困难。清晰的概念是理论和命题的基础。“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它必须反映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27)“人的安全”这种理念要成为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就必须概括出其独有的本质特征。但有关“人的安全”的各种定义,要么与“全球安全”等概念有不同程度的重叠,要么与“非传统安全”难以区分,要么成为“发展”、“人权”等概念的同义词。再者,人们在使用英文“human security”一词时,有的强调的是“个人的安全”,有的则是指作为整体的“人类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清晰,(28)意味着研究的对象不清楚。结果,“人的安全”这个概念似乎可以用来支持任何理论假说(或相反的假说),而这完全取决于特定研究者的偏好和兴趣。更糟糕的是,由于这个概念涵盖了人身安全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安全等内容,从逻辑上讲,人们实际上已无法确定某些社会经济因素与“人的安全”的改善或恶化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因素本身就是其定义的组成部分。(29)总之,要研究因果关系,就必须使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独立性。
第二,对于安全价值和安全威胁的界定过于随意,缺乏统一标准,因而难以形成共识。例如,上述作者显然认定某些价值比另一些价值更重要,却没有就此提出明确的理由。人们也可以认为其他价值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例如,巴耶派认为“身体安全”和“个人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并且把婚姻自由作为个人自由的一个例子,但这是否一定比诸如接受良好的教育等更重要呢?加里·金等人的缺陷则在于没有说明其五项指标与暴力冲突危害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其定义实际上排除了安全内涵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即免于暴力伤害。因此,这类尝试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如何缩减其内容以便建立一个更有分析价值的概念,而是确立一个能够用来衡量价值等级、进行价值选择的基本原则。(30)
第三,安全的目标过多并且轻重不明、缓急不分,要么可能使决策者做出错误选择,要么使他们无所适从。对决策者来说,由于资源、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他们不得不从众多目标中筛选出真正值得重视的问题,并寻找具体的解决办法。但各种安全概念不仅内容无所不包,而且往往没有区分众多安全价值、目标或原则的优先等级次序。不仅如此,“人的安全”的倡导者们大多强调这个概念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和“整体性(holism)”,在实践上,这意味着所有的安全利益或安全目标具有同等价值,只能“一揽子解决”,(31)而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例如,劳拉·里德等人在就“人的安全”提出一长串清单之后还特意告诫说:“这些相互重叠的类型并不代表某种从个人到国家、国际和环境权利的安全需求等级结构。相反,每个领域都与其他领域密切相关,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考虑具有内在联系。”(32)人们当然无法否认,人与自然的一切领域本质上都是相互联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需求、价值或政治目标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更不意味着决策者应该或者能够依靠有限的资源来追求各种相互竞争的目标。毕竟,“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成为国家安全议题”(33)或者国家决策者应该考虑的安全议题。
第四,安全价值的泛化,实际上还纵容了一种实用主义倾向。“人的安全”议题的某些倡导者有时不过是利用“安全”这个标签来服务于自己的需要,它们常常是“卖什么吆喝什么”或者“缺什么找补什么”,从而使“普遍”价值成了“特殊”价值的装饰品。
如果说某些概念的缺陷可能只是无心之过的话,在另一些场合,保持概念上的含混则是有意为之。界定“人的安全”所涉及的核心价值之所以困难,并不只是因为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很不一致,还因为概念的宽泛和含混有其实用价值,有助于把动机、目标不尽相同的政治行为体联合起来,各类组织、团体或个人都可以并且乐于从中各取所需,以服务于自己所倡导的事业或满足自己的价值偏好与利益诉求。一些行为体不过是想伺机谋取某些更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把渲染“人的安全”议题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因为,把某个议题上升到“安全”(在这个意义上即“国家安全”)的高度,可以突出其“紧迫性”,从而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并迫使政府提供资源。(34)而一个内容宽泛、意义含混而又陈义甚高、颇具道德号召力的概念,能够最大限度地缩小分歧、容纳各色人等的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精确定义的追求反倒显得有些多余了。“人的安全网络”在其多边外交活动中,很大程度上就是采取此种策略。例如,在2001年的部长级会议上,会议主席在总结陈词中宣称,该网络将致力于“加强人的安全,创建一个更加人性化的世界,让人们能够安全、体面地生活,免于匮乏和恐惧,拥有全面发挥其人类潜能的平等机会”。(35)
从某些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政策实践来看,它们把“人的安全”纳入其外交政策或外交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因为某些议题切合自己的需要,或者自己拥有更多这方面的外交资源,有助于扩大政治影响、提升自身形象。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加拿大和挪威都敏锐地意识到,把“人的安全”作为外交政策原则具有潜在的吸引力,是推动它们希望发挥影响力的某些议题的有效途径。例如,挪威关心的是自己拥有理论与区位优势的谈判与冲突解决问题,加拿大关注它率先倡导的禁雷问题,日本则乐于讨论国际发展问题。加拿大和挪威在90年代初竭力倡导“人的安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这有助于它们争取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游说活动。(36)一些欧洲国家还希望把“人的安全”作为一项指导原则,用来协调、整合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37)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以及各式各样的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也不断推出各种报告,根据它们对某些特定议题的偏好设定出不同的政策议程,以表达自己的诉求,彰显其存在的价值。于是乎,安全价值与安全威胁的清单越来越长,教育、公共卫生、水资源冲突、国际刑法、移民与难民、贩卖人口、性别与和平、全球化与发展等都成为讨论的主题。在某些情况下,“人的安全”已经沦为一种工具而不再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基本目标。
四 “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价值冲突与互补
“人的安全”确实是一种重要价值,从人文主义的视野来看,甚至可以说是最根本的核心价值。但问题在于,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现阶段,应该如何理解和处理“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等安全价值之间的关系?
人类所持有的文化价值观是塑造其安全观念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安全观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观,而安全观念无疑直接影响人们的安全策略。(38)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人们在安全的主体、内容、威胁、途径等方面有不同的价值偏重,“安全”一词被加上各种定语,从而衍生出一系列复合概念。(39)而且,在谈论各类安全问题时,“几乎所有世代、所有文明的人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其道德意义,表达他们关于尊重和维护、或侵犯和损害安全的是非判断与褒贬态度”。(40)
也许可以说,在20世纪后半期,人类的安全意识和安全价值曾出现过两次重要变化,一次是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为契机从国家安全到国际安全的转变,另一次便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国家主体向非国家主体、即人(类)的安全或全球安全的转变。后一个“转变”实际上并未完成。在理论的层面,不同的政治哲学与安全价值观仍处于矛盾、竞争状态,主要国际政治理论传统对国家、国际或人类(全球)安全的价值排序和相应的战略主张也大不相同。
“人的安全”观念是非传统安全和“新安全”观念的集中体现,并且与自由派国际主义的政治哲学和价值取向有更深的渊源。但其倡导者的思想成分实际上相当复杂。如前所言,尽管目的不尽相同,各种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或激进主义思潮也高举世界正义、人类安全或人的解放等旗帜,从而壮大了“人的安全”话语的声势。
“国家安全”则基本上是以现实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传统安全观念。尽管不断受到挑战,政治现实主义依然是当今国际政治尤其是国际安全领域的一种强劲有力的思想系统。从根本价值取向上讲,政治现实主义关注的是国家安全,而且主要是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并且把主权原则视为国家合法使用武力抵御外部军事威胁的根本依据),其他非国家安全主体或非传统安全议题并非其关注重点。不过,除了少数极端化形式,现实主义者一般都能认识到,过度或无限制的国际权势斗争不仅会危害特定国家的利益与生存,甚至可能摧毁主权国家所构成并在其中进行各类交往互动的国际体系。他们完全懂得,国家安全不仅取决于以自强、自助与竞争为特征的安全战略,也取决于基本的国际安全,即大多数国家独立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秩序与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41)换言之,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并无根本冲突。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主要不在目标上而在手段上。
但“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却要复杂得多。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辨析。
首先,国家安全和“人的安全”这两种安全关切或安全价值都有其合理性,但都没有理由无条件地居于绝对主导地位。
“人的安全”当然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基本目标和终极价值。一方面,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增多,人类共同体及其成员所面临的安全威胁确实有不断增多或加剧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包括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有了更高要求,对生活质量有了更多期待。因此,以人为本、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具有道德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然而,人既有个性也有社会性,作为个体的人往往相当软弱和无助。幸而人具有理性这一本质属性,因此既能够按照自然的法则合理地保存和造福自我,同时又具有与其他个体友好交往并结合成有序社会的天然倾向,这种倾向在现代世界还突出表现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创建、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国际社会的发展。因此,“人的安全”不是孤立的,与国家安全、国际安全乃至全球安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少在当前这个历史阶段,“人的安全”观念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替代其他安全观念。
民族国家体系已经走过了数百年的历程,在人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上,国家不仅处于实际的主导地位,国家本身也被赋予了道德价值和道德身份。按照近代西方以契约论为基础的国家学说,人类创建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走出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获得更大的个人安全与自由。按照当代西方社群主义的观点,社群(或共同体)本身就是一种“善”,也许是最重要的“善”。(42)道德以“共同意义”为先决条件,而共同意义又以共同尊重的社群为先决条件。国家实际上是范围更大的社群。(43)国家乃是人权的“容器”。(44)以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为核心的国家权利是个人权利的“集合形式”,(45)因此,对他国内政的不干涉原则是国家权利保护个人权利的必然结果。传统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观念,实际上也隐含着同样的意思,抵御外来军事入侵,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一个民族最大的共同利益。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国家安全的保障就是对其国民安全的保障。
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念与安全战略,确实忽视了许多非国家或次国家主体的安全需求,也不足以应对诸如环境恶化、流行疾病等外部非军事威胁。不仅如此,人们还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装暴力冲突主要发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而不是国家之间,而这些国家往往是所谓“脆弱国家(vulnerable/fragile states)”或“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46)国家治理失败往往伴随着政府与叛乱者或者叛乱者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武装冲突,大量平民尤其是妇女儿童则成为无辜的牺牲品。而对平民的主要暴力伤害者有时恰恰是警察、军队等国家机器,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尤其突出。换言之,国家(政府)本身也有可能成为个人安全的威胁来源。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同样根据契约论,包括现实主义经常引以为同道的霍布斯的契约论国家学说,国家及其统治者有责任保障民众的安全与自由,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成为安全与自由的障碍甚至破坏者,则统治者就失去了合法性。换言之,对于所谓“失败国家”的内部问题,国际社会有义务进行干预。
其次,尽管“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这两种价值取向在理论上存在紧张关系,在实践上也可能发生冲突,但如果处置得当,也可以相互兼容和互补,从而有助于提高各类主体的整体安全水平。
一方面,这两种安全关切所涉及的安全主体、安全价值和安全威胁以及相应的手段与途径都大不相同。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竞争关系,在国家实践的层面,也涉及价值排序和资源分配等问题。在国际政治的层面,则可能产生类似于“人权”与“主权”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众多经验事实表明,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严重的内部冲突或政治暴力,由于可能产生外溢效应,影响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安全乃至损害与之相距遥远但有着广泛政治经济联系的国家的利益,也有可能授人以柄,招致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无论是出于道德理由还是政治考虑)的干涉。此外,人民的安全与福祉、生存状态与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是国家认同、社会稳定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并不矛盾。
事实上,“人的安全”理念及其实践已被许多人视为践行《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宪章》、《日内瓦公约》、《渥太华禁雷公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国际文献的相关原则,确立新的全球与国家治理规范的一种途径。这不仅是出于伦理道德上的理由,也是出于现实政治考虑,因为发达国家以及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改善人们的生活处境、促进“人的安全”,确实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47)
五 伦理与政治抉择的原则与途径
显然,由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价值的多元性、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国家或国际社会应对安全挑战的资源的有限性,各种安全观念之间的竞争还会继续。从前面的讨论可知,有关“人的安全”的理论与实践,有几个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其一,人们对“人的安全”这个概念的理解还很不一致,大多数定义边界模糊、内容宽泛。其二,许多人没有区分“人的安全”所涉及的众多要素的价值等级和优先次序,不切实际地期望一揽子解决。其三,基本上没有厘清“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等其他安全价值之间的关系,其倡导者往往片面、孤立地强调“人的安全”,忽视了其他安全价值以及各类价值之间的潜在冲突。其四,“人的安全”话语本身具有鲜明的西方价值取向和自由主义色彩,在实践中有凌驾于主权国家安全利益之上的倾向。其五,所谓安全关切的主体从国家到个人的“范式转换”,过度贬低了主权国家在应对各类安全挑战中的积极作用。
这些问题尤其是后三个问题,基本上都源于一个根本的理论误区和思想盲点,即严重忽视或背离了现代世界体系仍然是民族国家体系这个基本现实。而这正是本文主题所强调的“国际政治视角”的意义所在。
不可否认,安全的内涵在当代已大为扩展,安全议题与安全威胁也日趋多样化。仅以21世纪以来的国际重大武装冲突为例,民族、部族问题已成为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恐怖主义也成为当代全球冲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当多的暴力活动伴随着各种犯罪行为,包括有组织跨国犯罪;贫困化、人口激增、环境生态恶化、土地与资源竞争等问题已成为冲突的重要起因,这在非洲地区最为突出;国家内部冲突归根结底是社会危机的体现,表现为民族(种族)矛盾、政治集团权力斗争、社会缺乏公正等问题所导致的政府一社会关系的严重紧张与冲突,以至于出现诸如科特迪瓦、刚果(金)、苏丹、伊拉克、索马里等大量所谓“失败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的内部冲突都有外部干涉的背景,与一些西方国家以民主、人权为由,谋求政权更迭和“颜色革命”有关,其中,超级大国更是表现出单边主义与“黩武主义”倾向。(48)
面对众多的安全价值,人类常常会陷入各种两难困境,因此不得不做出选择,既包括伦理判断与价值选择,也包括政治权衡与政策选择。而要选择就必须有原则或标准,既包括价值标准也包括利益标准。国际政治的实践伦理,其实质就是在政治实践中合理界定各种价值的等级,解决由于价值冲突所造成的道德两难问题。而安全价值的辨析,归根结底是要确定安全的具体目标并根据其重要性进行合理的价值排序,以便寻求最佳结果。
从这个目的出发,本文在此提出一个理解和处理“人的安全”与国际安全等安全价值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它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一般情况下应遵循的基本价值选择标准,即对各种安全目标进行价值等级排序;二是特殊情形下应对价值冲突的策略或例外措施,即根据主权平等与不干涉等国际法核心原则,并借鉴正义战争理论的分析模式,尝试就如何解决诸如“人与国家”、民族自决与国家统一以及主权与人道主义干涉等当代国际政治中最突出的、并且与“人的安全”有关的价值冲突问题,提供一套解决路径与基本原则。简言之,前者的核心是分清各类安全价值的主次与轻重缓急;后者的关键问题是合理选择安全手段,防止滥施国际干涉。
(一)兼顾各类安全价值,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
“人的安全”必须与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等各类安全目标放在一起权衡,才能得到合理的定位与恰当的处理。从国际政治实践的角度看,如果兼顾价值合理性与现实可能性,可以把当代安全的众多目标分成重要性依次递减的四个层次。(49)
第一个层次,核心是“和平”问题,即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最起码的国际安全,目的是使国际社会处于总体和平、有秩序和有基本行为准则的状态,包括维护国家体系本身的存在、国家的独立生存与主权完整、避免重大战争、限制国际暴力以及使国际承诺和协议得到遵守。其中避免重大战争和限制国际暴力属于“国际冲突”的预防与管理范畴。
第二个层次,核心是狭义的“发展”问题,即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经济处境有关的问题。其中的关键,是在推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促进国际经济正义、包括交换正义与分配正义,目的是消除贫困、缩小国际国内贫富差距,避免由于国际经济秩序与结构严重失衡所导致的国际与国内冲突。(50)由于“欠发达”实际上是许多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因此促发展具有“冲突预防”的性质。
第三个层次,核心是“国内冲突”的管理问题,即适时运用合理、有效的措施或机制,管控诸如国家治理失败以及民族、种族或宗教矛盾所引发的国内暴力冲突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象。与第一个层次不同,这里主要涉及那些可能影响国际安全与秩序稳定的国家内部冲突,属于国际社会在特殊情况下的例外与应急措施,因此必须严格界定干预的前提、手段、实施主体以及合法性来源。
第四个层次,核心是广义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即人类整体生存环境与生存质量的改善和人类文明的延续问题,包括应对诸如环境、能源、疾病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所有国家、所有人的长远利益,因此需要国际社会长期的共同努力。
也就是说,在解决“人的安全”问题时,尤其是当“人的安全”目标与其他安全目标发生矛盾时,原则上应该按照上述框架来确定其轻重缓急次序,以避免本末倒置或得不偿失。但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虽然这几个层次在价值等级和现实可能性上有轻重缓急之分,但很大程度上又是相互联系的。由于各类问题的联动性与外溢效应,“人(类)的安全”与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在确保第一个目标层次的同时,必须兼顾后几个层次。而且这种价值排序也不能绝对化,在特殊情形下容有例外。从更抽象的角度说,对于国家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或者国家个体利益、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与人类共同体(及其成员)利益,亦应尽可能兼顾和协调,在实难兼顾和协调的场合,其轻重缓急次序也“当依具体情况而非抽象原则来确定”。(51)例如第三个目标层次,由于其临时性、特殊性以及争议性,故一般只能处于相对次要地位,但有时又因其暴烈性或紧迫性,如出现大规模生命损伤并且有急剧蔓延或恶化的趋势时,也可能需要优先考虑和处理。但正如下文将讨论的,这在实践中仍然需要有一套合理的判断标准和行动准则。
本文认为,“人的安全”的首要目标是“免于暴力”。与人类全面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其他目标,尽管具有长远意义,但与主权国家独立生存等国家安全目标以及国际体系与秩序稳定等国际安全目标相比,在现有历史条件下并不具有优先价值,故不能以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为代价来片面追求“人的安全”。
总之,在处理“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等其他价值的关系时,既不能忽视基本的价值序列,又要视具体情况酌情对待。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与非传统、人与国家、个体与共同体、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等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已显得过于简单化。以国家安全为“核心”,其他诸种安全价值为“外围”的模式,总体上更加切合国际政治的现实,但并不具有绝对的合理性。
(二)合理选择安全手段,防止滥施国际干涉
对“人的安全”的不同界定,不仅事关安全价值的范围、安全威胁的类型及其轻重缓急次序的认定,实际上还影响安全战略与安全政策,即应对威胁的手段、策略或机制的选择。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面对各种安全价值的冲突,决策者或政策实践者们的态度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试图兼顾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二是完全排斥“人的安全”理念;三是只以“人的安全”为理由来证明其政策的正当性,从而包装、掩盖其真实的政治、经济或战略目的。(52)
对价值和威胁的不同理解,本身就预示了手段的选择。如果对“人的安全”做广义的界定,例如理解为“所有人类生命的核心价值”所面临的威胁之类,由于其内容的主观性和多样性,手段(包括预防性手段)当然也就多种多样乃至于无限。相比之下,“狭义派”在手段的选择上似乎更容易一些,但也并不简单。尽管他们把威胁限制在政治暴力上,但他们就“管控”国内与国际冲突所提出的对策也涉及众多经济、社会和政治措施。(53)
“人的安全”概念本身的狭义与广义之争,在实践中主要涉及矛盾的主次以及手段的选择、资源的分配与现实可能性问题。如果说“免于恐惧”的核心是避免暴力尤其是国内政治暴力,“免于匮乏”的核心则是谋求发展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当然并不排斥前者)。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消极自由”,后者则是“积极自由”。(54)对此,保利娜·克尔(Pauline Kerr)指出了一种颇具创意的协调途径。保利娜认为,两者实际上具有内在联系,鉴于欠发达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内部暴力冲突的一个重要、普遍的根源,因此,可以将前者视为自变量,后者为因变量。(55)也就是说,一方面,“人的安全”涉及内容广泛的欠发达问题,例如经济不发达、政府能力与治理水平较低、腐败、社会分化等;另一方面,“人的安全”问题又突出表现为各种政治暴力威胁,例如政府实施的(超越法律界限的)暴力、社会群体之间的暴力。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与前者有关。“发展”有助于避免“暴力”的出现;反过来,“暴力”如果得以避免,“发展”就更有机会,从而有可能进入良性循环,否则便陷入恶性循环。例如,贫困、疾病和治理不善可能共同导致政治暴力,而政治暴力反过来又会加剧贫困、疾病与治理危机。
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前一类问题更多地属于需要长期努力的“冲突预防”范围,参与主体包括当地、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各类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手段与途径可能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文明进程、治理机制、法制建设、公民社会等方面的相关措施。后者则更多地属于需要及时应对的“冲突管理”范围。其行为体可能涉及冲突各方、当地政府、地区与国际组织,手段与途径包括外交、谈判、第三方斡旋乃至维和力量的使用等。(56)这同时还意味着,前者只能通过经济、技术等手段或其他软权力来加以调节和改善,只有后者才能涉及强制性措施。而且,前者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促发展”,而不是单纯为了满足局外行为体的利益需要,后者的目的只能是限制暴力并防止外溢,而不是谋求政权更迭、扶植盟友等战略利益。
这就涉及安全策略或手段之争中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如何看待主权国家的作用,二是如何看待国际干涉。
1.正确理解国家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如前所言,在某些情况下,对于人们安全的直接威胁,包括暴力和其他威胁,有时恰恰来自国家(政府)。因此,“人的安全”的许多倡导者认为,国家本身就是问题或者问题的一部分,如果继续把国家视为世界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安全主体或各类安全的代理者,人的安全就难以完全实现,因此,国家作为“人的安全”的“手段”是很成问题的。
这种把国家与个人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显然过于片面。且不论国家的根本职能是为一国社会提供公共秩序和安全保障,在现实中,并非所有国家的行为或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观念都与“人的安全”背道而驰。而且,国家(政府)实际掌握着应对各种安全挑战的主要资源,无论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还是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其作用一般都是决定性的。例如,国家或政府在创造和分配财富方面的职能,显然是国际治理机构、非政府组织或公民社会所无法替代的。实际上,在应对环境恶化、流行疾病蔓延、全球变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国家依然是主要的依靠力量。而且,国家本身是一个有机体,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绝对的“好国家”或“坏国家”。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如果假以时日,许多国家的治理规范与治理水平都有改进的可能。
但另一方面,在应对日益多样化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方面,国家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也不是万能的,还必须借助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以非政府组织为例,在国内层次上,非政府组织作为“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那块制度空间”,可以弥补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不足,代表民众直接参与公共管理,帮助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此外还可以利用其多样化的手段和灵活的机制,合理利用人才、技术、信息等各种资源,为民众和市场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在全球层次上,国际非政府组织由于范围广泛、人员众多,拥有强大的人力、物力和信息资源,组织机构和活动方式灵活机动,因此在实施国际救援与社会救济,推动环境、生态与人权保护,促进国家间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帮助建立国际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传播与融合,促进国际和平与人类共同利益等方面,都具有各国政府和企业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
而且,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至少有三个:一是影响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的议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国体系内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与合作机制不断加强。迄今已有2000多个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享有正式咨询地位,有1500多个非政府组织同联合国公共信息部建立了正式联系。这类联系机制已成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和影响联合国决策的重要方式。二是推动有关国家政府的决策议程。无论是全球性、地区性还是国家范围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都日益重视与有关国家政府的联系与合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公共政策。三是在特定问题领域独立发挥作用,弥补政府能力的不足。例如,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促进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所开展的活动,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扶贫,从而为消除贫困做出了积极贡献。
因此,在“人与国家”的天平上,极端的看法是不可取的。不能脱离具体情况,简单地主张国家主权(安全)至上或个人权利(安全)至上。在“人的安全”尤其是与“发展”有关的安全问题上,既不能无视国家的主导作用,也不能单纯依靠国家的力量,全球与地区性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国际治理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体也可以与国家一道发挥作用。至于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是否会产生紧张关系,归根结底在于后者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是否能够遵守有关国家的法律规范或者坚守主权与不干涉原则等国际法底线。
2.严格界定干涉的前提与原则
如果说,在“发展”问题上,有关目的与手段的道德评判与政策选择相对较为容易,而往往与政府“失能”甚至“失德”有关的国家内部暴力,则使得人道主义干预尤其是武装干预成为国际社会激烈争论的焦点。对此,理论分歧不仅发生在“国家中心论”(国家安全论)与“人类中心论”(人的安全论)各自的拥趸之间,也发生在后者内部。作为“国家中心论”的代表,现实主义者认为,人道主义干预可能有加剧和延长冲突、导致更大人道主义灾难的危险。他们更担心的是,如果肆意践踏原本有助于防止国际冲突的主权原则,将严重破坏国际秩序,从而危害国际安全。“人类中心论”则认为,主权原则固然重要,但国际秩序与稳定也有赖于国家内部人民的安全。有人甚至宣称:“如果国民没有安全,国家也不可能有安全。”(57)而且,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一国内部人民的不安全状况可能会对周边乃至其他地区的国家和人民产生影响,因此通过干涉来改善国内状况、维护人的安全有助于国际稳定。实际上,这也是联合国在支持干涉行动时的主要理由之一。
然而,这种论证逻辑产生了一个悖论:如果干涉的理由是维护或恢复国际秩序与稳定,那么判断问题轻重缓急的标准就不再是国内冲突或人道灾难本身的严重程度,而是其可能产生的外部效应或国际政治影响。换言之,主要考虑的是国际安全(或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而不是“人的安全”。(58)因此,无论干涉还是不干涉,显然还需要有更多的理由和标准。
为了避免使用争议很大的“人道主义干预”这个概念,2001年加拿大“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ICISS)”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使用了“保护的责任”这个标题,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简称《成果文件》)也采用了这个概念。报告首先就指出,主权原则意味着使人民免于暴力威胁的责任主要在于国家本身。只有当国家不愿或无法履行这一职能时,“不干涉原则才能让位于国际保护的责任”。(59)值得指出的是,报告实际上也承认,人道主义军事干预只是一种“例外和非常规措施”,因此必须严格设定其前提与条件。
2011年以北约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安理会决议后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被西方称为“保护的责任”的首次实践,但国际社会对此颇有争议。“保护的责任”一般是指,当一国当局无力在本国避免大屠杀、战争罪行、种族清洗以及反人类罪行时,国际社会可以进行干涉。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力量可以无条件地进行干涉。联合国《成果文件》指出,“保护的责任”有三个支柱:其一,主权国家是保护其公民的最重要主体。其二,国际社会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有关国家政府承担责任的能力。其三,国际社会的干涉行动必须在《联合国宪章》框架下进行。而且,“保护的责任”还只是发展中的一项国际规范而非国际法原则。由于该概念没有涉及在实施保护性干涉过程中的责任以及适当终结和事后问责机制等问题,因此还很有争议。此外,“保护的责任”在实践中也存在着扩大化和被滥用的现象,例如试图改变他国政权,或者出于政治考虑把他国打击有组织暴力犯罪的合法行为定义为人道主义灾难,为国际干预制造舆论。(60)
对于人道主义干预这个最具争议的问题,一种可能的解决路径,是参照现有国际法关于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并借鉴“正义战争”理论的分析模式,为作为例外措施的国际干涉确立如下标准。
首先是“合法权威”,其组织实施者必须是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个别国家的单边行为,甚至上述加拿大报告所认可的诸如北约等地区性组织的行动,则不具备这样的普遍权威。
其次是“正当理由”,即干涉的前提或“门槛”,是出现大规模生命损失或大规模“种族清洗”。即使稍做扩展,按照迈克尔·沃尔泽所做的概括,历史上也只有三类涉及武力运用的干涉行为具有合理性并且较少争议:一是国际社会帮助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二是以人道主义干预制止大规模屠杀和种族清洗;三是在内战中以反干涉抗衡外部势力的干涉。(61)在全球化和安全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也许还可以加上一种类型,即在国家治理失败导致一国社会严重失序,陷入暴力冲突,出现大规模生命损伤并极有可能危及地区稳定与国际安全的情况下,国际社会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除此之外,国际社会迄今尚未就其他干涉理由形成普遍共识。
最后是四项具体原则:一是“正当意图”,即仅限于制止或避免人类伤害,而不是追求诸如民主拓展、政权改造、扶植盟友等目的。后者显然是超出国际法与国际伦理界限的强权行为,不具备任何伦理与法理上的正当性。这实际上是假定某种意识形态永远正确,把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当做宗教使命来加以推广,缺乏对多元文化与差异政治的体认与宽容。而归根结底,“最佳政治安排与生活在这种安排中的人民的历史和文化是密切相关的”。(62)二是“最后手段”,即必须首先尝试采取其他非强制措施,武力干涉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三是“手段相称性”,军事干涉的规模、期限和强度保持在必要的最低限度。四是“合理的前景”,即干涉有成功达到合理目的的可能性,不能适得其反。(63)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人的安全”的众多论述,似乎都在有意无意间抹杀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界限。实际上,“人的安全”的宽泛定义所涉及的许多问题,甚至包括某些个人权利问题,许多情况下属于一国内部治理、社会发展或公共安全范畴的问题,不一定需要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或者成为国家—政府关心的首要问题,更不一定是国际安全问题或国际社会应该干涉的问题。换言之,人们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主权与人权、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关系,注意到这些不同的价值各有其合理性与适用范围。试想,如果那些几乎无所不包的安全内容都可以成为国际干涉的理由,岂不天下大乱?因为这完全无视人类迄今为止依然普遍珍视的另一项重要价值、即民族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势必动摇现代国际法的基石,直接损害民族国家体系本身的存续和国际社会基本秩序与交往规范的维系。
因此,对于“人的安全”这个概念,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仍然心存疑虑。一方面,它们担心这个概念过于宽泛以至于被滥用;另一方面,它们也担心它过于狭窄,即过分专注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政治冲突,从而忽视发展问题,乃至于与“人权”这个概念一样,成为西方大国干涉非殖民化国家内部事务,推广自身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进而颠覆国家主权原则的工具。
即使是迈克尔·沃尔泽这类强调共同体价值的西方社群主义理论家也强调,国际干涉行为只能是出于挽救生命、自由及制止大屠杀等暴行,即捍卫基本人权的目的,“真理”、“正义”等意义含混的口号不能成为干涉的理由。因为一般正义原则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如医疗保险的分配),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普遍性问题,而是与地方条件密切相关了。(64)与此相关的一个典型问题是,尽管“自决”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最低限度道德原则,然而该原则不仅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解释,在实际运用时还必须考虑各种具体情况。(65)例如,对于少数民族自决问题或者民族分裂主义问题所造成的政治伦理困境,衡量“自决”原则是否适用,必须兼顾秩序与正义两个维度,为此在进行道德评判与政治选择时必须遵循三项标准:其一,现状是否极端不正义以至于必须改变。其二,是否完全没有和平调整与改良现状的其他途径。其三,民族分裂给该国或该地区其他相关民众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伤害以及引发的国际动荡是否过于严重。此外,同样还可以借鉴“正义战争”理论的相关原则,考虑到诸如分裂主义“成功可能性”有多大,手段、目的与结果的“相称性”,支持分裂是否会得不偿失、造成更大人道灾难等因素。(66)
总之,即使出于维持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稳定的需要,国际干涉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也必须严格界定和分辨干涉的前提与条件、目的与手段、动机与后果,尤其要区分军事干涉、经济制裁、外交压力等强制性手段以及经济技术支持、人道主义救援、人文社会发展合作等积极措施各自的适用对象与条件。(67)由于后果往往难以准确预料,必须慎用武力等强制措施,并且充分考虑干涉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而由于动机、目的具有主观性,更加难以确证,还要谨防以促进民主、人权或“人的安全”、捍卫国际法准则、维护国际秩序与地区安全等堂而皇之的理由干涉他国内政、谋取自身战略与经济利益的行为。为此,国际社会不仅要坚持道德评判标准的权威性和一致性,还要重视诸如联合国授权等干涉行动的合法性来源。
六 结论
从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四个基本结论:第一,“人的安全”是人类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价值,“人的安全”概念是对各种新安全挑战的自然反应。但在现有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的安全价值具有多元性,面临的安全威胁也具有多样性。“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无法相互替代。第二,“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既可能发生冲突也存在兼容、互补的可能性。促进“人的安全”有助于社会稳定从而巩固国家安全,但这个问题有时也可能成为国家主权与安全遭到破坏的原因或借口。国家总的来说仍然是“人的安全”或“人权”的“容器”,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成为其障碍甚至威胁的来源。第三,国家仍然是应对各类安全挑战的主要行为体。在解决“人的安全”问题上,既不能轻易否定国家的主导作用,也不能单靠国家的力量。人类的共同安全既有赖于民族国家政府层面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借助国际治理机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第四,在以民族国家体系为背景的安全实践中,必须兼顾国际体系总体和平、国际经济正义、人类全面及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内冲突管理等不同层次的安全需求,但同时也要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并根据威胁的性质合理选择安全的手段、策略或机制,对于必要的国际干预措施,必须对其合法权威、正当理由、合理意图等要素进行严格界定,防止滥施国际干涉特别是武力干涉,从而捍卫以主权与不干涉原则为核心的国际法基本准则,维持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稳定。
[收稿日期:2013-12-21]
[修回日期:2014-01-15]
注释:
①关于“人的安全”概念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关系,详见Jennifer Leaning and Sam Arie,Human Security: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 Setting of Crisis and Transition,Harvard Centr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Working Paper No.8,2001;与西方人权理论的联系,详见Lloyd Axworthy,"Human 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Putting People First," Global Governance,Vol.7,No.1,2001,pp.19-23; Emma Rothschild,"What Is Security?" Daedalus,Vol.24,No.3,1995,pp.53-98。
②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8页。
③详细讨论可参见Thomas Weiss and Leon Gordenker,NGOs,the UN,and Global Governance,Boulder:Lynne Rienner,1996; Ralph Pettman,"Human Security as Global Security:Reconceptualizing Strategic Studie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1,No.3,2005,pp.137-150.
④J.Peter Burgess,ed.,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New Security Studies,London:Routledge,2010,p.39.
⑤例如Richard Ulman,"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8,No.1,1983,pp.129-153。
⑥这方面的重要论述包括Caroline Thomas,The Environ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2; Daniel Deudney,"The Case against Link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Millennium,Vol.19,No.2,1990,pp.461-471; Daniel Deudney and Richard Matthew,eds.,Contested Ground: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the New Environmental Politics,Binghamt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
⑦有关代表作包括Ronnie D.Lipschutz,On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Williams,ed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cepts and Cas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 Barry Buzan,et al.,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Lynne Rienner,1998。
⑧J.Peter Burgess,ed.,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New Security Studies,p.48.
⑨一些代表性的定义,可参见Taylor Owen,"Human Security:A Contested Contempt," in J.Peter Burgess,ed.,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New Security Studies,p.41。
⑩Michael Pugh,Regeneration of War-Torn Societies,London:Macmillan,2000,p.21.
(11)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me,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4,New York,1994,p.22.
(12)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me,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4,pp.22-23.
(13)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me,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4,pp.23-25.
(14)Jorge Nef,Human Security and Mutual Vulnerability,Ottawa: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1999,p.25.
(15)Majid Tehranian,ed.,Worlds Apart:Human 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London:I.B.Tauris Publisher,1999,p.39,p.47.
(16)Sabine Alkire,"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Human Security," Harvard:CRISE Working Paper 2,2002,p.2,http://r4d.dfid.gov.uk/PDF/Outputs/Inequality/wp2.pdf,登录时间:2013年12月20日。
(17)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的推动下于2001年在纽约成立。该组织独立于联合国系统,其领导人是前联合国难民高级委员会高级专员绪方贞子(Sadako Ogata)和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8)Caroline Thomas and Peter Wilkin,eds.,Globalization,Human Security,and the African Experience,Boulder:Lynne Rienner,1999,p.3; Caroline Thomas,"A Bridge between the Interconnected Challenge Confronting the World," Security Dialogue,Vol.35,No.3,2004,p.353.
(19)Roland Paris,"Human Security: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6,No.2,2001,pp.87-102.
(20)Gary King and Christopher Murray,"Rethinking Human Security," Harvard University,May 4,2000,p.8,http://Sking.harvard.edu/files/hs.pdf,登录时间:2012年10月2日。
(21)Kanti Bajpai,"Human Security:Concept and Measurement," Kroc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 No.19; OP:1,University of Notre Dame,August 2000; Kanti Bajpai,"An Expression of Threats versus Capabilities across Time and Space," Security Dialogue,Vol.35,No.3,2004,pp.360-361.
(22)J.Peter Burgess,ed.,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New Security Studies,p.43.
(23)Andy Mack,"A Signifier of Shared Values," Security Dialogue,Vol.35,No.3,2004,pp.366-367.
(24)Human Security Centre,Human Security Report 2005:War and Peace in the 21st Centu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367.
(25)J.Peter Burgess and Taylor Owen,"Special Section:What Is Human Security," Security Dialogue,Vol.35,No.3,2004,pp.73-115.
(26)Taylor Owen,"Human Security:A Contested Contempt," p.42.
(27)把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比如,从白马、白纸、白雪等事物里抽出共同特点,就得出“白”的概念。
(28)概念的内涵,即所反映的事物之本质属性的总和;外延,即所确指的对象的范围。
(29)Roland Paris,"Human Security: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pp.87-102.
(30)Roland Paris,"Human Security: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pp.87-102.
(31)Roland Paris,"Human Security: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pp.87-102.
(32)Majid Tehranian,ed.,Worlds Apart:Human 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p.53.
(33)Roland Paris,"Human Security: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pp.87-102.
(34)一个突出例子,参见David Sanger,"Sometimes National Security Say It All," New York Times,Week in Review,May 7,2000,p.3。
(35)"Chairman's Summary," Second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Human Security Network,Lucerne,Switzerland,May 11-12,2000,转引自Roland Paris,"Human Security: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pp.87-102。
(36)Astri Suhrke,"A Stalled Initiative," Security Dialogue,Vol.35,No.3,2004,p.365.
(37)Taylor Owen,"Human Security:A Contested Contempt," p.47.
(38)参见石斌:《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1期,第22页。
(39)关于安全主体与内容的一种较为完整的概括,可参见Barry Buzan,et al.,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pp.5-7。
(40)时殷弘:《国际安全的基本哲理范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178页。
(41)参见石斌:《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1期,第26-27页。
(42)迈克尔·沃尔泽著,褚松燕译:《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页。
(43)Michael Walzer,"The Moral Standing of States:A Response to Four Critic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9,Issue 3,1980,pp.209-229.
(44)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New York:Basic Books,1992,p.61.关于沃尔泽的国际伦理思想尤其是正义战争思想,详见张书元、石斌:《沃尔泽的正义战争论述评——兼论美国学术理论界有关海外军事干涉的思想分野》,载《美国研究》,2007年第3期,第116-133页。
(45)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pp.52-54,p.88.
(46)这些都是源自西方的概念。自2005年起,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和美国和平基金会(Fund for Peace)每年还共同编制《失败国家指数》(Failed States Index),其中运用冲突评估系统工具(CAST),通过评估12项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指标,对各国总体的社会稳定性进行排名。排在前60位的国家被称为“脆弱国家”,它们对自然灾害、战争和经济衰退等打击的抵抗性较弱,社会稳定容易受到影响的国家。其中情况最为严重、处于崩溃边缘的则是“失败国家”,表现为社会内部秩序极度混乱,常伴有武装割据、暴力冲突甚至种族清洗,甚至丧失对领土的实际控制或者无法完全掌握合法动用武力的权力。2005-2013年的排名情况,参见http://ffp.statesindex.org/,登录时间:2013年11月15日。
(47)Allan Collins,ed.,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93.
(48)李少军:《全球重大武装冲突:现状与走势》,载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6页。
(49)以下关于安全目标层次的具体分类,与笔者原先的看法已经有所不同,但其中所遵循的原则仍然一致。参见石斌:《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1期,第36-37页。
(50)详见石斌:《秩序转型、分配正义与新兴大国的历史责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70-99页。
(51)时殷弘:《国际安全的基本哲理范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187页。
(52)Allan Collins,ed.,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p.91.
(53)Allan Collins,ed.,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p.96.
(54)按照某些和平研究者的分析框架,大概还可以把它们分别视为旨在消除“直接暴力”的“消极和平”和全面消除“结构性暴力”的“积极和平”。参见John Galtung,"Peace,Violen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6,No.2,1969,pp.167-191。
(55)Pauline Kerr,"Human Security," in Allan Collins,ed.,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p.98.
(56)Pauline Kerr,"Human Security," pp.99-100.
(57)这是芬·汉普森(Fen Hampson)等人的看法。参见Allan Collins,ed.,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p.96。
(58)Allan Collins,ed.,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p.97.
(59)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Ottawa: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entre,2001,p.xi.
(60)苏长和:《“保护的责任”不可滥用》,载《解放日报》,http://news.sina.com.cn/w/2012-02-08/070023898810.shtml,登录时间:2013年12月2日。
(61)此外,沃尔泽还指出,正义的意图并不能自动保证正义的结果,何况干涉动机不纯是常见的事实,因此即使干涉确属“绝对必需”,也应以尊重被干涉国的基本权利为先决条件,并尽可能等同于不干涉,即把干涉行为造成的消极影响降至最低。参见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p.90,p.104。
(62)迈克尔·沃尔泽著,袁建华译:《论宽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63)关于“正义战争”的分析框架,参见张书元、石斌:《沃尔泽的正义战争论述评——兼论美国学术理论界有关海外军事干涉的思想分野》,载《美国研究》,2007年第3期,第116-133页;周桂银、沈宏:《西方正义战争传统及其当代论争》,载《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3期,第22-30页。
(64)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第108-115页。
(65)但沃尔泽也强调,自决原则既要求承认差异,又需要对特殊主义有所节制。参见Michael Walzer,Thick and Thin: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London:Notre Dame Press,1994,p.x。
(66)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时殷弘:《中西伦理传统与当代国际干涉》,载《学术界》,2000年第4期,第74页。
(67)关于经济制裁这种强制性仅次于武力使用的常见手段,同样可以根据国际法原则并借鉴正义战争理论框架,确立一套合理与“正义制裁”的原则,详细讨论参见石斌:《有效制裁与“正义制裁”——论国际经济制裁的政治动因与伦理维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第24-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