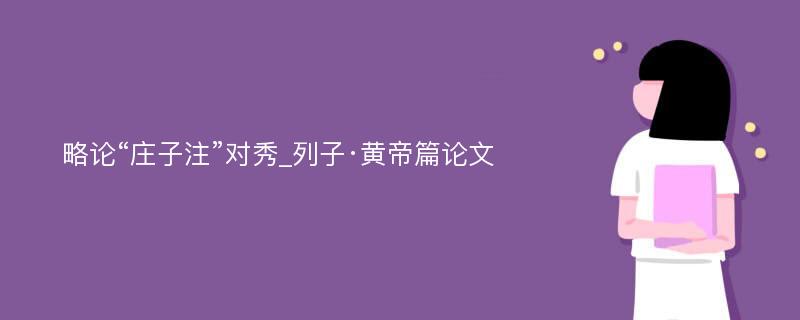
向秀《庄子注》别本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别本论文,庄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向秀、郭象两家《庄子注》的关系问题,历来颇有争议,并曾长期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在讨论中,由于立场的差异和资料的欠缺,一部分学者,根据《晋书·郭象传》,主张“盗窃说”,认为郭注是郭象窃向注以归己有,应把今本《庄子注》的版权判归向秀,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述广说”,认为《晋书·向秀传》所载郭注是对向注“述而广之”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反对“盗窃说”。显然,讨论的双方实际上都认可了一个理论假定,即以“述广说”和“盗窃说”是非此即彼、绝对排斥的。但这一预设的前提能否成立呢?二说能否并存呢?本文拟从向秀《庄子注》别本(简称向注别本)的角度对此略加探析,以求正于方家。
一、向注别本问题的提出
魏晋以前,《庄子》长期默默无闻,汉人论道家多言黄老而少言庄子;到了魏晋之际,因应着时代的需要,《庄子》突然流行起来,取代《老子》,成为当时士人关注的中心。因着《庄子》的流行,其注家也随之多了起来。继孟氏、崔撰、司马彪等同时或之后,向秀和郭象也先后注解《庄子》,分别有各自的《庄子注》,这是中哲史上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就向郭二《庄子注》,同一部《晋书》却有着不同的说法。
依《晋书·向秀传》,其记载是:
“……。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世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依《晋书·郭象传》,其记载则是:
“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这两种记载,有一致处,如都承认向秀在郭象之前注解过《庄子》,且向注与前注比较,在内容上别具一格,“发明奇趣”、“妙演奇致”等,在流行后亦甚有影响,“振起玄风”、“大畅玄风”云云;但比较起来,二者的差异较为明显:1.《向秀传》认为向秀注《庄》“已成”,已流传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世也”),而《郭象传》则认为向秀注《庄》未成(“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尽管有“别本迁流”,但“其义零落”,没有于向秀生前在社会上流行并发生影响(《郭象传》所言之秀注的影响当是秀注别本所致,与原本无关);2.在向、郭二注关系上,《向秀传》认为郭注是在向注基础上的“述而广之”,有推广、提高和发展,当然其义非一而有别,《郭象传》则认为郭象是窃向注为己有,不过补《秋水》、《至乐》二篇注,易《马蹄》注,其余只是点定文句,并“其义一也”;3.在郭象其人上,《郭象传》认为象“为人行薄”,《向秀传》则对此未加评说等。这些一致和差异处,学界都曾注意到,并对它们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讨论;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它的差别处未曾被注意到,且有助于向、郭二注问题之解决呢?
仔细比较《晋书》二《传》,我们认为,这个差别之处是有的,二《传》所指示的向秀《庄子注》的流行过程是不同的。
根据《向秀传》,向秀因“历世才士”虽观《庄》而“莫适论其旨统”,故作《庄子注》,其注因“发明奇趣”,故成书后在社会上流行且影响深远,“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世也。”一直到了惠帝之世,郭象在流行向注本的基础上才“述而广之”,推出自己的《庄子注》,以与向本并列;而在惠帝其时之前,向本是一直单独流行的。因此,《向秀传》所提出的向秀《庄子注》之流行过程,用箭头表示,应该是:向秀成书、向本流行→郭象在向本基础上“述而广之”→郭本出,二本并存→向本佚失。在这条向秀注本流传线路中,不存在向注别本。
根据《郭象传》,向秀注《庄》,尽管其注文“妙演奇致,大畅玄风”,但未曾注完即“早卒”且“其义零落”,不曾在社会上流行,但有别本迁流。郭象见及向秀注本,以其不传于世,遂窃为己有,并略作“补充”和“点定”即在社会上推出。只是在郭本流行之后,向注别本流出并与郭本并列,才揭开了郭象“盗窃”向注的事实和他的“为人行薄”。在《郭象传》中,向秀《庄子注》的流行过程,用箭头表示,则是:向秀早卒,其义零落→郭象窃为己有→郭本流行→向别本出,二本并存→向本佚失。在这条向注本流传线路中,存在向注别本。
显然,在这两条不同的流行线路中,向注别本的存在与否是一个关键。如果不存在向注别本,向本已先于郭本在社会上流行,郭本则只可能是在向本基础上的“述而广之”而不可能是“窃为己有”,《向秀传》的记载就是确实的,应为郭象恢复名誉;相反,如果向注别本是存在的,且如果向注别本即是向注原本(在内容上),那么,不论它与郭注本相比较的具体差异如何,它都证实了郭象“为人行薄”窃向注原本为己有的记载,两《传》记载的其它差异亦应因之而有新的考虑。那么,向注别本究竟是否存在呢?它与向注原本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二、向注别本是可能存在的
从史料的比较和逻辑的剖析中,我们认为,能够推断出《晋书·郭象传》中所谓的向注别本极有可能是存在的。先看史料的比较。向秀《庄子注》宋代早亡,不过其中部分文字由于人们曾加以引用,因而还可查考,据之也可与郭注比较,了解彼此的异同。在这方面,近代以来诸多学者均有重要成果,例如王叔岷先生即指出:
“今据《庄子释文》、《列子注》及他书所引,详加篡辑,得向有注郭无注四十八条,向郭注全异者三十条,向郭注相近者三十二条,向郭注相同者二十八条。”[1](P1)
在向注本佚失之前,尤其自东晋至唐,二本是并行于世的。当时的学者,如张湛、陆德明等,在引用时,或二注兼引,或单引郭注,或单引向注,说明二本在当时就是不尽相同的。这些不同之处,有些地方差异是很大的。如《庄子·应帝王》“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欤?众雌而无雄,又奚卵焉?”句,向秀注文是“夫实由文显,道以事彰,有道而无事,犹有雌而无雄耳。今吾与汝虽深浅不同,然俱在实位,则无文相发矣,故未尽我道之实也”,(《列子·黄帝篇》张湛注)全注近五十字。同一句,郭象则仅注“言列子之未怀道也”(注:比较今本《庄子注》与《列子注》等古籍所引郭象注文,内容一般相同,可断定今本《庄子注》即古郭象注本。王葆玹先生认为今本郭象注文在唐初曾经被当时士人用向秀注予以改编的看法缺乏理论依据。理由很简单,因为日本高山寺所藏《庄子注》(其乃南朝写本)与今本郭象注文对照,其内容一般相同,故可由此类推,得知今本《庄子注》即古本《庄子注》也。本文所引郭象注文均出自今本《庄子注》,其后不另注出。)八个字,差异很大。又如《庄子·人间世》“易之者,嗥天不宜”句,向秀注文是“嗥天,自然也”,(《经典释文·庄子音义》)重在注解“嗥天”一词之义,而郭象的注文则是“以有为为易,未见其宜也”,重在注说“不宜”之因。二注所注同一句,但所意指各有不同。这种情况,在二注的比较中还能举出一些。总合而论,就现存向、郭注文的对勘,“向有郭无共四十八条,向郭注全异者三十条”,合起来达七十八条,占所辑二注总数一百三十八条的近百分之六十,故王叔岷先生有言:“列此明证,然后知郭注之与向注,异者多而同者少,……就余所考得者,已足证《世说·文学篇》、《晋书·郭象传》所言之不足据信也。”[1](P1) 但细查此向有郭无之四十八条和向郭注全异之三十条,则正如近人杨明照先生所言,“多为短句小文”,其义亦多“只在诠释字句”,[2] 故简单的数字比较易导致表面化的结论。且就此不论,二注本亦有大量的相近和相同之处。如《庄子·应帝王》“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见吾杜德几也”句,向秀的注文是:
“德几不发故曰杜也。萌然不动,亦不自止,与枯木同其不华,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无感之时也。夫至人,其动也天,其静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渊嘿。渊嘿之与水流,天行之与地止,其于不为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见其尸居而坐忘,即谓之将死;见其神动而天随,便谓之有生。苟无心而应感,则与变升降,与世为量,然后足为物主,而顺时无极耳,岂相者之所觉哉!”
(《列子·黄帝篇》张湛注)
同一句,今郭象庄注本分为两句分别注解。在“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句下,郭象注道:
“萌然不动,亦不自正,与枯木同其不华,湿灰均其寂魄,此至人无感之时也。夫至人,其动也天,其静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渊默。渊默之与水流,天行之与地止,其于不为而自尔,一也。今季咸见其尸居而坐忘,即谓之将死;者见其神动而天随,因谓之有生。诚能应不以心而理自玄符,与变化升降而以世为量,然后足为物主而顺时无极,故非相者所测耳。此应帝王之大意也。”在“是殆见吾杜德几也”句下,郭象注道:
“德几不发曰杜。”
比较两注文,显然相同乃至雷同之处是巨大的。郭象的注文,不过是将向秀并在一起的注文拆开,以其注文的首句作为次句原文的注文,而在首句的注文共一百三、四十来字中,相雷同的即占了一百字还多,略有差异的不过是后面十来字,且在意义上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所异者唯语气罢了。就此句注文而言,可以说郭注与向注是近乎完全相同的。
完全相同的也是有的,《庄子·达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句,向秀注文是:
“累二丸而不坠,是用手之停审也。故承蜩所失者,不过锱铢之间耳。”
(《列子·黄帝篇》张湛注)
郭象注文是:
“累二丸而不坠,是用手之停审也。故承蜩所失者,不过锱铢之间也。”
两者相较,差异只在句尾“耳”、“也”虚词之别,可以说是完全相同。这些完全相同的注文,依王叔岷先生的考证,共有二十八条,再加上两注相近的三十二条,共六十条,占注文总数的近百分之四十;如果撇开向有注郭无注的四十八条(因其内容主要是简单的字义解释,故可能为郭象所删弃),则现存两注的同异之比是六十条比三十条,相同和相近的注文正好是相异注文的一倍。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两注本在内容上的重合是十分惊人的(注:苏新鋈在《郭象庄学平议》(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41页)中,通过史料比勘,认为“盖就已辑得之秀注遗文计,凡一三八则,其中有象注可资比较其异同者,共九十则。而在此可比计异同之九十则注文中,其文之“义”、“辞”皆同,或类同,或至少其义是相同者,殆有六十八则,占百分之七十五强。故此若视为一极自然的抽样考核论,则象注之“义”、“辞”相同,或类同于秀注者达四分之三以上,即至少已可据论郭象之庄学,殆若有四分之三乃直接源于向秀而来者也。”(苏氏乃王叔岷先生之弟子,此文亦曾经王先生审核,其结论应是可信的。)另外,《庄子·应帝王》之“列子见季咸”一节,今本郭注总数二十二则,与向注雷同及仅仅“点定文句”者达十七则,相同比更在十分之八以上。)。
对此应如何理解呢?我们认为它证实了向注别本极有可能是存在的。如前已论,如果《晋书·向秀传》所记载的向注本流行线路是确实的,那么向注原本已于郭本之前流行,则不存在所谓的向注别本,现存的向注佚文乃是向注原本所有。由于以上史料比较所示的向注佚文与郭象注文间在内容上的大量相近乃至雷同,则郭象就是直接地把当时已在社会上流行的向注原本中的大量内容基本上未经改变就作为己注在社会上推出并与向注原本并列流行。这种情况,我们认为,由于两注本在内容上的重合比例过高,即使在当时也许缺乏严谨的著书体例,存在着普遍的抄书之情况下,仍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注:余嘉锡先生在论及古书撰作者时指出“郑玄、赵歧、杜预注经皆只称氏,惟何休、何晏、王弼称名”,“今虽不能考其(著者自署其名)所始,要是汉、晋以后之事”;(《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1页)魏晋士人均甚为重视“立言”,重视要“成一家之言”以求不朽,且何晏在主编《论语集解》时即很注意著作权的问题,故学人之著作权观念的发生与发展或即就在此魏晋之际?要之,在郭象所处的西晋时期,学人中著作权的观念应该已经较为流行了。)。向秀是玄学名士,理论名家,社会影响很大。其《庄子注》倘在他生前即已问世,则必为当时已重新活跃起来的清谈名流们大量地注意、熟悉和理解;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把已在社会上流行并得到社会认可的向注原文大量照搬为己注,从郭象的角度考虑不太可能,即使可能,从两注并存于社会中流行来看,社会应该也不会接受;再进一步,即使社会接受,向秀有二子,“纯字长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逊,位至御史中丞”(注:《世说新语·赏誉》“林下诸贤各有贤俊子”条下,刘孝标引《竹林七贤论》曰:“纯字长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逊,位至御史中丞。”又引《晋诸公赞》曰:“洛阳败,纯悌出奔,为贼所害。”可见,即使秀卒时其二子甚幼,但至永嘉年间亦已四十左右,正为中年高宦。),当郭象庄注流行之时均已是当朝高宦,何能容忍他人剽窃其父之著作而不论不管?因此,从常理推断,向秀生前其《庄子注》未曾在社会上公开流行,现存的向注佚文是出自向注别本,此别本流行于郭象注本之后。也就是说《晋书·郭象传》所陈说的向注本流行线路才是确实的,向注别本应该是存在的。我们认为,这一推断,从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问题在于:如果向注别本是存在的,且出自郭象注本之后,那么,它与向注原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换句话说,向注别本是否后人好事之徒据郭注本伪造的呢?
三、向注别本即是向注原本
今人刘建国在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有关郭象部分中认为:
“《列子·张湛注》引《庄子向秀注》文,文异于《郭传》的只不必说是《郭注》,而文同的也只能说是郭象同意《向注》。同时,张湛注不独引《向注》也同时引有《郭注》,说明向、郭二注在张湛时并存,也都为张湛所承认。即或文字相同的,也还有一个‘其后别本出’是否有人据郭本伪造向注的问题。”[3]
上段引文中,“文异于《郭传》的只不必说是《郭注》”句,应订正为“文异于《郭注》的只不必说证实了《郭注》系郭象自注”,但要表达的意思还是清楚的。刘建国赞同“述广说”,他从两注本的并列及异处着眼作出的论断可不论,倒是他顺带提出的向注别本可能系有人据郭本伪造的问题值得考辨一番(注:此问题实属重要,因为向注别本的出现,疑点确实颇多。依史实分析,向注别本的迁流应在向卒以前,而郭本之流行,据学界的通常意见,应该是在晋后期永康乃至永嘉年间,则其间隔达二十余年。郭为太傅主簿,其注已流行,但其时向注别本未出,否则郭象“清誉”受损,司马越不会辟之为部属,庾顗亦不会需因其“操弄大权”方“畴昔之意都已尽矣”。查见过向注别本的学者,张湛应该是最早的,但其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晋孝武帝之时,距郭象之卒亦已有五十余年。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出现好事之徒依郭本伪造向注的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
经检寻,笔者认为,有几条现存向注佚文和郭注的加以比较能够说明向注是先于郭注的,郭注是对已有向注的修订,而不是相反。
《庄子·齐物论》之“罔两问景”句,向注为“景之景也”,(《经典释文·庄子音义》)郭注为“罔两,景外之微阴也”。向注简单而不确切,郭注则清楚明了,应该郭注是对向注的修订而不是相反。
《庄子·人间世》之“今吾朝交市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句,向注为:“食美食者必内热。”(《经典释文·庄子音义》)郭注为:“所馔俭薄,而内热饮冰者,诚忧事之难,非美食之为。”显然,郭象是认为向注解为“美食之为”有误,故予以重新解释。“非美食之为”说明郭注是对向注的改正。
另外,比较向、郭注之相近注文,明显可以看出向注较郭注要显得简单,郭注在向注基础上大多有意思上的递进和演绎,如:
《庄子·天地》之“手挠顾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句,向注为“顾指者,言指麾顾眄而治也”。(《经典释文·庄子音义》)郭注为:“言其指麾顾眄而民各至其性也。”郭注中的“民各至其性”就是对向注中“治”在具体含义上的演绎。
《庄子·缮性》“心与心识”句,向注为:“彼我之心,竟为先职(应为识)矣。”(《经典释文·庄子音义》)郭注为:“彼我之心,竟为先识,无复任性也。”显然,“无复任性”是对向注含义的递进。
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一些,但有这些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我们认为,向注佚文是出自向注别本,向注别本不是好事之徒依照郭注本伪造,郭注本乃是建立在向秀原注基础之上的,向注别本与向注原本应是同一内容,都出自向秀之手,我们可以依据向注别本佚文来比较向、郭二注的异同,前人在这一方面的比较结论也是能够成立的。
四、“盗窃说”和“述广说”是可以并存的
“向注别本说”出自《世说新语》,《晋书·郭象传》完全是对《世说新语》的转录。历来对《世说新语》记载的真实性颇有争议,或以其为野史,不尽可信,但就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的意图而言,应该说是尽可能追求真实,力戒虚构的。据《世说新语·轻诋》篇载,在《世说新语》之前流行的裴启所著同类笔记体小说《语林》,就因为它所载谢安语不实,为谢安所道破而致“于此语林遂废”。前车之鉴仍在,刘义庆当不致去自蹈覆辙;况且当时社会上向、郭两注本并存流行,士人能够很容易地对较两本的同异以证实其记载的真伪。刘孝标是见过并存之两本的,史载他“善于攻谬,博而且精”,(《史通·补注篇》)他在注文中对刘义庆所引材料的错谬(而非主观评价所致)都曾予以力纠,但对此处却未作变动,从一个侧面也证实了《世说》所载史事的真实性。因着前面所论,笔者认为,《庄子注》向秀别本极有可能是存在的;若其存在,则它在内容上与向注原本也是同一的;如此,则郭象是在向注原本“其义零落”的情况下将之窃为己有并纳为己注的,而后向别本出,两本并列。向注原本所以未曾流传,究其因,最可能的大概就是未曾完篇(注:依《世说》所载,向秀注庄,“惟《秋水》、《至乐》二篇未尽而秀卒”,但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引有《秋水注》:“正曏,向郭云:明也。”似为一反证。然而,此注文只能证明向秀注过《秋水》篇,并不能证明向注该篇完篇。实际情况可能是:向秀注庄,《秋水》篇注了前面的一小部分(“证曏今故”即处于该篇前面),但未完篇,《至乐》在《秋水》之后,则完全未注。)。向秀生卒约是公元227年到公元275年,不过活了40余岁,可算早卒,因其子幼而其义零落的情况,也是可能出现的。当然,秀义零落之前为什么会有别本迁流,其后别本又为何流出,由于史料的缺乏,这一问题已经无法确考了(注:刘宗周《人谱类记》载:“昔日注庄子者,皆莫就其旨,独向秀于旧注外另有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卒。时郭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誇衔于世。时秀门人亦有得其稿者,出与比勘,则象所著止《秋水》、《至乐》二篇而已,象为惭愧欲死。”这其中的说法太活灵活现,盖想像力发达之故。)。至于《世说新语》所言“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的问题,则应当是因为刘义庆(及其门客)在比较向郭二注时,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二注之同及所引致的郭象“为人行薄”的问题上,忽略或说轻视了二注本之异,同时也说明了作为编撰者,刘义庆缺乏必要的玄学理论素养,不足以理解到向郭二注在差异处表现出来的思想之衍化与发展,进而认为两注之异不过是简单的“点定文句”而已。《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否认其整个记载在史事上的真实性。《晋书》史臣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子玄假誉攘善,将非盗乎?”又赞曰:“象既攘善,秀惟瘅恶。”《世说》及《晋书·郭象传》所持之“盗窃说”是可以成立的。
在刘义庆之前,张湛《列子注》已经向、郭注文并引,可见向注别本至少在东晋时已经出现并与郭本并行于世。但与刘义庆不同,在注《列子》时,张湛或引郭注,或引向注,两注分引,说明他较多地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差别。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对其所言向、郭《庄子注》关系之史实不加纠谬,但却引《文士传》称赞郭象“少有才理,慕道好学,记志老庄,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进而说“象作《庄子注》,最有清辞遒旨”,表现出与刘义庆完全不同的态度与评价。唐陆德明因为修撰《经典释文》,他的目光就主要聚焦在两注本之异上。在二注本之异的比较中,郭本的优越性就直接体现出来了,即所谓“唯郭象所著,独会庄生之旨”。从两注之异处看,应该说郭象有“俊才”,其注是对向注的“述而广之”,是把向注纳入了己之内在体系并因此成为玄学发展的顶峰。这一点,近代以来,尽管向注早佚,但通过对向注佚文的搜集并与今本郭注文比较,王叔岷、冯友兰、汤一介等前辈学者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且已经成为了学界的普遍性共识。从两注之异处看,“述广说”无疑是正确的,但从两注之同处着眼,尤其是从向注别本的角度加以考虑,则任何以“集注体裁”或“郭象庄注后序未曾完篇”等为借口,将郭象的盗窃行为正常化、合理化的做法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盗窃说”和“述广说”是能够并存的,正如郭象的‘俊才’和“薄行”也可能确实是并存着的一样。我们应该把今本《庄子注》看作是向、郭两人共同的作品(注:关于今本《庄子注》的版权的问题,个人以为,其原著者为向秀,而郭象则应被认定为修订者。从原著者的角度看,郭象将向秀的原著者身份予以抹杀,应该说是存在学术道德问题的;但从修订者的角度看,则由于郭象对向秀《庄子注》的“述文”是强力的,甚至可以说是创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使得向秀的原著材料,通过郭象的修订,在郭本《庄子注》中应该说是获得了新的思想意义,故今本《庄子注》,尽管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其实乃是向秀所著,我们应也可以将之作为郭象的思想材料予以整体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