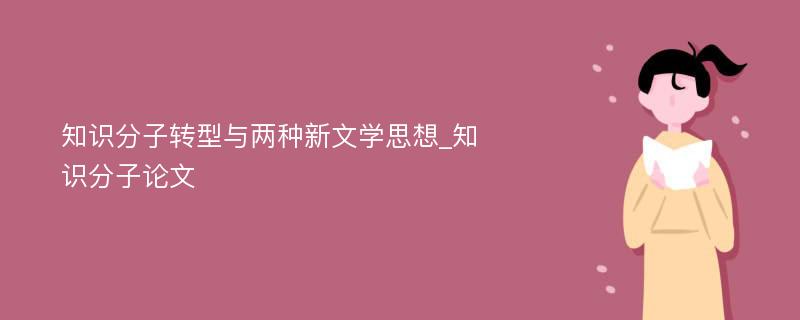
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两种论文,思潮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G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3)01-0103-10
一
“五四”这个概念是非常含糊的,准确的说,应该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次学生爱国运动。但是,我们今天在讲“五四”的精神,不仅仅局限在这个爱国运动上,我们往往把它衍生到从1915年开始的整个知识界的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它是以文学领域的语言革命和形式革命为契机而深入展开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大的新文学思潮。
现代知识分子是由原来的士大夫阶级转化而来的,士大夫阶级的基本价值是在庙堂上,那个时代的读书人通过对朝廷效忠来发挥他的能力。所以,传统士大夫阶级价值取向非常狭小,官做得越大,就越可能为国家做出大的贡献。所谓“学而优则仕”就体现了这种传统。
到了20世纪,通过科举进入庙堂的传统仕途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学校,是现代大学。科举制度跟我们今天的高考制度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是为朝廷培养人才的,它通过科举制度一级级地考,最后由皇帝来钦定你做什么官。古代读书人如果一辈子做不了官,就什么都没有了。到了现代社会,这样一个机制就中断了,并转化为今天的现代教育。现代教育中没有一个制度是可以推荐博士生毕业去当局长、硕士生毕业去当处长,因为国家干部培养是通过另外的渠道。现代学校的功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所以,一个合理的教育制度,跟社会人才机制是吻合的。过去为什么师范那么发达?就是因为国家需要普及教育,需要大量的师范生;现在为什么金融、计算机专业比较热门?是因为社会需要这方面的人才。现代教育机制是根据社会需要的变化来设置教育规模和结构。这样一种现代教育机制,导致人才为社会服务。这就是我经常强调的“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我们今天的读书是为了在社会上求职,为了在社会上求得一个岗位。在这个前提下,比如,学生毕业以后进入到某国家机关里去当公务员,那也是作为一个岗位,而不是一个官的概念。而社会有无数的工作岗位,并根据各种专门技术分出范围,如医生的岗位,教师的岗位,传媒的岗位,技术人员的岗位,做生意的也有商业的岗位等等,学校需要根据不同的专业设置来与社会人才需求发生直接的供求关系。
那么,当职业精神非常清楚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精神体现在哪里?古代读书人有一个基本的发展思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由下而上的理想。意思是说,读书人首先把自己管好,修身养性;把自己的家治理好,过去的家一般是指大家族;再上去就是要把国家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以后,我们就能平天下。这个“天下”有点像今天常说的“当今世界”的概念。所以当时知识分子的理想和他的活动空间是非常清楚的。比如曾国藩,他先是修身养性;然后进一步是治家,他练的湘兵都是当地的家乡子弟兵;后来太平天国起义势如破竹,他就带领子弟兵为国家打仗,那就是民间起兵治国。到晚年了,曾国藩掌握了清政府的重要权力的时候,他却更加关注文化,中兴儒学。明代徐光启翻译《几何原理》并没有译完,他就组织人重新引进西方的《几何原理》,企图重新推动中西文化交流,那就是我们说的“平天下”。曾国藩是中国封建士大夫理想的最后集大成者。他以后整个世界的局势都变了。现在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再做这样整体性的工作。于是就转换为直接为社会服务,拿自己的知识、文化、道德修养来为社会服务,做任何一个工作,都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都有荣誉感与价值体现。原来知识分子是人上人,现在就变成一个很平凡的社会成员。但是,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治国平天下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愿望,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这是一个潜意识的积淀。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就是在这样的传统中发展过来的,到今天,这样一种精神还是存在的。
另外,就是近代西方社会传过来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现代知识分子首先要有一个社会的民间岗位,这是一个前提,知识分子首先是有他自己的专门知识或者技术。有些人也关心国家大事,像出租车司机,他也会骂街,骂领导,骂警察,但是这不叫知识分子,只是一般老百姓发发牢骚。其次,光有这个岗位还不够,他还具有一种超越了职业岗位的情怀,对社会、对人类发展的未来有所关怀。这是比较抽象的,但又是一种很本质的东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看到社会上很多现象,不会就事论事地来讨论,而是上升到一个很高的角度:我们中国的前途怎么样,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中国和世界的潮流怎么样,等等。他要透视日常生活的问题来考虑我们国家的未来,考虑世界的未来。这样一种关怀在过去是通过很壮烈的行为来体现的,比如像俄罗斯的民粹派、法国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宣传、坐牢、革命甚至恐怖行为来达到他对社会的关怀。这样一个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但这样一种精神还体现在我们现代知识分子身上。
这样一种俄罗斯式的、对人类社会有终极关怀的精神,加上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两者结合起来,就构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状态。这两种传统是有矛盾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独立的精神,他通过自己的职业尊严和知识尊严,可以不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像陈寅恪先生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是通过最高政权,通过皇权、忠于朝廷而达到权力,达到治理国家。两者之间相互有矛盾,但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却是紧密结合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很自觉地把自己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政治力量结合起来。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摆脱不了参与新的国家建设的热情,现代中国的几次政权变更新旧交替,都不缺乏大量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与参与。
最典型的如熊十力先生。这是个高蹈的哲学家,向来是做隐士的,他一直在研究中国哲学。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董必武把他请去(熊十力是湖北人,和董必武是同乡),他在北京给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写了一封信,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研究生研讨国学,同时恢复三家民间书院:南京内学院,由吕徵主其事;浙江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其事;勉仁书院,由梁漱溟主持。这封信就是向最高领袖献计献策的。后来他又发表《论六经》,论证了《周礼》、《春秋》等经书里有社会主义思想,证明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社会主义思想,甚至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予确信全世界反帝成功后,孔子六经之道当为尔时人类所急切需要,吾愿政府注意培养种子。他的意思是我们要继承传统,要把中国古代学问作为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这样可以国泰民安。这个思路很有意思,也非常陈旧,毛泽东当然不会采用。但这说明像熊十力这么一个老知识分子,一旦到他认为自己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就变成治国平天下的人,认为按照他这个思路可以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他绝对不是反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反社会主义,而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学问用在国策的确立上,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其实不仅是熊十力先生,还有梁漱溟、冯友兰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的精英,都是在专业学术上达到最高层次的人,在这样一批知识分子身上仍然综合了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两种成分。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价值取向上是很典型的。
当现代社会发生转型,传统士大夫的经国济世的抱负无以施展、然而又不仅仅满足于自己的民间岗位的时候,知识分子必然要在这中间开辟一个渠道,让他们能发挥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与热情。这样一种发挥热情的价值取向,我把它称为“广场”。“广场”是个空间的象征,传统庙堂的对象是国君或者说统治者,那么,现代“广场”的对象是什么呢?当然是民众。“广场”里熙熙攘攘的都是老百姓。然后,“广场”需要英雄,需要能人,需要知识分子来告诉老百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中国的出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启蒙”。“广场”与庙堂在价值取向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成就的理论家冯雪峰曾有一个说法:知识分子实际上像一个门神。门神是贴在大门上的,门开了他是站在庙堂的门口;门关了他就面对民众,成了民众的导师。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门神是贴在门上的,如果庙堂接纳他,他就在为国家服务的行列里;如果庙堂不需要他,门关掉了,他在门外面倒变成导师了。这当然是一个自嘲,但用来理解20世纪初士大夫阶级到知识分子形成的过程很深刻。我觉得中国士大夫阶级在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初期阶段,通常就扮演了这种双重的角色。
中国20世纪文化跟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大区别,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文化是在一个自成一体的封闭体系里运作的,士大夫的道统、学统、政统是完全融合一体的,是非常和谐的。可是到了现代社会,由于西方的介入,这样一个自成一体的东方社会运作机制被打破。知识分子从这个打破的裂缝里面走出去了,学到了西方的一套所谓现代化的东西,就是说,中国要向世界学习,要跟世界同步发展,也就意味着必须要向西方学习,吸收甚至模仿他们的东西才行。
在这样一个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原来治国平天下的“道”被淘汰了,再去讲什么君君臣臣,跟这个现代化毫无关系。中国那么大,没有了原来的道统,中国人又没有恒定的宗教传统,不像西方,社会虽然变来变去,但上帝是不变的。中国原来讲究天不变道也不变,现在是明明白白地变天了,再去拿什么东西作为民族凝聚力,使这个国家能够重新凝聚起来?这个问题一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我们变来变去,好多次了,拿来的都是各种各样西方的学术思想和社会实践,除了新儒家企图重返儒家传统以外,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没有人谈了,日本的“脱亚入欧”获得成功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整个现代中国要走向世界,成为一个现代性的中国,必须要从西方引进一个适合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统来凝聚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尽管20世纪流行的思想学术内涵不太一样,它们的根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其根源都是跟西方的现代化有关的。我们总是引进最先进的,过去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现在是美国,它的生产力最先进,文明程度最高,总是把这样一个标准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而这个标准我们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就是“现代性”,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新道统吧。到现在还是这样。
那么,从追求、学习到整合、探索这样一套来自于西方的新道统,实际上也就是成了这部分知识分子的专利。其实也不是他们的专利,只是因为在“五四”的时候,他们这批人最早出国,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他们到国外,首先看到了西方先进国家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也不见得都学好,就是一知半解,有的学点技术回来,有的学点制度回来,有的学点文化风俗回来,实在没有的就学点语言回来,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用。这就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有资格在“广场”上启蒙民众的一个资本。这种资本也可以称作是在营造一个新的道统。当然,很难说真的有一个什么新的道统,但是有关这个新的道统的幻觉强烈地吸引着知识分子。这是启蒙知识分子引以为骄傲的资本。
知识分子的启蒙自觉是在戊戌变法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19世纪末还是延续着庙堂的传统,比如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希望通过君权来实现治国平天下。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知识界就开始有了从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自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转向了对民众的思想文化教育。梁启超办了《新小说》,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的口号,呼吁小说界革命,中国的现代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梁启超目的非常清楚,他提倡小说界革命就是为了“新民”。康有为说得更加赤裸裸,他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日本书目志》,大同译书局,1897年。)康有为说得非常具体,他们要传播新的思想,就要通过小说来完成。为什么不通过诗歌?因为诗歌比较艰深,小说是讲故事的,比较通俗。这个思潮以后就慢慢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所以,我们现代文学其实起点是不高的。它不像什么唯美主义,一开始就把艺术搞得很崇高很神秘,中国的现代小说一开始就是通俗文学。“通俗文学”是我们今天的理解,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因为小说和戏剧从来就是通俗的,他们就把它看成是一种向民众传播思想教育的工具。
当时的士大夫开始明显地意识到他们对国家社会所负的责任,今后不能再指望国家了,他们要把力量放在对老百姓的教育上面,就是所谓“开民智”。最典型的是严复。严复原来也是参与维新的,但这时他认为:“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他就说自己以后“惟以译书自课”(注:严复致张元济书,转引自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印《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页。)。严复后半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官,就是做过几个大学的校长,还有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翻译著作,从靠朝廷奉禄转换为一个靠版税来生活的职业翻译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从一个士大夫变成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再有可能通过获得政治权力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与梦想,他们只有利用民间岗位来发表自己的言论,表达对治国平天下的热情。这个民间岗位,就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的岗位,而是具有两层意义,一层是职业,一层是思想。知识分子的岗位跟一般的民间岗位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鞋匠,也有一个岗位,这个岗位就是为人家做好鞋,一个厨师的岗位就是把菜烧好。可是,知识分子的岗位通常既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同时,他会超越自己的岗位,超越自己的职业,成为一种思想。教师是知识分子的岗位,一个教师在讲坛上讲课,他讲的东西除了传授知识以外,还有一种超越知识的能力,鼓励大家从精神上去追求对人生的认识高度。一个报社的记者或者出版社的编辑,写新闻稿或者编书是他的职业岗位,但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可以创造出一种精神财富,这种财富为全社会所有。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第一次在“广场”上操练,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民间岗位的形式,而不是通过庙堂的形式,来履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你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通过什么渠道的?一个是北大的讲台,另外一个是《新青年》杂志,第三就是学生社团,如新潮社等,把知识分子的阵地——也就是岗位,把它们结合起来。陈独秀原来是一个革命家,他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的秘书长,是搞政治的,但到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他认识到光靠暴力、靠革命,还不行,他就转向了思想文化启蒙。当时他在上海办了《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青年思想杂志,里面有很多新的思想,比如反孔反传统。但是在1915年,他在上海办这个杂志的时候,虽然有影响,但这个影响远远没有后来那么大。上海是个商业社会,这个杂志在文化市场上与许多杂志放在一起,除了它比较激进外也没有特殊的地位。可是这个杂志一旦到1917年进入北大以后,其地位和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完全不一样,它有了高等学府这么一个知识分子岗位,这两个岗位一经结合以后,在全国的学术界、思想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我们整个民族国家的主流语言、思维形态和文化心理。所以,这件事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鼓舞,迄今为止,我们一讲到“五四”还津津乐道,觉得知识分子真的有过光辉的历史。就那么一本杂志,发表一些文章,居然会闹到那么大的一个局面。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因为那个时代整个“广场”上一片空白。这个“空白”有两个意思,一是还没有人那么做,第一个做的总是影响比较大;二是因为还是空白,所以国家统治者也没注意到怎么去控制它。当时的军阀政府只管自己争权夺利,注意力还没转到这个“广场”上面。新文化运动开辟了这一“广场”以后,它就直接起到了一个跟民众发生关系的桥梁的作用。这样一个现代文化运动,实际上包含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全部追求和全部梦想。
因此,我们所说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实际上已经不是通常说的学生爱国运动,而是整个知识分子在转型过程当中,必须要寻找到一个代表他形象、表达他声音的这么一种方式、一种渠道。这个方式和渠道恰好被陈独秀、胡适之、蔡元培他们找到,他们利用、创造了一个有学校、有杂志(我们今天说就是媒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他们自身拥有的来自西方的思想学术,通过这三个东西结合,构成了一个新的现代的知识分子的岗位。这个岗位里面透彻了职业和精神两个方面。首先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职业,他们写书要换稿费,教书要拿薪水,杂志要投入市场运作,赚钱赢利。但是,除了职业以外,它还有高于职业的这么一种精神能量。而这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
二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新文学思潮。我想以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的作品为代表,来讨论这个文学思潮的某些特征。为什么我们不讨论像陈独秀、胡适这样一些更有名、更具有原创动力的知识分子作为了解这个运动思潮的代表?一个原因是我们讲的是新文学思潮而不是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我们要限制在文学上讨论这个问题。当然陈独秀、胡适在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上也都有他们的贡献,但从文学创作来说,周氏兄弟更有代表性。我一向以为,要研究一种创作思潮,不能只看他们的理论宣言,更重要的是读他们的创作,从这一思潮的最有代表性的审美倾向中来把握思潮的文学意义。周氏兄弟的文学创作及其审美倾向,反映了“五四”新文学思潮的一个基本倾向和两种发展趋向。
周氏兄弟在“五四”前后新文学开创时期的文学活动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他们都是从章太炎那一路学术转向新文学,对旧的传统文化充满了批判的热情。他们对新文学又都是后起者,原先也不属于《新青年》文人集团的主角,但是一旦登上了文坛,立刻在创作上显示出新文学运动的真正实绩。鲁迅的小说和杂感,周作人的散文、新诗和文学理论,都是胡适、陈独秀所不及的。胡适曾经说他们这一般人在新文学初期“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注: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参见胡适纪念馆编印《胡适讲演集》(中册),1978年修订版,第385页。),但对周氏兄弟的创作成绩却是承认的。但周氏兄弟的创作成就虽然很大,他们各自所走的道路却很不一样。不仅是创作的艺术风格不一样,而且在风格背后体现出两种完全不同,但又是同根同源、相辅相成的精神传统。这两种精神传统与“五四”新文学思潮中知识分子的两种价值取向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通过阅读和研究周氏兄弟的作品可以大致了解新文学思潮的趋向。
20世纪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道”并没有真正形成,知识分子都是通过向西方学习,找来一种哲学、一种思想或者一种学说,作为中国人的一个范本。比如,胡适就是把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和西方的民主制度都看作是中国人努力的一个范本。其他人也是这样,他们习惯于把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与西方的某一种学说衔接起来,作为我们今天的指导方针。这样一来,急功近利的态度是必不可免的。有时为了引进和推广某种学说,免不了有些“机会主义”的态度。比如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注: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这是鲁迅说的。针对“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和民族自大症,拿来主义是一帖有效的良药,但是从吸收西方文化营养的本身态度而言,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适合我的就拿来,不适合我的就放弃,这仍然是一种急功近利。它不是从根本上来了解中西文化传统的特点及其结合的可能性,当然也就不可能对中西文化作出理性的科学的研究,以及尝试其彼此的融合。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佩服周氏兄弟。当他们在接受西方的时候,都关注了非常深远的东西。从表面上看,鲁迅与周作人的个人风格完全不一样,这些比较的话很多人都说过了。鲁迅好像也没有专门谈论过古希腊的传统,但是,在追寻西方文化源头的意向上,研究者们似乎很少注意到鲁迅最早的一篇小说作品,在1903年的时候,鲁迅发表了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这篇作品有点像编译的,过去一般学者把它当作翻译作品,很少当作鲁迅的创作来研究。但是,至今为止,好像也没有人指出这部翻译作品所依据的原本(注:《鲁迅全集》第7卷收入了《斯巴达之魂》,但没有注明本文是根据何种原本翻译的。日本学者山田敬三的《鲁迅世界》一书中讲到《斯巴达之魂》,指出该书“出典不明,但文中的‘愿汝持盾而归来,不然则乘盾而归来’的句子,与《新民丛报》第13号第5页的‘愿汝携玥而归来不然则乘楯而归来’(斯巴达小志)极其酷似,照例应出一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但真正的出处仍然没有揭示。而这文中所引的这句话,出自普鲁塔克《斯巴达妇女的言论》,收其《道德论集》)。见裔昭印《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转注。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79页。)。鲁迅后来对自己的这部早期作品也抱以少见的羞涩态度(注:鲁迅在《集外集·序言》里承认这篇小说是他在编杂文集《坟》时自己故意删除的。因为:“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欲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鲁迅全集》第7卷,第4页。))。在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把翻译也当自己创作,那个时候是不算剽窃的,因为它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一种选择和一种提倡。当鲁迅在日本的时候,很多文章都是把人家东西编译过来的,如《摩罗诗力说》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可是为什么对这篇小说却一定要强调它是翻译作品呢?至少,小说中所出现的神采飞扬、慷慨激昂的文言语言和民族主义的煽情,应该是鲁迅创作中非常独特的一种现象。
那么,鲁迅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斯巴达之魂》来表达他的愿望?这也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他是用文言文写的,写得是激情昂扬,完全不像后来冷峻的鲁迅。斯巴达是古希腊一个城邦,这个城邦的公民讲究尚武精神,非常狂热,他们为了一个信念,一种国家主义的道德观,常常表现出热血沸腾、甘愿牺牲。当时强大的波斯国来侵犯,斯巴达300壮士随国王出去打仗,结果都战死了。其中有2个人,因为患眼病去治疗,得以免死。他们两人意见分歧,一个带着奴隶重返战场,结果也战死了。另一个不愿意去死,就回到家里,可是自己的妻子正在与情人约会,——据说斯巴达城邦法律规定女性可以自己找情人,也可以与情人生孩子,都是允许的。这大约是斯巴达的男人比较容易牺牲的缘故,但后来欧洲的女权主义者把斯巴达的女性理想化了——这时,那位女权主义先驱者堵在家门口,不让丈夫进去,她说:人家都死了,你回家来干嘛?这个人嗫嚅地回答:我爱你呀。妻子听了就更加生气了,说:你如果真的爱我,就赶快去死吧,否则我去死。于是那女人就用刀自己抹脖子自杀了。这个逃回来的丈夫羞愧之下又重返希腊军队,终于在一场击退波斯国的大战役中也牺牲了。但是,当希腊人正议论要给他立烈士碑的时候,他妻子原先的那个情人出现了,说出了自己的情人以死激励丈夫的情景,于是希腊人为那位逃兵的妻子立了碑,这个叫作阿里司托戴莫斯(Aristotle,鲁迅译作阿里士多德摩)的人还是白死了。不过他也没有白死,许多历史著作都记载了这件事,他仍然名垂不朽。后来有个电影《斯巴达三百壮士》,内容有点不一样。但斯巴达精神一直流传,形成西方古希腊的一个传统。虽然斯巴达是个小国,但斯巴达精神到今天为止还在被人传说,被人们记着。这种精神就是一种狂热的、偏执的、爱国的、自我牺牲的精神。
从资料中发现,关于斯巴达城邦及其精神的主要依据都来自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里的《吕库古传》,吕库古是斯巴达律法的制定者,普鲁塔克很欣赏他,此人是个铁腕人物,他在斯巴达取消货币、取消对外贸易、提倡朴素的生活,将男女分住,还办集体食堂等等,推广原始的军事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使城邦一度变得很强大。后来的学者公认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受了斯巴达的影响。柏拉图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都是反对雅典城邦的民主体制,有贵族政治倾向,而通常贵族政治与专制制度有相通的地方。至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故事,主要依据的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关于这个阿里司托戴莫斯有这么两段记载:一段是说阿里司托戴莫斯回到家乡后受到非议和蔑视,以致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愿意把火给他,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说话,大家称他为“懦夫”,结果他在普拉塔伊阿的战斗中洗清了所蒙受的一切污名;另一段记载是说:战后希腊人评功的时候,有人提出阿里司托戴莫斯虽然最勇敢,但他是因为受到责备后抱着一死的愿望去杀敌的,这不算真正的英雄,于是没有得到光荣的表彰,但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那是别人嫉妒他才这么说的(注: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57、654页。)。但是很奇怪,所有的蓝本里都没有那个阿里司托戴莫斯的妻子,也没有那个在旁边目睹现场的情人,不知是鲁迅编出来的,还是当时在日本为其他通俗小说作者所编。其实这个烈女并不可爱,那情人更加可鄙,为这样的男女树碑立传不像鲁迅一贯的风格。所以鲁迅后来读了感到脸红。
不过可以肯定,鲁迅对斯巴达精神是倾心喜欢的。鲁迅后来写的小说里一直有这种斯巴达精神的成分,比如《铸剑》,就是强调了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样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我觉得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子里是有的。中国过去有武侠传统,有墨家传统,而且往往是知识分子继承的这些东西,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为了对朋友的承诺,宁愿牺牲自己,毫无眷恋。有人称为“儒侠”,既是儒,又是侠,平时饱读史书,一旦国家有难,也能挺身而出,从汉代的张良到清代的曾国藩,都有这种记载。中国知识分子当时学习西方成为思潮,在中西大交融的过程中,很多知识分子都感到眼花缭乱,一到西方觉得那么多好东西,喜欢什么就拿什么。而鲁迅恰恰相反,在他的最初的拿来主义里面,找到了古希腊的源头,他从这样一种欧洲最古老的狂热的精神传统中,寻找到了一种与中国传统相契合的东西。这也可以说是无意的,因为后来连鲁迅自己也把它掩盖起来;但又仿佛是有意为之的,是一个潜在的、必然的、不能小觊的思潮,这个思潮包括后来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左翼思潮,一路发展下来。这种精神其实也贯穿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的追求、奋斗和可歌可泣的牺牲中,那是一种为了一个信念可以自我牺牲的,带有狂热的、偏执的东西。
三
相比之下,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感情要比鲁迅更加深沉且持久。
周作人对于狂热吸收西方文化营养的思潮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北大的支路》,他赞扬北大敢于做人家不做的事情,譬如开多种外语课程等,接下来他就说:“近年来大家喜欢谈什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我不知两者是不是根本上有什么差异,也不知道西方文化是不是用简单的三两句话就包括得下的,但我总以为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希腊我想似乎不能不予以一瞥,况且他的文学哲学自有独特的价值,据臆见说来他的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总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他的,我可以担保。”(注:周作人:《北大的支路》,《苦竹杂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12页。)这段话我觉得他讲得非常之好,他后面还讲到了中国人应该注意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对英美文化霸权的抵抗(注:王友贵:《翻译家周作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不过那个时候要说英美文化霸权还嫌早了一些,当时别说法国德国,就连日本文化对我们来说大约也算得上是一霸。当时霸权也有多元性,不像近几年的中国学术界,一些名流学者只会跟着几个美国教授的观点走。但周作人对古希腊的文化的研究是贯穿其一生的,因为他真切地认为,欧洲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要吸取西方文化营养首先就应该从根子上来研究和学习。有的研究者指出,周作人对中国文化深层的东西失望太多,于是希望从域外文明中多引进未有的东西,并导之以人道的精神(注:参见孙郁《鲁迅与周作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页。)。这种从根本上了解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当时一些严肃的知识分子都意识到的,茅盾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茅盾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出过国,但他是懂一点英语的,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就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当时他就决心要学西方文化,要从源头学起,从古希腊学起,茅盾早期还编写过古希腊神话的著作(注: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有这样记载:“在当时,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既要借鉴于西洋,就必须穷本溯源,不能尝一脔而辄止。我从前治中国文学,就曾穷本溯源一番过来,现在既把线装书束之高阁了,转而借鉴于欧洲,自当从希腊、罗马文学开始,横贯十九世纪,指导世纪末。……这就是我从事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之研究的原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周作人一生都研究古希腊文化,到晚年80多岁了,还完成一部文学巨著《卢奇安对话集》的翻译,说这是他最愉快的工作。其实卢奇安不是古希腊时代人,他是公元2世纪古罗马时期的叙利亚人,但他用希腊文写作,以讽刺的喜剧笔法改写希腊神话故事,对神明多有挖苦讽刺,比如其中有一篇是描写希腊爱神与希腊战神私通,一个美丽一个勇猛,结果却在床上被人活捉,变得很可笑(注:周作人译:《卢奇安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4页。)。我想周作人翻译这部他向往已久的著作,肯定苦涩的脸上会时时露出微笑。周作人说这部对话集主要是“阐发神道命运之不足信,富贵权势之不足恃,而归结于平凡生活最适宜”(注:周作人:《愉快的工作》,收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597页)。这其实也是周作人所坚持的最本色的特点。
周作人多次翻译过希腊神话,他不喜欢基督教神话,不喜欢古罗马神话,惟独对希腊神话情有独钟,但他又以同样的喜欢来翻译那部颠覆希腊神话的《对话集》,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说明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充满了求知的兴趣和研究的态度,而不是狂热盲目的古典主义者。他对希腊文化的兴趣也是有选择的,比较偏重于理性的民主的求知的传统,我们也可以称其为雅典精神。雅典精神是古希腊的主流,很早就开始研究科学、民主、理性,进行学理的讨论。古希腊的哲学家都叫智者。他们往往关心的是比较抽象的形而上的问题,探讨宇宙的起源奥秘问题。这样一种绝对的求知精神,直接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周作人关于希腊精神写过许多文章,有的是翻译,有的是介绍,在一篇叫《希腊人的好学》的文章里,他特别讲了伟大的力学家阿基米德的故事。阿基米德发明许多力学原理,帮助了自己的城邦击退了敌人强兵的进攻,3年后,城被敌人攻破,他正在地上画几何图形,敌兵来了,他急忙阻止敌人,不让他们破坏他画的图形,结果被敌人杀了。这个故事其实大家早已经知道了,科学家对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的热爱,超越了任何现实的利害,甚至生命,这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岗位至上的精神。周作人在文章里也特别地说:“好学亦不甚难,难在那样的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非为实用。——其实,实用也何尝不是即在其中。”其实阿基米德发明的力学原理虽然被用在防守城池的战争中,但对科学家本人来说,他的兴趣似乎更在求知本身。所以,周作人最后说,这样的好学求知,不计其功,对于国家教育大政方针未必能有作用,但在个人,则不妨当作寂寞的路试着去走走(注:周作人:《希腊人的好学》,收《瓜豆集》,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88、89页。)。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话。在另一篇文章里,周作人把希腊精神归结为求知求真求美三条,这三条加上《卢奇安对话集》里所表现的过平凡人生活的思想,可以说,对周作人一生的学术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周作人终其一生在寻找一个人类文化,或者说西方文化的源头。我们看到,周作人的小品文始终是非常平和、淡泊、学理化的,思想里有一种非常透彻、非常澄明的智慧,而且他从来没有什么长篇大论,都是对话或者小品,三言两语,表达智者的一种启示。这样一种雅典式的理性精神后来也就变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种制约知识分子的倾向:坚守自己的民间岗位,探讨知识与学理,不迷信任何权威,尊重普通人的平凡欲望和世俗尊严,等等。我读过一本研究周作人翻译希腊文学的书,作者把周作人与这种希腊精神的关系分析得很贴切,他是这么说的:“《卢奇安对话集》写于早期基督教时期,跟文艺复兴以及之后的知识分子的对神的批判有所不同。卢奇安止于对神的质疑和后人对荷马史诗的在宗教意义上的迷信态度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有着将神话还原为艺术作品的作用。他并不像一些启蒙主义者那样暗中期望作神的取代者,作人类的精神导师。因而也没有试图在推倒神坛之后建立新的神坛。卢梭就是这一类启蒙主义者的代表。然而在批判精神和叛逆精神一面,卢奇安跟后者是相通的。在一点上,翻译家周作人亦是跟西方古代和现代知识分子神气相通。周作人自己一定没有意识到,启蒙主义已经浸透到他的每一条血管里,包括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难以更换的人类精神导师的道袍。周作人与卢梭们的不同,或许在于他慢慢地不想做那一呼百应的神,只想做一个人。这恐怕主要得益于古希腊文学和古代日本文学。”(注:王友贵:《翻译家周作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页。)这位研究者用了一个词:慢慢地,来说明周作人从“五四”初期的启蒙主义者到后来的变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使他“慢慢地”与卢梭式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也就是我说的“广场”的价值取向划分了界限,这个变化,也可以看作是古希腊的雅典精神和古代日本文学对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西方的哲学、历史和政治史的研究者早已经把古希腊的雅典精神与斯巴达精神视为欧洲文化的两种源头。但在中国,似乎很少有人这么来理解西方文化的渊源。公开揭示出这一现象并引起广泛注意的是顾准的遗著。顾准在研究古希腊政治制度的《僭主政治与民主》一文里专门指出:“我们说西欧民主渊源于希腊民主是对的,但是说希腊政治除了民主潮流而外没有别的潮流就不对了。希腊政治史和希腊政治思想史一样有两大潮流汹涌其间,雅典民主的传统,和斯巴达民主集体主义、集体英雄主义……的传统,雅典民主是从原始王政经过寡头政体、僭主政体而发展起来的,斯巴达传统则始终停留在寡头政体的水平上。如果说雅典民主引起了世世代代民主主义者的仰慕,那么,必须承认,斯巴达精神也是后代人仰慕的对象。”(注: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如果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知识分子充满着追求现代性的意义的向西方攫取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同样会遭遇到两种传统的资源。在古希腊的源头,所谓的雅典精神和斯巴达传统,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对应性,某种意义上又可以看作是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与民间岗位意识的区分标志,也可以看作是保守主义思潮与激进主义思潮的区分标志。我想顾准在困厄中潜心研究这两种精神传统,也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的。它们虽然来自于西方,但是都跟当时处于时代主流的新文学思潮中的知识分子处境、追求倾向密切相关,跟他们自身的文化素养与教育传统也是密切相关,所以它们就很容易也很快地传播到中国来,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践结合成如此密不可分的关系。
虽然周氏兄弟都是从中国文化传统熏陶中走出来的,可他们思想的出发点,他们所接受的西方文化,都与西方文化中最古老的精神渊源相关。所以在这两位作家身上比较深刻、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西文化在他们身上的结合,而不是那种捡到篮里就是菜的拿来主义。他们都是超越了现实的制约,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在最根本处挖掘中西文化的源泉的相同之处。这样一种从根本上学习西方文化的精神,即使到今天也是很少的。我们今天许多作家自称学习西方文学,只是随心所欲地读几本卡夫卡、纳博科夫、博尔赫斯的书,就可以做导师了。但是,谁拿起一本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的书,或者古希腊悲剧,真要从源头开始学起呢?这是很困难的事。而像周作人,他是学了古希腊文去读希腊语的书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所创造、所实践的两种学习西方文化的精神,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尊敬和深思。
收稿日期:2002-11-30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文学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士大夫精神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斯巴达之魂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