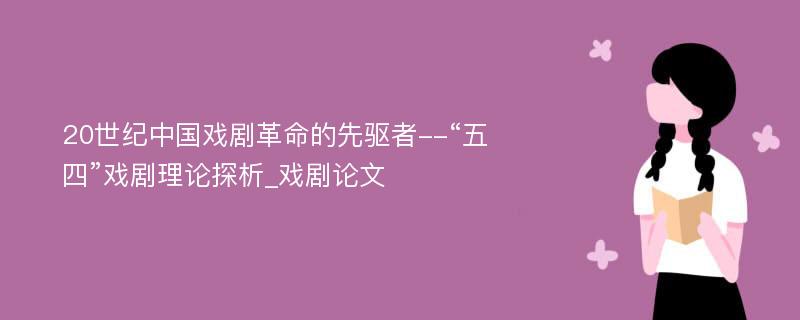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戏剧革命的先声*——“五四”戏剧理论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声论文,戏剧论文,理论论文,中国戏剧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20世纪;五四戏剧理论;中国戏剧革命;先声
一、起点:“文明戏”的衰落
中国现代戏剧的实践活动,要远远早于理论探讨活动。早在1909年,以曾孝谷、李息霜为首的留日学生,就在东京成立了“春柳社”,直接以外国戏剧为蓝本,上演了与中国传统戏剧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完全不同的《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戏剧。“春柳社”上演的这些戏剧,虽然在表演方式、情感体验、主题把握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但是,它的出现却犹如一股清风,带着西方文艺的气息,吹进了中国文坛。特别是“春柳社”诸人回国后,这股文明戏风潮也随之渐渐蔓延开来了,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文明戏出现了一时的繁荣。然而,几年后,这股文明戏风潮却渐渐走向了歧途,堕落成了小丑似的低级趣味的展示,不仅在内容上背叛了兴起时所崇尚的反专制、争民主的思想,而且在艺术上也一败涂地,既没有表演艺术的明确规范,更缺乏美的艺术追求,完全丧失了存在的活力。于是,中国剧坛,仍旧被传统戏剧控制着主宰权。
“文明戏”的衰落,呼唤新的时代戏剧,而新的时代戏剧又呼唤着新的戏剧理论。1918年,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学战线,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上刊载了《易卜生专号》,系统介绍了挪威近AI写作实主义戏剧家易卜生的生平事迹、思想主张以及他的代表作《娜拉》、《国民公敌》等话剧作品。同年,《新青年》又在第五卷第四号上,发起了“戏剧改良”的大讨论,全面拉开了建设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序幕。
这个序幕的主角是近代西方戏剧创作与戏剧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易卜生和戈登·格雷。当时介绍新戏剧的人们,之所以对这两个人物特别感兴趣,是因为除了思想倾向上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要求外,更为实在的目的则是,这两个巨子,分别完善了西方近代戏剧的两大课题:一个是戏剧文学(即剧本),一个是舞台艺术、舞台技巧等等。易卜生是前者的代表,而戈登·格雷则是后者的代表。在当时,先驱们引进西方戏剧理论,介绍、翻译西方戏剧创作,其直接的社会、艺术目的是,一方面为烛照传统戏剧的弊端,考察“文明戏”衰落的原因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为探讨新的中国现代戏剧模式和理论规范提供参照蓝本。这一时期的戏剧理论探讨,就是在反省传统戏剧和“文明戏”,认同外国戏剧与理论,重构现代中国戏剧理论这“三位一体”的形势下展开的。它的内容涉及到戏剧的各个方面,如思想倾向、剧本艺术、舞台艺术和戏剧作家、戏剧演员的修养、培养等等。
五四时期的戏剧理论活动的杰出代表人物,主要有胡适、傅斯年、欧阳予倩、陈大悲、田汉、洪深等人。他们以其辛勤的工作和学贯中西的学识,在新时代的戏剧理论园地播下了未来发展的种子,在戏剧的本质、目的、艺术规律、作用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开创意义的观点。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他们的理论探讨虽然涉及的面很广,但是,由于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探讨的起点是对于“文明戏”衰落的反思和对传统戏剧的改良,而文明戏的衰败与传统戏剧的源远流长又显示了这样的事实:文明戏功能始终就不全,而传统戏剧不仅功能齐全,且有成熟的规则与程式。这种最直观的事实对照,在很大的程度上启示了新文学同仁,使他们很自然地将探讨的重点放在了戏剧的功能上,并以此为中心探讨新戏剧的其它规范。
二、焦点:戏剧的功能
胡适是最早注意到戏剧功能的先驱。1936年,洪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戏剧集·导论》中说:“胡适的教人学习西洋戏剧的方法,写作白话剧,改良中国原有的戏剧,他底目的,是要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他诚然没有明显地把这个目的在他底文字里说出过;但他底重视易卜生这个事实,完全可以看出他的用意了”。胡适之所以要求戏剧发挥它的“作用”,就是因为他看到了戏剧有感化人、教育人的功能。不过,由于胡适谈这一问题时,着眼点主要在新文学的建设方面,因此,他对于戏剧的具体功能就谈得不是那么明确和周详。与之相比,陈大悲就谈得要清楚、直接得多。他认为,戏剧“其感化力格外伟大。种种的善德,如同情心,美感,创造的冲动”,读者“都能于不知不觉之间被戏剧引诱他从发展底路上走”〔1〕。 他还分别从戏剧的社会作用、人生需要等方面勾勒了戏剧的各种功能。他认为从本质上看,戏剧的功能是社会给予戏剧的一种价值判断,戏剧只有在作用于社会、人生时,才可能显示出自己的功能并发挥自己的功能。因此,探讨戏剧的功能,就必须从社会与戏剧的关系着眼,阐述戏剧的一系列准则、范畴。当时探讨戏剧理论的同仁正是基于这一点阐述戏剧的功能的。在探讨戏剧功能的重要性时,新戏剧理论的先驱们是从两个方面来加以探讨的,即戏剧功能的积极、消极作用以及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作为反面的事实是文明戏的衰败和传统戏剧的一些不良影响,作为正面的事实则是西洋的戏剧,而其理论依据则是西方的戏剧理论。文明戏正由于不尊重戏剧的艺术功能,“在表演时,因欲博得观众的拍掌或发笑,往往任意造作,任意发言,什么剧情、身份、性格,甚么情理,一切都不管,所演的戏竟至全无意识,不及儿戏”〔2〕,所以, 很快被人抛弃。而中国旧戏也“差不多全是助长病的状态的……引导社会向堕落退转的路上走”〔3〕,所以,也不能不受到批判。与此相反, 西方近现代戏剧,则不仅注意了戏剧的艺术功能,而且使戏剧发挥了感动人、净化人的思想情感的积极作用。田汉举例说“《沉钟》(德国著名剧作家霍普特曼的剧本)本是描写一种艺术生活与现实生活之冲突的悲剧,然而我看到末场……不觉得有甚么痛苦,却和Heinriich一样, 我们的灵魂化入令人神往的境地去了”〔4〕。 通过对中外戏剧不同性质功能的对比,新戏剧理论的先驱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旧戏不能不推翻,新戏不能不创造”〔5〕。陈大悲认为:“人们要希望那根深蒂固、诲淫诲盗的恶戏剧早早消灭,就得脚踏实地、抖擞着互助的精神,来创造一种有益于人类的真的新剧”〔6〕。 胡适认为:“采用西洋最近几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7〕。正是因为看到了戏剧对于社会的巨大作用, 所以,当民众戏剧社在1921年成立时,就明确宣布:“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地过去”,“戏剧,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8〕,公开表明了要发挥戏剧的积极功能为社会服务的意图。
如何发挥戏剧的积极功能呢?新戏剧理论的倡导者认为,必须依据一定的艺术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以情感为中介,以娱乐、趣味为形式,以思想内容为核心,在“三位一体”中发挥其作用于社会的积极功能。之所以要以情感为中介,是因为“观众富情感”〔9〕, 戏剧只有通过情感的媒介,“使观众看时受重大的刺激,欣然愉快,过后留有深刻的印象,幽然深思,于不知不觉中,增加了智慧,美化了情感,直接造成观众伟大的人格,间接便改善了人生”〔10〕;同样,戏剧固然是应教育人的,但教育人却不能以“教训”为形式,“若是一味对着他们宣讲道理,谁肯耐着性子听你的?”〔11〕而只能“利用娱乐的机会,以艺术的功能来发展再生的教化”〔12〕。总之,新的戏剧应该“拿极浅近的新思想,混合入极有趣味的情节里面,编成功教大家要看的剧本”〔13〕。
在对新戏剧的功能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中,汪仲贤还根据自己戏剧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戏剧的“提高”与“普及”的问题。他认为这两个问题如何处理,直接关系到戏剧能否发挥积极功能的问题。所谓“提高”,在他看来,主要是针对修养好的知识者而言的,他们是“眼界高的看客”〔14〕,而“普及”,则主要针对广大的民众而言,这些看客,“他们花了几毛钱来看戏”,主要不是为了受什么教育,而是为了满足“趣味”。一出戏,是以满足那些眼界高的看客为主呢,还是以迎合要求普及的看客为主呢?汪仲贤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以后的方针——我们演剧不能绝对地去迎合社会心理,也不能绝对地去求知识阶级看了适意”〔15〕。为了使新话剧能站住脚,宋春舫则认为,剧本的编写应当“不独迎合社会少数人心理已也,而尤当迎合多数人之心理”〔16〕,并认为“问题派剧本之失败,即在当时提倡者之昧于此旨耳”〔17〕,强调了戏剧“普及”的一面。但是,汪仲贤、宋春舫虽然看到了社会心理对戏剧的制约作用,特别是看到了在文化普遍落后的中国,民众心理对戏剧的制约作用,从而倾向于“普及”一面,然而,他们却忽视了戏剧对社会的反作用,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戏剧不仅受制于社会,也能通过自己的功能——发挥艺术魅力,来引导社会心理的变化,改变社会习惯。因此,他们只看到“剧本为被动的而非主动”〔18〕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剧本的上演能变被动为主动的一面。不过,欧阳予倩、傅斯年等,却在这方面弥补了前两位的不足。他们不仅看到了戏剧必然受制于社会心理的规律,而且,他们认为正是为了使这种制约变成推动戏剧发展的动力,才要求戏剧的创造必须针对这种制约——社会心理进行构思,通过创造的戏剧作用于人、唤起人的情感,从而推动社会心理的变革。傅斯年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中说:“有这样社会的心理,就有这样戏剧的思想,更促成这样社会的心理。”他看到了社会与心理的双向作用。欧阳予倩则直接指出,戏剧“必然代表一种社会,或发挥一种思想,以解决人生之难问题,转移误谬之思潮”〔19〕,他正是看到了戏剧的反作用功能而提出了创造戏剧必须注意使戏剧具有这种功能并发挥它。
三、落点:戏剧的本质与规律
我在前面说过,这一时期的戏剧理论探讨,是在“反省”文明戏、旧戏,认同西方戏剧及理论,重构新的戏剧理论这“三向度”上同时展开的,对于戏剧规律的探讨自然也是如此。傅斯年在谈新戏剧应具有怎样的艺术素质时,往往将“中国旧戏”的弊端作为反参照系,他指斥旧戏的弊端,正是要求新戏剧克服这些弊端,同时,他指出旧戏剧缺乏什么,又正是要求新戏剧具备什么。如,他认为中国旧戏缺乏哲学意识,“所以,仅可当得玩弄之具,不配第一流文学”〔20〕,而新戏剧呢?他认为:“我很盼望以后做新戏的人,在文学的技术而外,有个哲学的见解,来做个头脑”〔21〕。胡适在介绍西洋戏剧的发展时,也无处不指陈中国旧戏发展中的弊端,他认为“西洋的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戏剧便是只有局部自由的结果”〔22〕,所以中国戏剧就“不能完全扫除一切枷锁”〔23〕,从而形成了许多不尽如意之处。他举元杂剧为例,认为“杂剧的限制太严,故除一二大家之外,多止能铺叙事实;所写生活与人情,往往缺乏细腻体会的工夫”〔24〕。由此他呼吁:“中国戏剧的将来,全靠有人能知道文学进化的趋势,能用人力鼓吹,帮助中国戏剧早日脱离一切阻碍进化的恶习惯,使它渐渐自然,渐渐达到完全发达的地位”〔25〕。于此,他又指出新的中国戏剧的发展应“采用西洋最近几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26〕,从而实现中国戏剧的真正改革,创造新的戏剧。
这一时期,对于新戏剧规律的探讨,主要涉及到两大内容,一个是戏剧文学的规律,一个则是戏剧作为表演艺术的规律。在戏剧文学规律的探讨方面,贡献较多的是傅斯年、欧阳予倩、宋春舫。宋春舫认为“吾以为戏剧是艺术”〔27〕,他以大量外国戏剧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论述了戏剧的规律。欧阳予倩指出,戏剧首先应有剧本,“剧本文学为中国从来所无,故需为根本的创设。其事宜多翻译外国剧本以为模范,然后试行仿制。不必故为艰深;贵能以浅显文字,发挥优美之思想。无论其为歌曲,为科白,均以白话,省去骈俪之句为宜。盖求人之易于领解,为效速也。惟格式作法,必须认定。暇当专论之。中国旧戏,非不可存,惟恶毒习惯太多,非汰洗净尽不可”〔28〕。他在批判旧戏,认同西方戏剧中阐述了重构的新戏剧的美学特征。而傅斯年则更为具体地对戏剧文学作了六点规范:一、剧本的题材应以现代生活为主;二、情节结构应反“大团圆”;三、剧本事实以日常生活为宜;四、剧本人物以平常人物为主;五、要含蓄;六、尊重戏剧本身的艺术性〔29〕。
在五四时期的戏剧理论中,探讨戏剧作为表演艺术的规律,最初主要以介绍外国的理论为主。《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上登载的宋春舫的《戈登格雷的傀儡剧场》一文,是最早的代表作。在这篇文章里,宋春舫系统地介绍了戈登·格雷的两点主张,第一,戈登·格雷认为“戏剧是一种纯粹的科学,……演戏是一种科学,曲本的构造也是一种科学,至于光线、设备”等等,更是科学。第二,介绍了戈登·格雷关于剧场布置、表演等的具体主张,涉及到了表演艺术的许多具体技术。然而,宋春舫却没能在介绍中勾画出从剧本到演出的戏剧这之间的转化规律,这不是他的过错,当时的许多人也没有完成这一课题。这是因为当时的客观与主观条件还不成熟,新剧本的创作在当时还极度缺乏,而理论探讨者也大多没有表演戏剧的实践经验,所以,对于戏剧作为表演艺术的规律的探讨就不可能深入下去。然而,到了1921年,当《戏剧》杂志创刊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文学界走过了批判、“破坏”旧文学的阶段,已明确地发出了“建设”的号召,而在戏剧领域,民众戏剧社“更大的功绩,是在他们的建设理论方面”〔30〕。其中汪仲贤率先提出了“舞台上的戏剧”〔31〕的主张,从而使对于戏剧艺术规律的探讨,由纯文学性规律向着表演艺术的规律作重心转移。汪仲贤指出:“现在想提倡纯粹新的人……绝对没有人提到过某剧的表演方法是怎样的。换言之,只有纸面上的戏剧的理论,而无舞台上的戏剧的实际”〔32〕,因此,要使戏剧真正发挥它的功能,现在必须提倡“舞台上的戏剧”。随后,这方面的探讨文章多了起来。王统照提出了写作剧本“宜注意演作的表情”〔33〕的主张。沈冰血写了《演剧初程》、《假须的研究》等等,对戏剧的表演艺术规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在这里应特别提到的人物是洪深。洪深1922年从美国回国后,将西方的“表演”与“导演”体系引进了正探索着表演艺术规律的中国文坛,使中国现代戏剧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仅具有从事演剧的具体实践经验,而且有良好的理论修养,因此,他既探讨了戏剧文学的规律,又论述了戏剧作为表演艺术的规律。关于戏剧的文学规律,他认为应以“真”、“善”、“美”为根本追求,所谓“真”,即“是否能令观众对台上之事物不起疑问”;“美”,即“是否能兴起观众之美感”;“善”,即“是否能感化改善观众之性情”〔34〕。对于戏剧作为表演艺术的规律,他将戏剧与一般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进行了对比,指出两者有六个方面的不同,其中最为根本的不同在于,“剧本乃演在台上给人看的,说部乃印在纸上给人读的”〔35〕。在洪深阐说戏剧文学与戏剧的表演艺术规律时,已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中后期,可以说,洪深的理论是对这一时期戏剧理论探讨的一个总结,它标志着新文学的戏剧战线,已形成了独立的、较为系统的戏剧表演艺术和戏剧创作理论,也为以后戏剧创作与理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收稿日期:1995-07-06.
注释:
〔1〕〔2〕〔3〕〔8〕〔9〕〔10〕〔11〕〔12〕〔13〕〔14〕〔15〕〔16〕〔17〕〔18〕〔27〕〔30〕〔33〕〔34〕〔35〕转引自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戏剧集·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影印版。
〔4〕田汉:《致郭沫若的信》,载《田汉文集》第14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5〕〔20〕〔21〕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 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6〕陈大悲:《演剧人的责任是什么》, 载《陈大悲研究资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
〔7〕〔22〕〔23〕〔24〕〔25〕〔26〕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19〕〔28〕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29〕参见傅斯年:《论编制剧本》,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31〕〔32〕汪仲贤:《随便谈》,载《戏剧》1921年第7号。
